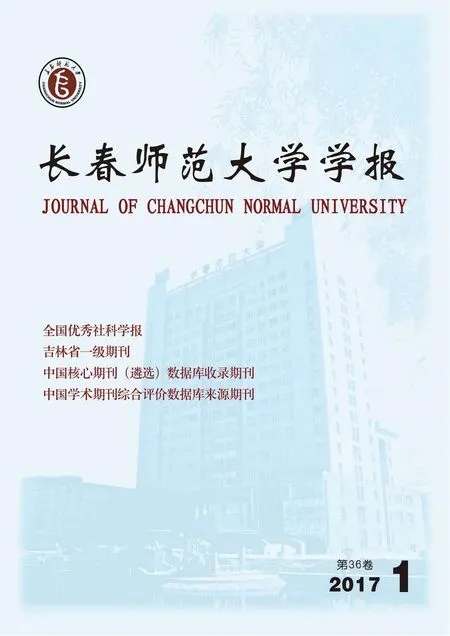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与戏曲传播
张青飞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721013)
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与戏曲传播
张青飞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721013)
今知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有46种。从文体看,有元杂剧、宋元戏文与明传奇三类;从版本形态看,有戏曲选本与单刻本。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在插图位置、形制、内容与功能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域的插图本具有鲜明的特色。作为明代戏曲刊刻的重镇,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促进了下层读者的戏曲阅读;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呈现了地域文化视野中插图史、戏曲史与出版史的交织。
插图本;建阳:戏曲;明代;出版
明代印刷出版业极为发达,乃中国古籍插图本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前人有“无书不图”之誉。福建建阳自宋迄明乃全国刻书中心,尤以明代为其黄金时期,刊刻了大量小说戏曲等所谓通俗读物,且多为插图本,其中小说插图本120种、戏曲插图本46种,占今所知明代福建刻书总数的35%[1]。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调查整理的基础上,就明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作一考述,主要探讨明刊戏曲插图本的概况与特征,从而揭示作为版本形态的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所具有的戏曲史意义。
一、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概貌
从文体看,现存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有元杂剧、宋元戏文与明传奇三类;从版本形态看,有戏曲选本与单刻本。
(一)戏曲文体
中国古代戏曲自宋元有固定剧本以来,即有杂剧与南戏两种文体类型。入明以后,宋元戏文一变而为传奇,中国戏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类型。
1.杂剧
据统计,有明一代建阳所刊之杂剧插图本仅《西厢记》1种,共有9种版本,分别为:万历二十年(1592)忠正堂熊龙峰刻《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间书林刘龙田乔山堂刊《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间三槐堂刊《重校北西厢记》,明后期潭邑书林岁寒友刻《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万历四十六年(1618)孟冬序刻明书林萧腾鸿师俭堂梓《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万历间书林萧腾鸿刻《鼎镌西厢记》(递修重印本),万历间书林游敬泉刻《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万历间潭阳刘应袭刻《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2],明后期师俭堂刻《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其中刘龙田刊本版式、内容与熊龙峰刊本相同,只不过字体、插图有细微差别,实乃刘氏重新雕版刊印。
2.南戏
南戏与传奇之界限,众说纷纭。此处以作品产生朝代来划分,宋元为南戏,入明以后为传奇[3]。有插图本的有2个剧目:《琵琶记》和《破窑记》。其中《琵琶记》插图本有4种: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孟东序刻《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明书林萧腾鸿刻《鼎镌琵琶记》,明书林余少江刻《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4],万历元年(1573)闽建书林种德堂熊成冶刻本《重订元本评林点板琵琶记》[5];《破窑记》1种:明书林陈含初、詹林我刻本《李九我先生批评破窑记》。
3.传奇
据统计,传奇插图本共有19种,分别为:嘉靖丙寅(1566)余氏新安堂重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南阳堂叶文桥刻万历辛巳(1581)朱氏与耕堂印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万历长庚馆刊《新编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明书林杨居寀刻本《红梨花记》,明万历间师俭堂刻本《西楼记传奇》,明万历间师俭堂刻本《麒麟罽》,明万历间师俭堂刻本《鹦鹉洲》,明书林游敬泉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明书林朱仁斋刻本《新刻浙江新编出像题评范雎绨袍记》,天启间建阳潭阳黄氏存诚堂刊刻《鼎镌郑道圭先生评点红杏记》,明书林萧腾鸿刻《鼎镌幽闺记》《鼎镌玉簪记》《鼎镌红拂记》《鼎镌绣襦记》,明万历萧腾鸿师俭堂刻《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玉簪记》,明师俭堂刻本《异梦记》,明末师俭堂刻本《西楼记传奇》,明师俭堂刻本《明珠记》,明末师俭堂刻本《丹桂记》。
(二)版本形态
从版本形态看,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有单刻本与选集本。
1.单刻本
单刻本,指一部单独刊刻出版流通的戏曲文本。杂剧、南戏与明传奇皆有单刻插图本。相较而言,单刻本部头小,制作成本低,制作快捷,能及时满足读者需求,在当时戏曲书籍的流通中占主要地位。
从现存元明杂剧刊刻情况看,杂剧单刻本较少,目前仅知有《西厢记》1种。《西厢记》五本二十一折,从容量看,其不同于杂剧传统的四折一楔子体例,因此在刊刻过程中可以单刻插图本形态流通。
南戏篇幅较长,其插图本皆以单刻本形态流通。目前所知2种南戏,其插图注重对故事情节与曲词意境的呈现,往往选择全剧出中的关键情节配以插图,一来吸引读者,二来可提示阅读。
传奇,作为一种在南戏基础上发展壮大的新的戏曲样式,其插图本形态与南戏基本无区别。在明代,传奇插图本多以单刻本形态流通,其插图既有故事图、曲意图,又有合二者于一体的插图,明刊戏曲插图的精华及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插图本上。
2.选集
戏曲选集,是编选者在浩如烟海的戏曲作品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汇为一编以方便阅读或查阅。明代戏曲选本数量众多,据统计其数量占古代戏曲选本总数的75%[6]。在选本中,很大一部分为插图本。
建阳刊戏曲选集插图本知有13种,分别为: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1605-1608)之间爱日堂蔡正河刊《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7],万历间闽建书林拱唐金魁刻本《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万历间闽建书林熊稔寰绣梓《新镌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万历三十九年(1611)书林敦睦堂张三怀刻《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万历间潭水燕石居主人刊梓《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万历三十八年(1610)孟秋月书林刘次泉原刊书林廷礼补板合刊《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万历三十四年或三十五年福建书林叶志元刻《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序署万历二十七年(1599)书林余绍崖绣梓《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万历二十八年(1600)书林三槐堂王会云绣梓《新锲梨园摘锦乐府菁华》,万历间书林刘龄甫刻《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万历间刻《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明末书林四知馆刊《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可见明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以选集本为多。
二、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特征
对戏曲插图本来说,戏曲插图形态之研究乃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对戏曲插图形态进行深入考察,才称得上是细部研究,才能对戏曲插图及插图本有深入认识。因此,在对现存明建阳刊戏曲插图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探究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在插图位置、形制、内容与功能等方面的特征。
(一)插图位置
在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中,插图位置分四种:上图下文、图嵌文中、插入卷中与置于卷首。
1.上图下文
上图下文即书页上半部为插图,下半部为正文。每一个页面都有图,一般是上面三分之一刻印图像,下面三分之二刻印文字。这一形式自宋元以来就存在,有着久远的传统[8]。对读者来说,在看到上面插图之时,就可以在下面找到相关的文字;在读了下面的文字后,可以对应上面的图画。图文互解,阅读极为方便。在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中,采用上图下文方式的目前所知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风月(全家)锦囊》,万历九年(1581)建阳朱氏与耕堂刊《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此外,万历三十八年(1610)孟秋月书林刘次泉原刊书林廷礼补板合刊《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版分三栏,图插于上栏或下栏,中栏无图,其实是上图下文的变形而已。
2.图嵌文中
图嵌文中指插图四周被文字环绕,犹如图嵌于文中。此一形式与上图下文较为相似,只是插图的上端一般有文字。目前所知此类插图本有:嘉靖四十五年(1566)余氏新安堂刊《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万历前期刊《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天下春》,万历二十七年(1599)书林余绍崖刊《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万历二十八年(1600)书林三槐堂王会云绣梓《新锲梨园摘锦乐府菁华》,万历间书林刘龄甫刊《梨园会选古今传奇滚调新词乐府万象新》等。
这些插图本以选本居多,成为建阳戏曲刊本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9]。
3.插于卷中
插于卷中指插图插于正文之中。就戏曲插图本来看,插图往往会选择在全剧的某些重要出(折),绘制插图插入其中。在明刊戏曲插图本中,这一类插图方式在万历以后较为常见。从数量上来说,多介于10~30幅之间,极少有每出皆有插图的。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至少有一半插图本的插图皆插于卷中。既有戏曲选本,如《八能奏锦》《大明春》《南北新调》《摘锦奇音》《徽池雅调》《词林一枝》;又有单刻本,如《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乔山堂)《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忠正堂)《破窑记》《红梨花记》《鼎镌幽闺记》《鼎镌西厢记》《鼎镌绣襦记》《鼎镌琵琶记》《鼎镌玉簪记》《鼎镌红拂记》《西楼记》《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重校北西厢记》。
4.置于卷首
置于卷首指插图放置于整部书的卷首,有时置于全书之卷首,有时置于上下卷之卷首。卷首插图乃一种较为古老的插图方式[10],在明刊戏曲插图本中,这一方式却不是最早出现的,大约出现于万历后期。今知有万历长庚馆刊《新编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明书林余少江刻《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4]、万历间潭阳刘应袭刻《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2]三种。
(二)插图形制
插图形制指插图的外形呈现,在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中,插图形制有4种。
1.上图下文
上图下文是中国古籍插图最传统的形制。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千佛名经》,上绘佛像,下绘佛名,实开上图下文形制之先河[11]。就明刊戏曲插图本来看,一般图占版面上部三分之一,下为文字。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共有8种采用此形制。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风月(全家)锦囊》,上图下文,插图占版面四分之一。由于插图面积狭小,其对人物场景的刻画较为简略,插图艺术性不高。再如万历九年(1581)建阳朱氏与耕堂刊《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上图下文,共插图175幅。从插图位置看,不论是上图下文还是图嵌文中,这种图式所占面积相对较小,无论人物还是背景皆为简单的示意,难以进行细致描摹,因而其艺术性较低。
2.单面方式
单面方式,指插图占整版半叶。单面方式形制的采用,相对上图下文图式,图像的面积增为占满单面,因此更易于对人物场景进行细致描绘。单面方式形制的出现,为戏曲插图艺术水准的提高提供了可能性。随着戏曲插图本的演进,晚明时许多戏曲插图本都采用此一形制。就建阳明刊戏曲插图本而言,今知有9种采用此形制。如万历间书林刘龙田乔山堂刊《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相较于上图下文式,插图幅面扩大,通过背景的铺陈营造来展现剧情与人物,丰富了插图的内容,大大提升了观赏性。
3.双面连式
双面连式,指插图占整个版面。相对于单面方式来说,插图面积扩大了一倍,可容纳更多内容。在明刊戏曲插图本中,这是插图的最大表现空间。读者在阅读时,视野会更开阔,一幅插图要移动视角才可以观尽。今知有14种采用此形制。如杨居寀刊《红梨花记》共插图10幅,工丽细致、婉约秀隽。
4.月光式
月光式,因其形制内圆外方如天上满月而得名。其如镜取形,在中国传统国画中经常出现,很受文人青睐。此一形制本身就很雅致,打破了传统的长方形插图形制,别具一格,给人一种新鲜感。这一插图样式最早出现于晚明的苏州、杭州,而后流行各地。在晚明戏曲插图本中,崇祯四年(1631)序刻延阁主人订正的《北西厢记》较早采用了这一形制。今所知大约有十余种,其雅致的形式更适合文化素养较高的读者把玩。在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中,仅知明末书林四知馆刊《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较为独特,卷首目录采用上文下图方式,下图为月光型。
(三)插图内容
明初至隆庆年间,戏曲插图内容为连环故事图,其数量相对较多。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风月(全家)锦囊》,上图下文,共有插图371幅。读者在阅读时只需翻看幅幅插图,便可以理解剧情。
这一时期戏曲插图有着明显的舞台演出痕迹。刊刻于嘉靖丙寅(1566)的南戏插图本《重刊荔镜记》,采用三节版,其中上层为诗词北曲,中层为插图,下层为正文,计有209幅插图;左右为用以释图的七字句为主之诗句,概述插图主要内容。插图外呈类似舞台外观之长方形,图中人物之背景极简,身姿呈舞台演出状。读者边阅读剧本文字,边观看中栏插图,便如同正面对舞台。在早期的戏曲插图本中,制作者极力使插图呈现戏曲作为场上艺术的表演之特性,力图追求“唱与图合”[12]。
戏曲插图本之数量至万历时期大为增加,在内容上故事图与演出图皆有,但出现了新变化。如刘龙田刊《重刻原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采用单面方式插图,所刻人物在画面中占较小比例,整个画面除注重人物与剧情呈现外,还注重背景描绘与意境呈现。尤其是万历间师俭堂刊刻的一系列戏曲插图本,如《鼎镌西厢记》,共有双面连式插图10幅,分别插于其中。首幅所画为张生赴京赶考途中所看到的山水风景,并题有诗句。整个画面不再以故事情节为呈现内容,而是营造出了山水意境之美。此时建安戏曲插图也一改以往的简单朴实、古朴稚拙之风,渐趋工丽纤细。
至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戏曲插图在呈现情节之余,更注重曲词之赏析,往往择取各异的书法字体题写曲文且钤印,从而使插图兼备叙事与抒情之双重特征;甚至出现了几乎与剧本正文无甚关联的副图,纯为玩赏而已。但建阳所刊戏曲插图中我们没有发现此种情形。
整体而言,建阳所刊戏曲插图以呈现故事情节为主,虽有部分插图呈现曲意,但并不占主流。
(四)插图功能
明刊戏曲插图的功能有促销、导读、装饰与批评四方面。其最基本之功能为导读,具有直观性之插图可帮助低层次文化水准的读者理解文意与欣赏剧,在早期明刊戏曲插图本中此点表现最明显。此时插图不但数量较多,且密度高,其中人物形象突出而背景极简,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书林詹氏进贤堂重刊《风月(全家)锦囊》,其插图乃主要为导读而设,可以为读者阅读提供文字之外的补充与说明,帮助其理解。
总而言之,明刊戏曲插图之装饰功能愈益凸显,而导读与促销功能愈来愈弱,插图之独立性增强。但就建阳戏曲插图本而言,其导读功能一直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与建阳书贾的营销定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建阳所刊戏曲插图也出现了诸如师俭堂所刊的带有意境且接近山水小品的插图,但这只是建阳书贾受到晚明戏曲插图雅化之流风所及,其插图仍以呈现故事情节、发挥导读功能为主导。
三、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之戏曲史意义
作为明代戏曲刊刻的重镇,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面貌独特,这种独特性具有一定的戏曲史意义。
1.大量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促进了下层读者的戏曲阅读
就读者而言,在戏曲插图本中,作为图像的插图具有直观性、可感性与形象性,能够发挥辅助阅读的功能,可以对故事情节加以形象的说明从而引导读者阅读。正如崇祯间《想当然·成书杂记》所云:“是本原无图像,欲从无形色处想出作者本意,固是超乘,但雅俗不齐,具凡各境,未免有展卷之叹。”[13]其制作插图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想出作者本意”,免却“展卷之叹”。
明刊戏曲插图本主要是用来阅读的,其对戏曲史的意义体现在案头阅读。不同阶层的读者群具有不同的知识水平、欣赏能力与审美趣味,出版者在面对不同的潜在读者群时会在插图本的面貌上有不同呈现。明建阳所刊戏曲插图之插图位置多插于书中,与文字保持密切关系,插图形制以上图下文为主,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插图本的读者群面对的多是文化素养不高的读者,这是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的独特之处。整体而言,明刊戏曲插图本的读者群有一个转变:前期以文化素养不高的读者为主,后期以文人读者群为主。但就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而言,以下层读者群为主,这也是建阳书贾在图书市场中的营销策略之一。
2.插图本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
在发生学意义上而言,文先出,插图后出,插图创作者在绘制插图时,其实是在进行二度创作。在作为文本的剧本内容的制约下,画家依据自身的独特理解与图像语汇来阐发剧本的内在意蕴。
在戏曲插图本中,戏曲插图是画家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理解水平来绘制的,每幅插图是对某部分文字的集约化概述,不同的画面构思透漏出其对剧情与主旨的理解。当所有插图联合起来构成图像序列时,插图对文本的再现就具有了独立的意义,插图内部往往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因此,当插图本进入读者视域时,这些理解最终会通过物质形态的书籍,传递到当时读者的阅读活动之中,其对剧本的阅读已是二次接受了。因此,由剧本到插图本到读者,由于插图本的介入,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带来新的接受。
3.呈现了地域文化视野中插图史、戏曲史与出版史的交织
明刊戏曲插图本是多重历史问题的交汇点与观察点,明建阳刊戏曲插图本便体现了地域文化视野中插图史、戏曲史与出版史的交织。就其所刊剧目选择看,以《西厢记》与《琵琶记》为主,前者因对爱情自由的书写,后者因对伦理道德的倡导,成为明代戏曲传播中的经典剧目,体现了书坊主在剧目选择上注重经典的倾向性;从版本形态看,以选本刊刻为主。容量大、精品多的选本插图本成为建阳刊戏曲插图本最为显著的特色,体现了明建阳地区戏曲阅读欣赏的独特性。
建阳所刊戏曲插图在明代戏曲出版市场上有其独特定位。万历间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曾云:“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14]其认为建阳刻书“徒为射利”,以追求数量为主,不计质量,透过此评价可看出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与建阳书坊营销策略间之关系:其刊刻追求数量,质量虽粗陋,流传范围却广泛,以下层读者群为主。尤其在晚明,戏曲插图本刊刻多以精美著称一时,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自有其独特的戏曲传播价值。
四、结语
作为明代戏曲刊刻的重镇,建阳所刊戏曲插图本在插图位置、形制、内容与功能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地域的插图本具有鲜明的特色,促进了下层读者的戏曲阅读,为剧本提供了新的阐释,呈现了地域文化视野中插图史、戏曲史与出版史的交织,为明代戏曲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34.
[2]郭立暄.论刘应袭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J].图书馆杂志,2006(5):74-78.
[3]俞为民.南戏流变考述—兼谈南戏与传奇的界限[J].艺术百家,2002(1):52.
[4]张棣华.善本剧曲经眼录[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30-31.
[5]黄仕忠.琵琶记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205-208.
[6]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
[7]郭英德,王丽娟.《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编纂年代考[J].文艺研究,2006(8):55.
[8]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9-10.
[9]涂秀虹.上图下文:建阳刊小说的标志性版式[J].福建论坛,2009(12):79.
[10]薛冰.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插图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4-16.
[11]张玉凤.论敦煌文献叙事图文结合之形式与功能[A].张玉凤敦煌俗文学与俗文化研究[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43.
[12]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13]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1190.
[14]谢肇淛.五杂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66.
2016-07-1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10&ZD105)。
张青飞(1980- ),男,讲师,博士,从事戏剧戏曲学研究。
G239.2
A
2095-7602(2017)01-01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