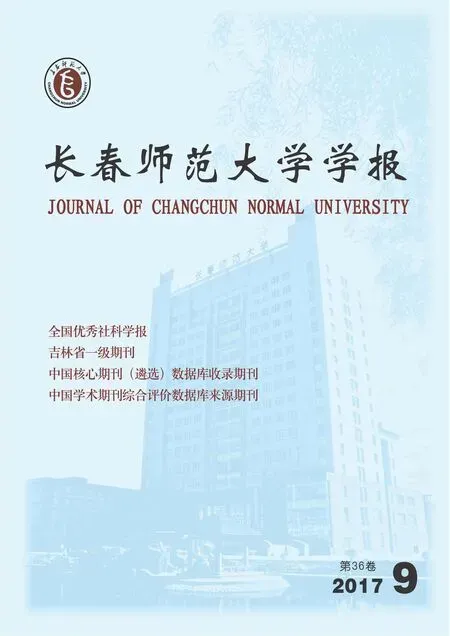论诺奖文学作品中语言隐喻手法的运用——以艾略特诗歌为例
乔莉萍,陈荔弦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论诺奖文学作品中语言隐喻手法的运用——以艾略特诗歌为例
乔莉萍,陈荔弦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艾略特是20世纪西方“诗歌革命”的发动者,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古典语言的广泛运用与历史典故的恰当再现,语言使它所谈及的一切都化为隐喻。隐喻之中包藏着诗、真理和美,其表现手法在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是普遍的。在艾略特之前,有意大利的诗人、文学家卡尔杜齐,之后有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从某种程度上说,隐喻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大脑的思维方式。
隐喻;语言;诗歌创作;表现手法
一、艾略特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托·斯·艾略特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于1906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受业于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白璧德的反浪漫主义理论教导并直接影响了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同时,艾略特对哲学非常感兴趣。1910年,艾略特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同年赴色黎大学研究亨利·柏格森的哲学,一年后回到哈佛大学任教。1915年,艾略特在英国结婚,从事教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担任银行职员,在银行供职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兼任伦敦文学杂志《个人主义者》的助理编辑,并替几家杂志撰写书评,闲暇之余开始进行诗歌创作。他的第一部诗集《普鲁夫洛克和其它观感》发表于1917年。当时他的诗作受象征主义诗人尤其是于勒·拉法格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还研究“玄学派彦诗人和雅各宾时期英国戏剧。由于健康原因,他向银行请假三个月并先后到伦敦附近海滨和瑞士洛桑疗养。利用病休机会,他将《荒原》定稿并准备出版。1922年1月,他从瑞士回英国,途经巴黎,征求埃兹拉·庞德对《荒原》的意见。同年稍后,艾略特在伦敦创办右翼文学杂志《标准》。该杂志持续出版至1939年,《荒原》就刊载于该杂志的第一期。1925年,艾略特成为费伯出版社的一名理事。1930年出版宗教诗集《圣灰星期三》,1935年发表第一出诗剧《大教堂中的谋杀》,1936年发表忏悔祈祷宗教诗歌《四部四重奏》的第一部《火灾后的诺顿庄园》,1939年发表第二出诗剧《家人团聚》。《四部四重奏》的另外三部《东科克尔村庄》《打捞出来的干岩石》和《小吉丁村社》,写于1940-1942年间。《四部四重奏》的合订本于1943年在纽约出版。1948年,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外他还写了三出喜剧《鸡尾酒会》(1950)、《亲信职员》(1954)和《政界元老》(1959)。
艾略特是20世纪西方“诗歌革命”的发动者。从艾略特开始,20世纪的西方诗歌开始摆脱并背离了以往在西方诗歌创作中占主流的浪漫主义文学手法和维多利亚诗风,在诗歌技巧和题材上实现了变革,充分表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精神面貌。为了表现新时代的精神和现代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感情,艾略特认为必须创造新的诗歌形式和新的语言结构。在诗歌技巧方面,艾略特格外重视用生动具体的感官印象语言代替以往那些空泛的拟人化抽象概念,用英语习语和口语等富有自然节奏和简练的语言代替陈旧、呆板、没有生命力的所谓诗歌语言,在诗歌内容方面也要摆脱旧有的模式与局限。艾略特的早期作品《荒原》与《稻草人》等在这些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和尝试,力图展示现代工业社会给人们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种种伤害,譬如快乐的丧失与感情枯竭、精神空虚与对生活厌倦、沉湎物欲与对人类前途幻灭之感,透过现代化的虚幻反映城市文明的拜物异化和广大社会下层人士的悲惨与无奈。后期作品如《圣灰星期三》《四部四重奏》等主要属于宗教诗歌,反映了艾略特皈依英国国教的心理过程——灵魂在追求新生中交替感受和经历的绝望、怀疑、希望和欢乐阶段,感受“人在时间一空间世界中的地位以及人追求超越时空限制的愿望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1]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略特是20世纪英语国家最杰出的诗人和批评家。他不仅通过《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等诗篇,确立了自己在英美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其批评论著,尤其是收人《圣林集》和《论文选》中的早期论文对20世纪英美文论的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是通过四个步骤完成的:第一步,通过诗歌的非个性化理论,向浪漫主义的表现理论发起严峻挑战,批判西方文学传统对文学发展的巨大制约作用。第二步,通过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和17世纪的玄学派诗歌,贬低弥尔顿和浪漫主义诗人,从而改写英国长期以来的文学史观。第三步,通过除旧布新,提出“客观对应物”理论,明确表达艺术中的感情如何客观化的基本理论,目的是改变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风,建构一套与时俱进、充满生机活力的诗歌理论。第四步,将批评的重心从诗人转向诗歌文本。[2]214在诗歌创作中,艾略特曾经以“催化剂”来形象地类比具体的诗歌创作过程。艾略特描述道,当把一根白金丝放入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容器时,两种气体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生产新的物质——硫酸,但白金丝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白金丝还是白金丝,依然保持着中性特质,新的混合物中也不含一点白金成分。艾略特以此说明诗人的头脑就是那少量的白金丝,它可以部分或全部作用于诗人本人的经验;但艺术家越完美,在他身上作为感受的人与作为创作的头脑就越彼此分离,头脑也就越能够消化和点化原是它材料的那些激情。
二、艾略特诗歌语言隐喻的运用
诗就是语言的仪式,诗就是一座由语言构筑的神殿。人在那儿通过自身所创造的神秘,表达对比自己更神圣的存在的虔敬与祈祷,人通过自身所创造的美向比自己更完美的事物双手合十,艾略特对此很有感触。他说:“伟大的诗歌应该既是艺术,又是娱乐,在像雅典人那样人数既多,又有文化修养的观众当中,伟大的诗歌可能既是艺术,又是娱乐。”[1]129隐喻的功能就是表达人们的祝福与感激,而祝福与感激是通过语音来完成的。语言赋予了万物得以存在的符号方式,把具体的物质现象概括抽象为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具有象征性的意蕴表达,把不同世界存在的不同经验转化为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对等并存关系。正因为如此,艾略特在谈到隐喻的本质时明确指出,隐喻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大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提高到某一高度就能产生大诗人、圣人和神秘主义者”。虽然诗人也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拯救现代文明所产生的思想与心灵上的荒原,但他还是要通过拯救语言来拯救现代工业文明所戕杀的精神生机,通过诗歌来拯救精神灵魂的荒原。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诗能够维护甚至恢复语言的美;它能够并且也应该协助语言的发展,使语言在现代生活更为复杂的条件下或者为了现代生活不断变化的目的保持精细和准确,就像是在过去或者一个更简单的时代一样。”[3]245
语言如同万事万物一样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语言所要表达的语义也是如此变化与富有弹性,正是这种动态性与模糊性才赋予了语言深刻的语义和隐喻,让不同时代的人对统一语言的表达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从而展示其永恒的价值。可以说,语言的语用效果和读者的阐释达到了“统一性”互动,而不是语言本身所表现的直白。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荒原》中“火的说教”部分是具有代表性的。《荒原》如此说道:
在莱芒湖畔,我坐下来饮泣。可爱的泰晤士,轻轻地流,直至我唱完我的歌。
但从我背后的冷风里,我听见白骨与白骨相碰的声音,还有一阵冷笑传过耳畔。
一只老鼠拖着粘滑的肚皮,轻轻地传过草地。
……
我一次又一次听见背后的喇叭和汽车马达的声响,它将在春天里,把薛维尼送到博尔特夫人那里。
……
我,提瑞西斯,虽是一个瞎眼的两性人,却能在暮色中看见人们纷纷往家里走去。[4]239
艾略特不愧为20世纪西方“诗歌革命”的发动者,在他的诗歌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古典语言的广泛运用与历史典故的恰当再现,譬如罗马神话中月神兼狩猎女神狄安娜就把看到她裸浴的猎手阿格坦恩变成了一只公鹿并被自己的猎狗撕成碎片。典故在这里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运用,古典语言和典故变成了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也要看到,神话传说毕竟是远离现代社会的,这决定了现代诗歌创作并不是为了从事神话的写作而写作。现代诗歌中“神话写作”本身显然是一种隐喻手法的运用,目的是要通过时空穿越来加深对现在和人性的理解。于是,语言与典故变成艾略特诗歌中沟通灵魂与上帝、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媒介。艾略特将典籍中的引语和古语以及历史中的典故等诸多成分汇入他的诗中,以此来表达生命循环中的种种不谐和,从而使语言本身转变为生命循环中诸多矛盾的隐喻体。
艾略特推崇一种真正被人们使用的语言,这暗示着他的一种感觉,即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是极端隐喻化的。这导致了单纯而不矫揉造作的表达,以及用一种与思想的重要性相适应的语言来表现的诗歌意念。“许多诗人在此时或彼时都曾感觉到确定的诗歌用语的不足,而且,由于个人原因或者更广泛的文化原因,他们都迫切需要创造新的手段来利用语言资源。”艾略特的前期诗歌如《普鲁弗洛克》《荒原》《小老头》《空心人》等表达的正是这种分崩离析的、种种不谐和的体验与感受。他追溯到玄学派诗人、但丁、远古神话不是为了赞美和回归过去,而是要为分崩离析的现代社会找到重新确立传统与秩序的坦途。然而让人无可奈何的是,即便诸神真的在现代社会复活,也拯救不了堕落的现代世界。古代的秩序毕竟只能以一种隐喻的对应结构若隐若现地潜藏在深处,诗人不得不面对和表现的仍然是支离破碎、无可奈何的现实。对此,艾略特只能如此感叹:
在古老的伤痕下歌唱
又修和了那早已忘却的战争
那沿着动脉所作的舞蹈
还有淋巴的循环
在星移斗换中显出身影
在夏日里上升到树梢
我们在移动的树上移动(《四个四重奏·燃烧的诺顿》)
三、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中语言隐喻手法的普遍运用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但语言确是构成诗歌最原始形式的要素,构成诗歌最原始形式的要素中必不可少的是隐喻。隐喻产生于人与万物之间的情感互动,是以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为基础而凝练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可以毫不隐晦地说,隐喻之中包藏着诗、真理和美,在人类的精神存在中牢牢地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始终保留着人与自然最真切、最原始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的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5]180
隐喻在诺贝尔获奖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是普遍的,在艾略特之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意大利的诗人、文学家卡尔杜齐。早在20世纪50年代,卡尔杜齐就出版了《声韵集》《青春诗钞》《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等。诗人谴责外来侵略和封建专制,抒发了当时人们渴求民族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感情。著名长诗《撒旦颂》完成于1863年,发表于1865年,这种与众不同的作品歌颂撒旦的叛逆精神,严厉抨击教会势力扼杀自由和理性的罪恶,赞美人的理性和物质精神对宗教的胜利和人世生活的欢乐,他在诗中讴歌到:
行星一颗一颗熄灭,流星亦黯然无光,象是空中落雨,天使们纷纷自天庭跌落。
只有撒旦永生不灭,他的权力至高无上,黑黝黝的眼睛,放出震颤的闪电。
是什么能给无常的生命注入活力,是什么能消除我们的悲伤,真心地给予爱?
那是你,撒旦,敢于藐视上帝,教皇和围王的叫喊,象一道闪电,把人们的心灵震撼。[4]29
在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歌中,诗就是语言的隐喻形式。在《圣经》中,“撒旦”是蛇的同义语,也是邪恶的形象和化身,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的运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在本质上是一种神话的命题,是神话在人类文化中的变体,或者说一种根深蒂固的生命宗教感和宇宙宗教感并未彻底丧失就转化和成就了诗,诗于是就具有一种冥冥神谕之力。因此,诗的精神总是要永恒地表达“光明的渴望”。
在艾略特之后,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及其获奖作品《柏拉特罗与我》也是如此。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是西班牙著名诗人,15岁赴塞尔维亚学习绘画,之后转入大学攻读法律,不久又热衷于文学创作。1916年到美国后正式投入诗歌创作之中,先后出版了诗集《诗韵集》《悲哀的咏叹调》《春之组曲》和著名的自传性散文诗集《柏拉特罗与我》等。其中《柏拉特罗与我》在195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该诗讴歌的柏拉特罗是一头小毛驴,诗人细腻地描述道:
“柏拉特罗绵茸茸的,又滑又软,象是一团棉花做的,只有它的眼睛坚硬透明,好象—对黑玛瑙的甲虫。”
“在往葡萄园的路上,我横过最后一条街,强烈的阳光映照在白粉墙上,几个吉卜赛孩子追着我们奔跑,头发蓬松,皮肤油黑,从红红绿绿的褴褛衣服中露出棕色的圆鼓鼓的肚皮。他们用又长又尖的声音叫道:‘疯子!’‘疯子!’”
“柏拉特罗是去年冬天死去的,我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它的坟墓,就在拉·卡纳果园中那棵青松的荫影下。在它的四周,四月用高高的黄鸢尾花点缀着潮湿的土地。”[4]281
《柏拉特罗与我》是“一首安达卢西亚挽歌”,诗人以极其深沉的感情记忆,伤悼那日渐败落的故乡小镇和已经消逝的青春岁月。诗歌通篇使用隐喻的表现手法,隐喻的运用表现了人类生命之初的一种“感觉的玄学”,一种纯思想的感觉,一个能思想的躯体。可以说,人们需要一种直接的语言,需要诗,需要神的启示,需要把世界据为己有的体验。而这一切都环绕着我们,就像“精神躯体”一样构成我们的存在。自然的声音就是诸神的话语,理解这原始的象征符号,也许就是天堂的重新发现。而这个自然就在我们的脏腑里。只要我们倾听自然之声,就会聆听到我们灵性的颤动,就会察觉到在我们的生命内部有一种意义的巨大震颤。所以说,言词在语言之后,进入那片寂静。就像艾略特《四个四重奏》所说的那样,只有凭着形式,图案言词和音乐才能够达到静止,就像一只静止的中国花瓶永远在静止中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语言使它所谈及的一切都化为隐喻。因为语言并不在于再现现实世界,而是以语言符号形式得以再现,也就是让某种东西成为语言的现“在”,让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成为“现”时的。那么,语言符号创造或建立了一个世界,这是相当于波普尔所说的独立于物的世界与主观经验世界之外的“世界三”——语言符号的世界。而人类所有的追问——无论是对物还是对人的发问——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三”的背景中提出。思的功能从这里被召唤出来,人们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符号的获得,或者说是象征功能的诞生,它表明了人类对真理的一种隐喻性探索。“海德格尔在《语言》中说,确认语言的位置,意味着恢复语言自身的地位,而不是:我们自身对于语言的占用。我们置身于语言的说话之中,置身于语言的寓言中。抛弃我们虚构的理性的中心位置,不仅通过智力,而且是‘在灵魂的富于想象的部分抛弃它’,这就是我们最初感受到的真实:语言说话。”[6]205
由此可见,语言的力量不是指示事物而是指示意义的那种力量。语言的力量与作用不在于为人们提供确定的所指,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丰富的“隐含的力量”。
[1]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2]杨冬.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托·斯·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245.
[4]刘文刚.诺贝尔文学奖名著鉴赏辞典[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239.
[5]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0.
[6]耿占春.隐喻[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I561.072;H05
A
2095-7602(2017)09-0110-04
2017-05-05
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语言学的新世纪外国文学作品译介与传播问题研究”(L13AYY004)。
乔莉萍(1969- ),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外国文学、传播学研究。
———摄影大师艾略特·厄维特拍的一组情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