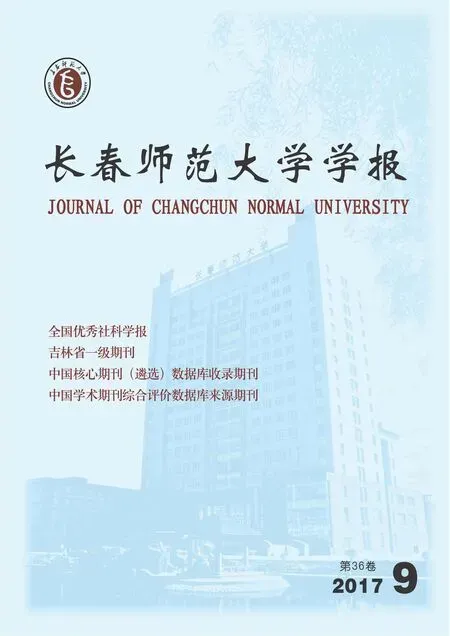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文心雕龙》“二章”考论
高 博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文心雕龙》“二章”考论
高 博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在《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章”作为文体名称,分别出现于《杂文》与《章表》两处。本文归纳总结了前人对此的看法,并以史书中相关记载为依据提出了新观点,即在刘勰所处时代,“章”既可指“章表”之“章”,又可作为“篇”的另外一个名称,其体例与作为“记文字之书”的“篇”相似或相同。
《文心雕龙》;杂文;章表;急就章;《苍颉篇》
《文心雕龙》作为我国乃至世界文论史上的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作品,以严谨的结构、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而著称,向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和推崇。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明确提出了“文心”的含义,即“为文之用心”,并将全书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和“剖情析采”三大部分。在“论文叙笔”部分,刘勰将当时的文体按押韵情况分成两大类,即“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这两大类共包含30余种体裁的文章。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其中既有文学作品,又有很多应用性质的文章。“章”作为文体名称,在“论文叙笔”部分分别出现于《杂文》与《章表》两处。
在《文心雕龙·杂文》里,刘勰提到了16种汉代以来的“杂文”,即“典、问、览、诰、誓、略、篇、章、谣、咏、吟、讽、弄、引、曲、操”,所谓“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1]165对于其中的“章”,各家解释多有不同,现择要抄录如下。
周振甫先生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译注》中所作的注解为:“章:详《章表》”[2]230。而在中华书局2013年9月出版的《<文心雕龙>今译》中,周先生所作的注解有所改动,即:“篇,章的结合;章,篇的分散。”[3]129
王志彬先生在中华书局版《文心雕龙》中所作注解为:“章:‘歌所止曰章’,一篇中包括若干章。”[1]165
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中所作注解为:“‘章’可入《章表》篇;所谓‘各入讨论之域’也。”[4]272
黄叔琳先生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一书中详细解释“章”的含义时,引用了《汉书·艺文志》相关记载,认为《杂文》中的“章”与李斯所作“《苍颉》七章”、赵高所作“《爰历》六章”、胡毋敬所作“《博学》七章”所代表的文体相同。[5]184
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引用了范文澜先生的注解:“章,详下《章表》篇”;又引李曰刚先生在《文心雕龙斟诠》中所作注解:“与《章表》篇之‘章’有别,推舍人意,当为叙述情由之文曰章。如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有《急就章》。”[6]520
其余各种注解,与上述解释多有相似或相同之处。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写道:
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1]260-263
对于此处所讨论的“章”,各家注解则比较一致,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译注》中引用蔡邕在《独断》中的说法,认为此处的“章”主要用于“谢恩,陈事”。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中则写道:“‘章’以谢恩,‘表’以陈请:两者用途不同,在前汉大抵如此;时至后汉、魏晋,章表的用途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例如,‘章以谢恩’而曹植有两篇《谢入觐表》,称表而不称章;后汉蔡邕《上始加元服与群臣上寿章》,便是用于‘庆驾’的章;又,《荐太尉董卓可相国并自乞闲冗章》和《荐皇甫规表》,同是荐举人才的,却一称‘章’一称‘表’,足见章和表,此时已名异而实同”[4]446。
以上所论,《章表》篇的“章”,应指群臣在给皇帝“上书”时所使用的文体之一。
对于刘勰在《杂文》篇中所提出的“章”与《章表》篇中的“章”所指是否相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何种区别和联系这一问题,按照上述各家的解释,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杂文》之“章”即《章表》之“章”。此派以祖保泉先生为代表。第二种,《杂文》之“章”是“篇”的组成部分。此派以王志彬先生为代表,周振甫先生后期也持此观点。第三种,《杂文》之“章”独立于“篇”之外,也与《章表》之“章”不同。此派以黄叔琳先生为代表。黄先生引“苍颉七章”“爰历六章”“博学七章”为例。又有詹鍈先生引《文心雕龙斟诠》说,《杂文》之章,“推舍人意当为叙述情由之文”,此处以史游《急就章》为例。
按上述第一种观点,则《章表》中所讨论的“章”已是在《文心雕龙》的“讨论之域”。若在《杂文》中再提“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似有重复之嫌。且按照《文心雕龙》的体例,《杂文》中的“章”属于“有韵之文”,而《章表》中的“章”属于“无韵之笔”,两者显然应属于不同的文体。
若按上述第二种观点,则《杂文》中的“章”这种文体应为“篇”的组成部分。
关于“篇”这种文体,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译注》中所作的注解为:“篇:编简成册,《汉书·艺文志》记周时史官教学童书有《史籀篇》,李斯作《仓颉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2]230
黄叔琳先生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则解释为:“《汉艺文志》:《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黄门令中游作。《元尚》一篇,将作大匠李长作。”[5]184
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中引黄叔琳先生的注解:“《汉艺文志》:《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又引范文澜先生的注解:“然皆属记文字之书,似非彦和所指,当别有以篇名文者。”[6]520
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龙解说》中则解释为:“篇,《说文》:‘篇,书也’。段注:‘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古曰篇,汉人亦曰卷。’篇,篇章也。荀子有《赋篇》。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到《诗》即称之为‘《诗》三百篇’。《尚书序》说孔子‘删诗为三百篇。’曹植乐府诗有《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傅玄有《明月篇》《豫章行苦相篇》。”[4]272
祖先生所举例子中,《赋篇》的创作年代在汉以前,与刘勰“祥夫汉来杂文”的说法不符。“《诗》三百篇”中的篇,应为量词,指诗的数量而非文体,且“《诗》三百篇”的创作年代也在汉朝以前。“美女篇”“白马篇”等,则都是诗歌的名称。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十五篇为周宣王时太史所作,是周代史官教学童识字用的一种“记文字之书”。《苍颉》七章,是秦朝名相李斯的作品;《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的作品;《博学》七章,则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这三部作品的体例和《史籀》相似,都属于“记文字之书”,后来合在一起“并为《苍颉篇》”。此后,又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急就篇》以及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所作《元尚篇》等,也都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7]1362-1363
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郭璞所注三苍三卷包括李斯所作《苍颉篇》,扬雄所作《训纂篇》和后汉郎中贾鲂所作《滂喜篇》。三者合称“三苍”,这些书与《史籀篇》一样,都属“字义训读”之书。[8]637-640
按以上史籍所载,《苍颉篇》《史籀篇》《元尚篇》《急就篇》《训纂篇》《滂喜篇》等书的体例应非常接近,都是古代供初学者学习识字所使用的“记文字之书”,它们有“无复字”“押韵”“便于识记”等共同特点,应属同一文体。正如陆宗达先生在《说文解字通论》的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产生于《说文解字》之前的“童蒙识字的课本”,都是先“杂取”一些文字,然后编成每句有固定字数的“谐韵的文句”,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让初学识字的人读起来顺口,易于记诵,而这些书对字形、字音、字义等“并不加以解析”[9]5。
史载《博学》七章、《苍颉》七章、《爰历》六章合为《苍颉篇》,正与王志彬先生和周振甫先生对“章”的解释相符合,又与上文所述第三种观点中黄叔琳先生所举的例子相符合。黄先生与王先生、周先生的说法不同,但从所举例子看,他们的观点是十分接近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篇”“章”从其作者和创作年代来看,《元尚篇》《急就篇》《滂喜篇》《训纂篇》等,都属于“汉来杂文”,而《苍颉篇》《史籀篇》等不属于“汉来杂文”。
第三种观点中,《文心雕龙斟诠》在解释“章”这种文体时,又举出汉代的《急就章》为例。《急就章》一名,亦见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汉代黄门令史游所撰。这里的《急就章》指的应该就是前文所述《汉书·艺文志》中的《急就篇》。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四十一·小学类二》所载,《急就章》共分四卷,作者是汉代黄门令史游。在《汉书·艺文志》:“作《急就》一篇”;晋朝人夏侯湛曾称:“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通甲子”;《北齐书》中记载一个叫李铉的人“九岁入学,书《急就篇》”;《隋书·经籍志》:“作《急就章》一卷”。按此,则《急就》“或有‘篇’字,或无‘篇’字,初无一定”,改称“急就篇”为“急就章”是北魏之后的事。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还记载了另外一种观点,即认为《急就》原本就叫“急就章”,“章草”即由此得名,而“急就篇”“急就”是“偶然异文”[10]1076。
《急就篇》的内容特别丰富,且便于识记,因此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受到了上至公卿权贵下至贫民百姓的广泛欢迎。当时的人们大都用它作为初学识字的教材。后世更有许多名家的作品是仿照《急就篇》体例而作的,如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等。以《急就》在当时及后世的巨大影响,若《急就章》和《急就篇》分别是史游所写的两篇不同的作品,各种史书应不至讹误;若是同一作品,那么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篇”与“章”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很可能是体例相同或相近的“记文字之书”。
另据《魏书》记载,有一个叫陆暐的人,生活年代与刘勰相仿,曾“拟《急就篇》为《悟蒙章》”[11]614。《悟蒙章》虽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但此条记载亦说明“篇”与“章”两者的体例,在当时已十分接近,甚或相同。
根据上述史料中所记载的情况可知,在刘勰所处的时代,“篇”很可能是一种供学习用的“记文字之书”;而“章”既可指“章表”之“章”,又可作为“篇”的另外一个名称。为什么在北魏前后会有这种“篇”“章”混用的情况出现?笔者认为,在《苍颉篇》《史籀篇》等“记文字之书”产生的时代,“篇”“章”之间尚有比较分明的界限,即数“章”合为一“篇”,“篇”与“章”的差异主要在于篇幅长短和内容多少。北魏前后,篇幅上的差异逐渐淡化,直至被人们忽略,因此产生了“篇”“章”混用的现象。
《史籀篇》《元尚篇》等书现多已亡佚,据陆宗达先生考证,今天流传下来的《说文解字》中的“籀文”即是许慎依据残本的《史籀篇》所辑录的,而“小篆”亦是“以‘籀文’为依据的”[9]25。可见《史籀篇》作为早期的“记文字之书”,在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之大。
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敦煌地区发现了大量汉代残简。从此以后,早已失传多年的《苍颉篇》陆续有残文被发现。现已证实的出土残简《苍颉篇》第一章的部分残文如下:“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轶群,出尤别异。初虽劳苦,卒必有意……”很明显,这段文字在形式上属于四言韵文,在内容上则有劝勉初学者之意。现存《急就章》部分文字如下:“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聊。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戴护郡,景君明。董奉德,桓贤良。……”这段文字在形式上属于三言韵文,在内容上则是将许多姓氏及其相关的著名人物等集合在了一起。由此可以看出,《苍颉篇》与《急就章》在形式上十分相似,每句都有固定的字数,押韵,且几乎没有重复的字,并皆与《章表》篇中群臣上书天子所使用的“章”有很大区别。
[1]王志斌.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5]黄叔琳.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9]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I206.2
A
2095-7602(2017)09-0090-03
2017-04-02
高博(1984- ),男,硕士研究生,从事《文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