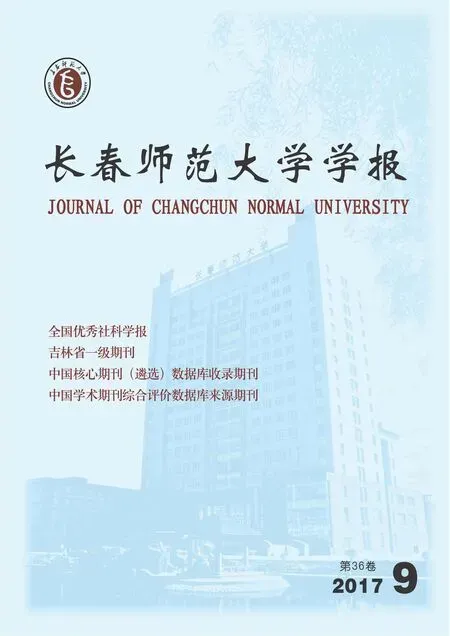操控论视角下葛浩文翻译选材研究
曾小峰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操控论视角下葛浩文翻译选材研究
曾小峰
(广东培正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830)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民开始重新关注中国文学的英译。而葛浩文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集大成者,其翻译思想与实践非常值得一探究竟。本文从操控论视角出发,探讨葛浩文本人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背景和主流意识形态对其翻译选材的操控。
葛浩文;意识形态;操控论;选材
自从瑞典诺贝尔奖协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奖文学奖之后,一直备受冷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展柜前立马门庭若市。人们渴望知道为什么是莫言,他的小说有什么魅力,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莫言背后的功臣——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汉学家与翻译家。
葛浩文出生于美国加州长岛,一次因缘巧合接触了中国文学,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翻译生涯。自1974年出版奠基之作《萧红评传》之后,他几乎垄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囊括了中国两岸三地杰出作家如黄春明、萧红、莫言、苏童、毕飞宇、姜戎、春树、王安忆、贾平凹、施叔青等人的经典作品。无怪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调侃道:“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几乎变成了葛浩文的自留地”[1]。然而,目前对葛浩文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从某个视角对其某文学译本的研究或对其本人的研究,鲜有对葛浩文本人与作品的宏观研究。本文致力于从操控论视角对葛浩文进行研究,试图探讨意识形态对译者和翻译的操控程度与效果。
传统翻译研究注重文本比较和语言分析,而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不再停留在语言学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文化、历史、政治与权力等更庞杂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考察译者主观因素和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及其效果。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引进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概念来研究翻译。Andre Lefevere认为意识形态是在某一社会某一时期所普遍接受的包含观点与态度的观念网格,读者与译者通过这个网格接受和了解文本。因此意识形态是某一阶级、国家或集体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哲学、诗学、宗教、道德和艺术等都反映了意识形态或权利的意志。因此这三大要素中,意识形态比诗学和赞助人更重要,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2-3]
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技巧的运用反映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意识形态可以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葛浩文是一名地道的美国人,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选择。下文从葛浩文的意识形态即其宗教身份、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具体分析意识形态对葛浩文翻译选材的操控。
一、葛浩文的宗教身份
葛浩文出生于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中产犹太家庭,大学毕业后参军并参加越南战争。战争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政治观,他变得更保守,对人性的阴暗面也更敏感。他笃信西方宗教中的原罪论在残酷血腥战争的催化下开花结果,本身的犹太信仰也大大地影响了他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运用。
葛浩文更倾向于那些反映人性和社会阴暗面的小说,尤其是苏童的小说。“我喜欢苏童的小说,特别是《米》和《我的帝王生涯》。《米》很好,几乎全文黑暗,没有一个好人或好事,充分体现了人性的阴暗面。事实上,人类不可能永远只有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或者一辈子都压制罪恶的一面。苏童在描写所有坏的一面时压制了所有的好的一面,登峰造极,所以他所创造的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也相信人性的阴暗面。”[4]
二、社会文化背景对文本选择的操控
自1978年以来,葛浩文致力于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长达30多年。30多年间,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沧桑巨变必然影响中国作家们的写作,也影响译者们选择中国文学作品的要求与标准。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与西方社会对中国关注点的变化,葛浩文的翻译选材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78—1990年间,相对保守和封闭的中国;1990—2000年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2000年后,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
1.相对保守和封闭的中国
在这一阶段,葛浩文的翻译重点是台湾文学和1949年前的大陆女性文学。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中国文学的主题经历了各种变化,但西方读者特别是评论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依然停滞不前,认为中国文学只是对共产党和政府宗旨的宣传,鲜有涉及老百姓生活的作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很少有机会进入西方读者视野。而这段时间,葛浩文正在台湾和美国学习中文,且其导师是台湾著名学者,所以他对台湾文学更熟悉。时至今日,他仍对台湾文学细腻、精致的写作风格和流畅的写作技巧赞不绝口。
这一时期,葛浩文翻译出版的作品包括台湾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猫》、李安的《杀夫》和白先勇的《孽子》等,大陆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商市街》和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及唯一的大陆男作家端木蕻良的《红夜》。
他的翻译在当时的文学评论界得到一致好评,TheJournalofAsianStudies,WorldLiteratureToday和TheChinaQuarterly都曾刊文赞扬其翻译,如 Hegel赞扬道:“葛浩文敏锐地选择了那些符合西方读者口味的作品,他的译本既生动又准确。”[5]
2.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媒体开始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渴望了解中国人关注什么,而文学就是反映行进中的中国的镜子。所以这一阶段,葛浩文的翻译对象主要集中于当时大陆主流文学家如王朔、莫言、虹影、刘恒和古华等人的作品。17部作品中有14部来自大陆文学家,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国和老百姓生活的变化。比如贾平凹的《喧嚣》通过一个西北小镇中两大家族的爱恨情仇,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在落后地区解放人们思想观念的困难,也反映了旧秩序的崩溃、穷人的不屈挣扎和抗争;古华的《贞女》反映了80年代中期传统贞洁观念与新道德伦理观的冲突;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则反映了文革期间年轻一代的迷茫、叛逆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葛浩文的翻译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Jeffery C. Kinkley认为“葛浩文的华丽丽的翻译,正如所期待的那样,将苏童的伟大成就在英语世界达到了顶端。”[6]
3.一个更强大和自信的中国
葛浩文自2000年进入翻译创作巅峰时期,大量翻译了各类文学作品,其高质量的译作帮助原作者在英语世界斩获各大奖项。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西方媒体和政府也逐渐主动研究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随之提高,莫言成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一鲜明例证。
这一期间,葛浩文共翻译了23部作品,其中17部来自大陆,4部来自台湾。苏童和莫言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他翻译了莫言8部小说,苏童4部小说。他的许多译作获得了国际大奖。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抱有极大希望,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度过了模仿时代,开始重建和重塑自我,将来的中国文学只会前进不会倒退。
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因素操控的文部选择
尽管中国文学经历了巨大变化,但西方读者在面对中国文学作品时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却野蛮、神秘、落后和复杂的国家。为了印证这些偏见,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满足他们原始想象的小说,而且那些批评中国政治和充满对现实不满、失望情绪的小说更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想象和期待。
1.对落后、神秘中国的固化印象
正因为西方对东方的神秘想象未能在中国文学上体现出来,西方读者为了满足和固化自己对东方神秘的想象,便会操控他们对文部的选择。葛浩文的近20部译作中,从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到莫言的《檀香刑》,共约四分之一的作品反映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古国的风风雨雨和人民的喜怒哀乐。
莫言的《红高粱》《檀香刑》,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碧奴》,刘恒的《苍河白日梦》,阿来的《尘埃落定》和李永平的《吉陵春秋》等等,一次又一次地验证着西方对中国的神秘、野蛮想象。以莫言作品《檀香刑》为例,《檀香刑》的故事和形式都取自山东的部地戏曲——猫腔,其中心内涵却是对晚清政府的严厉批判。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的大背景下,聚焦于女主人公孙眉娘和三个男性之间的关系:生父孙丙、公公赵甲和情人钱丁。孙丙作为义和团运动的领头人,被官府镇压并判处檀香刑,这是一种极端残忍的刑罚,即在确保犯人活着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处死犯人的刑罚,而公公赵甲便是执行处罚的刽子手。《檀香刑》中充满了对残酷刑罚的细腻而令人作呕的描述,给读者提供了残忍却鲜活的视觉与感官盛宴,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古老、神秘、野蛮中国的想象和猎奇心理。
2.对中国政治的批判
即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国外依然不乏批评意见。西方学者认为作家不能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所以他们批判莫言未能批评所谓政府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压制。这一批判倾向深深影响了中国小说的选择,《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千万别把我当人》等都隐含了对政治的某种批判。
《生死疲劳》讲述了一个善良、慷慨的地主西门闹在土地改革期间被错误处死,西门闹不服从命运的安排便在阎王殿大呼冤枉。阎王为了惩罚他,让他经历了六道轮回,做完驴、牛、猪、狗和猴子,最后才轮回为人类。西门闹家族和他的长工蓝脸家族的爱恨情仇、恩怨纠葛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和跌宕起伏。莫言在文中隐晦地批评了当时的政治变幻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
《天堂蒜薹之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8年的山东省天堂县,一个虚构的田园牧歌式中国北方乡村。当地县政府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蒜薹,但由于政府官员的短视和产销信息的滞后,农民们辛辛苦苦种植的蒜薹根本无法卖出去,只好任其在地里腐烂。蒜薹的压力、高额的税负加上当地政府的渎职和腐败成了最后的稻草,彻底激起了那些千里迢迢赶来卖蒜薹的人们的愤怒。他们冲击了当地政府机关,造成了严重后果。最后,政府逮捕了许多老百姓,两败俱伤。莫言在看到新闻报道之后,出于义愤,在短短一两个月内便完成了该小说,批判了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腐败以及老百姓的无奈与伤痛。瑞典皇家科学协会的常务秘书Peter Englund赞扬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感,表达了对为生存和尊严而战的平民百姓的关注和怜惜。
3.对痛苦现实失望的宣泄
二战后,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人们厌恶政府的廉价商业观和肤浅的伦理价值观,年轻人沉浸在理想缺失、信念崩塌的虚无世界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怀疑、背叛和失望,嬉皮士和雅皮士应运而生,吐露他们心声、宣泄他们情绪的作品广受欢迎。同理,反映中国年轻人反叛情绪、逆反心理和吐槽痛苦现实的小说也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和兴趣,痞子文学代表王朔和现代青春派小说家春树的作品便是典型代表。王朔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文学的坏孩子”,他的代表作《玩得就是心跳》反映了文革一代年轻人的迷茫、焦虑、痛苦和失望;春树的《北京娃娃》因其对年轻人糜烂生活和颓废的描述,一度被视为禁书。这些都反映了年轻一代的残酷青春以及对残忍现实的宣泄。
四、结语
葛浩文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学并顾及西方读者的需求,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不可避免受到宗教身份、中西方社会背景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译作在国际上获得的一系列奖项无不证明了他眼光的独到和对中西方文化的精通。葛浩文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半生笔耕不辍地执着与对中国文学的独到见解和高质量的译作值得学人深入研究。
[1]约翰·厄普代克.苦竹:两部中国小说[J].季进,林源,译.当代作家评论,2005(4).
[2]Susan Bassnett, Lefevere 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ngofLiterary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
[5]Robert E.Hegel. The Drowning of an old cat and Other Stories by Hwang Chun-Ming; Howard Goldbaltt[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81:534.
[6]Jeffery C.Kinkley. China——Rice by Su Tong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J].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6(2).
[7]Goldblatt Howard.“the Returen of Art” Manoa[J].word literature Today,1989:83.
H059
A
2095-7602(2017)09-0078-04
2017-05-13
曾小峰(1985- ),女,助教,硕士,从事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