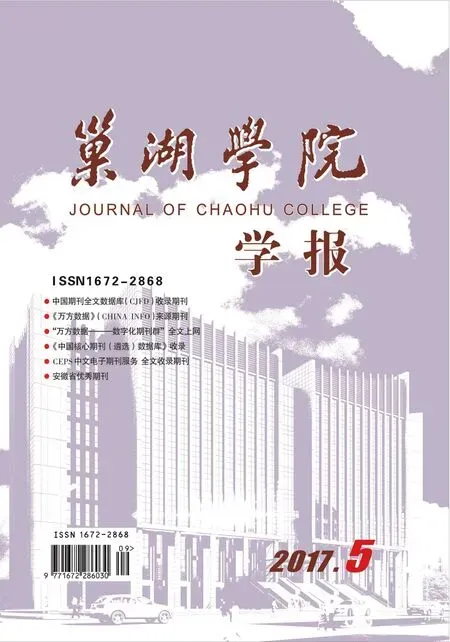侵害债权主观要件探析
龚正铭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侵害债权主观要件探析
龚正铭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63)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应当增加过失侵害债权的类型,行为人因过失导致债权无法实现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债权具有相对性,对于债权存在不能以道德或者理性人的标准给第三人课加“应当预见”的主观要求,对于未明确知晓具体债权存在时,行为人过失导致侵害债权不能适用此制度。同时,在行为人明知债权存在时,此时债权具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具有公开性的特征,如果行为人非以侵害债权为目的,但是基于重大过失或者放任的态度导致侵害债权时,也应有此制度适用的可能。
债权;故意;明知;过失
1 问题的提出
权利是民法的价值基础,我国侵权法以对绝对权的保护为主。我国侵权法规定了行为基于不同的主观方面造成损害时的处理方式,即以故意或者过失作为相应的分析模式。
债权虽然非为绝对权,但是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之规定,债权确有该条“权益”中“益”之适用可能。债权作为权利的一种形式,显然也具有不被侵害的特性,自然也应当受到我国法律保护。对于债权的保护,除了现有的“违约”责任规范外,我国司法实践和理论均承认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的适用,据此,在特殊情形下,受到损害的债权人可以选择“侵权”规范以排除“违约”责任规范的适用,该类型是法律人从实际出发,经特殊的解释而成。但是我国第三人侵害债权主流学说主要是承袭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故意且悖俗侵害他人利益的规定且要求行为具有目的性。显然,行为人基于重大过失或者放任故意侵害债权时难于适用“故意且悖俗”的规范类型决定了,在适用此类规范时,首先要检视第三人主观方面,而现有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显然难以覆盖此类侵权的范围。
上述逻辑意味着,只有承认特定的主观情境下的侵害债权之类型,才能解释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救济模式。本文意在分析第三人不同行为模式,展示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构造,在构造上首先展示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与局限,并引入司法困境与德国、台湾地区的理论与裁判,提取有益的要素,并进行要素分析后,分析此类侵权的构造。
2 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提炼与整理
2.1 主流学说的贡献
债权具有相对性,罗马法认为债是之于债务人之“法锁”,债权人就债的实现仅得向特定的债务人作出请求。根据债权的相对权特性,第三人的行为导致债权无法实现时,债权人通常不具有侵权损害赔偿救济的请求权基础。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但当行为人明知债权存在而故意侵害者,得按侵权损害主张救济。理由不外乎二:
第一、权利具有不可侵害的共性。债权与物权等绝对权相比而言有其特殊性,其产生非主要基于行为主体意思自治而产生。虽然其产生的基础、权利范围与效力和绝对权相比有所不同,但是无论何种权利,均有受法律保护不受侵害的特征,债权也不例外[1]。一项权利如果不能排除他人侵害,则难谓有行使的可能,因此权利的可不侵害性是所有权利均具有的共性。王利明教授认为,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是合同法与侵权法结合而产生的,它更加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地位[2]。债权可以成为侵权的客体,给特定第三人课加了不得妨害债权实现的义务,是对债更为周全的保护。
第二、债权具有对外效力。由于债权具有非典型公开的特征,通常不能成为侵权的客体。如果承认债权有对抗第三人的绝对效力,无疑也是混淆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界限[3]。因此,无论是《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还是《台湾民法典》184条,亦或是我国民法理论通说,均以行为人故意作为侵权成立的要素之一。而故意则意味着行为人已经明知具体债权的存在,债权相对于行为人而言并不存在一般债权的非公开的特征,此时承认第三人侵害债权并不会混淆绝对权与相对权的界限。债权相对性的特定性其并不与债权受到侵害的可归责性相冲突,应该说相对性与不可侵性非属于同一范畴,二者可以共存于法律体系之中[4]。
尽管侵害债权制度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侵害债权的要素问题却是讨论的核心,个中又以“故意”和“过失”之争为甚。在此争议之中,主流学说以行为人于受侵害债权之主观要素为区分之基础,当行为人之明知其行为会造成第三人债权受到侵害,且积极追求债权受到侵害的结果时,则符合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基本要素规范;反之,若行为人对侵害债权的故意非为积极追求损害结果发生时,债权受到侵害的结果之于行为人则为纯粹经济损失,行为人对债权受到损害的结果并不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债权人仅得就债未实现寻求债的救济。
概括而言,行为人即便是明知其行为可能或者必然造成债权无法实现的损害结果也不必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为行为人并不必然的具有追求债权无法实现的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5]。质言之,主流学说将行为人侵害债权的带有目的性的故意作为此类侵权的类型要素,并以此与纯粹经济损失加以区别。当行为人在认识因素上明知具体的债权存在,在意志因素上具有希望债权损害结果发生,且具有因个人私益而纯粹侵害债权的目的或动机时,行为人的行为即落入第三人侵害债权的法定模范类型[6]。此乃主流学说在实务操作及理论阐述中的贡献。
2.2 司法实务中产生的疑义
尽管通说认为第三人侵害债权以故意且具有目的性为必要,但另有学说认为除了直接故意侵害债权外,应当承认第三人重大过失或放任故意侵害债权的可能性[7]。显然,通说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而由此带来的却是实务中理论构建的混乱。不少法院承认第三人存在重大过失时侵害债权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碍于通说的影响,法院为了避免判决存在争议,往往以其他的理论进行解释,但如此却愈发显得首鼠模棱。而在下面这些实例中,也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中,审判者在理论适用的困惑,同时也可以揭示出对通说的疑义。
在“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宁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8],信达公司(债权人)与天一公司(债务人)欲共同出资设立天合基金,后两公司以设立中的天合公司名义在浦发银行开立验资账户,信达公司将验资款项汇入该账户。后浦发银行根据天合公司申请开立临时账户,并验资账户中的款项汇入了临时账户。同年,由于天一公司的原因天合公司无法设立,浦发银行将所有款项汇入天一公司账户并撤销了验资账户。但是天一公司在收到该笔退款后并未将其返还至原出资账户,而是挪作他用。其后,天一公司更因为经营不善宣告破产。天一公司破产后,债权人信达公司因债权无法实现,以浦发长宁支行违反了《账户管理办法》中“未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单位,在验资期满后,应向银行申请撤销注册验资临时存款账户,其账户资金应退还给原汇款人账户”的规定,认为浦发长宁支行明知该笔款项应退还至信达公司账户,却违规划款至天一公司账户,其行为客观上使天一证券得以挪用验资账户内的款项,给信达投资造成了财产损失,侵害了信达公司债权为由将浦发银行诉至法院。该案判决以浦发银行间接侵权为由,判令浦发银行对天一公司的债权承担补充责任。显然,第三人明知债权人存在的情况下,因重大过失或者放任故意侵害他人债权时并无需承担侵害他人债权的责任,当违约救济无法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时,否认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显然是难谓合理的。由此可见,承认重大过失或基于放任故意侵害债权在司法实务中却有适用的必要。
3 “明知”主观下,侵害债权解构与借鉴
3.1 放任故意与重大过失侵权分析
3.1.1 行为应受债权对外效力拘束
对于第三人侵害债权,持否定观点者认为,债权具有相对性,其权利义务仅在权利关系人之间,债权之于第三人而言并不存在,第三人对债权的实现也不负任何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即便是第三人行为导致了债权实现障碍也不能要求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然将导致法律逻辑的混乱[9]。在重大过失侵害债权情境下,第三人已经知晓具体的债权存在,其就债权存在而言并非不特定的第三人,债权的非典型公开性对第三人已经不存在。此时债权除了得请求特定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效力外,还具有一般权利的对外效力,亦即知道具体债权存在的任何第三人负有防止因自己行为导致债权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形发生。
在上海浦发长宁支行侵害债权案中,浦发长宁支行明知信达公司对注册中的天合公司有返还出资的债权,但是在天合公司无法设立的情况下,应其请求将验资款划入临时存款账户,继而划入到天一公司账户。简言之,对于信达公司的债权而言,浦发长宁支行已经有了具体的认识。此时债权相对于浦发长宁支行而言,已然产生了不受一般侵害的对抗效力,浦发长宁支行应当防止其行为导致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形出现。对于信达公司的债权无法实现而言,浦发长宁支行应当受到信达公司债权的对外效力拘束,虽然其行为并无直接侵害债权的意图,但是对于债权无法实现,长宁支行显然具有重大过失。
3.1.2 行为具有可归责性
对于一般侵权行为而言,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失责任、无过失责任、衡平责任。而过失责任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归责原则,其之所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耶林认为过失对于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就好比氧气对于燃烧的火一般,其关系一目了然[10]。当侵害债权人的行为基于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时,行为人明知债权存在,却疏于自身行为管理,对行为结果发生听之任之或者自信可以避免,最终致使侵害债权结果发生。从主观层面看,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过错;而在客观层面也产生了债权无法实现的损害结果。同时,产生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行为人的放任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因此,自然也应当承认其行为的可归责性。
对于前揭案例,从判决结果中可以看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浦发长宁支行行为的可归责性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因为按照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无侵害债权之目的性时,不能按照第三人侵害债权救济,因此该法院采取了知识产权领域中“间接侵权”用以说理。若依主流学说,笔者以为信达公司的损失应该纳入纯粹经济损失的范畴,唯得《账户管理办法》请求损害赔偿。
3.2 域外理论实务之借鉴
从比较法处理此类问题的态度上来看,虽然故意追求债权损害的行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也不乏承认过失侵害债权的学说观点。法国学者拉鲁便建议以《法国民法典》1382条作为侵害债权的请求权基础[11]。台湾审判实务亦有观点认为当债权为第三人可预见其存在却因过失加以侵害时,若令其勿用为此负责任也难谓合理。在租赁权等具有权利公示的外观时,过失侵害此类权利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在台湾最高法院审理的最“捷运施工侵害他人租赁房屋案”[12]中,原告作为承租人租用了被告一的房屋用于生产经营,其后,由于房屋出现漏水等情形,为了恢复正常的经营活动,原告请求被告一修缮房屋,但未获置理。此外,被告二公司因承揽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项目,在地下层开挖路线。由于被告二公司在开挖路线时未尽到安全防护义务,导致系争房屋出现漏水现象,致使原告得以正常经营的租赁权受到侵害,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承担侵害其租赁权及合法占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原告不具有侵害租赁权的请求权基础,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最高法院则以原审法院判决理由有误废弃了原判决。显然,该判决似乎承认了第三人因过失行为侵害特殊债权的适用余地。1968年“台上字第1504号判决”进一步指出:“按债权亦具有不可侵性,依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之债权者,固应负侵权行为上之责任,但此以第三人之行为对债权之存续或其法律上效力有直接影响者为限。”[13]
4 构建重大过失或放任故意侵权的体系效应
4.1 债权保护更为周延
与第三人侵害债权相近的理论是纯粹经济损失,即非基于绝对权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损失。在此类侵权行为中,债权人的损害从第三人视角观之,第三人行为并没有直接侵害债权人的绝对权利,所以债权人的损失实质上仍然是纯粹经济损失。不同于英美法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不予赔偿”的立法例,德国法规定只有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或“故意违背善良风俗”所致的纯粹经济损失才有可能通过筛选,这就基本排除了纯粹经济损失在侵权法下获得救济的可能性[14]。为了规制此类侵权行为,德国民法典826条做了例外规定,即规定了第三人侵害债权。由于826条规定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必须以“故意且悖俗”为要件,使得部分特定的纯粹经济损失无法获得赔偿,在不破坏德国立法框架的情况下,该国立法例又引用了“附保护第三人之契约”作为纯粹经济损失绝对不予赔偿的例外之一。
我国民法及侵权法上并没有规定纯粹经济损失以及第三人侵害债权等有关制度,但在理论及实务中均承认纯粹经济损失和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存在。但沿用德国第三人侵害债权带来的弊端就是我国制度建设不完备的情况下,由于并没有附“第三人保护之契约”等相关制度,刻板的移植德国有关侵害债权之立法例容易导致法律保护的不完满。笔者结合自身经历案件试举一例:
A公司将船舶出售给B公司,船款总价1亿元,其中已付8000万。为偿付A公司船舶尾款及其他债权,B公司向C银行贷款8000万,约定贷款中2000万元用于支付船舶尾款。贷款审批成功后,C将款项全部汇入B公司账户,并为其开通了支付权限。由于获得了付款权限,B公司将8000万贷款全部用于偿还案外第三方的欠款。后,B公司破产。然而,根据《固定资产贷款办法》,贷款金额高于500万的,应当采取受托支付的方式,即银行将贷款划入贷款人特定账户,并对其监管。贷款人使用该笔贷款时应向银行申请,由银行审批后进行划付。而本案,C银行给了B公司划款权限,致使B公司可以不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使用贷款,间接导致了A公司债权无法实现。
在本案中,C银行在审核贷款时,明知B公司的贷款中2000万应用于支付A公司的欠款,但是其违反了《固定资产贷款办法》规定的受托支付方式,致使A公司债权落空。此时,如果按照主流学说,因为银行的过错是基于其重大过失或者说放任的故意产生,A无法采取第三人侵害债权寻求救济,另B已经破产,A只得承担此损失。而《固定资产贷款办法》并未规定C对A有直接付款义务,A也不具有其他救济之请求权基础。但本案中,银行已经知道债权存在,其负有防止因自身行为致使债权损害之义务,债权之于银行有公开性和对外效力。其行为已经具备了侵权的一般构成。显然,只有承认此类侵权,才能有利于构架更为全面的侵害债权类型。
4.2 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在侵害债务人致使债权无法实现的案件中,行为人若明知具体债权存在,而因私侵害债务人,由于行为人非以侵害债权为直接目的,因此不能按照第三人侵害债权加以救济。根据损害赔偿的精神,原则上义务人应赔偿受害人实际遭受的与侵害行为有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全部损害,既包括积极损害(已的利益丧失),也包括消极损害(可得利益之不能获得)[15]。而根据此思维路径,此时债权人若想实现权利之救济,须以契约关系起诉债务人,债务人再以损害赔偿请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这一路径,不难发现诉讼程序的重叠。即当行为人有能力偿付因其行为导致的损害时,其负担的损害赔偿必须经过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诉讼以及债务人与行为人之间的两个诉讼才能得以解决。显然,承认在行为人明知债权存在的情况下过失侵害债权的可归责性,并对侵权损害赔偿加以限制,将更符合现下的司法实践和理论构建。
5 结语
行文至此,本文认为,如果仅依照“绝对权”与“相对权”去讨论第三人侵害债权是否必须以直接追求侵害债权的目的不甚恰当。无论是债权亦或是物权,均为财产权,自有受法律保护之必要。在侵害债权层面,当行为人对于债权得否实现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或者出于轻信可以避免的态度时,应将此类行为纳入到侵害债权的规范体系内。现阶段,我国并未从立法层面确立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但该制度已经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被广泛应用,如果严格按照主流学说关于侵害债权的类型要素之论证,必然导致该制度适用困难。在理论层面承认放任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债权的类型,将更有利于权利的保护。
[1]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3:152.
[2]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42.
[3]郭明龙.对“第三人侵害债权”的理论反思[J].新疆社会科学,2007,(6):75-80.
[4]余尘.我国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构建[J].社会科学家,2013,(03):96-99.
[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2.
[6]张松青.侵害债权行为的故意之认定[N].天津政法报,2016-06-28(3).
[7]梁慧星.民商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89.
[8]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
[9]魏盛礼.第三人侵害债权理论——理论创新还是法学歧途[J].河北法学,2005,(9):46-49.
[10]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11]王又明.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的法律思考[D].武汉:武汉大学,2003.
[12]台湾最高法院1990年台上字第803号判決书。
[13]王建源.论债权侵害制度[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3,(04):38-44.
[14]徐海燕,朱辰昊.纯粹经济损失赔偿制度研究——兼论证券市场中介机构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J].甘肃社会科学,2008,(3):139-143.
[15]高富平.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43.
D913
A
1672-2868(2017)05-0040-05
2017-08-01
龚正铭(1991-),男,福建宁德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
责任编辑:杨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