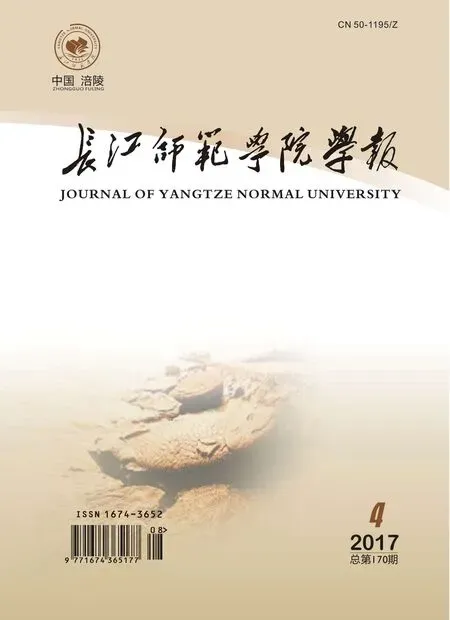六朝小农逃避赋役行为析论
郭 超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六朝小农逃避赋役行为析论
郭 超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六朝时期租调繁重,各类杂调、徭役层出不穷。小农欲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最有效的行为莫过于不纳或少纳赋税。其时不乏各类窃改籍注者,他们谎报年龄、疾病等状况;寻荫大户,入僧道户;混入仕流,诈买军勋、爵位;著录官、私学生。这些逃税避役行为虽然可以减少赋役方面的支出,但纳贿或资买方式毕竟有二次行贿或大族役使的代价,且加剧了下层小农生活的贫困化。
六朝;小农;逃避赋役;依附;行贿
中古时期,朝廷正赋或轻,而各种横调、杂税、徭役多繁于正赋,小农①本文“小农”指以耕、织为主要生计,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著籍民户。赋役负担实在不轻。正如王家范所揭示的那样:“产量长一寸,赋税量增一分,紧追不放,大体多占总产量的30%~50%上下。”[1]168但小农并非愚弱不堪,坐守困局,他们在政府课役、官吏盘剥以及天灾人祸时,也有比较丰富的应对经验。就六朝时期小农而言,在通常情况下会选择耕织结合,兼以园圃、采集、渔猎等补充生计。大多数小农还会将剩余农副产品及简单手工业成品、半成品拿到市场出售,以及从事佣工、向富豪权贵借贷等度过危机。此外,小农为了规避或减少课役负担,也有许多行为,这里仅就六朝时期小农逃避赋役行为略作分析。
一、窃改籍注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赋税之用。”[2]1379控制编户,编纂内容详细的各类籍簿,依律征收赋税是朝廷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从长沙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治下各类籍簿编纂已经相当完善。自东晋始,纸取代简牍成为官方文书书写普遍采用的材料。小农著黄籍,黄籍登记家庭成员名字、地位、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所有著籍项目都与小农是否承担赋役以及是否享受政府优抚政策密切相关。
汉代成丁年龄区间为15~56年,7岁以下以及60岁以上无课役。孙吴大致继承了汉代的成丁标准。从走马楼吴简上看,吴国成丁的年龄仍为15岁,称为大男、大女,15岁以下者称小男、小女。老的年龄据简牍所见最低为61岁,如“老男胡公年六十一踵两足”(壹·5162),老男陈州年六十一(壹·5312),或许老的年龄界限为61岁。两晋时期正丁的年龄区间扩大,为16~60岁,老的年龄推迟到66岁,半丁区间分为13~15岁、61~65岁。与之前相比,正丁的年龄段虽未增加,但老的要求提高到66岁;南朝大致延后,将正丁的年龄后延至18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3]674,征收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之前“计赀定课”,按户等征税,逐步转为按丁计征的丁中制度,调的标准也有所提高。
成丁年龄以及不课老人年龄规定事关小农切身利益,为了规避或减少赋役负担,小农大多希望将成丁的时间推迟,免老的年龄提前。据尹湾汉简,“西汉后期东海郡80岁以上老人有33871人,90岁以上者有11670人,分别占总人口比例2.42%、0.83%,这种比率甚至高于上世纪(笔者注:20世纪)90年代的高雄。”[4]557嘉禾年间,临湘县内有确切年龄记载的2499人,其中61岁以上的有271人,占比高达10.84%;临湘县残疾人口约占样本人口的9.68%,且男女比例为4∶1②相关统计可参见侯旭东《走马楼吴简初探》,文津出版社,2004年,第123-140页。。临湘县老年人口过多,已经达到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其中不乏为了获得免役特权而改龄者。在残疾人口中男性比例很高,所患疾病多为“刑”“腹心”“雀”“踵”“盲”,虽可解释为战争负伤或真实患病,但如此高的比例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其中有假冒病残以避征役者。
齐高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上疏痛陈时弊,提到:“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5]696百姓通过自残来避徭役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更多情况下,小农会选择相对和缓的方式,如沈勃自恃吴兴土豪,“辄听募将,委役还私,托注病叛,遂有数百”[6]1687。沈勃通过招募部曲的方式,假以杂役,伪注病叛,成功使数百编户脱离了朝廷控制。虞完之论道:“自顷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5]608百姓逃税避役各有其法,大多是在籍注项目上做文章,主要有改龄(盗易岁月)、注疾(身强而称六疾)、注爵(窃注爵)、注绝(户存而文书已绝)以及托言死叛、伪言隶役等,从“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避役的普遍化。南朝后期,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增大,南朝中央政府控制力仅局限于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这时各种征调课役的重压也集中到这些地区的百姓,尤以扬州为剧。史载:
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又横调征求,皆出百姓。[7]156
从这段记载看,诈病避役由来已久,政府并非不知,只是安平之际,货赂公行,不便揭露。一旦军国所需,征调急迫,往年因行贿而避役者不得不在追还租布与继续贿赂官吏中作出艰难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唯一没有遭受利益损失的只有各级官吏。他们里通上下,缓则纳轻贿,急则纳重贿。最终没有纳重贿的小农不得不追偿税调,承担新的横调。在一轮“尺布之逋,曲以当匹;百钱余税,且增为千”[5]692的过程中饱受煎熬。对于他们而言,改龄、注疾等并不能真正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二、入仕流与买军勋
六朝时期门户观念甚炽,对于小农而言,权门士族高不可攀,而士族内部分又为不同等级,旧门、次门虽势不显,但依然享有免役特权。朝廷历来明士庶之别,在黄籍上甚至登记门第等级。有不少发迹之士人、将军便出身于“三五门”“次门”“旧门”,如刘宋武念“本三五门”[6]2112。所谓“三五门”源自三五取丁制,来自民户,后入役门,社会地位低下。宗越“本南阳次门”,赵伦之条次氏族,已沦入役门之列,后因军功,得复列士族。小农当中资产丰厚者也可以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今反役人”[5]60。刘宋吴兴太守王僧虔就因“听民何系先等一百十家为旧门”[5]592以及私“度民与弟子”而遭免官。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收到了不少的好处。唐寓之起义攻占富阳时,“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7]1928,。这里所说的却籍者,即有不少昔日贿赂官吏诈注仕流近遭朝廷检户而去士籍的人。民间士庶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资产厚薄之争,出现“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极贫者,悉皆露户役民”[5]808的社会状况。上流社会“士庶之际,实属天隔”,对于基层社会而言,士庶之别,盖由赀定。凡赀厚者,历尽巧伪,所谓“吏贪其赂,民肆其奸。”由于贪渎之风盛行,原本严格的士庶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了,正如梁武帝时沈约上书提到的那样:“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7]1462当然对于乏资露户而言,这种贿赂成本过高,是他们难以承受的,而冒入行伍,窃得功勋或许更易为之。
将领与部曲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除领主控制部曲生活的命脉——土地外,还与将领乐施小惠、滥注军勋有关。苏峻之乱平定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5]609。可见逢战之后,勋簿所上,多非其实。宋明帝泰始元年,益州刺史萧惠开不遵朝廷法度,明帝遣其弟惠基宣旨慰劳。之后引起氐民不安,益州土人引“氐贼围州城”。萧惠基晓谕利害,几乎兵不血刃就平定了益州之乱。还朝后,“惠基西使千余部曲并欲论功,惠基毁除勋簿,竞无所用”[5]810。在没有经历大的战争的情况下就有“千余部曲论功”,可以想见,在规模较大的平乱战争后,争功者当不啻万人,勋籍所载,可谓滥矣。宋大明年间后,“缘寇难频起,军荫易多,民庶从利”[5]608,通过滥注军勋而免役更加普遍。萧齐时,朝廷籍簿不实十分严重,虞完之曾上书道:“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5]609滥注军勋者多非前线将士,“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这些人正是通过诈买军勋而免役。
萧齐初年,民间“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8]59-60。“一万许钱”于富人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于小农来说仍是一笔较大的数额。以当时物价而言,略相当于百斛之米,非寻常人家所能承受①萧齐时“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既是优评,当属优质米的高于市价的估价,可见常评米价尚不及百钱。拙文《东晋小农家庭经济状况分析——以经济支出为中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5期)曾以80亩垦田数额估算支出、收入,认为年结余米23斛左右,这只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东晋南朝虽然亩产达到2.5斛(米),但小农家庭垦田因大族侵夺、战乱、灾异等原因往往不过50亩,小农家庭年口粮约为百斛(米),若将税调等支出考虑入内,则很难有较多的剩余产品。。时人亦深知其弊,钟嵘曾上书梁武帝,奏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9]694梁武帝虽以为然并“敕付尚书行之”,但不见有显著效果。骑都尉、散骑侍郎等职向来“二品士流”充当,庶民挥金而得,不难想见,二职以下买授必定亦滥。
总之,有资者有逃避赋役的诉求,而各级贪婪官吏有著录籍簿、征收赋役的职能,二者一旦结合,便出现了不少通过买军勋而混入仕流者。南朝后期,国家编户不满百万,正常赋税本就不能足纳,这种行径使本已陷入危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未买军勋、入仕流者在“杂役减阙”后承担了更多的正调以及杂调、杂役,加剧了下层小农生活的贫困化。
三、寻荫大户与入僧道户
六朝时期,士族地位上升,他们不仅左右朝政,控制地方,而且大肆“封略山湖”,孙吴时期已是“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10]。其言虽不免夸张,但形象地反映出世家大族在经济生活中的强势。王公贵人在法禁宽弛下莫不挟藏户口以为附庸,小农依附大族,充当佃客、衣食客、附隶等也成为一种有效的逃税避役行为。以“荫客”为例,依制是“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衣食客三人……九品佃客五户,衣食客一人”[3]674。实际情况是权贵依势多逾此制。史载吴时会稽焦征羌“人客放纵”[11]1236。东晋时期,京口“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12]1846。大族荫客放纵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萧齐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7]156。所谓役人即是须服役之吏民,多依士人无疑是为了取得附隶身份而免除徭役。他们虽能免朝廷之役但却仍免不了为大族提供各类役使,“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6]1319。由于被指派从事各种杂役,荫客们已经失去完整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附隶大族的代价。还有一类所谓“门生义故”,他们多非真正意义上的授业门生,而是大族依附人口中的一种,可以资贿买。刘宋颜竣“多假资礼,解为门生”[6]1966。又如徐湛之“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6]1844。一旦成为门生,便可不纳课役,甚至可以得门主荐举,获得一官半职。但说到底,门主与门生之间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门生虽然部分脱离了朝廷的控制,得以“优复蠲免”,但仍不免于为门主从事农作、杂役等。谢灵运“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7]540。门生还要忍受各种索纳,沈勃“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6]1687。从索贿金额上看,非富室不堪承受,通过纳资礼等贿赂手段成为门生并得以维持的只是极少部分的富裕小农。
六朝统治者对佛教多加扶持,不仅施以数以亿计的钱财,而且设僧正管理天下僧众。一时之间,“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7]1720。在世家大族中也有大量信徒,例如王坦之“舍园为寺”[13]482;张孝秀“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敬慕三宝,“率以力田,尽供山众”[9]752。世风浸染,小农多有事佛者。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信奉佛教不仅是一种精神生活的安慰,更有现实的经济利益。僧道户不著民籍,不纳赋税,“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14]3455,他们甚至“家停大小之调”。小农入僧道户或将自己的土地寄名寺产以避赋税,这种风气在南朝尤甚。“民间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填街溢巷,是处皆然。”[5]609百姓剃度为僧或假名出家,“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7]1721-1722。上层僧尼大多资产丰沃,富比封君,乃有一僧资财数百万者。朝廷甚至将富裕僧尼与富有之家并称,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侵,形势严峻,宋文帝诏:“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8]250可见寺产之丰厚。
对于小农而言,寄名僧籍或者托为寺产并非万事大吉,只是剥削方式由政府课役转为寺僧役使。刘宋时释法显3岁便度为沙弥,“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13]87。僧众尚且如此,细民为生计所迫,受寺门奴役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晋海陵人董幼,“年十八,谓母曰:‘幼病困,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终不得活。欲依道门洒扫,以度一世。’”[15]784除此之外,僧尼不守寺界,肆意侵占原属国有的山林、水泽,对民产也不放过。梁武帝就曾下诏:“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9]86他们还欺骗信众,“交纳帛布,卖天堂五福之虚……豫征收赎,免地狱云(六)极之谬殃”[14]3769。
寺院依附者众多,俨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谈到都下“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14]2141。不羁之众,多为贫民,由于衣食无着,这些依附寺院者甚至“谋反”。比较大的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6]2386,皇帝因之震怒,下诏:“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民间非戒行精苦者,强令还俗。梁时北兖州“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9]463,一时声势颇大。寺产丰厚一度成为统治阶层觊觎的对象,“武帝军东下,用度不足,伟取襄阳寺铜佛,毁以为钱”[7]1291。依附大户的小农,“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8]13,不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还要为富人提供各种杂役,这实际上不亚于朝廷各类劳役。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6]1319。他们并没有独立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小农非形势逼迫,一般不会选择依附大户,奴事富人。
四、著录官、私学生
以资纳贿成为大族门生或者买军勋、入仕流毕竟需要较高的成本,且有二次行贿或被著籍官吏纠正的风险,通过入官、私学而免役相对来说其成本较低且属合法。此时六朝教育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官学与私学并存,是六朝教育的基本格局。”[16]无论著籍官学生还是私学生本人都享有免役权。在走马楼吴简中有私学简数百枚,私学别立籍簿,“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孙吴时期的私学除了缴纳限米之外,未有缴纳其他赋役的记录,也没有服徭役的迹象。”[17]215虞翻远徙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11]1321,当有不少“因连避役”者。同时期的蜀人李宽“能祝水,治病颇愈”,至吴后,“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18];东晋时庾亮在武昌开设学馆,明言“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6]364,从中可以窥见入学免役成为当时之通例,故需禁止。这些官员、名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也与小农“避役”诉求的强烈有关。东晋孝武帝时,国子祭酒殷茂进言:“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6]364由于生源“混杂兰艾”,平民子弟多为避役,故一旦著录为学生,目的达成,便不笃志向学。
南朝中央官学生享有免役、供食宿以及物质赏赐等权利,其生源通常有士族身份限制。名士隐居教授,对学生没有出身限制,其数目少则数十百人,多则数千人。例如沈驎士“讲经教授,从学者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5]943。贺玚“于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余人”[7]1509。徐孝克,“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18]337。之所以形成如此宏大的授学场面,一方面与为师者学艺精湛、师德高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徭役繁重、细民以避役为目的而著录为学生的结果。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小农逃税避役主要是:编户民改籍注与改变隶属脱离编户。买军勋、官爵,入仕流实施的成本较高,“一万许钱”并非普通小农家庭所能承受。改籍注在政府括户和检籍下有被纠正或二次行贿的风险,著录官、私学生只能本人免役,作用有限。寻荫大户与入僧道户只是剥削对象由政府转为大族、寺观,仍须忍受各种役使。六朝尤其是南朝富裕小农通过行贿或资买不纳或少纳赋税十分普遍,陈时山阴“县民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18]460。在这种情况下,中下层小农不得不承受朝廷编户损失后税调增加的负担。
参考文献:
[1]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郑樵.通志二十略(下)[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
[3]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张房慕.云笈七签[M]//道藏(第2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6]张承宗.六朝教育格局多样化[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5-10.
[17]于振波.长沙走门楼初探[M].[中国台湾]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
[18]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责任编辑:丹 涪]
K235
A
1674-3652(2017)04-0077-05
2017-01-11
郭超,男,河南信阳人。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