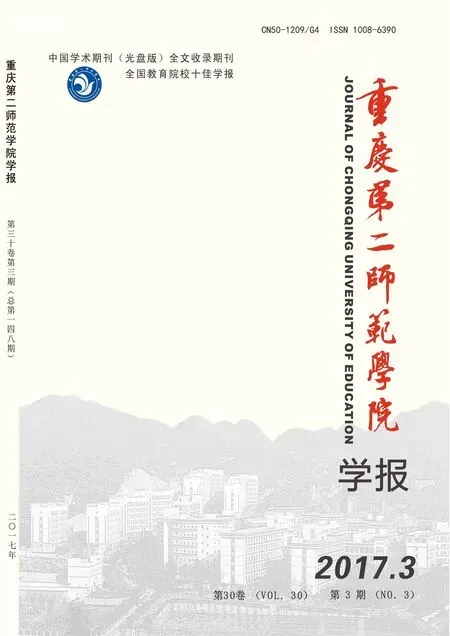历史名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信仰问题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学术思考之三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 400067)
历史名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信仰问题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学术思考之三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 400067)
从《新新游记》残本中,可以发现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有关《圣经》的基本观念及其“见证基督”的巨大热情,而其临终遗嘱有关十字架的特别安排,更是其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认同的体现。如果剥离其基督信仰,刘子如就不是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了。刘子如人生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基督新教信仰实践的达成,而其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更体现了当下两种价值关系中信仰问题的研究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历史名人;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价值取向;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1924年环游世界,历史文献显示,这是一个虔诚的中国基督徒环球“全程证道”之旅。先看几条历史文献:
1.1939年1月1日,《前线旬刊》第13期《大时代——战地服务记》载:“十年前(即1924年——引者)曾一度游历欧美各国,宣传基督博爱精神,备受各邦人士欢迎。”[1]2.1998年4月20日,定居加拿大温哥华的台湾运康公司董事长葛家瑗和夫人,为刘子如生平事迹撰写近3000字的评语,其中涉及刘子如游历欧美时的证道演讲。葛家瑗夫妇认为,刘子如对《圣经》的认识很深,境界很高,在国外学校、教堂宣扬福音,“令会众感动立愿。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更上电台证道、演说,有专人翻译”,还不忘考察国外的现代化建设与“都市景观”,“既爱上帝又爱国”[1]P377,让人非常敬佩。3.《綦江县私立青山孤儿院史话》记载:刘子如1924年应英属加拿大教会邀请,出席联合布道团百年纪念大会并主持开幕式;应英国基督教美以美会邀请,出席纽约召开的董事会并应邀发表演讲,“近一年自费环球考察,每到一地必发表演讲。在渥太华等地受到了贵宾级的隆重欢迎,为国争了光”[1]37。
可见,刘子如1924年环球之行的目的,应与英属加拿大教会、英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邀请分不开。刘子如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机会,借教会联系的方便安排落实到有关国家的宗教考察计划,并加上相应的国情了解与顺道的旅游,让这次环球旅行体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笔者细读《新新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残本[1]294-341,对此印象颇深。这些历史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刘子如环球游历中自觉的基督徒身份认同。
一方面,即台湾运康公司董事长葛家瑗和夫人记叙的“演讲证道、宣扬福音”。这是《游记》重点记录的内容之一,共计24次,远超有关国家旅游景点(不到5次),考察与教会有关的商业、慈善、教育、医疗机构(不到10次),工农业(不到5次)等的记录次数。《游记》残本所记加拿大境内的游历活动,即可见证其“演讲证道”的特点。如,卷三第十章第九则:“午前先在意大利人会堂演讲,继至一堂讴诗后,到大会堂礼拜,以‘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为题目。午后亦先至中华青年学生会演说……后至美以美会、青年会演说……余以‘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字为主,鼓励……归入正轨也。”再如,卷三第十章第二十三则:“本日演讲三次。午前在大堂主讲,听者七百余人。午后行青年礼拜,听者八百余人。夜间亦在大堂主讲,听者千余人。每次讲毕,辄有多少人士等候握手……”再如,卷三第十章第三十一则:“余住加拿大境内二十余日,遍历各城演说,常闻人云:较一干西人返国之报告尤佳。各埠报纸每日均载有子如演说之事。在火车站,在码头,在街市所(遇)人士之友人,无不向余握手也。”这些记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刘子如《游记》记录了演讲《圣经》教义见证的基本内容,如第十章第九则:“以‘马可福音’十四章四节为题目”,“‘约翰第一书’四章之爱字为主”等;也有记录话题具体内容的,如“余略论本身自历明证,兼毛宅三、段青云之信道史”(同上第三十则)。其次,记录现场听众的大概人数,热情程度等,说明自己《圣经》见证的实际效果。第三,记录媒体及舆论综合评价个人见证的主要观点与社会反响。
另一方面,现存文献信度较高的《刘子如毁家助善实录》(1934年1月12日出版)收录的《刘子如自述》一文,直接袒露了一位虔诚基督徒助善动力来源的心路历程,及其宗教慈善事业的全部经济账目。个人信教、经商与慈善关联均有具体表白[1]251-254。查阅《刘子如毁家助善实录》[1]251-277提供的相关信息,刘子如成为商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的社会影响,与其信奉基督新教的信仰实践[2]息息相关:1896年刘子如结婚一年后“入教归主”,成为基督新教“伦敦会教友”;1898年起经营卜内门洋碱业务等多种商业活动均告失败,后转代销缝纫机业务并在1901年任美商胜家公司缝纫机四川总经理;1913年兼任江西南昌、九江胜家公司经理,开始将商业盈利按照基督新教伦理回报社会,创办重庆孤儿院等慈善机构;1921年创办中华基督教重庆青年会,“自传”基督教义,遵循基督新教教旨“爱教进而自觉爱国”,“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哪年打日本,就去参加”[1]412,表现了鲜明的国家认同价值取向。不难看出,刘子如在个人商业经营步步成功的同时,加大回报社会力度,举办重庆孤儿院等慈善事业,在西南教区名声日隆。直到1924年,应英属加拿大教会邀请,出席联合布道团百年纪念大会,再应英国基督教美以美会邀请,出席纽约董事会并应邀发表演讲,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福音派基督新教的全球知名人物。《刘子如自述》还以个人成为基督徒的经历为线索,重点开列按照基督教义开展社会慈善事业的“实洋”账单,也是其个人基督徒身份认同信仰实践的最有力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刘子如的国家认同不仅体现在其《游记》关注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行动与内心表白方面,而且表现在抗战初期的爱国举动上。其时,刘子如以自己的社会声望组建重庆战地服务团,搁置个人参与的商业活动以及家庭事务,带团到前线劳军三年。有媒体评价说:“对于这样一个家境富裕、生活安逸且年近七十岁的老人,出此举动,不免有些难解。然而事实上这位‘老当益壮’的英雄……一年多当中,领导着重庆战地服务团男女青年数十人,由重庆出发沿长江赣浙皖诸省……担起了民族求存的责任。”[1]411-412由此可见,历史名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国家认同,存在两种价值取向(即身份认同价值取向与国家认同价值取向)的关联认识关系,它深刻影响着历史名人信仰的实际表现,成为当代中国历史名人研究的难题之一,很有普遍性。这就是本文提出的,在地域名人文化研究中,作为“历史名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信仰问题”的基本含义。譬如,重庆抗战时期的历史名人,超越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阶级属性、政治面貌与文化影响等的爱国行动,是其国家认同的社会行为,但其阶级属性与政治面貌等身份认同的信仰选择,我们可能难以得出正面的肯定性文化评价。回避这个问题的学理探讨,不利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因为身份认同的价值取向,是个人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展示,往往会跨越时代、社会的局限,顽强地体现在个体生命历程的最后阶段。具体到刘子如而言,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尽管刘子如晚年身体每况愈下,但临终嘱咐字字清楚,要求一定要在其坟茔上放置十字架[1]485。这表明刘子如平生视其基督信仰高过一切,基督信仰成为其终极价值取向,也是他事业成功之后,一切社会行为的精神动力之一。笔者认同戚功的观点[3],如果避谈刘子如的基督信仰问题,那么评价其现代化思想、爱国精神、商业头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慈善事业、抗战热情以及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当下意义等,就难以说清楚。因为一个剥离了基督信仰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爱国者与实业巨商的刘子如,就不是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了。刘子如人生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个人信仰实践的不断激励,而其国家认同价值取向表现的高昂爱国热情,则体现了对两种价值取向关系的认识在当下的巨大学术意义。
二、《圣经》观念、“见证基督”与十字架:刘子如基督徒身份认同的三个要点
如前所述,刘子如《游记》残本对环球之行“演讲证道、宣扬福音”的有关记载中,《圣经》是刘子如“见证基督”的基本依据,更是他作为一位基督徒身份认同的重要特征之一。
除了《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第九则日记之外,刘子如提及“《圣经》见证”的还有某卷第八章“英京之汗漫游”第七则:“至卫斯理总会堂听讲,系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之事。”所记当是在教堂听讲《圣经》。而《游记》直接出现“见证”一词的有两处——卷三第十章第三十则:“十四号晨,在大堂见证,听者千有余人。午后课书礼拜三处,每处千余人。”“课书”即主讲《圣经》,到了三个讲经处,听者都很多。《游记》卷三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第五则:“夜,年会请各地代表于大学校晚餐,由余见证,大得感动。”间接提到“见证”一词的也有两处——《游记》卷三第十章第二则:“请余备讲自历明证。”《游记》卷三第十三章第十则:在浸礼会讲道“因余非传道之人而能为主做证,故使彼辈受感匪浅”。其中的“自历明证”与“为主做证”,与“见证《圣经》”内涵相同。
刘子如以“非传道之人而能为主做证”,对《圣经》的崇拜、熟悉、认知、理解与个人实实在在的信仰体验是基础。刘子如早年在重庆市渝中区木牌坊伦敦会福音堂聆听《圣经》,成为其信奉福音派基督新教的开始,奠定了其身份认同的基础。基督福音派坚信,信仰及其实践的最高与最终权威只能“源于《圣经》”,上帝之道的《圣经》,是“最高与最终”的规范或原则。这样,福音派认同的信仰权威在《圣经》之中,《圣经》权威的性质成为信徒关注的中心。当基督徒们对《圣经》的理解出现争议的时候,上诉的“最高法庭”在哪里呢?依据神学家詹姆斯·帕克的论断,权威仍然“来自于上帝的启示,上帝对现在的人所说所做的一切,也就是他通过耶稣基督而对世界所说所做的一切,而《圣经》就是对上帝所说所做的权威性见证。”[4]
上述话语的内在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圣经》是上帝之道,当然是完全真实可信的,由此成为信徒思想与生活的最终权威。《圣经》内蕴的教诲,就是上帝对教会与信徒言说的“道”,要明白了解“上帝的意思”,人们就必须求助于《圣经》中“书写的道”,个人的领悟与体验自然成为其中的关键。因为由上帝“默示而来的《圣经》,是完全而明白的神启的记录、解释和见证”[4]。这样,福音派神学当然将《圣经》视为发现宇宙之“道”的终极所在,相信它才是永久保存救赎福音的“神授文献”,是判断基督徒信仰实践的最高权威。
有意思的是,刘子如《游记》有两则记录似乎暗合研究者上述对《圣经》权威的论断。一则即第八章“英京之汗漫游”第七则:“至卫斯理总会堂听讲,系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之事。”一则即卷三第十二章“再赴加拿大”第四则:“大雨未出,特记多能(伦)多基督教发轫之历史……更忆余父母所奉之瑶池教(指佛教——引者)纯系诈欺取财之法门。”“余今入基督之门,始悉大道不分中外”,断然放弃佛门而认信福音派基督,这与刘子如的信仰实践过程息息相关。“属灵之事”与基督徒“灵性生活”相关联,刘子如对福音派新教的信仰实践深有体会[5]。他19岁时为了个人的前途,孑然一身“负气出走”至重庆主城区。正当他举目无亲,饥饿难耐,命悬一线之时,蒙临江门下红庙当家和尚收留,天天与庙内菩萨抬头不见低头见,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与刘子如在家里目睹父亲执着于佛像崇拜却没有得到佛道感应的经历有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刘子如皈依福音派基督新教成为“伦敦会教友”四年,一心信奉《圣经》教旨,虽然经受生意场上的一连串失败,却能阵脚不乱,在耶稣基督信仰实践的引导下“三十而立”,此后商业经营一帆风顺。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属灵之事”,有刘子如自身“证道”的“属灵”经验,当然倍感亲切。
可以说,“以《圣经》为中心”见证基督的记录,在刘子如《游记》残本中处处可见。刘子如近一年的环球之旅,从一位福音派基督新教信徒所为而言,就是“以《圣经》为中心”环球见证基督的信仰实践。因此,有关记录虽然简短,却往往直接道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布道”“灵性”对《圣经》教义的认知、理解与体验。刘子如在有关文字表述中,对见证基督信仰实践的现场效果与心情记录很多,如《游记》卷三第十章“初赴加拿大”中的几则。第二则:“午后,赴课书礼拜堂欢迎会,请余备讲自历明证,由彭普乐、唐医生二君移译英语,大受欢迎,争行握手礼者,不计其数”。第十六则:“入堂礼拜。沿街见各商店门前首悬余肖像下注明,今日在何堂演讲,甚至通衢繁区亦悬余放大之像,注明如前。余于晨间在少年礼拜堂演讲,有三百余儿童入听……其间向余握手言欢者指不胜屈”。第二十四则:“夜在大堂主讲。未讲之先,有四百余人同余握手,亲爱至极。受感者云:余愿尽忠至死也。”
福音派基督徒倾心见证基督,“布道”“灵性”“事工”的相关信仰实践,体现特定的神学内涵。简而言之,见证基督的“见证”,即“为福音真理所做的见证”。福音派信徒认为,他们是牢记耶稣“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诲的信徒,因此坚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福音派宣教主要关注普通信徒,认为传播福音不仅仅是专职教牧人员的工作,也是每一位信徒的神圣使命。这种“将一切信徒皆为祭司”的观念,可以将福音传播推向极致。而有关福音真理的见证,还被神学家视为“灵性成长”的主要手段与方式,“它为个人的灵性状态提供了一种公开的指标式标志。福音派信徒极为乐于同他人分享福音信仰的现象,甚至成为福音派限定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4]。《游记》卷三第十三章第十则云:“因余非传道之人而能为主做证,故使彼辈受感匪浅。”可以认为是上述神学阐释的最好例证。
如果说,1924年环球见证基督福音,让刘子如福音派基督徒身份认同感得到极大增强,成为1925年子如先生“毁家助善”——为重庆社会公益事业献出全部私人财产的直接原因,证实其福音基督新教信仰实践“实质性”开启的话,那么他的临终遗言有关十字架的嘱托,则有力证明了其福音派身份认同信仰实践的事实存在。至于为何选择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作为基督信仰的象征和标志,福音派新教神学的论断有三:其一,“上帝的爱与正义的终极启示”;其二,“对恶的决定性的胜利”;其三,基督徒“得救的根基”“牺牲的最高榜样”“奉献的最有力感召”。笔者认为,有关话语的内在逻辑如下:人原来与神关系和谐,因为人的罪过而与造物主疏远,甚至整个人性完全堕落。上帝通过十字架的“神秘作为”,标明神对世人可能“重新悦纳”。由于上帝的“圣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救赎,人得以重新站到上帝面前,在“信仰与爱”的侍奉中与上帝和好。十字架为上帝的子民开启了一条唯一的现实的自由通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彰显“神爱世人”的核心内涵,确立起基督在信徒崇拜与宗教生活中的“中心性”。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最终成为“福音派神学与灵性生活中的核心意象和观念,它遍及信徒之宗教信仰与实践的一切方面与领域”[4]。
刘子如不是神学理论家,而是福音派基督新教的信仰实践者。选择十字架作为自己身份认同象征符号的价值取向,可见他对福音派基督信仰所达到的认识境界,这也自然留下福音派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有关时代影响的痕迹。据史料记载,福音派基督新教在重庆的传教活动始于1888年,刘子如在1896年“入教归主”。1901年至1920年,是福音派教会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在华传教事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据教会统计资料,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开辟的教堂总数仅次于广东、江苏,教徒人数超3万人,四川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总数已位列江苏、直隶、广东之后,“1920年成为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发展巅峰”[6]。值得注意的是,这20年也正是刘子如个人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福音派新教在四川的传播出现了问题,并很快走入低谷,而正处于个人事业峰值阶段的刘子如,却十分渴望基督信仰的见证机会。1924年他能成为中国西南教区数万信徒的唯一代表,应加拿大教会邀请,出席世界联合布道团百年纪念大会,又应英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邀请,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董事会并发表演讲,可见其在世界福音派基督新教界的代表性。
三、身份认同概念内涵的辨析及其与国家认同价值取向关联的信仰问题
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界关于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等的“认同研究”不断深入,成果颇丰。本文限于篇幅,难以对相关学术成果进行全面梳理,仅就有关“身份认同”概念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加以比较,提出历史名人文化研究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关联的信仰问题。
《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一文立足于社会学的“身份/认同概念的发展”角度,从解析“身份”与“认同”概念的特定内涵开始,追踪“认同”概念研究20年的发展轨迹,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提出了研究者的学术论断。“身份”,当下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关联,主要用于揭示社会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目标,似乎集中于身份认同研究与社会认同理论等方面。英语“identity”,有本身、本体、身份即“我是谁”和“相同性、一致性”有关事物认知两个方面的含义。认知“我群一致性”必然伴随“他群差异性”。因而,“对身份的研究,也就是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关系的研究”[7]。追踪社会学领域中影响身份/认同研究的五条理论脉络(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G.H.米德和符号互动论、舒茨和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和批判理论),可见学术界关于身份/认同研究不同阶段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是身份/认同研究发展的“关键时期”,种种社会运动的不断涌现,促使相关研究扩展到非常宽广的领域;至20世纪70年代,身份/认同研究“更多应用于经济研究”,同时“逐渐理论化”。这样,学术界几十年努力探讨身份/认同的内涵发展,认同从“心理分析的技术术语”,转型为“社会学研究的综合概念”。认同从个人心理描述,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认知,表明身份/建构的过程特点,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所以,认同研究应该置于“时代的情境”之中,兼顾历史文化的影响与当下具体社会结构情境的制约;认同离不开与他者关系的建构,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认同的变化;个人认同多重,身份认同多重,多重身份管理成为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任务。总之,身份“多重认同是分层次的,在不同情境下会侧重不同的认同”[7]。
《上海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及成因分析》一文将社会学的身份/认同理论,应用于宗教社会学具体案例分析的项目操作,对上述内涵复杂的身份/认同概念作了简化,因为研究目标的清楚确认,其内涵的核心认同要点得到明确认定。关于“身份认同的含义”问题,研究者先从应用的术语词组说起,重点探讨身份认同英语词源的本义,最后落实到汉语成语的对应理解,这个思路有利于解决理论应用问题的讨论。
认同问题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如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性别认同等[8]。据笔者了解,近年来涉及的认同热点问题,还有国家认同、社会认同、族群认同等。因为认同一词在日常生活用语的普遍应用,一些学者常常不加学术界定直接应用于问题研究,每每造成歧义。但只要按照学术规则,明确认同研究实际对应的研究对象,认同问题具体确认,诸如基督徒身份认同、刘子如国家认同的基督徒身份问题,认同研究就不会像一些文献资料那样给人似是而非的感觉了。据相关资料,“认同”一词是外来语,译自英文单词“identity”,现代汉语同时译为“身份”和“自我同一性”。1989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英汉大词典》中的“identity”词条有如下释义:名词。1.身份;本身;本体。2.同一人;同一物。3.同一(性);相同;一致。4.个性;特性[9]1601。笔者认为,“identity”词条释义有两层含义:同一性与独特性,表现为相同时间跨度中一致性及其连续性。“认同”一词之重要在于它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实质关系。相似与差别就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认知方面。一个人经历前后的同一性与一个群体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他人的差别。当“identity”用于突出时间不同,就译为“身份”;为了表明同一性的存在,就译为“认同”。因为是一个概念,它不是词义分裂的存在,所以也变通译为“身份/认同”的组合词,以兼顾“identity”内涵的个体和群体意义。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identity”译为“认同”比“身份”动态意义更显豁,英文的原意在后现代立场上保留更清楚。因为“从后现代来看,身份本身变得既不确定,多样且流动,正需要一个‘认同的过程’去争取。身份来自认同而认同的结果也就是身份的确定或获得,成语‘验明正身’即有此意”[8]。例如,刘子如1924年的环球见证基督,一年之中在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城市见证演讲70余次,可以认为就是他作为基督信徒造成世界影响“认同的过程”之一。
因为对认同问题的实际考察与相应学科知识的应用限制分不开,不同学科中“identity”一词的译法也就不一样。例如,心理学译为“自我同一性”,哲学译为“自我认同”,社会学和文化学则译为“身份认同”。不同译法所侧重的意义有所区别,但“身份”和“认同”两个义项始终包含其中。对于历史名人的文化研究而言,通常运用“身份认同”相关的社会学、文化学学术研究成果。例如,刘子如基督徒身份认同问题,探讨的是刘子如对其基督徒角色合法性的确认,人们的有关共识以及影响的社会关系。因此,刘子如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判断,应符合个体基督徒身份认同的以下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个体能明确自己所属群体。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身份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它是个人系列个性的统一,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整体标识,他是个人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0]58刘子如的基督徒身份认同,其临终前有关葬式十字架的要求应该最有说服力,这是刘子如 “我是谁?”——“我是基督徒”的最后确认。
第二,个体能明确自身在群体中的角色地位及其承担的责任、义务和权利。这是因为身份认同是借助于身份系统功能实现的,是社会成员的类别区分。不同类别角色被赋予不同的权利、责任及义务,由此形成群体公共生活的“支配与服从”的社会秩序。《刘子如自述》就是刘子如作为一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明确其在群体中的角色和地位、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其应具有的权利。对于这样的基督徒身份自我认同的范本,这里没必要重复展开分析了。
第三,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上述两个判断标准,更多考虑的是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而第三个标准则有关身份认同的内在价值。社会心理学认为,群体本身有四个特点,即“角色、地位、规范、凝聚力”。群体规范的认可以及凝聚力的产生,都必须有“价值观的支撑”[8]。毋庸置疑,身份认同的第三个“判断标准”非常重要。就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研究的文献资料而言,符合身份认同“外在表现”判断标准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方面的资料相对多一些,《刘子如研究与史料选集》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而除了《游记》残本、《刘子如自述》之外,有关刘子如基督徒身份认同内在价值的史料却几乎没有,这是非常遗憾的。
抗战爆发初期,刘子如自发组团前往浙皖前线劳军三年,成为他爱国情怀的集中表现,得到国民政府的褒奖,这与他的基督信仰有关联吗?刘子如所表现出来的抗战激情,就是他践行国家认同的证明。有学者指出,定义国家认同这个社会文化现象研究的专属概念,实际上有两种表述方式:第一是看“谁认同”,以描述心理过程去定义,明确所属国及其心理认识活动的经历。一个人对国家产生认同与热爱是渐进的过程,最后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支持和依赖”。第二是看“认同什么”,主要包括所认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国家主权”等核心内容。概而言之,“国家认同是一个人或群体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之后形成的一种对其认可与接受,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的情感”[11]。学术界一般将国家认同划分为文化性与政治性两种情感类型:“文化性”国家认同,是对国家的“主流传统文化、信念”等方面的认可程度;“政治性”国家认同,则是对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等方面的认可接受程度[12]。我们知道,政治学研究首次引入国家认同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民族主义革命后,那时国家认同的政治学意义逐渐得到展示。现代国家非常重视国家认同公民意识的教育。从学理上而言,一个人出生即具有所属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在这个人随后的人生经历中,国家公民意识产生,并逐渐形成对所属国家“历史、文化、主权及信仰”等的认同。一般而言,一个人确认了自己的归属国,国家认同感会随着“分享”其所属国的文化传统而产生,而且“认可与服从”所属国法律、制度、领导人等国家的“权威要素”,产生依附于所属国的归属感以及效忠心理和行为。一个公民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自愿归属于所属国家的时候,就有特定的“乡情”依恋。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就会自觉扛起武器保卫国家。国家认同政治教育重要性的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依靠这种国家认同的公民意识”[11]。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信仰实际上成为刘子如国家认同自觉表现的指南。信仰基督教对“自我的肯定”,这让刘子如的自我意识得到自觉建构。笔者认同基督教文化影响研究者的论断,即基督教信仰确证“个体存在的价值和独特性”,强调责任感和群体归属,对于公民身份认同的形塑不仅仅具有外在性意义,而肯定自我的存在与价值,在现代中国早期意义非凡,因为这可能促使公民个体真正“从内心产生对身份的自我认同”[8]。总之,一个人自我认同自觉达成的经历,应有一个三阶段(层次)进步的完整过程:个体经历“群体认同”,再到“社会认同”,最后才可能真正抵达“自我认同”。而“个体存在的价值和独特性”没有得到确证,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基石的公民就不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子如基督信仰的身份认同,成就了其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国内福音派基督信仰的社会实证研究的学术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即一个人如果笃信基督,他最关心的将是自己与所属群体与上帝的关系。如此执着的关注,会成为这个人及其所属群体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坐标系”,最终成为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毋庸置疑,刘子如的信仰经历就是最好的说明。从主观上来看,基督徒因为对上帝驯服形成其“优良品性”;而这种优良品性在客观上却“表现为对社会的驯服”,甚至对国家的忠诚。这样,“基督徒通过与神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实现了与人、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8]117的历史名人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信仰问题,的确值得深入探讨。
[1]重庆历史名人馆编.刘子如研究与史料选集(下)[C].内部资料.
[2]赵心宪.刘子如的基督教信仰——重庆历史名人《刘子如自述》文本解读与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313-319.
[3]戚功.关于倡导子如精神的五点建议[G]∥重庆历史名人馆编.刘子如研究与史料选集(上).内部资料.
[4]董江阳.现代基督教福音派思想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7.
[5]刘子如.刘子如自述[M]∥重庆历史名人馆编.刘子如研究与史料选集(下).内部资料.
[6]刘稚旖.简论近代西方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60-62.
[7]王莹.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0-53.
[8]华桦.上海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及成因分析[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9]英汉大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1]陈光军.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及二者的关系[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2):52-56.
[12]马得勇.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J].世界民族,2012(3):8-16.
[责任编辑 文 川]
2016-12-09
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武陵地区传统聚落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12CM2038)
赵心宪(1948— ),男,重庆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巴渝文化名人。
G112
A
1008-6390(2017)03-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