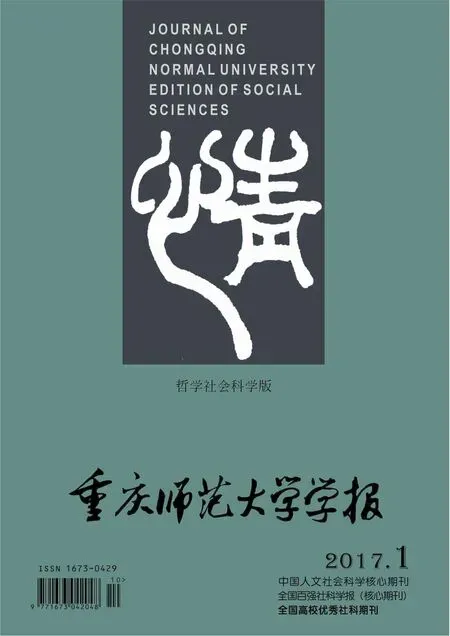棒球棍、青痣、井
——《奇鸟行状录》意象浅析
杨 晓 莲 沈 荣
(1.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1;2.南通智联外语培训中心,江苏南通 226000)
棒球棍、青痣、井
——《奇鸟行状录》意象浅析
杨 晓 莲1沈 荣2
(1.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31;2.南通智联外语培训中心,江苏南通 226000)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从这部作品开始,村上小说由前期所关注的内心世界转为更开阔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奇鸟行状录》的三个核心意象——棒球棍、青痣和井,与作品抗击暴力的主题相挂钩,最后回到日本现代社会中不断传承的暴力体系的分析,以及作品对于侵华战争责任的反思,讨论作者通过这三个意象所要表达的主题:抗击暴力、铭记历史、反思战争责任。
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棒球棍;青痣;井
村上春树是当代世界文坛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他的《奇鸟行状录》于1996年获得第47届读卖文学奖。2009年获得了具有“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之称的耶路撒冷文学奖。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评价该作品是“村上春树创作的转折点,也许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伟大的作品”[1]185。在小说中,“作者完全走出寂寞而温馨的心灵花园,开始闯入波谲云诡的广阔沙场”[2]。《奇鸟行状录》“是一部正面描写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暴虐罪行的小说,作为战后出生的作家,这是村上在对同代及下一代人讲述战争之于血肉之躯的恐怖”[3]。这是一部得以窥见日本黑暗、残暴的过去的作品,对于认清当今日本社会国家体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倾注较多心血的作品。村上曾坦言:“那个故事在等待我来写,我所做的不外乎把它顺利地解放出来。”[4]《奇鸟行状录》由横、纵两条情节线构成。横线是主人公“我”——冈田亨寻找突然下落不明的妻子,其中牵涉到以妻子兄长绵谷升为代表的日本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邪恶。纵线是间宫中尉对于诺门坎战争的回忆 ,以及因与赤坂肉豆蔻、肉桂母子相识从而陆续浮出水面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往事等,这部分较为集中地表现了战争背景下的暴力。在小说中,横线纵线交错展开,表现了作品抗争暴力的主题。
目前学界对《奇鸟行状录》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战争和历史方面,而作品的意象还没有被充分研究。所以,本文试图探究与小说抗争暴力主题紧密相关的三个核心意象:棒球棍、青痣和井,来分析作者通过这三个意象所要表达的主题: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反思,对于历史的铭记以及对于暴力的抗争。
一、棒球棍意象——承载暴力和抗击暴力
棒球棍是《奇鸟行状录》这部作品的重要意象,它一方面既是暴力行为的承载物,也是打击暴力的武器。
在小说中出现过两根重要的棒球棍,一根由“我”从一位民歌手处获得,他不明不白地对“我”发起攻击,“我”从其手中夺得并保留了下来,作为最终对决的武器;另一根出现在纵向情节中,肉豆蔻的父亲是一名脸上长有青痣的兽医,他曾亲眼目睹日本兵用棒球棍将一名中国人打死,而本该已死的中国人却死死抱住兽医不放,想要将其拖入尸坑。
此外,小说中还多次出现过与棒球棍有关的暗示,如邻家女孩笠原May在院中晒太阳时身边放着的一根球棍,照她的话说只是因为握在手中安心;再如,“我”准备摆脱所处的险恶环境,意欲逃至所谓庇护所的希腊时,却被一个带着棒球帽的大块头“猛地抓住胸口一抡”[5]357;而在纵向情节中,被处决的中国人更是身套棒球服,这些暗示都不禁让人联想到棒球棍与“打”这一动作的关联。
棒球棍作为一种体育器具,由于其独特的长水滴型设计,给人良好的握感,方便持有者做出“打击”的动作。然而小说中的棒球棍却全部用于打人。第二部第17章中,“我”追随曾有一面之缘的流浪歌手时却被其用棒球棍偷袭,“我”夺过球棍反击后仍“欲罢不能”,而被“我”殴打的人竟然“呛着自己的口水笑得嗤嗤有声”[5]389,仿佛暴力这件事情是可以传染的。“我”在打完人后下意识地将棒球棍带走,晚上睡觉时“右手依然攥得紧紧的作格斗状”[5]390,这种反应意味着暴力是融于人类基因之中的。棒球棍担当的虽然只是“打击”这一动作,实际上还承载了人类对于暴力行为的放纵,甚至是渴望。
在纵线情节中,脸上长有青痣的兽医目睹日本兵处死四名从“满洲国军官学校”逃跑的中国学生,四人穿着带有编号的棒球服,其中三人被刺刀刺死,“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5]609,唯独最后一人被下令用棒球棍打死,因为他在逃跑前用球棍打死了日本教官。在这短短的行刑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刑具:枪、刺刀和棒球棍。枪是现代战争中的武器,刺刀和球棍在一定意义上则属于冷兵器。棒球是日本社会中极其流行的一项竞技体育,美国有常春藤体育联盟,日本则有甲子园。这是一项几乎融入日本人血液中的体育运动,不难将其与大和民族的某些精神内核联系在一起。如同武士道精神要通过武士刀这样一种外化的兵器实体表现出来一样,人类内心深处的暴力倾向也被灌注到棒球棍中。棒球棍选手在击球区的预备动作是下半身半蹲,上身右转面向前准备击球,这与武士手握武士刀的动作是极其相似的。“傍晚强烈的阳光把球棍粗大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面”[5]612,这时的球棍分明就是砍刀,只不过比起寄托武士精神的刀,这幅球棍表面已布满凹痕,沾有皮肉毛发。人们内心的暴力通过用棒球棍打人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棒球棍是承载暴力的工具。
棒球棍表面上看只是一件打人的凶器,作者在其中还加入了是非观的思考——打人是暴力,抵制暴力却也需用暴力,所以在《奇鸟行状录》的第三部高潮部分,棒球棍成为了打击暴力的武器。“我”把从民歌手中夺来的棒球棍带下枯井,像“进球区的棒球手双手紧紧握住棍柄”,“用棍头轻轻叩击井壁以测其硬度”[5]469,之后“我”发现可以由“井”进入妻子被囚禁的房间,最终的决斗眼看就要到来。此时的棒球棍俨然由承载暴力的凶器变成了打击暴力的武器。作者的善恶观也由此得以窥见:有恶就要抗争。但外化为棒球棍这件冷兵器的抗争精神,有可能成为一发不可收的暴力,也有可能使斗士在打击暴力的斗争中胜利。
作品中描写“我”与恶斗争的情节颇耐人寻味:对方“那一团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使用的是匕首,“我”使用的则是棒球棍,双方就这样在黑暗中进行一场日本武士对决似的战斗。在黑暗中,“我”能伤及对方,对方亦可刺到“我”的情节也颇具东方武打对决的特色,很明显作者在追求的不是昆汀电影式的暴力美学,不是把滴着血的肉翻出来给读者看,但读者分明能够透过纸页闻到血腥味儿、暴力味儿和死味儿。最终棒球棍击中了“那个东西”,胜过了更具杀伤力的匕首,这是一种暴力抗击另一种暴力的胜利。
暴力已经融入了人类的基因,作者通过棒球棍这一暴力的外化物从施加暴力到打击暴力角色的转换,丰富了整部作品抗击暴力主题的内涵。
二、青痣意象——铭记历史的印记
青痣是《奇鸟行状录》中非常值得思考的意象。作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比如让这块青痣隐隐发烫、作痛、低烧,甚至让它活起来,试图唤醒人们对于遗忘过去的屈辱感和与邪恶作斗争的命运感。
小说中有两个主要人物的脸上长出了一模一样的痣。在横线情节中,“我”在妻子失踪后下到井中思考与妻子的相识相知,并发现自己可以透过井壁到达妻子被囚禁的宾馆房间,升井后发现自己的右脸长出了一块婴儿手掌大小的青痣。“我”带着这块青痣与恶进行决斗,获得胜利后青痣消失不见。在纵线情节中,肉豆蔻向“我”讲述其祖父——一位右脸长有一块青痣的兽医的见闻。他见证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在侵入“战前的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暴力。但是面对暴力的演进,兽医感受到的“寒气”却永远没有从其体内散去。
青痣在作品中主要有两个象征意义:铭记历史的印记和区分庸人与斗士的标记。
青痣是屈辱感具体化的意象,每个人犯下罪孽后都会背负上一份屈辱感。证件照摄像师也只能用粉将青痣暂时盖住,使其显得不那么明显;“我”曾妄图逃往理想中的乐园希腊以重新开始生活,但带着这样一份屈辱是行不通的;邻家女孩笠原May年轻时因为自己的贪玩和一时的恶意造成恋人去世,她也一直带着眼角的疤痕活在忏悔之中。“我”触及她的伤疤以及她仔细舔舐“我”的痣,都是接受这份屈辱感的表现。作者通过这样一大块青痣的形式将这份屈辱感烙在脸上,体现了不忘屈辱与坚定斗争的决心。
村上通过青痣与历史的关联,以青痣代表屈辱感,探讨了何为真实的历史。“我”在第一次升井后,加纳马耳他问“我”身体是否发生了变化,“我”曾打趣道:“要是背后长出翅膀,估计再不情愿也还是察觉得到的。”[5]316但加纳马耳他告诫道:“了解自身状况并不那么容易。……人无法以自己的眼睛直接看自己的脸,只能借助镜子,看镜里的反映,而我们只是经验性地相信映在镜中的图像是正确的。”[5]316“自己的脸”指本民族的历史,“自己的眼睛”指本民族对于历史的审视。大多数日本人和“我”一样,认为只有“长出翅膀”这样的大变化才能被注意到。部分日本人在战后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去,但同时各种否认战争责任的呼声也甚嚣尘上,历史修正主义和鼓吹“国家正史”的民族主义开始泛滥,使得一个国家在自身身份认同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村上在《奇鸟行状录》中表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因而自己构建了这样一部“拧发条鸟编年史”(《奇鸟行状录》的日文原题为「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ねじまき’意为‘拧发条’,‘クロニクル’(chronicle)意为‘编年史’,直译应为《拧发条鸟编年史》),以横纵线交替的形式筑成一部历史体验录:从间宫中尉那里,“我”得知了暧昧不清的诺门坎战争,从赤坂肉豆蔻、肉桂母子处,“我”得知了发生在中国东北的血腥事件。棒球棍、青痣和井意象将“我”与历史的尘埃联系在一起,使“我”感受到应该铭记历史,承担起对历史的责任,正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这种源自过去,迎面走来,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中理解自己”[6]。
无论脸上长出的青痣是何物,它起到的起码是区别作用——区分脸上有痣的人和没有痣的人。作品中有多处关于有痣与无痣之人的对比。在横线情节中,路上的行人会以“那位有痣的大阿哥”称呼“我”;干洗店的老板看了一眼我脸上的痣,丢下一句“够你受的”;拍证件照的摄像师对“我”的脸又是打光又是盖粉;美容师看了一眼镜中的“我”,便“活像看着一碗满满敷着一层芹菜梗的盖浇饭”[5]463。但是“我并不觉得它难看亦不觉其污秽”,并且“意识到必须接受它”。在纵线情节中,脸上有青痣的兽医见证了日本兵在苏军即将攻进中国东北之际枪杀动物园中动物,以及处死中国逃犯的情景,他自始至终带着这块青痣经历了恶行,却无从逃脱这彻头彻尾的恶;而“我”却带着这块青痣与恶进行斗争,最终夺回妻子。作者通过多对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用痣将庸人与斗士区别开。一方面,庸人经历恶却不以为意;另一方面,斗士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现实和历史的使命感,带着一份屈辱进行斗争。
这一块婴儿手掌大小的痣将上世纪30年代的满洲、外蒙和80年代的日本联系起来。在第二部第28章中有大段关于兽医对于“命运形成宿命式达观”的描述:“小时候他非常憎恶他人没有自己独有的这块痣。……若是能用小刀把那个部位一下子削掉该有多好。但随着长大,他渐渐找到了将脸上的痣作为无法去掉的自身的一部分,作为必须接受之物来静静予以接受的方法。”[5]602兽医认为世界是被命运的巨大力量统治着的,他虽然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宿命论者,但他也不曾实际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单独决定过什么,于是兽医看着动物被残忍射杀,看着中国逃犯被以极端的方式杀害。命运感使得兽医被动地接受着自己身处的历史,他感到无能为力,觉得人们不过是被有着“自由意志”外形的历史欺骗而已,因此兽医始终都没有摆脱这股强大命运感的束缚。
而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我”并不觉得它难看亦不觉其污秽。“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必须接受它。”[5]463虽然两人都接受了脸上的痣,但“我”带有很强的战斗性:“我”能够一眼认清绵谷升虚伪表面下潜藏的恶,看出恶的流动和传承。“我”完全是一个斗士的形象,不同于村上小说其他主人公遭遇离奇事件而表现出的“卷入感”和无奈,比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精算师和读梦者,以及《1Q84》中的青豆和天吾,《奇鸟行状录》中的冈田亨主动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决心与恶势力斗争。
作者围绕青痣意象展开有关情节的写作时主要运用的手法是对比:遗忘过去和铭记历史,斗士抗争和庸人妥协等,以此呼唤要铭记历史。
三、井意象——自然和谐的象征
小说中出现过两口重要的井。在横线情节中,一口井位于“我”家附近的空宅内;在纵线情节中,另一口井出现在间宫中尉的回忆中。“我”家附近有一幢不断发生怪事的空宅,院里有一口枯井。妻子失踪后,“我”下到井中回忆与妻子的往事,体验到了濒临死亡的感受,并发现自己可以透过井壁进入妻子被囚禁的208号房间。在第一次升井后,“我”的脸上多了一块婴儿手掌大小的青痣,之后多次下井进入208号房间探寻妻子失踪的真相。最终,脸上长着青痣的“我”带着棒球棍下井,与“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对决,救出了伤痕累累的妻子,之后“我”所身处的枯井竟然重新涌出地下水将我淹没。而在诺门坎战役中,间宫中尉当时与同伴潜入满蒙边境执行机密任务,被抓到后投入荒漠中的一口枯井中,体验到了濒临死亡的感受。
作品中有关井的情节错综复杂,异常抽象,既是能否出水的井这一自然之和谐的象征,又是囚笼或者杀人凶器的井这一灵肉分离器的象征。井意象将主人公现实身处的东京与1938年外蒙的诺门坎联系在一起,又与棒球棍意象,青痣意象建立联系,完整地将《奇鸟行状录》抗争暴力的主题包含在内。
井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以至于“投井”成为了一种杀人方式;干枯的井则是一个深入黑暗的囚笼,一个开放的地牢,一个杀人凶器。在小说第一部,间宫中尉被外蒙兵逼入枯井中,他在谈话中如是回忆:“面对这劈头盖脸的光明,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甚至忘却了恐惧、疼痛以至绝望,只顾目瞪口呆地坐在辉煌的光芒中。”[5]186“……整个人就像被一股巨力彻底摧毁了,我想不成什么更做不成什么,连自身的存在都感觉不出,仿佛成了干瘪的残骸或一个空壳。”[5]187“……我还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在井底或者腐朽下去,有时甚至以为那才是真正的现实,而眼下日复一日的人生倒是梦幻。”[5]191在横线情节中,“我”的妻子莫名失踪,“我”便下到井中思考种种与妻相识相知的往事。当邻家女孩笠原May将“我”得以凭借升井的绳梯拉走并将井盖死死盖住后,“我”在井下也体验到了濒死感,“我”感到“身体便如被剥制成标本的动物,里面空空如也”[5]281。而这样一种濒死体验还具象化为一块青痣长在“我”的脸上,时时刻刻起着提醒作用。
从以上横线和纵线中有关“井”的情节可以看出,井是“通往潜意识的通道”[1]189,人在井下成了类似于纯精神的存在。间宫中尉在井下被每日只有短短几十秒的光照所感召,成为了一具空壳,生命的内核被焚毁一尽;“我”在井下追忆了从前与妻子的生活,回想从与妻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出现的无以言表的奇怪之处,回想妻子堕胎的往事。井深入大地,使得井底之人能够赤裸裸地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拷问自己的灵魂,使得灵魂摆脱束缚,得以剥离出肉体。 “井”在给予濒死体验的同时成为了一个灵肉分离器:透过井壁的“我”已经不是现实的“我”,更多的是一种想要救出妻子的决心的意念集合体,“我”进入的也不是现实中关押妻子的房间,对决的邪恶也不仅仅是绵谷升本人。井将“我”的灵魂和肉体分离,使“我”能够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找回妻子。“我”首次下井时,感到:“身体如被剥制成标本的动物,里面空空如也。……这委实不可思议,我继而感觉的分明类似一种达观。”[5]281“动物被剥制成标本”是濒死体验,而感受到的“达观”是“我”直面内心世界后的一种释然。“我”在现实中寻找妻子,在井下则探寻自己的内心,井为这两种探寻提供了媒介。
村上通过将历史与现实联系,将死亡感受与拷问内心相联系,实则还是要表现须铭记历史的主题。在《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付梓之际,村上曾实地考察过诺门坎战场,他回忆到:“站在那曾经激战的战场遗址上时,我清楚地感受到了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深夜突然睁开双眼,发现房间在剧烈摇晃,到了无法走路的地步。开始以为是地震,在黑暗中爬行,打开门来到走廊,发现外面一片寂静,我才发现摇晃的并非这个房间或是世界——是我本人。”[1]174村上来到曾经充斥着死亡的战场,感受到了内心的震颤。死亡的存在迫使作者直面历史黑暗和残暴的深处,并引发作者对于战争以及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暴力的思考。间宫中尉体验到了战争的暴力而“我”因为妻子被莫名夺走也慢慢感受到身边无处不在的暴力。井连接了两个时空,并让“我”酝酿与暴力抗争并且夺回妻子的决心。
水是生命的源头,是自然慷慨赐予的产物。但井作为水源在作品中绝大部分情况却处于干枯状态。笠原家能够使用清澈甘甜的地下水,而仅一墙之隔的宫胁家却只有一口枯井,给人以“灭顶式无感觉的感觉”[5]77,使得宫胁家怪事不断;灵媒加纳马耳他曾去水源最好的地方修行,为了喝到最好的水,她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我”和妻子例行拜访算命先生本田,得到了要注意“水流”和“水脉”的告诫,并得知“该上之时,瞄准最高的塔上到塔尖;该下之时,找到最深的井下到井底”[5]60;“我”从房产经理人处得知宫胁家的那口枯井“战前还出水来着,不出水是战后”[5]428;而在最终对决中打败邪恶后,“我”坐在井底淹没在涌出的井水中。
以上情节表明,井下无水便怪事丛生,恶被打败后井中便有了水。有水之井是自然和谐的象征。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除去了恶,自然才能和谐,才能继续慷慨地给予人类生命的源泉。在第二部结尾部分,“我”在游泳时感觉自己置身于巨大的井中,意识到“这是世界上所有井中的一口,我是世界上所有我中的一个”[5]404。在现实与意识的边缘,“我”又进入了妻子被囚禁的房间,接收到了妻子向“我”求救的信号,明确了“至少有我值得等待又值得寻求的东西”。在水中,“我”顺应了自然的召唤,决定夺回妻子。
在小说结尾部分,“我”通过想象自己在水中从而进入了房间:“想象自己在游泳池往来爬游的光景,我忘掉速度,只管静静地缓缓地游动不止。……如此游了一会,渐觉身体竟如乘缓风,自然随波逐流。[5]654由此可见,“水”和“井”在主人公抗击暴力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在与恶对决胜利后,原本干枯的井底竟然重新涌出了水,“水再过五六分钟就将堵住我的嘴和鼻孔,随即灌满两个肺叶。……我的肺拼命要吸入新空气,但这里已没有空气,有的只是温吞吞的水”[5]697。井让“我”体验到死亡感和暴力,将“我”剥离成一个空壳之后,当“我”战胜邪恶后又再次用水将这具空壳灌满。“我”以为水即将把自己淹死,其实新涌出的水是一种洗礼:婴儿在母体中靠灌满肺部的羊水获得氧气,“我”在接受洗礼之后也重获新生,这是自然在对个体注入新的生命。
井通过给予“我”的濒死体验,产生灵肉分离作用,使“我”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井也作为自然和谐的象征,在“我”抗击暴力的过程中给予启示,在胜利后给予“我”自然的洗礼。井意象与作品主题层层挂钩,是整部作品中最为复杂且内涵丰富的意象。
结 语
本文所选取的三个核心意象和《奇鸟行状录》打击暴力、铭记历史和反思战争的历史都息息相关。棒球棍是暴力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暴力的打击者,在实施暴力与打击暴力角色相转换的同时,作者融入了一定善恶观的思考;青痣是铭记历史的印记,作品中的历史便是黑暗而残暴的战争,这块青紫色的痣便是黑暗历史具象化的展现;井是供人探索内心世界的媒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水井与枯井的区别象征了自然和谐与否。
棒球棍、青痣与井三者之间也互相联系:主人公下井体验到了濒死感后,脸上便出现了青痣,而青痣作为贴于外表的一份屈辱感与命运感又使我想起过往黑暗的历史,驱使着“我”用棒球棍打击暴力。在小说的高潮部分,这三个意象最终得以重合:脸上长着青痣的“我”,双膝夹着棒球棍坐在井底,最终夺回妻子。井作为一个有自然灵性的地方,让“我”找回了自己,带“我”到达妻子被禁之处得以抗争暴力。这时,武器、抗争的决心和媒介缺一不可,都是“我”得以最终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对于现代中日两国关系来说,战争遗留问题、封闭性社会体系等问题是绕不开的话题。村上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在《奇鸟行状录》中对于不断传承的暴力体系,以及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与反思,都与战后的一些日本作家形成鲜明反差。正如王向远指出:“这种情况表明,日本文学界对战争的责任,对侵略战争尤其是侵华战争的罪恶,还远远没有形成普遍的悔罪意识,对侵略战争的普遍的正确的认识还没有形成。”[7]村上春树通过《奇鸟行状录》,揭示出日本现代社会残暴的、封闭的暴力系统,批判了本质上毫无变化的日本社会体制。
[1] 杰·鲁宾.洗耳倾听:村上春树的世界[M].冯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林少华. 追问暴力:从“小资”到斗士[J].《奇鸟行状录》序.2009,(8).
[3] ヅエイ·ルビン.村上春樹『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の翻訳に对して[J].群像.2003,(12).
[4] 村上春樹.村上春樹全作品1990-2000④ 『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1、2』“解题”[M].讲講談社,2003.
[5] 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与索引(修订译本)[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 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
[责任编辑:左福生]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and the Well: an Analysis on Core Imageries ofTheWind-upBirdChronicle
Yang Xiaolian Shen 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48, China)
TheWind-upBirdChronicleis the turning point of Haruki Murakami as a writer, from which Haruki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of significance than to human’s inner world of mind in the earlier stage. In this thesis, the three core items, namely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and the well, all of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novel’s theme of combating against violence, are deeply analyzed. In the end, the continuous violence system in modern Japanese society, and the author’s pondering on Japanese Aggressive War against China, are contained in this thesis. All in all,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re combating against violence, bearing in mind the past and pondering upon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ggressive war.
Haruki Murakami;theWind-upBirdChronicle; the baseball bat; the green mole; the Well
2016-11-02
杨晓莲(1964-)女,四川省岳池县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沈荣(1994-)男,江苏省南通人,南通市智联外语培训中心国外部教师,主要从事雅思托福写作教学。
II3
A
1673—0429(2017)01—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