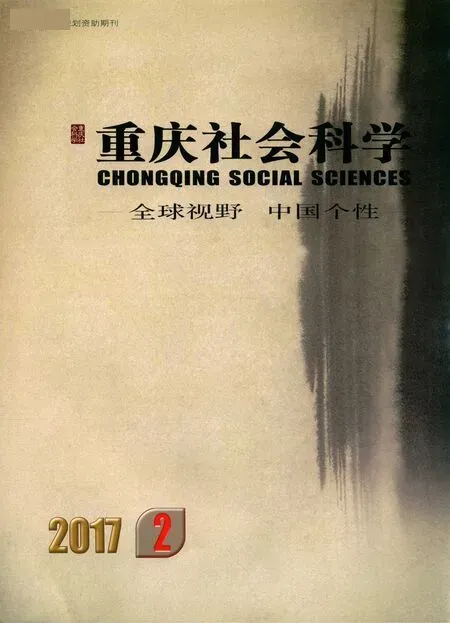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述评*
乔 虎 柴婷婷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述评*
乔 虎 柴婷婷
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源起和理论意义、分工的实质、分工的类型、分工的双重后果以及“消灭分工”及其途径等方面,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文本研究,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提升研究层次,拓展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视角;立足中国实践,彰显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 分工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分工”的专著,他们的“分工”思想散见于一系列的著作之中。从文本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的论述是整体分散,部分集中。尤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有较为集中的论述,这些思想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内容丰富的分工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学界兴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浪潮。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年来,在老一辈学者如赵家祥等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持续关注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青年学者,如王虎学、徐国民、张薇、杨芳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分工范畴的初始论域和理论意义的研究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分工范畴的初始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即马克思最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探寻异化的根源时注意到了分工这一范畴。同时,马克思对分工范畴的详细考查与探索为其构建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部分学者认为分工范畴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分工范畴的初始论域
在《手稿》末尾,马克思指出“考查分工和交换是很有意思的”[1]。这表明马克思开始认识到分工与劳动异化、私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姚顺良在对《手稿》进行详细考查后,认为马克思不断地对“异化劳动”根源进行追问,从而在“巴黎手稿”末尾的两个“片段”和“穆勒笔记”中,关注到“分工”(和交换),提出了“谋生劳动”概念,迈出了“用分工说明异化”的第一步。这表明人本主义“异化”范式在马克思那里开始解构,而且预示了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来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泛分工论”的特殊方式。[2]这一观点在王虎学的《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一书中得以体现,在该书的作者看来,“异化构成了分工的初始论域,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在追问异化劳动根源时发现了分工;另一件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中阐明了分工的本质”[3]。还有的学者在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进行考查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遇到的“物质利益”问题,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哲学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将研究视角转向经济学,并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发现了“分工”这一劳动组织形式,通过对分工的历史考查,赋予分工以哲学内涵,从而解开了“历史之谜”。[4]
(二)马克思主义分工范畴的理论意义
一是分工范畴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1890年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明确表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5]。这说明分工范畴是理解唯物史观的一把钥匙。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通过分工范畴探索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考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唯物史观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郝孚逸认为:“马克思的《手稿》直接从分工和分配这一主题入手,在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为建立新的唯物史观的人的哲学奠定了初步的但又是永久性的基础。”[6]杨芳在《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特点》一文中指出正是通过社会分工这个概念,马克思系统地分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有制、阶级、国家、上层建筑、人的发展等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为科学地分析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7]
二是分工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8]。这体现了分工范畴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罗文花在 《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新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范畴本身具有一般性,它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行的特殊经济规律,也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所以它应当是待建立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支撑和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9]杨慧玲认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一个以协作与生产效率的互动机制为基础,涵盖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还有的学者尝试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中嵌入“劳动”和“分工”两大理论硬核,构建以“劳动—分工—所有制”为主线的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框架。[11]
近代以来,“分工”这一范畴最开始是被亚当·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应用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经济学术语,而马克思则赋予其哲学意义。在批判地吸取分工这一范畴后,马克思不仅在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分工为线索构建唯物史观,还在中晚期著作如《资本论》中通过分工与协作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事实上,在马克思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唯物史观的创立与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互济互补的关系。在很多时候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分工所具有的“双重身份”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全貌和各具体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二、关于分工的实质的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对“分工”的实质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分工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还是生产关系的范畴这一问题来讨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有 “生产力范畴说”——分工属于生产力的范畴;有“生产关系范畴说”——分工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还有“中间环节说”——分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具有双重属性。最后一种观点在近十年来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如高中华认为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分工的形式,一定历史阶段的分工又决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生产力通过分工这个中间环节和纽带进而决定着生产关系。[12]王虎学对这一观点有进一步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来看,分工是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中介;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分工作为“中介”本身并非纯粹中介性、从属性的存在,而是具有其独立地位的存在。[13]这一观点突出了分工范畴的独立地位。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社会分工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它既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又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因此,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直接体现,或者说,社会分工就是生产方式的外化形式。[14]
总之,发现分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并认识到分工的中介地位是学界对分工的实质的认识的一大进步,但仅仅停留在这里是不够的。这仍然是把分工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框架中去界定分工的实质,并未把分工理解为有独立地位的范畴。事实上,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分工范畴不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起中介作用,而且与意识形态、阶级、国家等上层建筑也具有密切关系。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来看,分工范畴具有哲学和经济学的“双重身份”。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逐渐重视和深入研究,有的学者就分工的定义和实质提出了独到见解。王虎学通过对分工概念的生成语境的考查,认为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式,是特殊劳动方式的整体,分工在于“结合”而非“划分”,分工范畴只是一定历史形式下的 “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抽象”,而不断变动发展着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则构成了分工的现实内容。[15]徐国民从对社会分工的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把握中,认为社会分工就是社会总劳动不断地被细化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若干专门劳动的过程。[16]薛秀军从人的本质的视角考查分工的实质,认为分工是作为群体化的存在联合开展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所结成的内在的人与人的劳动技术组合方式。[17]许崇正认为,分工是指统一社会生产体系中各种劳动和他们相互制约的活动过程,是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而这种活动过程和存在形式又是建立在一种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和彼此相联系的劳动活动类型与形式的体系之上的,并且这种劳动体系活动过程存在形式又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化的。[18]这个观点强调了分工的历史性和不断发展性。
三、关于分工的类型的研究
关于分工的类型划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也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分工的类型作出不同的划分,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从分工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可划分为自然分工、自发分工、自觉分工
学界往往将分工的三个阶段对应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种社会形态”,即自然分工对应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自发分工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觉分工对应的是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人的自由个性与全面发展。赵家祥在《分工的实质及其社会作用》一文中将分工划分为“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半自觉分工、自觉分工”[19],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工处于半自觉分工的阶段,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工仍然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张爱华则从社会历史形态与人的发展的角度将分工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自然经济形态——自然分工与人的“原始圆满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分离与人的不发达的完满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分工、交换与人的片面性;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自由交换与人的个性丰富性。[20]
(二)根据分工生产的形式状况,可将分工划分为社会分工和生产机构内部分工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注意到社会分工和工场内部分工的区别。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将分工划分为两种形态是对斯密的伟大超越。有的学者在认真考查这两种分工形态及其联系和区别之后,认为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生产分化为各个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生产部门和商品生产者。社会分工既包括农业和工业等“一般的分工”,也包括部门内部的“特殊的分工”。而生产组织内部的分工属于 “个别的分工”。这两种分工形态产生的时间不同,性质不同,但是相互促进,相互替代。[21]还有学者对马克思分工的“二分法”和“三分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社会分工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二分法”,是从一定历史形态的分工出发对分工的区分;而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个别的分工的“三分法”则是从“单就劳动本身来说的分工”出发对分工的区分。“二分法”凸显的是“分工特殊”的逻辑,揭示的是分工的两种形态;“三分法”凸显的是“分工一般”的逻辑,指明的是分工的三个层次。[22]应当说,这种对于分工类型的内在逻辑上的把握是到位的,厘清了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对分工类型的论述的内在联系。
(三)从分工的主客体角度,可划分为劳动分工与劳动者分工
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赵家祥,他认为劳动分工使社会总劳动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包括不同的劳动领域、不同的劳动部门、不同的工种以及同一工种的不同工序等,这是分工的客体方面;劳动者分工使总体劳动者分解为不同的部分,长期的、稳定的固着在不同的劳动活动中,这是分工的主体方面。[23]还有的学者将社会分工分为生产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两种基本形式,生产性分工是指由生产的需要而引起的专业化、专门化劳动;社会性分工是指在特定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下,劳动者在从事专门化、专业化劳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差异。[24]这实际上也是从分工的主客体角度进行划分的。由于这种划分方式既看到了分工的客体方面即劳动划分组合方式,又注重分工的主体即人的方面,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同。
四、关于分工的影响的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25]。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26]。学界对分工(自发分工)的作用普遍持辩证的态度,认为分工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双刃剑”,具有双重影响。
(一)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分工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分工一经产生便提高了生产效率,它是社会财富增长的源泉,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分工使意识具有了相对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分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共政治机构使人类社会由“无序”状态进入到“有序”状态,从而促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但同时分工造成了社会劳动条件及其产品的不合理分配,造成社会成员发展的不平衡,使人们在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造成了阶级压迫。[27]
(二)个人层面的双重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杨芳在《从“专业化”到“碎片化”——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分析》一文中指出,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社会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技能和总结劳动经验,能将有限的个体能力整合为类整体的能力。社会分工对人的制约性体现在:社会分工造成了人的劳动、活动的固定性、片面性;造成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对抗性。杨芳还对社会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分工导致了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分工的彻底结合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了人的“碎片化”发展。[28]还有的学者着重强调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受压迫的状态,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控制人们努力争取到的自由时间,并且在“文化工业”内部,也不断强化推进着更为严格精细的生产分工,形成类似于物质生产的文化生产的“流水线”,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审视自身、审视自己生活的视野和进行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使每个人都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变得日益狭隘、片面、丧失反思精神而更易于控制,从而造成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自由发展的不可能。[29]这种观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视角分析了自发分工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自发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固然终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消亡,但在它所存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又有其历史合理性。在关注批判对象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发分工得以扬弃自身的道路。在对自发分工进行反思和批判时,我们要注意到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发分工对人的压迫和奴役,但正如张曙光所说:“对于社会矛盾的另一个面相即‘统一性’,以及对于劳动分工、社会分化本身所具有的互依、合作、整合功能的轻视,也势必导致对事物看法的片面性。”[30]
五、关于“消灭分工”及其途径的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消灭分工”的论断的,在之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要消灭“旧的分工”。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消灭分工”就是要消灭“旧的分工”,即旧式分工,而不是消灭作为劳动技术划分和组合方式的分工本身或一切分工形态。
(一)对“消灭分工”论断的解读
基于对旧式分工的不同理解,学界对“消灭分工”这一论断的解读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消灭自发分工。这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消灭分工”的对象是指与私有制相结合的旧式分工,是分工发展的特定阶段,即自发分工。其根本特性就是强制地把人长期甚至终生限制在某种单一的职业上或束缚在某一局部活动范围内,其后果是造成了生产者智力和体力的片面化和畸形化,并通过交换逐步形成由商品、货币、资本支配人的物的世界。[31]
二是消灭劳动者分工。这部分学者认为“消灭分工”是要消灭分工的主体方面即劳动者分工,而分工的客体方面,即劳动分工仍将长期存在。赵家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一文中论证了劳动者分工消灭的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劳动者职能的流动性,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劳动者的固定的专业划分的现象必将不复存在。[32]周绍东认为 “消灭分工”是要消灭 “异化劳动——强制性分工——私有制”这一连锁路径,消灭强加给劳动者的分工角色。同时周绍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际,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发展的长远指向并不是简单的“消灭分工”,反而要推动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并利用分工这一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和所有制变革。[33]
(二)消灭旧式分工的途径
对于消灭旧式分工的途径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其根本途径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有学者认为分工是发展了的生产力但又是相对不太发达的生产力的结果,是同私有制和阶级相伴随而生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分工,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消灭阶级存在提供坚实基础。[34]至于消灭旧式分工其他的具体途径,有的学者认为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消除旧式分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35]还有的学者认为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职业分工产生了深刻影响,引起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变化,引起职业的经常变换和职能的全面流动,使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性质发生变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必然导致旧式分工消灭。[3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从对分工的特性及其自身发展的过程的把握,认为分工具有自我扬弃的历史必然性,其自身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否定性力量。这主要表现在分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新的生产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分工使得普遍的世界交往成为可能,有利于摆脱阶级和地域的桎梏,增强个人的独立性;分工造成了劳动者在不同专业、岗位上的被迫流动,激发了个人独立性和全面性的要求。这些多层次的自我否定的力量,最终会促使“旧的分工”的自我消亡。[37]总之,“旧的分工”是一个历史范畴,凡是在历史中产生的,也必然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消亡。
六、研究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进行了持续的关注,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有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要看到,总体上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争论,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实践发展的需要。这需要我们在文本研究和研究层次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一)加强文本研究,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研究上,还存在着两点不足。一是学界普遍对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研究较少,在恩格斯晚年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也对分工作了重要的论述,但这方面鲜有学者关注。二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研究得不够全面。近十年来学界在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研究较多,而对于马克思中晚期著作如《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关注较少,近十年来学界也认识到这一点,并陆续有对《资本论》的研究,但总体上成果不多,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
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基础。要将分工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当中,从而从一个历史的、立体的、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视阈下审视分工理论,而不单单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事实上,自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所谓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从而开始转向经济学研究,到1844年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中和追寻异化根源时发现分工范畴,再到1845~1846年以分工为主要线索探索社会基本矛盾规律、构建唯物史观,直至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将生产机构内部分工视为“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马克思构建唯物史观的必经之路,如果没有对经济事实的关注,没有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马克思是不可能创建以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根本作用为原则的唯物史观的;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是进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资本论》中始终贯穿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张一兵所说,二者“是一个双向的构建过程”,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互济互补、密不可分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对于分工理论本身和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提升研究层次,拓展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视角
近十年来,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着重研究分工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在分工范畴的中介地位、分工形态的划分、“消灭分工”论断的解读等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论,如学界目前还未对分工的概念和实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同时缺乏对一些基本概念如分工、交换、协作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另外对马克思主义分工思想的理论渊源的深入研究较少。总之,对基本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但同时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内在逻辑上的把握。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深入透析其内在逻辑和规律,对于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是必要的。
事实上,分工不仅是哲学和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需要拓展研究视角,不仅要在哲学和经济学相统一的视阈下把握分工理论,也应借鉴其他学科成果,从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进行考查,并要注重与国内外思想家的优秀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另外,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是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上,将分工的产生和演变置于人类社会的进程之中,将分工与人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把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需要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注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其“物化”思想、意识形态批判等思想对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三)立足中国实践,彰显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近十年来,学界较多是从理论层面上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而对我国现实问题关注不够。一个科学的理论必然是产生于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并对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发展实践起到指导作用的理论。立足我国具体国情和实践,彰显其现实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工还存在着较大的自发性,存在着贫富分化、职业分化、地区差距、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而这些往往是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导致的。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38]。社会分工导致城乡分离,而这是社会分化的综合体现。目前我国农民人口有6亿多人,农业生产并未完全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农民生活水平仍然相对较低,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现代化。“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目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指导,而相关研究仍然比较薄弱,落后于实践发展的理论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研究,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把握统筹城乡发展的着力点,进一步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逐步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来,分工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第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有的学者甚至把服务业的产生称为“第四次社会分工”。同时一大批新兴产业纷纷出现,分工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职业不断拓展、细化。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对这些新变化进行解读,有利于人们对社会分工的新变化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化分工不断深化,这是分工在当代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当代的国际化分工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国际化所推动的,是资本进行全球控制和渗透的手段。我国如何抓住机遇,健全对外开放的新体制,利用好 “两个市场”,如何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强与国际组织在重大事务上的合作,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保障国家核心利益,这也是我们要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2]姚顺良:《从“异化劳动”到“谋生劳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范式解构的开始——兼与张一兵教授的“穆勒笔记”解读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第 128~134页
[3][13][15][22]王虎学:《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年,第 86、230、139、171 页
[4][27][31]张薇:《唯物史观视阈下的马克思恩格斯分工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53、187、99 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9页
[6]郝孚逸:《论分工与分配的经济学哲学内涵——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不同理解谈起》,《江汉论坛》2007 年第 8 期,第 9~13 页
[7]杨芳:《论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特点》,《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1~1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304页
[9]罗文花:《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新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第64~69页
[10]杨慧玲 张伟:《马克思分工理论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 10期,第 14~21页
[11][33]周绍东:《以劳动与分工为硬核的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 1期,第 8~14页
[12][34]高中华 徐岩:《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5期,第 154~156 页
[14][16][24]徐国民:《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与理论反思——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指向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5、16、111 页
[17]薛秀军:《分工:透析现在生活的棱镜》,《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2期,第58~62页
[18][36]许崇正:《论分工与人的全面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第 61~68页
[19][23]赵家祥:《分工的实质及其社会作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3期,第24~29页
[20][35]张爱华 邓小伟:《〈资本论〉中的分工与人的发展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 4期,第 16~22页
[21]崔向阳 钱书法:《论马克思社会分工制度理论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第142~148页
[25][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79、184 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 403页
[28]杨芳:《从“专业化”到“碎片化”——社会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分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第44~46页
[29]薛秀军:《分工与自由: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逻辑进路初探》,《哲学研究》2013年第 4期,第26~28 页
[30]张曙光:《“意识”与“语言”——历史构成的第五个因素》,《河北学刊》2008年第 2期,第11~19 页
[32]赵家祥:《〈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7期,第4~15页
[37]薛秀军:《分工与解放:马克思分工理论的价值意蕴》,《哲学动态》2015 年第 10期,第 25~30 页
A Review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Qiao Hu Chai Tingt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the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mainly focuses on the origin,theoretical significance,the essence,the type,its double consequences and its ways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which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it's necessary for us to strengthen the text research and grasp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from the whole,to enhance the research level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and to base on the practice of China to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ntemporary value.
Marxism,division theory,Marxist literature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长春 130024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近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