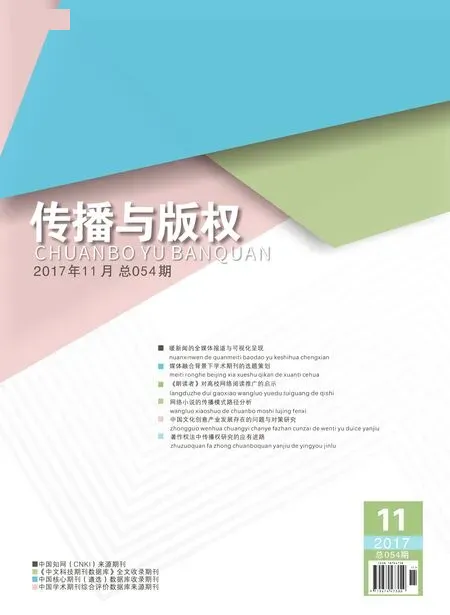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哲学思考
王俊琴
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审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
(一)出版的“传统”与“新兴”之辨
何为传统出版?何为新兴出版?学术界和出版界似乎都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分类和解释。即使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2015年3月31日发布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里,也找不到二者的明确定义,只是指导性地提到要“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把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由此,我们不难推断现阶段所谓的“新兴出版”的概念和互联网有着密切关联。之所以使用“现阶段”这一限定词,是因为出版业的“传统”与“新兴”是两个对立统一的动态概念。运用哲学的辩证法,我们不难理解,今天的传统出版往往是昨天的新兴出版,今天的新兴出版也有可能成为明天的传统出版。如今被视作传统出版的纸质出版,兴起之初,相对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结合前的出版形态,也曾属于新兴出版之列。这启发我们,用静止、具体的定义去描述发展着的动态概念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们转而寻求相应的动态划分标准来解决这一出版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二)如何划分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考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以此为标准划分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相应地,用这一哲学思想统观出版史,笔者认为划分某一阶段的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支撑出版的技术是否有革命性变化,它包括出版物的生产方式、物质形态和内容呈现等;二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出版的产业运作模式,包括盈利模式等是否有本质变化。需要与立足出版史划分其发展阶段所不同的是,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出版形态只要满足二者之一,即可将其划归为该阶段的新兴出版。于是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数字出版(同时满足两条标准)毫无疑问当属新兴出版,而近年来涌现的基于互联网的众筹出版、众包出版、自出版等(满足标准之一)也都可划归到新兴出版的范畴。这再一次说明,新兴出版只是一个与传统出版相对的概念,新兴出版的内涵除了凭借先进的出版技术进行颠覆性的产业革命之外,还包括运用高新科技(先进生产力)对传统出版产业模式(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改良。
(三)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意义
讨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二者为什么能融合?一方面,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内容的生产和服务,这也是出版的本质含义;另一方面,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能融合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出版产品的需求是多层次、多维度、多形态的,而单一的物质形态无法与之相适应。这意味着新兴出版和传统出版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融合打破了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原本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两极化对立关系,使得二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共生共荣、此长彼长成为可能,这正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意义所在。
二、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未来
笔者认为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的未来在于出版的全方位开放和对出版本质的回归。
(一)出版的全方位开放
“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放,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也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必然趋势。开放的本质是发展,这与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的目的不谋而合。不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出版,想要在未来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尽可能大地进行开放。
1.载体的开放。载体的束缚是现阶段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都需要突破的。一方面,就目前的纸质出版物而言,其实质是囿于纸上而几乎没有对外开放的一堆数据。即使是在载体开放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的MPR出版,其开放也是有限而不彻底的——它仅仅开放了纸质出版物获取网络数据的单向通道。
另一方面,尽管epub 3.0的出现以及HTML 5在移动端的普及,使得包括电子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等在内的网络出版物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和更充分的信息互动,但目前PC端、手持终端、移动终端等的文件格式的壁垒直接制约着出版内容的传播,文件转码浪费了出版这一内容生产行业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载体开放,基于载体开放的跨文本搜索和进行各种深度链接的可能,将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带来无限的遐想。例如,当前火热的3R技术——VR、AR、MR,通过二维码和智能终端结合,实现了纸质出版物和场景再现的结合,在出版领域掀起了体验革命的热潮。[1]而3R技术的应用根本上正是源于这些出版物及其衍生品的载体开放。载体开放是当今全球一体化大背景在出版业的一个投影,也是出版发展的必然趋势。
2.内容的开放。不论传统出版还是新兴出版,一旦内容开放,其释放的价值将是巨大的。例如,互联网创作众包将原本由一个作者完成的庞大创作内容,开放性地分解给若干创作者,从而极大地缩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出版效率。内容的开放为作品的重新演绎带来了可能,极大地提升了人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模糊了阅读与创作的边界,甚至重新定义“作者”及作者权益。这可能引发出版文化的深刻变革。可喜的是,出版已正逐渐认识到内容开放所蕴含的价值。例如,2014年加拿大电子书制作与分享网站Wattpad就推出了开放故事平台,作者以知识共享协议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版权协议,授权并鼓励任何人去分享、修改、重新演绎自己创作的内容。[2]
此外,过分的数字版权保护,导致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不断更新升级,这实际上是与内容开放的精神和趋势相违背的,其根源还在于缺乏更为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而内容开放带来的颠覆传统盈利模式的变革或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通过内容的开放,至少是有选择的内容开放来跨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跳出出版物本身来现实出版盈利。诸如web 1.0时代的“免费+广告”模式,当前的“粉丝经济”模式,以及未来在出版物上提供付费接口实现互联网与物联网双网融合的模式等,都为内容开放后的盈利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内容开放带来的出版外的可观收益可以远远超过出版物本身所带来的原始利润。
(二)出版本质的回归
出版技术作为改造出版的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为出版的内容生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先进的生产工具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保障。新兴出版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将突破传统出版在载体、复制(印刷)、传播(发行)、仓储、物流等方面的种种束缚,使出版从繁杂的过程操作中解脱出来,进而专注于出版的本质:独立于技术之外的内容生产和服务。
当前根植于内容的IP衍生开发,其品牌联动带来的经济上的雪球效应已经让出版界重新认识了内容所裹挟的巨大价值。在未来极尽开放的出版产业中,所谓的“渠道为王”“平台为王”等最终将在“内容为王”的面前变得不堪一击。2012年,“乐视”凭借一部《甄嬛传》的独播在“优酷”和“土豆”强势合并后形成的绝对霸权和垄断的视频播放器市场异军突起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如今Kindle Unlimited电子书订阅服务的困境也正在于缺乏优质出版资源的内容支撑。
内容为王,不仅指出版企业要紧紧依靠自身的IP资源,进行全面开发,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出版社要严把内容质量关,做出具备良好体验感的产品,以此来共同维护出版业态的健康发展。《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融合要实现“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放、一次开放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显然,这一要求的根本落脚点就在于内容的生产。“内容为王”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必然归宿。
三、关于当前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实践的一点思考:融合有没有捷径
近年来,大型传统出版企业积极并购优质互联网企业,试图通过“借船出海”的方式加快自身出版产业链的调整,探寻出一条快速融入飞速发展的新兴出版领域的捷径。其中,中文传媒对智明星通高达26.6亿的并购案,更是将中国出版企业对互联网企业的并购推向了一个高潮。[3]然而,传统出版企业仅倚仗资本的积累优势,尚不足以走通融合的捷径:并购完成的仅仅只是整合,并购后的互联网企业多数仍保持着业务上的独立,其与并购主体在传统出版主业上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因并购而变得更加紧密,出版主业上“1+1>2”的融合效果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乐观估计的阶段。
笔者认为产业模式相对落后的传统出版企业带领新兴的互联网企业所走的非内生变革的“捷径”,未必有预想得那么乐观。恰恰相反,让原生互联网企业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并购传统出版企业,或许有可能走出一条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的捷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怎样,传统出版企业已经勇敢地迈出了借助外力自我革新的一步,这一步哪怕是试错,也是值得去努力实践的。
[1]王扬.VR+:出版融合发展的新方向[J].出版参考,2017(3):8-11.
[2]任翔.2014年欧美数字出版的创新与变局[J].出版广角,2014(23):24-29.
[3]左志红.出版业最大的并购案是怎样炼成的——中文传媒与智明星通结缘探秘[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05-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