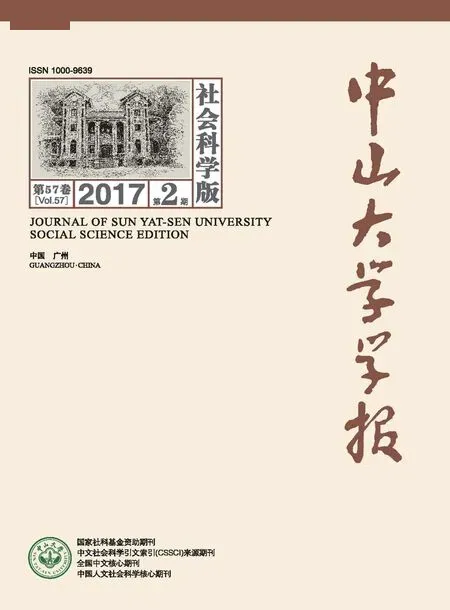“拟作传统”与“文学缺席”*
——郤正《释讥》的文体考察与文学史定位
孙 少 华
“拟作传统”与“文学缺席”*
——郤正《释讥》的文体考察与文学史定位
孙 少 华
郤正是三国时期蜀国著名文人。《三国志》称其曾著诗、论、赋百篇,《隋书》、《旧唐书》有《郤正集》一卷,但后世大多亡佚。《三国志》郤正本传录其《释讥》一篇,此赋拟自崔骃《达旨》,在形制、主旨上有汉赋传统,但从体式、音韵上看,又有后世骈文的某些元素。文学思想上,《释讥》既与《答客难》、《解嘲》、《达旨》、《答宾戏》等有着类似的“赋体”思想渊源,又与《释诲》具有相同的“释体”思想渊源,其中蕴含的大量四六韵文句式,使其具有“赋”与“文”“双重文体”特征,但总体上属于“赋”体作品。文学史之所以对其很少留意,原因较为复杂,而郤正的“贰臣”身份,或者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郤正; 《释讥》; 拟作
郤正,本名郤纂,字令先,河南偃师人,在蜀先后为秘书吏、秘书令,为郎三十年不迁。蜀降曹魏,郤正受命撰降书,后随刘禅入魏,受封关内侯。晋泰始中,为安阳令,晋武帝司马炎赞其“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陈寿:《三国志》卷42《蜀书·郤正传》,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1页。,迁其为巴西太守。《隋书》、新旧《唐书》有《郤正集》一卷,证明其书或者北宋尚存。今存者惟有《释讥》一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45《三国志》条:“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此《释诲》当为《释讥》之误,《释诲》为蔡邕作品。,《三国志》本传收录全文;另有《姜维论》片段见《三国志·姜维传》,《为后主作降书》,见严可均《文编》。姚振宗曰:“按史言郤令先著述垂百篇,《隋》、《唐志》著录乃只一卷,所佚多矣。”*姚振宗:《三国艺文志》,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9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郤正具有很高的文学地位。史书称其“性澹于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陈寿评其文“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陈寿:《三国志》卷42《蜀书·郤正传》,第4册,第1034、1042页。。应该说,将东汉以后有成就的文人与“张、蔡”相提并论,既是当时品鉴士人的一种方式,也是对所比较文人的最高评价。陈寿评郤正“有张、蔡之风”,应该指的是他的赋作;同时期曹丕《典论》,亦称王粲、徐幹之赋“虽张、蔡不过也”。由此易知,郤正在辞赋上的水平,与王粲、徐幹相当。
然而,对于《三国志》郤正本传中的《释讥》一文,我们很难在一般文学史上见到介绍。笔者所见,一些赋体选本,只有龚克昌主编的《全三国赋评注》收录此文,并给予了充分肯定。据《三国志》郤正本传,《释讥》乃其模拟崔骃《达旨》而作;然《达旨》又模拟于扬雄《解嘲》,《解嘲》源于东方朔《答客难》。此类文章,郤正之前还有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崔寔《答讥》、蔡邕《释诲》、刘瑾《应宾难》等,其后又有陈琳《应讥》、皇甫谧《释劝》等。这种以“答”、“解”、“应”、“释”为题的文章,具有大致相同的结构体式与写作模式,刘勰以为最初起源于宋玉《对问》。由此知《释讥》有其特定的“拟作”传统与文体渊源。东方朔《答客难》诸文,刘勰归入“杂文”一体,然后世多以其为“赋”。这种文体矛盾,同样反映在《释讥》一文。另外,后世赋学史或一般文学史,对《释讥》皆不置一词,其中原由,值得思考。本文即以此为例,讨论《释讥》的文体性质及其被文学史“遮蔽”的问题。
一、《释讥》的句式与韵部归属
《释讥》句式有三、四、五、六、七言。一个句子之中,多个四字句可能包含一个以上的六字句、七字句等,为研究方便,我们将其泛称为“四六字句”或“四七字句”*七字句中的虚词基本上可以省略,即变为六字句。在此我们仅将其视作一种理论上变化的可能性,并非一定省略某字皆视作六字句,因后世骈文亦有如此句式,如唐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著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分段原则以相同韵脚为准,两个“句群”之间,一般会有换韵情况发生。四、六句之间,换韵情况不一。其中的叹词、虚词、副词、连词等皆省略,以括号标识。其他律此*引文文字以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三国志·蜀书·郤正传》为准,个别标点偶有修改。参见陈寿:《三国志》卷42《蜀书·郤正传》,第4册,第1034—1038页。。
1.四七字句(实际上可看作是“四六字句”)
创制作范,匪时不立。流称垂名,匪功不记。名(必)须功而乃显,事(亦)俟时以行止。身没名灭,君子所耻。
此处可以视作4个四字句领起2个七字句,再以2个四字句作结。若将“名必须功而乃显,事亦俟时以行止”之“必”、“亦”字省略,即为六字句。则此句式即为“四六”句,即4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再以2个四字句作结。
韵脚:立、记、止、耻。两汉时期,“立”属缉部,入声;“记”、“止”、“耻”属之部,且“记”在两汉为去声字*本部分韵部分类,依据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因文字较为分散,不再一一注明页码。。“止”、“耻”韵,蔡邕《释诲》使用过。据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的统计,未见缉、之部合韵情况。三国时期,缉韵字独成一部*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62—169,324页。,此处以两汉缉部之“立”字与之部字合韵使用,很可能是蜀地方言的影响。
2.四六字句
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辩者驰说,智者应机,谋夫演略,武士奋威;云合雾集,风激电飞,量时揆宜,用取世资,小屈大申,存公忽私,虽尺枉而寻直,终扬光以发辉。
此处可分为两节讨论,第一节“达人研道,探赜索微,观天运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是一个标准的“四六句”;“辩者驰说”以下为第二节,是由10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
韵脚:微、衰、机、威、飞、资、私、辉,此处数字皆属脂韵。微、衰韵又见于张衡《南都赋》;机、威韵又见于崔瑗《郡太守箴》;辉、微、机、飞韵又见于蔡邕《光武济阳宫碑》,等等*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62—169,324页。。 由此可知,郤正对东汉赋、文的韵字情况较为熟悉。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一句之内也有合韵情况,如“云合雾集”,合、集属于缉韵字。
3.四六字句

4.四六字句
(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质,兼览博窥,留心道术,无远不致,无幽不悉;挺身取命,干兹奥秘,踌躇紫闼,喉舌是执,九考不移,有入无出,究古今之真伪,计时务之得失。
此处12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韵脚:质、术、悉、秘、执、出、失,其中秘为脂韵,其他皆为质韵。总体上判断,此处当为质、脂合韵。此合韵用法,东汉曾见于班固《答宾戏》*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236页。。
5.四字句
(虽)时献一策,偶进一言,释彼官责,慰此素飧,(固未能)输竭忠款,尽沥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并有闻焉也)。
此处为8个四字句。韵脚:言、飧、肝、元,皆属元韵。其中,“飧”作为元部韵,又见于扬雄《逐贫赋》、王褒《洞箫赋》。两汉作品皆有以“言”为韵者,“肝”、“元”多见于东汉作品。
6.四六字句
(盍亦)绥衡缓辔,回轨易涂,舆安驾肆,思马斯徂,审厉揭以投济,要夷庚之赫怃,播秋兰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图。
此处4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韵脚:涂、徂、怃、图,皆属鱼韵。
7.四六字句
(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管窥筐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纮之形埒,信万事之精练(也)。
此处为6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韵脚:面、艳、见、练,其中“艳”属谈部,其余3个属元部,故此处属于元、谈合韵,此用法曾见东汉崔瑗《东观箴》、班固《幽通赋》等。
8.四六字句
昔在鸿荒,朦昧肇初,三皇应箓,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书,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惨虐,吞嚼八区。
(于是)从横云起,狙诈如星,奇衺蠭动,智故萌生;或饰真以仇伪,或挟邪以干荣,或诡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弃直就佞,忠无定分,义无常经,故鞅法穷而慝作,斯义败而奸成,吕门大而宗灭,韩辩立而身刑。
此处可看作是先以10个四字句领起,后以两组4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
韵脚:初、符、书、扶、区;星、生、荣、矜、佞、经、成、刑。
第一组,此处用韵较为清晰,初、符、书、扶、区皆属鱼部。
第二组,矜属真韵,其余韵皆属耕部。此处显然属于耕、真合韵,此种用法多见于东汉碑铭文,如孔融《张俭碑铭》、无名氏《张公神碑》、无名氏《唐扶颂》等*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97页。此处我们以“矜”为真韵,后汉还有以其为侵韵者,如西汉韦玄成《戒子孙诗》“心矜”韵。。其中星、生、荣、经、成韵,曾见于边韶《老子铭》。
9.四字句
利回其心,宠耀其目,赫赫龙章,铄铄车服。偷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极,和鸾未调(而)身在辕侧,庭宁未践(而)栋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缩其泽,人吊其躬,鬼芟其额。初升高冈,终陨幽壑,朝含荣润,夕为枯魄。是以贤人君子,深图远虑,畏彼咎戾,超然高举,宁曳尾于涂中,秽浊世之休誉。彼岂轻主慢民,而忽于时务哉?
这里可看作是24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中间有换韵。
韵脚:目、服、仄、极、侧、覆;泽、额、壑、魄;虑、举、誉、务。
第一组,目、覆为沃韵,其余为职韵,属于沃、职合韵,此用法曾见于马融《广成颂》。
第二组,泽、额、壑属铎韵,两汉诗歌作品铎部中未见以“魄”为韵者,中古音在陌部,两汉属铎部,此或者属于三国时期的用法。
第三组,四字皆属鱼韵。
10.四六、四七字句
自我大汉,应天顺民,政治之隆,皓若阳春,俯宪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泽以熙世,扬茂化之浓醇。君臣覆度,各守厥真。上垂询纳之弘,下有匡救之责,士无虚华之宠,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
(然而)道有隆窳,物有兴废,有声有寂,有光有翳。朱阳否于素秋,玄阴抑于孟春,羲和逝(而)望舒系,运气匿(而)耀灵陈。
冲、质不永,桓、灵坠败,英雄云布,豪杰盖世,家挟殊议,人怀异计,(故)从横者欻披(其)胸。狙诈者暂吐(其)舌也。
从句式上看,我们可将此段材料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个,6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再以2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再以2个四字句作结。
第二个,4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再以2个七字句作结(当然,也可以省去2个七字句中的“而”字,将此句看作是4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
第三个,6个四字句,领起2个七字句(或省去“其”,作为六字句)。
韵脚:民、春、文、醇、真;责、迹、益;废、翳、春、陈;败、世、计、舌。
第一组,五个字皆属真韵;
第二组,迹、益为锡韵,“责”为锡部之麦韵*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41,169页。,皆属锡韵。
第三组,废为祭韵,翳未见罗常培、周祖谟先生的统计,疑当为祭韵字;春、陈属真韵。两汉无祭、真合韵例,故知此处一句辄换韵:前四句四言为一韵,后四句六言为一韵。
第四组,败、世为祭韵,计为脂韵,舌为月韵,此处当为祭、月、脂合韵。此合韵用法曾见于马融《长笛赋》与《广成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41,169页。。
11.四六字句
(今)天纲已缀,德树西邻,丕显祖之宏规,縻好爵于士人,兴五教以训俗,丰九德以济民,肃明祀以礿祭,几皇道以辅真。(虽)跱者未一,伪者未分,圣人垂戒,盖均无贫。(故)君臣协美于朝,黎庶欣戴于野,动若重规,静若叠矩。
济济伟彦,元凯之伦也,有过必知,颜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鹰扬鸷腾,伊、望之事也。总群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计,敷张、陈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华英而不遑,(岂暇)修枯箨于榛秽哉!
此段句式,可分为两个单元分析:
第一个,2个四字句,领起6个六字句,再以4个四字句,领起2个六字句,最后以2个四字句作结。
第二个,8个四字句,领起6个六字句。
韵脚:邻、人、民、真、分、贫;野(音墅),矩;伦、仁、治、事;计、世、秽。
第一组中,邻、人、民、真、分、贫皆属于真韵;野、矩属于鱼韵。此节有一次换韵情况。
第二组,伦、仁属于真韵,治、事属于之韵,两汉无真、之合韵,故此处当为四句一换韵。另外,计为脂韵,世、秽属于祭韵,此为脂、祭合韵。
12.四六、四八字句
然吾不才,在朝累纪,托身所天,心焉是恃。乐沧海之广深,叹嵩岳之高跱,闻仲尼之赞商,感乡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进可而替否。
故蒙冒瞽说,时有攸献,譬遒人之有采于市闾,游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广福祥,输力规谏。
此句为4个四字句,领起6个六字句;2个四字句,领起2个八字句,再以2个四字句作结。
韵脚:纪、恃、跱、己、否;献、畔、谏。第一组,纪、恃、跱、己、否属于之韵。第二组,献、畔、谏属于元韵。
13.四六字句
(若其合也),(则)以暗协明,进应灵符;(如其违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进退任数,不矫不诬。循性乐天,夫何恨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无(者也)。狭屈氏之常醒,浊渔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怼。
此句为10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
韵脚:符、愚、诬、诸、无;醉、怼。
第一组,诬,中古音在虞韵,两汉当为鱼韵;符、愚、诸、无皆在鱼部。
第二组,醉、怼属于脂部之微韵。
14.四六字句
合不以得,违以不失,得不充诎,失不惨悸。不乐前以顾轩,不就后以虑轾,不鬻誉以干泽,不辞愆以忌绌。何责之释?何飧之恤?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执也。
此段为4个四字句,领起4个六字句,再以6个四字句作结。前后2个四字句中有换韵。
韵脚:失、悸、轾、绌、恤;入、执。
第一组,失为质韵,悸、轾中古为脂韵,上古为质韵;绌、恤中古为术韵,两汉术部字属于质韵。此处可皆视作质韵。
第二组,入、执为缉韵。
15.四七、七四字句
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游禽逝不为之鲜,浮鲂臻不为之殷。且阳灵幽于唐叶,阴精应为商时,阳盱请而洪灾息,桑林祷而甘泽滋。行止有道,启塞有期,我师遗训,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辞?
此段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2个四字句,领起4个七字句。第二部分为4个七字句,领起6个四字句。
韵脚:群、林、殷;时、息、滋、期、尤、己、辞。
第一组,群、殷为真韵,林为侵韵,此为真、侵合韵,此用法见于冯衍《显志赋》、李尤《函谷关赋》*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206页。。
第二组,皆为之韵。
16.四六、四七字句
辞穷路单,将反初节,综坟典之流芳,寻孔氏之遗艺,缀微辞以存道,宪先轨而投制,韪叔肸之优游,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归,泛皓然以容裔,欣环堵以恬娱,免咎悔于斯世,顾兹心之未泰,惧末涂之泥滞,仍求激而增愤,肆中怀以告誓。
(昔)九方考精于至贵,秦牙沈思于殊形。薛烛察宝以飞誉,瓠梁托弦以流声。齐隶拊髀以济文,楚客潜寇以保荆。雍门援琴而挟说,韩哀秉辔而驰名。卢敖翱翔乎玄阙,若士竦身于云清。(余实)不能齐技于数子,(故乃)静然守己而自宁。
此段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2个四字句领起的14个六字句。此处之“辞”,与上句之“我又何辞”之“辞”,构成顶针关系。
第二部分与前一句关联,应该是2个四字句(“辞穷路单,将反初节”)领起的12个七字句。
最后这一段以长排比句式,制造了一种恢弘的气势,这在以往的辞赋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
韵脚:节、艺、制、逝、裔、世、滞、誓;形、声、荆、名、清、宁。
第一组,节为质韵,艺、制、逝、裔、世、滞为祭韵,中古音以“誓”为祭部,此处之“誓”亦为祭韵;此处为质、祭合韵。此用法曾见于刘向《九叹·惜贤》、扬雄《冀州箴》*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95—196,235页。。
第二组,皆为耕韵。此类韵字,东汉多见于碑铭、民歌*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195—196,235页。。由此处看出,郤正《释讥》将两汉箴、碑铭、民歌等文体中的用韵援入赋体作品,呈现出散文化倾向。
综上所述,《释讥》全篇以四六句式为主;如果将其中七字句的某些字省略,可以说全篇皆为“四六句式”,并且不乏后世所称标准的“四六”句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相比,《释讥》在句式上的最大特征,就是比它们的四六句式更多、更工整。即使与其时代最近的《达旨》相比,也是如此。有人评价此赋“全篇以骈俪为主,对仗工整,用典密集,声律和谐,辞采华美,实开西晋赋风之先河”*龚克昌、周广璜、苏瑞隆主编:《全三国赋评注》,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697页。,是有道理的。
西晋陆机《演连珠五十首》,被认为“骈偶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他本人则是“骈文成立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杨明:《读陆机的〈演连珠〉》,《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这种说法没有问题,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的确是较早对南朝骈文具有重要启蒙意义的作品之一。问题是,在此文之前,已经有郤正《释讥》导夫先路。例如,陆机《演连珠五十首》的句式,主要以4个四字句领起的2个四六句为主,但也多含单独的四字句、4个四字句领起的2个六字句、多个四字句领起的多个六字句等等。这种句式,皆能在《释讥》中找得到。而郤正《释讥》将箴、碑铭、民歌等文体中的韵字援入《释讥》的做法,确实使得《释讥》具有了散文化特征。有人提出,郤正《释讥》属于散体大赋、韵散结合,并有散文向骈文过渡化特征*张东:《守正持义论郤正》,《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还有人直接将《释讥》看作是“骈俪文”*高新伟:《蜀汉文学论》,《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这说明郤正《释讥》兼具赋、文两重性质。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重点讨论。
二、《释讥》“主客问答”的“拟作”传统与思想渊源
《三国志·蜀书·郤正传》录其《释讥》,“其文继于崔骃《达旨》”,可知在体制、主旨上,《释讥》仿《达旨》,有汉大赋的思想渊源*现代学者多将《释讥》视作辞赋,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年)、杜松柏《三国蜀汉辞赋考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田鹏《三国蜀汉辞赋再考——兼与杜松柏先生商榷》(《文化学刊》2015年第3期)等。。而据史书记载,崔骃《达旨》又模拟于扬雄《解嘲》,同类赋作还有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可知此类“主客问答”赋*目前的文学史认识,皆将此类“主客问答”体视作赋体。,自汉初至三国,一直有其体式传承。就思想内容而言之,此类“主客问答”体,主要讨论的是“立功”、“立言”,其背后则又有政治、社会、文化的背景。
《释讥》“其文继于崔骃《达旨》”,二者主旨相近。《达旨》撰作原由是:“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崔骃故“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范晔:《后汉书》卷52《崔骃传》,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09页。。此处所言“太玄静”,与西汉末扬雄被人嘲笑“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固:《汉书》卷87上《扬雄传》,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65—3566页。相近。《释讥》主要被人讥讽“九考不移”,且“虽时献一策,偶进一言,释彼官责,慰此素飱,固未能输竭忠款,尽沥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并有闻焉也”*陈寿:《三国志》卷42《蜀书·郤正传》,第4册,第1035页。,与扬雄、崔骃埋首文章学术而追求“玄静”,同时政治上不受重用的遭际非常相似。班固《答宾戏》的撰作原由是班固“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所(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东方朔《答客难》也是因为“客”责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总体上看,他们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立言”与“立功”之间,他们“立功”不成,只能重“立言”而轻“立功”。这些文章的共同办法就是,更加强调“立言”的重要性。
由郤正上溯崔骃、班固、扬雄、东方朔,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或曾受到皇帝的信任却不得升职,或位居一职久不得迁,但皆以学问为重,追求“玄静”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待利禄与学问的态度,反映了一种“修身”或“隐逸”思想。
《答客难》东方朔答客问的理由,是“时异事异”,同时指出:“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荣!”这就从“修身”角度对“客难”提出驳斥。此外,还指出盛世多贤俊,不应该对“处士”未获重视或其生活方式的选择提出非议:“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并认为客人的这种“问难”,实际上是一种“不知权变而终或于大道”的表现*班固:《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9册,第2865、2867页。。东方朔的认识,是以人处盛世、人才辈出之时,当“修身”以安之若素。
扬雄《解嘲》在回答客人的嘲笑时,首先指出了当时的三种社会弊端。第一,儒学的兴盛导致了家家自圣、人人自贤的现象:“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第二,国家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带来了个人政治地位的瞬息万变与政治生命前途莫测:“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第三,“选贤”方式的僵化与用人制度的弊端,带来了人才选拔的畸形:“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在此情况下,扬雄提出了“守玄”思想:“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班固:《汉书》卷87上《扬雄传》,第11册,第3568、3570、3571页。在扬雄这里,“守玄”已经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并且是一种“援儒入道”的改变。他对当时选贤、用人制度的批评,已经比东方朔更为尖锐和深刻。
班固的《答宾戏》,其“戏”与“难”、“嘲”、“讥”意义接近。班固答客之戏,主要有三个认识。第一,与东方朔相同的“时移世易”思想:“因势合变,偶时之会,风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反对“厚古薄今”:“今子处皇世而论战国,耀所闻而疑所觌,欲从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怀氿滥而测深乎重渊,亦未至也。”第二,反对“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提出“道不可以贰”:“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彼岂乐为迂阔哉?道不可以贰也。”第三,认同扬雄《太玄》思想,提出“默”、“守道”、“守命”观点:“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颜师古注曰:“言修志委命,则明神听之,佑以福禄,自然有名,永不废也。”*班固:《汉书》卷100上《叙传》,第12册,第4227、4228、4231、4232页。颜师古之说以及文中提出“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密尔自娱于斯文”,都是符合儒家思想的一种“道”。班固所处的时代,与东方朔相同而与扬雄迥异,故其思想没有批判性,只有如东方朔一样心平气和的解释与接受,甚至是一种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
崔骃《达旨》,也是因遵循“玄静”而受到“时人”之“讥”,其所处时代,适逢“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的盛世。崔骃答“时人”之思想,与班固相似。第一,遵循“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儒家思想:“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臧,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在浮躁的时代,世人多浮华而崔骃埋首经学,独“收其实”,表现的是一种超然世外、用心于学的精神。第二,保持着学者的精神高洁,反对“夸毗以求举”和“暴智燿世因以干禄”的做法:“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第三,提出与班固相似的“守道”、“守则”思想,同时具有道家的“存性”思想:“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惟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絷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对于此处之“性”,李贤注曰:“天命之谓性,言隐居以体命。”*范晔:《后汉书》卷52《崔骃传》,第6册,第1714、1715页。这就说明至崔骃,其与班固的一个差异,就是“隐逸”思想的出现。

《三国志》称郤正《释讥》拟于崔骃《达旨》,由二者皆有儒、道思想看,此说合其事实。然由后世文体看,东方朔《答客难》以下,似乎只有班固《答宾戏》与其以“答”为题,扬雄《解嘲》名“解”,崔骃《达旨》实为“答”,郤正《释讥》自以“释”为题,其内涵实际上皆为“答”体,“解”、“释”不过是“答”之变体而已。由此言之,自东方朔《答客难》至郤正《释讥》,从思想、形式与结构上,皆有其一以贯之的传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前后继承关系。
然而,据《后汉书》蔡邕本传记载,蔡邕曾仿东方朔、扬雄、班固、崔骃等作《释诲》,可知“释”体,实蔡邕改创新体而为之。从文体新变的角度上看,郤正《释讥》或有另一种新的“拟作”传统。
三、另一种“拟作”传统——《释讥》的“释”体渊源
从另一种角度看,《释讥》却又有较为近世的“拟作”传统,即对“释”体的继承。《后汉书》蔡邕本传称其“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范晔:《后汉书》卷60下《蔡邕本传》,第7册,第1980页。。在此,蔡邕“韪其是而矫其非”,显然是在继承前贤基础上,又进行了适当的“改造”。这无疑是一种“新创”。对于这一点,徐师曾看得很清楚:“按字书云:‘释,解也。’文既有解,又复有释,则释者,解之别名也。盖自蔡邕作《释诲》,而郤正《释讥》,皇甫谧《释劝》,束晢《玄居释》,相继有作;然其词旨不过递相祖述而已。”*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4页。这就是说,《三国志》虽然称郤正《释讥》主题模拟自崔骃《达旨》,但从文体角度分析,该文很大程度上可能模拟自蔡邕的《释诲》。陈寿说郤正“文辞灿烂,有张、蔡之风”,当有所指。从模拟对象上看,《释诲》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释讥》与之完全一致。
从写作目的上看,蔡邕《释诲》*蔡邕:《释诲》,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59—560页。也是拒绝与中常侍为伍而“闲居玩古,不交当世”之作。这一点,郤正“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与蔡邕不与宦官为伍的态度相似。就此而言,《释诲》、《释讥》具有相似的写作背景。
从他人所问的问题看,《释诲》实际上与其他文章也极为相似,即皆被人问难何以“默而无闻”。这说明《释诲》与其他文章的写作主旨,主要因“功名”问题。
从结构上看,《释诲》、《释讥》具有如下相似之处:第一,《释诲》“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点出文题“诲”;《释讥》以“或有讥余者”,点出文题“讥”。第二,务世公子的教诲语句较多,且多三、四、五、六言句式,之后是内容仅为一句话的“胡老傲然而笑曰”、一句话的“公子谡尔敛袂而兴曰”然后是“胡老曰”引起的四段文字,最后是“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内容为七句骚体文,这与之前其他文章的结尾都不同。《释讥》的结构与《释诲》基本一致,即先以一大段“或有讥余者曰”提出问题,继而是一句话的“余闻而叹曰”、一句话的“或人率尔,仰而扬衡曰”,最后是“余应之曰”引起的四段文字。与《释诲》不同的是,《释讥》结尾并无“讥者”言行。但如果忽略《释诲》这一独特的结尾方式,《释诲》与《释讥》的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三,《释诲》最末一段的韵脚清、灵、宁、亭、生、征,亦见于《释讥》最后一段,其中形、声、荆、名、清、宁,与《释诲》相同。从这里推测,《释讥》借鉴了《释诲》的题名方式、结构与用韵模式。
综上所言,与其说《释讥》仿崔骃《达旨》而作,倒不如说袭崔骃《达旨》主题,而其结构、文体则袭自蔡邕《释诲》,具有“释”体的新特征。
四、“释”体作品的文体矛盾与定位
一般的辞赋选或赋学史,皆将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视作赋体,然对模拟四作的蔡邕《释诲》、郤正《释讥》等则不予置评。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因为对东方朔等四作,《文选》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为“设论”,显然未将其视作赋体。按照此说,则崔骃《达旨》、蔡邕《释诲》、郤正《释讥》等,亦当归入“设论”一体。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则将这些作品归入“杂文”一体*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254—255页。,他以东方、扬、班、崔、蔡之文,皆从赋体中析别出来,单独列为“杂文”。萧统之“设论”与刘勰之“杂文”,其意义接近,皆将此类文体视作“文”。这一方面反映了南朝人对文体的细致划分认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赋”、“文”的认识与判断。但是,《文选》、《文心雕龙》并未提及郤正《释讥》,如果按照一般规律推定,《释讥》显然也应该属于“设论”或“杂文”。然而,根据我们分析的郤正《释讥》的音韵情况看,郤正该文用韵符合赋体规律,同时符合南朝盛行的骈文的体式。简单将《释讥》视作“设论”或“杂文”,显然不合适。
那么,该如何界定《答客难》直至《释诲》、《释讥》一类作品的文体性质?
从篇章规模上看,《答客难》、《解嘲》、《答宾戏》、《达旨》的文字差不多,而《释诲》、《释讥》与皇甫谧的《释劝》,规模相似。这就是说,《释诲》、《释讥》、《释劝》之类的“释”体,确实与之前模拟对象有所差异。
从体式上看,皇甫谧“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房玄龄:《晋书》卷51《皇甫谧传》,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411页。,可知其创作初衷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郤正《释讥》一致,皆为“解难”而作。但在事情的原委上,则有所不同。如果说,《答客难》、《解嘲》、《答宾戏》与《释讥》,主题皆与功名有关,并且“客”问难的态度,皆有讥刺主人公“久仕不迁”反而埋首苦读之意,那么,蔡邕则是“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是一种主动的辞官不做;崔骃属于“未遑仕进之事”。皇甫谧《释劝》,则发生了变化:“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房玄龄:《晋书》卷51《皇甫谧传》,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411页。这就是说,皇甫谧作《释劝》不是回答他人问“久仕不迁”的问题,而是“迁而不就”。前者是仕之迁黜问题,后者是迁与隐的问题。这一点,与蔡邕极为相似,但也有差异:蔡邕是在乱世之中的无奈之举,皇甫谧是乱世初定之后的自觉选择。也就是说,在东方朔《答客难》体现出一种“隐逸”思想之后,至皇甫谧《释劝》的“逸民”思想则更为强烈,也更自觉。同时他提出的“出处”观,是对“盛世”的一种特殊理解,即“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是盛世多元社会的一种自然表现。这种认识,较之以往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
从用韵与体式看,《释劝》亦多押韵,且多三、四、五、六言杂用,与《释讥》非常相似。但是,《答客难》、《解嘲》、《答宾戏》、《达旨》与《释讥》,在“其辞曰”后,紧接着就是“客问”文字,而《释劝》与此前诸文的一个不同,就是在“其辞曰”后有一个长序*房玄龄:《晋书》卷51《皇甫谧传》,第1411页。。此序的基本内容,是详细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国宠”)、写作缘起(“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写作目的(“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这个内容,作者以“序”的形式交待出来,与《答客难》、《解嘲》、《答宾戏》、《释诲》、《达旨》、《释讥》等以“客问”形式显然不同。
《释劝》此序的出现,改变了《释讥》以上诸文的结构形式。《答客难》至《释讥》,前面虽有类似于“小序”的介绍性文字,但并非在文章的正文,而是在史书正文,且第一段即为多属有韵之文“客问”;《释劝》在“客问”韵文之前,增加一段叙事文字,实际上就使得全文具有了“杂”的特征。按照刘勰的说法,将《释劝》定为“杂文”,或有道理。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此前真正出于作者本人之手的赋序,至东汉才正式出现*王芑孙《读赋卮言》:“周赋未尝有序……西汉赋亦未尝有序……(《文选》所选)西汉赋七篇,中间有序者五篇:《甘泉》、《长门》、《长杨》、《羽猎》、《鵩鸟》,其题作序者,皆后人加之,故即录史传以著其所由作,非序也。自序之作,始于东京。”《渊雅堂全集》嘉庆刊本。。而东汉的“赋序”,多以介绍写作背景或缘由为主,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赵岐《蓝赋序》、边让《章华台赋》、蔡邕《述行赋序》等,皆是,且序文多了了十数字至数十字不等。即如魏晋曹丕《感物赋序》、《感离赋序》、《柳赋序》、曹植《洛神赋序》、嵇康《琴赋序》等*嵇康《琴赋序》文字稍长,然亦不足二百字,且无叙事、抒情手法。只有晚于皇甫谧的潘岳《闲居赋序》,方具有《释劝序》的写作特色。,亦是如此。《释劝》序文长达265字,本身即是一篇含有叙事、议论、说明、抒情等写作手法的短文。从这种文学特征上说,以《释劝》为“杂文”,或符合刘勰的认识。
从文体发展的进程看,结合萧统、刘勰的认识,《释讥》等文,或者当属“文”一体;但通过上文论证,依照当下的文学史认识,《达旨》、《释诲》、《释讥》一类作品,又具有“赋”体的某些文学特征。从《释讥》开始出现大量的四六句式看,将其视作骈文的最初雏形,也不为过。结合当下的文学史观判断,《释讥》应该是汉赋、杂文一类文体向骈文过渡的典型代表作品,兼具“赋”、“文”双重文体特征。也就是说,“文体”是“流动”的,尤其是在文体形式发生转换的特殊时代。就此而言,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某类文体之时,除了关注其最后被文学史认定的文体身份,还要关注该文体在孕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体的联系、区别或交融的过程。《释讥》等文的文体矛盾证明,在几种文体交融、转换、新变之际,某些作品的文体归属不能简单而论,甚至同一作品被归入不同的文体中也有其道理。这就说明某些作品可能具有“双重文体”性质。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以历史发展的辩证眼光去看待。
五、《释讥》何以“缺席”文学史?
根据史书记载,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在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著述宏富,并且有比较著名的文学作品,但都未能进入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史家或诗文评家的视野,造成了文学文本在文学史上的“缺席”。郤正《释讥》就是一例。自陈寿《三国志》录郤正《释讥》,其下数世,直至宋代方重新审视郤正的文学成就。然宋叶梦得《避暑诗话》、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仅仅论及篇名,明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列“释”体始见置评,然犹有贬词,直至有清《三国志文类》方见重收全文。《释讥》在文学史上的“缺席”,甚至文学史重曹魏、轻蜀吴现象,说明文学史家在文本选择上有故意遮蔽的可能。
首先,《释讥》被文学史忽视,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遮蔽了吴、蜀文学所致。以三国时代为例,曹魏禅汉以后,三国归一,魏又被晋禅代,“汉—魏—晋”成为史家的正统史学叙述。这种历史断代,自然将吴、蜀两国切割出去,文学史观中也自然“遗漏”了吴、蜀两国的文学成绩。文学史家关注这一段的时候,多以“汉魏”、“魏晋”称之,故对三国文学的叙述,主要以曹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为中心。萧统《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即主要以“建安七子”为文学叙述重点。殊不知一个时代的文学史,按照王朝来划分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很容易将同时期其他王朝、地域的文学忽略掉。《释讥》无法进入东汉、魏晋文学史,就是这个原因。
三国时期的文学与学术,在当时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魏蜀吴皆有非常发达的学术与文学。即以蜀国为例,如果梳理史书,蜀国的文学成就,丝毫不亚于魏晋。例如,陈寿《三国志》所载,《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许靖,本传称其“文多故不载”,又录其《与曹公书》;秦宓,本传录《荐儒士任定祖书》、《答刘璋书》等,又称其“文多故不载”;吕雅,本传称“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向朗,“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杜琼,“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李譔,“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汉中陈术(字申伯),“著《释问》七篇、《益部耆旧传》及《志》”;谯周(字允南),“父(山并),字荣始,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凡所著述,择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第4册,第929、967、972—976、988、1011、1026—1027、1027—1033页。。由此看出,蜀国当时学者在经学、文学、史学、谶纬各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我们今天书写学术史、文学史,不能忽视蜀国文人的成就。
其次,《释讥》缺席文学史,可能与其文体不清有关。宋以降,人多以其为“文”;然其作为拟作,又与“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今天看来,第一,《释讥》虽然与蔡邕《释诲》一样,皆为模拟东方、扬、班、崔之文的拟作,然二文已经脱离了汉赋盛行的特殊时代,与完全意义上的汉赋已经出现了差异。第二,处于汉魏之际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赋、文二体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换,刘勰已经将此类文体视作“杂文”,后人对《释诲》、《释讥》的文体性质更是无法完全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绕开《释讥》这个难题或者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笔者推测,《释讥》的被屏蔽,或者与扬雄、桓谭的某些作品亡佚一样,皆与作者本人的“附逆”、“贰臣”身份有关。因为按照陈寿的说法,作为曾有“张、蔡之风”的郤正,文名与王粲、徐幹齐,且其入晋曾任巴西太守,然其文后世大多亡佚,似乎不太正常。究其原因,笔者推测有二:一者郤正受谯周劝降、亲自撰写降书、其父随孟达叛蜀降魏等影响,身上具有浓厚的“贰臣”色彩,必为后人所诟病,故其作多不传; 二者晋禅曹魏为正统,三国之中,文学史家更重视魏国文人及其作品,致使蜀、吴作者多被屏蔽在文学史之外。
西汉扬雄、刘歆、桓谭等人的作品亡佚,与其附逆王莽不无关系,但时至今日,他们在学术与文学上的成就,已经完全被文学史、学术史所接受。魏蜀吴三国争雄,属于东汉以后不同军事集团对正统政权的争夺,当时不同地区的文人因地域关系分属不同政权,乃是形势所迫,并非政治、军事、民族矛盾尖锐对立下的主动选择。三国归晋以后,司马氏政权完全接纳了三国的文人,并未从政治立场、忠臣节义角度鄙视他们,包括促使蜀汉投降的谯周、为刘禅撰写降书的郤正。“至于贰臣,亦唐以前人所宽”*《三国知意》,《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0页。,这种认识一直延续至唐代,《郤正集》于宋代亡佚就说明了这种事实。但在民族矛盾突出的历史背景下,如宋辽、宋金、宋元等对立的时代及其以降,汉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中文人的政治选择,已经开始具有突出的民族主义因素,君臣大义、忠孝节义始成为文人关注的重点话题*刘咸炘称:“君臣大义虽传之自古,实至赵宋始精,自唐以前皆甚宽不严。”。此时对谯周、郤正等人的诟病会更加激烈。
唐前对“贰臣”的认识或有较“宽”的一面,但我们不可否认,“贰臣”为历代士人(包括唐前)所憎恶。即如谯周,时人对他的抨击,自晋代已经出现*陈寿:《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第4册,第1032页。。唐罗隐《筹笔驿》诗亦称“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亦可知唐代文人对谯周憎恶之深。从历史评价看,王夫之以为谯周之恶胜于冯道。尤其是在蜀国尚存、姜维等武将力战曹魏情形下,谯周竟然著《仇国论》“为异说以解散人心”;在黄皓擅权蛊主、民劳兵疲情形下,谯周“塞目钳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奄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其“罪通于天”*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1、282页。。正如王夫之所言,谯周不过是在司马昭灭蜀前,提前为亡蜀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对郤正的评价,或者因其曾舍家从刘禅入魏,“后主赖正相导宜适”,故后人并未将其与谯周等同。从其《论姜维》看,似乎郤正与谯周有所不同*陈寿:《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第4册,第1068页。。然而从事实上看,郤正未死节并代作降书,与谯周劝降无异。后人苛责郤正较少,实际上是因为谯周之罪甚大,后人即多以写降书之事归罪于谯周*卢弼:《三国志集解》卷42《蜀书·郤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845页。。这是后人的误解,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谯周之罪遮蔽郤正之罪的事实。其实,即使在古代正统士人看来,郤正算得上出身于“叛逆世家”,如其父郤揖,先为孟达属下,后随孟达降魏,任中书令史。
郤正后来追随刘禅入魏并表现得忠心不贰,似乎体现了他对刘禅“忠诚”的一面。郤正《释讥》本“事无关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6《三国志·蜀·郤正传》,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陈寿将其全文收录于《三国志》,除了郤正文学水平不亚于张衡、蔡邕,还有对其“忠义”一面的肯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作为在刘禅身边“九考不移”之人,作为降臣、罪臣的郤正,如果在刘禅落魄之时不能追随其左右,并以此类“忠诚”作为一种政治投资,他还能有什么资本去博得晋朝的赏识并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呢?更深层次上看,郤正之父郤揖早先降魏,为郤正降魏准备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或政治机会。在“降魏”这一点上,郤正较他人可能具有更大的主动性。无论如何,郤正的一些做法,一定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士大夫,尤其是民族关系紧张、重视士人气节的宋代士人所不齿。其《释讥》被“屏蔽”,其书《郤正集》在宋代亡佚,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是《释讥》保存在郤正本传中,今天我们可能根本见不到《释讥》全文,甚至根本不知道此文的存在。总之,对《释讥》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文学史上蔽而不彰的某些作品,可能很好地保留着该作品所在时代或之先的语言、文字、音韵使用情况。《释讥》的“拟作”传统与体式渊源,以及其后仍有类似作品产生的现象*其实,不仅文学作品具有此类“拟作”传统,即如经部、史部、子部作品,皆有此类“拟作”现象,如扬雄《法言》、《太玄》拟于《论语》、《周易》,后世史家对《史记》、《汉书》之模拟,桓谭《新论》对陆贾《新语》之模拟以及后世以“新”为名的作品模拟,等等。,说明此类文体的性质较为复杂,可能具有“赋”、“文”双重文体特征。这种“拟作”现象,值得深入考察。《释讥》“缺席”文学史,既有文学史书写的原因,也与作者本人的文学地位、社会身份、政治态度等有关。今天我们重新书写文学史,对古代逆臣、贰臣、叛臣、降臣、奸臣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谴责、鄙弃,对其文学作品(甚至其他文艺作品)的价值,则应给予客观评价。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2016—1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 作者简介: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