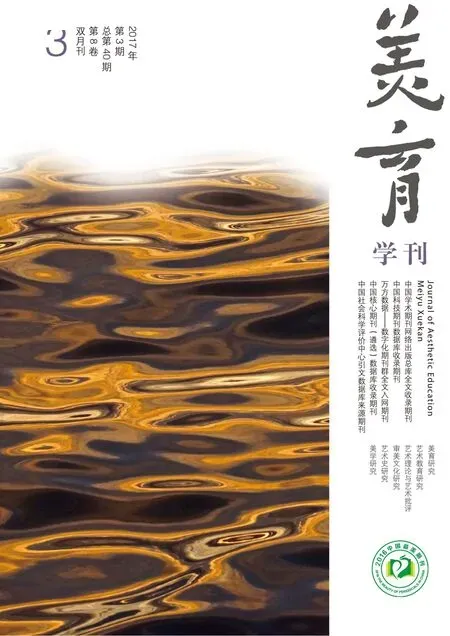“美感”一词及其中国现代美育发生
赖勤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美感”一词及其中国现代美育发生
赖勤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0世纪初汉语语境中的“美感”一词,与“美学”一样,都是外来词。“美感”一词初显为“中国”的美学术语,大致体现为从纳入1903年《新尔雅》到1915年《述美学》一文的阐释这一过程。作为译词,“美感”在王国维、蔡元培前期的文本中有所浮现,但并不明显和稳定,这是美学在初入中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在梁启超前期的文本中,虽然几无出现“美学”“美感”等词,但是以功利性作用为主导的美感观念得到突出表征。“美感”一词能够在后来得以普及,很大程度得益于美育之提倡。把“美育”释为“美感教育”,这是对“美感”的中国美学身份的一次重要确认。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的汉语体验,是他们切近中国现代美学尤其是美育发生于本土实际问题解决的直接方式。
“美感”;美感观念;“美感教育”;中国现代美育发生;汉语体验
美感问题在美学中具有根本性,“牵涉到美学领域里所有的基本问题”[1]。中西美学围绕这一问题而形成的见解不胜枚举,因此形成的争议也是不可胜计,这与“美感”一词本身有重要关系。“如同美一样,‘美感’这个词也是词意含混而多义,包含着好些近似却并不相同的多层含义。”[2]汉语“美感”一词具有间性的词性特点,在流行用法里出现杂乱状况,这是必然的。廓清“美感”一词,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杜绝理解简单化、泛化,较好的方式就是从汉语语源上进行考察,追溯历史,在美学上进行观照。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因西学东渐而产生了一批新名词,它们进入日常生活,亦进入思想文化领域,其中许多发展成为包括美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基本用语。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他们无不是西学东渐的介入者。借助他们的相关文本,可以探得“美感”一词在20世纪初(大致以1915年为界)汉语语境中的呈现情况,以及识得中国现代美学尤其是美育发生的一种特殊性。
一、作为译词的浮现
美学术语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美学条件下展开的,具有一个从日常的到专业的或者说从边缘到中心的美学化过程。就“中国”的美学而言,美学之有是以入中国为前提,故又存在术语译介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美学”本身就是一个外来的译名。“美学这个学名和学科,犹如哲学、文艺学(或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心理学等学名和学科一样,是舶来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美学”一词代表了中国美学术语形成的一种典型情况,即作为文化舶来品,有一个“汉化和合法化”的历程。[3]对于“美感”一词,首先亦应做如此观。其次,“美感”一词词义在现代汉语中并非单一,它的形成也有一个增加过程。在古代汉语中,“美”与“感”基本是分开使用的,如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礼记·学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所作的疏解:“善歌,谓音声和美,感动于人心,令使听者继续其声也。”因此,“美感”往往不可作为一个词看待,甚至不能承认它是一个原始的汉语词。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就是把“美感”当作外来词的。1903年上海明权社发行的《新尔雅》是20世纪最早出版的汉语辞典。在“释教育”部分提到“美感”一词:“离去欲望利害之念,而自然感愉快者,谓之美感。”[4]值得注意的是,该词被着重加点,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日译词看待。辞典、教材、译作、学校等都是近代中国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载体,它们提供的用语是中国现代学术话语形成的语言基础。作为外来词的“美感”,成为本土的美学术语,同样需要借助各种载体,并与本来就是外来的“美学”一道译入和并行。这一过程颇为复杂,但其结果是显然的。
清政府于1902年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两个章程都明确规定设立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的重要性,由此出现了一批从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著作。在这些译介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中,包含着与“美感”一词十分接近的情况,如:1902年东亚公司新书局发行的《心理学讲义》(服部宇之吉)有“纯粹悦美之情”,1903年上海时中书局编译的心理学讲义《心界文明灯》有“美的情感”,1905年留日学生陈榥编译的《心理易解》有“物之足使吾人生快感”,1907年杨保恒编写的《心理学》提出以“体制”“形式”“意匠”为“三要素”的美感概念。[5]相比之下,美学的译介在当时并不十分突出,这种局面的改变直至20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世纪之初的十余年,是中国现代美学观念的重要发生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事实上,现在通行的许多美学术语已在那时浮现。在译介的各科教材、专业著作中,都存在大量的专业术语现象,其中有些是无意识地带进或夹入,有些则是被有意识地运用。总之,它们都是美学术语得以生成的条件和环境。以下着重前期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文本。
据统计,王国维前期(1889—1911年)的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译稿约20种,包括署名的和未署名的(均刊于由他主编的《教育世界》)。在这些译稿中,已出现诸多现代美学基本词汇。如在1901—1902年翻译的《教育学》(立花铣三郎)、《教育学教科书》(牧濑五一郎)、《心理学》(元良勇次郎)中,已出现“美感”“审美”“审美的情感”“美术”“美之学理”等。又如1905年在两本“教育学”译著基础上编成的《教育学》中有“审美之情”一说:“其由美丑而生者,谓之曰审美之情;……教育不可不以制裁下等之感情,及养成高尚之感情为务。”[6]再如1907年的译文《孔子之学说》(蟹江义丸)中有这么一段:“诗,动美感的;礼,知的又意志的;乐,则所以融和此二者。苟今若无礼以为节制,一任情之放任,则纵有美感,亦往往动摇,逸于法度之外。然若惟泥于礼,则失之严重而不适于用。故调和此二者,则在于乎。”[7]这里两次出现“美感”一词,前者属古代汉语用法,后者已属现代汉语用法。就这些而言,王国维已创造了包括“美感”在内的各种语词,但它们的区别并不十分分明。
蔡元培前期(1898—1912年)含著、译、编等多类文本,涉及教育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各种学科,亦以译介为主。1901年10月他在绍兴及上海搜集国内外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学堂教科论》。该文对各级学校的课程进行研究,并分析清代学风败坏的原因。文中提到日本学者井上甫水把学术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哲学”。写于1901年10月至12月的《哲学总论》指出心理学是一种“心象之学”,是考定情感、智力、意志三种心象之性质、作用的“论理学”,其中“论情感之应用”的“应用学”为“审美学”。1903年的译作《哲学要领》(科培尔讲述,下田次郎笔述)把“宗教哲学及美学”都作为“心界哲学”。其中有对“美学”的介绍:“美学者,英语为欧绥德斯Aesthetics。源于希腊语之奥斯妥奥……其义为觉与见。故欧绥得斯之本义,属于知识哲学之感觉界。……要之,美学者,固取资于感觉界,而其范围,在研究吾人美丑之感觉之原因。好美恶丑,人之情也,然而美者何谓耶?此美者何以现于世界耶?美之原理如何耶?吾人何由而感于美耶?美学家所见、与其他科学家所见差别如何耶?此皆吾人于自然及人为之美术界所当研究之问题也。”[8]9-10还有对“美术”的介绍:“美术者Art,德人谓之坤士Kunst,制造品之不关工业者也。其所涵之美,于美学对象中,为特别之部。故美学者,又当即溥通美术之性质,及其各种相区别、相交互之关系而研究之。”[8]101906年的译作《妖怪学讲义录(总论)》(井上圆了)出现了许多谈“美”说“情”的译句:“论理、伦理、审美为心性作用之智、情、意各种之应用,以真、善、美三者为目的;教育学者,智、情、意总体之应用,以人心之发达、知识之开发为目的。”[8]94“世人知美之为美耳,以学术考之,必分析其所谓美者,而一一示其成分,如美丽、宏壮、适合、一统等是也。”[8]169“怪情者,非独美情之反对,具写之于美术,转示美性,而生几分之快乐。故人多喜妖怪之小说,及妖怪之绘画。”[8]171这两部译作出现了“美学”“美术”“审美”“美情”“美性”等一系列词,颇耐人寻味,有的显然与“美感”近义或等义。
蔡元培前期矢志“教育救国”,历经从“委身教育时代”到“教育总长时代”,期间赴德留学(1907—1911年)。他对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教育制度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展了实际工作。如在伦理学方面,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册。这些作品对“人格”“平等”“权利”“义务”“公德”“私德”等伦理学重要概念进行厘定,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具有拓荒的意义。伦理学与宗教、美学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故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学。如《伦理学原理》(1909年,据蟹江义丸日版再译)译道:“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于珍域,故为限制者,而非发生者”[8]356;“多神教常畀诸神以人类感官之性质,至为自由,故在美学界,极美满之观,是吾人今日所以尚惊叹于希腊诸神也”[8]413。又如《中国伦理学史》(1910年)指出传统(儒家)伦理学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又称哲学、心理学、军学、宗教学属伦理学,“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9]468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学习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等课程,特别注重实验心理学及美学,给他留下“极深之印象”的是美育。1911年10月归国后,他开始全力提倡美育。而他之所以提出美育,原因在于“美感”具有这样的性质和作用:“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10]这是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7年)中特别说到的。而“美育”“美感教育”是他在“教育总长时代”正式提出的(另论)。
美学是西学。美学进入中国是一个不断译介的过程,而之所以被译介又是一种选择行为。受时代风气影响,王国维、蔡元培注目西学,自觉、主动地学习外文,体验异域文化。王国维两次游学日本,蔡元培则三次赴欧洲,在德国学习哲学、美学。作为将美学译入中国的先行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美学渐入中国的两种路径。当然,译入中国的“美学”并不就是“中国”的美学,它包涵了许多异质成份,特别是日本因素。王国维22岁时到上海,入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他学日文,译日书,结交日籍老师。蔡元培而立之年在北京学习日文,先后试译日文版的《〈万国地志〉序》《日人败明于平壤》《俄土战史》《日清战史》《生理学》。他们在日文方面用功甚深,广泛涉猎译本书,不仅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而且与日本文化结下了难解之缘。从前期的译介情况看,他们无不首先从日本文化中汲取滋养。日本在美学从西方到中国的过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是中国现代美学术语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美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美学术语不明显、不稳定都是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译介的增多,“美学”“美感”等将作为完整的汉语词形式并被普遍接纳,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1915年,兹举二例。一是《辞源》列有“美感”词条:“[美感]谓审美之感觉也。其要质有三:一曰物质,如色、音之类。二曰关系,即集合物质而变化调和之,如图画之颜色、音乐之节奏。三曰理想,即趣味,为构成美感所尤要者。”[11]114同时,所列词条有“美学”“美育”“美情”等。如:“[美情]心理学名词。由美丑之判断而生之情操曰美情,亦曰审美的情感。如见天然风景及绘画、雕刻之美者,则愉快。见不洁丑恶者,则不快是也。”[11]113二是徐大纯的《述美学》言及“美学的定义,及其历史,其要素,其分野,其内容与形象之种类”。他称“美学”是“最新之科学,亦最微妙、最繁赜之科学”,“美”是一种“特别之感”,“而凡特别之感之中,惟快感为美之重要元素。……而其快感是名美感。Aesthetic feeling,美感者,由美而生之感者之谓也。”还说“快感”为“美之重要元素”,“然快感与美感,正自有别。……即如何之快乃为美,如何之情感乃非美。此在美学上,诚最有研究价值之问题也。”[12]《辞海》和《述美学》都对“美感”一词予以解释,利用“审美的感觉”“快感”等不同概念进行揭示,释义内容比较丰富。不仅如此,两者代表了日常的(辞典的解释)和专业的(美学的解释)两种释义方向。这种分化倾向表明“美感”一词已具术语特征。当然,进一步将“美感”专业化,提升它的美学内涵,还需要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二、美感观念的表征
语词与思想是表里关系,特别是外来词,这种关系更为显著。一种外来语之输入即代表某种外来的思想的进入。作为外来词的“美感”必然因此而成为美学期待,亦唯此才能成为地道的美学术语。20世纪初是一个思想杂陈、新旧过渡的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为新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机遇。蔡元培、王国维译介外国美学,多少是在直接“接触”各种外来美学术语的基础上实现的。相比之下,梁启超显得特殊。作为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之一,他是个不谈“美学”的美学家。他的笔下竟无“美学”二字,“美育”也仅是在1922年4月北京美术学校讲演《美术与科学》中提及(“贵校是唯一的国立美术学校,他的任务,不但在养成校内一时的美术人才,还要把美育的基础,筑造得巩固,把美育的效率,发挥得更大”)。至于“美感”一词,他首先使用是在1910年初《国风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说〈国风〉中》一文(“即以一身论,舍禽息兽欲外,不复知有美感”),而再次用及直至在1920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湖景之美……助长起我们美感”)。故对梁启超,需要单独在这里论及。
先说“观念”。观念是需要借助语词(或曰关键词)来表达的可社会化的思想,有一个选择、吸收和再创造的形成过程。作为观念,它往往由诸多的概念共同构成。观念的复杂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表征方式。用于表征某种观念的并非一定就是某词本身,还有与这种观念相通的其他语词。外来词有一个本土接受过程,起初在词形、词义上必然并不固定,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时人缺乏相应观念。溯源“美感”一词还需要考察美感观念的其他表征语词,如“美术”“文学”。两词在蔡元培、王国维那里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美学概念形式。蔡元培在1900年前后多次谈到“美术(学)”,如:“美术学,为抒写性灵之作,如诗词绘事”(《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1900年);“文学者,亦谓之美术学”;“近世乃有小说,虽多寓言,颇详民俗,而文理浅近,尤有语言文字合一之趣”(《学堂教科论》,1901年)。把“文学”归为“美术”,而“美术”又可作“美学”(“审美学”),这种说法在今天有所影响。我们常把“美的”“美感的”或“审美的”,皆视为可通用。王国维不仅译介了这些概念,而且有更为深刻的见解,如:“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红楼梦评论》,1904年)。又如:“古雅之致,存于艺术而不存于自然”;“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术品之公性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年)。再如:“文学者,游戏的事业”(《文学小言》,1906年);“诗歌者,情感的产物”(《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年)。王国维以西方美学(文论)来反观“美术”和“文学”,确立了审美独立性原则,而这与他的“学术独立”“哲学独立”等观点是统一的。他重视“美”的性质、功用的阐释,专注的是“美”而非“美感”,所建立的是一个以“美”为核心、以人生价值为取向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偏于形而上学,注重的是哲学、美学,指向的是现代人生。蔡元培、王国维的见解,都已包含美或美感的作用是超功利的先进认识。
再看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的梁启超。戊戌政变之后(1898年秋),梁启超负笈东渡,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还有诗(话)、文、小说等,后辑成《自由书》(1899年)、《新民说》(1902年)、《德育鉴》(1905年)、《饮冰室诗话》(1902—1907年)等。此时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初发期,以“三界革命”说最著名。他在《夏威夷游记》(1899年)中提出以“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为“三长”的“诗界革命”和以“觉世之文”“欧西文思”为内涵的“文界革命”。他又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以下简称《论小说》),成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此文倡言“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不仅思想深刻,而且影响深远。正如张法所评价:“他以《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在一种‘革命’营造中,一方面使小说为艺术的最上乘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诗文书画为主体的艺术结构,另一方面让艺术成为唤起民众、塑造现代性新民的有力武器,显示了美学巨大的政治/社会功用。”[13]藉此名篇,并结合其他,我们可以一窥梁启超遣词造句的特点,而这恰恰能够彰显梁启超前期美学话语的特色。
延用。这是指保留已有语词形式(但词义有所增减)或者进行简单的改造(如增减字数)。古代汉语文论范畴不胜枚举,一个显著特点是言简意赅。体现在《论小说》中就是把小说“支配人道”的“四力”概括为“熏”“浸”“刺”“提”。其中谈“浸”时又这样说:“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14]884-885还有称“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小说”既“可爱”又“可畏”,等等。梁启超在具体说明时,好用“余×”“可×”“大×”等构词方式。又如《惟心》(1900年)先这样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接下来举例说:面对月夜、黄昏、桃花或江、舟、酒时,分别产生“余乐”/“余悲”、“余兴”/“余闷”、“欢憨”/“愁惨”、“清净”/“爱恋”、“雄壮”/“冷落”的“绝异”之“境”。同样的美感对象,产生不同的美感境界。他认为,造成美感的不同,“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此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表述:“天下之境,无一非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乐之、忧之、惊之、喜之,全在人心”,“境则一也,而我忽然而乐,忽然而忧,无端而惊,无端而喜”,“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15]361-362这些尽管并非纯粹谈美和美学,但都与审美(美感)现象直接相关。梁启超善用例证的论证方式和对举、排比、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段,在措词方面颇有讲究。
借用。这是指利用日常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术语、概念进行说明的一种方式。中国传统文论本具有这种特点,如“取象”“比兴”蕴含的就是一种借物喻人的伦理观念,再如“境界”原是道家、禅家的用语,而在后来成为重要的审美范畴。《论小说》包含了许多佛语、佛义、佛理,兹不详举。梁启超对佛教、佛学从社会、文学等多方面展开讨论。如《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指出信仰佛教的六大条件:“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独善”“入世而非厌世”“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同时还指出佛学之“广”“大”“深”“微”。[14]906-9101920年代初他转向佛学研究。《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年)指出佛典的输入和翻译具有重要意义,如拓展中国人的视野、扩大汉语词汇、增辟人们的想象空间,能带来汉语语法及文化的某些变化,同时还对学者思想、文人创作产生深刻影响。可见,翻译文学对中国一般文学、国语(包括词义、语法、文体)的影响很大。梁启超对佛教、佛学的深刻体会,还表现在《什么是文化》(1922年)一文借用佛家术语“业”(即创造、创造力)来形象地说明“美感”:“美感是业种,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诗,落到颜色上成一幅画,是业果,是呆的。”[16]佛教成为包括美学在内的梁启超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新用。这是指在不参考已有的各种语词的情况下进行创造的方式。一般地说,外来词是一种新造词,典型的如音译这种方式。《自由书》是梁启超的留学日记,其中有一篇《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他这样解释:“‘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15]375“烟士披里纯”,今译“灵感”,本是一种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但并不神秘的审美心理现象,这里却把它当作包括美术家在内的一种人格动力机制。梁启超的新造词,当以“移人”为代表。该词两次出现在《论小说》:“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文字移人,至此而极。”又如《佳人奇遇·序》(1898年):“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再如《新民说》:“天下移人之力,未有大于习惯者”,“崇贵逸乐,最足移人。”与“移人”相似的还有“情之移”“移我情”,前者如《饮冰室诗话》第87、179则,后者如《饮冰室诗话》第161则、《致汤觉顿》(1910年10月23日)、《〈秋蜷吟馆诗钞〉序》(1915年)、《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1915年)、《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1922年)、《致胡适之》(1925年7月3日)。出现在论文、诗话、书信、序文等之中的“移”词,显然是与“移情”一词十分接近。但从来源看,并非出自立普斯美学,而是梁启超自创。
梁启超文本用语讲究,思想蕴含丰富,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的一道独特景观。作为最早的西学译介者之一,梁启超以融西入中、除旧启新为理想之追求。他在小说方面独树一帜,理论、创作、翻译并举,尤其是提出的“力”“移人”等美学范畴具有标识性。而他之所以在这方面用力甚多,实际是把“小说”作为“文学美术”的代表,以之进行启蒙宣传。正如他在《新民说》中所言:“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抵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17]单就“文学”而言,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如他对小说、诗、戏曲、美文等文类采取“离合、重组以及等级的升降”的态度,“于文学版图的分割屡屡变异”,但是最终也都指向“从偏向文学功能到注重文学美感的理念转化”。[18]如此看来,梁启超“善变”中有“不变”的一面,体现之一就是重视“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与启蒙功能。他几乎不提“美感”,但“新民”、文类等诸多问题并没有游离于美学视域之外。事实上,谈文学、美术都无法避开谈及美和美感,而美与美感又是十分接近甚至一致的概念和问题。当然,从建立美学身份的角度而言,“美感”一词需要在相应的理论、学科和思想的不断发展中确立和完善。
三、关于“美感教育”
“美感”一词能够在后来得以普及,很大程度得益于美育之提倡。美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特色。从世纪初的王国维开始,美学就被烙上美育的标签,而美育大行其道,又始于蔡元培在民初的提倡,以《对于新教育之意见》(1912年,以下简称《意见》)一文的发表为标志。该文先后在《民立报》《教育杂志》《东方杂志》上公开,特别是以“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之名登载在《临时政府公报》,显示出权威性。在《意见》中,蔡元培初次提出“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9]而这个“美感之教育”,在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中明确为“美感教育”:“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美感教育精神也在随后的各类各级教育规程中得到体现。如:“图画要旨在使详审物体,能自由绘画兼练习意匠,涵养美感”(《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2年12月2日);“陶冶情性、锻炼意志,为充任教商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师范学校规程》,1912年12月10日)。提倡美育作为教育宗旨的一部分,由官方公布并逐级落实,这种“自上而下”的途径,在有利于尽快完成改革教育制度的同时,使得美育理念得到广泛传播。
蔡元培是致力推行美感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他宣传美育是一个不断阐释“美感”的过程。“美感”是构成美育观念的关键词。从《意见》一文使用情况看,“美育”18次,“美感”9次,两者相得益彰。而这个由康德所创造、具有中介作用的“美感”概念,被蔡元培尝试利用,成为“超轶政治之教育”的“世界观”和“美育主义”的主体内涵。在约写于1912—1916年期间的《孑民自叙》中还一度称“美学(之)教育”:“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种哲学思想为前提。而哲学思想之涵养,恃有美学之教育,故美学教育为最当注意之点。”[20]随着“五四”前夕发表“以美育代宗教”,通过演讲等方式的不断深入阐明,至1930年代初他已表述得十分清晰。如为《教育大辞书》(1930年)而撰写的专门条目:“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21]又如《美育与人生》(1931年前后):“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22]前者从目的,后者从对象、作用两方面解释了美育,强化了美育的内涵,即是对感情的陶冶和激发,而这无疑就是“美感教育”的实质。但就蔡元培在民初初次提出的“美感(之)教育”而言,它毕竟是“新学语”。显然,对于“美育”的理解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方式,还有“情感教育”(简称“情育”)、“审美教育”“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美学教育”等,有的甚至先于“美感教育”而出现。因此,“美感教育”这一概念的合法性,还需要我们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做进一步分析。
王国维曾发表多篇论美育的文章。如《论教育之宗旨》(1903年)指出:“情”是精神的一部分,“美”是“情感之理想”,而“美育”即是“情育”,“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又为德育与智育的手段”。又如《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年)则是“备举孔子美育之说,且诠其所以然之理”,用以启发“世之言教育”。再如《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年)指出:“古雅”处在优美与宏壮之间并兼有两者之性质,而它又是一种能够通过后天修养而得之的能力,“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这些都已成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之经典,具有开创性意义。王国维阐说美育,吸收德国的哲学、美学,致力发掘中国美育传统,是成功开创中西“化合”的典型。他的“先知先觉”也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王氏所论,且皆近代教育之先导,其头脑清新,眼光明锐如此,于开发近代风气,厥功伟已。”[23]160对于王国维的美学、美育之贡献,似乎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然而从时间上看,蔡元培比王国维更早地使用“美育”一词并提出“情育”的观点。《哲学总论》写于1901年10至11月,在谈到纯正哲学研究之目的时,他说:“教育学中,智育者教育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9]357“美育”是“情感之应用”,是与“智育”“德育”相区别的“情育”。蔡元培从一开始就把美育夯定在知意情分立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为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全面倡导美育做好了铺垫。“情育”的观点与稍后的王国维的观点相呼应。从《哲学总论》到《意见》的十余年间,是蔡元培广泛学习包括美学、美育在内的成长时期和重要的学术积累时期。他对美育的“美感教育”的理解已不只是定位于哲学的“情育”,而是有着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考量。此时期尽管也是王国维研究美育的重点时期,但是他热衷“哲学的观察”,深陷哲学之困境。美育只是王国维为学的一个阶段所为,而蔡元培是把美育之提倡作为个人的终身事业。
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有《霍恩氏之美育说》(1907年,为佚文,或是译文)。此文是一篇介绍西方美育家的专论文章,其中有“审美教育”“审美的教育”“审美的感动”“审美之休养”“审美之兴味”等各种“审美”用词。在王国维的文本中,则有“审美的嗜好”(《红楼梦评论》)、“审美之境界”“审美之趣味”(《孔子之美育主义》)等多种形式。把“审美教育”作为一个概念使用,实以李叔同为早。在《图画修得法》(1905年)这篇被认为中国最早介绍西洋画知识的文章中,他写道:“今严冷之实利主义,主张审美教育,即美其情操,启其兴味,高尚其人品之谓也。”另在“自在画概论”部分提到“精神法”,其中又这样写道:“吾人见一画,必生一种特别之感情。若者严肃,若者滑稽,若者激烈,若者和蔼,若者高尚,若者潇洒,若者活泼,若者沈著,凡吾人感情所由发,即画之精神所由在。”[24]此中提及的“审美心”“特别之感情”等说法接近“美感”。除曾译“美学”为“审美学”之外,蔡元培也只是在《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美学讲稿》(1921年)等中偶尔使用“审美”的说法,遑论“审美教育”。“审美”一词应当有特殊用法。正如陈望衡指出:“审美,在英语中为aesthetic,它很少独立存在,总是与别的词连在一起,构成诸如‘审美态度’、‘审美判断’、‘审美愉快’、‘审美价值’等概念。这样说来,审美就不能等同于审美感受——美感了。”[25]故此,“审美教育”与“美感教育”有所不同,前者突出美育实施过程中的客体(美的对象)与主体(受教育者)的主次关系,而后者突出对这种关系的超越及统一,两者不能完全一致。
把文学、美术作为教育课题,王国维、梁启超都有切实的思考。王国维在关于“文学与教育”的“教育偶感”(1904年)中,有感于“美术之匮乏”而要求“文学之趣味”,并称“精神上之趣味”必定是通过千百年的培养和个别天才人物的引领才能达到。他告诫那些倡言教育者:如果不谋求“精神趣味”,那么将是十分愚昧无知的。梁启超在《自由书》(1899年)中指出:改变“固无精神”的现状需要“浚一国之智,鼓一国之力”,其方法就是以“自由”为工具的“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就是“自由教育”。他在第77则诗话中又说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26]他们都提出了用于改造国民性的“精神教育”,其包含的美育精神已昭然若揭。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美术教育”的说法。“美术教育”的核心在于“美术”。“美术”也是一个外来词。它经由王国维、刘师培、鲁迅等一批先见者的主导和铺垫,通过“南洋劝业博览会”“上海图画美术院”《美术丛书》等会展、学校、出版物的社会辐射面,不断扩大和普及,终为民初社会所全面接纳,被确定为现代汉语的固有名词。而它的涵义,则从“美育”“美学”“美化”或“文学表现”(即美之“术”)、“艺术”等混用状态中逐渐疏离出来,成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特称。[27]这就是说,“美术”一词在形、义两方面至民初已基本定型,并成为流行的美学概念。从这方面说,“美术教育”也就不能等同“美感教育”。当然,蔡元培对“美术”的理解有一个趋于细密、明确的过程。他译介“美术”始于1900年,是把“美术”作为广义的概念,包括“文学”,又与“美学”通用(见前述)。至《意见》一文,则视“美术”为“美感”:“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这是取美术的美感作用,故又有“图画”“唱歌”“游戏”等皆为“美育”之论。《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指出“歌词”“演说”皆有“美术作用”,还把“美术”作为与“宗教”的对应。再至《美育代宗教》(1932年)则直接断言“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术不能代宗教”,而“美育”与“美术”之所以不可互代,是因为“美育是广义的,而美术的意义太狭”。蔡元培谈美育不离开美术,这是他从偏美育理论到重美育实施的思想之体现。
应该说,“美感教育”是一个更为严谨、科学的概念。“情育”“审美教育”“美术教育”“美感教育”各有偏重,而“美感教育”更具包容性,其内涵和外延也更大,故也更加适合表明美育之提倡的可行性。蔡元培在民初提出美感教育的美育,固然是他的自觉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时代必然。正如王善忠指出:“要给美育下定义,一是不可能离开美感(当然,也离不开美,因为没有美,美感也就无从谈起)和教育这两个基本构成要素,二是还要考虑到这界说能为人们所理解、赞同和把握。”[28]王国维、李叔同、梁启超的美育观的影响程度,受制于一些客观的条件,或因理论精深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或因在域外刊物发表而鲜为国内读者所了解。而蔡元培美育观之所以得以广泛流行,很大程度是与他的特殊身份,与教育革新、政治运动的密切配合有直接关系。正如刘海粟所评:“蔡先生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口号与儒家学说作了综合,使新老知识分子皆能接受。美育一说,更加引起我的共鸣。”[23]292
谈到“美育之提倡”,我们还不能忘记鲁迅的贡献。鲁迅前期(1902—1917年)多次提出有关文学、美术具有美感作用的观点,如:“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也”(《科学教史篇》,1907年);“纯由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旨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化偏至论》,1908年)。他在加入特别班问学期间(1908年)与章太炎讨论文学定义时还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29]这些观点萌生于他留日期间,表达的是通过文艺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启蒙理想。1909年夏留学归来之后供职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的5年期间,鲁迅做了大量的推广美育的工作。1913年他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对美术作用作出了独到见解:“播布云者,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还对美感的产生作了科学的、唯物论的解释:“盖凡人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一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30]该月刊还载有他的两篇译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上野阳一)。除传播艺术美育、社会美育之外,鲁迅还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推广美育的实际工作,如到“夏期美术讲习会”讲演,筹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筹建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关注新剧(话剧、文明剧)的发展。鲁迅前期的美育观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和蔡元培思想的直接引导。随着“文学革命”的展开和唯物主义美学思想的深入,鲁迅对美感的社会性和其中潜在的功利因素又逐渐加以阐明,使之趋于完整。
四、结 语
在20世纪之初的汉语语境中,“美感”一词处于微妙的境地。把它从外来的转化为本土的、从日常的提升为美学的,并作为美学术语用于解释美学问题,这一过程包含了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学人的不断努力。特别是美育之兴起并被蔡元培确立为“美感教育”,这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所谓“起国人之美感”(鲁迅语)就是激发、培养国人的情感,张扬国人的生命活力。这使得中国现代美育成为有深度的美学理论,成为以“育人”为目标、以“救国”“救人”为直接目的的文化思想。从改造、提升国民精神这一高度审视,中国现代美育的发生的确是在观念、思想层面展开,但是不可能离弃具有定型功能的汉语。西学东渐背景下,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生需要通过学人汉语体验才能形成实质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汉语的现代性,也正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才有感于新学语之输入或者创造的必要。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的汉语体验,是他们切近中国现代美学尤其是美育发生于本土实际问题解决的直接方式。至于“美感”一词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之后的流变,笔者将另行追踪。
[1] 朱光潜.美感问题[N].光明日报,1962-07-16.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02.
[3]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8-179.
[4] 沈国威.新尔雅:附题解·索引[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55.
[5]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J].文史知识,2000(1):75-84.
[6] 王国维.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8.
[7]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47.
[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9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0]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08.
[11] 陆尔达.辞源[K].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12] 徐大纯.述美学[J].东方杂志,1915,10(1):63-67.
[13] 张法.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J].文艺争鸣,2008(1):40.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4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63.
[17]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7.
[18] 夏晓虹.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86.
[1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
[20]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16.
[21]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99.
[22]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90.
[23] 陈平原,王枫.追忆王国维[G].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24] 郎绍君,水天中.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卷[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4.
[25] 神林恒道.“美学”事始——近代日本“美学”的诞生[M].杨冰,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2.
[2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8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333.
[27] 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G]//浙江大学美术文集:上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351-385.
[28] 王善忠.美感教育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10.
[29]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27.
[30] 鲁迅.鲁迅大全集:第1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68.
(责任编辑:紫 嫣)
The Term "Beaut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LAI Qin-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erm "beauty" in Chinese context is a loan word from abroad like "aesthetics". It first became a Chinese aesthetic term during the time when it became an entry inNewEryain 1903 and was elaborated upon inOnAestheticsin 1915. As a translated word, "beauty" occasionally,not steadily, appeared in the earlier works of Wang Guowei and Cai Yuanpei, a phenomenon that was bound to occur after its initial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Although they did not appear in the early works of Liang Qichao, a utilitarian aesthetic concept was clearly visible. The subsequent spread of the term "beauty" was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efi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s "education of the beautiful" was an important step in establishing its Chinese aesthetic identity.The language experience of these three great masters at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was the direct way in which they tried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posed by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or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at matter.
"beauty"; aesthetic idea; "aesthetic education";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7-02-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美学的日常生活维度研究》(14YJA75101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赖勤芳(1972—),男,浙江金华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3-00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