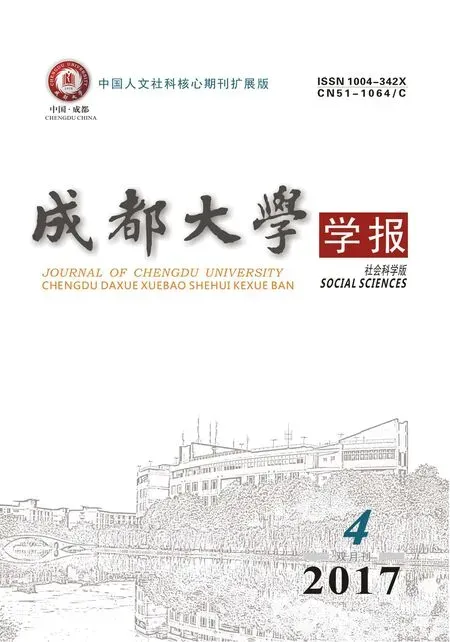奈达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面对面”
杨司桂
(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语言文化·
奈达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面对面”
杨司桂
(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奈达翻译理论是一种建构在20世纪60年代对《圣经》翻译的实践研究基础之上且被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已经“过时”了的翻译理论;而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是构筑在生态学基础之上且被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当下的“热点”译学理论之一。通过对这两大理论在文本选择、语境、译者因素以及文本转换等维度之比照阐释,我们发现,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下不仅没有过时,还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及强大的生存力,在某些方面比生态翻译学还略胜一筹。最后,基于奈达翻译理论的视角,文章对生态翻译学今后之建设提出美芹之献。
奈达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比照阐释;译学建设
一、引言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以及翻译理论家,其翻译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后,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的翻译研究,还激发了中国学者向西方学习翻译理论的热忱,在中国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刘士聪教授曾经这样评价过“奈达在中国的知名度:奈达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奈达的名字你不可能不知道”[1]81。可好景不长,到了后来,奈达的翻译理论跌落为人人批判的靶子,不仅“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2]8,还“对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横加批判、甚至彻底否定”[3]4。
那么,奈达的翻译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在当下的翻译研究中真的过时了呢?本文将对奈达的翻译理论与当下译学研究热点“生态翻译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对该理论的后续建设提出美芹之献,旨在说明: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下仍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及强大的生存力。不仅如此,还对“生态翻译学”之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启迪作用。
二、奈达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学之“面对面”
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建构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人类学、词汇学、信息论等理论基础之上,针对《圣经》翻译实践之研究而萌发、发展及不断完善的。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是建立在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即: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选择/适应”理论为基石[4]80-87,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尽管这两大理论表象上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主要内容上如出一辙:
第一,生态翻译学的核心观点是“翻译的适应选择论”,具体而言就是:“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4]86胡庚申把第一部分简称为“天择”,即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而把第二部分简称为“人择”,即译者接受了原文的生态环境之后,又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最终行文的选择。[4]87翻译的适应选择论就是从“天择”到“人择”的转换过程。胡庚申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为例对“天择”进行说明,认为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应当是诗人译者,或者是对译诗有一定造诣的译者,否则这个译者就难以被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所选中,或者说,在这一点上译者就有可能被淘汰掉。接着,胡庚申又以读者为对象对此进行论述,认为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的是儿童作家译者或是对翻译儿童作品有一定造诣的译者。如果被淘汰的或未被选中的这些译者硬要去翻译,其译品质量就会不尽人意,可能免不了会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惩罚”[5]121-122。
关于“翻译的生态环境选择译者”,尽管奈达没有使用过这一表述,但说过类似的话,“大体上掌握一种语言是一回事,精通某一学科知识则是另一回事”[6]150,“对所译题材必须十分了解,既有一般的了解,又有特殊的理解,这也是向翻译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不论译者技艺多么高明,如果对所译题材的内涵意义无所知晓,必会铸成翻译大错。"[7]58-59他还指出,译者必须具备“移情”的本领,体会原作者的真情实感,“除非译者对原作者也有真情实感,否则即便具备了所有必要的技术知识,还是未能把翻译工作做好。”[6]151其实,对原作之了解及“移情”,就是译者适应原作,或原作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倘若对原作不了解(包括一般了解及特殊了解),没有什么情感而言,译者也不会去翻译此类文本材料,否则就达不到应有的翻译效果。不过,一个对译语能充分发挥优势的优秀翻译家也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种文学题材的翻译,如诗人及翻译家徐迟就深谙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题材的翻译,冰心也是如此,既能翻译诗歌,又能翻译文学小说。从这点来说,“原文生态环境选择译者”这种说法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我们再来看看“人择”。“人择”指的是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选择的阶段。至于怎么选择,胡庚申认为,总的原则是“择善而从——即译者为‘求存’而‘择优’”。[5]125即是说,只要译文能被译入语的翻译群落所接受,译者可以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等,在具体的句式、语态等微观操作层面上也可适时而变。我们认为,这种“人择”的观点,与奈达所说的为使译文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而对原文做出灵活处理”之说法如出一辙。奈达在他的《翻译新视角》一文中强调:翻译过程就是“译者要做出成千上万次的涉及选择与处理的决定,以顺应另一种文化,顺应另一种语言,顺应不同的编辑和出版商,最后还要顺应读者群”[8]7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译入语生态环境,译者须在翻译过程中费劲心思,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照顾到不同的阅读对象、赞助人因素等译入语翻译生态群落,而这一点,奈达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实例。在宏观上,他把翻译的过程划分为四个过程:分析、传译、重组和检验,具有可操作性;而在具体的微观操作层面上,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解读能力及潜在的阅读兴趣,奈达认为可以把原文翻译成不同的译文:为儿童而翻译,或为初识文字者而翻译,或为成人识字者而翻译,抑或为专业人士而翻译等。[6]158此外,奈达还使用了“功能对等”这个“总闸”来协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平衡,在原理上也具科学性。
第二,生态翻译学上的翻译生态环境与奈达的“语境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翻译生态环境又称“译境”,是生态翻译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即‘翻译群落’)互联互动的‘整体’。”[4]90它既有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之分,又有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别;既包括客观环境与主观环境,又包括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等等。尽管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新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的译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或活力。然而,反观一下奈达对语境的阐述,我们发现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环境已被囊括其中,尽管“貌离”,实则“神合”。例如,奈达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与非语言语境,语言语境又包括横组合语境、纵聚合语境、语篇语境等,非语言语境包括口头语境、交际语境、场景语境、受众语境以及文化语境等。[9]157-182而其中的文化语境主要指的是原文及目的语中整个的人文环境,而文化主要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度文化,所以说,奈达的文化语境可以说是囊括了一切人文环境。尽管两者“异曲同工”,但奈达的语境论在分类及内容的阐述上要比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环境论要稍胜一筹。胡庚申认为,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生态环境”与“语境”有所不同,如语境就不包括语言本身或语言使用[4]89,但是我们发现,奈达语境中的横组合语境与纵聚合语境就是一种语言的组合关系,是一种静态的语言搭配关系,应该属于语言本身或语言的使用语境。从这一点来看,奈达的语境论与“生态环境”也别无二致,实乃“貌离神合”。
第三,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论”或“译者主导论”在奈达的翻译观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生态翻译学的一大特色就是突显译者的作用,把译者从“原文—译者—译文”这三元关系的流程中抽离出来并加以强化,把活生生的、感性的、富有创造性的译者推向译论的前台。而这一理念最终的落实需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微观操作层面、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另一个是在宏观理性层面、在翻译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4]221其实,微观操作层面以及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导,具体而言,就是在协调译者与“翻译群落”其他成员的关系中起到的主导作用,使译文最终在译文的生态环境中得以存活以及长期有效,此外微观层面上的“译者主导”还体现在译者主体性在具体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充分施展。而这一点,奈达的翻译观均已触及,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例如,在微观的翻译操作层面上,奈达是在竭力调节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既要使原文作者的一切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又要顾及译文读者的接受力,还要照顾到目的语中其他角诸如出版商、编辑等的感受。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奈达的翻译理论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所谓译者的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作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征,简言之,指的就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10]91。鉴于此,奈达在实施翻译行为过程中的分析、传译、重组和检验等四个阶段无不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的主体性。在分析阶段,主张对原文做到体贴入微,竭力“达旨”;在传译阶段,主张充分利用译入语的优势,寻找自然对等语;在重组阶段,主张为适应译入语的生态环境而进行修订或增补;而在检验阶段,注重“事后追惩”制约机制的介入。这一切无不凝结了译者的主体性。而在宏观理性层面、在翻译伦理层面的“译者责任”,奈达在其翻译观中也进行过更为严密且深入的阐述:
“翻译工作者要想做出一流的译品,必须具备某些基本的条件。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语言能力强,能够准确、清晰以及流畅地表达思想。翻译工作者必须才思敏捷、反应迅速,记忆力强。还必须具有语言创造力。……对所译题材必须十分了解,既有一般的了解,又有特殊的理解,这也是向翻译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翻译工作者还必须心智诚实,具有译德。……翻译工作者必须能够与人共事,欢迎并接受别人的意见,否者不宜参与任何翻译项目。”[7]58-59
第四,生态翻译学中“文本移植说”所牵涉的“三维转换”(语言、文化与交际)与奈达的为取得“功能对等”而采取的对原文一系列之“改写”措施,可谓是“志同道合”。生态翻译学认为,所谓翻译就是“文本移植”,“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生态系统中去”[4]201。由于每一文本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生态及文化生态,有着固有的文本生态结构系统,所以“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像个人或民族的‘适应’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的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11]6翻译生态学认为,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能得以“求存、生效”[5]42,或为了取得较高的“存活度”[4]241,就得对原文进行语言维、文化维以及交际维上的“三维转换”。具体而言,在翻译时,在语言层面上要关注文本的语言表达,要把原文表达形式的输出以及接受语读者的接受力协调好;在文化层面上要考虑翻译的语境效果,即接受语对“异域文化”的承受力,能否在接受语文化语境中得以接受;在交际层面上就是要使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得以呈现。
其实,奈达的翻译观也是一种为了使原文在接受语中得以生效及存活的翻译观,与生态翻译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语言表达上,奈达一面注重在接受语中寻找自然对等语,一面注重原文形式的保留,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生态平衡”。在文化维度上,奈达认为翻译家不应进行文化翻译,而应对原文文化给予保留,只有在三种情况之下才对文化或文化因素进行加工处理:“(1)语篇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2)语篇在读者看来可能毫无意义;(3)译文‘语义过载’而不能为一般读者所看懂。”[12]110但是,另一方面,奈达又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所以翻译时又不得不对文化进行调和,最终使翻译达到一种较好的接受语境效果。至于交际层面,奈达论述得更为深刻,因为他主张“翻译就是一种交际”,“必须清晰地反映原文的意义和意图”[6]166。除此之外,奈达还讲究在其他层面上进行调整,如受众语境、及时交际语境等,总之,奈达的调整幅度及宽度要比“三维转换”要多些,真正做到了多维转换。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中许多内容,甚或核心思想与奈达的翻译理论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或类似之处,囿于篇幅,就不一一进行比照阐述。此外,由于生态翻译学与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如此之“叠影重重、心心相印”,我们从中能领略到:奈达的翻译思想在现实的翻译研究中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及强大的生存力。不仅如此,还对当下的热点译学“生态翻译学”之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启迪作用。
三、对当下生态翻译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生态翻译学是利用生态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学科,不仅给我们的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兴奋点”及“增长点”,刷新了人们对一些翻译研究现象的认识,而且拓宽了翻译研究的研究视域,产生了新的翻译研究范式。但是,通过生态翻译学与奈达翻译观之“面对面”,我们发现,生态翻译学有一些需要充实的地方,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一,正如胡庚申所说,生态翻译学毕竟是建构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特征之同构隐喻和概念类比基石之上,因而生态翻译学的内容“喻指”的多、“实指”的少。如在提到“翻译生态环境”时,其论述还是万变不离其“语境”,尽管胡庚申反复指出,“翻译生态环境”在内涵上比“语境”要宽,是一种“译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一种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体,然而,这一定义其实是“语境”概念的泛化。另外,胡庚申在对“译境”分类时,只是把它分为大、中、小等环境,或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等,但是这些细化的环境之具体所指却语焉不详。而奈达在对语境进行分类时,不仅做到了细化,还进行了非常翔实的阐述。又如,在论述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时,胡庚申说道,适应选择包括以原文为要件对译者进行适应以及以译者为要件对译文的最终行文的选择,但在具体的论述上也显得空洞苍白。有关生态翻译学“实指"层面的内容,尤其是对语境进行分类等方面的“实指",我们期待着胡庚申给我们呈现出更为精彩的界定或论述。
第二,在喻指的层面上,“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契合度能否更为贴近?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论是借用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内容,达尔文在其适应选择论中提到,自然界中的物种对环境的适应以及环境对物种的选择是绝对的、“刚性”的。一旦大自然对某个物种进行了淘汰,就意味着该物种“绝迹”、“消失”或“灭绝”,如恐龙、南极狼等;而生态翻译环境对某个译品的适应选择则是相对的,某个译品在某个时期可能被“淘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译品可能会被“激活”,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例如,鲁迅主张硬译的译品在他那个时代可能被“淘汰”了,不过,现在主张异化的学者或读者对鲁迅的这种译品却“情有独钟”,此外林纾的翻译作品也是如此,限于篇幅,在此就不展开阐述。总之,一个是“刚性”的喻体,而另一个是“柔性”的本体,如何把这两者更好地结合,或找到更好的契合度,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三,为生态翻译学多注入“特质”,增强本学科之“个性”。通过生态翻译学与奈达翻译理论之比照,生态翻译学几乎还没有跳出传统译论的“窠臼”,如“译者中心论或主导论”;“三维转换”之文化维、语言维以及交际维;事后追惩中的“读者反应”等。“译者中心论或主导论”其实就是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或翻译主体性研究;就国内对这两者的研究状况而言,葛校琴[13]的《后现代性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2006)以及段峰[14]的《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2008)这两本专著已经把翻译主体性以及译者主体性谈得很透。至于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其实质是为了顺应目的语的接受语境而进行的一系列“改写”,多少带有“顺应论”的影子,而顺应翻译论又是人们常谈的语用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研究得很普遍;而对于读者反应,无论在论述的深度还是广度上,也都很难出奈达之“右”。不可否认,就论述的视角而言,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理性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的,能够刷新人们对以上概念的认识,增强人们对以上概念的感性认知,但是,这些认识只停留在“喻指”层面,建构在隐喻同构认知之上,至于“实质”层面的学科“个性”,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养料不断填入,使这门新兴的学科不断得到丰满,不断走向成熟。
第四,圈定自己的研究“疆域”,锁定本学科的研究焦点。我们主张不断地为本学科开疆拓域,丰富本学科的研究内容,但要有一定的界定,承认自己领域的有限性,否则就有“万精油”学科之嫌[15]71,因为如果一门学科什么都研究,却什么都研究不透,那么其结果必然什么都不是。生态翻译认为其内涵丰富,是一个整体概念,其研究的具体内容是:
“既可以指以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整体,也可以指以自然生态隐喻翻译生态;既可以指维护翻译语言和翻译文化的多样性,也可以指运用翻译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发展;既可以指以生态适应来选择翻译文本,也可以指以生态伦理来规范‘翻译群落’;当然也会包含以生态理念来选择生态翻译文本以及翻译生态自然世界,等等。如果单一地从文本角度来看,生态翻译也可以指基于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文本移植’。”[4]206
从以上对生态翻译的论述,可推论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内容可能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只要带上“生态”的东西,都可以成为生态翻译研究的对象,这样研究范畴就有点扩大化,如此一来,生态翻译学就显得没有自己的学科“疆域”及研究焦点。另外,从生态翻译学研究对象的类别来看,即“宏观”、“中观”及“微观”,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畴也有点扩大化。而我们再来看看奈达的翻译理论,其研究焦点就是“功能对等”,为了取得功能对等,奈达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整个理论体系也是围绕着“功能对等”这个焦点而展开的,如提出“翻译就是交际”这个命题,谈文化翻译,翻译的过程论,读者反应论等等,不一而足;有理有据,研究理路严密、严谨;其研究的路径清晰,即由“点”到“面”而展开。一言以蔽之,生态翻译学应从奈达对其翻译思想的构筑中学会:如何实实在在地限定或扩大本研究范式的论说范围,以及学会如何使本研究范式得以充实及成熟的思维方式。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在中国学者提出之前是‘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可谓之‘无中生有’”[4]2,最终使国内译学界实现了译论生产之零突破,也为国际译学界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不过,我们还是认为,目前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内容是散而不专,“引”而未“发”,阐述有余,建构不足;离一门真正成熟的研究学科还有一定的距离,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正如王宁所说:“生态翻译学还任重而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16]15“一门新学科的建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成的,它只是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17]61我们期待着:今后的生态翻译学研究呈现出更多以及更好的成果,不断呈现出更鲜明的个性化特性,不断完善自己,最终走向成熟。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与生态翻译学之“面对面”,奈达翻译理论在当下的译学研究中不仅没有过时,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及强大的生存力;此外,还对如何提升及完善生态翻译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或启迪作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曹明伦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1]林克难.论读者反应在奈达理论中的地位与作用[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2):81-85.
[2]杨晓荣.翻译理论研究的调整期[M].中国翻译,1996(6):8-11.
[3]谭载喜.当代译苑的恒久之光——追忆一代宗师奈达[J].东方翻译,2011(6):4-14.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6]Nida,Eugene A.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7]Waard,Ja de. & Nida,Eugene A.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M].Nashville:Thomas Nelson,Inc.,1986.
[8]Nida,Eugene A.A Fresh Look at Translation[A].In Beeby,A.,D.Ensinger & M.Presas(Eds).Investigating Translation: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Translation[C].Barcelon,1998.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0:1-12.
[9]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1]Warren,R.(ed.).The Art of Translation:Voices from the Field[M].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
[12]Nida,Eugene A.& Taber,Charles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Brill,1969/1982.
[13]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4]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15]陈水平.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中国翻译,2014(2):68-73.
[16]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2):10-15.
[17]李运兴.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M].外国语,1999(1):55-61.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7-03-04
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奈达翻译思想再研究”(遵师BS〔2015〕23)。
杨司桂(1972-),男,遵义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H059
:A
:1004-342(2017)04-63-06
——再论奈达对翻译本质属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