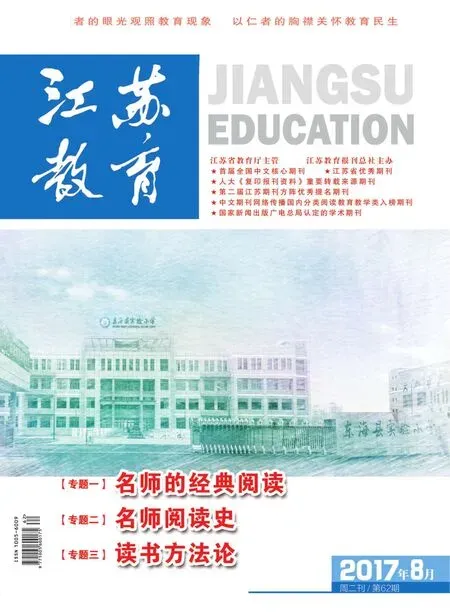多“用”,让阅读“带得走”
冯卫东
多“用”,让阅读“带得走”
冯卫东
阅读必然伴随着遗忘,遗忘率高、记忆率低,是阅读不能产生应有作用与价值的重要原因。要克服遗忘、增强记忆,有三条可行路径,即读而想,读而写,读而做。这三者都是广义的“用”:多“用”,能让阅读“带得走”。
阅读;想、写、做;“带得走”
阅读的目的不是“记住”,更不是做“两脚书橱”。但倘若读后了无所记,那么,阅读的功效与意义等都要大打折扣。事实也常常是,阅读之后有所记忆,才能让阅读的作用得以发挥,阅读的价值得以显现:阅读才“有用”了。
可是,读多记少几乎是每一个阅读者都面临的问题,有时会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免令我们沮丧。在一所学校讲学,一位青年教师问我:“冯老师,您的记性怎么那么好,记得很多读过的内容。而我读了就忘,这是为什么呀?”我自非博闻强识之人,某个冬夜竟在洗脚之后上演了“拿着袜子找袜子”的“滑稽剧”;但另一方面,确实在读后记住、记牢了不少东西,阅读记忆力还似有愈老愈强之势。寻思个中原因,答案是,好多东西我是且读且“用”、且“用”且读的。这大致符合著名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它认为,通过不同方式学习的知识、获得的信息在两周后的留存率以“学后即用”等为最高,有90%之多。
因此,建议读者朋友更多把阅读所得拿来“用”,也更多为了“用”而去读——既学(读)以致用,也“用以致学”,在学用之间实现“互哺”。这样,强化的不只是“带得走”的记忆力,更是“用得活”的实践力。
我所说的“用”包括“用来想”“用来写”和“用来做”等三种情形。想、写、做之间显然不是完全平行的并列关系,它们有着“交集”,譬如“想”就横贯全程,而我这里所讲的“想”,只指让读的东西在头脑里“盘旋”(而非付诸言说或外化于行)的一种独特思维活动。不作如是界定,就会把三者混作一体,混为一谈。
一
“想”也是一种“用”,甚至比起“写”与“做”更是一种“大用”,因为它更便捷,更普适,可以不择时、不择地、不择方式方法,“拿来就想”,“拿来就用”……总之,“想”使阅读所得特别“好用”;“想”作为一种“用”,其功能尤为强大。
13年前我走上专业科研之路,起初有一种强烈的“本领恐慌”,驱使我用好几年时间,像饿人扑在面包上,贪得无厌地读所能见到、所能寻得的好书,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读书季”,我读了几百本各种各样的书。但毕竟从一线教学岗位走出不久,理解力有限,因此较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实现读与想之间自然而深度的“联结”。随着时日推移,自我底蕴不断丰富,厚度不断加大,对阅读的选择性越来越强;当然也由于工作任务重,并且年岁渐大,每有老眼昏花之感,所读不再像头几年那样“海量”,相对少了、慢了、精了,这一过程恰恰是由一般性的“读”向专业性的“想”逐渐过渡的一个进程。更多去想,更多深度地想,如此一来,真正汲得的知识在整个阅读量中的“占比”与日俱增,好多书上、刊中的文字竟常“于我心有戚戚焉”,似乎变成我的东西;或者说,就像我先前潜意识中即存在着,现在通过阅读,发现“它,就在那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读中、读后的“想”,会有如此斩获。
先是走马观花地看,后是牵马缓步地想,眼前晃过的风景少了,心里积淀的思想却多了。以去年花了整整两周才读完的 《林崇德教育演讲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571页)为例——
林教授主持研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热词,我不必“跟风”深度研究它,但应整体把握它,这本书一定会有大量相关内容,由此或可窥见“核心素养”概念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不出所料,它有一些篇章直指“核心素养”;另一些虽不直接关联,却可看到与“核心素养”间接而又内在的血脉关系,如《人是教育的对象: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多变世界中的品德发展:中国的观点》等。儿童心理、儿童品德发展其实都是“核心素养”的组成部分或生成机制,我边读边想,自然留下较深印象。
而《我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考》,则是最细读慢品的一篇。我知道,“核心素养”体系的提出自非林教授一人所为,但他毫无疑问是“厥功至伟”也最有发言权的人士,这篇演讲理应比他另一些相关论文更能具体生动地勾画出 “核心素养”的思想发展脉络与轨迹。他说:“核心素养主要指向于过程,关注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体验,而非结果导向……也是一个伴随终身、可持续发展,并且与时俱进的动态化过程……”
我曾以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某一时间节点业已养成、相对固定的能力、水平与修养等,将它理解成一个静态的“名词”,现在想来,它还是一个变化中的“动词”,表现为某个过程。“冲突”引发深思,深思镌入灵府。作者的文字成了我的“思想原料”,经过“加工”,最后变成自我的理念,还将影响今后我对某些教育问题的思考:“想”确乎就是一种“用”,当两者完美结合时,阅读便成了一种颇有意趣的“享用”。
二
我是读书较勤而非读得最多的人,远的不说,只与两位通州老乡——凌宗伟和朱国忠相比,就倍觉汗颜。前者常常一天一本书;后者差不多做到“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取书的路上”。让我引以为豪的是,读得不算多,写得却不少,尽管写作量也不比前两位,但所写与所读的比例却应高于他们,高于大多数阅读者。读后而写的“转化率”很高,“转化”使我记住许多东西,特别是记住写作时所引用的那些文字与资料。
非常喜欢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教授的话:“我只有说,才能想。”所谓“说”指的是表达,包括说写。我说(写)故我思,我思故我读,套用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名言“人是他自己吃下去的东西”,我曾撰文《文字是作者吃下去的东西》。因为“吃下去”许多有益的精神营养,所以才能写,才有了这些文字(文章)。
读后之写至少有两种情形。
一是写随感、读后感或读书笔记。随感常呈碎片化,它无处不可写。我向来不爱书面的干净,以为不时“批注”、与作者对话,这就是对书本身的珍爱。因此,只要是自己的书,读过之后无处不留痕,无处不“花脸”。譬如读冯建军《生命与教育》一书,他关于“教育与儿童未来”关系的一段论述,我不完全赞成,于是写下一段随感:
我觉得,在是否为未来生活作准备方面,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可取。应该承认,儿童当下的生活——受教育,是有为未来准备的作用与意义,但不唯“准备”而已;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准备”而损害现在的状态。儿童的健康成长应该是贯穿生命全程的旋律。“准备”是要有的,“准备”得不露痕迹,才是儿童当下所能接受的。
自己的心得自己记得,连同“我不完全赞成”的作者的观点,都难以释怀。
至于写成篇的读后感或读书笔记,我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的南通老乡、现供职于苏州工业园区教研室的优秀青年教师徐飞几乎每有所读,必有所写,他说,写这两类文字,常能让所读之书深铭于心。
二是写论文、写专著。前不久我刚写完 《为“真学”而教》一书。为了它,我专门的阅读量应该不少于500万字,而电脑摘录的也有几十或上百万字之多,当然最后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文字量很有限,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5000,其中三分之一左右出自《可见的学习》和《人是如何学习的》两本新书。对引用的文字我还做不到熟读成诵,但其中所表达、所呈现的主要观点却记得颇为牢靠,这既源于我与观点之间的共鸣,也仰仗于引用它们以佐证自我观点时有意无意中对它们的进一步“确认”与“确证”。
还有为写而读、读后再写的情形。“写”作为一项任务指令,“驱动”自我进行专题或聚焦式阅读,“功利性”倾向显著,而“有利可图”的事往往最容易“上心”,此时阅读常有很多东西积淀心底,或者镶嵌到自我心智结构的某些特定区间。
顺便提及,我是一个“思想大于言说”的人,所思甚多,所写相对较少,但换一个角度看,有些隐形的思想过程即为一种“潜写作”状态,虽然未曾形诸笔端,但也有或朦胧或清晰的“腹纲”,犹如一个框架或者一壁书橱立于大脑某处。有时看似很随意的阅读之所得也能自动放置、归并其中。结构中的或者讲与更多内容发生网络式关联的东西不再是机械式接受的“惰性知识”或“无活力的概念”(怀特海语),而常变为情境性或有意义的识记,它们特别便于提取,也随时可以“用得上”。
三
“听过了就忘掉了,看过了就记住了,做过了就理解了。”而理解的东西又能更好地加以感觉,加以记忆。我这里所言不是做过了的事情,而是在做中得以践行与检验的知识、理论,包括先前未曾读闻,而在某种行为、某项行动之中或之后才接触到却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的那些文字,它们或许比先前读过的内容更能烙到灵魂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所蕴含的知识及道理也是行动者自己“做出来的”;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岂会“随风而去”?
在我专业从事教科研之后,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教育哲学,希望自己能钻到“故纸堆”中做一番玄奥的研究。后来渐渐认识到,如此坐而论道的研究作用不大,必须来到现场,回到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双向建构,特别要把自己所学到的理论、所悟得的道理运用到教育教学探索行为中。几年里,我与如皋师范附属小学合作进行“倾听教育”研究,与海安县海陵中学合作进行“经历教育”研究,与广州某小学以及南通市崇川学校合作进行“玩—动课程”建设研究。它们有的是“从理论出发”的,譬如“倾听教育”,受益于佐藤学《静悄悄的革命》中“应该追求的不是发言热闹的教室,而是相互倾听的教室”等系列观点的影响;有的是“就时弊着眼”的,譬如“经历教育”,我们痛感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裁剪过程、压缩经历的问题,希望借助一些变革性实践及研究裨补缺漏,走向应然;有的是“以发展立意”的,譬如“玩—动课程”,追求以课程结构及其内容的改变使儿童学习更灵活、更有效、更优质……为此做了很多事,也读了很多书,其间最大的感受是,一旦理论为实践所拥有,实践为理论所指导,实践则风生水起,理论则活力四射:是的,它已然不是需要努力去记诵的教条,而是常取常新、生机盎然的活水;而“活”又恰恰是(知识能被)“带着走”的必要条件,也是“带着走”的重要特征。
说说“经历教育”——让学生发生和“打开”更多、更丰富学习与生命经历的一种教育理念、教学范式。我体会到,要尽力驱动和引导学生在“捂·焐·悟·晤”中“把知识做出来”,要善于把“有质量的时间”(俞敏洪语)花在“长效的核心知识”(顾泠沅语)处。以前一种体会为例:关于“捂”,读到荷兰著名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的话,“泄露一个可以由学生自己发现的秘密,这是坏的教学法,甚至是一种罪恶”;关于“焐”,读到朱熹有关读书方法的论述,其中有“鸡抱卵”的比喻;而如何把“悟”出来的东西拿来“晤”(展示与对话),则读到学习科学中有关“迷思概念”向“科学概念”进行“转换”的理论……这犹如千万里追寻恋人一样,终于追上和寻到了,如此美妙的“学习事件”又怎能不进入长时记忆,乃至毕生印象?说到底,这是“知行合一”朴素哲理无以撼动、所向披靡的巨大力量所使然。
——多“用”,让阅读“带着走”。阅读终究是要“经世致用”的,让我们在乐学活用中,带走知识的能量,也带来教育生命的无限魅力……
G40
B
1005-6009(2017)62-0072-03
冯卫东,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南通,226000)副院长,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