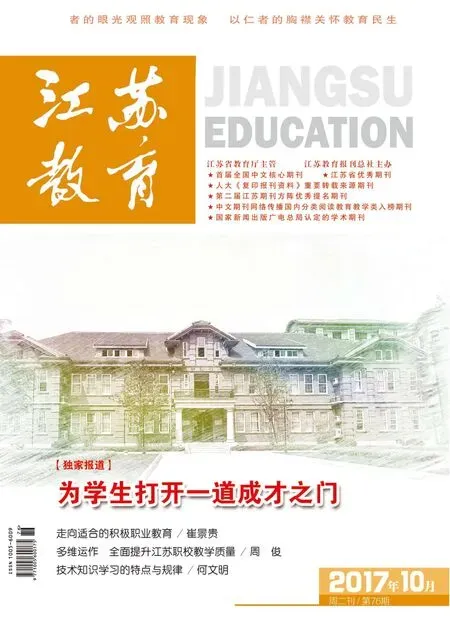为“校园禁令”投赞成票
臧志军
【点评】
为“校园禁令”投赞成票
臧志军
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国会为在全国中小学推广校服的计划背书,美国教育部还为此发表了《校服手册》,宣传在学校穿校服的好处,其中包括:可减少暴力和偷窃,阻止学生穿着有黑社会元素的衣着,有利于对学生行为进行约束,帮助学生应对同学的衣着压力,使学生集中注意力于学习等。列举出的这些理由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我国许多学校的着装政策,比如不希望学生产生物质追求上的攀比、希望学生更多关注学习等。正因为承载着相当强烈的教育信号,所以尽管克林顿的校服计划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但至今还有超过25%的美国公立学校有明确的、公开的、书面的着装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标榜个性自由的美国,学生的着装也不完全是私人事务,需要受到学校规范的约束。正因为此,我才对讨论中大家众口一词反对学校使用规范学生着装的权力感到迷惑不解:在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人们为什么会觉得通过着装政策传递主流价值观是件错误的事?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如何着装(以及如何对身体进行何种装饰)绝不仅仅是私人事务。既然着装是公共环境的组成部分,由一个公共机构制定公共规则应该是合理的。法可以分为硬法和软法,那些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律属于硬法,那些道德、民间习惯和非权威机构确立的规范都可以属于软法。与其说着装由道德来调整,还不如说由软法来调整,毕竟道德与硬法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线,由隐性的道德规则参与推动而成的成文软法可以填补其间的模糊地带。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对学生在校园内的着装行为做出规范无可厚非,甚至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应该成为社会纠偏机制的一个部分——当整个社会浮躁到把握不了正确方向时(服饰的过度自由化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征),学校应该对传统进行必要的坚守。所以自产生以来,学校主要以保守主义的面貌出现。这一点在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状态后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连学校都不能传递主流的价值观,社会凝聚力的流失将更无法想象。香港近年来的社会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学校中的价值观混乱与对学生规训能力的减弱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校作为未来公民的养成场所,有必要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对学生的言行进行起码的规范,即使这种规范以学生部分个体权益的丧失为代价。
有人不反对学校提出规范,但无法认同目前的规范产生方式,所以提出了更加民主化、更加程序化的建议。我曾经认同甚至鼓吹过这种观点,但近年来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西方政治或教育学中关于选民理性的论述并不总是事实,个人在进行与个体利益相关的选择时经常不够理性。因此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参与相关决策,但由学校主导决策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诚然,学校里的某些决策有着浓重的长官意志色彩,但没有受到校内其他决策者的强烈抵制本身就说明,这些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意见。所以即使某些学校推出的规定、“禁令”在程序上并不完美,也不构成对其价值一票否决的理由。
有人担心学校过强的规训会抹杀学生的个性,会影响学生探索新事物、新生活的动力。我相信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尽管学校教育相当保守,但并没有妨碍我们社会的多元化进程,也没有阻止中国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创新者、创业者,其成就的直接体现就是中国与美国一起,成为当今世界互联网产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这说明学生的多元个性、创造力的形成因素很复杂,在这些因素中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也许被我们这些教育者高估了。至于说不让学生穿自己喜欢的服装或染发烫发就会影响他们的个性或创造力发展,二者之间有多大的关联度还值得讨论。
说到教育,西方人喜欢说以学生为中心、要理解学生,而中国人喜欢说“传道、授业、解惑”,其差别在于西方人放弃了外在的教育标准,而中国人却相信总有一个超越学生的以成人世界价值观为基准的教育标准——“道”的存在。当教育的使命是“传道”时,规训是必不可少的,学校不应推卸这个责任。只要学校推出的规定、“禁令”真正出于教育目的,而不是掺杂了金钱、个人利益等非教育因素,那就应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范围,其生成方式、内容、边界等问题就交由学校和学生自己去解决吧。
被西方似是而非的学生中心论所迷惑可能是大家一致反对学校出台“校园禁令”的根本原因吧。这也是很多教师一方面在体制挤压下规训学生,另一方面却感到违背自己的教育理念而异常痛苦的原因。我想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呼吁:理直气壮地举起规则的大棒,规训本来就是学校教育的应有之义,我们可以调整执行规则的过程,但对规则本身还是要多些尊重。
G717
C
1005-6009(2017)76-0076-02
江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