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时光里的记忆
花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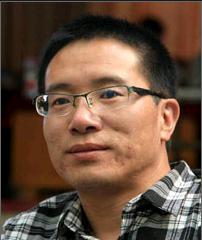
屋檐下的鸽子
它们一定是相爱的,幸福的。每次我看到它们的时候,都是比翼齐飞,甚至看到它们的亲昵,像极了喀尔钦那对老人。黄昏,温暖的光芒泄露一地。它们就在我每天路过的破旧屋檐下,不是燕子,燕子冬去春来;它们是鸽子,灵魂的两位使者,在高原的严寒里不离不弃。
起初,它们一看到有人或听到响动就迅速飞走;后来,只要有人靠近或刺耳的响动,它们就警觉地飞走;再后来,它们看到或听到什么,只是挪动几步,但不飞走,它们对世界的信赖像一滴透明的水。直到被几双贪婪的眼睛盯上,直到它们被一双血淋淋的手摁到欲望的胃里……
每次经过,看不到它们的时候,我就看看粘在椽子上风干的鸽粪,心里就惶恐万分。那些粪有黑色、白色和灰色的,也有黑白相间的,但它们一定是生命的颜色,一定是和平的色彩,一定是爱的光芒。只是,很多时候,人类像抹去自己的未来一样将这一切抹去,只剩下风,在空荡荡的屋檐下飕飕逃窜。
蚂蚁的队伍
喀尔钦不大,它面前的草地却一直绿着,至少现在是,像一块巨大的绿毯。
被脚印踩出的一块空白处,蚂蚁排着长长的队伍。如果不蹲下来,人类的眼睛已经很难注视到这些坚强的生命。
它们一个跟着一个,不掉队,也听不见有谁在喊“一二一”“一二三四”或别的什么。我听不到蚂蚁的语言,但我相信它们一定在谈论着什么,比如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雨,在雨水到来之前迅速抵达安全的巢穴。
我像一个罪恶的人,用小棍划断它们的队伍。惊慌失措之后,它们很快赶上前面的队伍,继续排起自己的长龙,钻进绿色的海洋里。
风一吹,海浪一波一波涌来,但我坚信,它们在海浪下,不会像人类一样手足无措,等待死亡。
雨,滴答滴答地下
小时候,下雨的时候。屋漏,我们用脸盆、木桶、木勺、坛坛罐罐等器皿盛漏下的雨水。一时间,叮叮当当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曲美妙的音乐萦绕在屋子里,遮挡住屋外的雨声。
那时候,屋顶修了漏,漏了修,像缝缝补补的岁月。而我们像快乐的小鸟,穿行在音乐里,听不到父母的叹息,也看不到父母脸上的愁云。只要下雨,就开心地搬动盛水的器皿,该搬的也搬,不该搬的也搬。
屋子重新翻修了,不漏雨了,我们却一直盼望下雨,盼望雨滴答滴答地下,屋子里叮叮当当地响。不漏雨了,我们就拿着器皿在屋子里叮叮咚咚地敲,直到敲碎了一只碗,被父亲赶出门外,在黑夜里偷偷啜泣。母亲责怪父亲后,打着火把满村子找,带着哭腔满村子喊。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哇哇大哭,眼泪像雨,滴滴答答地落……
雨,滴答滴答地下,我们嗖嗖地成长。
叶落的时候,心里心外都是雨。
世界漏雨了,我们却再也找不到盛雨的器皿。
奔跑的山泉
通往老屋的小径,掩映在浓密的草丛里。晶莹的山泉从木桶里荡出来,打湿脚下的花儿。顿时,花儿的眼睛便朝着你的方向盛开。旁边流淌的泉水,漫过光滑的石头和干净的沙粒,跟着你的脚步哗哗地跑。
挑水的村妇已经进了村,回到了老屋,山泉还在奔跑,它们追赶什么呢?从我记事起,它就在跑——牛羊吃草经过泉边时,跟着牛羊跑;我去饮驴,驴叫的时候跟着驴叫;我们一群孩子玩累了、渴了,直接趴下喝时,它就咯咯地笑,我们走远了,它的笑声还在身后追赶,一不留神,它就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春风一吹,我们就离开村子,跑进城。剩下许多田地就荒着,村子一下子就空荡荡的,只有那个叫狗蛋的孩子,每天在村口张望。天黑下来,他提着一壶泉水,给爷爷煮饭。冬天了,一场雪接着一场雪,我们在苍茫的白里归来……
我们带来了播种机,牛羊驴都被牵走,狗蛋和山泉一样追着跑;自来水拉到了灶房,我们不去挑水了,扁担被高高挂起,但狗蛋还提着水壶去舀山泉,他看见山泉还在追着自己跑,它在追赶什么呢?后来,我们继续像風一样在跑,跑着跑着就发现我们丢弃了什么,我们在跑什么呢?
树上挂满了鸟鸣
泥土的味道弥漫在雨后的黄昏。小村的牛羊踏着泥泞,慢条斯理地回到圈里。老母鸡领着孩子们回到鸡窝。那头公猪嘶叫了一下午,终于在换来了一桶麦麸拌杂草的晚餐后,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村子泥土小巷里一堆堆的牛粪,还在冒着热气,像屋顶上一缕缕的炊烟,弥漫着家的味道……一切像梦一样恬静。
突然,巷口传来无数的鸟鸣,数不清的麻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树上挂满了鸟鸣。村子一下子被麻雀淹没,被鸟鸣淹没。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麻雀和鸟鸣震颤着。但我相信,它们一定是在互相呼唤着,怕落下一个亲人;它们一定有家,可是为什么不回家呢?
是啊!它们为什么不回家呢?
天快黑了,它们在寻找什么呢?
前面的前面是天空
门前是水渠,水渠的一头是树林,另一头是磨房,磨轮吱扭吱扭地转动。
向前是一块菜园,里面的韭菜、菠菜、芹菜等菜绿油油的。菜园边上围着篱笆,但被喇叭花、豆角缠绕得看不到它的存在,远看,似乎这些植物都在站着。
向前是一块沙滩和一条小河,阳光落下,沙滩和小河白花花的,像十万雪花银。小河马不停蹄地奔跑,转眼间,十万雪花银被流水哗哗地带走,只剩下石头上一圈圈的痕迹。
跨过小河,是几块油菜花地,金黄色的油菜花像梦一样迷人,生命一样尊贵。再向前,是一座山,被梯田打扮得五彩缤纷。一级一级的梯田延伸到山顶,再向上就是天空……
我一直梦见自己向前走,走了三十多年,依然在走。我不知道前面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前面究竟有多远,只记得奶奶三十年前背着背篼,背篼里装着我去赶牛——
你的前面是什么?奶奶。奶奶的前面是什么?是吃草的牛。牛的前面是什么?是草地。草地的前面是什么?是山。山的前面是什么?是天空。天空的前面是什么?是前面。前面的前面是什么?是天空……这样对答,一直到使我在奶奶的背篼里梦见辽阔的天空。
像麦垛一样
收割后的洮州,像披着一件缀满补丁的战袍。
麦垛是他的子民,一排排整齐地站在田地里,守候着这座古老的城。他们,照见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城外的村庄,传来一声声鸡鸣和犬吠,像戳穿谎言一样,轻而易举就打破了城的沉寂。
我相信,麦垛是真诚的,一闪而过的光芒是温暖的。
母亲愈加苍老,她的手指偶尔会被针刺破,她将流血的手指含在嘴里,让骨肉相连的痛浸满一丝丝温暖。接着,又开始不知疲惫地拿起针线,缝补我们漏洞百出的生活和伤痕累累的日子。
母亲缝出的补丁,一块接着一块,刚好抵御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霜。
而我,麦垛一样,裹紧单薄的身子,把自己丢在风中,找不到春天的出口……像一粒干瘪的种子,被荒草掩埋。
那些云朵
像一片柔软的雪,一触即破。但我们触摸不到,只有风才能与它共舞。
它在高远处,变幻着各种鬼脸,但我们无法去猜透它的心事和思想。我们在低处,仰望,挥手,但它看不见,它需要关注更多大地上的事情,然后和风一起去实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未必都是真实的,也未必都是虚幻的。悲哀的不是我们看错了什么,而是明明知道错了,却不容置疑,死不悔改。
我们仰望与低头之间,或许只需极短的时间,像某种意识的瞬间产生,某个事件的突然发生……然而,让它们像云一样轻,一样白,一样消失,却需要一年、一生或者更久的时光。
我们再次抬头,仰望。风吹过,云就跟着风儿一起离开。
我们再次低头,沉思。风吹过,生活的云却沉甸甸的,压到自己喘不过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