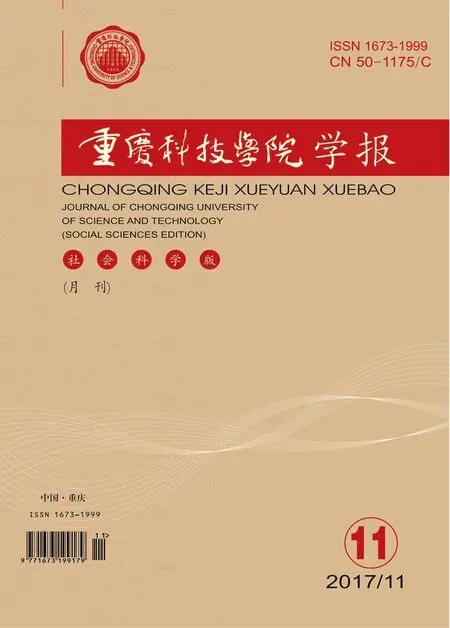小说《微笑的狼》的身份建构与记忆叙事探析
颜丽蕊
小说《微笑的狼》的身份建构与记忆叙事探析
颜丽蕊
小说《微笑的狼》描写一对少男少女的短期旅行,他们在旅行中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追寻记忆中的家园。在非现实与现实相交织的叙事时空中,展现了日本战后特殊时期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特殊人群对于身份与记忆的建构,通过建构想象的流变身份,体现人物的创伤与成长。小说的记忆描写具有不确定性,并且与具体的场所相结合、与梦和幻想相结合,通过记忆对象来激发创伤记忆,呈现出小说独特的记忆书写风格,刻画了个人和群体的时代创伤。
《微笑的狼》;身份建构;记忆叙事
津岛佑子(1947—2016)是日本现代文学界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先后斩获泉镜花奖、川端康成文学奖、平林泰奖、伊藤整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野间文学奖、大佛次郎奖等多个日本文学奖项,在日本现代文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汉语等多国语言,国际评价相当高。津岛佑子的文学实力非常雄厚,文学技巧精湛醇熟,创作视野宏大,文学作品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批判精神,是一位不断开拓文学创作新天地的日本当代女作家。津岛佑子的文学创作透露出新世纪日本的女性书写从內向性转向宏大论述的趋势[1]。发表于2000年的小说《微笑的狼》表现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批判,体现出作者书写主题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一、流变的时空布局
《微笑的狼》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连续运动中展开情节。叙事时距变化大是《微笑的狼》在叙事时间上的特色。小说的第二部分“准备出发”与最后一章中的自述部分,被设定为小说撰写之时的1999年,小说的主要篇幅是女主人公回忆40年前也就是1959年(昭和34年)发生的事情。小说主要章节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叙述1959年发生的男、女主人公进行旅游的经历。在叙述过程中,以回忆的形式穿插叙述了1946年男主人公与父亲的墓地流浪生活、1947年的墓地情杀事件以及1954年12岁的少年到访少女家的情节。小说借助多重的时间分层和多变的时间转换,使故事不断从现在回到过去,深化了涉及的时间和几种不同的时间层次,使回忆的事件变得更加清晰可见[2]。
《微笑的狼》在叙事时间安排上的另一特色是打乱时序。小说结构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跳跃性和张力,对多年之前不同时段的童年记忆的追忆叙述、正在进行中的旅行过程的叙述、旅行结束40年后的1999年的倒叙等3种叙述相互交错、相互越位。这种空间、时间的重叠,造成叙事内容连贯性的丧失以及阅读效果的混乱,导致读者因感觉小说零散难解从而把握不好小说的结构。小说充分体现了现代小说在追求空间审美时的双重性:一方面拓展了作品阅读的空间广度和历史深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理解作品的难度[3]。《微笑的狼》的这种现代小说所运用的叙述技巧超越了传统叙事技巧的限制,向读者发出了解读挑战,使读者既被诱惑着、又被干扰着阅读小说作品。小说“在一个与以往小说全然不同的时空下展开,摆脱了故事的逻辑束缚,努力创造非理性的不和谐情景,抹除了真实与虚构的界线,以想象的、夸张的、离奇的、滑稽的、漫画式的方式重构碎片化的现实空间,表现扭曲变形的现代生存状态。”[4]《微笑的狼》大量运用碎片化的记忆描绘、多种文体交错、梦境与现实交织对照的叙事方式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创伤心理,这种对现实的重构与审视包含了作者独特的创作意图。并且,体现碎片化叙事特色的时序安排,并没有导致整体情节的断裂和无序,而是体现出作者的独具匠心,小说的开篇没有让读者陷入时空的迷雾,而是体现出时空交错的渐进性。即使是在40年前的往事叙述过程中,正常的故事时间被打乱,穿插了主人公童年的碎片记忆和对家人曾经的幻想。这些都展现了作者在幻境与现实之间自由穿梭的写作技巧,从而使读者能够根据小说文本明示的时间和作者的提示来确定故事时间,使读者对小说所表现的创伤的认识更为深刻,增强了艺术效果。
小说中的旅行被压缩在几天时间里,但在叙事时间上独具匠心的安排,为突出小说的现代性特色和表现主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小说的叙事空间和意识空间的描写上也很有特点。叙事空间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色,伴随着变化的叙事空间,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时空也非常广阔。人物的意识空间描绘包括对想象、梦境、幻觉等非现实的空间描绘,在与现实时空的对照中突出了两大时空的巨大差异,引人深思。
小说叙述不仅在不同的时间内交错展开,而且叙述空间也不断变化。两位主人公的旅行路线总体上是一路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从东到西,沿日本海向东北,中途多次换乘其他列车,路线是随意的、没有计划性的。正如女主人公雪子所说:“离开东京这六七天期间,不断换乘火车本身已经成为我们的目的了,火车是开往哪里的,经过什么地方,已经不去关心了。只是茫然地任凭火车拉着走,仿佛就算完成了重要的义务似的,我也不再感觉不安了。”[5]294在这种交错的时间中进行的看似东南西北自由旅行的空间、没有目的地的茫然之旅,达到了“以形式游戏去破坏中心在运动中对于边陲的支配地位,并使中心消融在区分化的连续运动中”[6]的效果。对于两位主人公来说,刚开始他们是有“西伯利亚”这一旅游目的地的,原因是它是“家园”的代名词。然而,他们连去西伯利亚的具体路线都不明确,实际的乘车朝向也并不是西伯利亚,旅行的目的性消失了,在围绕相对中心的连续游荡中,他们寻找的目标在消失后发生了异化,转变为对彼此依靠的温存感和家族般的连带感的谋求与依恋,并且他们满足于这种久违的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宽阔的时空视野下,作者利用良好的控制能力实现了自由转变,在漫无目的的漂流旅途中精准把握和描绘了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
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意识空间的扩展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发展。意识空间是主人公的心理空间范畴,包括想象、梦境、意识流等,它不同于小说叙事过程中所描述的所有空间范畴的叙事空间,指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7]。小说运用大量的对意识流似的幻想的描绘、内心独白以及回忆与现实的交织,通过引入想象世界,来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内在的不安情绪。童话故事和梦境的穿插,将梦境与现实交错设置,把梦境和想象描绘得无比奇幻,从而把日常生活导入了非现实的世界,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奇幻色彩,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作者的大部分作品都频繁地使用超越时空的故事融合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或多或少都表现了这种扩展的人物意识空间,或者描写另一个时空的景象。另一个时空有时以梦境的形式出现,有时以人物的意识流或想象的方式出现,给读者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例如,《在夜光的追赶下》以突然失去9岁儿子的“我”,以大约14世纪的王朝文学作者为对象写信为情节,表现生活在现在的女性的记忆与生活在过去的女性的记忆相重合,在叙述中生发出平和与鼓励。《太过野蛮的》讲述了生活于1930年代的台湾的日本女星美世与获得跨越至2000年代的她遗留的情书和日记的侄女茉莉子相互交谈的故事,最后两人在似梦的时间中相见。可以说,津岛佑子的小说经常通过不同时空的人物对话、交流或者反观,在宽广的跨度中探寻永恒的主题,如此安排也正好对应了现实世界混沌多元的本来面貌。
空间对人的性格塑造和限定是强烈和持久的。《微笑的狼》漂泊不定的外在空间设定与人物的身份和归属感的内在心理的不确定性互相照应。小说的中心故事发生在二战初期,当时日本经历了二战的破坏和战后重建,其空间被重新分配,这促使作者把空间的变化归咎为历史变迁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作者通过对阶级、国家、历史、政治等问题的思考,讨论了历史变迁中各种力量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在空间重组中的作用,可以说是津岛佑子这一时期空间观的缩写。一边是开放的、正规的、和平的童话世界里的理想地理空间,一边是灰暗的、狭窄的国家强制力控制的贫民的现实空间,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小说通过理想与现实这两个时空的对照,对现实世界的非人道与反人文性质进行了批判,从而体现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社会与历史的反思。
小说尝试打破常规文体和语言规则,通过在各种时空之间的自由穿梭,在交错的梦幻与现实中,在游移不定的叙事时空中,开始小说主人公寻找和确定自我身份的旅行。小说中人物的意识空间异常开阔,鲜明地突出了现实空间的狭小。小说多变而开阔的时空叙事在体现小说现代性特色、突出人物和表现主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想象的流动身份
津岛佑子非常重视非现实的想象对于家族和人类群体的重要作用。她曾谈道:“血缘呀,家人这种东西,是毫无根据的妄想,但是却实际存在着,并在左右着现实。没有妄想,人类就无法生存,对于人类来说,现实和妄想是无法分开的。”[8]《微笑的狼》充分体现了津岛佑子的这一观念。关于血缘和家人的想象、现实与妄想的交错贯穿于《微笑的狼》中,对小说人物的命运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的少年一直在为寻找一种自我身份和父亲存在感的证明苦苦追寻,找到了报道当年墓地殉情事件的报纸,还找到了事件当事人之一画家(少女的父亲)家人的地址,邂逅了少女并展开一段疗伤之旅。在旅行途中,少年和少女被彼此所妄想的亲情般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微笑的狼》中关于少男少女的叙述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少男和少女在精神成长中经历了这一次旅行之后,对人生、对自我的认识有了飞跃的变化,最终脱胎换骨,成熟起来,使原本是负荷的记忆不再是现实世界的屏障。
女主人公雪子通过旅行经历了从“孩子”到“大人”的成长。倘若起初的回忆将自己定格为排斥父亲、叛逆妈妈的年轻少女,经历了旅行的少女则经历了人生的蜕变,已然成为一个有所担当的成熟的人。重拾关于母亲和家庭的记忆,使她树立了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她采取积极的姿态,修好与家人的关系,回归家庭,重新开始与家人的共同生活,重塑全新的自我。12岁少女自小常年生活在以弱智哥哥为中心的单亲家庭中,既缺失父爱又未得到母亲足够的关爱,并没有充分感受到家庭温暖的少女和母亲的关系也并不亲密,她“长成了一个不太听话的孩子”[5]31。未告知其母便擅自开始一段外出旅行,表现出其叛逆的性格倾向。而对父亲殉情自杀的抵触与屏蔽的回避态度则是少女自我保护意识强、自我封闭的表现。少女在与少年的旅行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在不信任的同时又十分好奇,将其当做父亲的替身,到极为信任、忠实地追随,甚至“想把一切都托付给他”[5]47,在少年生病时,“像大人似地守护”着他,互相支撑与依赖。在彼此的依靠中,她也时常惦念远方的家人,在梦境中思念曾经守护自己的母亲。在这一过程中构建的想象的“家园”空间(梦境),可视为一种追根溯源的虚构,一种追缅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正是通过与少年的旅行,她得以重新认识创伤事件和理解创伤感受,体会到家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也完成了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心理建设。
少年也在与少女的旅行中,将其视为最珍贵的伙伴,给予她父兄般的温暖。当上初中时,他找到了那篇与父亲当年在墓地共同亲历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异常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确认了自己的记忆是现实的,从而忘掉了一直缠绕自己的不安。所有的一切都是确有其事的,小孩真想把这些事讲给每一个认识的人听”[5]21。他只想通过这种寻找的方式,证明自己模糊的关于与父亲共同生活的记忆是真实存在过的,想证实自己曾经切切实实地感受过父爱。他寻找到了事件当事人之一(与情人殉情而死的画家)的家人的地址,当被允许进入家里交谈时,少年“喜极而泣”,他向女主人(少女的妈妈)坦白了自己的想法:“想要向他们表达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关联。想要确认这个关联。此外没有其他的奢望。”[5]29但是,与他不同的是,女主人想要忘却那段经历,也劝少年忘记并开始新生活,少年感到迷茫,因为那是唯一一段与其父有共同回忆的时间。时隔5年之后,当少年再次造访事件当事人的家时,巧遇了少女。通过自我暴露和叙述创伤,少年向她描述了自己的孤儿院生活和童年与父亲的墓地流浪经历,流露了对父亲的追忆,畅谈了自己的创伤体验,与少女建立了新的联系,逐渐从一个封闭内心的个体转变为一个与人沟通交流,能够信任、依靠、守护他人的人。并在相处中加深了对少女的感情,逐渐互相需要、离不开彼此。在听到少女说道:“我们血脉相连”后,“不想和‘卡瑟’(少女,笔者注)分离的痛切愿望在‘雷米’(少年,笔者注)胸中倏地闪过,使他感到一阵战栗。 ”[5]248通过多次的暴露和重新认识创伤,少年重建了自我,得以走出创伤的阴影,能够以一个正常社会人的身份重新回归社会。然而就在此时,被警察强行终止了与少女的旅行,被捕时他的脸上没有眼泪,只有恐怖。他“闪着蓝色的眼睛,使我联想到狼的眼睛”[5]300,少年的善良与被假定的“坏角色”——狼也有共同之处。以警察为首的“人类的窝”想要强加给这位善良的少年以罪名,幸而最终因为少女及其母亲的澄清与辩护,他才被释放了[5]303,而这无形中又造成了新的创伤,有待今后再度进行创伤疗愈。
男、女主人公利用故事进行自我重新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想象着各自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用童话故事(《没有耳朵的芳一》《冰雪女王》《森林的故事》《无家可归的孩子》)创造新的自我,创造自己想象的空间和身份。在共同的旅行中,两人编织着“血脉相连”的故事,寻找着祖先和一种家族联系的感觉。在互相照顾和依靠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体会到类似生命结合体的连带感,也追寻到了一种缺失的来自父亲的爱和家人般的温暖。少年在照料少女的过程中扮演父亲和兄长的角色,将少女想象成同一群体的同伴,他用童话故事里的出场人物给他和少女命名。但是,在自我命名重构身份的过程中,他们不停地改变姓名,由光夫与雪子变成“阿克拉”和“莫古里”、再到“雷米”和“卡琵”,都是取自狼和狗这两种童话故事里正义善良并且有亲缘关系的出场动物的原名。这种即兴创作产生于对孤儿身份和遭遗弃创伤体验的清除和否认。进入孤儿院的时候,少年的真实名字被丢弃了,开始旅行之后,少女的姓名也被丢弃了。少年即兴取的姓名正面肯定了自我身份的一种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与生存在日本战后这个陌生而令人困惑不安的环境中是不可分割的。少年4岁时跟随父亲在墓地里生活,居无定所,而在和少女的旅行中的漫无目的、乔装打扮以掩人耳目,都和年幼时的流浪生活很相似。少年在这一过程中重温类似父子流浪生活期间的记忆。那段记忆,是少年唯一一段和亲人发生关系的时间。
三、记忆与不确定性
日本学者松浦雄介认为:“津岛佑子的小说中有非常鲜明的记忆的想起。即使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也有持续潜伏的记忆。这种记忆不论经过多长时间,也会被事无巨细地——几乎是过剩地——鲜明地被想起。不论是记忆的缺失还是过剩,同样都是现代的倾向。”[9]但是笔者认为,《微笑的狼》中的记忆书写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并且通过激发创伤记忆,使过去与具体的场所与印象(墓地、家园的院落)相结合、与梦和幻想相结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质。
小说中的记忆具有不确定性。在故事开篇写到少年回忆墓地生活时,讲到虽然他对某些细节的记忆非常清晰,但是他“只记得这些。可是,怎么想不起来被白雪覆盖的墓地的景象。不记得曾经为那片雪白感到惊讶”[5]11。 当少年亲身来到墓地时,“他对这里的一切没有亲切的感觉。真的是这里吗?他踌躇起来”[5]14,即点明记忆乃至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这种对于记忆与主体认同的挫折经验以及从中生发的寻找姿态与小说人物的身世、创伤体验密切相关。男、女主人公不仅是在回忆中追述自己的童年和家园,也是在回忆中追寻自己存在的身份记忆,甚至是隐藏在背后的历史记忆。故事在少男少女的回忆中不断绵延、迂回往复,使过去与现在不断交织渗透,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完成了小说叙述形式与主题的同步升华。
小说中的记忆往往与创伤相结合。二战后不久日本进行了清除流浪者的行动[10],“《流浪儿及其他儿童保护等的应急措施实施相关事项》(1946年4月15日,厚生省社会局长通告地方长官)指示:都道府县与社会事业相关者,灵活使用警官,努力发现流浪儿、引渡给监护者和收容至儿童保护设施。”[11]这一政府举措促使处于流浪状态下的少年被迫与父亲分开,且再未见面,这也间接导致了少年儿时记忆里的创伤体验,而且他一直活在这个心理创伤阴影里,无法得到治愈。这种未治愈的创伤导致了12年后的旅行。这位17岁少年仅仅记得自己4岁时曾和父亲有过墓地流浪生活,在父亲生病后被送到孤儿院的“儿童之家”,少年在孤儿院并未得到家庭般的温暖,逐渐成长为一个孤独地活在自我构筑的童话世界里的人。慢慢长大的少年悉心寻找点滴与自己身世、经历相关的信息。少年真正寻找的是一种自我身份和父亲存在感的证明,也正是这份对寻找的坚持,使他邂逅了少女并展开了一段疗伤之旅。而少女也自小丧父,没有切切实实地感受过父爱,母亲对智力损伤的哥哥的过度关注也让她感到母爱的缺失,个性较为叛逆。因此,不论是少年还是少女,他们的儿时记忆都是与孤独、丧父、离别交织在一起的,是饱含创伤体验的记忆。
小说中多次出现墓地这一意象。墓地、图书馆里的新闻报道是记忆的重要载体,照片被认为是带有记忆的镜子,而集结成册的照片,不仅是人生历程中的重要节点的记载,连接起来的照片实际上是完整的人生印记[12]。但是,少年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那报道父子相关记忆的新闻报纸则更为珍贵。作者津岛佑子运用经典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的热拉尔·热奈所说的重复叙事,以表现人物精神上的某种困扰[13]。少年被以梦魇的形式反复拉回到与已逝父亲的墓地流浪生活景象中,不由自主地反复追忆曾经和父亲在墓地的流浪生活,这种记忆闪回体现出主人公所遭受的创伤的深度和持久性。少年对墓地生活念念不忘,他的父亲亲历的墓地殉情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所提及的(殉情事件中的一人是刚从西伯利亚收容所回来的复员兵)“西伯利亚”这一地名具有重要的意义。“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少年遇见过一些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人们。他们一两个小时地讲述西伯利亚的事情……他们讲的是挨饿、寒冷、疾病以及冰天雪地的故事。听着听着,少年觉得西伯利亚可能就是他和父亲过夜的地方。‘西伯利亚’这个词的发音,和自己记忆中的那些石柱和泥土的感觉太接近了。父亲已经死了,所以那个地名就像怀念父亲的诫名。父亲的音容笑貌已记不清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曾经和父亲一起裹在发霉的枯叶和毛毯里睡觉的场所,对孩子来说已成了父亲的替身。”[5]14由此可知,“西伯利亚”成为“家园”的代名词,一个想象的记忆中的家园,对小说主人公而言,它不仅成为了旅行的目的地,而且,这次旅行也成为一次追寻父亲的旅行,是一种自我心理的探寻。
男主人公的记忆通过过去与具体的场所——墓地相结合。成为中学生后,他第一次独自去了墓地。“墓地的名字记载在关于父亲和孩子的书里。他对这里的一切没有亲切的感觉。真的是这里吗?他踌躇起来。不过,他对几个石碑有些印象。它们都变成了平凡的小石碑了。记得应该是个更宽敞的地方,现在却紧巴巴地冷漠地挤在一堆。他找到了一个大一点的墓,回想着和父亲搂抱着睡觉的那个小孩的样子。虽然在地上垫了一堆树叶,身上裹着毛毯,可是这样的地方每天晚上怎么睡得着呢?而且又是大冬天的时候。孩子呆若木鸡,仿佛这些都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他不由感到屈辱,急忙逃离了那里。 ”[5]14少年苦苦追寻要去存有父亲气息和回忆的场所,所以墓地和西伯利亚在小说里反复出现,不仅表现了少年的创伤和寻根意识,也体现出对于自我身份的探寻。小说设定的家园,既是曾经失落的家园,也是心灵所向往回归的家园。文本的空间故事也在呼应这个主题,男、女主人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这样的家园。男主人公追寻曾经的家园,女主人公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之后又回到家乡。她的记忆是结合于家园的院落这一特殊场所,多次有关家人的梦境都发生在院落这个场所中。
小说《微笑的狼》的记忆书写往往与梦和幻想相结合。不论是少年还是少女的记忆,都糅合了非现实的想象,现实与非现实穿插交错,呈现出小说独特的记忆书写风格。小说运用大量的意识流似的幻想的描绘、各式梦境的描写,将想象的世界引入现实,使回忆与现实交织和共存,在深入探寻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内在的复杂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幻想和梦境的非现实世界的描绘往往融合了人物的童年记忆,在小说中与现实世界交错,尤其对梦境和想象的描绘非常奇幻,从而把日常生活和非现实的世界并存于小说的时空中,不仅增添了这部小说的奇幻色彩,扩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还有利于刻画人物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1]范铭如.当代台日韩女性小说比较初探[EB/OL].[2017-02-06].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81392.
[2]弗兰茨·斯坦策尔.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M]//福柯.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3.
[3]霍士富.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时空美学:论《同时代的游戏》[J].外国文学评论,2009(1).
[4]宁云中.时空压缩与后现代文学想象: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阐释与文学表征[J].湖南社会科学,2012(4).
[5]津岛佑子.微笑的狼[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高宣扬.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89.
[7]高建华.库普林俄国时期小说的叙事时空特性及伦理价值[J].外国文学研究,2016(2).
[8]川原塚瑞穂.津岛佑子の文学:物语と记忆[M]∥学内教育事业.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际的情报伝達スキルの育成」活动报告书.东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教育改革支援プログラム「日本文化研究の国际的情报伝達スキルの育成」事务局,2010:5.
[9]松浦雄介.记忆の社会学:不确定性について)[D].京都:京都大学,2004.
[10]逸见胜亮.败战之后の日本における浮浪儿?戦争孤儿の历史[J].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院纪要(第103号),2007(12).
[11]儿童福祉法研究会.儿童福祉法成立资料集成(上巻)[G].东京:ドメス出版,1978:343.
[12]多重记忆书写: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J].当代外国文学,2012(4).
[13]罗钢.叙述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6.
(编辑:文汝)
I106.4
A
1673-1999(2017)11-0065-05
颜丽蕊(1986—),女,硕士,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2017-07-17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记忆理论视阈下的津岛佑子小说研究”(SK2017A0678);安徽新华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精品课程“日语翻译”(2016JPKCX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