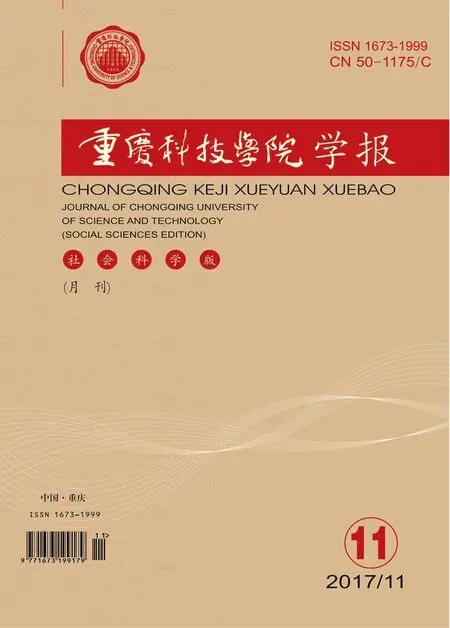集体意向与实践理性
柳海涛,杨羚
集体意向与实践理性
柳海涛,杨羚
个体打算参与一项集体行动时预先蕴含着对与该项集体行动相关的某种共同实践的内在理解,共同实践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基本背景。背景在行动中不进入行动者的信念-愿望结构,它与具体的行动者和行动类型没有直接关系。个体基于实践理性对行动形式的反思性评估使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集体意向;循环性;行动形式;共同实践
意向性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它一般是指个体意向。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集体行动,如“德国足球队战胜法国足球队”“苹果公司与三星公司发生专利权纠纷”等。完全用个体成员的意向是不能充分解释这些行动的,需要引入一个类似于用个体意向来描述个体行动的概念,这就是“集体意向”。塞拉斯曾提出过“我们意向”这一概念,并对它进行了初步论述。芬兰哲学家托米拉自1988年以来发表了系列论文来分析“我们意向”,认为“我们意向”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不可还原的意向性类型。当前,随着对集体意向的深入探索,布莱特曼、吉尔伯特和塞尔等人都对集体意向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集体意向已经成为心灵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共同关注的热点论题。现有的集体意向理论大多以个体行动和个体意向为出发点来解释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还原主义和非还原主义的争论,以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进路的竞争。
个体行动者决定参与一项集体行动时,必定预先包含着他对该项行动的内在理解,这种内在理解的根基是人们的共同实践。因此,任何运用个体行动和个体意向对集体行动的描述,都预设了实践理性的存在。比如,我和你准备一起打乒乓球,我有和你打乒乓球的意向,你也有和我打乒乓球的意向,只有如此,一起打乒乓球的集体行动才有可能实现。但是,我和你在产生“一起打乒乓球”的意向之前,我们各自的头脑里事先已经蕴含着对“打乒乓球”的理解,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产生“一起打乒乓球”的意向,而对“打乒乓球”的内在理解是我们在生活世界的共同实践中形成的。因此,集体意向的产生潜在地包含着对相应集体行动的事先理解,而这种理解的基础是人们处于共同体的实践理性中。本文分析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在共同实践中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认为,共同实践是比行动者(不论是个体或集体)和行动(不论是个体行动或集体行动)更基础的基本背景,它不进入行动者的信念-愿望结构,但它使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向成为可能。文章第一部分阐述现有的集体意向性理论对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向的解释。认为行动者对集体行动的预先内在理解是集体合作行为的前提。第二部分分析行动的具体过程,从语法时态上把行动分为未完成时和完成时。认为正是在行动的未完成时,个体对行动的评估和选择,只有能够设想到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形成集体意向和合作行为。第三部分讨论对行动形式的评估。行动形式不是具体的实际行动,而是一般性的、非人格化和非时空性的共同实践,它具有类的属性,它可以在不同时空被不同行动者以不同方式实施。第四部分阐述背景能力与心理的信念-愿望结构的关系。只有个体对行动形式进行评估,才能使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但对行动形式的评估是一种背景能力,其本身不进入行动者的信念-愿望结构,而背景的基础则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共同实践。
一、对集体行动的内在理解
对集体意向的辩护,大多以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基础。首先来看托米拉的“公告板”论证。假设:一个集体的负责人在公告板上通知,计划下周六清扫停车场,愿意参加的人在通知下面签名。这种集体行动是基于成员间明确表示的一致同意。托米拉对集体意向的论证如下:
集体G中的任一成员A有“我们意向”做集体行动X,当且仅当:
(1)A意图做X中他的份额。
(2)A相信X将会实现(或至少有实现的可能),特别是A相信G中有适当数量的成员为了实施X而将会做X中他们各自的份额。
(3)A相信在G中,成员之间有一种信念,即为实现X而愿意做其中各自的份额。
(4)(1)部分原因是因为(2)和(3)[1]。
在这个定义中,“A意图做X中他的份额”,A必定知道X是什么。假若没有A对集体行动X的预先理解,他就不知道自己在X中的份额,从而无法参与其中。不同个体都可以对X产生内在理解,其原因在于他们处于共同实践中。可见,在托米拉的“公告板”论证中,结论中的集体意向已经隐含着行动者对集体行动的预先理解。
吉尔伯特在论证集体意向时引入了复数主体,她认为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的主体是“我们”。集体成员有集体意向做某事,当且仅当他们共同承诺作为“一个主体一样”做某事[2]。吉尔伯特的论证是这样的:F表示愿意实施Y,并且E也表示愿意实施Y,从而F和E形成共同承诺,进而F和E构成像“一个主体一样”的集体行动者“我们”,“我们”有集体意向做Y。相对于个体,吉尔伯特强调集体与其有同样的本体地位,但在论述集体的形成时,吉尔伯特依然把它归结为个体意向。不同个体对同一集体行动事先产生共同的内在理解是形成集体的前提,进而集体才拥有集体意向。
塞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根据自己的生物学自然主义观点,把集体意向看作是心灵固有的意向类型。他坚持心灵只存在于个体大脑中,但个体大脑中的意向类型既有个体意向也有集体意向,并且与外界缺乏互动的私密性的“缸中之脑”也会具有生物本能性的集体意向。塞尔的唯我论式的论证,无法解释集体意向的规范性功能以及个体意向之间的协作。而且,塞尔虽然觉察到了集体意向的共同实践基础,但他没有在这一点上深入下去。可以说,只要接受只有个体心灵,没有“集体脑”,任何集体行动的产生都无法避免个体对集体行动的预先内在理解。塞尔没有区分开内在理解和集体意向之间的微妙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把集体意向归属于个体还是集体,都必须承认行动者处于共同体的实践中,而实践理性蕴涵着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为了剖析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的实质,就需要厘清共同实践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对行动的具体实施过程的分析是一个颇具意义的途径,从语法时态上,可以分为行动的未完成时和完成时。
二、行动的未完成时与完成时
一个行动意向得到满足,当且仅当它的意向内容在真实世界中实际发生。个体行动的未完成与完成相对简单。例如,“我打算到办公室”,当且仅当我到了办公室,“我打算到办公室”的意向才得到满足,这个意向行动就完成了。否则,行动意向就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意向行动没有完成,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内在的原因,比如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想去逛街。第二,外在的原因,如路上出现了障碍,或者是下雨了等。
集体行动的实施过程就要复杂得多。假设:两个恐怖分子企图刺杀一位政治家。经过密谋,他们决定采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一人驾车,另一人坐在车里开枪射击。当且仅当他们两人密切合作,杀死了政治家,两人“刺杀政治家”的集体意向行动才得到实现。如果这项集体行动没有完成,其原因会有以下3种情况:
(1)内在的原因。比如,在他们开始行动时,看到了政治家活泼可爱的女儿,良心发现,使他们同时认为让一个幼小的女孩失去父亲是错误的,于是都改变了主意,取消了行动。
(2)外在的原因。如在他们行动的路上,汽车突然发生了故障,无法继续前行,于是行动终止。
(3)混合型的原因。在行动过程中,看到政治家的女儿时,车手改变了主意,扭转方向盘改变了行车路线,以致枪手在射击时没有击中目标,行动失败。
前两种情况和个体行动相似。关键是第三种情形,在集体行动中,只要它还未完成,有一个参与者改变或取消了行动意向,“刺杀政治家”的集体意向就不复存在了。此时,作为集体行动者的“我们”也不存在了。即使另一个行动者仍然朝向原有目标行动,这时的行动已经转变为他自己的个体行动。这表明,在集体行动中,每个参与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像切蛋糕一样,切走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考虑其他剩余部分。
行动的未完成时可以这样表示:对于任一个意向行动W,在某一时刻它正在进行,并且在此时刻它又没有被完成。在行动的未完成阶段,W是可能失败的,或者被错误地实施。这时,行动者心灵中的“W”并不是实际的行动,而是一般性的行动形式。比如,建造房子。只要房子没有建造出来,“建造房子”的意向就在行动者的心灵中以一般行动形式被表征着。“建造房子”的行动可以被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实施,从而建造出各式各样的房子,每一种建造房子的实际行动都是“建造房子”这种行动形式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在“刺杀政治家”的行动中,只要没有杀死政治家,“刺杀政治家”就仅以一般性行动形式存在于参与者的心中,当参与者对“刺杀政治家”的行动形式进行反思性选择时,它才有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可能。其中任何一个参与者中途改变意愿,都会导致集体行动失效。在未完成的行动中,它以一般性的行动形式存在于行动者的头脑中,因而,行动有可能失败或者发生错误,也有可能实际进行的行动与行动者心中的行动形式不一致。如果行动者在行动的实现方式上采取与他人合作,就有可能形成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因此,对行动形式的评估就是关键。
三、对行动形式的评估
行动形式是一般性的、具有类的属性,它不指向具体行动,它可以被不同人在不同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执行。既然行动形式有类的特征,那么它必定具有一个公共标准,从而使不同的行动者可以依据这个公共标准对其进行评估,作出选择。因此,不同行动者对同一行动形式,依据共同标准作出不同的评估,就会实际产生不同的行动类型。能够根据公共标准对行动形式进行反思性评估的基础是共同实践,它们的实现离不开行动者所处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对集体意向的论证都必然预设了某种共同实践,共同实践本身恰好蕴含着集体意向所要实施的那项集体行动。
个体行动者M对集体行动D的内在理解,是对D的一般性行动形式的评估。例如,单纯地说“散步”就是一种行动形式,它不涉及具体的行动者和行动类型,并不受时空约束。但当M对“散步”进行反思性评估,并选择具体实现“散步”的方式时,“散步”才有可能是集体行动或者是个体行动。如果M选择与他人一起散步,那么“散步”就成为一项集体行动。在评估时,M不一定必须根据D的公共标准表达出自己的行动意向,也不必一定加入一个集体来行动。行动形式不具备人格性和时空性,因此无所谓失败或成功。集体行动就不同了,它有失败或被错误实施的可能。只要它没有实际被完成,它就存在于未完成的领域。在未完成领域中的行动只是在行动者头脑中被以一般性行动形式所表征,并被不断地评估,从而采取不同的实现方式,如采取个体行动或是集体行动,前者就是“我做D”,后者就是“我们一起做D”。在形成与他人合作的意向前,D是作为潜在的一般性行动形式存在着的,每个个体之所以能够对D产生同样的行动意向,是由于他们处于共同实践中形成了对D的相似的评估。
共同实践的意义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塞尔所提出的“背景能力”,它是个体之间产生共同理解的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分析哲学的视角看,“背景”是一组非表征性的心理能力,它使意向状态成为可能,而背景能力本身不是意向状态,它独立于外在的真实世界。真实世界中的事物以意向性的形式被认识,然而,意向状态的产生和实现离不开“背景能力”。例如,我想打乒乓球。我不会想着和一块石头合作,因为在我的“背景能力”中石头没有合作能力。社会学家米德也曾经进行过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某人作为人存在,因为他属于一个共同体,因为他接受该共同体的规定并使之成为他自己的行动。他用他的语言作为媒介借此获得他的人格,然后通过扮演不同角色这一过程,逐渐取得该共同体成员的认可[3]。这表明共同实践建构着个体的意向态度,它是人的社会性的根基。但共同实践本身并不是集体行动,就像一把刀,它本身并非必然是杀人凶器,只有人的意向性选择使用,才使它成为了凶器。
四、背景能力和信念-愿望结构
行动形式统一于共同实践,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内在理解是基于共同实践的。可能会有人问,对行动形式的评估似乎隐含着集体意向。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有两个地方容易产生混淆:一是对集体行动的内在理解与集体意向;二是对行动形式的评估与集体意向。对集体行动的内在理解和对行动形式的评估具有相同的含义,可以把两者等同起来。但它们都不同于集体意向,其本身更不是集体意向,原因在于它们是集体行动和集体意向产生的背景,不进入个体心灵的信念-愿望结构。
一个句子仅凭其自身并不能够被恰当地理解,往往需要一个背景才能理解它的含义。比如,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对这句话的恰当理解包含着许多句子之外隐含的前提:一个地方叫做食堂;一天中某一次吃饭被称作午饭;我知道你是要吃饭,并且你也知道我也要吃午饭;我们都用嘴巴吃饭……这些隐含的信息构成了一个网络结构,但它们并不进入说话者的意向状态,更不是说话者的信念,它们就是背景。背景的功能与信念的功能不一样。我投票选举某人当系主任是因为我相信他比其他候选人更合适,我有很多理由来支持这种信念,这是信念在我们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正确理解“我们一起去食堂吃午饭”这句话的背景并不像信念那样发挥作用,说话者并不需要首先确信“食堂”“午饭”“嘴巴”等事实的存在,然后才可以说“我们一起去吃午饭”。在这个层次上,行动好像是“无根基”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我们仅仅是做它”。这意味着,在决定某一行动时,我们并非不得不首先去建立这个行动所隐含的条件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关注行动本身即可。
可见,背景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深层能力,它不是意向性。事实本身并不表征,通过意向性才使事实被表征出来,但对事实的表征离不开非表征的背景。背景是我们能够交流和合作的基础。在集体行动中,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内在理解并不进入他的信念-愿望结构,它不是个体的意向状态,但它形成了个体反思性选择的基础,从而使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因此,共同实践作为背景,它本身不是信念,而是信念和意向状态得以被理解和实现的条件。显然,对集体行动的预先内在理解与集体意向虽然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由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共同实践决定的。
五、结论
本文通过把行动过程分解为未完成时和完成时,从未完成时的行动存在失败的可能性的角度,反向追溯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产生的深层根源,从而揭示出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是个体在共同实践中依据公共标准对一般性行动形式进行评估而做出的选择性行为。共同实践是人的基本生存背景,它不进入行动者的信念-愿望结构,但它是集体意向的实践理性基础。
[1]RAIMO T.We-intentions revisited[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5(3).
[2]MARQARET G.Shared intention and personal intention[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9(1).
[3]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7.
(编辑:文汝)
D023.2
A
1673-1999(2017)11-0007-04
柳海涛(1977—),男,博士,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原理;杨羚(1994—),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2017-09-18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知觉问题研究”(1020607820150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知觉哲学研究”(2015M57023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后物理主义研究”(106112017CDJXY0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