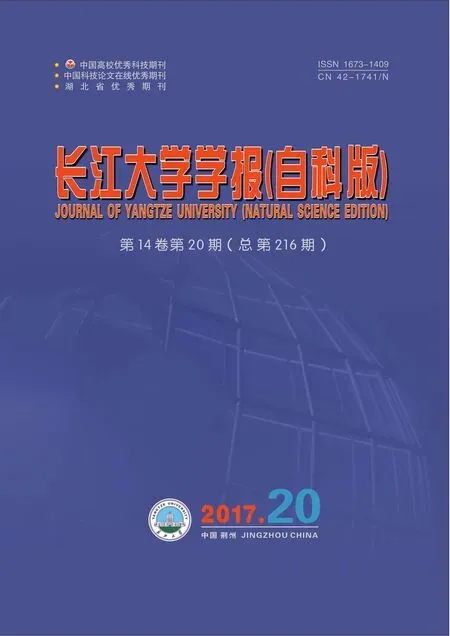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视域下的“学术自由”的度
郑晓艳
(江汉大学期刊社,湖北 武汉 430056)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视域下的“学术自由”的度
郑晓艳
(江汉大学期刊社,湖北 武汉 430056)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观是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指导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坚实理论根据,对我国的学术出版自由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新闻出版观中的阶级性、人民性、非行业自由等思想对如何把握好学术期刊中“学术自由”的度,具有借鉴作用,也是促进学术期刊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学术性与政治性原则的关系;处理好学术自由与学术争论的关系;学术自由与学术价值的辩证统一。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自由”必须要遵守学术规范、学术纪律,行之有序,言之有度,方能“自由”。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版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期刊
在中国,提起“学术自由”一词,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传播学术自由思想的主将蔡元培,蔡先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后被概括成“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研究主要是由大学或专门的科研机构承担,从广义的角度看,学术自由一般被理解为学术研究或教学机构的学者有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不受不合理干扰和限制的权利,包话讲学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狭义来看,学术期刊中所涉及的“学术自由”隶属于出版自由。
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指根据我国《宪法》和《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学术期刊编辑部享有刊发学术论文的自由权;另一方面是指学者们进行学术活动的自由,即专业人士有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保护其权利主体免受其它学者或者社会责难的权利。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求“真”的过程,任何一种新的研究成果的提出,都难免会出现不同的意见或者引起负面的后果,尤其是自然科技期刊的研究中,新成果的现实应用有时会不如理论预期效果,但这与研究者本身的善恶无关,学术自由就是要使学者免受因学术成果的不完善或不正当使用而引起的责难。如果没有这两种自由权利,那么学者们就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大胆探索,交流思想,促进社会的知识的整体进步和发展。学术期刊也会因为缺乏创新性而丧失了活力,无法实现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科学进步的载体功能。学术自由为从事学术活动的人提供基本的精神环境,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学术成果的载体,同样应享有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
但是有了这种自由是不是能代表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地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呢?显然,学术自由一旦被嵌入学术期刊的范围内,就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而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即在合法、合理、合情范围内的自由。作为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其它学者或普通民众也有宣传引导功能,可见,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要包括不能违背人类的道德底线,同时也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发展人类文明服务的,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生活和谐,人类进步的,而不能有违社会伦理,危害社会稳定。学术自由的运作,需要在一个开放的、有生机的环境中进行,一个不僵化的环境提供了这个空间,学者们才能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一个有生机的、不僵化的环境,自然包括了一定的学术秩序、学术纪律、学术规范。“学术自由真正理论基础是: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1]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自由”必须要遵守学术规范、学术纪律,行之有序,言之有度,方能“自由”。
1 马克思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和学术自由
马克思的新闻出版自由观是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指导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坚实理论根据,对我国的学术出版自由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新闻出版观中的阶级性、人民性、非行业自由以及出版法的思想对如何把握好学术期刊中“学术自由”的度,具有借鉴作用,也是促进学术期刊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1 新闻出版自由具有阶级性
历史实践证明,在阶级社会中,利益的多样性和异质化无法满足各个不同阶级对自由的需求,出版自由必然与某个阶级利益交织在一起。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在传播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在批判其虚伪性的基础上,指出新闻出版自由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基本性质及其阶级特征[2]。与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自由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同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目的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促进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在我国,学术期刊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学术研究脱离了实际,只会走向无产阶级的相反面,“学术自由”也会变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化”。
1.2 新闻出版自由具有人民性
马克思曾提出“人民报刊”的概念来强调人民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主体,“报刊不应该从代表少数特权等级的私人利益出发,而是要从反映大多数民众的普遍利益出发”[3]。不管是自然科技期刊还是人文社科类期刊,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造福社会,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也具有人民性,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就要求,一方面,学术期刊不能发表那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进步的论文,如宣传暴力犯罪等,这与办刊的宗旨背道而弛;另一方面,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应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宽松的学术科研氛围,使他们免受行政机构体制和外界舆论的干扰。学者们也要敢于大胆创新、开展学术科研工作,使学术观点能自由碰撞交流,促进学术繁荣。实现了人民性,意味着实现了真正的学术自由。
1.3 新闻出版自由不是行业自由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对新闻出版自由和行业自由作过区分,前者的目的是人们为了真理,不是为了其它目的而追求的一种精神自由或思想自由;后者是出版商为了营利而追求的营业自由,马克思坚决反对这种为了牟取利益而进行写作。在我国,学术期刊编辑部基本上都属于非营利性质单位,其经济来源都是依赖国家或学校的拔款,几乎没有营业性的收入。但是近年来,不少学者们将“学术自由”当作追求升职、评职称、排名、多拿报酬的手段,导致学术逐渐走向功利化,利益之争淹没了学术研究真正的意义,从而丧失了提倡学术自由的价值所在。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不应该沦为一种行业自由,马克思的出版自由观对规范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4 新闻出版法是对出版自由的保护
马克思曾批判过“书报检查令”,认为这种书报检查是资产阶级以法令的形式对出版自由的剥夺,同时论正了真正出版法的本质是要保护人民享有新闻出版自由,并主张进行真正的新闻出版立法。[2]学术期刊汇集和保存了学者们的科研成果和交流学术思想的重阵,我国的《宪法》《出版管理条例》是公民思想言论及出版自由的保障,学者们可以自由讨论和交流不同的意见、观点、在不违背道德与法律的前题下,对不同的学术思想的冲突,政府均不干涉。学者们“真正享有的是国家赋予的出版自由,既规范公民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又确保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发表价值”[4]。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不应该是任意随心驰骋的野马,对于学术研究主体来说,不应该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进行危害国家、社会、人民的研究活动,学术期刊编辑部也不能发表有损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社会正义的论文。
2 如何把握学术自由的度
学术期刊是报刊中的一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自由思想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尊重学者的主体地位,发挥学者的创新精神,促进学术发展。学者享受学术自由的时候,有责任证明其学术观点不违反法律法规,保证其真实性、客观性、实用性。期刊编辑身为学术成果的把关人,在审读稿件的时候,更应该把握好“学术自由”的度,编辑需要有敏锐的政治性和学术鉴别力,有责任剔除那些不符合法律法规、恶意危害社会或他人的论文,保证学术成果的高质量。
2.1 学术自由与政治性原则
学术期刊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的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任何期刊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首要是将政治性放在第一位,政治原则是期刊的生命,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命。脱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意味着学术期刊的终结。梁凤鸣在《论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与政治性原则》中指出:“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必须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也必须具有政治性。”[5]郭柏寿等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何种社会制度下,期刊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的期刊自然而然要服从和服务于此,要圆满完成时代赋予期刊的重任,就要求期刊在政治上必须过硬。”[6]
除了政治性外,办好学术期刊的重中之重在于其学术性,不具备学术性的刊物,不能称之为学术期刊。学术研究是追求与探索真理的过程,需以思想自由为基础,学术自由的诉求来自于学者们能够不受干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学者们在享受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科学的态度,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学术期刊在坚持政治性原则的范围内,应持有宽容的精神,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发表有独道见解的论文,能包容和接纳不同的意见、学术争论和观点,不拘一格,形成自己的特色栏目。我国现阶段在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中,存在着非学术规范对学术自由的束缚,政府部门和学术期刊自身为了追求期刊的整体利益,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干预和控制学术自由。如在大学内部,学校的行政系统权力集中,具有参与管理学术的权力,真正的学术权威则很少有发言权。再如,某上级部门在审读期刊后,认为该期刊中研究西方的论文过多,作出“言必称希腊”的评语,并责令其期刊进行整改,殊不知学术价值并不是由“言必称希腊”或“言必称中国”来决定的。每个期刊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不违反《宪法》《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学术期刊有权利决定发表的内容,这种干预过度、过细对学术自由是一种妨碍。
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在把握“学术自由”的度的问题上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一方面,编辑要有清醒的政治敏锐性,熟知《出版管理条例》,判断学术论文中涉及的问题是否有“过界”或者“踩界”现象;另一方面,编辑也要有准确的专业判断力,对论文的学术价值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拘泥于形式,敢于突破创新,抵制行政管理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保证学术能充分享受“自由”。
2.2 学术自由与学术之“争”
提倡学术自由,就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提供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不同的声音可以进行辨析,争论,学术争论是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需要和同领域的人进行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论证自己的成果,有交流就会有意见分歧,就会产生争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大明认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通过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沟通,互相砥砺切磋而产生共识的过程,争论是交流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7]科学客观合理的学术争论是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繁荣的必经之路,也是辨别“真伪科学”的重要手段。学术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是鼓励学术之争的,争论既体现了对已有成果的尊重,又能推动研究的创新,没有经过争论的学术论文严格来说其学术价值是有限的。比如西方政治哲学中,正是诺齐克、德沃金等人与罗尔斯就正义问题展开争论,才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有的学术期刊甚至会采取同时发表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的论文,或者就某一具有争论性的问题,连续性刊出不同观点的论文,这些在学术自由的范围内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学术之“争”毕竟不同于口舌之争,无论是证伪对方的观点还是证实自己的观点,都需要以平等、尊重为基础,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以充分的证据,进行学术切磋。反观如今某些学术争论,辩论双方在争论过程中出现剑拔弩张的气氛,抓住对方一两句话不放,断章取义,甚至用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去攻击对方,丧失了学者应该的风度和修养。这种学术之争,明显带有个人情绪性,偏离了学术争论的主题,沦为一种个人意气之争,无益于学术的发展。
所以,学术期刊编辑在面对学术之“争”时,也需要把握好学术自由的度。有了学术自由,不代表能够任意妄为地使用这种自由去抵毁他人的学术成果。学术争论的对话双方应该是平等地交流,真诚地互通有无,只有具有这样的心态和品质,才能开展学术交流与对话。编辑在审读稿件时,既要能包容地看待学术之争,判断这种争论的学术价值,也要能够避免论文中的过激言语表述方式,对其中某些含有个人情绪化、中伤他人的语句进行修改或润色,防止学术之争成为一种庸俗化的学术闹剧。学术期刊的编辑只有把握好这种度,才能使学术争论走向理性和深入,彰显出学术的价值。
2.3 学术自由与学术价值的辩证统一
学术论文必须具有学术价值,学术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学术成果的价值体现在对原有理论的创新和突破,本质上就是能推动人类精神文物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学术自由与学术价值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学术自由是实现学术价值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们能自由思考、自由研究、自由争鸣、自由发表,才能发展社会的科学文化事业,真正实现学术成果的价值。而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学术成果社会价值的实现,又反过来使国家和政府在政策上能赋予更宽松的学术环境,给予其更大的学术自由权,学术自由的相关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
学术自由为学术价值的创造提供了条件,但随着人们自由意识越来越强,也有一些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表学术论文,造成这种权利的“滥用”。他们大量发表、出版学术成果,不顾内容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有无学术价值,有的甚至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极大地腐蚀了学术风气,降低了学者的人格。现阶段,学术论文中不乏有些缺乏创新性、实用性,为了发表而发表,学术价值不高的学术成果,更有一些学术界外部人士,为了某种利益,也鱼目混杂地加入了“学术活动”。他们不懂任何学术规范,也没有经过深入地研究就自以为是地从事学术这一行,“享受学术自由的待遇,其结果不仅损害了学术自由本身,更是践踏了保障学术自由的学术规范”[8]。
学术期刊编辑是论文的学术价值的最初判断者,要把握好学术自由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学术自由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如果这种自由度放得过宽,有可能造成大量学术价值不高的平庸之作,对国家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如果自由度过严,有可能会打击学者的积极性,抑制了学术繁荣。对于学术价值的判断,既与编辑自身的专业水平有关,又与其阅历有关。专业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平时的不断学习,阅历的丰富有赖于平时的积累,多看、多问、多思,才能提高自己的编辑水平。编辑的责任担负着两重责任:一是在不违反政治性原则的范围内,站在时代的前沿上,敢为天下先,为学术观点的碰撞和升华提供机会;二是注重学术价值,不盲从、不附和,从而保证学者们能将高水准的学术思想表达出来。
3 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
学术自由是学术繁荣的基础,一旦丧失了自由,学术活动成了无源水之,无本之木,随之也失去了活力和创造力。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取决于学术自由和创新的社会环境;学术自由的环境也反过来影响着学术研究。我国的学术期刊在学术自由的问题上容易趋向两种极端。
第一,刊物评价等级化的方式造成学术功利化。刊物的等级之分也使学术论文有了等级之分,以高校为例,教师或研究者们为了完成每年的科研工作量,或者为了评职称,获奖项,报项目,都会追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有的宁可在核心期刊排队等上1年的时间,也不愿意在普通刊物上及时发表,这种行为其实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学术期刊在审稿时,也是按照基金项目课题的等级来排序,大都希望作者能够挂较高等级的课题项目,国家级的课题优先于省级的,省级的优先于市级的,一层层下来,有些没有课题项目的论文就被淘汰掉了。一些期刊一旦进入学术界或期刊界核心指标体系数据库,如“全国中文核心”“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会按等级论价,按价发表。学术的功利化使学术论文的发表演变为一种商业化的运作,使学者浮躁,学术异化,论文质量下降,失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
第二,以行政化的管理方式约束学术,束缚了学术自由。学术机构,尤其是高校内,行政部门以职权干涉学术事务现象屡见不鲜,一些非专业的职能部门领导膨胀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决策过程重视行政而轻视学术、职能运行上行政代替学术、系统协调上行政主导学术”[9]。行政部门掌握着学术资源配置权,对学术可以进行行政干预,甚至职能部门的领导利用权力之便,夹塞人情稿、关系稿,人为地造成了学术的不公平,违反了审稿制度,妨碍了学术自由,不利于学术繁荣。如果学术期刊为了迎合领导权威来办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滋生学术腐败,催生学术垃圾。学术事务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组织,高校的行政权力应该是为学术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学术,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繁荣,而不是限制和妨碍这种自由。
综上来看,学术自由是学术期刊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要想真正实现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必须以马克思出版自由思想为指导,在建立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上,既要敢于批判、敢于创造、也要注意分寸与尺度。学术自由是在学术秩序和学术规范下的自由,期刊编辑游刃于学术性与自由性之间,应该遵从学术自由规律,回归其学术本位,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
[1]林毓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自由[EB/OL].(2015-03-03).http://www.aisixiang.com/data/84604.html.
[2] 刘文科.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观点与当代实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 (11) :72~76.
[3] 金伟.马克思义义新闻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13(8):189~193.
[4] 于小艳,冯梓明.审视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J].今传媒,2015, 23 (6) :46~48.
[5] 梁凤鸣.论学术期刊的学术自由与政治性原则[J].新闻战线,2014 (8) :166~167.
[6] 郭柏寿,潘学燕,杨继民,等.科技期刊涉及的有关政治性、法律性及保密性问题[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2 (6) :941~943.
[7] 张春海,饶嘉.学术争论:重理性,去庸俗[EB/OL].(2016-10-21).http://ex.cssn.cn/zx/201610/t20161021_3243698.shtml.
[8] 高晓清,顾明远.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对我国切实性问题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4 (5):5~6.
[9] 董云川.大学行政权利的泛化[ J].高等教育研究,2002(2):60~63.
2017-07-20
郑晓艳(1978-),女,博士,编辑,主要从事期刊编辑与外国哲学研究, zxyfly@126.com。
[引著格式]郑晓艳. 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视域下的“学术自由”的度[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 2017,14(20):86~90.
G230;G213
A
1673-1409(2017)20-0086-05
[编辑] 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