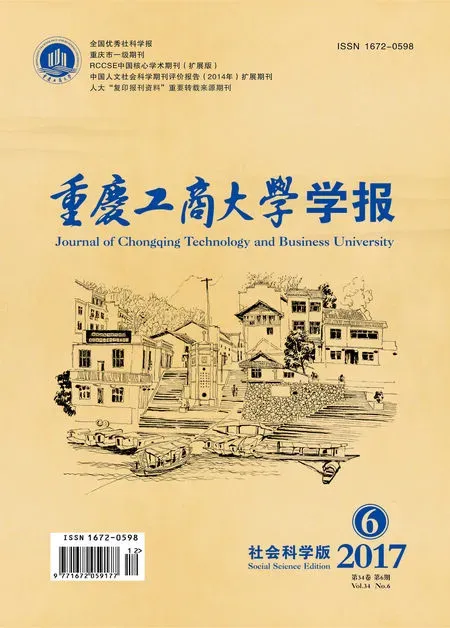数与混沌
——以麦卡锡西南部小说中的数三为例*
张小平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数与混沌
——以麦卡锡西南部小说中的数三为例*
张小平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作为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数有语言、文化、符号等多重属性。数文化中倍受重视的数三,更是以其神秘性、神圣性及其与当代混沌学的多方联系,得到了当代美国小说家科麦克·麦卡锡的青睐。在麦卡锡的西南部小说中,数三经常出现,不仅为麦卡锡的小说叙事增添了数文化的神秘魅力,更使麦卡锡的小说有了当代混沌学的内涵与思维特点。
数;麦卡锡;混沌;美国小说;《穿越》;《老无所依》
学者叶舒宪曾经指出,“文明的开端始于文字,文字的开端始于数字”[1]1。不仅如此,相比“数字”而言,“数”则更为原始,因为在数字没有形成之前,就有了数。数,是人类呈现世界的方式之一,不仅只用来表示数目这么简单,而是兼有语言、文化、符号等多种属性。数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历来被许多民族所重视,反复出现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诗歌、习俗等方面,具有神秘或神圣的蕴含。数文化中的数(字)三,较为特殊。数三,既指确定性的数目三,也常与不确定性的“多”“复”(复杂、重复、往复等)、“混沌”等相联系,具有当代混沌学意义上“混沌”的符号所指:确定的不确定性或有序的无序。事实上,数三因其与当代混沌学的多方联系,还有“分形”“自相似”“决定性混沌”等混沌学范畴的特殊内涵。
当代著名美国小说家科麦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1933)的西南部小说——《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1992)、《穿越》(The Crossing, 1994)以及《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an, 2005)中,经常出现数三。数三在麦卡锡小说中的运用,不仅为其小说叙事增添了数文化的神秘魅力,同时也使得麦卡锡的小说有了混沌学内涵。研究数文化,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重要路径,自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点。鉴于此,考察数文化在麦卡锡小说中的运用,不仅可以了解数文化与麦卡锡小说的混沌学思维的关系,还可以由此反观当代美国文学的创作动态与发展动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数三与混沌思维
从数三的产生来看,它起源于人类社会计数不超过三的时代。人类学家对于原始民族的研究表明,许多原始民族用于计数的名称只有“一”和“二”,间或有“三”。“三”相当于“多一个”或“多几个”的意思。如此,当原始人计数的时候,凡在“二”之外多出的若干个数,都可称之为“三”,因此“三”又具有“许多,很多,太多”乃至“无限大”的含义。老子的著名宇宙生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数三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的意思是“多”,也即万物、世界、宇宙之意。除了代表多以外,数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性,还在于其“作为万事万物生成发展的基数,宇宙创化的单元”[1]47。老子的“三生万物”说认为,从道到万物,其间最大的创生飞跃就在于“三”。如果说数的开端始于一,一可理解为道,而道就是混沌,那么混沌再分成阴阳(即数二),阴阳也即天地(或乾坤),继而天地(阴阳)相交而生人。因此,“三”还可以指“天地人”。《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系辞下》亦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自《周易》始,天地人这个“三”数被正式命名为“三才”。可以说,是“三才”说的形成,使得数三在中国文化中有了天人合一的象征,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三位一体的哲学思维,同时也成就了中国文化集体潜意识深处数三的宇宙论意义。
中国帝王体系中的“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说,正是对应了三才说,从中也体现了数“三”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的文化投射。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数三的印记随处可见。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道德纲领,儒家对读书人教诲中的“君子三畏”“日省三身”“三人行必有我师”“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等,乃至中国古代官吏制的“三公”“三卿”“三官”“三省六部”等众多的“三”式花样,无不体现了数三这个结构素在中国文化中的普遍现象。道教文化中,数三更是一个圣数。道教文化中的“三官”(天帝、地袛、水神),说的是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道教最高的清境为“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当然,道教的三位尊神——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手中所持宝物的象征(元始天尊的无极、灵宝天尊的太极、道德天尊的两仪),组合起来恰是道教一元三分式的宇宙图式。中国的佛教尽管是外来宗教,然而佛教中的“三世”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生”说(前世、现世和来世)、“三界”说(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以及“三宝”(佛、法、僧)、“三藏”(经藏、律藏、论藏)、“三皈依”“三法印”“三阶教”“三谛圆融”说等,无不体现了佛教与人类通用语数三的众多联系。
如果说数三的神秘性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那么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人类共同语汇的数三,也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在西方神话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三位一体”的神袛。希腊神话中有命运三女神、机遇三女神、复仇三女神,还有美惠三女神。当然,希伯来文化中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信仰,影响更是深广久远。圣父、圣子和圣灵折射了天父、地母和人子的三角关系。尽管西方文化的神本位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论有着重大差异,但数作为万物之因和万物之本的观念,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已经有将万物归结于数的关系的传统了。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提到,“每个数都有属于自己个别的目的,某种神秘的氛围、某种‘力场’”,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样被神秘气氛包围的数,差不多是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原始民族也只知道这几个数,它们也只是给这几个数取了名称。在已经上升到关于数的抽象概念的民族中间,正是那些形成了最古老的集体表象的一部分的数,才真正能够十分长久地保持着数的意义的神秘力量”[2]202。可以说,一旦神秘数这种观念产生,就会有极其顽强持久的生命力,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1]1。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知识生产成果最为丰硕的世纪,用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世纪。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众多知识生产域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混沌理论,则是大转型的典范。与以往分析性的思维范式有很大不同,混沌理论是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其核心问题就是认识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混沌状态。混沌理论意义上的“混沌”,不再是传统思维中“无序”和“混乱”的代名词,而是“有序的无序”或“无序的有序”,也即有序和无序的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以往的科学研究往往看重的是有序的、稳定的世界,而混沌理论研究的则是我们生活的宇宙和世界中无序和随机的方面,可以说,混沌理论属于一种后现代科学,其混沌学的思维范式,重新改变了我们对待宇宙和世界的看法。
接近于《周易》的象思维以及老庄文化对于人类世界和宇宙的看法,混沌理论也由数这种符号来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与宇宙。数学家詹姆斯·约克(James Yorke)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洛伦兹所指出的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每一个角落”[3]67。在他的“周期三意味着混沌”一文中,洛克指出,“任何一个一维系统里,只要出现周期三这一正规周期,这个同一系统不仅能显现其他长度的周期,也能表现完全的混沌”[3]73。约克的这一发现,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直觉认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以为,在现实世界里造成一个周期“三”的振荡,将其自身不停地重复下去时,并不会使得系统产生混沌。而约克的发现,不仅呼应了中国古老哲学对神秘数“三”宇宙演化论的认识,更是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了数三与决定性混沌(deterministic chaos)的联系。实际上,数三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后现代科学意义上决定性混沌的象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有序而无序。
不仅如此,数三在混沌理论中还有“分形”的概念。混沌理论认为,分形就是决定性混沌运行轨迹的“类像”,可以用来映射非线性动力系统中物质运动的相空间。分形的主要特征是“自相似”,指的是部分常常呈现出与整体相同或相似的性质,而部分与整体的这种自相似性,暗示了图形跨尺度上的重复对称性。因而,无论从周易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宇宙演化论,还是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数三与世界关系的精妙解释,抑或从道教的“三清”神尊,佛教大雄宝殿上巍然耸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尊佛之间既同一又有差异的关系,不难看出,数三还具有混沌学意义上分形的内涵。
此外,作为一个敏感数,数三还与科学中的三体问题有所关联。格雷克(James Gleick)认为:“科学中的两体问题相对简单,因为牛顿已将此问题完全解决。任一天体,如地球和月亮,会以其完美的椭圆形轨迹围绕系统共有的重力中心运行。但如果多加一个其他有重力的物体进去,一切都会改变。三体问题相对复杂,有时甚至比复杂还要糟糕。正如庞加莱的发现,三体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可能性。我们可以用数暂时地算出他们运行的轨道,如果利用强大的计算机的话,也只能稍稍略长一段时间跟踪它们轨道的演变,但很快就会被不确定性操控”[3]145。如此一来,混沌理论意义上的数三便有了新的神秘性,也即混沌性,“与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相关”[5]156。
二、混沌、分形与“周期三”
麦卡锡的西南部小说中,数三经常出现。在小说《穿越》中,数三在叙事中的频繁运用,显然与混沌理论的分形相关。首先,《穿越》有三个部分,讲述了小说主要人物比利(Billy Parham)三次跨越美墨边境的故事。然而,无论是他首次跨域边境送一头受伤的母狼回普拉尔山的家乡,还是第二次跨越边境只为找回父母被盗的马匹,或是第三次带弟弟到墨西哥而最终返乡的却是弟弟的尸骨,总之,每一次比利决定的后果不是死亡就是失去。决定改变人生,而比利的每一次失去,却总与他生活中的微小事件有关。他没有告知父母就为林子里流浪的印第安人送去食物,这个决定为他的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招致了父母被杀以及家中马匹被偷;没有遵照父亲的嘱咐,一旦发现狼群中了陷阱就立即回家禀报,而他冒失决定送受伤的母狼回家的“乌托邦”理想,招致一系列人生之旅中悲剧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写了个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周围人以及母狼的命运。同样,无论是比利第二次的跨越边境旨在找回父母被盗的马匹,还是他第三次跨越边境带弟弟到墨西哥去,结果与他一起返乡的却是弟弟的尸骨。总之,比利的众多失去,无不关乎他生活中的微小决定。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动力系统的最终演化,取决于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依赖。尽管小说没有直接指出比利的生命系统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依赖,但却明显表现出比利生活中因果不成比例的混沌特征。在小说末尾,比利彻底成了一位孤独的流浪者。
其次,《穿越》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在比利穿越边境的主体叙事结构下,又镶嵌了比利遇见的三位智者——前牧师、盲人革命者、吉普赛人对他讲述的三个故事,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宏观与微观上“跨尺度的自相似性”,也即分形。混沌理论认为,分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决定性混沌运行轨迹的“类像”,可以用来映射非线性动力系统中物质运动的相空间。分形的主要特征是“自相似”,暗示了图形跨尺度上的重复性对称。通常,在一个分形的图形中,会有许多彼此相似的图形镶嵌其中。《穿越》中,比利与狼的穿越边境之旅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叙事部分,而比利三次穿越边境的旅行中从前牧师、盲人革命者、吉普赛人处所听到的小故事,则是小说主体叙事部分下的镶嵌故事。这些镶嵌故事就小说的主旨而言,几乎与小说主要叙事部分有某种程度上的“跨尺度的自相似”,构建了小说叙事内容和叙事结构上的分形特征。正如小说中的人物前牧师所说,“对我们来说,世界就是一块石头或一朵花......一切置于其中的无非就是一个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所有更小的故事的总和。所有的故事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又含纳了其他的故事......准确地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5]145。事实上,上述三个镶嵌故事的讲述者,的确如麦卡锡其他小说中的健谈者一样,他们充满宇宙真理与生活哲思的智慧“独白”,“是对小说主要叙事部分的内容所做的反思或评判,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叙事的真相”[6]122。可以说,分形的叙事形式是对叙事自身自我指涉性的强调。当然,麦卡锡也借前牧师之口表述了他对叙事的看法,“一切都是讲述”[5]155。
再者,除了小说主体结构与镶嵌结构上数三的运用,《穿越》还有多处细节与数字三相关联。比利首次荒野之旅的伙伴是一只受了伤的三条腿的母狼,第二次旅行他在卡博卡(Carboca)遇到的那座破旧教堂,仅仅靠三条腿站立,第三次旅行他碰到一只瘸了腿(也是三条腿)的小狗。还有,比利曾三次报名参军,但三次均因心脏有杂音被拒入伍。小说中比利还哭过三次,做过三次梦,梦到母狼、父母亲遇害及其与弟弟荒原行走的场景等等。从某种程度上看,数三的运用,呼应了小说《穿越》叙事结构上的分形,使得文本的微小细节呼应了文本主体的叙事部分,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多维呼应。总之,大量与三这个数有关的文本细节充斥在小说《穿越》中,使得小说的叙事文本与混沌理论的分形有了一致性,构成了文本上的重复对称性。
如果说三这个数在麦卡锡的小说《穿越》中,与混沌理论的重要概念——分形有关,那么,他的另一部西南部小说《老无所依》中,频繁出现的数三则与宇宙的混沌行为关联。有趣的是,发生三次的事件,频频出现在《老无所依》的叙事中,突出了该小说的混沌叙事模式。小说伊始,警长贝尔(Bell)就谈到他曾把一个年轻的男孩送进死刑毒气室,后又亲自“去看过他两三次。是三次”[5]1。接着,小说围绕三个主要人物的“旅行”展开:莫斯(Moss)为逃脱旭格(Chigurh)和墨西哥毒贩派来的杀手的追杀以及贝尔的追捕的逃难之旅;旭格为追讨巨额赃款而频频制造血案的死亡之旅;贝尔为抓捕莫斯和旭格无功而返的失望之旅。上述三个人物的相互追逃,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并以三重结构的形式出现,使得小说运用事件三的叙事模式更加完整。例如,莫斯有三次遭遇旭格:前两次莫斯靠着卓越的枪法与反侦察能力,成功逃脱,第三次他则不再幸运,与一个搭他顺风车的女孩在旅馆门前被旭格射杀。同样,旭格也是三次死里逃生:第一次,尽管使用牧场上宰杀肥牛用的气缸这种奇特的作案工具暴露了他的身份,然而在被警方捕捉后却又巧妙地用镣铐杀掉了看守警察而逍遥法外;第二次,尽管他在与莫斯火拼时被射中要害,但却靠着他非同常人的毅力,摆脱了死神的控制;第三次,他在艾尔帕索镇(El Paso)追杀莫斯的妻子简(Carla Jane)后被车撞成重伤,竟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小说中,贝尔也是三次遇到旭格,却三次与其失之交臂,不是他到达案发现场,旭格前脚刚刚离开,便是旭格从贝尔的眼皮下扬长而去,使得贝尔错失抓捕旭格归案的多次良机,最终未能及时遏制暴力的蔓延。小说呈现旭格与他追杀的对象的谈话也被安排为三次:第一次是他与加油站老板的谈话;第二次是他与毒枭派来的职业杀手卡森·威尔斯(Carson Wells)的对话;第三次是他与莫斯的妻子简的长谈。混沌理论认为,混沌主宰着我们生活的宇宙。我们生活的世界乃至宇宙,混沌无处不在,非理性与非线性才是生活的常态。数三频繁出现在小说中,尤其是情节事件出现的“周期三”,使得小说《老无所依》的混沌叙事模式更加突出。
麦卡锡的作品中,暴力这个挥之不去的主题常常为人诟病。然而,对麦卡锡来说,尽管其笔下的大小人物,无一不被卷入了暴力形成的混沌系统中,暴力却不仅仅是“一种随机的极权力量,深深地扎根于这个国家的起源中”[8]7,更是“一种事实、一种确定性、一种力量,从不中断,令人不得而知”[9]89。小说《老无所依》中,暴力集中体现在变态杀人狂旭格身上。有趣的是,麦卡锡笔下的恶人大多口才极好。就如《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 1985)中的法官霍尔顿(Judge Holden),旭格的谈吐往往类似哲人。每次杀人前,旭格总会和他要杀的对象,就随机和决定论说上一长段饶有哲理的言论。在他看来,上帝不再慈善关爱,而是“抽象冷漠,只对人类难以理解的原则有兴趣”[7]160-1。不仅如此,杀人之前,旭格总要给被杀者一个抛掷硬币的机会,随机决定对手是杀或是留。旭格不仅借助抛掷硬币的或然率,来确定被杀者的命运,还以此来解释他对人类生活的神秘性以及世界的确定与随机性的看法。
实际上,旭格不仅仅是人类对暴力非理性的渴望以及血腥的恶的化身,也不完全是制造生命中混沌涡旋的恶魔,其本身就是混沌的象征。麦卡锡把混沌理论的意象与混沌理论的内容,融入旭格复杂而又哲理的话语中,并以此来讨论命运、随机与确定论,不仅突出了旭格本人作为混沌涡旋的特性,同时也因混沌理论对麦氏小说《老无所依》的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塑造的介入,使得小说有了混沌叙事的动态特征。
三、混沌、分叉点与三体问题
数三在麦卡锡的小说中,不仅有分形的混沌内涵与空间塑形,而且还体现了我们生活的宇宙混沌无处不在的神秘性。有趣的是,在他的小说《骏马》中,数三与宇宙中的“三体”问题发生了关联,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麦卡锡小说的混沌学思维的内涵。《骏马》的情节安排与《穿越》与《老无所依》极为相似,也是三分结构,分别是格雷迪(John Grady Cole)骑马进入墨西哥高地、墨西哥牧场的生活与牢狱困境以及格雷迪最后回到家乡德州。除了结构的“三分”法,小说的主要人物总是呈现三人一组的形式,而这样的搭档出现在格雷迪旅行的每一阶段,使得格雷迪的生活多了混沌感。
豪金斯(Harriet Hawkins)认为,“科学中的三体问题与无处不在的三角形同源,而这个三角形可以解决文学中类似的问题”[4]157。他曾用科学中的三体问题分析莎士比亚戏剧中常见的人物之间的三角结构。在他看来,讨论三体问题,有助于解释戏剧中的三角结构为何使得戏剧的发展有种不可预测性,即使奥赛罗(Othello)和苔丝狄梦娜(Desdemona)之间存在矛盾,但他们的矛盾却很容易解决,只是因为伊阿古(Iago)的卷入,才会使得问题愈加复杂起来。[4]156就《骏马》来说,小说人物的三体问题不亚于莎剧的复杂,尤其是格雷迪的荒野旅行,本身已经充满了混沌性,既可预测也不可预测,而随着第三方介入他的人生旅行,便有了其动力系统的分叉点,使得他的生活系统愈加复杂,甚至混乱起来。
首先是布莱文思(Blevins)这个来路不明的神秘人物加入了格雷迪与朋友罗林斯(Rawlins)的荒野旅行,小说人物首次有了三人一组的形式,恰好构成了混沌系统中的第一个分叉点。可以说,在他出现之前,格雷迪与罗林斯的墨西哥旅行一切顺利,偶尔还会有荒野冒险的快感,但布莱文思的加入却使一切都陷入了混沌,不仅朋友情谊起了变化,甚至改写了格雷迪美墨边境旅行的人生轨迹。在罗林斯看来,布莱文思谜一样的出身和他来路不明的马匹,以及小小年纪却携带枪支,这一切将会带给他们灾难。两个朋友就是否带上布莱文思起了争执。而布莱文思盗马后开枪杀了墨西哥狱警,使得格雷迪与罗林斯遭到牵连而锒铛入狱,最终分道扬镳。罗林斯提前返回德州,而格雷迪则重返墨西哥。重返墨西哥可谓彻底改变了格雷迪的人生轨迹,使他的生活陷入了另一轮的无序。因布莱文思的牵连,格雷迪失去了恋人父亲及其女傅的信任,永远失去了他实现包括稳定的家庭、牧场生活以及浪漫的爱情等人生所有梦想的可能性。试图为布莱文思复仇,格雷迪独自越过边境回到墨西哥,他在绑架狱警上尉时,腿上多了一道伤疤。这次创伤彻底改变了格雷迪的人生观。小说末尾,格雷迪找到罗林斯,送还他丢失的马匹,两个好友对家乡的看法已然不同。圣安吉罗(San Angelo)在罗林斯看来依然是个好地方,即使当不了牛仔,他也可到油田上谋份差事。但在格雷迪眼里,“这儿已经不是[他]的家乡......[他]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他]也不清楚这块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10]199。这片有着古老边疆神话传统的土地,曾经鼓励他拓疆冒险,来实现他的美国梦。然而,一切无非只是“图画上的骏马”而已,他不得不继续在荒野上流浪,甚至将永远只能走在路上。总之,格雷迪荒野旅行后所遭受到的一系列失去,都与布莱文思这个第三方进入他的生活系统有关,最终使得他的人生旅程成为缺乏稳定性的涡旋。
一般来说,系统通常在经过分叉点后,有序与混沌的变化愈加复杂,这时的系统不但难以稳定下来,甚至趋向混沌的变化速度也会呈指数地增长加快。除了布莱文思,女傅阿尔芳莎(Duena Alfonsa)也是三人一组人物中的“第三体”,尽管此时的人物关系从朋友变成了爱人。因为阿尔芳莎的介入,格雷迪的生命系统便多了个分叉点,使得他的运动轨迹从短暂的有序再次跌入混沌的涡旋中。墨西哥的普利希玛牧场(La Purisima)就如格雷迪艰辛旅程之后的伊甸园,四天之内能为一大群马匹配种,甚至可以不休息连续工作,格雷迪卓越的工作能力为他博得了庄园主与女傅的欣赏,重新获得了期望良久的牛仔工作。不仅如此,爱情也在向他招手。此时的格雷迪甚至幻想过要在这个远离美国的墨西哥庄园里生活“一百年”,可以说,在墨西哥牧场格雷迪有了一段短暂的自由安静的牛仔生活。麦卡锡的迭代语言技巧,如“他喜欢骑马。说实话,他喜欢被人看到在骑马。说实话,他喜欢她看到他在骑马”[10]199,突出了格雷迪重获牛仔身份和甜蜜爱情后的欣喜。幸福总是短暂的,墨西哥庄园不是“一个刚刚得到牛仔身份的年轻人的天堂所在,而是异国他乡”[11]127。由于与雅丽杭德拉(Alejandra)的恋爱,格雷迪再次陷入了人生的涡旋中。
格雷迪因爱情而跌入的人生涡旋,不仅因为恋人之间的国别和文化不同,或是因为格雷迪失去了恋人的父亲和女傅的信任,真正的原因还是恋人之间阶级、地位与身份的差异而使他再次失去爱情。格雷迪尽管是个美国人,但他的牛仔身份不过是牧场中最为普通的一个工人罢了。如果追溯他的家族史,至多是德州西部早期的拓荒者。在美国人的意识里,牛仔常被浪漫化。实际上,他们远非自给自足独立的个体,而是依靠他人的“工资-奴隶,要靠艰辛的劳动才可勉强生存,他们经常受控于较大的牧场主,而就连这样的依附地位也并不是常有”[12]154。他们“经常挣得很少,吃得很差,”而他们的地位“只是比那些流浪者稍高一些,不得不游走在各个牧场之间寻找工作,时常是把一个牧场的菜牛赶到铁路边运走后,才可换取一些咸肉、豆子,一个月仅仅挣到40美元”[13]575。与格雷迪相比,雅丽杭德拉却出身高贵,其门第延续了好几代,甚至可以追溯到墨西哥历史上的皇族。恋人之间的地位悬殊,从他们见面时的坐骑,即可一窥端倪。雅丽杭德拉骑的是一匹纯种阿拉伯马,美丽、高贵、速度极快,而格雷迪骑的是一匹新配过种的赛马,不过是在牧场里出力劳作的普通杂种马。表面上看,二人恋爱的失败好像是为了家族的清誉而交易的结果,女傅答应帮雅丽杭德拉从狱中救出格雷迪,而雅丽杭德拉承诺从此两人永不相见。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实际上,个人生活系统中多个变量的相互关系与变化,才是这场恋爱失败的真正原因。
混沌理论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由有序与无序组成,二者的交替变化取决于对初始条件敏感性的依赖。与雅丽杭德拉的恋爱,原本可以让格雷迪实现他所有期冀边疆冒险而完成的人生梦想。然而,现实却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如埃利斯(Jay Ellis)所说,格雷迪“对雅丽杭德拉的钟情,对于这个出身高贵且品性端庄的女人来说,有些降格”[14]212。事实如是,在墨西哥这个保守的父权制国家,“一个女子的名声就是她的全部”[10]136。在和格雷迪的谈话中,阿尔芳莎用了许多如弈棋与造币等有关偶然性和不确定的意象,无非是提醒格雷迪现实与梦想的差异。与布莱文思和阿尔芳莎一样,卷入格雷迪生活的雅丽杭德拉的确为他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灾难。这个美国亚当的“夏娃”,其人生的一段浪漫插曲,却彻底结束了格雷迪天堂般的墨西哥庄园牛仔生活,并因此构成了后者人生运动轨迹的又一个分叉点。失恋使得格雷迪再次遭受了生活中的失去,而这一次的失去不只是雅丽杭德拉的退却,而是以母亲化身的阿尔芳莎的介入和干涉为起因。不能在墨西哥重新赢得爱情,也使得格雷迪失去了重新获得牛仔身份并与马儿一起的牧场生活的机会。世间的事情,似乎总在循环轮回,之前因为格雷迪的母亲拒绝施以援手,格雷迪失去了祖上留下来牧场,远离了钟爱的骏马;前恋人凯瑟琳(Mary Catherine)的背叛,让他品尝了失恋的痛苦。生活中一次次失去的重复,为格雷迪的生活系统增添了混沌性。
对于麦卡锡来说,格雷迪的困境“就是稳态运动与有序突然被投进无序与涡旋的一个案例”[15]19,而这一切的产生皆缘于因果的不成比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相互联系,没有一种事物可以孤立存在或与其他事物绝然分开。此类观点在小说中多次迭代。先是罗林斯说,“这世界运行的方式......你根本不清楚它要往何处发展”[10]92;接着便是一位墨西哥人指出,“一个人出生在这个国家而非其他国度,绝不是偶然事件”[10]226;后来阿尔芳莎救格雷迪出狱时也提起,事物之间互为联系,“人的决定从来不会取决于一个茫然无知的因素,而恰巧受与此结果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决定的调控”[10]231。简言之,正是“三体问题”造成的分叉点,引起了系统中多种变量的变化,使得格雷迪的生活在有序与混沌中间漂泊动荡。
四、结语
作为呈现世界的一种方式,数的独特性,在于它在中西文化中特有的集体无意识的投射。相比其他数,数三的独特性,则因与当代混沌理论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和宇宙的多方同构,多了一重“混沌”的意义。作为当代科学与文化界的一种新的思维范式,混沌理论给了麦卡锡新的创作思维,在他的作品中,混沌理论的概念和原则时常被用来建构他的叙事王国。
从数三这个独特的视角入手,观照麦卡锡的西南部小说,我们发现,在麦卡锡的西南部小说中,数三不仅被用来实现小说叙事内容与叙事结构上宏观与微观的跨尺度的自相似,更是在其小说的叙事模式上,呼应了小说人物人生命运的混沌性。从某种程度上,小说的混沌学思维暗示了人类世界的偶然性与随机性、人生的荒诞与无意义,以及现实生活中“牛顿范式”的漏洞。总之,麦卡锡对数三的青睐,使他直接在他的西南部小说中,将数与世界的混沌性相关联,不仅丰富了数文化的当代内涵,而且使得他的小说有了混沌学的叙事思维,在当代美国文学中魅力独具,独树一帜。
[1] 叶舒宪,田大宪.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 布留尔. 原始思维[M].丁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Gleick, James.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7.
[4] Hawkins, Harriet. 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 Chaos Theory [M].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5.
[5] McCarthy, Cormac. The Crossing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6] 张小平.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论麦卡锡《穿越》中分形的空间构型 [J]. 国外文学,2014(4):119-127.
[7] McCarthy, Cormac. No Country for Old Men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8] Giles, James R. Viol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 An End to Violence [M].Columbia: Univ.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9] George, Sean M. The Phoenix Inverted: The Re-birth and Death of Masculi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rauma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D].Texas A. &M Univ.-Commerce, 2010. Ann Arbor: UMI, 2010. ATT 3405822.
[10] McCarthy, Cormac. All the Pretty Horses [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92.
[11] Cant, John. Cormac McCarthy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8.
[12] McGilchrist, Megan Riley. The Western Landscape in Cormac McCarthy and Wallace Stegner: Myths of the Frontier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13] Kollin, Susan. “Genre and the Geographies of Violence: Cormac McCarthy and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2.3 (Autumn 2001): 557-588.
[14] Ellis, Jay. No Place for Home: Spatial Constraint and Character Flight in the Novels of Cormac McCarthy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15] Slethaug, Gordon E. Beautiful Chaos: Chaos Theory and Metachaotics in Recent American Fiction [M]. Albany: State Univ. of New York Press, 2000.
TheNumeralandChaos:ACaseStudyoftheNumeralThreeinMcCarthy’sSouthwesternFiction
ZHANG Xiao-ping
(The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YangzhouUniversity,JiangsuYangzhou225127,China)
As one of the presenting modes, numerals have their own specific qualitie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signs, which c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literary studies. Due to its mysterious and sacred qualities and its multi-associations with contemporary chaos theory, the numeral three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writer, Cormac McCarthy. In his south-western novels, the numeral three appears frequently, which not only makes McCarthy’s fiction mysterious and chaotic with its association with numeral culture but also makes the fictio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with connotation and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chaos theory.
numerals; Cormac McCarthy; chaos; American novels; The Crossing; No Country for Old Ma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6.014
2017- 04- 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WW039)“科麦克·麦卡锡小说研究”;扬州大学(2014)“新世纪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培养项目
张小平(1971—),女,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小说研究。
I712.074
A
1672- 0598(2017)06- 0096- 07
责任编校:杨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