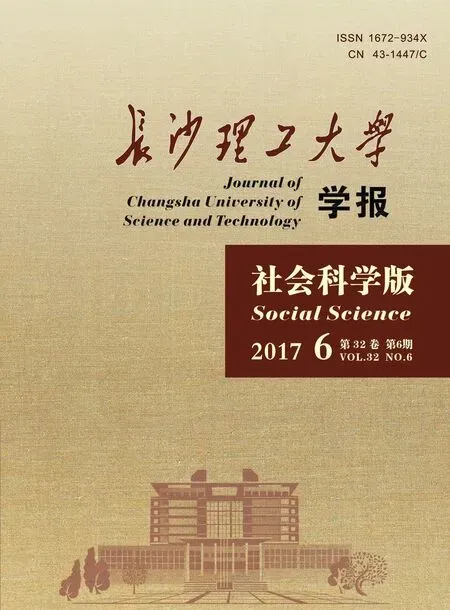孝的目的论思考
王金平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孝的目的论思考
王金平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5)
在目的论框架内,存在着对孝的两种类型的根本思考,一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思考,它以自爱为根本假设,依据其对行为者个体的超越,从低到高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互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一种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思考,它以爱为根本假设,认为爱的最高境界是仁及于万物,而孝乃其始基。就超越性而言,在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中所作的对孝的思考,无疑是在目的论框架中对孝所作的可能最高层次的思考。
孝;目的论;利益;自爱;爱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孝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也是一种基本的义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若要谈论孝,就必须要么在美德论的框架和义务论的框架内做选择。因为在规范伦理学中,除了美德论和义务论这两种基本的框架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框架,这就是目的论框架。而目的论框架常常被人忽视,导致一些人认为在目的论框架中思考孝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有失偏颇。
一、把孝纳入目的论框架内思考
亚里士多德说:“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是以某种善为目标。因为人们都有个美好的想法,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1]这就是说,人所思所做都有着一定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是哲学中一切目的论的根本出发点。即便是不把目的当成最高的道德范畴的道德理论,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一点。康德的“人是目的”的口号[2](P175),就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康德除了说“人是目的”以外,还谈论了三种价值。而在伦理学中,几乎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与目的联系在一起。虽然康德说道德是自足的,根本不考虑目的,但是,他是在谈论纯粹的人时那么说的。当谈论到具体的个人,即处在关系中的人时,他便不能不谈目的了。“人是目的”这一口号,便是康德在谈论如何对待包括自己在内的具体的人时提出的。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康德那里,“人是目的”这一口号是从属于绝对命令的[2](P175-185),离开了绝对命令来谈论“人是目的”,将是对康德最大的误解。
但是,在目的论框架中,目的的考虑却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注意,目的论框架的核心概念是善,因此,当我们在目的论框架中来谈论孝时,是把孝当作一种善来谈论的。
二、孝不是最高的善
百善孝为先,这意味着,在一个人所有的善行中,孝是居于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孝是最高的善。
其一,孝是行为者与其父母祖先之间的关系。孝既然是行为者与其父母祖先之间的关系,它就不可能是一种目的。因为目的总是行为者意在实现的目标。孝显然不是孝行的行为者要实现的目标,因为孝本身是行为者的一种行为,而任何行为都不可能是其自身的目标,否则这样的行为将是没有主体的,而没有主体的行为,只可能是一种纯粹自然的行为,与人的意志完全没有关系。孝可以说是自然的,但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自然,而是道德意义上的自然,即出于人的本性或不违背人的本性。而且,当我们认为孝是自然的行为时,我们已经预设了人性本善。在不预设人性本善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孝是自然的。但是,即便我们不预设人性本善,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孝,比如在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况及其弟子韩非那里。而且,我们谈论孝,多数是在人的意志基础上,而不是在人的本性这一基础上。因为不论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孝作为人的行为,都是有主体的,都是与行为者意志联系在一起的。
其二,孝作为行为者与其父母祖先之间的关系,主要不是指向行为者自身,而是指向行为者的祖先、父母。对于祖先,行为者的主要任务是安灵;对于父母,行为者的主要任务是敬养;对于行为者的后代,行为者的主要任务是抚育成人。可见,行为者行孝,追求的不是行为者自身的目的,因为孝行的主要指向者不是行为者自身,也不是行为者自身之内,而在行为者自身之外。但是,即便是祖先、父母和后代,这三者都不构成行为者孝行的目的,它们既不是孝行的直接目的,也不是行孝者的终极目的。因为行为者孝行的直接目的是父母祖先之所思所愿,祖先、父母和后代不过是父母祖先的所思所愿者之载体而已;而行为者的终极目的,是行为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和一切行为的归宿,这是远远超出孝行本身的。
其三,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最高的价值为仁义或道义,或者简单地说,是仁。依据《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P43-44)孝悌是仁之本,本立而道生。有孝行,成为孝子,只是道生,只是走向仁的道路的开始,而不是这条道路本身,更不是这条道路的归宿。因此,孝不是行为者的最高目的,而只是行为者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的开始,或者获得在社会中立足的基本资格。
显然,孝本身不是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在目的论的框架中来谈论孝。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在目的论的框架内谈论孝。
三、对孝以利为基础而作的目的论思考
当我们在目的论框架内谈论孝时,我们意在说明或探讨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行孝,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时常有人说,在利己主义的框架内不可能谈论孝。这样说,虽然不能说没道理,但可能有点过于绝对。正如在利己主义的框架内可以容纳助人的行为一样,在利己主义的框架内也可以容纳孝行。正如霍布斯以看到乞丐令人不快乐而向其施舍钱财使乞丐快乐时也令自己快乐来为自己辩护,认为向乞丐施钱合乎自己的利己主义[8](93-105);我们在中国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当有人以自己孝顺父母将来自己也会被自己的子女孝顺来劝人行孝时,该劝说者就是出于利己的考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弃老而不养,其根本的理由便是孝养父母于己大大不利,这也是典型的利己主义思考。韩非为了强调法的至上性,批评人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来考虑忠孝,认为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源。他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群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5](《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忠孝之本,在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奉亲,而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准,因为私利是乱之根源。
利己主义背后的基本假定是仁爱自己。倘若这一假定不成立,那么,利己主义也便难以成立了。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们设想,爱自己若成了唯我论,可能将适得其反,因为唯我论若贯彻到底,最终必将毁灭自己,而不是成全自己。要破除唯我论,就必须超出自我,便必然触及人情;而在人情中,最为宝贵的就是亲情,特别是亲子之情。爱自己之子女,是爱己的根本体现之一,这是生物界的基本法则之一;但是,爱自己的父母,却不是生物界的基本法则,传说中的“反哺”“跪乳”[3](P4),在生物界中实属稀有、例外。这意味着,在生物界,爱自己的父母,并不是爱自己的根本体现,因为在许多时候,爱自己的父母可能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就像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所显示的那样,爱自己的父母与爱自己的儿子在现实中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说,孝在许多时候是与自己的自爱情感相冲突的。因此,基于自爱,孝在生物界中是不可能被普遍化的。依据康德式的可普遍化原则,是不可能前后一贯地基于自爱原则或利己主义来谈论孝。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可普遍化原则,那么,即便存在着大量的反例,也不能否认,针对奉行自爱原则或利己主义的人,我们还是可以对其论孝,这种谈论可能没有普遍性,但是,却可能是有效的。我们虽然不能否认在利己主义这种目的论框架内谈论孝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要在利己主义这一目的论框架内谈论孝,是不可能以一贯之的,因为在这种想法的背后,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人是为己的。
利己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或标准,其中所涵盖的自己,可大可小。小到个体,大到家庭、民族乃至国家、种族、物种。但不论利己主义中所涵盖的自己是大是小,它都是偏狭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他者,除非他者皈依或皈顺,不再成为他者。显然,在利己主义这种目的论框架内,暗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暗含着非此即彼的思考。这样的对立性思维,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道德建设的。因为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6]那么,自我之外的他者,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就理所当然地将会成为消灭的对象。除此之外,若以孝为利己,那么,孝也就可能成为自己取利的工具之一,那么,孝将成为逐利之工具,一旦不能以此取得实际的利益,孝作为工具,被弃的命运也就不远了。显然,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对孝的极在讽刺。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3](P116)的时代,这样的例子出现得太多了。也许正是为了克服在利己主义这种目的论框架内谈论孝可能具有的偏狭性,有人从行孝并不指向其自身这一点出发,提出孝在根本上讲是利他的。这样谈论孝,是以利他来克服利己。的确,从孝行本身来说,利所加者,不是行为者,而是行为者之外的存在者,这确实可以说是利他。不过,这所利的他,是属于自己的那些他。利己主义的目的论框架所存在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论框架。
我们必须看到,在利他主义这里,依然存在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4](P119)(《论语·颜渊》),他的话就体现了这种对立。孔子的弟子宰我说“父母之丧,期可已矣”,意思是三年之丧太长,期年就够了。对于这样的言论,孔子与其弟子宰我有这样的对话:“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4](P163-164)(《论语·阳货第十七》)。孔子认为,宰我的话,明显是克己不够的表现。因为克己不够,所以在父母丧后一年就食稻衣锦而心安。
不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在利他主义那里采取了与在利己主义那里相反的形式。在利己主义那里,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路子;在利他主义这里,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是以他者为中心的路子。这两条路看似相反,实则形式相同,都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为依据,都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处理,都要求牺牲其中的一方。不过,就孝本身来说,利他主义比利己主义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孝中,行孝者是在付出而不是在获取,在实际利益上确实更直接是在利他,虽然在情感上是可能有直接地利己的成分。
那么,是否可能有一种目的论框架,孝既可被解释为利己的也可被解释为利他的呢?实际上,确实有这么一种目的论框架,它就是互利主义。在中国的孝道故事中,经常有“子欲养而亲不在”之语,说的就是敬养父母,实际上可能出于子女自己本能的情感要求,当然,这种情感要求的基础是报本或报恩心理[3](P3)。知恩图报,在人类社会中被公认是一种美德。有恩不能报,可能是人生一大缺憾。孔子对宰我的批评中,就含有宰我知父母恩而不尽力报的意味:“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4](P163-164)(《论语·阳货第十七》)。子生三年,方能免于父母之怀,因此,父母丧,子守丧三年,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是忘恩。
为了使自己人生不至于有太多的缺憾,于父母在世时尽量行孝,可能是最为恰当的行动。但是,孝显然不止于与父母的关系,它上及祖先,下及子孙。那么,互利主义这一框架是否也可适用于这两种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就与祖先关系而言,有献祭与荫庇的回馈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被认为是观念性的);就与子孙关系而言,有抚育与养老的回馈关系。因此,以互利主义来解释孝,相对于以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来解释孝,因为其涉及的关系更广更深,而相应地显示出其优越性,尤其是道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利益之相互依赖性。
但是,无论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还是互利主义,都不能摆脱宗派主义的嫌疑,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就是利益团体,而一般的利益团体总是有着趋于封闭的倾向,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以利益团体为社会基础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和互利主义这三种目的论框架,从根本上讲,都具一个根本的缺陷,即缺乏开放性。
为了克服缺乏开放性这一缺陷,目的论中出现了另外一种框架,这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最大优点,不在于其功利原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2](P112),而在于它是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来考虑问题的。在这一思路下,无论是得利者还是不得利者,只要是与行为的后果相关的,都被考虑在内。这样,如果我们把孝放在其中来考虑,那么,我们考虑的就不是行孝者得利还是孝行的指向者得利,抑或是行孝者与孝行的指向者都得利,而是孝行能够使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这样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实际上有许多人是在这个目的论框架内来思考孝的。其中最为典型的说法是孝使家庭和睦,万民敦厚,从而家和万事兴,乃至扩孝为忠,牺牲我一个,幸福亿万人。可以说,在功利主义这一目的论框架中谈论孝,孝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孝为万善之首,孝乃仁爱之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可以从功利主义这一框架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利他主义、互利主义与功利主义从根本上讲都像利己主义一样,是以自爱原则为根本假设的,因此,就像在利己主义原则下虽然不能普遍有效地谈论孝,但可以个案有效地谈论孝一样,在利他主义、互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下,同样不可能普遍有效地谈论孝但却可以个案有效地谈论孝。所以,它们也面临着在利己主义框架下谈论孝时所遇到的指控一样的指控。其中最深刻的指控,就是这样地谈论孝,是以自爱为根本的。而在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那里,自爱是人的病态,因而,以自爱为基础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着病理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批评者来自康德及康德主义者。
四、在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中对孝的思考
那么,在目的论框架中,有没有一种超越自爱的形式,使我们可以有效而且普遍地谈论孝呢?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目的论框架是存在的,它就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为代表,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以易经哲学所说的“宇宙大化,生生不已”为代表。由于孝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的地位特别重要而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地位很低,因此,我们对孝的谈论,是以中国伦理思想史为根本思考对象的。
依据中国易经哲学中所体现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框架,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生生”这一根本原则而进行的,都是在为这一原则服务。所谓“宇宙大化,生生不已”是也。这一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内容,典型地体现在《易传》的这三段话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7](P81)(《系辞上》)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7](P94)(《序卦》)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7](P79-80)(《文言》)
这三段话,第一段讲得理成位,第二段讲宇宙秩序,第三段讲圣人之行。其中心就是人法天,而子女效父母。孝的要求就蕴涵于其中。
在这一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框架中,“生生”便是终极目的,孝是服务于这一终极目的的一种根本手段。这种基本手段的核心就是效,即效法天地。当中国人说“天地是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人类效法自然,自然当繁衍自身,生养后代”[3](P2-5)是在效法天地时,这时孝的主要内容就是“生育”,其核心内容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3](P10)。中国人讲效法天地为孝,这时,我们讨论孝的框架,便自然地由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并进而过渡到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不过,自然主义的目的论,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一种变形,从根本上讲,不能说是非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如果我们把G·E·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2](P508-513)之所指,反过来想一想,就可知道,即便是考虑到“超自然”这一因素,“形而上学的”与“自然主义的”二词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同义的。
在目的论框架下谈论孝,经常受到这样一种批评,即它是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如此以来,在目的论框架下谈论孝,经常被认为是怀利以相接,会导致在可计算的利益不存在时无法谈论孝,而在可计算的利益存在时把孝作为一种计算的标的而导致孝成为相对的。显然,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在目的论框架下谈论孝,完全可以不以利益的计算为基础,因为形而上学的目的论之所以被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恰恰是因为它超越了器的层面,而在道的层面上来考虑问题。当然,我们效法天地,肯定是因为这样做在根本上是于我们有利的,但天地的那个“生生不息”的原则,却是不考虑于我们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一个小团体的人是否有利的,因为在许多时候,“生生不息”的原则恰恰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一个小团体的人是不利的,此时依据“生生不息”原则来行事,就意味着奉献自己或牺牲自己。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其基本原则不是自爱,而是一种超越自爱的爱,是大爱甚至可以说是爱本身。自爱有界,大爱无疆。效法天地的孝是无疆的;而基于自爱的孝是有疆的。也正因为这样,效法天地的孝是可以普遍化的,而基于自爱的孝是不可普遍化的。
五、结语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任何一种目的论框架中,我们都可以谈论孝。不过,在不同的目的论框架中谈论孝,我们会遇到由于那个目的论框架内所具有的缺陷所带来的种种质疑。因此,就逻辑严密的程度而言,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互利主义、功利主义、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就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顺着这个阶梯往上走,人们在其中谈论孝时所体现的超越程度越往上越高,越往下则越显得低俗。
因此,如果一定要在目的论框架内来普遍化地谈论孝,那么,用来谈论孝的那个目的论框架,要显得高雅而不低俗,就应当是不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目的论框架,因为以利益计算为基础来谈论孝,显得过于低俗而有失高雅;如果要显得高雅,就只能是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框架。在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目的论框架下,孝是从属于“生生”这一终极原则的,是作为中介或手段而存在的,它的根本原则是生命的延续,这是孝的最根本的内容。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
[2][美]汤姆·L·彼彻姆.哲学的伦理学[M].雷克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舒大刚.至德要道——儒家孝悌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4][宋]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国书店,1994.
[5][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3:465-466.
[6]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5:913.
[7]苏勇,点校.易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8][英]乔治·爱德华·摩尔.伦理学原理[M].长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3-105.
Teleological Thinking on Filial Piety
WANG Jin-ping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Changsha,Hunan 410015,China)
In teleological framework,there are two typical kinds of thinking about filial piety.One is based on interests,which takes self-love as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according to the transcendence above individual agents,,there exists from low to high egoism,altruism,reciprocal altruism and utilitarianism.The other is based on metaphysics,which takes love as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 and believes that the highest state of love is inputting benevolence into all things on earth,and filial piety is its starting point.In terms of transcendence,it is undoubtedly the highest to think about filial piety from metaphysical teleology among all think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eleology.
filial piety;teleology;interests;self-love;love
D032
A
1672-934X(2017)06-0149-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6.024
2017-10-19
王金平(1968-),女,湖南长沙人,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