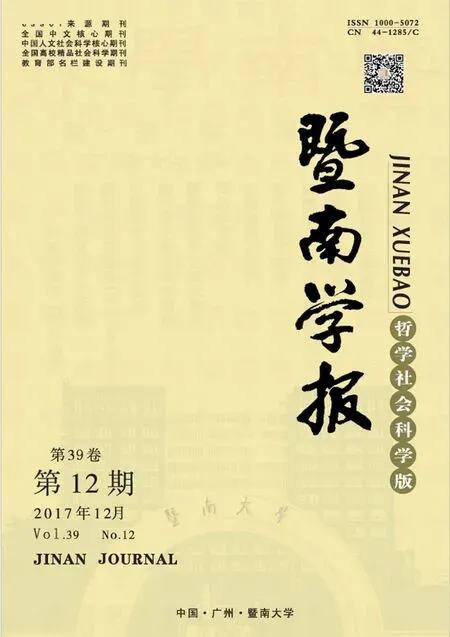空间建构与地方认同
——清初岭南三大家罗浮山书写研究
蒋艳萍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作为道教“第七洞天”和“百越群山之祖”、“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不啻为岭南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千百年来,在文学领域,罗浮山始终活跃在文人想象和诗词歌赋里,成为岭南著名的文学景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罗浮山的文学形象出于岭外文人的凭空想象,在诗文创作中被一步步强化为蓬莱仙岛之一股、道教之洞天福地,“仙山”逐渐凝定为罗浮山的固有文学形象。而这一过于神化的景观描写与真实的罗浮山却相差甚远。宋明之后,岭南本土文人的自我意识崛起,他们或隐于罗浮,或游于罗浮,或求学于罗浮,已经不能满足仅仅将罗浮山描写成遥不可及的仙山仙境,在他们的笔下,罗浮山变得可亲可近、可栖可憩。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的罗浮山书写为著,他们以其享誉全国的赫赫声名、带着遍布全国的游历视野返回并对自己的家乡罗浮山进行全方位书写,极大地丰富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的内蕴,凝就了其岭南文化的特有品格,推动了罗浮山文学景观由虚拟性向实体性的转型。通过对家乡山水的积极书写和地方认同,他们也自觉参与到对家乡文化的有意识建构与对外传播中。
一、方外之想与隐逸之思:罗浮山的固有空间建构
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在文学史上,关于岭南的文学书写较为晚近,岭南文人的自我书写就更加滞后,“岭南”在中原文化的强势观照下,成为莽荒之地、未开化之地。罗浮山却似乎是个例外,它很早即进入中原文化体系,在秦汉时期已有盛名。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考罗浮始游者安期生,始称之者陆贾、司马迁,始居者葛洪,始疏者袁宏,始赋者谢灵运。”自秦代安期生开山之后,罗浮山就成了四方术士梦寐以求的修仙之地。魏晋时期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葛洪辞官隐居于此,炼丹采药,建观授徒,著述不辍,自此之后,罗浮山名传渐远,历代不断有人上山建寺修观,而且香火十分旺盛,遂形成九寺十八观的宏大气势,使罗浮山成为古代道教圣地,被誉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名闻遐迩。历朝历代仰慕者、游山者、访道者绵延不绝,留下了大量歌咏罗浮山的诗词文赋。
仔细研读这些罗浮山诗词,我们会发现,宋代以前关于罗浮山的书写都是来自岭外文人的手笔,例如谢灵运、李白、杜甫、李贺、刘禹锡等著名文学家都有过对罗浮山的书写,但本土文人对罗浮山的文学书写却是缺失的,即便是出生岭南的唐代大诗人张九龄也没有留下关于罗浮山的具体描写。岭外文人通过自己的想象在文学中将罗浮山建构成一座神仙之山和隐逸之山,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和隐逸之思,这一文学形象犹如一个恒久的标签,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称道。
(一)神仙之山
据《广东新语》载:“蓬莱有三别岛,浮山其一也。太古时,浮山自东海浮来,与罗山合,崖巘皆为一……《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可见关于罗浮山的来源充满神话色彩,通过为其“正名”更显出其“出身不凡”。蓬莱在上古民间传说中便是“三神山”之一,在《山海经》与《列子》中是“海上神山”的形象,因此罗浮山的身份便天然地带有“神山”色彩。再加上魏晋以来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的影响,关于罗浮山流传下来的一系列道教神话传说,不断经过后人的口口相传、演绎以及文人墨客的反复书写,逐渐巩固、丰富其仙山道山形象。
晋朝谢灵运梦茅山而得道教《洞经》,上面记载罗浮山事,谓茅山与罗浮相通,“与梦中意合,遂感而作《罗浮山赋》”,赋中视罗浮为九大神仙洞府之一,是“朱明之阳宫,耀真之阴室,洞穴之宝衢,海灵之云术”,极言罗浮山作为仙山之奇谲与神秘,像隐于深夜的朗日,在幽境的映衬下更显光辉。在唐人诗作中,罗浮山也被认为上有不死之药,住着神仙之人,珍禽异兽、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如李德裕诗云:“龙伯钓鳌时,蓬莱一峰坼。飞来碧海畔,遂与三山隔。其下多长溪,潺湲淙乱石。知君分如此,赠逾荆山璧。”对罗浮山为蓬莱边山浮来充满好奇心。身不能去,心向往之,所以有诗人会梦到罗浮,如“罗浮多胜境,梦到固无因。知有长生药,谁为不死人。根虽盘地脉,势自倚天津。未便甘休去,须栖老此身”。也有诗人通过送友人归罗浮表达自己的向往之情,如李洞《赋得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山》:“旧山归隐浪摇青,绿鬓山童一帙经。诗(一作符)帖布帆猿鸟看,药煎金鼎鬼神听。洞深头上聆仙语(一作觉船过),船(一作楼)静鼻中闻海腥。此处先生应不住,吾君南望漫劳形。”可见唐人多对罗浮充满想象,但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实际上并未亲临,只不过在其罗浮诗词中表达企羡之情。
宋代很多官员被贬岭南,罗浮山成为很多贬官必游之地。但是仙山的描写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如杨万里已到罗浮山脚,但其诗中仍看不到具体的实景描写,他在《罗浮山》一诗中说:“罗浮元不是罗浮,自是道家古蓬丘。弱水只知断舟楫,葛仙夜偷来惠州。罗浮山高七万丈,下视日月地上流。黄金为桥接银汉,翠琳作阙横琼楼。不知何人汗脚迹,触忤清虚涴寒碧。天遣山鬼绝凡客,化金为铁琼为石。至今石楼人莫登,铁桥不见空有名。玉匙金龠牢锁扃,但见山高水冷冷。我欲骑麟翳鸾凤,月为环佩星为从。前驱子晋后安期,飞上峰头斸丹汞。”罗浮山在杨万里眼里仍是充满神奇色彩的道教仙山。经过历代累积,文学中的罗浮山被不断神化,罗浮在他们笔下犹如蓬莱、瀛洲,不是地理方位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座山,而是一个有特殊意味的符号,是神仙洞府的代名词,充满神奇瑰丽的方外之美,“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生活经验的浇灌,地方也会累积出某些特殊的文化资产。”至此,“文化利用地理使特定空间被赋予特定意义”。罗浮山早已脱离简单的地理属性,在地名的背后,蕴含了极深远的仙山文化的特殊意蕴。
(二)隐逸之山
仙山往往伴随着人们的隐逸之思。在文人的想象中,罗浮山钟灵毓秀,奇峰峻秀,也是适合避世隐逸的世外桃源。慕名题写罗浮的历代文人,有不少表达欲隐罗浮的夙愿。例如李白、杜甫没有亲历罗浮,但都对罗浮之隐充满仰慕之情,李白直言“余欲罗浮隐”(《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其一》)、“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此去或未返”(《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杜甫在国家危难之际,明知“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但自己无法力挽颓势,只好学“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南为祝融客,勉强亲杖屦。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咏怀二首其二》),他们都将罗浮山视为远离世外烦扰、求仙访道的绝好去处。

岭外文人由于对岭南风物的陌生感,从不同于本土的视野出发,留下了许多对岭南的新奇记忆与审美观照,给身处其间的岭南人带来发现自己和重新审视家乡美的契机,为后人留下难得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也可发现,岭外文人对罗浮山的书写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违和感,要么仙异化,要么陌生化,缺乏一种地方意识的认同与建构,与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罗浮山相差甚远。
二、罗浮仙山的岭南化:岭南三大家的本土认同
作为一处虚拟性和实体性俱存的文学景观,罗浮山更多地将自然美与不断积淀叠加的文化内涵紧密结合,以厚重的人文感呈现出来。随着本土文人的崛起,他们赋予了罗浮山特殊的乡土怀想和家园情怀,经由本土作家润色打造的罗浮山重新走向全国视野,由以往的虚构的遥不可及的仙境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岭南地标。这种本土文人对罗浮山想象的有意识建构在南宋时期初现端倪,古成之、崔与之、余靖、留正、李昴英等一批岭南士子的参与使罗浮山文学形象有了新的色彩,有了一定的家园感和地方感。而真正展开对罗浮山全方位的书写是在明清时期,其中尤以清初岭南三大家为著。“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地方暗示的是一种‘家’的存在,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与重大的成就积累与沉淀,且能够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仙山的岭南化恰反映出以岭南三大家为首的岭南士子对自己家园的认同和对岭南地方感的建构。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朱明王朝倾覆,许多汉族文人沦为晚明遗民。屈大均、梁佩兰、陈恭尹也不例外,他们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又同为岭南人,因此经常饮酒唱和,相互欣赏,相互慰藉,共同抒发家国情怀。罗浮山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园意象经常出现在了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据粗略统计,他们的诗词中提到罗浮山的达四百多篇。他们笔下的罗浮山虽然也延续了历代文化累积所形成的固有的仙山和隐逸之山的意象,但是也逐渐剥离了岭外士子赋予的附加意义,显得轻灵可爱、清丽动人,以岭南山水特有的风韵情趣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自是罗浮人”的身份认同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均是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屈为广东番禺人,陈为广东顺德人,梁为广东南海人。三人都曾游历各地,有着开阔心境与写作视野,表现出相似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被后人誉为“岭南三大家”。屈大均人生经历复杂,不仅参与反清复明抗争,而且曾削发出家以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他以化缘为名游历四海,北上东游,履及多处。陈恭尹作为明末清初广东抗清斗争的发起人之一,曾往返于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联系抗清的各地义军,还曾赴云南欲投奔永历帝。梁佩兰不同于屈、陈,热心仕途,科考多年,因才气出众声名远扬于名公巨卿、达官贵族之间,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留京写诗为乐,士大夫争相延请品题吟哦。
当一个人身处异乡时,身份的归属变得尤为重要。身处异乡或宦居在外的游子更容易通过对家园的回望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表达对家乡的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地方认同“即个人或社群以地方为媒介实现对自身的定义,并在情感上认为自己是属于地方的一分子”。在岭南三大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三人通过标注家乡地方表达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其中最为中原文化熟知的岭南名山——罗浮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的首选。例如屈大均早年号为“罗浮道人”,陈恭尹自号“罗浮布衣”,这种以罗浮明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自己绝世隐居之志,符合罗浮隐逸之山的固有情怀,另一方面以家乡标榜自己身份也恰恰彰显了岭南士子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除此之外,还有多处诗表达自己作为罗浮人的身份归属,如屈大均“以予罗浮人,白鹇同飞骞”(《赠别甘处士返豫章》)、“我本罗浮五色鸟,化为仙人出炎峤”(《题王山使独鹤亭》)、“我从罗浮万里来,逢君文采一徘徊”(《客山阴赠二祁子》);陈恭尹“城头江汉一千里,座上罗浮两个人”(《庚子元旦毛子霞招同何不偕登黄鹤楼》);梁佩兰“罗浮仙山人所晓,罗浮与我情不少”、“我家南海波涛住,罗浮隔断扶桑村”(《望罗浮》)等,字里行间渗透着“我从罗浮来”、“我是罗浮人”的对自己故土身份的认同感。
身处异乡,羁旅之思也通过罗浮来舒展。屈大均写道:“雁门无数雁,一夜尽南飞。我忆罗浮暖,难将雨雪违。”(《闻雁》)大雁南飞,飞往游子的故乡,也把游子的思念带回罗浮,而北地的寒冷更加剧了对温暖家乡的怀想。“影落千山远,声来九塞愁。频年羁客梦,曾否到罗浮。”(《寄李烟客黄逢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罗浮作为故乡的意象缠绵在诗人的梦里徘徊不去,反复加深了这种思念之情。在游览其他地方的山水名胜时,望着眼前缥缈朦胧的景象,诗人又忆起罗浮的四百三十二峰:“平生五岳游,今上谢公楼。楼里多山水,空濛云气流。故乡在南海,夫子有罗浮。置我丹青上,芙蓉四百秋。”(《呈周栎园·其一》)游五岳、登高楼,望着相似的景色,仿佛眼前皆是故乡的影子,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可见一斑。
陈恭尹对罗浮也有着独特深沉的情感。他多次写到罗浮酒酿:“难醒易醉罗浮酒,叶润花酣赵尉楼”(《中秋后一日黄积庵招同吴山带罗仲牧梁芳济何楚奇王也夔集见堂雨中即事同限秋字二首·其一》)、“琼苏南岳闻常设,仙桂罗浮酿不无” (《次屈翁山韵寿王君佐》)、“使君正醉罗浮酒,不免樽前忆故乡” (《风乾萍果惠州王子千使君席上作二首·其二》),耽于醉酒似乎有醉生梦死之感,但饮的是家乡酒也失为解思乡之愁的方式。更何况在颠沛流离中对罗浮的思念更是充满伤情,如:“罗浮风暖鹧鸪啼,山下梅花客未迷。十里娇歌传玉笛,一竿残月泊沙堤。生存华屋人何处,营垒清秋马独嘶。扶醉西州他日路,潘郎怀旧岂堪题。” (《西樵旅怀五首·其一》) 全诗前半段追忆罗浮气候温和、浪漫舒适的场景,与当下凄凉的人生情境相较,照出了坎坷艰辛的前途末路,正如其序言之:“戚日苦多,浮生如寄。西山东尽,风雨昏昏,追昔伤兹,凄然有作。”在后来陈恭尹的许多赠别诗中,诗人送别友人去往罗浮,或是寄诗给居住罗浮的友人,忧愁之中不仅有思念友人和离别之不舍,更夹杂着自己归乡无期的失落与惆怅。“寰中花鸟正春新,四百罗浮日日春。送子不堪临水别,昔年曾是住山人。”(《送何左王入罗浮兼答留别之作》)“经岁旌旗驻菊坡,罗浮秋色近如何。”(《寄戴念庭三尊时署增城》)“罗浮山高人所钦,罗浮水清君子心。罗浮之外君何有,归对罗浮尽日吟。”(《罗浮山水图歌为陈岱清司李》)这些诗歌情绪含蓄蕴藉,委婉平淡,在揣摩与玩味之余才能感受到作者浓浓的乡愁。
经久在外漂泊,归隐罗浮更为他们的最大心愿。如屈大均言:“戎马时方急,罗浮我欲还。相思蓬海隔,流泪损朱颜。”(《怀悬公》)“我将终罗浮,服食惟朱草。”(《古诗为叶金吾寿》)“浮丘已作谢公墩,复把罗浮当漆园。”(《前制府吴公以生日往罗浮山赋此寄寿·其一》)“太华虽言好,未若归罗浮。”(《冲虚观》)“我愧疏慵应早退,罗浮归养采芳兰。”(《留别建陵孟太守·其一》)“愿作罗浮大蝴蝶,与君朝朝食花叶。愿作罗浮五色禽,与君暮暮宿花林。”(《陈丈种花歌》)这些可以说是反复咏志,表明向往自然疏淡无忧的田园生活的心迹。陈恭尹有“仙遗衣化罗浮蝶,蝶化山蚕复作衣。栩栩未离庄叟梦,丝丝还上玉人机”(《李苍水司训长乐以罗浮蝶茧数双及茧布见寄云布即蝶茧所成翌蝶出茧中五色纷翍玩对之间因成一律寄谢其意》),通过描写罗浮蝶回环往复形态的转换营造诗人对坐忘、忘机的境界的迷恋。“只为平生志未灰,罗浮家近是蓬莱。曾窥抱朴书千首,易得安期枣一枚。峰顶三更时见日,村前十月早开梅。期君共隐谁宾主,浊酒相欢不厌陪。”(《春感十二首》之八)自己的家乡就在蓬莱仙境的旁边,这种地理优势使自己也充满归隐求仙的愿想。梁佩兰也写到“骑驴一踏蓟门春,便拟抽身作隐人。将上罗浮峰四百,黍珠庵畔结山邻。”(《答佟声远次原韵》)“服药寻仙自可求,罗浮门户是浮丘。”(《题赠》)。关于归隐罗浮的志趣,在三位诗人的作品中呈现出相似性。“易代世变之于遗民,既是国的悲剧也是家的灾难。同时也肇始了遗民的漂泊人生。较之物质意义上的‘家’毁于战火,文化生存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的丧失——精神漂泊于灵魂流浪,才真正为遗民的心头之痛。”比较而言,岭南之地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较晚受到战火的荼毒,也是南明政权得以维系的基地,故而罗浮山水成为岭南三大家在山河破碎之际抚慰受伤之心的最好良药就不足为奇了。从我是罗浮人,到归隐罗浮、终老罗浮,表现出诗人们对生命轮回的认可,以及对生于兹、死于兹的归根情怀。
(二)仙山的岭南化
罗浮山作为蓬莱左股的传说由来已久,这是历代描写罗浮的文学家都了如指掌的典故,也是最常见于三家罗浮作品的题材。作家来到传闻中的仙境,必然要赞其神奇,咏其玄妙。关于罗浮的神话传说遍布三家罗浮诗词,四百三十二峰、罗浮日出、罗浮梅、罗浮蝶、罗浮雀等成为其中常见意象。如屈大均有多首咏罗浮梅花蝴蝶的诗歌:“何来蝴蝶车轮大,知是罗浮小凤凰。”(《题张璩子罗浮山下书舍》)“罗浮梅花天下闻,千树万树如白云。开时花似玉杯大,枝枝受命罗浮君。”(《罗浮探梅歌为臧喟亭作》)诗中的梅、蝶等意象经过比喻、夸张的处理均化为“仙物”,更突显其神奇色彩。梁佩兰善于用大开大合的笔法将神话传说与他的奇特想象和恣意夸张以及罗浮神秘的风物景象结合在一起,使罗浮仙山的意象更为鲜明。在长篇古体诗《望罗浮》中他写道:“鬼神琢划良有以,风雷交会非等闲。我家南海波涛住,罗浮隔断扶桑村。白马随潮簇雾来,飞禽决眦迷烟去……倒落金银台,挂起珊瑚殿。鱼龙跳峰头,蝴蝶飞水面……神仙于此山,故意作诡谲。使人双眼望,望亦不可测……”无论是状美禽、白云、飞雪,乃至描写罗浮整体景象,梁佩兰都采用纵横捭阖的笔法,上溯至上古“祝融司南溟,耀真挺灵岳。丽离判元始,妃合封浑噩”(《罗浮》)、“大化岂有本,我生幸同时。先天与后天,相望一间之”(《将至罗浮望四百峰作》),在时间轴上呈现出巨大跨越,展现罗浮山作为自然景观的历史性;又有“谁知蓬莱山,今晨于此见。割来自左股,飞出向西面”(《初入罗浮登华首台,宿尘公精舍》)、“四百青芙蓉,初日破烟晓。我身无羽翼,一日焉能了”(《望瑶石台云母大小石楼》),拓展了诗学地理空间,磅礴之气油然而生。诗人不断在诗歌中拓宽时间长度、空间宽度,使罗浮山这一仙山形象脱离了时空维度的限制,呈现出缥缈、广阔、无限的意蕴。
三位诗人一方面沉浸在罗浮仙境的超现实想象中,另一方面真实的居山、游山体验又促使他们不断地将罗浮山由虚拟的仙境转化为现实的乐园,生发出强烈的地方感。“地方感”的形成,须经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积累过程;经由意象、观念及符号等等意义的给予;经由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以及个体或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及关怀的建立,才有可能使空间转型为地方。也就是说,地方感的建立不是仅仅通过书本的知识体系,或者前人文献累积而来的文化认同,还应该经由人的居住、经常性的涉入、“真实”感官经验的持续刺激,才能使虚拟性的空间变成实在的“地方”。正如郑毓瑜所说:“如果人身与外物相交接的经验被考虑进来,景物所在的空间背景也因为这交接经验的环绕,而成就具有切身意义的‘地方感’,不再只是仿如参考文献的史地知识而已。”岭南三大家把自己真实的居山体验写入文学作品中,看到了罗浮山不同的四时风景,各种风物都尽显其妙,日、月、星、云、雾、雪、梅、松、瀑、峰、花、蝶带着岭南特有的韵味扑面而来,一改罗浮仙境描写的富丽华瞻,给人们清丽脱俗、秀媚可亲之感,一如岭南现实的山水。这些感受都是长久浸润于罗浮山才可能有的。
屈大均写有《罗浮杂咏》四首、《望罗浮》、《罗浮曲》各两首、《咏罗浮》八首,《送人入罗浮》四首,或是赞其风景秀美,或是赞其水瀑、流云、林木花草、日出等等。 如“空外日氤氲,茫茫四百君。雨将双岳合,晴以一泉分。石柱支青壁,香炉吐白云。穿林深浅去,惊起碧鸡群。”“峰路时时断,翻嫌瀑布多。水浮苍树去,山逐白云过。饷客惟朱草,牵人是绿萝。踟蹰石梁畔,心奈欲归何。”(《罗浮杂咏》)生动地再现了罗浮山多峰多瀑,物种丰饶,四季常青的自然风光。“罗浮四月春泉决,流出千溪万溪雪”(《绿绮琴歌》)、“弱柳垂烟重,夭桃破雪新……罗浮多笋蕨,采采及青春”(《壬子春日弄雏轩作》其一),写出了罗浮春天的清丽可爱;“本是罗浮岫,南来逐海潮”(《罗浮》)、“登山若浮海,舟航即轻策。浮山复浮去,与罗万里隔”(《登罗浮绝顶奉同蒋王二大夫作》),写出了罗浮与海相邻的特点,也暗合浮山“浮海而来”的典故;“可怜罗浮山,离合亦有时。天雨罗浮合,天晴罗浮离” (《罗浮曲其一》),写出了罗浮乍离乍合之态,将罗浮的美丽传说与现实晴雨气候变化融合在一起,既体现浪漫之遐思,又表达游观之雅兴,体现出虚实结合、相映成趣之美。
屈大均还记载了一次罗浮冬天的气候异常:“峤南自古无大雪,况复罗浮火洞穴。山人不识冰与霜,白露少凝阴道绝。今年季冬太苦寒,雪花三尺如玉盘。麻姑玉女尽头白,四百缟素失峰峦。天气忽将南作北,层冰峨峨路四塞。浮碇岗头似白山,罗阳溪口成勑勒。千株万株松欲催,梅花冻死无一开。北风惨吹笼蔥裂,猿狖僵卧吟且哀。辟寒有方得仙客,斫取龙鳞薪琥珀。地炉烧出日轮红,天井迸来云箭白。咫尺空濛接海津,光摇宫阙失金银。玉作越王烽火树,瑶华飞满珊瑚身。天鸡夜半冻不叫,曜灵忍失朱明照。久伤鸟羽坠重光,安得烛龙衔一爝。欲挽羲车力士无,穷阴苦逼岁华徂。麑裘不暖难消夜,坐拥瑶琴影太弧。”(《罗浮对雪歌》)岭南一向气候温暖,屈大均在塞外的时候最怀念的就是罗浮的暖和,“我忆罗浮暖,难将雨雪违”。可是这一年岭南却遭受了极寒气候,天气苦寒一下子似乎使南方变成了北方,到处冰封雪冻,耐寒的梅被冻得开不了花,猿狖被冻得僵卧哀鸣,甚至夜半的天鸡也被冻住了,不再叫醒浮海而来的一轮红日。但是这少有的大雪却也给罗浮山带来一种别样的美,大如玉盘的雪花、皑皑白雪覆盖的四百三十峰、傲雪挺立的松梅等,都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岭南特有的物产也常常入诗,如陈恭尹诗“采砚每逢蕉叶白,买舟频系荔支红”(《赠别潘稼堂简讨二首·其二》)、“田收晚稻余秋色,寺入溪桥隔竹声”(《九月晦日同连双河湛天沐慧容上人二儿士皆自增城将登罗浮中路宿资福寺》)、“罗浮风暖鹧鸪啼,山下梅花客未迷”(《西樵旅怀五首·其一》)、“明年荔熟醉何处,为报君家酿老春”(《登合江楼饮王使君南区宝坻酒次坡公韵》); 屈大均诗“罗浮蝙蝠红,双宿芭蕉叶”(《定情曲·其七》)、“山人遗我荔枝瘿,得自罗浮第三岭”(《箪友篇》)、“南枝稀越鸟,余尔鹧鸪群”(《郑方二君以生鹧鸪数双见贻赋诗答之》)、“应看木棉发,莫听鹧鸪啼”(《别天生·其二》)、“冬有芙蓉亦有桃,绝喜岭南霜雪少”(《陈丈种花歌》)等,涉及的芭蕉、荔枝、木棉、芙蓉、冬桃、早梅、晚稻、鹧鸪等都是南方特有的物种,大量岭南风物入诗,无疑使仙山充满了扑面而来的人间气息。这种以现实的空间诠释罗浮山的方式,经由听觉、视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经验的描绘而建构起罗浮的地方感,使罗浮山文学形象不再仅仅是带上隐喻性质的罗浮仙山,其意蕴更加丰富,更显多元。
可以说,仙山的岭南化和地方化,不是坐井观天的自吹自擂,不是“子不嫌母丑”的敝帚自珍,罗浮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可企及的空想之地,而是现实可触的充满幸福遐想的人间福地,对其不再是刻意的神异化,而是来自对本土家园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游历多方后对“我的家乡就是仙境”的自豪与自信,是在比较大千世界之后对家园的更高层次的肯定。
综上所述,正如新人文主义地理学者Allan Pred所说:“地方(place)不仅仅是一个客体。它是某个主体的客体。它被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岭南三大家书写罗浮山具有强烈的地方意识和丰富的地缘色彩。罗浮山因为有了著名文学流派的集体书写,文学形象更加丰富,岭南三大家多次践屡,游历大小景点,对罗浮山水反复吟咏,这些游观作品的加入,使罗浮山作为宏大抽象的文学景观的同时又有了许多细部、具体文学景观的支撑,使罗浮山文学想象呈现出虚实结合、浪漫情怀与现实游观结合的双重特点。本土诗人充满地方特色和满怀家园情感的细节书写使得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罗浮山进行观照。这种去陌生化的书写,回复到其本来面目,改变了岭外文人对岭南的他者化的异物书写,去除了岭南山水风物的人为的莽荒色彩,在文化心理的意义上建构起岭南文化自我认同的自觉与自信。故乡情结的寄寓使罗浮山作为具有公共意义的符号,从“域外仙山”形象转化为岭南“乡愁”的代表,在文学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