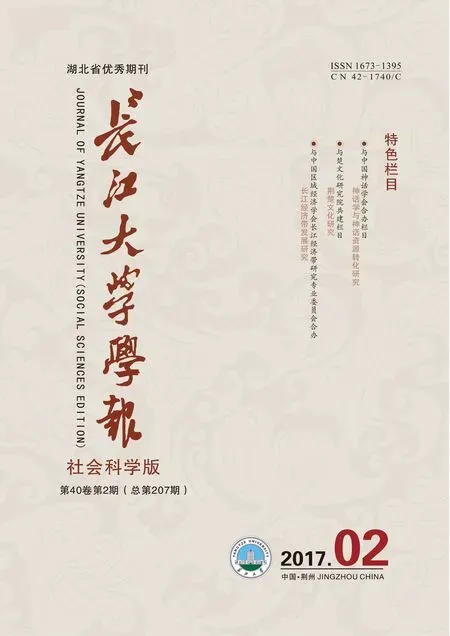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盛开莉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书写
盛开莉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群体,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面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婚姻的精神围困,一面以出走的方式逃离。作者赋予这些女性以丰富的生命质地,改变了父权制话语下沉默的传统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对于女性的自我发现与生存拓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施叔青小说;围困;出走;艺术结构
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施叔青的姐姐施淑,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施叔青的创作特点:“飞短流长成了艺术结构的特质。”[1](P2)毫无疑问,“飞短流长”指的是施叔青小说有着和张爱玲小说一样的世俗化题材。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为内囿沉默的,遭受凌辱压抑和毁灭的女性。施叔青笔下的女人们,虽与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们一样拘囿于家庭之中,但其命运和选择却有了新的可能。因此,揭示父权制家庭中女性受压抑受迫害被奴役的现实,并试图探寻女性的出路,就成为施叔青小说的重要主题。
一
“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妇女的命运。直到今天,情形仍旧一样,多数女子不是结了婚,便是结过婚,或准备结婚,或因未结婚而忧郁。”[2](P199)用西蒙·波娃的这句箴言来解释大多数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命运,是极为贴切的。从张爱玲、苏青到施叔青,虽经历了岁月穿梭,世事变幻,女性的故事却万变不离其宗。施叔青继承了女作家特有的立场,以寓言的语义化途径,言说家中的天使被围困的生存真相。被剥夺自由的婚姻或是情感状态,及其所带来的无力感和绝望虚无感,是施叔青小说里女性群体共通的生存状态和感受。
施叔青小说对恩格斯有关父权家庭的理论总结——父权家庭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中,做出了形象的阐释。对这一本质的认识,是女性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当女作家从两性关系入手,以颠覆父系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时,其写作也就成为一种文本策略,具有了政治意义。在小说中,女作家以两性关系为逻辑起点,袒露了房中的安琪儿的实际命运。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女性是守护家庭的天使;而这听上去美妙无比的称谓,同时也成为遮蔽女性生存真相,模糊家庭权力关系的掩护。事实上,在温馨的面具背后,家庭或许会呈现出一副压抑囚禁女性身心的狰狞面孔。《困》中的丈夫像狱卒一样冷漠,完全忽视了叶洽的情感需要,使叶洽成为一个对生命感到绝望的女人,最后在酗酒中,失去了对生活的感觉。《蓦然回首》中的范秀美,像插翅难逃的蝇蝶,受困于无边的黑暗里,看不到一丝可以逃遁的希望。在美国的她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逃回台湾父亲的家;但父亲的家不仅没有成为她避难的港湾,反而将她拼命往外推搡。无家可归的范秀美只好求助于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的冷漠与怀疑,却逼得她想要发狂。在丈夫的家和父亲的家,以及心理医生所代表的社会合力构筑的森严壁垒下,绝望的范秀美走向了疯狂。在这些作品中,家庭完全成为男性囚禁女性的场所,丈夫则成为迫害妻子的主谋,而疯狂则是最仁慈的家庭中女性心灵空虚、精神萎缩的结果。《完美的丈夫》中的李素如同被判了终身监禁的囚徒,始终受困于婚姻的高墙里。《后街》中的朱勤是在大公司里打拼的独立白领,年逾30而未嫁,在遇到萧后,也同样被困于后街。朱勤虽然没有步入婚姻,但因为萧对其身份的不予承认,她永远也走不出后街。《寻》中的杜伊芳仅仅因为无法生育,就被丈夫打入冷宫,在无边无际的冷漠里,如同死刑犯一般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与张爱玲不同的是,施叔青小说里的部分女性人物打开了牢狱的大门,尝试着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如果说,张爱玲作品呈现了女性的深层人格特征即内囿的话,那么,施叔青笔下的女性,则通过对不自由的反抗,以及对牢狱的逃离,呈现出与张爱玲笔下女性群体不同的特征,即对内囿的反抗。出走或者逃离,是施叔青中期小说中女性所普遍选择的生存方式。《愫细怨》中的愫细,在发现丈夫有外遇后,不纠葛,不哭天抢地,而是坦然面对,主动选择了离异,化身为精明强干的职场白领。《窑变》中的方月与姚芒的相识,缘于她对丈夫和婚姻的无望,而这本身就是对婚姻的逃离。随后,当发现姚芒依然不能予她精神慰藉时,她再次选择了出走,逃离了姚芒那个像博物馆一样的家。《票房》中的丁奎芳为了自己的艺术事业,放弃了丈夫和孩子,从大陆出走到香港。《困》中的叶洽,在发现丈夫无论怎样都和自己是精神上的陌路人之后,选择以酗酒的方式而获得精神上的逃离。《常满姨的一日》中的常满姨,发现丈夫是个赌徒加嫖客之后,以出走的方式,从台湾乡下来到美国。这样一个下层女佣,在以往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往往难以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施叔青却站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以叙述表层的若无其事,对其表达了令人动容的深层关怀。
二
女性出走,意味着走向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与出走相伴的,则是女性精神内质的变化。因此,女性生命质地的丰富性,也成为作者在小说里所呈现的重要内容。在父权制文化模式的监禁下,女性长期内囿于家庭之中,被放逐在文化和知性的边缘,沉默和贫乏是女性一直以来的标签。“女性的沉默贫乏是女性心灵遭受压抑的焦虑性表达。”[3](P4)女性长期被置于与男性代表的文明理性相对立的一面,被看作非理性、肉体和自然的代表。在男性文学作品中,长期以来,有知识的女性常常是令人厌恶的老学究、老处女。施叔青则通过一系列台湾留学生婚姻小说和香港故事系列小说,以男性的沉默贫乏,反衬出女性的精神优越,呈现了女性丰富的心灵世界。
《愫细怨》中的愫细,是施叔青有意翻转张爱玲作品中沉默贫乏的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留学美国的教育背景,使愫细以平等的精神价值,赢得了美国人狄克的爱情。与狄克离异后,她变身为德国公司独当一面的设计主管。从婚姻里出局后,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女性通常会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可是在愫细身上,离异所带来的失败感不仅全无痕迹,而且她还将这次生活的变故当作一次重生:“对新的自己凝视片刻……愫细恢复了她对自己的信心。”[4](P217)依凭职场复归,愫细快速地重获了对自我的认知与肯定。面对广东乡下来香港打拼的小老板洪俊兴,愫细有着十足的优越感。她故意邀请洪俊兴到她家里。发现书架上全是英文书后,“他抬起头,和愫细挑战的目光接触,赶忙掉开去,讪讪的,脸都涨红了。愫细有着目的得逞后的快乐”[4](P223)。愫细“讥笑他没有逻辑观念,缺乏学院训练所说的话,永远愚蠢可笑。凭着愫细起伏的情绪,洪俊兴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从美妙的情人降至粗蠢的小老板”[4](P236)。愫细的教育背景、独立的职业女性身份、富于智慧的谈吐、有品位的生活,使得洪俊兴只能暂时凭借物质来换取一点自信。洪俊兴一厢情愿地以为,凭借物质,可以缩小他和愫细之间的距离;但最后,他还是在太过直白的物质换取中,被愫细彻底击败。而这一次,是因为愫细感觉到,洪俊兴用物质威胁到了自己始终保有的精神优越感,故而她猛然抽身而退,捍卫了自己高傲的尊严,主动让一场风花雪月戛然而止。传统女性的苍白贫乏,在愫细身上无迹可寻。愫细时时彰显出强悍的个性,充沛的精神,丰富细腻的感情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洪俊兴的自卑、粗俗、乏味、谨小慎微。施叔青用女性话语,消解了父权制话语机制下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物质,灵魂/肉体,社会/家庭。在父权制意识形态话语中,代表人类文明的男性,占据着社会公共领域,诸如政治、权力、军事、科技等等;而女性则代表着相对低级的自然、肉体,隶属于家庭领域。如此一来,在精神力量上,男性势必高于女性,诸如沉默顺从、无欲无求、精神贫乏,这些在男性身上可能被看作缺陷的品质,则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女性的基本特征。但在《愫细怨》中,在与洪俊兴的交往中,愫细不仅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且在精神层面上始终高于洪俊兴。由此可见,女人的精神优越感,已成为该作品的叙事主线。而其小说《困》,也传递出同样的意味。在小说中,叶洽的丈夫王溪山“是个极普通的人,有一颗极普通的心灵”[4](P121)。在作者的刻意强调和着力表现下,王溪山的普通,进而演化成无可救药的乏味和平庸。比如,两人在恋爱阶段时的约会,谈话内容乏善可陈,大半个晚上,统共没讲几句话。静默中的约会,尚可理解为此时无声胜有声;但当王溪山告诉倚在他肩头的叶洽,他一个晚上都在数松山机场降落的飞机有多少架时,却令人忍俊不禁。不仅如此,王溪山的住所也单调得索然无味,“客厅就像王溪山的人一样,给人一种极贫乏的感觉,毫无情趣可言”[4](P122)。在精神上,王溪山无法与叶洽有任何共鸣相通之处。“你一直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王溪山在小说结尾处的悲鸣,让人不自觉地想起了张爱玲笔下沉默贫乏的代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只是在施叔青的笔下,这一角色变成了男性。
曾有学者指出,在文学作品中,男性的魅力通常源于力量。这种力量既包括他对女性的征服和吸引力,也包括用武力统治世界,“而不是源于他自身某种丰富的、极富生命力的东西”[5](P234)。在优胜劣汰的商业社会里,男性的魅力常常源于他所占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至于生命的丰富质地、精神层面的富有,则常常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而退居其次。施叔青却在小说里有意展现这一层面:男性如果精神贫瘠,即便富可敌国,也无法让女人真正折服。同时,作者又将作品中男性所缺失的丰富的生命质地,慷慨地赠予了女性。《窑变》中的方月,是个很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她眼里,阔绰的丈夫除了钱一无所有,富有的追求者就是只会用名牌包俘获女人的猎艳高手。女性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对精神自由的渴望,使得她哪怕放弃男性给予的物质庇护,也要构筑自我精神家园——重新写作。与小说里占有大量财富却精神贫乏的男性相比,女性呈现出高人一等的精神力量。施淑认为,施叔青的作品“精力旺盛,血肉丰满”,“这种在质地上的丰富、生命力,是可圈可点的”。[1](P2)这种质地上的丰富和生命力,无疑来自于她笔下的女性群体;而这种生命力的真正源泉,或许来自于她们对父权制意识形态下性别秩序的大胆僭越。《一夜游》里的雷贝嘉本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却始终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斗胆向殖民地文化官员发起了攻势。她有着强悍的主动进攻的精神,不甘心听凭命运摆布的举止,却全无传统女性柔顺被动的一面。《情探》中的殷玫,虽然过着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的生活,但她有品位的装扮,撑门面的作家头衔,精明算计的手段,所有这一切,都很难让人把她与那些沉默贫乏,只会肉体交易的传统意义上的风尘女子相提并论。这些女性形象,如果以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秩序来衡量的话,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因为她们对传统性别制度所规定的女性气质,如沉默、贞洁、柔顺、牺牲等,常常并不认同,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她们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有了一种由被动变主动的气势和从容。这些女性形象,对于质疑父权制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女性气质,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女性冲破不公正的性别秩序所带来的压制,走向全面的个体解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三
女性主义批评家早就指出,女性有别于男性的人生经验,势必会影响到其对世界的认知及其思维模式;而女作家有异于男作家的思维模式,则直接影响到了其文本的艺术结构。自古以来,建功立业,开疆辟土,天然地成为男性的理想,故男性易于形成注重开拓与扩张的思维模式。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学线性情节观,即属于吻合男性思维模式的文本结构观。线性情节观强调时间的连贯与情节的推进,注重结果与答案。女性长期生活于狭小的庭院之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势必会影响到女性的思维方式,继而对女作家的文本结构产生影响。施叔青的小说结构,就呈现为有别于线性情节观的独特格局。“施叔青的小说在形式上越来越走向一种分歧的结构。她的小说,在过完了青年期的梦魇阶段后,经常是由一个可能的关注或激情的中心散文性地分歧出来。在这种叙述结构下,意念的发展或答案不是小说的重点。它的重点在热热闹闹的分歧本身,在它们之间的戏剧关系,以及与之呈现的问题,而这形成了她的小说在内容上的故事性的丰富和风格的多样性。”[6](P2)情节的线性进展的确不是施叔青所喜好的,她甚至很少给小说以答案。男性小说的核心情节观,是不断探索新事物、新目标。在这一意义上,停滞是最大的败笔。因“女性的思维过程更具关联性,倾向于在相互的关系中考虑问题,在道德判断方面更多地注入感情”[7](P28),所以施叔青的小说结尾多趋向于开放式,或者在某一个点上突然停止。
施淑曾从女性主义及精神分析角度,探讨过施叔青作品中的禁锢与颠覆意识。她认为,施叔青作品中“浓烈矫情的象征,漫无节制的臆想,没有出路的情节布局”,可以理解为“女作家对理性的、流丽的父权大叙述的质疑抗颉”。[8](P276)施叔青善于描绘庞大的人物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尤其擅长场景横断面式的铺排。横断面意味着切断了时间的绵延与流动序列,使时间停滞在一个点上,因而在形式上走向热闹的分歧本身。比如《票房》,从开头到结尾,其场景都是上海票友联谊会,就线性情节而言,几无进展。小说四节犹如四幕戏,以从北京流落至香港的刀马旦丁葵芳的期待开始,到她的最后被愚弄作结,展现了香港社会人们的势利。小说从丁葵芳出发到另一个人物,再从那个人物回到丁葵芳,然后再以丁葵芳为基点,如蜘蛛织网般来回循环。作家着力刻画了每一个出场人物的特征,准确而丰富,俨然舞台指示。
“建立在女性的经验和视野之上,施叔青的小说艺术不免于带上被女性一向的社会角色所决定了的手工的性质。这个与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有着较直接和亲密关系的艺术劳动,一方面使作品像日记一样隐秘地、热切地追逐着个人的生活;一方面产生了絮聒的,然而独断的全知叙写观点。”[6](P1)施叔青的小说艺术带有女性社会角色所决定了的手工的性质,这显然不是施淑的一己之见。其小说中将女性日常生活细节美学化的琐碎描述,如时常不厌其烦地赘述沙发、餐桌、窗帘等室内陈设布置、服饰妆容等的搭配,以及意趣盎然地穿插的作者的审美趣味,使小说带有浓厚绵密的叙述特征;而其所展现出的女性独特的生活经验,则无疑强化了其文本特色。
[1]施叔青.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回来——《夹缝之间》自序[M].香港:香江出版社,1986.
[2](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美)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M].陈晓兰,杨剑峰,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4]施叔青.愫细怨[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施淑.颠倒的世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7]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8]施叔青.施叔青集[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The Female Writing in Shi Shuqing’s Novels
ShengKaiI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Lanzhou730030)
The female group in Shi Shuqing’s works presen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group in Eileen Chang’s Novels:one side is under the spirit of the family and the marriage,and the way of "leaving".At the same time,the author gives women a rich texture of life,a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women in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creation of Shi Shuqing’s novels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women’s self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Shi Shuqing’s novels;siege;flee;artistic structure
2016-12-10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YB019);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31920150139)
盛开莉(1980-),女,甘肃武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I207.42
A
1673-1395 (2017)02-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