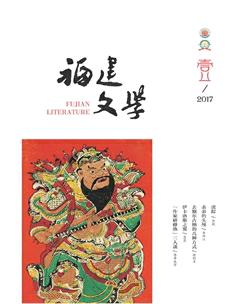秘境
张久升
一个人的行走
与草木为伍,我是天地间行走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君王。
向每一条河流致敬,它们优美的身姿,抚慰着每一个漂泊的灵魂。
向每一座山峦瞻望,它们伟岸的身躯,让徘徊的游子找到方向。
那纷飞的落叶,是水中鱼,游弋着投向母亲的怀抱。
路,一条别在城市半腰之上的路,一条通向不知名山村的路。你可以驱车而行,抵达目的地而返;也可以一伙人当作踏青秋游,还可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可以在漫山的夜色里看城市的灯火阑珊,握住温存的流光;也可以在丽日里借着路的延伸和高度,俯察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像洞悉和回忆一个渐行渐远的自己。
此刻,我一个人走在这样的路上。漫无目的又使命暗付。没有生命的到来是冲着目的而来,但每一个生命的走向莫不是最后都完成了它的使命。彰显如伟人,推动影响着历史的车轮;命如草芥,自生自灭,芸芸众生贩夫走卒多是如此,但也完成了生之为人的过程。路在脚下延伸,漫走也许可以与记忆暗合,也许可以发现新的自己。
距离,产生美,而向上的距离,却让人油然而生审察的意味,仿佛上帝之眼借你俯视众生。这种体验我在台北101大厦的高层临窗而望车流如蝼蚁时猛然袭来;在飞机直上千米万米高空,城池田野在我的视野里急遽地缩小,千朵万朵的祥云在机窗外涌起时,我也有这种失重和超重感。
想必上帝是孤独的。不是唯我独尊,却是唯我独醒。
鸳 鸯 之 死
秘境有秘密之意,但既为秘密,必是终有人所知。大自然如此坦荡,向来无秘密可言,只是人有限的觉知尚未发现。所谓的秘境,可以说是为一个人、一些人所知,却不为大众知道。
但在这个无限互联的时代,在这个许多人都愿意分享或炫晒的时代,秘境几乎在劫难逃。
远古时期,丛林是秘境,海洋是秘境,太空更是极其神秘的。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探秘的历史。那时,更多的是为生存去掠取食物,去扩张地盘。但现在,人们更多地或者是为了躲避一种人气,去自然界寻求人烟稀少之景、之趣。
鸳鸯是恩爱之鸟,又极喜清幽。家乡有鸳鸯溪景区,早年据说那里是鸳鸯南方过冬的福地。鸳鸯们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恩爱成了人们的向往,人们必须借它们的选择而选择。借爱侣圣地之名,那里很快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地。这样的秘境一旦被公开,人们可以去秀恩爱,但鸳鸯们便难再了。
前不久微信上有朋友得意地晒出了所发现的邻县另一处鸳鸯秘地。长焦头拍出了恩爱之鸟悠游的画面,高山深涧,秀水静谧,又确乎人间秘地。图片一出,点赞追问线路者众。心想,此一秘境亡矣,为那些寻寻觅觅而终难逃人类的追慕的鸟儿们叫苦。偌大的天地世界,鸟儿不知道享不享有隐私权?它们无从抗辩,唯有离开。离开,或者,改变心性,同流合污。
微信的事向来是一窝蜂的,不多久,此文图匿迹。不知道,那些鸳鸯们怎样,我是自始至终都不敢去过问。生怕,一关注,都会走向事物的反面。
古 村 逃 亡
走一些古村。它们藏在深山之中,有密林遮掩,由山涧滋养。岁月爬在墙头、屋瓦,静得没有一丝火气。它们世外桃源般的气质常常会一下子攫住外来者的目光,也仿佛可以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停泊。除了村子的古老与安宁可贵之外,一种不为众知的发现秘境的快乐是内心里另一种满足,如遇见一个期待已久的知己。
但这样很快会陷入两难境地,无论于村子,还是于自己的心灵。于村子来说,这样单纯地保存着的世外桃源一经外人涉足便成为不可能,这陶公的笔下早有预言。其实在他的笔墨下,自魏晋以来,桃花源也只是文人士子的一个精神乌托邦。现实更多的是,老去的村子往往陷入人去楼空的境地,或者是一个一个的老人,与村子同呼吸共命运着。老人离去,村子死亡。也许,终成为永远的秘境。作为一个村庄,它的生命在于成长、延续,那么外来的冲击、嫁娶、同化将是它成长的不可避免的步伐。随着脚步的杂沓,秘境终将不再。于内心来说,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些人发现的快乐而让村子在古老里故步自封,是不是有点自私与残忍?而如若人们终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询问来处和安顿去处的村庄,是不是另一种悲哀?
当我发出这样的疑问后不免自审自嘲,杞人忧天。村庄可以老去,代有新人。而生命之新,在孩童眼里,世界就是一个秘境。
香格里拉之梦
这仿佛是我多年的梦境。
四野靜寂无声。大山、湖泊、花、草,树木,各安其所,它们在熹微的晨光中不愿醒来。空气中有清冷的风在轻轻地拂过,野地里自然的清香蔓延开来。丢开从车上带来的氧气瓶,仰面深深地吸了一口,又一口,像是清冽的泉水激活了沙滩上的小鱼,又仿佛是爱情突然降临到一个失恋者的心上,整个的我通体透亮,活了过来。
四野迷茫,梦乡的纱帐还在低垂。她们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仿佛触手可及,却无法真正走过其里。隔着雾气蒸腾的水泊,你看到了几缕剪影,似姑娘曼妙的身姿和如泻的长发,呵气如兰啊,你想去帮她们搂一搂,却只是在栈道上静静地看着,看她们给你一个纤尘不染的微笑。这时候,你纵有千万种惊呼在心头激荡着,却压抑着不敢轻易言语,生怕惊扰了那倏忽又翩翩的梦境,只是旋目四望,想抓取那瞬间即逝的光景。是的,一切都在转瞬即逝之间,这是天地之间的一个大梦,趁着凌晨曦光的指引,我们闯进天地之梦工场来了。
寂静无声,可你仿佛听到了壮丽的大乐章。你胸内纵有万千言语,如潮情感,却只能扼紧喉咙,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形容这样的瑰丽与纯净,再汹涌的情感也无法衬得起这样的壮阔和清美……
这是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关于香格里拉,最初我完全是受着它美丽名字的诱惑而把它作为此次云南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曾经的丽江已被商业化扰攘得无插足之地,异邦的大理已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之后,我对这个最早的认知是印在酒瓶标签上的香格里拉藏秘已不再有期待。直到缺氧得难受,直到圣境把我从昏晦的边缘带入这个梦境,我想放任我的灵魂去游走。
其实,说这话时,我脚下走的是栈道,我乘坐着铁皮轮船和旅游电车,我身旁也有着一拨又一拨的各色人群……但在这里,除了相距近十公里的出入两端,没有高楼,没有商铺,没有游商,目之所及,只有湖光,只有山色,只有云天,没有人类自以为是的建设。树枯了就枯了,在水中慢慢倒下也是一种美。草长了,马羊来了给它们挠痒痒;它们低到土里去了,马羊撒下的粪便仿佛是回报,又是下季约定的信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还有云杉、高山松、松鼠、黑颈鹤、苔藓……它们是这里的主人,我,我们只不过偶然路过了它们的梦境。
我相信,这是我走过的人间最后的净土。回来好一段日子,记忆被荧屏上无数各地的美图所覆盖,存留的只是那种感觉。像做了一场梦,终于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许,天地之间,什么也不必留下,如梦一场,最是干净。
存一方天地
有一友人,嗓音条件不错,中气也很足,老大不小了,突然想起学唱歌。大约想想半辈子奉献给工作之外,也无甚深癖,誓把唱歌当作后半生的事业。不求登台亮相,但求自娱自乐。但歌唱是一项“不甘寂寞”的事,若不发出为声,声而不大,纵腹内千回百转,气贯天门,也是徒劳的事。不能扰四邻,不宜广场闹,那么就择秘地吧。
城内要寻一能让人发单调的“咪咪嘛嘛”音之地殊非容易。郊区野外又有交通不便。好在小城三面环山,稍稍远离人居的山垭口,道路尚可通达而人迹罕至,他便可纵情放声。早先时附近有老农在地里,闻之愕然,疑其精神有问题。友人友好相笑,老农多闻乃明白其故,复农作,间而拄锄闻视,相乐之。月有余,友人声腔畅通,老农闻之若润耳。相见欢。
一日,兴之所至,我们随友人到其所说的好地方。背离高楼、人群、车流,见山川、草木、田垄。时暮春三月,新绿展枝,虫蛙萌动,羽雀欢腾。未曾歌之,天地之间早已是荡漾着春之圆舞曲。友人展喉,初而微婉,继而放声,山鸣谷应,群鸟飞掠,薄枝款款,自然之美荡于胸,而我的身心早已融进了這方天地。
此方秘境,大约是友人于歌唱之外的最大收获。
念及自己,与文字为乐。一书一本或一键一屏即可。最怕有外人左右移动走之晃眼扰心。那年,在办公室工作,常人来人往,间或同事谈笑之声,难以安静做事。电脑装于简陋的打印室,可于我却是一个安心做事之所。当理完公务杂事之余,抬眼窗外,一方不大不小的天空让人可以穿越现实与周遭,思绪和情怀反而在文字里驰骋飞翔。斗室囿困,又何尝不是一个自我的秘境?
这么说,秘境是可以让心安泊的地方。
可以是自然的馈赠,可以是两个人的共享,可以是众人的狂欢,更可以是一个人的独行,一个倾听自己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