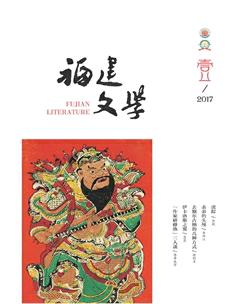小朝颜
刘梅花
村支书“咣咣咣”叩门,院子里没有声气儿。
门口的白杨树叶子像日子般稠密,树枝上一群麻雀突然厮打起来,激烈地叽喳着,揪头拔毛,聒噪得很。乡里的麻雀,野蛮剽悍。我凑在庄门缝隙里瞅瞅,一头老乏牛有气无力地走过来,也把眼睛凑到门跟前瞧,“呼哧呼哧”喘息,倒是唬得人一跳。村支书大笑,他晃动着庄门钌铞,三推两搡,一阵细碎的磕碰之后,门开了。
我像个窥视者,贸然闯入陌生人的家里,心里忐忑不安。不过,村支书说,屋子里肯定有人——病人瘫在炕上哩。院子真个儿大,寂然无声,一地白剌剌的日头。南墙边有个不大的园子,鸟啼花香,蔬菜也有几行。
老吴哩?老吴哩?村支书在院子当中大声吆喝屋子主人,还是没有应承。他的声音回荡在院落里,暗暗有些尘土飞扬的粗犷。倒是那头乏牛,趁机拿头顶开庄门一路小跑逃走了,亏得老腿老蹄子还跑那么疾。村支书撵出去追牛去了。出门就是庄稼地,老牛最喜欢啃嫩草。树上的麻雀又厮打起来,声嘶力竭地激烈。眨眼,又齐扑扑飞走,大概到旷野里厮打去了。
这户人家房子倒是多,也气派,拔廊,落地窗。装了玻璃的门半开半掩,花布门帘挑起来,高高悬在门楣。窗台上晒着一溜儿艾草捻子,一种苍凉的绿,令人感到丝丝清淡的愁绪。廊下还晒着几筐子锯末,白惨惨的,仿佛晒了几百年,不知道今夕是何年的那种恍惚。
门槛一隅,一只蜂窝煤炉子上正炖着砂罐子,“咕咚咕咚”,草药的味道远远飘过来,像一枝分出无数插枝的酸刺树,大剌剌地横冲直撞。
这时,有个老人从南墙的浓荫下悄然出现,飘出来的一样。一身黑乎乎的衣裳,眼睛却分外红,像两盏小灯盏。他的脸瘦长瘦长,比马的脸还要长一截。真是奇怪,世上竟然有这么狭长的脸。
几只鸡突然从他身后跑过来——腿那么短,却跑得旋风一样,什么鸡啊?鸡儿一路狂奔,跑到院子中间的破瓦罐里饮水去了。它们低头啄一会儿,高高扬起脖子,簌簌抖着,把嘴里的水珠抖下去。水喝到一半,它们又齐声“咕咕咕”叫着,撒开脚丫子冲到屋子里去了——天知道它们的小脑袋里想什么。
有个苍老吃力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谁放开了鸡儿?该死的!滚开!然后听见隐约的扑打声,大概是鸡儿飞到炕上扰民去了。紧接着,一只鞋子从屋子里飞出来,挨了打的鸡儿也飞扑出来。然后呢,它们又返回去,继续纠缠不休。屋子里传来扑打声和咒骂声,鸡儿们固执地从门口吐出来又吸进去。
我觉得惊诧,正打算和蹒跚独行的老人打个招呼,村支书撵牛回来了。他吆喝一声问,咋哩老吴?电话也不接,庄门也不开,偷着吃肉哩?
黑衣裳的老人挺古怪的,说话也不利索,也不看人,走路那样慢,似乎每走一步都要把脚印深深烙在地上。他一边撮着嘴唇啁啁地唤鸡儿,撒了一把秕麦子,一边含糊地说,添草去了,牛饿了一早上。鸡儿们在走廊里留下几摊子鸡粪,一窝蜂撅着尾巴跑到院子里争抢秕麦子。屋檐下的鸽子咕噜咕噜念经,瞅见秕麦子,树叶一样飘落下来,优雅地走过去,挤进鸡群里,脖子一伸一缩。这时候,屋子里传来硬拽拽的声音问:谁来了?包村的干部吗?村支书大声回答说,不是,一个采访的,报纸上写文章的。屋里头顿然没了声气,寂静下来。
古怪的老头儿这才从鸡群里收回目光,举起枯瘦的鸡爪子一样的手,遮在额前,挡着亮烈的阳光,细细打量了一番。半晌,他看着我,忖度着说,穷不瞒人,病也不瞒人。家里的瘫在炕上两年了,动弹不了,全身都是褥疮,看不成。少了药,万万不行。家里若是短了什么,只能赊欠着过,到处是层层摞摞的账债。你在报纸上给写写,有啥帮扶款,先考虑下我们哈……
我有些愧疚。一个写文字的人,只是喜欢那份儿知黑守白的从容而已,能力之弱,根本不是他期盼的那样,实在帮不了他的苦闷与担忧。很多时候,我自己都煮字疗饥,捉襟见肘,哪里帮得了别人。若是说文字的用处,唯一的,不过是取悦自己的心灵罢了。
但是,在这个陌生的村庄里,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怯弱无用来。我只适合在大野里,穿了长裙散漫地走动,作为风景的点缀。我所追逐的幽静清寂,只合适我,与别人是无用的。别人巴巴地坐在那里等钱使,而我还在迂腐地谈论诗歌。
村支书打断老人的絮叨,皱眉说,工地下月就开工了,到时候叫你儿子去砌墙,工钱比别人高些——不要总等着救助,自己也好歹动弹着巴挣些。
老人的红眼睛里透出哀怜的光来。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声音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回响着,犹如画里的声音。那头老牛也跟着哞哞了几声,声音刺破寂然,不像在現实里,倒像是在一种迷糊混沌的状态里。
也许,女子也该回来了。老人喃喃自语,一丝清涎水挂在几根灰白的胡子上,眼睛分外的红,一种低黯苍然的红。眼角斜上去——这种吊梢眼总是给人一种奸诈的感觉。可是一个衰老的乡村老人,又能奸诈到哪里去呢?
这时,屋子里的病人突然高声呵斥起来,似乎是炕上铺着的锯末都尿湿了,还没换成干燥的,艾叶也没点燃熏熏屋子,苍蝇又那么多。然后又责骂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疼她,又诅咒该死的病折磨着她,想死不得死。又责骂钱都花光了,出的多进的少……她的语气硬而冷,一句一句从屋子里往外砸。
村庄也是个空荡荡的村庄,路上几乎没什么闲人。院子外面的寂静与院子里的寂寥,一脉应承。那位瘫在炕上的老人,两年不肯下炕,两年不曾看到园子里的花朵,只是不断地和闯进屋子里的鸡儿较劲,细数几声牛哞罢了。在偌大的寂然中,她的白发日渐稀少,生命也会日渐稀疏。
庄门外有人叩门,老人照旧无动于衷,捉了一只公鸡剪秃翅膀梢子,怕它飞出院墙。那人晃开了钌铞,推门而入,大声问着,老吴哩?你家女儿捎回来的东西——害得我少拉了一个客人,短了几块钱。
哦,她捎什么回来了?如果下次见到她,捎个话,叫她回来一趟。家里该洗的东西都没人洗……
真是的,你不会打电话告诉她?洗洗东西,也要从县城里喊女子回来——你自己难道没有长手着呀,又不是腿短腰塌,连个衣裳都不能洗。
来人扔下个纸箱子唠叨一番走了,庄门外响起小客车发动的声音,有些刺耳,有些笨重,大概是个破车子了。老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眼窝更加红了。这当儿,村支书接了几个电话,他确实忙。他说,这样,作家,你和老吴慢慢聊聊,写什么尽管写,我先去忙,等会儿来接你。
他帮着把纸箱子抱到廊下,扔在木凳子上噔噔噔走了。屋子里的病人显然听明白了,扯着声音问,女子捎回来什么东西?快些给我看看。
老人弯下腰,撕开胶带,扒拉着箱子里的东西,神情漠然。他不断地揉着红眼窝,擦着迎风流出的眼泪,回头悄悄儿说,女子在酒店端盘子,一个月两千过些——她都三十五岁了,死活不嫁人。若是嫁了人,人手倒是多些。
他家屋后的槐树非常茂密,树枝子探过来,几乎伸到廊檐下了。风一吹,树叶子稠密地翻动,一俯一仰,发出“簌簌啦啦”的声音来。麻雀们又聚集在槐树上,叽叽喳喳聒噪得不行。老人拾起一根劈柴,可力气扔到树枝上,粗声呵斥驱赶着:“呕——呕——”
屋子里病人也在大声催促着,急切地想知道捎来的东西。老人索性抱起纸箱子,进屋子给看去了。边走嘴里边絮叨说,也不肯到院子里晒晒,日头这样的好——我便是背,也能把你背出来。
我不下炕,不晒太阳,也不见生人——我是经不起风吹的,受不得一点日头。
屋子里的窗帘也是常年遮着的,病人怕光。她直着嗓子呱呱叫喊,底气倒是足。她大概是梗着脖子的,连额头的青筋都会暴起来。可是,常年躲在幽暗的世界里,连生人也不愿意见,只感叹疾病缠身的人,或许是懦弱的。她的内心,一定梗着一块冰碴,一触就疼。日出日落,时光移动,她是怎么感受到的?别人都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可是在她屋子里,终日黑沉沉的,怕是漫长而遥迢的吧?
我不敢跟进去。老人也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早先路上等村支书摩托车的时候,遇见拾牛粪的那位老婆婆告诉我说,这家病人瘫痪之前,是个极刚烈的人。本来也不会瘫掉,但是她和儿媳妇吵架,没吵赢,气急了,想着喝一口水接着吵。结果火气太大,用力过猛,把一口水吸到鼻腔里,吸进肺里。呛水之后剧烈地咳嗽,挣断了脑子里的毛细血管,慢慢瘫掉了。
老婆婆又说,儿媳妇在婆婆瘫痪后不久,就跟人跑了——其实那个媳妇人还是好的,只是嘴巴子厉害些。婆婆动辄就在人跟前说儿媳妇把自己骂瘫了,是个败家的祸害。偏是吴家本家户大,妯娌又多,口舌重,话难听,把个媳妇子逼走了。走的时候把孩子也抱走。也活该吴家倒灶,现在钱也没,人也没,病人还天天骂人哩——家里的气数都骂尽了。
我暗自思忖,家长里短这事,真的够蛮缠的。自己嘴里这样,别人嘴里那样。倘若心里老是存着郁郁不平,日子过得一定够呛的。俗世之俗,就是有许多绕不开的牵绊和得失。屈辱有,微小的荣耀也有。烦恼疼痛有,赏花听风的愉悦也有。形形色色的东西原本是为着构成光阴的,若是心思一路狭促过去,被这些琐碎的现象蒙蔽,自己把自己逼到绝境,日子只能过得一塌糊涂。内心的愤怒喷发,便是暴脾气。内心的情绪过滤,便是淡然。嘴狠,不过赢一时。心广,才能赢一世。
病人大概并不懂得这些,只管叫骂抱怨。可是,光是愤恨,顶什么事呢。
红眼窝老人慢慢从屋子里踅出来,走出廊下,踅到院子里。他缩着脖子,沉闷得像一团旧了的棉絮,灰头灰脸。好久,才压低声音说,算命的婆子说,她还有五年的活头——生生要拖垮一家子人。
他说完,回头觑着眼看了一眼屋子里,有些心惊胆战的那种不安。那双红眼窝里,有些捂不住的东西在响动。真是不可思议的人家,我心里暗暗猜度着。而且他家的院子虽大,草木也多,但总觉得空落落的,根本没有干净与幽致的气息,反而有一种不清爽的颓废感。
你是作家?唔,到底来写什么?
喔,是受朋友的委托,写一篇因病致贫的稿子,所以才找到您。也许,稿子写出来对您帮助不大,他们的报社,并不很有名气。
老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原来如此”的神色。一些说不清的东西在他的脸上辗转反侧了许久。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是个懵懂的人。
他转身拎起半桶水去浇花。园子里,开着好几种花。不是很繁密,但开得还算好。清亮的水珠溅到草叶上,似乎寒凉蚀骨,草茎们都打着寒战。老人浇花的神情认真无比,半晌,絮叨着说,这花儿都是女子在春天种下的,若操心不好枯了几枝,回来又要发火吵架。家里人人都是暴躁脾气,只我一个受气包,一辈子憋屈死了。她们都命贵,只我贱,天生是个受作践的。
她喜欢花,怎么会发脾气?应该是个柔和的女子才對。
柔和?以前是的。那年她谈了个对象,小伙子是南方的。家里老婆子死活不同意,怕女子私奔,就锁在屋子里。后来,这门亲事自然黄了。可是打那以后,死女子竟然再也不嫁人,一直干耗着,怄气。今年都三十五了。脾气也是打那以后就暴躁得很啊,说一句顶回三句,錾子来钉子去,真个儿顶嘴的犟丫头。你说,能有啥办法嘛?
老人的眼窝愈加地红了,手脚笨重地打理花草。他扶起一枝纤细的草茎给我看,说,这是啥花儿也不知道个名儿,清早开花,薄薄的花瓣,核桃大,怪好看的。日头一照就落了,倒是阴雨天还开得时间长些——女子最爱这个花,得操心给打理好才行。
太阳当天照着,我来得自然迟了些,不得见这种脆弱的花。实际上,我也不喜欢太柔弱的花,连一层日光都经不起,喜欢个什么劲儿呢。也许,这花就是清少纳言说的朝颜那类吧,太阳一晒,顿然凋零给你看。人有人的心事,花也有花的脾气。大概,凋谢也是一种逃离俗世的方式。
这世间的悲喜沧桑,都弥散在花叶一脉淡淡的微凉和孤寂里,都凋零了。是的,我坚信凋谢就是逃离。那个女子,从俗世的庸常里撤退,抽身回到了自己的从容与清淡里,自此心神宁静,生命澄澈坦荡,不嫁人,独守芳华。可是细细琢磨,算不算是一种决然的逃离?
园子的篱笆矮墙边上,钉着一根木头桩,白寡寡的木头上,刻着一行小字:那年花开时节遇见你,草尖挂了露珠。可你还是去了远方,直让我等到枯草结霜,大雪封门,然后杳无音讯。
突然就心里一阵诧异。这野村荒地,竟然有一个文学女青年,如此婉约多情。可是细读这几行字,似乎是一个小伙子的逃离。或许女子家人的干涉,只是夹杂其中,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也或许不过是她自作多情了,小伙子只是对她好,并没有娶她的意思。一个天南海北走的人,能死心塌地把心留给乡里女子?她妈妈大概是怕小伙子走了女儿名声不好嫁不出去,就大张旗鼓锁在屋子里——你想,几百户人家的大村,脸面是多么重要。
不过那女子着魔了,自此再也看不上村里的小伙子,就一直老姑娘着。
浇了水,除了杂叶,老人又去草垛上撕黄草。他一直不停地忙这忙那——忙碌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淡化忧愁、担忧和气恼。这些东西忘是忘不掉的,只能淡化,处理得模糊一些,把锐疼转换成钝疼。能够坦然面对现实,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麻木,在思想上逃离。家人应该是相互依赖的,可在他看来,一地鸡毛,碎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偶爾,他用眼角的余光看人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一闪而过。或许,我的想法是错的,因为根本不能透彻地了解一个陌生人。
我想留一点钱给他,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不妥。也许顾虑身上带的钱太少,也许觉得自己也过得很省,还没达到帮助别人的地步。
老人家,等您家女子回来了,替我问声好,她一定是个美丽的女子。这会儿,应该还有通往镇子上的车吧?
话是这么说,可她已经过了美丽的年纪,都要奔四十岁了,老牙衰草的。出门往右边拐,顺大路走,有个两三袋烟的工夫就到了公路上,路过的车都可以拦,去镇子五块钱——你采访的就这些吗?不跟村支书打个电话了吗?报纸啥时候出来——如果你认识县里的干部,我家的情况给反映一下,都瘫了两年了,钱花出去不少……
抵达镇子上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饿得很了。路边的凉皮摊子一家挨着一家,摊主都用眼巴巴的眼神瞅着,一时不知道坐在哪儿合适,挑挑拣拣。
抖去衣襟上的浮尘,拂顺耳边被风吹乱的发丝,坐下来吃一碗凉皮。其实,这便是寻常的日子。路边一种单薄的小花开得非常繁密,顶着一头灰尘,却不减生命的旺盛。人一辈子,也许觉得漫长遥迢,不过在大自然看来,也和这路边的花儿一样,不过一朝一夕的盛开,一春一秋的枯荣罢了。把自己看低一些,把别人看高一些,冷静而简单的生活,一定会减少很多牵绊烦恼。光阴,还是寻常顺其自然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