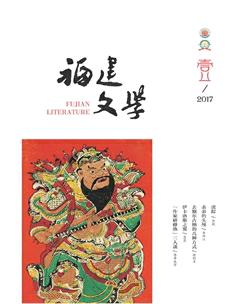穿越之路
沈念


九月的梅关古道,被一场秋雨淋个透湿。星罗棋布的鹅卵石,横卧竖立,情状不一,像一面面镜子,在脚步下越磨越耀眼。这样一条古道,对我这个外来者意味着什么?我匆匆行来,急急离去,仅是走过那漫长时光里微不足道的一小段。我记下它所呈现的荒凉,那是所有古道共同的命运。在离开后的許多个夜晚,那一道道“耀眼”又意外地走进梦境晃荡,幻变成一个纠缠不休的孩子,生气扭头踩破平静的水面,溅我一身惊慌。
还是从雨说起,雨雾弥漫,梅岭上的一切都进入无法表述的幽深之中,古道多添几分幽怜。从广东南雄市出发,到珠玑巷,再抵达这里,起承转合的午后光阴,让人在跟随车辆的恍惚摇荡中出神,犹豫着是否要从梅关古道开启一次短暂的远行。
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匆促步履,重叠影像,人生的终极追问也曾在这里发生。我很疑惑,镶嵌在时间深处,隐藏在大地褶皱之中,与现代交通工具断然隔绝,适合怀旧的古道,穿越了什么?它某天闪身为一个闹腾的动词,那些背包客、露营者、观光者,那些俱乐部、驴友圈、亲友团,在这里聚集偶遇,一次次完成向时间致敬的仪式。
梅关古道所穿越的梅岭,藏身于五岭之一大庾岭之中。逶迤五岭,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山谷纵横,林深峰立,很早之前就把广东这片南蛮之地隔绝在中原之外。地域的隔绝终被强悍的权力打开。刚吞并七国而成为中国第一代皇帝的秦始皇,站在自己的疆域图前沉思片刻,咀嚼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深长意蕴,尔后决绝地发令:“北逐匈奴,南开五岭。”二十万秦军在声威震天的马蹄和呐喊中推进,残酷而血腥的战争扑满梅岭的沟坎旮旯。争夺、烽烟、厮杀、血泊,军事战略上的关隘意义,注定了梅岭进入历史视野的传奇沾满鲜血。汩汩血流,顺着一场场大雨浸入粤北大地,又长成一株株暗香低悬的古道梅花。
梅岭这个发光体,吸引着自秦以来的“居庙堂之高者”的眈眈虎视,剑气般的反光又刺痛他们的肉眼。秦始皇遣屠睢、赵佗率大军驻梅岭、攻岭南,当地番民愤起抵抗,秦军“三年未能越岭”。屠睢死后,秦军大将任嚣与赵佗施以民族亲和之策,平定百越之地,建郡立县,并于公元前213年在梅岭巅峰筑关。“番禺负风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可以立国。”任嚣病危中的一句话,又让赵佗狂妄一次,这个小县令在秦末汉初的混乱时局中锁关自立,顺顺当当地做起了南越王。虽然赵佗最后不得不向巩疆固土、强悍难挡的汉文帝俯首称臣,但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从此镌刻在了这条南来北往翻山越岭的古道之上。两百多公里长的梅关古道,如蜿龙匍匐,横亘广东、江西两省之间,地势险要若人之“咽喉”。这是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岭南第一关”的声誉毫不夸张地落在它头上。兵家必争带来的战火与纷乱、杀戮与毁灭,沉沦大海销声匿迹,但又有谁能抚平古道的隐痛和创伤?那些战争的始作俑者是否会感慨,“只要一想起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岭南”?
多少古道被时光吞噬,大地上踪迹杳无,典籍中也读不到片言只字,一切终成幻影,梅岭却还在。缓步寻找古道上的碎痕残迹,百步之遥就有宽厚的石凳相候,凳身深深浅浅地长着或绿或黄的苔藓。苔藓无语,最忠实的信徒,蜉游在时间的孤寂里。时令的不对,接踵而立的梅树未到绽放清香之际,粗细不一的枝杈虬曲裂散,仿若画中旁逸而出伸向山谷之上的云朵。古道上静止的草、树、石头、苔藓,活跃在丛林深处的虫、鸟、兽,像一个个吸光体,吸尽天光、目光、水光。鲜艳色彩瞬间隐匿,时间使它沉郁黯然,扑满一身抹不净的尘灰。
古道斜行向上,一个尽头踅进另一个尽头。当地朋友绵长的讲述,像阅读者翻看那些以文字记忆编绘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书写者,我的耳畔蹦来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崎岖的古道上,他们是南迁的贬官、获刑的罪犯、无家的流民。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人,他的脚步和我在时空的不同维度重叠,我踩在他往返重叠的脚印之上,大地愈加坚实。他是张九龄,岭南第一个考取进士并到朝廷做官的著名诗人,也是梅关古道的筑造功臣。在我故乡洞庭湖的众多抒情者中,孟浩然的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扛鼎之作,殊不知这首“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投赠之作,实则是他临烟波洞庭,吐露欲渡无舟、临渊羡鱼的感慨,曲折表达的是对丞相张九龄援引的渴盼。
唐开元四年(716年),因排挤主动告假南归侍母的张九龄路经梅岭,眼之所见,如他在《开大庾岭路记》所言:“岭东路废,人苦峻极”,“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要知道,经贞观之治的唐王朝,日渐强盛,与海外通商的需求愈加迫切,那时的广州已是拥有六万多人口的最大商港。岭南以沿海之利,商业发达,东南亚、阿拉伯诸国商人、使者,多从海上到广州,越梅岭而上长安。这种情况之下开凿梅关古道的利害性不言自明。处江湖之远,张九龄仍不忘为君分忧。向唐玄宗谏言开凿梅岭获得允许后,在那一年的冬月他开始主持这条古道的修筑拓宽工作。路陡,狭窄,难行,荆棘,山石庞大,开凿艰巨,三个月时间,一条宽一丈多、长三十华里、可容五辆车并行的山道畅达四方。
张九龄代表的官方之举,悄然将梅岭和梅关从军事意义向经贸文化交流转型,一条古道改变了南北交通格局。写在历史记忆中的实况是,古道通拓,商旅络绎,沿途店号鳞次栉比。广州等地客商货物由水路北上到雄州,经古道运往岭北;由岭北南下的客商货物,则由陆路经古道运到雄州,而后转水运往广州等地。距古道三十公里之外的南雄城迅速崛起,梅关古道成就了这座“南来车马北来船”、“十部梨园歌吹尽”的热闹、繁华的商业城镇。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在《唐代的广东》中评述:“张九龄开凿新路,就是将南北的喉咙,也即是把广东北面的重镇南雄开通,因而可以使广东的港口和中原交通得到便利,并且间接使经由广东而与中原及海外各国的交通便利。”
所有的古道,都是被马蹄和脚步踩踏出来的。站在那幅古代地图前,细心地比较,会让人发现,梅关古道所代表的穿越之路曲折弯绕,似乎距离略长些,这“略长”折算成实际里程居然有一千里之遥。也就是说在以长安为出发地和归结地,取粤北过郴州到长安的距离要比走梅岭近。舍近求远,不是明智者所为。查究原因,是梅岭北接的扬州有更为便利廉价的水路航线。水运之利托起了扬州这座唐代长江流域的最大商业城市,也成就了一千多年里由岭南通往中原最便捷的梅关古道。那些在今天看来的“香药路”“珠宝路”“陶瓷路”,叠印在梅岭的影里,又成就了南雄这个中转之地的繁华兴盛。
不绝的喧闹戛然沉寂,我又有些恍惚了。雨从铺满道路的石头上滑过,缓慢而有节奏,眼前的萧索和静谧,把当地朋友的叙说击成碎片。嘚,嘚嘚嘚。有人模仿马蹄之声,引我竖耳倾听。我眼前莫名地浮出一些陌生的面孔,和鸟雀般欢跃的人声,躲藏在林丛深处。那一刻,我相信,从雨雾深处,刚走过一支马帮,和我们擦肩而过,他们看到了我。古道为一双双磨出血泡的脚板而延伸。站在梅岭的巨大石碑之前,抬头是“南粤雄关”四个红色大字,再往前走十余米,一道坡坎,就是江西境内。前面,后面,一眼望去,古道仿佛通往时光隧道的深处,无法探知,充满悬念和诱惑。祖先令我们叹服的是,再高耸重叠的峰峦,再迢远艰难的崎岖山路,也束缚不住他们行走的脚步。
自张九龄开凿梅关古道后,历代有识之士尽心尽力屡修屡护。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蔡抗、蔡挺兄弟二人协商议定,分筑所辖境内路段,种松、梅于道两侧。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南雄知府郑述征集民工,用鹅卵石、花岗片石铺砌岭道路面至南雄城,九十余里。明正德年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自称“十年两度手栽松”,“种提青松一万株”。到明末清初,历愈八百多年的古道上,“官道虬松”已成南雄一景。
古松林立,蜡梅却空枝相照。任何一条古道都逃不出孤独的宿命。作为一个天地万物的读者,我以徒步的方式走进梅关古道,呼吸那些过往的生命与魂灵的气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距离之间的腾挪闪回,无疑出卖了我们自己。像著名摇滚歌手崔健所说,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只是,这样的走,被高铁、飞机、高速取代。我们行走的速度越快,与大地的距离就拉得越远。
我的朋友祝勇说: 隐藏道路的最好办法是使道路变宽。当它像世界一样宽的时候,道路就不存在了。”梅关古道却以另一种瘦弱而坚韧的方式隐藏着。轰然巨声在耳畔的深夜炸裂,这条千年古道在冥想与睡梦中蜿蜒浮沉。它覆盖着泥土和落叶,深陷的马蹄印长成大地的黑痣,祖先一路遗失的魂魄在历史的光阴深处涌动。喧嚣,孤寂,纷乱,时间,梅岭穿越它们也被它们穿越。而我穿行于梅岭,是把双脚交给古道,把生命体验中隐秘的欢乐与沉思交给了在地图上厮守“南雄”的这片土地、自然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