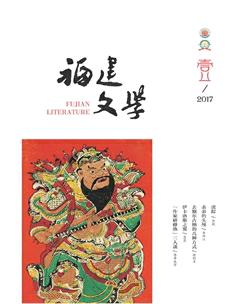给我一颗西地那非
林为攀
后来——在应召女郎的怀里,第一次闻到浓郁的香水味的时候,他有好几次想哭。终于,他要离开这个热情给予他温暖的女郎了,不远处的海湾传来轮船隆隆的马达声,那是它在即将远航之时对这块土地发出的最后思念,沙哑,撕裂,本该前往一个陌生又惊奇的世界,但在一个历经漂泊、始终在寻觅温暖的巢穴之人听来,却像自己的真实写照。然后,那个难得的夜色成了最浪漫的回忆,在参加各种文学比赛的那几年,在麻木地辗转于陆地、海洋、岛屿的时候,在他走下轮船,踩在那块陌生的土地的时候,在他需要靠药物才能重焕精神、需要靠西地那非才能进入那些女郎身体的时候,然后是未曾中断的写作生涯,那里有神圣的秩序、固定的作息时间、衣食住行的各项保证,以及时不时的新书签售会——后来,他终于得以一步步地从他原本以为真实的世界走向之后所有不真实的境地:就像从一个陌生的异乡走入另一个陌生的异乡。
他第一次从船上见到海洋,第一次令自己的閱读印象得到了真实的验证,他存储在脑海、骨骼及血液中对大海的印象,在那个雾气沉沉的早上都复活了,就像泳池的蓝遇到了大海的蓝,所有的一切都体现在了他沾上鱼腥味的脸上。这么多年,他终于从广袤的陆地来到了广袤的海洋,在陆地跋涉的那些时日,他风餐露宿,与乡村的牛羊为伴,很多时候,夜色总是在犬吠中苏醒,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只有动物还散发着热气的粪便提醒他,他还置身于这个世界,他的头顶还是星月将至的苍穹,他的脚底还是雾气越来越凉的土地。在路上,他很多时候同时处于这个世间的两端,一端是贫瘠的乡村,绳索替代桥梁的河流,另一端是风驰电掣的高速公路,繁华的夜市。他很多时候想不通,当他无数次想回到学校,当他在应召女郎的怀里想念女友清纯的脸,当他对着苍老的父亲心里却渴慕他早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心:在被道德束缚的同时也向往罪恶的泥淖。从那以后,他对自身的处境变得坦然很多,不再为磨破一块脚趾甲而怨怼丛生,也不再为吃到一口热饭而泪眼蒙眬,他把自己受到的苦难和享受的幸福,都当作平常。
所以,他不再懊悔离家前对父亲冷眼相加,所以,他不再为自己中途肄业感到丝毫歉疚。他还记得,父亲在月台送他坐上那列开往北方的火车之时言犹在耳的教诲:钱省着点花,不要看些无用的书。当他到达北方那座贫瘠的城市,通过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来到大学校门口的时候,他的心在那一刻变得冷硬,事后他看过很多作家的回忆录,他们回忆起自己学生生涯的时候,无不津津乐道于开学第一天迎接他们的漂亮学姐。他不禁揣测,他们在男女之事上的开悟,可能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学姐。而他,不仅没有学姐,连一句欢迎都没有。那个脑满肠肥、屠夫扮相的老师第一句话便是:学费带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说道:要交现金。
父亲怕现金路上被窃,给他办了一张他此后用了数十年、卡上数字被磨损后才寿终正寝的银行卡。这张银行卡伴他走过了此后所有的漂泊生涯,并在无数次他行将饿死之时慷慨解囊,有时是几十块,有时是一百块。这些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通过乞求一些朋友得来的。那些冷峻的银行就成了他路途中难得的亮色,ATM机上无法取出零钱,需要到柜台上取。他在那些衣着光鲜、妆容精致的柜台小姐身上遇过很多冷眼,这些零钱是不值得她们浪费时间办理的,由于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他对那些冷眼并未放在心上,只有再次困窘之时,这些冷眼才会释放它们本该有的毒素,让他的心变得寒冷,变得屈辱。而那时,银行卡还很新,卡上凸起的数字,甚至仅靠手指就能辨明到底是几,他在车里,坐上了老师的车,老师正在开车,望着前路,他义务帮助这个学生去银行取钱,他可以抽取一点点学费当作辛苦费,说不定这个学生还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知道尊师重道的重要性,在取完钱后请他撮一顿好的。
而他,并未如是想,那个时候他还很容易被一些小事影响,还没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对这个老师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当老师看到他只取出一千块钱的时候,他见到老师脸上那种不知道如何形容的表情时,他觉得自己扳回了一局。他没有取出所有学费,剩余的学费成了他之后有底气离开学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学费让他在路上度过了一段堪比旅行的美妙时光,不过那时,老师看到只有寥寥一千块钱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个学生在玩弄他,而是为又看中一个穷学生而懊悔自己的眼光并未随着教龄的增长而有所提高。他找了个借口驱车走了,只留下这个手里还揣着一千块学费的新生。他走进一家带有北方特色的餐馆,大吃了一顿,那个时候,他并未高度评价北方美食,当他走在那些四下无人的乡村小路之时,这顿食物的余味才会最终萦绕在他的舌尖。
当ATM机吐出那十张钞票时,他第一次对贫穷有了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间接影响了他的金钱观,当他终于不再为三餐而到处奔波时,他甚至对这些能够让自己过得体面的金钱产生了罪恶感,他的骨子里还是想保持一个穷人对金钱的远观态度。这些钞票叠成一起,很薄,但在他心里却形成一堵厚实的墙,为他遮风挡雨、砌这堵墙的是他的父亲——那个远在南方,每日穿梭于丘陵,驻足每棵高大笔直的松树跟前、不经意间就已步入老年的父亲。每年开春,父亲都要看遍故乡的每座山,这些山上松树成群,松涛阵阵,他要选择一座有遒劲树干的山,用一把刀锋开叉若蛇舌的刀子,把这些树干切开一道道口子,让松油流入底下放置的油桶。这些松油摞成了一堵儿子可以平安抵达北方的无形的墙。
那个时候,他对一切轻易到手的东西都不太珍惜,比如这些钱,他那一顿饭就吃掉了五百多块,甚至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要过很多年,当他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望着形同枯槁的父亲就着咸菜喝粥时,他才会对当年无耻的挥霍行径痛哭流涕。那个时候,他已经好多年没见到父亲,好多年没再回家乡。发达的通信设备不仅未拉近他与故乡、与父亲的距离,反而让他们嫌隙渐生,导致成了最熟悉的陌路之人。
在路上的时候,好几次他想拿出那台老式诺基亚给父亲拨打求救电话,当他看到手机里可有可无的信号时,他往前走了几步,前面是一个拱形的桥洞,走的时候,信号有时满格,有时微弱,终于在他置身桥洞之时,信号完全消失了,这个桥洞打消了他的求援计划。他再次出来时,天已经和桥洞一样暗了,这次他拨打了电话,只不过接电话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自己的朋友。朋友终于给他打了一点钱,这点钱支撑着他度过下一个开口借钱的时期。这台诺基亚最后也无可避免地被淘汰了,当所有手机都变成触屏的时候,他格外怀念诺基亚,怀念那个用手指按键拨号、打字的手机,他还记得在那段困顿的岁月,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安慰了自己无数个漫漫长夜。当他使用上那些甚至用脸颊就能输入字词的手机时,在联系变得愈加便利的同时,他与四周的关系却愈加疏远了。
此外,穷困之时除了不珍惜金钱,对感情他也抱着可有可无的心态,但又不像金钱那样只令他产生非爱即憎的二元论,不,感情更加复杂,在他陷入瓶颈的那大段岁月里,他甚至怀疑正是因为感情让自己首次害怕面对空白文档。他对那些走进他生命中的女人排序后发现,一直自诩颇佳的女人缘与事实并不符合,只有寥寥几人而已,而且那几人还是同一个人变化而来。这个人他已经忘记了姓名,也忘记了模样,只记得那双眼睛很明亮,在他漂泊的时光里,这双眼睛堪比星辰,照亮了前方任何歧路。当他终于厌倦大学生活,拎着一个背包跳过那个铁丝网,绝尘而去时,在他的背后,在那个还在风中摇晃的铁丝网后面,就是这双眼睛让他差点忘记继续前行,好几次他想回过头去,投入这双眼睛里,但不行,他在学校待不下去了,老师只要见到他,都会问他学费什么时候交。学费早就被他当成路费,支撑今次的远行。他几次支支吾吾,言辞闪烁,都被老師解读出了另一番意味:贫困学生。他厌恶这个说法,但未交齐学费的事实又让他对此说法不敢多加置喙。他终于陷入自己一手制造的困境中,只有离校才能得到最终救赎。其间,北方口音的老师打电话给他父亲,他的父亲当时正在地里割稻子。每年夏天,父亲都会用几天时间先把地里的稻子收割完后,才上山继续割松油,割松油需要抬头挺胸,割稻子需要弯腰驼背。这两种姿势无疑直接影响了他写作之时和签名之时的形象。写作时,他挺直腰身,让头脑的思绪像树上的松油一样源源不绝;签名时,他低着头,像倒伏的稻谷,把自己的名字尽量写好看点。父亲割稻子认真,从不错过哪怕一粒稻子,当割完一亩地时,父亲兜里也会变鼓,那是在割稻的间隙从地里捡起来的谷粒。父亲割完后接到了电话,他在盛夏炎热的风中接到了一个来自北方的电话,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打电话来要生活费了,他一手把兜里的谷粒掏出来,一手接电话,但却是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陌生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学费没交,再不交就要开除了。他的父亲很紧张,也很担心,放下镰刀就跑回家,回到家就跨上那辆锈迹斑斑的摩托车。在打钱之前,父亲第一次拨响了他的电话,问他是不是学费没交。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学校出来两天了,他对学校会告诉父亲他逃学之事早有准备,所以,他当作很坦然的样子接听了电话,但父亲说的话却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在最热的夏天,他突然间掉到了最寒冷的冰窖。不过,他很快就有了应对的方案,他告诉父亲,现在骗子很多,谨防上当。听到儿子这句话后,这位着急儿子的父亲走出银行,跨上摩托车,在田埂处停下,然后,“再不交就要开除”这句带有浓重北方口音的话在他的父亲嘴中就成了“千万别上当”。母亲听后,仰头“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继续割稻。父亲站在还没割完的另一半稻田里,稻浪迎面扑来。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夏日最温暖的笑容。
他义无反顾地往未知的前方走去,身后那双担忧的眼睛直到暮色四合后才转移到喊吃饭的同学身上。他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在他创作陷入瓶颈的时候,这些经历成了他最可贵的创作财富。有人问他写作秘密是什么之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让这个秘密在烟圈里四处散去。他是后来才学会抽烟的,在此之前,他很讨厌烟气,并把它当成噪音一样讨厌,此后,吸烟成了他继喝咖啡之后又一行之有效的提神剂,而噪音却始终没被他正眼对待过。他抽过很多牌子的烟,倘若以这个国家的地名来算,他简直可以说抽遍全国。从白山黑水的“长白山”抽到天涯海角的“椰王”,甚至薄荷口味的万宝路他也抽过好几款,可以说,他走过多少个地方,就抽过多少种烟。只是,在学校出来的时候,这些烟还躺在属于它们的出产地,需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先后纳进他那个肺活量越来越低的肺中,然后被他当成空气,吐在他所经过的每一片土地上。
轮船正在穿过迷雾,身后的海岸模糊一片,只有一些兜售海鲜、水果的小贩叫卖声隐隐传来。他上船之前买了一些水果,其中有北方罕见的芭乐,现在这些芭乐被他拿在手里摩挲,就像他在北方之时,手攥两颗核桃一样。不同的是,芭乐表面光鲜,核桃表面皱纹遍布,像初生婴儿到行将就木之人的形态。他漂泊的终点在一处小乡村,这个乡村有犬吠、鸡啼,还有一座座迥异于南方的山峰,这里的山峰像锥子一样戳着湛蓝的天空,山上都是裸露的巨大石块。当他的行程进入这座乡村的领地时,迎接他的是一条吐着舌头、流着哈喇子的黄犬,参差不齐的犬牙就像几日后他在此地翻遍的那些山。后来,他不再害怕狗,甚至有一段时间,他爱上了圈养大型犬类,当这些宠物在牢笼里发出低沉的乞食声时,多年前那个差点葬身狗腹的经历就这样不期而遇,他当场大笑起来,笑声让笼中的畜生一度安静不少。不过,那个时候,他必须先想到对付这只黄犬的办法,他捡了一块石,往它身后丢去,在狗去追那块石子的时候,他必须趁它回过神来之前逃离它的视线,不然,他的下场就会和那块被它衔进嘴的石子一样。他使劲奔跑,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跑过这么快,好在黄犬没有追来,他在一条河边停下了脚步。渔人捕获的大鱼溅湿了他的脚,不过他丝毫不在意,他看到这条大鱼时,看到的是自己拿着筷子从鱼腹开始享用时的画面,他咽了好几口口水,他那稚嫩的喉结还没被之后的珍馐养刁,还在这条鱼上做着饕餮一顿的美梦。
大鱼在阳光下脱下自己的鱼鳞一片一片,鱼鳞像无数双眼睛望着衣衫褴褛的他,同时望着他的还有渔人的眼睛,不同的是鱼鳞不会说话,渔人的声音很响,这种声音他此后一直避免再次听到,却在将近晚年之时,对这种声音的关心胜过了盖棺之语。在他签售的那些日子,周围被严格限制人流,有时候人群过于密集,实在限制不过来时,工作人员就给他戴上巨大的耳机,耳机里面没有声音,就像世界最开始的模样,一切都是安静的,那些草履虫等单细胞生物静静地分裂,海洋里的鱼类也在时间的长河中变成化石,鱼骨变成镌刻在岩石上的木梳……
渔人问了他很多问题。
如果是几年以后他遇上这些问题,说不定他会不置一词。但现在,这些问题恰如其时地出现在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有必要停下来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了。当天晚上,他在渔人家里过夜,当大鱼变成一架鱼骨的时候,他打着饱嗝回答了这些问题。渔人对他如此年轻就有如此遭遇感到惊讶,并义务献出了自己的建议:该操逼的操逼,该日屁眼的日屁眼,人生就是这样,各行其是。这些忠告带有斑驳的岁月印记,并沾有鱼腥味,此后,当他离开这座小乡村的时候,他对这些建议就只剩下绵密的霏霏细雨了。
之后,他花了几天的时间,看遍、翻遍了每一座锥子山,他没挑那些树木生长的山,而是选择了露裸有巨大石块的山。他翻了很多石头,石头背阴处和向阳处恰好各占每块石头的一半,然后,他挑了几块丢进了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没有打招呼,独自一人踏上了返程。在路上,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来自大海彼岸的电话,是一个获奖电话。直到那刻,他的出行意义才最终凸显。
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父亲打电话要钱,之后,他从来没有再给父亲打过一次要钱的电话,即使在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岁月之时。这次打电话口吻前所未有地轻松,并难掩自豪,而且还传染给了父亲。他知道这个消息会让父亲最终卸下压在肩头沉重的包袱,在此之前,父亲对他爱上写作一直颇有微词,除了在物质上得不到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怎么向邻里解释儿子的爱好。舅舅也在那一刻联系到了他,并开了一句影响他深远的玩笑:作家怎能不会抽烟?
他没有选择乘坐飞机,而是坐上了轮船。他仔细比较过两种交通工具的优劣,最终对高空的恐惧让他选择了轮船。当他置身于轮船上时,不仅他之前阅读过的所有与海有关的文章都在那刻复活了,他还隐隐期望收获一段类似方鸿渐在船上邂逅鲍小姐般的艳遇。不过由于生性胆小,他错过了好几次搭讪陌生女郎的机会,只能站在甲板上,独自咂摸昨晚与应召女郎的温存片段。海风吹拂,前方是一片未知的海域,跟多年前从学校出来时不一样,这次他的前方充满了光明,起码他认为光明在前方等着他,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很奇怪,他对即将要到来的一切都很模糊,唯一让他真真切切感受到的还是那个应召女郎的体温。其实,那个夜晚他就在尝试抽烟了,只不过呛人的烟雾几次让他放弃了,当烟雾钻进他口腔的时候,他的脑子瞬间混乱了,晕乎乎的状态让他无法直观打量女郎诱人的酮体。他去厕所洗了一把脸,等脑子平静下来,回到女郎的身边,这次他没有停留,没有犹豫,而是果断地、直接地在女郎身上狠狠“耙了一回地”。
他一直没把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在那些自传或半自传的小说里,他也没有假借人物之口说出。倒不是出于自身名誉考虑,也不是由于那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他对前者从来不看重,很多人慕名前往结识他的愿望破灭后,在每个公开或非公开的场合恶意中伤他时,在很多朋友见流言大有打垮他并仗义为他申辩时,在他唯一的社交网络页面上都充斥着大量污言秽语时,他也没有静坐下来,花一点时间,逐个回应这些谣言。至于后者,只要看过他大部分作品的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作者本人对一些道德观念丝毫不关心。他之所以对此事讳莫如深,就在于他那次得到的体验并不完美,曾有一度,他把错误全部归咎于对方头上,他认为自己像一只羊落入了老练的猎人手里,猎人在他身上得到了快感,而羊收获的只有恐惧、惊慌,如果羊与猎人的位置能对换下,或许那次初夜留给自己的回忆会是一颗蜜桃,而非现在的黄连。但,很快他就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他无法行使一个男人的职责,当他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夜晚的情景再次浮现在了他眼前。他提着肿胀的下体以为能顺利进入的时候,却在半道缴械投降了,之后枪上膛了无数回,依旧无法发射子弹。应召女郎就这样嫌恶地推开了他。他穿好裤子后,发现夜色将明,载他前往彼岸的轮船已经发出远航的汽笛声。在船上的时候,他对此并不介怀,因为在他的阅读史中,任何男性角色的第一次均以失败告终,他虽然身怀别人所不具有的创作禀赋,在这一方面却和其他普罗大众没有区别。直到他踏下轮船后的第五天,为了打消自己隐藏的担忧,他再次走入一块陌生之地的风月场所,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他失望了,他真的不行。作为一个男人,有什么比“不行”更令人绝望?于是在那个夜晚,他从灯红酒绿的仄室一头撞入充溢着槟榔和各色小吃的台北夜色中,而身后的仄室,烟头盖满了那个心形的烟灰盒。烟是台北特有的“长寿”,是他在十日台北之旅中继槟榔之外唯一对这座城市有所好感的特产。
这是他终生未婚的直接原因,而非他在自传里再三强调的“崇尚独身主义”。他既不反感延续香火一说,也不排斥所谓的大男子主义,只是在他这不长的一生中,上天并未赋予他这两种职权。在好几本书里,他都虚构了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形象,而且这个大男子主义还儿女成群,家庭和睦。这或许就是他这辈子除写作之外最为强烈的宏愿。他为评论家赋予这些角色与他的构想相去甚远的评价哭笑不得,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以“女性代言人”的身份慢慢步入他生命的终点。
“长寿”让他领会了吸烟的妙处,从那以后,不管是签售会,还是写作之时,他都烟不离口。当初一身烟气的父亲让他退避三舍,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也带着一身烟气出入那些公开场合。只是,再没有人会像他当初嫌弃父亲那样嫌弃他满身的烟气,烟成了他的招牌,为他的作家身份镀了不少金,而且,在无数个服用西地那非的日子里,也是这些烟掩盖了他的紧张之感。台北之旅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从那以后,他的每一本小说,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不知道这是借助于那些西地那非的帮助,还是烟的功劳。这其中,咖啡的功用在最初也得到了有效的见证,有时候,在空气糟糕的那些日子,在他感冒生病的日子,他暂时放弃手头燃烧的香烟,改喝咖啡提神,病好后,他突然发现烟和咖啡的结合可以使自己的思路更加顺畅,从那以后,咖啡和烟就成了他写作之时最常用的伎俩。只有在某些“发情”的日子里,他才会偷偷事先服用储藏书柜隐秘之地的西地那非。
他这辈子收藏了很多纪念品,有各种牌子的香烟盒,咖啡匙,最值得纪念的还是要属多年前的那张船票。这张船票被他和那些火车票、汽车票、飛机票放在一起,这些票见证了他落魄到发达的所有过程,而那张船票无疑是分水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把这些票张贴在墙上,就是一张世界局部地图,为此他感到非常自豪。当然,他也同样收藏了每次购买西地那非的收据,和那些票不一样的是,这些收据被他藏在最不显眼处,甚至可以说除他之外无人知晓的角落,远不像那些票一样“光明正大”。这是他最柔软最羞耻的见证,他打算在死前付之一炬。
船上没有艳遇,更没有一个女郎留意过他。之后数年,或许是出于报复,他拒绝了所有主动投怀送抱的女郎,他只对自己征服的“猎物”感兴趣。父亲对误入歧途的儿子很快失去了耐心,这位在最开始对儿子由衷自豪的父亲,在儿子三番两次让他失望后,终于不再纠结对方的婚事。他好几次让父亲最原始朴素的愿望落了空,父亲一直想抱孙子,这个念头直到他晚年无法开口说话之时还非常强烈,只是作为儿子的作家,从未切身理解过父亲。在同龄人纷纷当上爷爷之后,父亲觉得自己有权让儿子实现自己也当一个爷爷的愿望,儿子刚开始一口答应了,条件是要他写完手头的小说。父亲对此给予了充分理解,在那些寒来暑往的日子里,父亲在割完稻子之余,唯一的盼头便是看着日历,用手指计算每一个良辰吉日。他一直让父亲变卖家里的那几亩地,跟他一起生活,但父亲始终没有同意,如果说之前种地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在他晚年之时,种地就成了一种精神寄托。他最后终于没再说什么,只是对父亲在每一个所谓的吉日问他同一个问题感到不堪其扰。
在此之前,他的写作都不成系统,在那些葬落日的乡村小道,在那些践雪径的北方小城,他的书写更多的还是带有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照实描摹,一直到他出了好几本书以后,他才会让这些风景带有异域的风情,随意涂抹自己想要的色彩。他在路上用那台此后从未离开身边的诺基亚写作,这是在没有固定的桌椅板凳的前提下,他随时掏出手机记录转瞬即逝的灵感,手机的电量只能支撑他写不足五百字,他需要在下一个充电之地到来之前,赶紧写完脑海中的思绪。等到了旅馆房间,或是陌生人的家里,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充好电,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事先裁剪好的白纸——这些纸是他从学校偷来的,继续路上未竟的写作。或许就是白纸的存在,让他此后养成了珍惜纸张的习惯,并在写作工具日渐发达的几年之后,还是没有最终放弃在纸上写作。此外,他更加习惯在诺基亚上敲字,敲击键盘的清脆声让他能够近距离观察缪斯女神的降临方式。这种观察方式让他忘记了置身荒野的苍凉之感。
他写作不必如此辛苦后,人们会在他的房间看到很多白纸,这些白纸很粗糙,摸上去像触摸一块墙皮剥落的墙壁,纸上不着一字,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光,这种光在他无数次起夜后让他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尤其结合自己跳动的脉搏,更是让他俨然回到了几十年前那个荒郊野外。至于那台诺基亚,则成了古董,很多人出高价购买,但都被他否决了,他知道它并不值那些钱,而是因为自己的存在才让它获得了一种与自身不相符的价值,他更清楚,诺基亚的打字功能,只对彼时的自己有用,对这些前来问津的有钱人,作用并不比一块卫生纸大。键盘已经斑驳了,还有几个键失效了,但对于他不啻比宝贝还宝贝。
它见证了他的创作之路从遄飞到枯竭的全部过程,直到那刻,他才最终明白,他的创作生涯和自己的性欲刚好相反。创作生涯遵循一条普遍的规律,年轻时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年老时,为寻一个合适的字词数次推敲,而他本该在年轻时喷薄汹涌的性欲却在年老时才焕发生机。这个现象是他在一个夜晚无意间发现的,那个时候,他刚刚“征服”一位经常上门采访他的女记者。在那个夜晚,他首次面对空白文档端坐良久,烟灰盒里堆满了烟屁股,咖啡也喝了好几杯,还是无法进入他脑海中那个神奇的世界,他发现自己不会写作了,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他和女记者约好了今夜相会,没想到却忘了事先服用一颗蓝色菱形薄膜衣状的西地那非。敲门声越来越急,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开了门,在见到女记者那张炽热的红唇时,他的生命像一座喷发的火山,在那刻,把毕生的岩浆都融入了对方体内。
之后,他再也没办法正视空白文档,萦绕在脑海的都是娇喘和诱人的裸体。他几次强迫自己进入创作状态,但都失败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提前老了,再也无法写作了。他本来想对外宣布自己封笔,但他始终没有这么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这个一直以高产量著称的作家在生命的中途便偃旗息鼓。女记者看他只对男女之事感兴趣、却对自己的新作三缄其口后终于投入了别人的怀抱。他在那些不能写作的日子里,很快苍老了,市面上对他的指摘愈加甚嚣尘上,其他问题他可以付之一笑,唯独“创作为何中途停止”这个问题他不敢不正视。人们对他的任何解释都不买账,直到此刻,他才回忆起那个渔夫的问题。
年轻时,他回答过这些问题,现在他却在这些问题面前乱了阵脚。他至此才发现,自己的那些文字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寻到答案。然后,他在那些每天被逼问的日子里,陷在回忆里痛哭流涕。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作家时,他已经无法讲话了,他过早地患上了和父亲一样的失语症。父亲在彻底放弃当爷爷后,没过几天,就不会说话了,一张瘪唇,像酒瓶盖一样,两手哆嗦,对大老远回来见自己的儿子没正眼瞧过一回,而他却不能不正眼瞧那些质问他的人。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念了一遍事先写好的稿子,他那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话并未让他们听懂他在讲什么,只听到一句“封笔”和“谢谢大家”。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最后带着一身败兴回到各自就职的报社。当天晚上,他打开书柜,从书柜的角落拿起还未服完的西地那非,把它们放在掌心,掌心放不下,就放在桌上,然后一粒一粒地吞进肚,最后嫌麻烦,就用手心攥紧全部,一骨碌全部仰头服了进去,滚动的喉结就像多年前母亲在地里喝水时的模样。然后,他消失已久的精力全都回来了,他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脑子里回荡着许多画面,这些画面引诱着他坐在电脑前,但是他很兴奋,去卫生间自慰数次才稍稍消停,然后终于可以坐在电脑前了,脑子再也不会一团糨糊了,两手也不再哆嗦,最重要的是,他發现自己永远不会再害怕面对空白文档了。他下笔如飞,敲击键盘的声音让他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荒野,那个旅馆房间,那个陌生人的家里。自此,他终于及时给自己的生命挽歌画上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