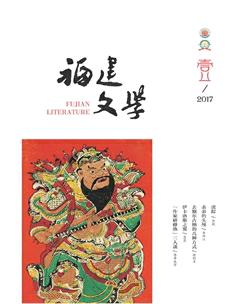表弟的头颅
李师江
一
从我家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半山村,那是表弟春仔的家。
说是山,其实不过福建沿海海拔不到一百米的小丘陵,小时候跟着妈妈,磨磨蹭蹭也要走一个小时。在靠近山顶的一个山坳里,途经一座古寺,叫慈圣寺,不大,灰砖外墙,里面白石灰抹墙,陈旧洁净。慈圣寺分前后院,后院墙上画着地狱受刑图,血淋淋的,算是我最早看过的漫画。妈妈还会给我解说,哪一种罪孽遭受哪一种惩罚,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妈妈有时候会抽签问事,大事小事公开的事秘密的事都能问。身穿旧青袍的胖和尚拿着巨大的扫帚拂地,朝我们微笑,端茶、解签的时候耐心而生动,我也能听个一知半解。佛国宽容而优雅,给我深深的印象。
慈圣寺再往前一里许,还有一棵百年榕树,树下有一个小庙,供着一个红脸大眼、白牙紧咬的神。到了树荫下我总想休息,妈妈一把把我拉走,走了许远才告知:这个神原是躲在榕树上的一个妖,对来往路人不怀好意,各种不客气,后来村人集资给它修了这座庙,落庙为神,改邪归正。它毕竟出身不好,万一触动它的邪性,又让人头疼脑热也未必可知,还是少惹为妙。
后来知道这尊神叫白将军。这么邪性的神不知为何取了个风雅的名字!
这一条上山下山的路,途经树林、庄稼地、坟堆、庙宇、小水库,每一棵小树都有传说,故事多姿多彩,我又是恐惧又是喜欢。如果让我一个人走,那绝对不敢。
下了山,走了片刻,就到半山了。这个村子的喧闹与山上的静谧成反比,到处都是运砖头的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村子周围有很多黄土,是制作砖头的材料,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刚从广东引进的机器制砖是一门好生意,村外建了几个红砖厂,吸收了村中的主要劳动力。一进村子,就能闻到那种被泥土被烧焦的干燥的气息。
春仔是姨妈的孩子。到了春仔家,妈妈就跟姨妈聊一块去了,她们有聊不完的鸡零狗碎的大事。我和春仔最聊得来,因为他比我小一岁,而两个表哥比我又大得多,没有什么交流。主要是,春仔喜欢听我的话。
“有一只老虎,躲在草丛里,远远地看着我,真的,我看见它的眼睛了。”我对春仔讲路上的见闻。我说些若有若无的东西,自己也不清楚是我脑子里还是眼睛里的,这样可以吸引春仔对我的崇拜和信赖。
“它没有扑过来吃你?”春仔眨着眼睛问。
“有神的保护,他不敢。”我笃定地说,“没做过坏事的人,都有神的保护。”
那时候我应该是三年级,春仔是二年级,对世间充满了好奇。
“你见过神吗?”他问。
“榕树下那个神,我经过的时候,我看它一眼,它也盯着我,但我不能确定它是否也看着我,不过对我没什么恶意。”我绘声绘色地说,“虽然它是出身不好的神,但我估计也能成朋友。”
“你是想去放牛吗?”春仔问道。
之前我跟春仔说过,我不太想上学,想让我爸爸买一只牛,到山上放牛。我可以骑在牛背上,和神灵、若有若无的野兽混在一块,聊胜于在学校里被同学各种开涮。
“是呀。”我说,“我已经跟我爸说了,他只是点点头,并没有完全同意,但希望也很大。”
春仔在我的影响下,也有同样的愿望。
“啊,我也想要这样。”春仔无限向往,不知道是真的感兴趣,还是只想学我。不过他信誓旦旦地说过喜欢放牛胜于上学。
“那你爸答应吗?”
“还没有。”春仔兴奋地说,“不过我已经想出办法了,我会一直哭,一直哭,白天哭到晚上,不吃饭不睡觉,这样他就会答应。”
“哪里学来的?”
“邻居有个女人,不停地哭,什么愿望就都实现了。”春仔不愧是个聪明的小子。
我提醒他:“哭是很累的,眼泪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我会喝很多水,我也不怕累。”春仔说,“到时候你从那边山上,我从这边上山,我们在山顶上碰面,如何?”
“最妙不过,我就可以摆脱那些可恶的同学了。”我说,“不过山上也有可怕的东西,你可得小心。”
“哦?”
“我看见一只鬼,跟在我后面,有点透明,走路飘飘忽忽的,你怕吗?”我再次说起路上见闻。
“那你怕吗?”
“有妈妈在一起,不怕。”我说,“而且一路上都是神,鬼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也不怕。”春仔说,“我可以给你一根红线,把鬼系起来,做成风筝。对了,你知道怎么抓鬼吗?用血,或者大便,你一见鬼,就把血或者大便泼过去,它就被制服了。你回去的时候,我给你拉一坨大便,不过你抓到鬼也要分我一只。”
妈妈和姨妈正在厨房便忙活边拉呱,我们在厅堂也叽叽喳喳,本来井水不犯河水,猛然间她们听见“鬼”的字眼,赶紧冲出来,叫道:“呸呸呸,还不赶紧收口,你们这臭嘴!”
大人是不讓孩子谈鬼的。
二
很长一段时间,妈妈都不带我去春仔家。她独自去,回来了我才知道,干后悔也没用。我问妈妈为什么不带我了。妈妈:“这……以后去吧。”我看她回答得很勉强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有一天夜里,我睡着了。爸爸和妈妈性交,把我闹醒了。
我们家只有两间房,一间是爸爸妈妈和我睡,还有一间是姐姐们睡。我夜里怕鬼,和妈妈睡一头,爸爸睡另一头。农村人,一天到晚干活累,晚上闷头就睡,房事也耗体力,不频繁,半月一月一次,一般趁我睡实了,妈妈到爸爸那一头。我睡眠浅,被惊醒,不知道他们作甚,也知道是不宜大张旗鼓之事,假寐。
完事,他们乘兴聊点家常。
“哎,那么小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妈妈说。
“你妹妹怎样?”爸爸问。
“也去了半条命了。”妈妈说。
我在瞬间醒悟,翻身起来:“是不是春仔死了?”
在黑暗中,爸妈吓了一跳,还尴尬。妈妈连忙爬过来,把灯开起来,抚慰我道:“你做噩梦了吧!”
“春仔是不是死了?”
妈妈不得已,点了点头。
“不,你们骗我。”我号啕大哭。
我闹了一个晚上,妈妈煮蛋给我吃,哄我,我也没吃,早上两个白里透黄的蛋安然在碗里。
再一次,妈妈要去半山的时候,我缠着去,妈妈用各种理由拒绝我。我想起春仔的话:“只要你不停地哭,什么愿望都能实现。”我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妈妈说:“如果你不哭了,我就带你去。”
我停住了哭声。我一定要去看春仔,他不可能死掉的,我们的约定还没兑现呢。没有跟我告别,他不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
正在祭祖的时候,姨妈在家里烧纸钱,哭得死去活来。妈妈过来就是为了防止她伤心过度,哭着哭着就死过去。我知道姨妈爱春仔就跟妈妈爱我一样,虽然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着实爱得紧。
桌上摆着菜肴贡品,点着香烛,姨妈一边烧纸钱,一边唱着丧歌,眼泪一点点地洒在红色的火堆,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妈妈扶着她,生怕她一头倒在火堆里。我四处张望,寻找曾经熟悉的踪迹。姨妈的房子在马路边,我以前到马路上还没进门,春仔就会兴冲冲地迎上来,我不相信这次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春仔,你怎么提着头颅呢?”我叫了起来。
我看见春仔提着自己的头颅走了进来,他的头颅在朝我笑,而脖子上是空的,怪异极了,不得不使我大声疾呼。
姨妈停住了哭声,愣住了,她一把抓住我,哑着嗓子像公鸭一样喊道:“你看见春仔啦?他还是没有头吗?在哪里?”
我往门口春仔进来的地方一指。不过说实话,春仔在瞬间不见了,就在刚才姨妈抓住我肩膀的一瞬间,我的眼睛被一种雾气蒙住,我看不见春仔了。本来他就是那么薄薄的一片飘忽的纸人。
显然,姨妈更看不见。她朝着那片空气跑了过去,好像抱住一个人的样子,她的哭声前所未有的凄凉:“我的宝贝呀,你没有头呀!”
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个人浑身瘫软晕死过去的样子,像一根油条瞬间软了。
姨丈和妈妈等过去,把她抬到床上,掐她人中,用凉水打她耳光,似乎要把一个死人打活过来。
我再找春仔,已经看不见了。我的眼睛蒙上了一种猪油一样的东西,我再也看不到我心中所爱的物体了。但从他进来的表情,我能感觉他要回来吃饭的,他一定像平常一样,踩着凳子爬上去,跪在凳子上才能够得着桌子。他现在一头提着头,一手吃饭,着实比以前难多了。我坐在另一张凳子上,陪着他吃饭。桌上烛火摇曳,我想有可能是春仔和我开玩笑。
春仔的墓就在慈圣寺边上。它比一般的墓地要小很多,但是很可爱,也简单,也没有普通墓地的制式,只是像一块长条馒头一样,边上立一个墓碑。周围的荒草围绕着它,随着摇曳。种地的农户、山中游走的众神甚至是觅食的走兽,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小小的墓地。
墓地选在慈圣寺旁边,是有讲究的。
妈妈说,非正常死亡的人是有罪的,包括被谋杀、车祸、暴病等等。只要你不是静静地死去,你都是负罪而亡,要下地狱的。
船仔家的门口就是砖厂的交通要道,每天都能听见“突突突”的声音,马达像射精的龟头有力乱窜。春仔横穿马路时被运砖的拖拉机碾死。
他死得很惨,轮子从脖子上碾压过去,身首分离。碾压发生之后手还在抽动。
他才八岁,谁也不知道他身负何罪,死得这么残忍。
妈妈和姨妈都相信他有罪,也许是前世的罪。墓地选在寺庙旁边,这里是清净之地,有利于修炼,可以早日从地狱出来,投胎成人。
姨妈整整数月,关在房子里,听不得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
姨丈就在砖厂烧砖,是个技术能手。自己的砖厂的车碾死了孩子,这是哪里造的孽呀!他也不敢再去砖厂。但他毕竟是男人,迫于生计,歇了一段又重新出山了,他忍住不去想孩子的事。
三
半山村的村医池德明算是村中有文化的人。他自幼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医术,后来又去进修了一番,草药、西医都通晓,在村中的诊所虽然仅是一个小门面,但药材齐全,用药科学,不曾发生过治死人的现象,在村医中实属难得。
姨妈来到池德明的诊所,没进门脸就哭成花了。她跪在池医生面前,哀号道:“你救救我们春仔吧,求你了。”
池德明皱了皱眉头,站了起来。他觉得这女人疯了,可是也不能对她怎样。还好他店里有人,他吩咐道:“去把他家人叫来吧。”
姨妈不管不顾,眼泪与鼻涕沾在医生的西裤上。医生从她怀里拔出腿来,问道:“怎么救呀,他都死了。”姨妈道:“把他的头接起来,我的儿子不能是无头鬼呀,呜呜呜。”
从症状来看,医生更加确定姨妈的精神有问题。
姨丈赶来了。他把姨妈拖回来,但是泣不成声的姨妈像蚂蟥一样吸附在诊所,实在是拉不走。如此僵持很久,姨妈没有哭得那么厉害,终于能把话说完整了。
姨妈的意思是,请池医生在烧香祭祖时,告知池医生的父亲,在阴间给春仔接上头颅。
池醫生的父亲池老医生原是赤脚医生,擅长接骨,用草药,也在大饥荒时帮人治疗浮肿、便秘,发明过用羊屎当药丸的方法。他在临死前得知自己要死,穿上寿衣,闭目而亡,算是个异人。姨妈认为,池老是医生,死后也是当医生的鬼,要接上春仔的头颅,非他不可。
“荒唐,愚昧!”池医生摇着头,断然拒绝。他不会让这荒唐的举动毁坏自己的英明。人死了就死了,一切烟消云散。而所有的仪式风俗,只不过是生者的寄托,作为医生,他对生死的理解理性而有分寸,这种见识支撑着他的事业,乃至他的人生。
秋高气爽的一天,姨妈铤而走险,到池老医生的坟墓上点起香烛,祭起魂灵。她烧了大量的冥纸,献给池老医生。如果这些钱都能在冥币银行兑现的话,池老医生足够建起一栋别墅,或者开一个诊所。堆成山的冥币,每张冥币上都有金箔,那是姨妈半个月日夜劳动的成果。冥币燃起了熊熊大火,被风卷过之后,在空中飞舞。姨妈很高兴,她明白这是魂灵来收冥币了,她的送礼即将成功。大火蔓延开来,把整个山头都烧了,西山头那片松树,被烧得焦头烂额。镇上的人赶来救火,根本于事无补,火烧到资圣寺边上的时候,自然熄灭。资圣寺边上的菜园安然无恙。
作为纵火者,姨妈被抓了起来。烧山毁林是要坐牢的,这在民间普及多年,已是常识。姨丈也要被逼疯了,他失去了一个孩子,现在妻子也成疯魔,又要坐牢,真是祸不单行。
姨妈很高兴。她看见火从池老医生的坟墓烧到春仔的坟墓,说明池老医生明白心意,收钱做事,速速赶往春仔的地方。医术上,池老医生无所不能。大饥荒时,大伙儿吃糠便秘,屎塞在屁眼里出不来,难受得嗷嗷叫。池老医生用耳勺,把一个个肛门里的屎挖出来。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春仔的头颅应该不在话下。
池医生更是气急败坏,父亲的坟墓被烧得乌烟瘴气的,凭空沾上这种倒霉事,愤怒是难免的。他到镇上,揭发姨妈的精神有问题,任此下去,以后非但是烧山,就连村子也要被烧毁。池医生毕竟是医生,在这方面的建议不得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池医生的举动挽救了姨妈,使她免于坐牢,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
妈妈每几天就得到关于姨妈的各种消息,一惊一乍,忙得不可开交。来传消息的都是来往半山走亲戚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伞花嫂,她是一个长得像画一样好看的女人,就是嗓门大,喜欢走亲戚,顺带传递各种消息,每个消息都说得夸张而邪乎,引人注目。她娘家就在半山,经常回娘家,一路上笑声朗朗,极为招摇。她确实是极为少见的连小男孩都觉得好看的那种女人,有一种想让全世界男人都来操她的顾盼生姿。她从半山回来,离妈妈好远就张口劈里啪啦,妈妈捂着心口叫道:“伞花,你说轻一点儿,别让我心跳出来。”
她像个演员一样,悲哀地摇着头,说:“天哪,你妹妹连精神病院都没法治了,怎么办呀!”
“哎哟,怎么个没治法?”
“遣送回来了呗,谁家里能容得下一个疯女人呀,你快去看看吧。”
伞花把消息汇报完毕,瞬间又兴高采烈起来,由悲剧演员转为喜剧演员,眼神流转。她只有被舒舒服服操一顿才能消停下来。
妈妈像陀螺一样又往半山走。那条石板山路,她恐怕走了数百遍。
原来,姨妈在精神病院住了不到一周,就被姨丈领了回来。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说,没见过这么精神可嘉的病人,在医院里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儿,再让她待下去,护工全要失业了。
四
我翘课了,壮着胆子爬上山头。老蟹伯正在路上山上给花生锄草,见了我,笑了起来,道:“你背着书包来山上干吗?”
“我来找我的表弟,你有看见吗?个头跟我一般大。”
老蟹伯擦了一把汗,指着山中散落的坟墓,道:“山上有的是鬼,没有人,没小孩愿意来上山干活的。”
“我表弟就是一个鬼,提着自己的头颅。”我说。
“鬼能看见人,人是看不见鬼的。”老蟹伯道,“这满山都是鬼,我们看不见的。”
站在山头,能看见慈圣寺,春仔的墓地就在边上。我想,春仔一定会在这一带玩耍的,即便他是一个小小的鬼。
山中有覆盆子、小红果,在树上也有鸟窝,我知道这些都是春仔喜欢的。
“春仔,我来找你了,你看见了吗?”我站在高地呼喊着。
山间有小小的回声,但春仔没有出现。
“即便他听见了,朝你走来,你也看不到他。”老蟹伯停下锄头,指点我道。
“可是我曾看见过春仔,他提着头颅,像一片模糊的、半透明的纸人。”
“哦,最亲的人能看见。”老蟹伯笑道,“也许他就在你身边。”
我在山头凝望良久,有灌木的地方影影绰绰,感觉春仔在和我捉迷藏。本来要下山去白将军的庙里问一问,但是妈妈对白将军的印象让我觉得恐惧,犹豫着最终还是退缩了。
后来我对着空气喊:“春仔,如果你能看得见我,一定要来找我,我们可是有约定的。”
我想问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要受到这样的惩罚。
人找鬼不容易,鬼找人一定容易得多。
方圆数里,有几个通灵的巫师,我们村的妇女鬼英就是其中一个,名气也大。鬼英四十多岁,有一张白皙的脸,她会的通灵术叫“去阴”,顾名思义,就是去往阴间。农历七月,中元节前后,是阎王把鬼放出来与亲人团聚的日子,鬼英会在七月间“去阴”一次,想打探阴间消息的人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会蜂拥而来。
姨妈自然不例外,她在这天凌晨就赶到我村,见了我,摸摸我的脸蛋,估计想起春仔,又泪汪汪了一阵子。
“见到春仔了吗?”她眼泪汪汪地问道。
“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点了点头。
妈妈说:“去阴的时间是晚上,你这么早来干什么?”
“在家我哪能待得住。”姨妈说。
晚上,大概七点的时候,鬼英的家围了里外三重,有一部分人专门来问事的,也有一部分人来看热闹的,大人小孩都有。鬼英坐在凳子上,靠着一张方桌,头上是一盏昏黄的灯。她点起香,念了咒语,把头伏在桌子上,右手有節奏地擂着桌子,声音渐小,睡去。俄而醒来,魂儿已到阴间,神情如醉如痴。她的魂儿漫步阴间,见了相熟的鬼,便会问候,那鬼也会回答,她便一人饰演两角,表情口气秒变,惟妙惟肖,让人不得不信。
“见到我的春仔了吗?他喜欢爬树,有可能在树上,你在路边仔细找找。”姨妈不时地在鬼英耳边喊道,惹得旁边的人很不满。
鬼英的魂灵到了阴间,能够见到什么哪一家的鬼,都是碰运气。让他专门去找春仔,这个不太可能。鬼英如果碰到谁家的鬼,谁家就能和鬼对话。对于姨妈的催促,鬼英置若罔闻。
“阿如婆,你在吃什么呀,这么大口,哈哈哈,你的两个女儿都要问你话呢。”阿英像在赶集的路上一样,说话兴高采烈。
妈妈一听,赶紧道:“啊,碰到我娘了,你们让开一下,娘呀,你还饿肚子呀?”
阿如是外婆的名字。外婆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据说是饿了,吃谷仓着火后烧成碳的粮食,难以消化而胀死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她是饿死鬼还是撑死鬼。
鬼英瞬间变成外婆的语气,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道:“怎么不饿呢?天天饿,也没东西吃。”
“烧了那么多纸钱,你就不够买东西吃吗?”妈妈伤心道。
“哪有那么多钱,到我手里就没几个,七扣八扣的。”外婆不咸不淡地说,“再说了,什么能吃得饱呀,从来就没尝过饱的滋味。”
妈妈就哭了。妈妈参加过几次去阴仪式,去阴师都碰见了外婆,外婆老在路边吃脏兮兮的东西,有时还是垃圾堆里的食物,倒是容易碰上。妈妈每年给她烧更多的纸钱,希望她能吃到高级一点的食品,可是每次都在路边吃,每次都喊饿。妈妈嘴上没敢说,但心里笃定她是个饿死鬼。这样的鬼,还有什么好做呢!
姨妈抓住鬼英的手,叫道:“娘,你看见春仔了吗?你的外孙呀?”
外婆悠悠道:“他那么小,来阴间干什么?你们别骗我。”
“他确实在,娘,你去找找他嘛,他太小,照顾不了自己的生活。”姨妈瞪大眼睛。
“要找你自己找。”外婆没好气地说,“我饿得走不动路,你们谁管过我。”
姨妈大哭,几乎要把鬼英的身子当成树来摇晃,哭道:“你是不是做鬼做糊涂了,他是你亲外孙呀,我的儿子呀。”
姨妈被人拖了出来。鬼英从外婆身上脱身,又往前走,看她的表情,确实是在阴间的一个集市上,打招呼的人特别多。
仪式进行了三个小时,终究没有看见春仔。妈妈和姨妈擦干眼泪,浑身瘫软回家。
姨妈不甘心,她希望鬼英能再来一次,专程去找春仔。这不太可能,我们跟鬼英没有这么大的交情。
姨妈豁出去,使了一大招,决定花五块钱让鬼英来一次。姨妈和表哥赚的钱拢到姨妈手里当家,姨妈有这个能耐。妈妈去当说客,软说硬说,洒了几把眼泪,鬼英最后咬牙打破规矩,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今儿就应了这句话。不过可得说好,我可以去阴,但找不找到春仔,可不打包票。”
协议就这么达成。七月是鬼来到人间走亲访友的月份,过了这个月,大多数鬼就关进去,要找就更难,姨妈希望立马执行,既然能找到外婆,就能找到春仔。鬼英说:“三天后来吧,可别走漏风声。”
鬼英去阴一次,元气大伤,需要养个三天。如去得频繁,还会折寿,阴阳来回,付出代价颇为沉重。
第二次去阴,只有妈妈和姨妈在身边。姨妈有准备,鬼英灵魂出窍之后,姨妈唠叨道:“春仔也有可能去供销社,他喜欢玻璃瓶里的糖果,有时候会巴望一整天,你看下阴间有没有供销社,有的话就太好了,活着的时候就没吃过几个糖,整天念叨。学校里就别找了,他不爱上学,见了书就头疼……”
不知有没有听到姨妈的提示,鬼英神情恍惚,右手攥拳擂着桌子,以示她在阴间活动。今天路上的鬼没有那天的多,那天是鬼的集市,今天鬼买足东西都散了,鬼英不得不東张西望地找鬼。有的鬼不熟识,鬼英就一脸失望,叹了口气。时见了熟识的鬼,鬼英就抬手招呼:“嘿,阿伯,有见到春仔了吗?阿如婆的外孙,一个八岁的小鬼,没有脱罪,还在修行,这种小鬼很少,你见到应该有印象,想想在哪儿,告诉我……”
如此往复,不厌其烦,可见鬼英的尽心尽力。
突然间,鬼英变成了一个苍老的男声,慢悠悠道:“看见啦,就从这儿过去,扒在一台拖拉机上,那孩子太皮。”
姨妈愣住了。她朝鬼英叫道:“别让他扒车,太危险了。”
鬼英神情严肃,擂动桌子的拳点更加密集,表明她在阴间剧烈走动,十分费劲,有可能是跑起来了,可以听见她急促的喘气声。姨妈更加着急,恨不得帮鬼英架一双翅膀。
终于她大口大口喘气,似乎停住脚步,叫道:“春仔,你下来,你娘有话跟你说。”
姨妈瞪大眼睛,只差抱住了鬼英。
鬼英笑了起来。天哪,那是春仔的笑声,春仔做错了事之后那种得意的,带着请求原谅的笑声。
“春仔,春仔,我的儿呀,你怎么死一次都不怕,还在扒车呀!”姨妈抓住了鬼英的手,泣不成声。妈妈扶住姨妈的肩膀。
春仔细细的声音回答:“坐车快呀,我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玩。”
姨妈抓紧鬼英的手,惊慌道:“别去,听娘说,你在那边去找外婆,她最亲,她是你最亲的亲人,好歹会照顾你。”
姨丈突然进来了,后面跟着伞花嫂。姨丈见了这架势,就知道姨妈干什么勾当了。他痛心疾首,妻子变成了一个说疯又不疯说不疯又是疯子的女人,他辛辛苦苦赚的养家钱,被她花去搞子虚乌有的迷信事,求神拜佛大手大脚,家里堆着大把的香烛纸钱,却在饮食饭菜上缩手缩脚。他和两个表哥大春、二春都在砖厂干活,那是体力活,需要结结实实的饭菜打底子,她却汤汤水水,能对付就对付,这让老实、隐忍的姨丈真他妈的气急了。
伞花嫂在身后,眼神紧张而饱含期待,不用说,给姨丈传消息、带路,全是她一手操办的。
姨丈虽然愤怒,但毕竟修养还可以,没有拳脚交加,只是咬着牙一字一句质问道:“这个家你还要不要,还有两个儿子,你还管不管!”
姨妈被这一幕有所干扰,但并不影响她面对春仔的专注。她哀求的眼神盯着姨丈,希望他不要破坏这神圣的一刻。她把姨丈铁塔般的身子摁了下来,坐在凳子上,更加耐心道:“爸爸来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吗?”
春仔细细而调皮的声音从鬼英嘴里出来,愈显真实,道:“爸爸,我想要一头牛。”
姨丈就那样愣住了,他突然抱住姨妈,发出猛兽一样低沉的恸哭。男人一生很少这么失控地悲伤的。
这个愿望是春仔和姨丈的秘密,也是我和爸爸的秘密。
姨妈忍着悲伤,把哭声控制住,理智重新回到了脑海,她哽咽着轻声问:“池老医生来看你了吧,他把你的头安上去了吧?”
春仔不屑道:“我整天在外玩,他找不到我,不过我听说他找过我了。”
“那你的头能安上去吗?”
“安上去又掉下来,还不如提在手上。”春仔满不在乎道,“不过一吃东西就从脖子上掉了下来。”
“啊!”姨妈撕心裂肺地惨叫着,直至昏死。姨丈号叫着抱住她。人生凄惨,莫过于此。
春仔好动,能说这么多话都已然不错,趁着间停的瞬间,又溜走了。鬼英悠悠醒来,恍如一梦。她无力地被妈妈扶着躺倒床上,妈妈喂她备好的党参汤,她也无力喝下,只想休息。几天之内,两次去阴,她的元神耗到极致了。
五
我终于在梦中等到了春仔。那种感觉很神奇,我觉得春仔还活着,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妈妈。
“孩子,你别老想这事,想了就会做噩梦。”妈妈告诫我。
“不是做噩梦,是好梦,是春仔来找我的。”
“哎哟,胡说,你欠着春仔什么啦?”
“不,我在山上叫春仔来找我,他听得见。”
妈妈这才信了,仔细打量我,看看我是说胡话还是怎么的。
“春仔在做什么?”妈妈开始认真查询。
“吃冰棍。”
“他的头还没接上吧?”
“没有,嘴里吃的冰棍,从脖子上流下来。”
“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要吃冰棍呢?”妈妈叹道。
妈妈特别不喜欢小孩子吃冰棍,因为我吃冰棍曾经闹过肚子。
“春仔没钱,是从街上讨来的。”
“胡说,你姨妈给他烧了不少钱。”
“钱被扣压了,到不了他手里,春仔是罪人。”
“天哪,阴间也这么黑。”
妈妈听了状况,紧跟着就去告知姨妈,每一个关于春仔的消息,都能给姨妈带来一点惊喜。她们商量着请一个神,来帮助春仔的窘境。
伞花嫂是个演员,也是个观众,她喜看人间的极致的悲喜剧,这会给她带来阵阵高潮。那是农村还没有电视机的时代,可想而知,所有的戏码她必须自导自看。靠着这种精神的营养,她笑面如花,笑声朗朗,回荡在村落之间。她是我见过世上最快乐的人,没有忧愁。
“你妹妹死了。”她大嗓门在我家后门响起。
妈妈惊得从门里窜出来,她几乎跪在伞花前面,抓住她的腿:“她怎么啦?”
伞花嫂一仰脖子,做了个喝农药的手势,惟妙惟肖。那是农村妇女自杀的流行方式。
我妈慌了神,就要往半山走。我死死拉住,要跟着她去。春仔死了,我不知道;姨妈死了,我一定要去,我要看看死是一种什么玩意儿。这个死神,我要把你揍死!
妈妈又气又急,见我像一团鼻涕甩不掉,她从大扫帚里拔下一条小竹枝,剥开我的裤子,抽打我屁股,像针刺一样又痒又痛,留下细细的血丝,爽得不得了。
伞花嫂建议道:“重一点,屁股蛋打花了,他就有记性了。”
伞花嫂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竹枝落在我屁股蛋上,看得極为认真。
妈妈抱着我的腰,边抽打边哭道:“你这个冤家,就是你一句话害死你姨妈了!”
伞花嫂默默地去屋里拿了醋,帮助妈妈涂在我屁股上,那种电击般的刺痛,一辈子难忘。我蹬着腿号叫了一阵,感觉自己像一只被捆绑起来的猪。
妈妈说:“还去不去?”我说:“不去了。”
妈妈总共这样打过我两次,还有一次是我去河里游泳,被收拾了一顿。村里有孩子在河里淹死过,游泳极为忌讳。这次收拾也是下了狠手。
妈妈把我收拾妥了,失魂落魄地往山那边走。走了一百米,又被伞花嫂叫回来,道:“回来回来,不是那里走,她已经抬进城了,现在应该在医院里。”
“有救吗?”
“还不是死马当活马医,吐白沫翻白眼,死相很难看的。”
妈妈掉转方向,朝村里的另一头走,要到隔壁村才可以坐公交车进城。我抹了眼泪,远远跟在后面,到村口的一棵荔枝树上坐着,等妈妈回来。
姨妈在医院里被抢救过来。妈妈就在那里照顾。我夜里一个人睡一头,心惊胆战,但也有些安慰:我不相信姨妈会死,所以姨妈还活着。我也不相信春仔会死,所以我相信春仔还会活着。
只是,他在哪里活着呢?
春仔,如果你再次来到我梦中,你一定要告诉我怎样你才能活过来。因为你不该死,一个小孩子不该离开爸爸妈妈跑到另一个世界的,那太孤单。
池医生跑到医院去看姨妈,不仅出于一种道义,还带着满腔疑惑。当初他认定姨妈精神有问题,他的话是有权威的,但是进了精神病院,不到一周就放出来,这对自己的判断明显是一种羞辱。而现在喝药自杀,不正说明精神确实有问题吗?
另外,这个女人的死去活来,跟自己当初的冷漠拒绝有关吗?池医生是个自信的人,有一套现代的生活理念,自己的种种做法,是合情合理合法,破除迷信合乎科学精神的。但又隐隐觉得总是有一点不妥,不妥在何处,无从所知。一个人的身体出现问题,他能抽丝剥茧找到源头,现在他觉得生活出现了问题,这让一个乡村医生想破了头却没有答案。
池医生把两盒罐头放在床头柜上,坐在病床前,他审慎地观察着姨妈。这个从阎王爷手里被揪回来的女人一脸苍白,精神尚好,只是在遗憾为什么没有死成功。
“你有几个孩子?”池医生轻柔地问,他在考察姨妈的神智。
“三个。”姨妈缓缓伸出三个手指。
“那是以前,现在只有两个了,知道吗?”池医生劝诫道。
“不,还有一个,在别的地方。”姨妈坚定地说。
这个答案也还算及格,不能肯定她的精神有漏洞。
“为什么要自杀呢?”池医生问道。
“我想去那边照顾他。他接不上头颅,一吃饭就漏下来,我的孩子呀,他日子怎么过,别的鬼怎么看一个整天提着头颅的小鬼?肯定欺负他。”姨妈悠悠道,“大春二春都长大成人了,春仔更需要我,我就想去那个世界。”
池医生当头遭到一闷棍。他终于可以确定,这个女人不是精神病,是傻,是痴,是没有接受过一点儿科学文化的教育,是比精神病更可怕的愚昧。
不管如何,作为医生,总是有善意的初衷的,因此池医生耐心道:“这个世界没有鬼,也没有神,只有我们看到的一切,你懂吗?”
姨妈可怜地看着池医生,为池医生的无知表示遗憾,她比池医生更耐心道:“你爸爸去找春仔了,只是没有找到,他是个守信的老人。”
池医生摇了摇头,道:“那些个神汉神婆装神弄鬼来骗你,你不要再相信了。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你死了也白死。”
池医生告辞了。这个世界的愚昧,中国民间几千年方术的积淀,不是靠他一张嘴就能说服的,他爱莫能助,已经尽力了。
“给你爸烧纸钱的时候,代我谢谢他,他是个有德的医生。”姨妈对着池医生的背影道。
为了姨妈家的事,妈妈心力交瘁。外婆死得早,妈妈照顾姨妈和舅舅,既当姐姐又当妈,一人管着好几家,整天挂在嘴上的都是烦恼,没有过快乐的时候。即便跟爸爸性交的時候,她也是满腹心事。
我在妈妈身边长大,满脑子也都是忧愁。人活着就是满腹心事,解决了一件又来一件,没有放得下的。直到长大了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觉得伞花嫂那种女人其实是最好的,根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别人多么不开心的事,在她眼里都是一个开心的调料。她死后一定是一个开心鬼。能娶一个伞花嫂那么漂亮那么笑声朗朗的女人为妻,实在是再妙不过的人生。
我屁股上的小伤疤渐渐结痂,摸上去沙沙的,就如屁股上长了一脸麻子。有一天睡觉的时候,妈妈摸了摸我屁股上的一脸麻子,问道:“还疼吗?”
“不揭开就不疼。”
我偶尔手贱,会把一个痂揭开,新的皮肤还没长好,又露出红彤彤的带着血丝的肉,汗水一渗,又是那种麻辣酸爽。
“妈妈也不想打你。”她感叹道。
“你打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爱我了。”
我没有朋友,跟爸爸也比较疏远,对妈妈极度依赖。妈妈,春仔,以及山上的神,是我屈指可数的亲密的人。
“明天妈妈带你去姨妈家。”妈妈岔开话题道。
“太好了。”我扑在妈妈身上。当我和妈妈之间恢复了其乐融融的关系时,那是难得的让我有安全感的极度放松的时光。
“不过,你要对姨妈说,你看见春仔了,他的头已经安上了,他玩得很开心。”妈妈循循善诱,她极少有这么缜密的思路。
“不,我已经看不见春仔了,我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猪油一样的东西。”
“看得见看不见不重要,但你要这么说,知道吗?”妈妈坚决道。
“不,说谎会下地狱,被割掉舌头的,这你知道的。”我坚决反驳道。
我一下子就想起慈圣寺的后院墙上的地狱受刑图。那些有罪的恶鬼,有的下油锅,有的被火钳子炙烤,而被割舌头的鬼,正是因为撒谎。妈妈跟我一起看过很多遍,对此我们心知肚明。
妈妈抱住我,说:“可是你不这样,姨妈还会死的,她的脑子里全是春仔。听妈的,没错,救人的谎言也许没那么严重,如果真要受刑,妈妈也会替你受的。”
一边是遥远的谎言的下场,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妈妈的垂泪哀求。我只是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对于真理的把握根本没那么硬朗。
我忧心忡忡地跨上了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当演员。
姨妈正在灶间起火,她憔悴得像个人干,眼神黯淡,像一个活着的死人。
“我刚才看见春仔了。”我不自然地说,好在厨房黯淡,只有灶肚的火光照耀她自己的脸。
“在哪里?”姨妈有点不信。
“在路上哟,骑着一头牛。”
“啊,真的呀。”去阴之后,姨妈烧了一头很大的纸牛给春仔,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收到了。姨妈惊叹道:“他怎么样,还提着头颅?”
“不,他的头已经完好了,跟我的头一样。”
“天哪。”姨妈眼里露出精光,像一道闪电把她身体激活了,她朝山的方向跪下,道,“池老医生,你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他年我到了那个世界一定给你做牛做马。”
她虔诚默念,相信自己的每句话池老医生都能听见,她的额头顶在地上,嘴巴亲着地上的泥土。她的吻直通黄泉。
仪式完毕,她对我说:“你再去看看,春仔还有没有在,看看有没有别的孩子欺负他。”
我趁机跑了出来,闷闷不乐地走到屋后的池塘边坐下。三两只在塘面飞旋的白鹭,意欲停落。我默默看着,我撒下的赤裸裸的谎言在心中堆积,不由眼眶湿润。以我的见识体系,我能感觉到地狱的判官已经在记账本上记下了我的罪过。
姨丈不知何时坐在我身边,握住了我小小的手。他收工回来,也得知了阴间的讯息,他默默的感激加重了我的愧疚。他拾起一块泥土,朝塘中停着的白鹭扔过去,白鹭受惊,起身翻飞。
“为什么要扔白鹭?”我问道。
“它吃池塘的鱼,胃口可大了。”姨丈说。
“可是它是最洁净的鸟,它会不会是最善良的人的灵魂变来的?”
姨丈不是很理解我的想象,不过我的说法终究启发了他,停了片刻,他说:“其实它是一种好鸟。一个池塘里白鹭突然云集,说明这个池塘的鱼病了,提醒人们要换水。”
哦,这种说法与我的直觉相通了。白鹭的洁净一定意味着某种东西。
姨妈做了几个菜给说我们吃,她瘦瘦的身子已经充满活力,在灶间灵活翻炒,眼里含着闪烁的泪花。我却怎么也吃不下,扒了几口。饭后我自己央求妈妈早点回家,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
从半山村出来走到山脚,依旧是尘土飞扬,拖拉机来往飞蹿。我默默无语,眼前出现一副图景:一个恶鬼被铁链锁着,赤裸着跪在地上,一把长长的剪刀,剪着它的舌头,它嘴里流着血,疼得已经喊不出来了。
走到山脚下,风拂着山上的草木与庄稼,喧嚣消失,尘埃落定,被姨妈烧掉的那片黑色的山清晰可见。
“妈妈,鬼被割了舌头会痛吗?”我打破了沉默。
我感觉一直沉默下去,恐惧会要走我的命。
妈妈低下头,惊叫起来:“啊,你脸色这么白!”
我没有回答,我不愿流露出我的恐惧。但我的一切写在脸上。我和妈妈对人生的全部认识,来自于《三世经》,那是讲前世、今世与来世因果报应的文字,三世人生都紧紧相连。一切罪恶,大的,小的,都会被记账,在轮回中接受惩罚,在地狱受刑图上具体表现。妈妈深知其中三昧,她无法编个话来哄我。她正正经经地认为,说谎是要被割舌头的,特别是我这种触犯阴间律例的谎。
以前我在夜里怕鬼怕黑,她抚慰说:“有妈妈的孩子都不应该害怕。”于是我的心就定了。现在,她连这句话也不敢说了,她无法跳出轮回报应的学说。
她紧紧拉住我的手,试图给我力量,不让我颤抖。但我无法控制,我加快脚步,觉得只有山上的众神才会给我力量。
到了榕树下的时候,一种力量让我突然挣脱妈妈的手,第一次贸然走进白将军的庙里。对着神像狰狞的面孔,我祈求道:“白将军呀,春仔究竟犯了什么罪,居然要死得那么恐怖?他那么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有点顽皮,都是平常不过的,却受到这样的惩罚,没有天理呀。即便他前世犯下了错,也不应该这么小就受到惩罚。阎王爷是怎么想的?他们家没有孩子吗?我知道,你不仅是个讲道理的神,还是打抱不平的神,请你到阎王爷那里说一句,肯定是他们搞错了,请他让春仔活过来,活过来!”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流利完整地说出这样的话。也许自从春仔死后,这样的质问就在我心中酝酿,今天在恐惧中一气呵成。说完,奇迹并没有出现。白将军还是一脸狰狞,目光炯炯。如果他有灵的话,一定听懂了我的每一句每一字。
树上几只白鹭突然被某种声音惊飞,在树荫间翩飞。我突然明白,白将军,就是白鹭化身的神,一定是个被人认为邪恶其实追求公平纯洁的神,它一定为世道不公而努力。
白将军肯定认同我的想法,难怪很早之前,我就觉得跟他心有灵犀。
妈妈愣住了,赶紧把我拖了出去,急匆匆往山顶走。在她的意识里,白将军还是喜怒无常的神。
我一路想,春仔这样的死是不公平的,那个主宰天理的神一定有失误。无论何时何地,人间或者阴间,我所到之处,我都要争辩它的失误,这是我现在能懂的真理,必须坚持的真理。这么想着,我好像找到一把打开恐惧的钥匙。
“啊——春仔,我一定让你回来,我们一起放牛!”我在山顶大喊了一声。
妈妈慌了,摸着我的额头道:“孩子,你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