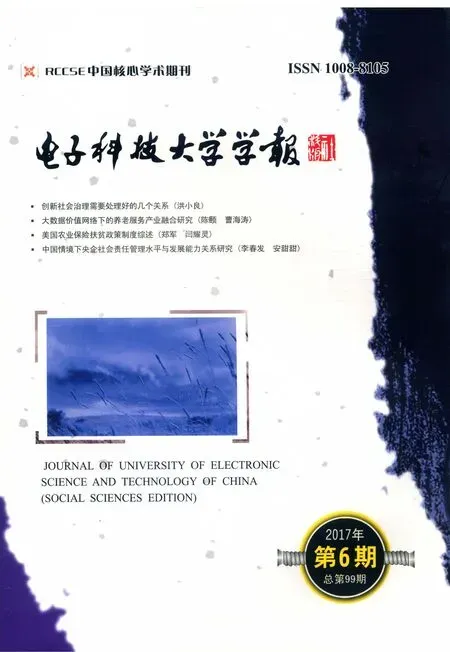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论王世贞的巫风思维
□崔 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 语言文学 ·
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论王世贞的巫风思维
□崔 颖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都能在巫文化中找到线索。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文化变革,使巫君所承担的神圣天命演变为儒士所应肩负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君的内涵,也由巫君合一转变为君子有德。身为儒士,王世贞认可巫王合一的文化传统,其思想彰显出巫风思维。首先,王世贞将君子之德表述为以儒立身的淑世情怀,因家国使命而与政敌抗争,因民生民瘼而忧心不已,因苍生福祉而为民请命。另一方面,王世贞推崇明君贤臣身上的巫特质。在与同时代士人的交往中,王世贞赋予儒士君子多奇的特征,从而使巫文化成为承接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转变的关联点。王世贞的巫风思维对其政治生命、世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其巫风思维,有助于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王世贞。
王世贞;巫风;儒家;君子
远古时代,巫君合一。周公制礼作乐,将巫的外在形式理性化、系统化。孔子释礼归仁,将巫的内在情感人文化、鲜明化。周孔二人对巫文化的改革使巫君所承担的神圣天命演变为儒士所应肩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王世贞肯定巫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对巫文化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就王世贞来说,巫风思维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广义的巫,即巫君合一观念影响下演变而来的巫儒品质。第二层是狭义的巫,即以祈福禳灾的干预术、望气观星的占卜术为核心的民间巫术。前者影响了王世贞的政治生活,塑造了王世贞以儒立身的巫儒形象。后者丰富了王世贞的世俗生活,呈现出细节化、具象化的文人风貌。王世贞在评价儒家士大夫这一群体时,往往记叙这些人的神奇经历,例如祷雨立澍、神灵护佑、孝感梦兆、灾异示警等,赋予士大夫精诚通灵、君子多奇的特质。可以说,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的文化演变,体现了由巫及礼的历史进程,也表露出王世贞的巫儒理念。
一、巫君合一
中国文明有许多特征,例如祖先崇拜、家族体制、中央集权、实用主义、乐感思想,这些概念从某一角度阐释中国文化。从远古至于今,中国文化保持着祖先崇拜的传统。“祖先生是人,死为神,或生即半神。无论生死,祖先(主要是氏族首领的祖先)都在保护着‘家园’——本氏族、部落、部族(酋邦)、国家的生存和延续。在这里,人与神、人世与神界、人的事功与神的业绩常直接相连、休戚相关和浑然一体。”[1]而实现这种相连、相关、一体的具体途径就是巫。巫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天地相通,民神异业。此时期民神不杂,民祭祀神,神庇佑民。第二阶段,家为巫史,民神同位。此时期民神杂糅,民不祭祀神,神不庇佑民。第三阶段,绝地天通,民神不扰。此时期重司天,黎司地,王祭祀神,神降意王。自绝地天通后,只有巫能够联系神界与人界,而作为政治领袖的王是最大的巫,表现出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的特征。纵观历史,上古的帝王,夏商周三代的明君贤臣,他们拥有发号施令的王权,又掌握沟通天人的神权。例如,颛顼拥有神权,命重、黎绝地天通。大禹会禹步,夏启擅巫舞、能御龙。商汤有汤祷,文王有天命。
除了君王,政教合一的传统也适用于贤臣。姜太公以阴谋秘术得国,宋儒斥责其异于道,王世贞为太公任术而正名:“凡太公之所为,多阴谋秘术见于《金匮》《六韬》诸篇者。……夫齐之后强于鲁而益远于道,谁使之,太公使之也。……太公而称功臣,则不得不任术。”[2]王世贞对太公的评价,既契合巫君合一的文化传统,又涉及道与术的文化差异。在太公所处的时代,巫的含义尚未有太大的分化,巫能通灵致神,巫会阴谋秘术,这是无可厚非的。其后周公制礼作乐、孔子释礼归仁,巫的内涵有了改易,一部分内容提升为以祭祀、礼仪为核心的儒家精英文化,一部分内容下降为以禳灾、占卜为核心的民间巫术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两条脉络。历史往往由精英把控,精英群体站在文化高点批判民间巫术,因而在宋儒看来,太公使用阴谋秘术,远离儒道。不同于宋儒脱离时代的历史评价,王世贞将太公置于其所处时代,以历史眼光还原太公的巫君形象。王世贞对太公的誉美,恰恰表明其巫君合一的历史思维。
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文化有儒家精英文化和民间巫术文化两条发展脉络,精英群体往往訾议巫术文化。是以身为传统儒士的王世贞并没有明确提及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是写下许多与巫相关的文字。剖析这些文献,可进一步了解王世贞的巫风思维。第一,祭祀、禳灾、占卜是巫术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均有具体的现实目的。这些巫术活动,或是为了解决民众的生产需要,或是为了摆脱个体的精神困惑。郎署决狱,旋风吹落狱舍之瓦,王世贞写下《告狱神文》,表明自己勤恳尽职之心,祈求狱神护佑是王世贞的现实目的。兵备青州,新神、旧神并存,王世贞撰写《祭城隍神文》以正视听,请城隍神庇佑民众是王世贞的现实目的。郧阳大旱,王世贞祈雨而降雨,以《谢雨文》感谢神灵,求雨是王世贞的现实目的。可见,在王世贞看来,巫术活动是有所求的,鲜明的现实需求是巫术活动的第一重特质。第二,巫术活动有一套极为复杂的外在形式,对行为、容貌、语言有严格要求。由于巫术活动繁复的动作与高难的技巧,即便是巫师祭司,也会遗忘、弄错一些细节,因而后世不断简化其形式,但核心的祈祷仪式是不变的。以祈雨而言,王世贞笔下的求雨仪式包含素服、斋戒、露身、为文等几个内容。郧阳大旱,王世贞“素服,却驺从,走坛所,为文而告之。”[3]王世贞在为温少谷写的墓志铭中,提到温公露身求雨的细节:“公斋三日而祷,立澍。公既露祷雨中,又以暑故不为雨具,寒内侵,遂得疾。”[2]温公斋戒三日,露身祈祷。露身有明显的献祭意味,祈祷者在烈日下灼晒身体,如果神灵体恤,便会降雨。旱灾求雨,要为文露身祈祷,同样的,水灾求晴,也要为文露身祈祷。杨九华止雨,“身露立城上,慷慨为文以祷。”[2]祈祷者在雨中袒露身体,任雨水浇打冲击,表露出献祭、自苦的决心,如果神灵庇佑,便会止雨。巫术活动发展至明代,虽然仪式内容有了变化,但对核心形式的坚守却是不变的,这是巫术活动的第二重特质。第三,巫术活动十分注重情感因素,参与者必须进入精诚、敬畏的心理状态。原始巫君在巫术活动中呈现出来的敬畏、精诚的情绪力量,逐渐演化为君王、贤臣的个体道德。这种道德具有献祭、自苦、惩戒的内涵,参与者除了要斋戒、素服、露身之外,更要相信神灵、敬畏神灵。随着巫术活动的流传,诚和敬逐渐内化为民众的自我品格。王世贞在《谢雨文》中写到:“爰借神休,脱我于责。诸二千石,黄墨绶吏。敢不涤心,以承神赐。”[2]谦卑的语气,皇恐的姿态,呈现出与神同在的心理模式。可见,巫术活动的参与者,在沟通神明时,必须保持精诚、敬畏的精神状态,这是巫术活动的第三重特质。
二、以儒立身
在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周公和孔子分别从形式和情感两方面改造巫文化。就巫文化的形式特质而言,巫术活动中的身体姿态、步伐手势、容貌语言,逐渐发展成一套体系。周公制礼将巫术体系系统化、理性化地改造为规范准则。这套社会准侧既包含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人事分配,又涵盖饮食起居、应对进退的个人行为守则。就巫文化的情感因素而言,孔子将巫术活动参与者精诚、敬畏的神圣心理改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以仁要求以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情感,从而使日常世俗生活具有神圣意义。经过周孔二人的改革,巫一方面分化为巫、卜、祝、医的专业职官,流入民间,形成以下层巫术为核心的中国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巫实现了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身份改变,巫演变为儒士,使巫君合一的根本特质,在以儒家仁礼体系为核心的儒家精英文化中保存下来。儒家精英群体往往批判民间巫术,并远离甚至忽略儒家文化中的巫特质。然而王世贞对儒家文化中的巫特质以及民间巫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王世贞与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稍显另类,展现出巫儒思维。
由巫及礼、由巫到儒,其实质就是把巫君沟通天人的神圣感转化为儒士心怀天下的使命感。王世贞倾向于以巫的视角阐释儒者生平,但最终的落脚点是以儒立身的淑世情怀,具体表现在政治抗争、忧心民瘼、为民请命三个方面。其一,王世贞反对严嵩专权,不满严党乱政,他通过诗歌与严党抗争,体现出以儒立身的政治情怀。明朝废除丞相制,君主高度集权,虽有内阁学士统管六部,但内阁也只是君主的附庸,承其旨意、仰其鼻息。在王世贞所处的时代,嘉靖帝常年不朝,却大权独揽,朝堂分为清流和严党两派。清流上疏指责嘉靖之过、朝政之失,严党大力打击清流、维护嘉靖权威。因而,为了维持政局平衡,嘉靖帝默许严党专权。作为明朝的臣子,王世贞虽对嘉靖帝的做法心有不满,但无力反抗帝王权威。再加之明朝士人的地位极其卑微,稍有不慎,则被下狱、杖毙。因而一方面,王世贞与严党直面抗争,另一方面,他又要顾及帝王形象和一己安危,多重权衡之下,王世贞选择以巫风思维引巫入诗,将严党比喻为祸国妖氛,以示自己对严党的抗争。嘉靖三十五年,王世贞出察京畿狱事,归京途中适逢燕中来者,诸人因得罪严党而遭罢官,王世贞同情其遭遇,也痛恨严党之无行,遂作诗讥刺严党。王世贞以巫入诗,将严嵩比喻为“上帝有弄臣,戏博太山巅”,将严党乱国比喻为“千秋绝至技,万象横妖躔”,燕中来者与严党抗争,却“争道误一叱,中谗堕风烟。”燕中来者的悲情经历,激发了王世贞的抗争精神,他慷慨激昂,有“叱羿射狂日,令娲补漏天”[2]的豪迈之志。王世贞对严党的政治抗争,其实质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为百姓争得一个政治清明的太平盛世,体现出以儒立身的淑世情怀。
其二,王世贞关注民生,忧心民瘼,展现出兼济天下、心怀苍生的儒者精神。原始农业时代,自然气候对农业收成有着决定性影响,农业收成又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风调雨顺,则国泰民安;一旦发生旱灾水患,粮食减产,则容易引发饥荒、暴乱、时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格外渺小。由于缺乏科学精神和自然常识,古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气候现象。在他们看来,天地中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由神灵精怪所控制,神灵精怪又能引发水旱灾害。古人的这种思维即巫风思维,王世贞也相信并实践着巫风思维。旱灾和水灾是王世贞诗文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旱魃引发旱灾,雨师带来水灾,这是王世贞对水旱灾害成因的一种思索。嘉靖二十八年,王世贞任职刑部。五月,京师大旱,王世贞写下《苦旱歌》[2],旱魃为虐,引发大旱,天地干裂,原草如烧。农家儿女日夜不停汲水,依然无力浇灌农田。王世贞忧心百姓,中夜不眠,坐待天亮,表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精神。嘉靖三十二年,京师春旱,王世贞认为此次春旱有两方面的原因,“女魃乘修虫庸,末途竟流焦。阴阳无赢胜,贵在得所调。”旱魃肆虐,是自然原因;阴阳不调,是人事原因。“燮理岂在隅,咎衅内惭招。亮深为牺念,敢以一身要。”[2]帝王失策,王世贞无力与君权抗争,只能一力荷担苍生之苦,一己承受天意之责,以求化解旱灾之祸,体现出兼济天下、拯救苍生的悲悯情怀,可谓以儒立身。
第三,如果说关注民瘼是王世贞的儒者情怀,那么,为民请命,则是王世贞的现实行动。王世贞以儒立身,胸怀天下,对百姓之苦感同身受。吴兴淫雨,王世贞不忍百姓遭受水灾,为文祭祀,雨水立止。郧阳大旱,身为地方长官,王世贞素服祭祀,大雨立澍。遇到旱涝等灾害,王世贞斋戒祭祀,祈求上苍归咎于己身,切勿施祸于民,这是王世贞的为民请命。力所能及地行动,即便力有不及,也不会偃旗息鼓,而是向执政者反映民情,这就是王世贞的为民请命。万历十七年六月,金陵大旱,太仓尤甚。王世贞致书王锡爵,叙及江南灾情,希望执政者赈灾救民,“尽蠲兑运之米,或蠲其半,而以其半减价改折”。内阁之中,政事复杂,人心莫测,“二三大老调剂甚难,言者主上未必信,左右未必喜,司农未必担当。”王世贞深知王锡爵处境之艰难,但他毅然向王锡爵请命,“然宗社之安危,万姓之生死,实系于此,若太平宰相谁不乐为之。”[4]王锡爵对王世贞一家颇有恩惠,世贞之父王忬得享恤典、世贞之子王士骐隶属兵部,皆乃王锡爵从中斡旋。因而,虽比王锡爵年长,但在与王锡爵的交往中王世贞却谦卑有礼。此封信中,王世贞一改平时的恭敬之态,以凌厉的语气劝示、敦促王锡爵。可以说,这封信是王世贞的请命书,蕴藏了儒者的情怀风骨和家国担当。在王世贞看来,为百姓谋福祉,为万世开太平,乃儒士之则,避无可避。因而,他为民请命,为民发声。
周公、孔子对巫文化的改造,完成了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文化过渡,同时,也使巫君的神圣感演变为君子的使命感。君的内涵,也由巫君合一转变为君子有德。君子之德指个体以兼济天下、匡救时弊为责任和义务。就王世贞而言,君子之德表现为以儒立身,因家国使命而与政敌抗争,因民生民瘼而忧心不已,因苍生福祉而为民请命。
三、君子多奇
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历史进程,实现了由巫君到君子的变化。巫君之君到君子之君,不变的是君。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像巫君那般精诚敬畏,保持与神同在的状态。这样,即使是在饮食起居、应对进退中,也能砥砺道德、涵养品性。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即为君子。巫君的神圣感异化为君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借此来赋予世俗生活以神圣意义。然而,儒家精英群体高扬君子之道,忽略甚至抨击巫文化。与主流儒者不同,王世贞肯定巫君合一的思维方式,认可巫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王世贞往往将历史人物还原至其所处时代,推崇明君贤臣身上所呈现的巫特质。在与同时代士人的交往中,王世贞赋予儒士君子多奇的特征,从而,巫文化成为承接巫君合一到君子多奇转变的关联点。
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和底色,虽然周公和孔子分别从形式和情感两个方面改造巫文化,但巫君合一的思维方式却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君权受巫文化影响,与王者之相、祥瑞异兆等神秘因素相关。另一方面,经历了由巫君到君子的文化转变,普通民众也可以具有神圣感。王世贞将这种神圣感表述为君子多奇:君子,即儒士的使命感和道德感;多奇,即儒士精诚通灵,与神秘因素相关,有神奇经历。具体说来,在评价有德君子时,王世贞往往引入神秘因素,从祷雨立澍、神灵护佑、孝感梦兆等几个方面彰显君子之德,刻画君子精诚通灵的形象。
自绝地天通起,只有巫君方可沟通神明。其后,周公制礼作乐,孔子释礼归仁,君权逐渐压倒神权。原本由君王所掌控的祭祀、占卜事务交由专职人员,随之有了巫、礼、祝、医等职官分配[5]。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祭祀礼仪,每天都有数目繁多的祭祀活动,君王不可能事事亲临,因而君王一般主持大型祭祀,而小型祭祀则由礼官代劳。在地方事务中,如果出现旱涝灾害、异象咎征,那么地方长官要承担责任,主持祈福禳灾等活动。原始农业社会,地方长官参与的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即祈雨。王世贞笔下的儒家士大夫,大多曾任地方长官。属地出现旱灾,长官有责任有义务要想出解决方法,他们往往通过求雨活动向神明忏悔,祈求神明降雨。如果降雨成功,说明地方长官有君子之德,神灵愿意护佑。
首先,王世贞以祷雨立澍标榜君子贤德,展现出巫风思维。在古代,地方长官能否求雨成功,直接关系其德行的评价。大城令忽君有贤德,祷雨立澍,王世贞写下四首绝句赞美忽君。具有巫风思维的王世贞将忽君塑造为精诚通灵的儒士,贤德感动上天,上天庇佑忽君及其治下百姓,惠降大雨。王世贞不仅在诗歌中赞扬君子祷雨立澍的美德,在为友人写的志铭中,往往记叙传主的求雨经历,以彰显君子之德。在王世贞笔下,温如玉“旱祷而澍,卒以勤死,合于古祀法矣。乃其临殁而约束郡邑,毋令污我为也,此何下结缨易箦哉?”[2]醴陵令胡古愚“诅于神,以幽明相质责,且请代民死,遂澍雨,岁稔。”[4]求雨立澍,是王世贞笔下检验君子德行的重要标准,也最能体现其巫风思维。
其二,王世贞以神明护佑誉美君子贤德,彰显出巫风思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神明昭昭,护佑君子。王世贞在为友人写的传记、墓志铭中,常常提到神灵护佑的事迹。在为张佳胤之父张文锦撰写的墓表中,王世贞提出“多奇”这一理念。张氏一族有很多奇异的经历,始祖张天性夜闻“吕奉里,宜孙子”而定居吕奉里,守拙翁求子土王祠而生张文锦。张公为度侍郎修墓复享,度侍郎以黄牛白马报之,度侍郎在黄牛峡牵引张妇之舟,在古白马地滑县保全张子佳胤性命。张氏一族的种种奇遇,使王世贞发出“甚矣,张之多奇也”[2]的感叹。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但不代表儒家不相信怪力乱神。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由巫文化精诚敬畏的精神传统一脉而来,并随着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进程而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祭如在的信仰模式到了王世贞这里,转化为君子多奇观念,君子有淑世之德,其德能精诚通灵,因而君子祭祀求雨,神明可达成所愿;君子有性命危险,冥冥之中,神明会护佑君子。王世贞在为友人写的传记中,多次提到神明护佑。萧秋岩“尝部诸生宿于江夜,有龙起,邻舟尽坏,而公舟独吹徙陆以免。”[4]在王世贞看来,萧公精诚通灵,神明保全其性命。
另一方面,君子具有浩然正气,这种气与天地同质同源,有神圣意味,可抵御灵怪精异。在为礼部右侍郎欧阳崇道写的神道碑中,王世贞提到欧阳崇道的奇异事迹:“归下峡,舟束于盘涡,欲覆,众呌号不已。公色自若,徐命取器物投之涡,杀其势。而会风怒薄舟于滩以免,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2]王世贞坚信,是欧公的大臣器量、凛然英气,吓走了水中精怪。从无神论的角度出发,神明护佑、抵御怪异这些事迹,大多为巧合,乃时人有意附会。从巫文化的视野来看,王世贞相信神明存在,相信神明会护佑君子,而君子精诚通灵的神奇经历,愈发彰显出君子的美好品德。
其三,王世贞以孝感、梦兆歌颂君子品德,流露出巫风思维。弗雷泽认为,巫术有接触率和相似率两大原则。巫术的相似原则,与中国巫文化的感应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感应在王世贞笔下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人感应,灾异示警。一类是孝感而应,表现为孝感心动、孝感生瑞、孝感有梦[6]。在孝道至上、以孝治国的古代社会,孝是衡量君子德行的重要标准。就孝感心动而言,君子心系父母,和父母心心相连,能感应到父母的身体状况。王世贞在为张幼于父亲写的小传中,盛赞张父之孝行:“君之母疾病,君祷于天,刲左股而进之愈。又行贾觉心动曰:‘大人得无有恙乎?’趣骑归,父则已困床第间待君而起。”[2]就孝感生瑞而言,父母归去,君子治丧甚谨,守礼甚严,神明为君子孝心所打动,降下祥瑞。王世贞在为太学生金塘写的行状中,提到金君为父治丧,“君哭毁甚,治丧,丧车且数千,两芝生墓者再,乡人艳称之,目其堂曰孝芝。”[2]就孝感有梦而言,君子侍亲甚孝,心系父母,君子以梦的形式感应到父母近况。王世贞在为申玉田写的墓志铭中,叙说玉田心系父亲疾病而有梦:“先生梦若帝语之曰:‘以而故赐而父生。’饮之青冰,矍然苏,呕秽血败肉数升,遂与贡士公俱起矣。”[4]申父病疽,玉田为父吸毒,毒发昏迷。神明为玉田孝心所动,托梦玉田,令父子痊愈。不管是孝感心动,孝感生瑞,亦或是孝感有梦,在王世贞看来,孝感而应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君子以孝德沟通天地神明,其孝心孝行感天动地,故能有感应、生祥瑞、感梦兆。在王世贞笔下,君子的孝心孝行,与感应、祥瑞、梦兆等神秘因素联系起来,赋予君子精诚通灵的特质,从而突出君子的德行节操。
梦的不确定性,赋予梦各种可能性,世人也往往将梦和神秘未知的因素联系起来,使梦在巫文化中享有重要地位。除孝感而梦外,王世贞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尚有出生胎梦、死前梦兆、日常所梦。日常所梦与占卜解梦有关,此处暂且略过。就出生胎梦而言,王世贞以胎梦的形式为君子的出生渲染神奇效果,证明此人乃非常之人,有非常之才。王世贞笔下的胎梦基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长辈梦到日月云霞等美好壮丽的自然物象,母体遂有妊生子,延续巫文化中感孕而生的神话传统,以突出君子多奇、君子才能。王世贞在为王守仁写的传记中,提到王守仁乃五色云所化:“有长者称母曰郑夫人当娠,而王母岑媪梦神人衮冕乘五色云下,抱一儿授之,惊寤闻啼声则已生守仁。”[4]王守仁实践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乃儒家君子之典范。王世贞以胎梦的神奇来印证守仁之勋业,彰显其君子多奇的巫风思维。王世贞笔下的第二种胎梦,是长辈梦到童子、贵人,母体乃有孕生子,君子乃神明所授,可以说,君子的出生即是精诚通灵的结果。在为潘允哲撰写的墓志铭中,王世贞提到潘家兄弟的出生经历:“公之生也,恭定公时为祁州守,曹夫人夜梦神人掖二童子,手丹桂如之,而以语夫人曰:‘大夫有功德于祁民甚深,帝嘉之用锡二贤子以昌大其门。’寤而产公,又二年而右方伯允端生。”[4]在胎梦中,潘家兄弟乃神人所授,以光耀潘家门楣。兄弟二人的出生梦兆,使潘氏颖异聪慧、为政有道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出生胎梦的描述,延续了巫文化感生和梦生的神话传统。王世贞借助梦这一特殊形式烘托君子多奇、精诚通灵的特质,从而为君子异于常人的才能、煊赫奇绝的功业找到合理的解释原因。
就死前梦兆而言,王世贞有意记叙君子死前的异象、梦兆,赋予君子精诚通灵、预知后事的神奇能力。在神秘因素的加持下,君子的德行品质愈加完美。王世贞在为彭年写的墓志铭中,记载彭氏预知归期的奇异事迹:“无何,彭先生竟不起。当彭先生不起,能豫为日,至日炷香以测晷且尽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2]彭年因时为迹,匠心成言,应不狥物,止不近名,有隐德之风。去世之前,能欲知化期,有精诚通灵之奇。王世贞在为沈懋学撰写的墓表中,提到沈氏的梦兆:“已梦昙阳子趋之去,又梦所奉关帅者亦趣之曰:‘不能为斯世挽先生,奈何?’先生醒而曰:‘已矣,不复有所为矣。’”沈氏师奉昙阳,又崇信关羽,其心甚诚,其行甚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因而沈氏梦到昙阳子和关羽催其化去。王世贞与沈君典感情亲近、往来颇多,沈氏以其真实经历向王世贞证明了精诚通灵的可行性,同时引发王世贞就现实和梦幻的真实性展开思考:“嗟乎!先生前后所梦,真耶?幻耶?岂幻者真,而真者幻耶?抑真与幻皆梦耶?”[4]沈氏的梦兆令王世贞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也坚定了其巫风思维。
身为儒士,王世贞推崇君子之风。王世贞笔下的君子大概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有突出政绩的贤臣。这些贤臣中的文臣为官一方,关注民生,忧心民瘼,为民请命;武将护卫属地,破贼剿匪,平乱戡正,保境安民。文臣武将,亦或文武兼备的臣子,他们德行美好,令名远扬。冥冥之中,神灵护佑,因而君子能够祷雨立澍、保全性命、孝感有梦。第二,以文采扬名的儒士,出生伴随着祥瑞胎梦,梦中的日月云霞象征君子日后的绝世文采。第三,以德行名世的素衣,这部分君子或是科举不利,或是不愿仕进,但孝侍父母、雅好诗文,王世贞颂扬其隐德之风。这三类君子不管是宦海仕进,还是隐于江湖,职属虽有不同,但对君子之德的坚守却是相同的。为了最大程度地突出君子的品质操守,王世贞引入神秘因素,以巫风思维叙述君子的神奇经历,从而使君子多奇、精诚通灵的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王世贞以君子多奇的视角撰写君子生平,既契合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文化进程,又延续其巫君合一的巫风思维。王世贞对君子的刻画,以刻画、颂美君子之德为核心,也表明王世贞身为儒士的立场与诉求。
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都能从巫文化中找到根源。身为儒士,王世贞的思想彰显出巫风思维。首先,由巫及礼、由巫到儒的文化进程,使巫王合一的特质融入到儒家思维。同时,巫王与天沟通的神圣感也演化为儒士兼济天下的责任感。王世贞肯定巫王合一的巫文化思维,并将其贯穿到以儒立身的个人品行中。其二,王世贞赞美德行美好的君子,并从精诚通灵的角度塑造君子多奇的形象。王世贞的巫风思维对其政治生命、世俗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分析其巫风思维,有助于后人更全面地了解王世贞。
[1] 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5.
[2]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Z].明万历年间世经堂刊本.
[3] 王士骐, 等.王凤洲先生行状合编本[Z].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4]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Z].明崇祯年间刊本.
[5] 刘黎明.灰暗的想象——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巫术信仰研究[M].成都: 巴蜀书社, 2014.
[6] 李零.中国方术考[M].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7] 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M].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8]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9]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0]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1] 柳存仁.和风堂文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编 辑 邓婧
Divine Shaman and Magical Confucian: The Study of Wang Shi-zhen’s Shaman Thinking
CUI Y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Shaman culture is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where you can find many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The cultural change from Shaman to Confucianism made the sacred fate of the monarch evolved as the Confucian’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At the same time, the connotation of gentlemen changed into noble character from divine psychic ability.As a Confucian, Wang Shi-zhen recogniz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Shaman.First,Wang Shizhen expressed the gentleman's virtue as a Confucian’s love and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therland and people, so that Wang Shi-zhen protested against his political opponents, worried about the people suffering, fought for the people’s benefit.Wang Shizhen admitted the Shaman character of the monarch and courtiers.In the exchanges with contemporary people, Wang Shizhen found the magical attributes of Confucian, so that Shaman culture became a point of association in the divine Shaman and magical Confucian.Wang Shizhen's Shaman thinking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 political life and secular life, and analyzed the way of his thinking could help future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Wang Shizhen more comprehensively.
Wang Shi-zhen; shaman; confucianism; confucian
I206.2
A
10.14071/j.1008-8105(2017)06-0101-06
2017-09-20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12amp;ZD159).
崔颖(1988-)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