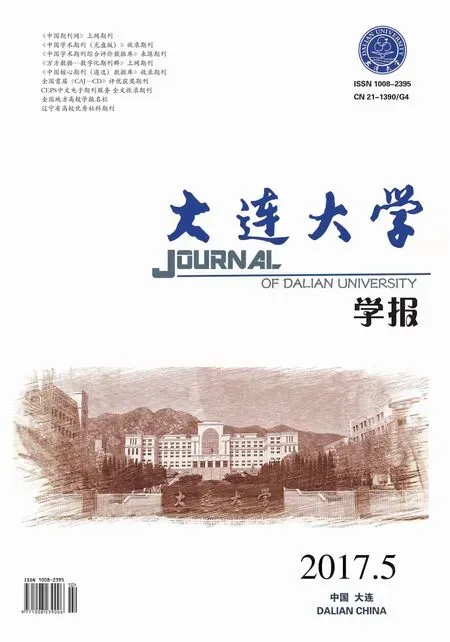笔下论语译不孤
——汪榕培《诗经》英译“非常论”集萃
蔡 华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笔下论语译不孤
——汪榕培《诗经》英译“非常论”集萃
蔡 华
(大连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译介人士译作等身者,常因翻译有道而付诸笔端。作为《诗经》最新全译本译者,汪榕培教授数次撰写专题文章,纵横捭阖地类分、比读中外《诗经》英译道法,其定量定性的非常论,遂成为典籍翻译研究与批评领域借鉴性常识。
《诗经》英译;译例并置;比较性译论;复译思维
汪榕培是中外《诗经》英译当下最新译者。他写的《诗经》译介专题文章计有7篇,基本上是在他的《诗经》英译本出版之后。其时,1994、1995年见证了他4篇文章依次发表在主流学术刊物《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与《外国语》,代表着翻译领域与“诗经学”体系之间的交叉与互鉴态势,在多个层面产生了影响。及至他为其《诗经》译本收录到《大中华文库》再度述怀为序,先于图书于2007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述文章书写着汪榕培十余年间翻译思考,体现了他的翻译实践在定位上的笃定与娴熟,在境界上的思辨与开放。
纵观此等撰文,几乎篇篇都不乏中外《诗经》荟萃比读的内容。特别是“漫谈”“殊途同归”与“说东道西”等篇目中就有整合与比鉴的方法论导向。在分头梳理前,有必要先交代汪榕培关于《诗经》英译的总体视域:自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出现《诗经》英译本以来,其译介形式不断演变,多元共存,而理雅各(James Legge)的散文式直译,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的韵译,韦利(ArthurWaley)无韵体翻译以及庞德(Ezra Pound)的自由译,都是主要代表。汪榕培的《诗经》视域中,中外英译译况一贯比对而出。他在“漫谈《诗经》英译本”一文中,严格区分《诗经》英译类型时,举隅许渊冲、杨宪益教授为本土佼佼者代表,与西方译者相提并论。
作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大中华文库”《诗经》版译者,汪榕培本人在研读中外《诗经》译本的过程中,体验经历了诸多观感、判断与反思。它们初散落于汪榕培各处文章中,后集萃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中,进一步引起相关学界的深度关注。
国外英译中国典籍人士,学者出身者为数众多,这一类译者长于实地调研、汇总创见,其译作往往结晶为“厚”翻译类型的译本。在中国译界,译而言的传统传承中,实践的译者常常译往而言出,形式上从点到为止,到长篇大论,参差不齐。显而易见,这种言论具有描写翻译学的性质,无论是凝练的论述,还是密集的描述,要么是由译而发,要么是举一反三,它们集合一处,与“厚翻译”译介现象分而治之。显然,与附着于译文本、与译文互文关系的“厚翻译”不同,处于译文本之外的译学言论与译文之间则是对象与研究之间派生性质的研究关系。如果说“厚翻译”译者往来无白丁,那么“功夫在诗外”译者则“谈笑有鸿儒”。典籍英译领域的汪榕培教授就是一位厚积译本,薄发译文的译介鸿儒。观其典籍英译众文本,“洁译”体例是常态的形式。所谓“洁译”,即译者专注于译文正文本身,鲜有注解、旁白、补记、附录等任何译文以外的译者表现,与读者谋面的唯有与原文匹配而出的译文呈现。换言之,译者将阅读完全放开,让读者自行其是,这岂不是传播文化、丰富阅读的非常道。
汪榕培始终以“洁译”自治,无意苦争译,然而他撰写与其翻译及翻译对象相关的文章时,罗致中外互鉴,举一反三时毫不吝惜笔墨,属意形影神。在汪榕培著述中,《诗经》是汪榕培翻译撰文中的高频词,多达127例,毕竟《诗经》英译复译的繁密现象是汪榕培英译中古诗歌其它几则对象不能企及的。涉及到英国译者理雅各的说法累积几十例,其中一半的措辞语境基于理雅各《诗经》译本而发,这种跨时空的观察与思考所云,理应为《诗经》译本读者所知所议。先从汪榕培最近的《大中华文库》版序言文章倒叙说起。
例文1《诗经》的英译——写在“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即将出版之际
汪榕培的这篇文章首次刊登在《中国翻译》(2007(6):33-35)。因《大中华文库》具有对外推广的属性,汪榕培文中多次以理雅各经典翻译为译介背景进行对比,这样的“谈译录”弘扬了理雅各《诗经》译本在中国的经典性影响,同时,也是一种中国同行存异立译,积极介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态度。
“西方出版的《诗经》译本对于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诗歌的悠久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译本出版年代较远,未能体现《诗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加上译者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局限、当时诗风的影响,未能完整地体现诗篇的真正内涵。我国译者有责任担当起重新翻译的任务,使英译的《诗经》能反映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思想面貌和诗歌特色。”[1]90
汪榕培坚持发挥本土译者的优越性,在“本位观照”(王宏印用语)的局域中,对比论述在“原汁原味”与“洋腔洋调”之间进行维新的或然性,“传神地达意”适时成为变或然为存在的翻译指南与操作策略。以此为纲的翻译原则与汪榕培的目的读者定位密不可分。与西方学者、汉学家的翻译动机不同,汪榕培自觉转向英语世界大众读者群体,因此,译介不采用考证性质的注释方法,吸引目标读者直接阅读译文本。为此,汪榕培始终运用其提倡的基本翻译原则“传神地达意”。“传神地达意”可以一分为二地展开理解:
在汪榕培看来,“达意”是其典籍诗歌英译的出发点,诗篇的理解和阐释是译出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中国古诗素以“诗无达诂”著称于世,本土译者在译文中担当着民族诗篇的解析与传播使命。于此,汪榕培举例“国风”首篇“关雎”首联的典型英译译例,进行比鉴,体现本土译者的翻译认知特色:
Hark! From the islet in the stream the voice
Of the fi sh-hawks that o’er their nests rejoice!
From them our thoughts to that young lady go,
Modest and virtuous,loth herself to show.
Where could be found to share our prince’s stare,
So fair,so virtuous,and so fi ta mate?”[1]91
汪榕培认为,西方译者,如理雅各,以经书释义“歌颂后妃之德”为会意基点,对比给出本人最新英译,其中原典旨意的坚持,对英诗体制的运用触类旁通。“在他们的译文中,描写的对象都是‘lady’‘prince’或者‘lord’。我们认为,‘国风’为经文人整理的民间歌谣。这里是一首情诗,用水鸟之间的相互唱和,比喻男子对倩女的爱慕之情,所以,我们的描写对象是,中国古代的结婚年龄—般在十六岁左右,其它的理解区别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译诗中都有体现”:
The Waterfowl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
A lad would like to woo
A lass with nice and pretty look.”[1]91
对比看到,中西方两译的会意截然不同,仅仅诗眼的译词lady与Lord,lad与lass,就集中反映了中外译者“达意”反应方面,天然地存在着文化时空差异,理雅各的韵体翻译之差是西方英译出现整体内容偏差的冰山一角。因此,中外“达意”互鉴始终是必要的,以利于《诗经》复译的长译久治。
按照汪榕培个人的理念,“达意”宜是“传神地达意”,没有“传神地”“达意”,也不是理想的翻译。在汪榕培看来,理想化的“传神”是传递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意蕴的统一体。从这个规范形态观察汪榕培、理雅各英译《诗经》“郑风”篇“将仲子”,区别一目了然。汪榕培之所以举此译例,是因为作为复译者的他看到了前译者的翻译基调与原诗不相符。理雅各起句“I pray you,Mr.Zhong”中Mr.Zhong书面语的腔调和诗中部的重言,使得原来诗文中营造的世风民情特色瞬间遭遇屏蔽。汪榕培在复译中,顺其自然地规避了这一再现误区,直截了当地化解为地道的英语表达“Prithee,my dear sweet heart”,借助下文中代词you的呼应,原文自在的少男少女青梅竹马的小调,形式与意蕴,瞬间兼而得之。
由此可见,从“传神地达意”的翻译认识与反应角度来看,理雅各与汪榕培个译中反映的中外译者差异,不单单是个别译者的个别现象,其普遍性在历时的典籍英译中是一种客观存在,本土译者在予以修订翻译之际,要注意入乡随俗的分寸感。汪榕培所译就的中古诗歌,预示着一种中学西用的趋势与刚需。鉴于诗歌本身,是集语言艺术、审美情趣于一体的表情表意文学体,那么其外在主要形式,如诗节、律动、气韵、隐喻方面,总会因共情而有所共鸣,此时,因再现诗性而置换甚至补偿,都是值得尝试的翻译述求。为此,汪榕培精选文人作为的“小雅”中的“采薇”最脍炙人口的联句进行对比分析,前者为理雅各所译,后者为汪榕培本人英译:
At fi rst,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1]93
When fi rst we took the fi eld,and northward went,
The millet was in fl ower; — a prospect sweet.
Now when our weary steps are homeward bent,
The snow falls fast,the mire impedes our feet.
Many the hardships we were called to meet.[1]93-4
能够将个人英译与经典《诗经》英译并举的译者,绝非意气译事。作为复译者,汪榕培不仅研读理雅各译本,而且通读了几乎所有的《诗经》英译本,因此,他的见解表达可以说是既译出有因,又高屋建瓴。他认为,虽然理雅各译句中显示着斯宾塞诗体ababbcbcc韵式,仍与原诗每联一唱三叹的婉约风格相去甚远。不仅理雅各译句的声韵传神差强人意,而且其毫不留白的填补性翻译,使原诗句不确定诗意的想象空间局促起来,意蕴传神几乎消失殆尽。
也是在这篇专文中,汪榕培在书写与理雅各《诗经》译文互鉴的行文中,笔锋时常接轨“传神地达意”。处于“洁译”主导的译介模式下,汪榕培“传神地达意”的译介原则始终如一。在举凡《诗经》风、雅译例的同时,汪榕培也选取《诗经》“颂”篇“清庙”进行例说。原诗主题“清庙”在理雅各与汪榕培对应译诗中都移就到位,但诗歌语境既视感明显不同。理雅各的the ancestral temple in its pure stillness,与汪榕培的the sacred temple,一个清雅,一个凝重,前者理译因其be动词的搭配关系,愈发静穆;后者汪译因不及物动词stand的组合,愈加肃穆。“传神”与“达意”对比感更突出的是对句“济济多士,秉文之德”。理雅各译句Great was the number of the of fi cers/All assiduous followers of the virtue of king Wan.[1]96“达意”过度超载(如of fi cers,followers)居高不下,“传神”在其母语的统摄下也不逊色。汪榕培译句A crowd of ministers gather round/For Lord Wen’s virtues are profound.[1]96传递了原文简洁的诗品,但“传神达意”宗旨有得有失。“文王”译词Lord比较理雅各King更贴合原诗历史原貌,此为偏得;失的是叠词“济济”译语a crowd of在语意张力上不及理雅各great was the number of的变数。不过,殊途同归的是,中外译者统一译就出“清庙”自带的静谧与神秘特色。总之,与西方《诗经》翻译的代表译,即理雅各的散体译本相比,本土译者汪榕培以《诗经》本义为本,以英诗为媒的演绎方式在保留民俗性优势的同时,也显出了独特的英译媒介态势,惠及双语读者。
显而易见,在这篇文章中,汪榕培时时处处以并置理雅各与其《诗经》译例,据此不断地比附比较译论,质疑国外经典翻译有礼有节,译论翻译推陈出新有理有据,预示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本土学者应有的姿态与风范。汪榕培的这种比较与发现的译介思维不是朝花夕拾的奇思妙想,而是厚积薄发的译介宣言。他在汉译外方面体现的文化自信、译介商榷由来已久,从时间顺序来看,他最先的阐释见诸于——说东道西话《诗经》—从“关雎”谈起。(现代外语.1994(4):58-61.)
例文2说东道西话《诗经》——从“关雎”谈起
在汪榕培翻译研究其他的撰文中,理雅各其人其诗屡屡跃然纸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近出《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全书中,“理雅各”中文名累计19例,英文名字达25例(包括中英双语名字并置)。当理雅各《诗经》译例出现时,多以其“散体译本”面貌举凡比鉴。显然,在汪榕培看来,理雅各《诗经》首译散译本比后来韵译本的影响更经典而深远。汪榕培向来认为译者译本的第一首译诗是最经得起翻译推敲的,故在“说东道西话《诗经》”文中,他便以“关雎”为例,和盘托出理雅各散体译本的全诗。于此,汪榕培针对全诗五个诗节,一一细致入微地描述与论述,给出的“忠实至致”、“逐字的翻译”说法,不仅与理雅各自拟“一分不增译,一分不损减”的翻译标准不违和,而且贴合《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72-1901)主持编辑欧德理所说的理雅各对自己《诗经》英译工作“几乎到了挑剔的地步”[2]的盖棺定论。汪榕培这样的翻译判断也确实是理雅各《诗经》译文与其他后来英译文本的一个经典的常规性比较视点,甚至也是以理雅各译本为底本的国外《诗经》英译本,如詹宁斯、艾伦、庞徳重译本中“译差”考辨的权威性参考底本。
无论汪榕培如何摆渡东、西《诗经》译介实况与个中译理,显而易见,在他的《诗经》英译整合与归纳的视阈中,理雅各始终是一位可进行多视角比较的经典译者对象。中国文化以译介为媒介走出去的进程,是依托译语中植入文化阐释的流变过程。这方面,理雅各《诗经》1871年译本的文化阐释、1876年译本的语言移就,既吸引到国外译者频繁复译,也影响到理雅各《诗经》英译期待的专业读者,还拓展到普通英语读者中间。一句话,东译西译,译者有为,道术未裂,这是《诗经》自身经典性超语言认知的开发结果,也是跨时空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实况。
例文3殊途同归译《诗经》——《桃夭》英译比读
汪榕培的这篇文章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外国语》(1995(2):52-55)发表。虽然汪榕培认为东西英译《诗经》有别,但他始终认定,彼此之间的翻译并非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汪榕培再一次与理雅各具体译诗进行对比研究时,“桃夭”成为他选取的译例,成为其梳理立论的论据。他总结道,英诗四行诗(quatrains)与原诗诗体可以对等,因此,理雅各的《桃夭》译诗呈现为三节四行诗:
The peach tree is young and elegant;
Brilliant are its fl owers.
This young lady is going to her future home,
And will order well her chamber and house.
The peach tree is young and elegant;
Abundant will be its fruit.
This young lady is going to her future home,
And will order well her house and chamber.
The peach tree is young and elegant;
Luxuriant are its leaves.
This young lady is going to her future home,
And will order well her family.[1]109
理雅各译引起复译者汪榕培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译诗基本上是分行的散文,既没有使用节奏,又没有使用韵脚,但是读来十分流畅自然。”[1]109此言在界定理雅各极致“忠实”翻译的同时,似乎也在致敬此译别具“传神地达意”气质,如贯穿译诗全部三个诗节的四行译句中,原诗句“桃之夭夭”与“之子于归”的复沓完全再现之余,原诗句“灼灼其华,有蕡其实,其叶蓁蓁”在英译中有所破相,原来的表述句法结构破格地升格为整齐划一的英语倒装句,期间,修饰语与中心词匹配毫不错位凌乱,译入语的文辞特点喧宾却不夺主。此译诗有破有立,为“殊途同归”立论的非典型佐证,值得关注与推敲。所谓“殊途”,理所当然地意指理雅各等不同时空中的外国译者的英译形式各异,而“同归”则指各个译者形式不等,并没有影响到英译内容尽量切向《诗经》原文,当然,切合的重心与程度存在着一定的视差。
从发表时间上看,该文是汪榕培“说东道西”之后跨年的翻译再认识篇。文中,字译的翻译形式在翻译视阈中的阅读维度在扩大,如“读来十分流畅自然”的说法,此外,汪榕培也在重申首个全译本、重译本依据等阅读之外的翻译地位与影响因素。的确,汪榕培视理雅各译本为标准译本的意识正是他时常参照的译介前见。此外,汪榕培教授细读其他英译者《诗经》译本的目的主要为“推陈出新”进行重译服务,毕竟,汪榕培的英译总体目标在于“反映当代我国学者《诗经》研究的新成果……在中西前辈的基础上有所前进。”[1]116
例文4传神达意译《诗经》
上文中,笔者将汪榕培“说东道西”与“殊途同归”隔年的两篇文章首尾相接,予以论述,主要基于它们内在的翻译阐释逻辑。回到时间纬度的就是这一篇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4):11-15)上刊登的撰文,这是汪榕培第一次书面化、正式地将其典籍英译的翻译原则与其诗歌正典英译结合起来的专文。文中涉及诗歌英译“传神达意”的讨论。就“以诗译诗”“传神地达意”的表征而言,要创造原诗生动逼真的原生态形象,还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诗的风格。理想的形式要求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都尽可能相同或相似;尽管从具体操作实践来看,形似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例如《诗经》“螽斯”的中外英译: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这首诗由三个诗节组成,每个诗节的一、二、四行是三字句,第三行是四字句,每个诗节的韵式为“xaxa”。
下面是James Legge的译文:
Ye locusts,winged tribes.
How harmoniously you collect together!
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Should be multitudinous!
Ye locusts,winged tribes.
How sound your wings in fl ight!
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Should be as in unbroken strings!
Ye locusts,winged tribes.
How you cluster together!
Right is it that your descendants
Should be in swarms![1]118
“这个译文是分行的散文,每个诗节的行数跟原诗相同,但既未考虑音步,又未考虑韵律,连自由体诗都算不上,离形似是有很大距离的。”[1]118显然,汪榕培不断地从音律两个角度来视察理雅各的散体《诗经》译本,即使理雅各的韵译本在诗体译诗的音律方面有相宜的表现,但不同体式译介的译文,对比相对比较,在几率和程度上都更直观,也更易于总结出真知灼见。于是,相比之下,汪榕培“传神地达意”原则演绎的译文有的放矢地进化着:“汪榕培的译文中每行末尾音节都有韵脚,其韵律安排是abab,整个诗节结构严谨,音节铿锵,韵味无穷,再现了原诗的美感。如此绝妙的规律说明译者对原诗的深刻理解和透彻的研究及译者深厚的英文功底。”[3]《诗经》依旧在,英译各不同,当下创新译,有待后人说。
对比而言,汪榕培在典籍诗歌英译方面,孜孜以求地以“诗体译诗”为媒介,落实“传神地达意”的翻译主张,而这正是散体译诗体制与践行都无法企及的。
例文5漫谈《诗经》的英译本
顺应时间序列,汪榕培此文在例文4后发表,隔年同见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3):40-43)。该文中,汪榕培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于《诗经》前译的梳理与界定,如James Legge是“学者型”译介;William Jennings是“半形似型(韵体)”代表;Ezra Pound是“神似型(自由体)”类型;Arthur Waley可为“半形似型(无韵体)”方面的垂范;许渊冲则是“神形皆似型”的佼佼者。汪榕培此等分类已经在典籍诗歌英译领域先声夺人,引起广泛共鸣与相关讨论,同时,该范畴认定对于典籍是复译实践,也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翻译指南。
名为“漫谈”透视着学者的儒雅与谦和,行文中,汪榕培丝毫不怠慢《诗经》英译本的专题译论。正是在这篇学术论文中,他严格地区分《诗经》英译者的类型,理雅各名副其实地成为“学者型”代表,而汪榕培此前论述理雅各“忠实”的观点此时更有了有的放矢的立足点。作为主张并实施“洁译”的类型译者,汪榕培感喟于理雅各的“功夫在诗外”的学术态度与作为,其“逐字翻译”的译法不再是理雅各“学者型”译介的唯一昭示所在,更常为人知的是,理雅各《诗经》初译版林立的“副文本项目”彰显着学者大家的译而研翻译惯性铁律。此文中,汪榕培以被东晋谢玄誉为《诗经》中最佳诗句,即《小雅·采薇》第6章中的八句为契机,评议理雅各的散体译文为忠实再现原文字面意义的译介典型,这样的看法在汪榕培书写《大中华文库》版《诗经》序中旧话重提,应该是作者有心在将其英译走向英语世界之际,与英语读者沟通最好的方式就是与其译介前人典范对话,认定并有所创见的译介态度与表现,译有创译无定译,复译者了然于胸。
汪榕培笔谈《诗经》英译的数篇文章,发表时间分前后两个时段。《大中华文库》序文除外,余者数文时段集中。表面上,前段各文文脉呈现着从“说东道西”到“漫谈”的散论路线;实际上,“说东道西”并非无稽之谈,“漫谈”亦非闲言碎语;中间时段的“殊途同归”与“传神达意”两篇文章之间关乎译道的“互文”现象绝非空穴来风。前文中“从七种译本的表现形式谈起,进而论及其它艺术手法和文本理解上的差异。”[1]108篇首语与后文中“译诗的标准可以多种多样,但是,从根本上说,‘传神达意’四个字就足以概括。”[1]126此翻译总则在后期撰文,即十余年后的大中华“序言”文中仍余音不断:“我们的基本翻译原则是‘传神达意’,更准确地说是‘传神地达意’。”[1]90时段不等、各有题中之义的数文集中起来,不失为汪榕培发散《诗经》英译脉络,指向古典传统到现代研发的译介思维学术共同体。其中,瞬息万变的译介时空因素,随主沉浮的中外译者争鸣等,种种翻译经典问题于无声处听惊雷,而乐在其中的汪榕培,在其翻译主张、翻译对象、翻译标准之间游刃有余,译例举凡频“传神”,说理叙译皆“达意”。综上,各文共享的鲜明特点正是以下“三观”:
其一,中外译文客体比对细读。汪榕培每每提到理雅各《诗经》译本时,主要援引其1871年散体译例进行必读。面对专门运用韵体译方法英译过《诗经》的理雅各,汪榕培此举特别耐人寻味。一贯主张以诗译诗的汪榕培大部分论述中,往往选用理雅各散体译例为比较阐释的媒介,其中原因无外乎凸显彼此翻译立法的大不同。各英译《诗经》为复议者如此重用,这绝对是理雅各译介为本土译界接受层面的专业性体现。作为后来译者,其叙理中明显以“后视性”视阈行使着前瞻性判断主体性:“我一直对汉诗和英诗都很感兴趣,涉及汉诗英译却是近年来的事情。翻译理论中的‘信、达、雅’到了具体译诗的时候好像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抽象,Tytler的翻译三原则白了。倒是Theodore Savory的话给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只有以诗译诗,才能更忠实于原作的形式,更好地保留原作的格调、韵律以及各种不同的形式等。’当然,Savory在这里更多地是在强调形式,形与意的结合是译诗难于其它翻译的关键所在。”[1]105如此说来,“传神地达意”此时具有了“以诗译诗”的译介新思维内涵。因着这样的译介导向,汪榕培严格以“转益多师”自律,但显然不似“厚翻译”类型译者那般,耿耿于怀于译文内的考据与解析,建构了中国典籍英译的洁译“普通读本”,其形成的译文直击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平衡与转换。也因为如此,汪榕培随即笔谈其译其评的做法属于“功夫在诗外”的外副文本(热奈特术语)写作,而译本译者亲笔所作的外副文本内容不失为非译者外副文本作文的第一手考据语料,也自然是业内专业读者不会错过的元文本援用对象。
其二,译者主体译介言说以中外译例为本的比较论述。上文若干例文大体上随汪榕培《诗经》初版译本发行后发表,集中反映着译者对其中古典籍诗歌英译“首译本”采取的翻译与研究并重的译介方式。无论汪榕培如何编选国内外英译对比,理雅各译例是永远在场的国外代表译者。汪榕培始终以理雅各文化译介来定义其译本形态与功能,身为当下《诗经》的复译者,他占有“后出转精”翻译资源的同时,坚持自我定位与译为的路线,如其《诗经》“关雎”前四句“诗体译句”The waterfowls would coo/ Upon an islet in the brooks./A lad would 1ike to woo/A lass with pretty looks.浓墨重彩之余,汪榕培拓进叙理,以强化其译介之道可道。即使全力译之,汪榕培对其《诗经》英译仍秉持开放的态度,他表示:“有待倾听专家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1]118纵观汪榕培5文中,汪榕培时时处处以比较的方式架构译论素材。首先从《诗经》译例比读的角度看,“关雎”、“桃夭”与“螽斯”居高不下,而“关雎”分别从形式“传神”(见“说东道西话《诗经》”文)与内容“达意”(见大中华文库“诗经序言文)在两篇不同文章中复现,足见其译介阐释功能的多样性。其次从译者的层面看,国外的理雅各、韦利与庞德遥遥领先;国内的杨宪益、许渊冲首当其冲,于是,中外“双关”译介对比不是单一片面的一言堂,群体症候与规律性一言九鼎。
其三,上述专文本质上围绕《诗经》复译主题展开,是汪榕培针对《诗经》复译现象的反思与总结表征。据此,复译的意义不再仅仅是理想的、吐故纳新的进化范式,而常常是伦理的、兼听则明的比鉴模式。“中国诗学是一个涵盖极广、蕴含极丰的研究领域。”[4]因此,英译此中的中古诗歌自然是一门蕴含深广的显学。“译而优则论”的汪榕培在其《诗经》英译专题文章中,一直运行比鉴的诗话方式来推演、解析其译介观察与思考,译例与译理翔实服人。既能够实地比读有物,又能够归纳总结得法的言说者非资深复译者莫属。汪榕培以《诗经》当下全译复译者的身份,常年书写着中古典籍诗歌翻译的诗话新知,无疑是后来译者阅读“翻译前见”,引以为鉴的复译箴言。
汪榕培英译之际坚持自律,复译之余坚持自省:“国内外探讨诗歌翻译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完整体系,多数有关诗歌翻译的经典名言都是属于诗话的性质,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1]325这样的译介思维与表达方式,与本土思维传承的代表,如写作《中诗英译比录》的现代语言学者吕叔湘,提倡“点染法”的翻译家瓮显良一脉相承,各抒己见。汪榕培感悟吕叔湘“诗体译诗”之“流弊三端”之说,理解吕叔湘所说的“平实与工巧之别”[5]13。汪榕培也感遇翁显良“欣赏才能再现的译介心语”[6]同理,汪榕培依托于译例相互之间的种种生发,其译介之道“非常论”(1992年提出)乃因同样的因缘契机,势必对中古诗歌英译译论剥茧抽丝,鞭辟入理产生应有的影响。存心的专业读者,自会发现吕叔湘“比录”中选取的7首《诗经》诗篇英译比对译例中,每一首诗英译译者群体中,都有理雅各其名其译,其曝光次数与频率不亚于汪榕培专题研究撰文中所列的理雅各译例之密度(汪、吕译例交集篇唯有“关雎”),学者谈译略同的复乐园,吾等闲之辈,得入内,幸哉!
[1]汪榕培.汪榕培学术研究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2]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M].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3]岳峰.略论《诗经》英译的韵脚处理——《小雅·采薇》译文的启示[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54.
[4]王小舒.神韵诗学论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5]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
[6]翁显良.意态由来画不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69.
Surviving the Paratextual Comments:Wang Rongpei’s Collection of Contextual Integrity Regar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ijing
CAI Hua
(School of English,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It has been a universal practice of actual translators of Shijing to compose experimental findings and analytical arguments.Being the translator of the late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ijng,Wang Rongpei’s exceptional narrative accounts arenormative referenc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and criticimssimply because of his quantitative comparisons and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s.
English retranslations of Shijing; parallel exemplific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retranslational implications
H059
A
1008-2395(2017)05-0079-07
2017-01-08
蔡华(1965-),女,博士,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