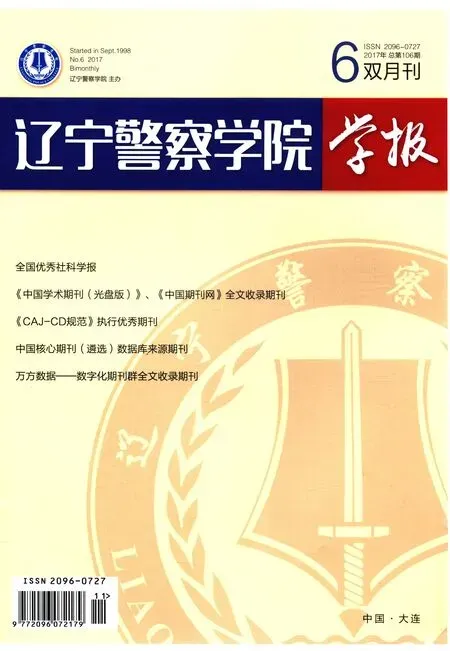网络教唆他人自杀犯罪的防范对策研究
--以“蓝鲸”死亡游戏为例
何炬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8)
网络教唆他人自杀犯罪的防范对策研究
--以“蓝鲸”死亡游戏为例
何炬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8)
“蓝鲸”死亡游戏,源于鲸鱼搁浅的自然现象,实际上是一款通过社交媒体,引导游戏参与者完成自伤自残任务,最终走上自杀的游戏。揭开游戏的外衣,该游戏本质上一种犯罪行为,而且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犯罪。“蓝鲸”死亡游戏参与者多为青少年。游戏过程中分工明确,暗含心理陷阱,危害巨大。防范“蓝鲸”死亡游戏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对其的定性与处罚,建立网络监管的协同体系,加强学校网络安全教育,增加家庭关爱以及鼓励青少年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蓝鲸”;死亡游戏;特征;防范对策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4月,短短半年,俄罗斯一款名为“蓝鲸”(blue whale)的自杀式死亡游戏便夺去了 80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虽然游戏的发明者——俄罗斯某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ikin)已于2016年11月被逮捕,但这款游戏却继续在各国的社交媒体上继续蔓延,我国也未能幸免于难。2017年 5月,国内多家主流媒体披露了多起未成年人组织或参与类似“蓝鲸”的死亡游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安徽泾县6名学生沉迷于“蓝鲸”死亡游戏,最终被警方营救。四川攀枝花,一名家长向派出所反映,有学生在互联网上玩“蓝鲸”游戏。此外,广东湛江已抓获一名涉嫌组织死亡游戏的犯罪嫌疑人,年仅 17岁;浙江温州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及时查处了一起涉及煽动参加“蓝鲸”死亡游戏的案件。“蓝鲸”死亡游戏企图假借游戏之名,行犯罪之实,必须对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否则将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
一、“蓝鲸”死亡游戏的性质及刑法评价
(一)性质:借游戏之名,行犯罪之实
“蓝鲸”死亡游戏,是指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对游戏参加者进行心理引导和控制,使之完成各项自伤自残任务,从而产生消极厌世的心理,最终自杀的一款暴力游戏。游戏要求参与者在 50天内,完成包括“4:20起床”、“观看恐怖电影”、“在手臂上刻画鲸鱼图案”以及“到阳台边缘”在内的50个任务,终极任务就是自杀。
游戏,应该是一种给人们带来愉悦的活动,使得人们能够暂时忘记悲伤,并且基于玩家自身的选择,可以随时退出,不受限制。同时,游戏也是虚拟的,应与现实生活有明确的界限。反观“蓝鲸”死亡游戏,从参加游戏开始,一些恐怖血腥的任务毫无愉悦之感,其真实的目的反而是为增加参与者内心的负面情绪而设。一旦参与游戏,玩家或因为受到组织者的“洗脑”,或受到组织者人身威胁,均不能自愿退出。更可怕的是,“蓝鲸”死亡游戏以实现参与者自杀为游戏的最终目的,已经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给广大青少年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蓝鲸”死亡游戏已经不是一款游戏,而是利用游戏的元素,一步步地实现自己杀人目标的犯罪。互联网的去边界和组织化,降低了各种极端亚文化的认同和参与门槛。其中就包括放大和强化某个群体的特有行为心理,并将之引向实践。[1]自杀游戏已借助互联网,打破了与现实世界的物理隔绝,如“蓝鲸”此类“有毒”的游戏,不仅是对个体生命健康权的侵害,也是对网络安全的破坏。“蓝鲸”死亡游戏是一种新型犯罪:一方面是,游戏的外衣掩盖了杀人的本质,通过所谓的游戏教唆他人自伤自残。该如何定性和追究责任,这是一个新问题。另一方面,有组织的自杀行为已经突破时空的限制,网络这个自由空间为此类极端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是一个新形式。
(二)刑法评价:涉及多类犯罪,应受严厉处罚
1.涉及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在“蓝鲸”死亡游戏中,组织者通过发布“游戏”任务,劝说、诱导,甚至威胁参加者实施自伤、自残,自杀的行为涉嫌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主观上,组织者希望并积极追求参加者自残、自杀的结果,具有杀人故意的心理;客观上,组织者实施验证身份、发布任务、诱导执行等一系列行为,实际策划组织并参与了这样的犯罪行为。对于相约自杀为名诱骗他人自杀的,我国刑法的通说对其评价为故意杀人罪,仅造成伤害结果的,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的相关内容进行处罚。
2.涉及传播极端主义思想
极端主义是指任何个人或组织为实现其某种严重脱离于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并排斥与之不一致的任何理念,而针对自身或第三者采取暴力或其他非暴力的手段,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行为。[2]“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无所有”,“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我们到底还要经历多久?”,“蓝鲸”死亡游戏在组织过程中,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自杀的信息与图片,吸引他人参与,积极宣扬自杀是一种解脱等反社会思想,从而实现教唆参与者自伤、自杀的目的。“蓝鲸”死亡游戏暗含极端主义思想,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国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以制作、散发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或者通过讲授、发布信息等方式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构成宣扬极端主义罪。
3.涉及传播淫秽物品、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蓝鲸”死亡游戏除了危害公民生命健康,危害公共安全,其还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根据媒体的报道,“蓝鲸”死亡游戏中存在不法分子利用“带人入群”的方法,专门骗取女性参与者的裸照,并将裸照转卖。这种以牟利为目的,传播贩卖女性裸照的行为涉嫌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若不以牟利为目的,也可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此外,通过网络传播“蓝鲸”死亡游戏的相关信息,属于刑法中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行为,因此可能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若同时涉及其他犯罪的,则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4.涉及敲诈勒索、网络电信诈骗
“蓝鲸”死亡游戏传入我国后,又衍生出一些新的犯罪形式,涉嫌侵犯公民财产,危害巨大。在我国,一些不法分子瞄准“蓝鲸”死亡游戏的热度,精心策划敲诈勒索的骗局。不法分子在参与者申请加入“蓝鲸”死亡游戏时,会要求女性提供个人信息并且上传裸照;如果为男性,则会要求其提供个人信息以及家庭成员信息和真实住址。当参与者上传这些信息后,不法分子则会利用手中的信息敲诈勒索参加者给予其一定数额的金钱,否则将公开其裸照和个人信息,有的还以家人安全相威胁,若不给予钱财,将上门报复其家人。行为人虚构“蓝鲸”死亡游戏,以公开其裸照等隐私信息或者以危害家人安全为威胁,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二、“蓝鲸”死亡游戏的特征
(一)传播范围广,隐蔽性强
网络传播打破传播的时空限制,使得“蓝鲸”死亡游戏传播范围广泛。起源于俄罗斯的“蓝鲸”死亡游戏已经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引起了各国的警惕,包括英国、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均发出警告。在国内,涉及死亡游戏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目前有超过 15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发布了抵制“蓝鲸”的公告。此外,“蓝鲸”死亡游戏利用QQ群、微信等社交媒介进行传播,通常每一个游戏群的参与人数都达数百人,更是扩展了其传播的范围。除了传播范围广,“蓝鲸”死亡游戏的隐蔽性也逐渐增强。由于各国对于“蓝鲸”死亡游戏的严密监控,与“蓝鲸”、“死亡游戏”等有关关键词均被删除,但其并未就此消亡。调查发现,受到封停的“蓝鲸”死亡游戏群改头换面,以“LJ”、“4.20”、“4:20叫我起床”卷土重来,有的甚至取名“游戏交流群”来逃避打击。针对“蓝鲸”死亡游戏隐蔽性增强的趋势,多家互联网企业已经逐步扩大关键词屏蔽范围,最大程度地阻隔该类游戏的危害。
(二)组织者与被害者均为青少年[3]群体
青少年接触网络的机会增加,其组织参与“蓝鲸”死亡游戏的机会也在增加。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截止到2015年,我国青少年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2.87亿,青少年网民占总体网民的一半左右,网民低龄化趋势较为明显。网络的使用造就了大量的“屏奴”,户外活动不足与中小学生近视率逐年上升、少年封闭孤僻与交流障碍增多、碎片化冲击注意力游移等问题愈发严重。[4]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疏远、学业压力增加都使得青少年越发在网络虚拟世界中找寻社交情感、自身认同,从而深陷“蓝鲸”死亡游戏的“陷阱”中。据报道,“蓝鲸”死亡游戏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多为青少年群体。例如广东湛江的徐某组织“蓝鲸”群时,年仅 17岁;江苏南通的三起组织“蓝鲸”死亡游戏群案件中就有一名14岁的组织者;浙江宁波的黄某,建立”死亡游戏”群时年仅12岁。而这些案例中,参与“蓝鲸”死亡游戏的基本都是青少年,其中未成年人占大多数,多为在校学生。
(三)设置门槛,组织分工明确
“蓝鲸”死亡游戏组织者在选择参与对象时,会设置准入门槛。真正的死亡游戏群主为验证参与者是否真有自杀的意图还是纯属好奇观望,会要求参与者先完成诸如“在手臂上划出一道浅浅的口子”等简单任务,并上传图片。此外,一些游戏群主为防止参与者后悔,会让参与者提供真实个人信息,如男性加入时需要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甚至亲人的信息;如女性则是要求提供手持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的裸照。此外,此类死亡游戏群组织分工明确,管理严格。通常,群里主要存在四种角色,分别是管理员、游戏“导师”、旁观者和直接参与者。管理员主要负责入群人员的审核,讲解游戏规则,并随时观察群里动态,及时清除群里的“反鲸人士”和未完成游戏任务的参与者,属于游戏核心组织者。游戏“导师”是群里具体负责指导参与者完成任务,并在任务过程中监督参与者,同时也负责不断向参与者不断“洗脑”,让其接受游戏任务。有的群管理员和“游戏导师”是一人兼任,有的则不是。旁观者,主要是在游戏群中,并未直接参与游戏而是围观参与者执行任务的人,属于游戏间接参与者。他们通常扮演的是“冷眼的旁观者”角色,对参与者的自残自伤行为叫好,鲜有指出游戏危险,劝阻参与者退出游戏。在一定情况下,游戏中的旁观者会成为游戏中的管理员或者“游戏导师”,也有可能成为直接参与者。
(四)循序渐进,整个过程暗含心理陷阱
“蓝鲸”死亡游戏看似简单,但却暗含心理陷阱,通过任务层层递进,最终实现心理控制,诱导参与者实现自杀的终极目标。首先,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游戏组织者会在网络中招募参与者,并附上一定的入群条件,如提供真实信息或者在手臂上浅浅划出鲸鱼图案,就是在筛选出具有好奇心或有自杀念头的人员。然后,组织者会通过投射技术、心理劫持、系统脱敏、认知塑造等心理学方法,层层递进,实现对参与者的精神控制。以“蓝鲸”死亡游戏中的具体任务为例。在早期接触游戏时,组织者会对参与者表达心理上的认同,并且在任务中继续使用这种投射技术,目的是让游戏参与者无条件服从,如“在论坛发帖附加上“我是条鲸鱼”的标签”、“与‘鲸鱼’聊天是有必要”以及“是时候该和鲸鱼见面了”等。在游戏过程中,有参与者因害怕而不能完成游戏或者想要退出游戏,组织者就会使用心理劫持的方法,用入群时提供的真实个人信息和裸照来威胁参与者继续游戏。此外,蓝鲸死亡游戏中本该用于心理治疗的系统脱敏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穿插在任务中的“4点 20分起床看恐怖电影”、“克服你的恐惧”、“看一整天的恐怖电影”和“4点20时去屋顶”、“去大大的屋顶,然后站在屋顶边缘”、“坐在屋顶边缘”以及逐渐加深的自残任务等都是在试图麻木参与者对恐惧的敏感程度,从而更容易引导参与者自杀。游戏中的图片、文案和音视频资料都具有导向性,主要目的就是消磨参与者的意志,从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对游戏产生依赖。50天完成50个任务,看似不可思议,但正是有了这些心理陷阱,才使得游戏“杀人”成为现实。
三、“蓝鲸”死亡游戏犯罪背后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应对“蓝鲸”死亡游戏,我国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方面,正如上文谈到,“蓝鲸”死亡游戏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是多种罪名的交织。另一方面,“蓝鲸”死亡游戏属于新型犯罪,目前中国尚无因玩此游戏而自杀、自残的报道和案例。具体来说,首先,组织者的行为该以何种罪名进行处罚也尚无司法解释的指导。我国司法实践还没有就“蓝鲸”死亡游戏的认定及处罚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存在一定难度。其次,在打击过程中,认定组织者方面就存在难度。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确认组织者的证据难以取得,组织者的身份较难核实。目前,还尚未有相关部门出台关于打击防范“蓝鲸”死亡游戏及其类似犯罪的刑事政策性文件。关于防范“蓝鲸”死亡游戏,仅有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做好“蓝鲸”死亡游戏预警处置工作的通知》及各地在此基础上出台的防范通知,暂时缺乏打击防范的法律依据,防范力量没有得到有效调配,难以抑制“蓝鲸”死亡游戏的传播和危害。
(二)网络监管存在不足
网络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当其受到某些心怀不轨的人的利用时,很可能因缺乏必要的监管而沦为不法分子侵害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监管。从监管主体方面看,政府在“蓝鲸”死亡游戏的监管方面只是少数几个有职责的部门在监管,缺乏各部门的联合应对机制,同时,政府与网络运营企业间的合作还较为有限,虽然在一定程度可以抑制“蓝鲸”死亡游戏的传播,但是并没实质上解除其带来的社会风险。从方法论上讲,我们主要是抵挡、删除、过滤、引导、制止等传统手段,可称之为只抓一点,我们缺乏的是进攻或者积极防御的能力与战略。[5]目前,针对“蓝鲸”死亡游戏不断升温的趋势,各地文化执法部门主要是加强预警处置工作,加强排查,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只是查删有关群组,屏蔽关键词。采取防控措施之后,“蓝鲸”死亡游戏并没有逐渐减少,而是更换群组,名字更加隐晦,甚至转移到微信群里,“蓝鲸”死亡游戏的防控还任重道远。
(三)学校忽视网络安全教育
网络安全教育是指针对有可能来自网络的各种各样的侵害,为了确保青少年身体、心理、财产等方面的安全而对其进行的教育。[6]目前,从“蓝鲸”死亡游戏的案例看,学校对于网络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有限。首先,缺乏必要的网络安全教育的课程。大多数中小学校虽然都开设了网络课程,主要内容是学习基本的网络技术知识,缺乏网络安全教育的内容,仅有少部分学校会把网络安全教育放到法制教育课中。其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的形式单一。在仅有的少数开展网络安全教育的学校中,网络安全教育的形式往往简单,流于形式,如仅仅是利用主题班会的时间进行宣讲,内容简单,方式单一,并不能引起学生的关注,自然效果有限。最后,老师在网络安全教育中的“基本功”有待加强。一方面,老师并没有及时关注学生日常思想动态,没有为学生打好网络安全的“预防针”。另一方面,在处理已经存在问题的学生时,有的老师存在处理简单,不关注心理疏导;有的老师知道心理疏导的重要性,但不具备心理疏导的能力。综上,由于忽视网络安全教育,没有培养学生对于网络不良文化的自控力和自律性,这些涉世未深的学生难免沦为“蓝鲸”死亡游戏的“牺牲品”。
(四)缺乏父母关爱和家庭温暖
父母采用情感、温暖、理解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将会促进孩子心理健康良好发展,若较多的采用惩罚、严厉等消极教养方式将会阻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7]受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家庭教育通常以严厉为主,打骂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之过分关注孩子学习成绩,这样的教养方式忽略孩子的内心需要,堵塞了他们疏解压力的最佳渠道。此外,家庭问题也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忽视,家庭矛盾等问题给孩子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易产生抑郁和自杀想法。从涉及“蓝鲸”死亡游戏的案件来看,大多数都存在因为父母离异,或只关心学习成绩而忽视与孩子沟通,从而导致孩子无法疏解心理压力的问题。例如,浙江义乌六名初中生参与游戏并离家出走,背后原因就是成绩不好,家长总是打骂自己;江苏常熟的少年因为父母离异,缺乏对其的关爱,只能通过上网来填补内心空虚,因此给了死亡游戏可乘之机。
(五)参与的青少年自身存在心理问题
青春期发育过程中,青少年身体变得强壮,第二性征出现及内分泌机制的完善,使他们的心理也发生复杂的变化。青少年早期,往往是一个人开始寻找可融入群体、觉察自我成熟的时期,也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认同危机”时期。[8]“蓝鲸”游戏之所以能诱导青少年自杀,一方面利用了青少年睡眠过少会严重影响大脑对重大事情的认知和辨别能力的生理特点,另一方面,该游戏利用了青少年时期,孩子开始关注精神自我、彰显自己独特性以及寻求社会认同感的心理特点。[9]“蓝鲸”死亡游戏的组织者正是利用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征,使用一些具有视觉冲击的图片和煽动性的文字,使得一些不能明辨是非的青少年掉进“陷阱”。此外,参加“蓝鲸”死亡游戏的青少年都存在成长中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或来源于家庭问题,或来源于学习压力,或是人际交往受挫。本身就处于青春期心理发展变化复杂,加上心理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关注和解决,一些青少年就容易受到“蓝鲸”死亡游戏的引诱。
四、“蓝鲸”死亡游戏的防范对策
(一)法律:依法依规,防患未然
犯罪学家贝卡里亚曾说过:“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而想要预防犯罪,其中就要“把法律制定得明确而通俗”。[9]面对“蓝鲸”死亡游戏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危害后果严重的形势,国家应当制定有效的刑事政策。有关部门据此则出台相关的应对措施,落实政策。此外,司法机关有必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组织此类游戏将承担何种责任,会受到什么惩罚。应当明确界定“蓝鲸”死亡游戏的犯罪性质,通过司法解释为防范此类犯罪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有利于形成威慑。犯罪学家李斯特有一句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此外,相关部门要切实负担起防范此类犯罪的责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积极开展合作,制定协同防范机制,发挥社会政策的预防价值。目前,就预防“蓝鲸”死亡游戏的大范围传播,仅靠文化部印发的《关于做好“蓝鲸”死亡游戏预警处置工作的通知》还稍显薄弱。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制定完善网络监管的法律法规,明确网络监管的主体责任,主动应对此类犯罪的挑战,确保监管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二)监管:协同监管,多维并治
网络监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网络参与主体共有的责任。网络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形成一个良好网络监管的联动机制,才能应对“蓝鲸”死亡游戏的威胁。以“蓝鲸”死亡游戏为例,政府应当建立行政监管、企业有责、网民参与的积极主动的监管机制。首先,政府内对网络安全负有监管责任的主体单位,应当加强信息交流,消除壁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其次,网络运营企业要增强企业责任意识,不断加强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保障支持,发挥他们在网络监管中的技术优势。除利用后台数据管理的便捷条件,除删除、过滤等一般手段外,运营企业还要密切关注“蓝鲸”的动态情况,及时掌握相关电子证据,上报相关情况。最后,网民也是加强监管的重要主体。目前,全国多家网站已经公布举报受理电话并开通了“网络举报”移动客户端。如果网民及时发现存在传播组织“蓝鲸”死亡游戏可以及时举报,积极维护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
(三)学校:重在预防,教育引导
随着青少年网民数量的进一步增加,青少年网络犯罪及被害的概率也随之上涨,网络安全教育已经成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堂“必修课”。针对“蓝鲸”死亡游戏对青少年群体的“腐蚀”,各中小学校应当开设网络安全教育课程。通过网络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培养他们辨别网络陷阱的能力,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网络价值观。在网络安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学校应当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要积极扩展教育形式,发动学生主动参与。在网络安全教育中还要使用生动具体的案例,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网络危险离他们并不远,从而增加教育引导的效果。此外,抵御“蓝鲸”死亡游戏的心理陷阱,还需要老师及时关注学生心理状况,重视对学生的心理辅导。在日常的管理中,老师要自觉充当学生的心理导师,关注学生厌学、情绪低落、人际冲突等问题,积极化解积累的负能量,避免学生出现更严重心理问题。最后,学校要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培训,培养老师心理辅导能力和学生价值观引导塑造能力。
(四)家庭:父母关爱,亲子沟通
家庭是青少年社会化的“第一课堂”,也是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的“避风港”。之所以青少年会陷入“蓝鲸”死亡游戏的陷阱,是因为他们缺乏家庭的关爱和与父母的交流。预防“蓝鲸”死亡游戏,提高青少年的家庭关爱教育十分重要。家长要合理分配时间,多陪伴他们,与他们沟通交流,给予他们关爱和帮助,指导他们正确释放心理压力。同时,家长应当合理管理青少年上网时间,避免青少年沉迷网络,并通过增加日常社交活动和体育锻炼,减少青少年对于网络的依赖程度。调查显示:孩子的心理问题有90%是来自家庭,另有 9%来自社会,自身心理疾病的人群只占 1%。[10]。家庭问题的及时解决也是保护青少年远离“蓝鲸”死亡游戏的关键因素。家长应当注意自身在青少年心里的形象,及时化解家庭问题,避免因家庭矛盾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创伤。“蓝鲸”死亡游戏主要吸引的是那些存在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而家庭关爱和亲子沟通则是疏导青少年心理问题,抵御侵害的天然“防火墙”。
(五)自我:认清危害,自觉抵制
我国尚未出现因“蓝鲸”死亡游戏而自杀的案例,但俄罗斯那几十个花季少年的陨落充分可以说明该游戏的危害性。青少年虽然辨别能力不及成年人,但通过网络安全教育也能培养其清楚知晓该游戏的危害性。广大青少年要认清“蓝鲸”死亡游戏的本质,勿要因为好奇心而参与游戏,时刻警惕网络陷阱。此外,同龄人的劝说会比家长的说教起到更大的作用,广大青少年要在同龄人中传递正能量,劝说身边的同学远离死亡游戏。青少年群体中不乏网络安全教育的小助手,要培养他们的参与抵制“蓝鲸”死亡游戏的积极性,并教会他们遇到有人参与“蓝鲸”死亡游戏该如何应对。
“蓝鲸”死亡游戏虽然来势汹汹,但尚未在我国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才能够抵御该类犯罪在我国继续蔓延。从法律层面、协同监管、学校网络安全教育到家庭关爱以及增加青少年自身“抵抗力”,防范“蓝鲸”死亡游戏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关注青少年成长中的健康,为他们营造一个干净文明的网络环境。
[1]朱昌俊,死亡游戏“蓝鲸”来袭 我们准备好了吗[N].中国青年报,2017-05-11.
[2]卢有学,吴永辉.极端主义犯罪辨析—基础理论与立法剖析[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2):37.
[3]姚伟宁.青少年网民群体特征与上网行为的动态变迁——历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研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2):90-97.
[4]陈德权,王爱茹,黄萌萌.我国政府网络监管的现实困境与新路径诠释[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176-181.
[5]赵国玲,常磊.青少年网络被害的学校教育原因实证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09(1):43-48.
[6]刘胜凯,卢立平.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心理健康关系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4(9):85-88.
[7]田 丰.“蓝鲸”游戏背后是青春期认同危机[N].佛山日报,2017-05-23.
[8]薛应军.蓝鲸:走向现实的死亡游戏[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7-06-04.
[9](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2-103.
[10]牛伟坤.调查显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90%源自家庭[EB/OL].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2-14/8149377.shtml,2017-02-14.
(责任编辑:朱春华)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Crime of Abetting Others to Commit Suicide by Internet—Take the “Blue Whale” Death Game as an example
HE Ju-song
(Graduate Division,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china)
The “blue wha le” death game, o riginated fro m t he nat ural phenomenon of wha le run aground, is actually a g ame that through social media, organizers guide the part icipants to complete a series of tasks on self-injury, self-mutilation, and commit suicide finally. Uncover the game’s coat, the game is a kind o f crime essentially, and also a n ew type of cyber crime.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 e“blue whale” de ath ga me a re teenagers. In th e course o f th e game, the div ision o f labo r i s cl ear, the psychological trap is implied and it’s a huge threat. To prevent the “blue whale” death game needs further clear it s legal qu alitative and pun ishment, e stablish th e system of co operative n etwork supe rvision,strengthen network security education in school, increase family care and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evention.
“Blue Whale”; death game; characteristics; countermeasures
D6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727(2017)06 -0063-07
2017-07-20
何炬松(1991-),男,重庆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犯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