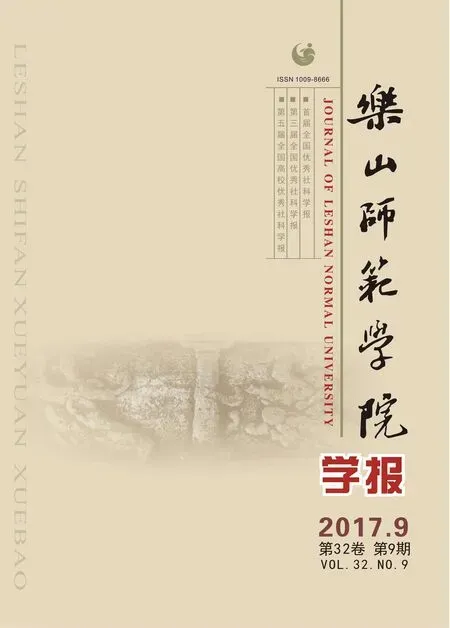论库柏的中国至印度之行及其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
张 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渝中 400015)
论库柏的中国至印度之行及其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
张 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渝中 400015)
英国人库柏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中印商贸捷径的第一人。其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1868年溯扬子江而上,取道重庆、成都,经打箭炉,穿越藏东到巴塘,尔后在云南维西被“阻回”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涉及到湖北平原、扬子江上游、川西、藏东及滇西北的地理地貌、自然风物、民风民俗、商贸状况等诸多方面,成为近代前期外国人认识中国西部尤其是藏东地区的一大重要信息来源。
库柏;西藏东部;中印商贸捷径;印茶入藏;《贸易先锋游记》
自17世纪以来,西方人就对穿越中国内地进入神秘的藏区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传教士和其他西方人的活动深入到中国内地;一直期待进入西藏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们,开始进入西藏东部开展考察和探险活动,试图揭开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神秘面纱。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外国人进入藏东虽然没有明确被视为非法活动,却遭到了当地官、僧的强烈抵制,外国人尤其是多批法国传教士经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进入藏区乃至西藏中心拉萨的意图更是均以失败告终。1845—1846年,擅自潜入拉萨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 和秦噶哔 (Joseph Gabet,1808—1853)就被清廷押解经昌都、巴塘、打箭炉等地出藏东至成都,后被遣送到澳门。[1]1,9,23
继古伯察、秦噶哔之后,英国人库柏成为近代英国到藏东探路的第一人,并自称“贸易先锋”。1868年1月4日,库柏从汉口正式踏上他计划已久的穿越中国内地、探寻中印商贸捷径的探险之旅。他溯长江而上来到重庆,然后取道成都抵达打箭炉,又由此经理塘、巴塘到达云南维西后被“阻回”,终未完全达成其旅行目标。1871年库柏将此次旅行札记出版,即颇有价值的著作——《蓄辫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游记——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本文简称《贸易先锋游记》)①。
库柏的《贸易先锋游记》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人、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东部情况为数不多的一大重要信息来源,受到西方读者的青睐,同时也颇受英国政府及商界的重视。出版当年,就有英国杂志对此著述作过相关评荐。②
国内外学术界对库柏著述的《贸易先锋游记》亦给予了较多关注,其内容后来为中外学者多次引证。西方学者对其游历考察活动的论述最早见诸于1880年出版的威廉·吉尔的代表作《金沙江》③一书;而国内学者赵艾东,对库柏在藏东的考察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专论《唐古巴的考察与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④。此外,相关研究或引证散见于吕昭义、于乃仍、黄嘉谟、董志勇、高志鸿、黄康显、冯明珠、向玉成、肖萍、马森(M.Mason)、兰姆(A.Lamb)、罗伯茨 (J.A.G.Roberts)、何溯源(William M.Coleman IV)、卡伦(P.P.Karan)、罗斯基 (Thomas G.Rawski)、维辛(Douglas Wissing)、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G.C.Allen&Audrey G Donnithorne、James George Frazer、Joseph Earle Spencer、D.P.Choudhury、Gaines K.C.Liu、Paul Pelliot、Tkroy Choudhury、Y.Lu、P.Watson、Samuel Thévoz、R.Gardella、J.Bacot,E.Chavannes等中外学者的著述中⑤;《永昌府文征》《新纂云南通志》等汉文志书对其人其事亦略有提及⑥。
迄今《贸易先锋游记》有法文译本出版,即Le voyage en China(《中国旅行记》)⑦,与英文版书名略有差异。但就有关此著作的中文译作成果来看,目前仅见两篇摘译文章。其一是载于《教会》总第53期上的《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八)》⑧。该文实际上译自1877年八月的《亿万华民》所摘录的库柏所著的《贸易先锋游记》的相关章节,也就是库柏在重庆逗留期间所记述的罗马天主教四川传教使团的传教历史;其二是曲小玲译自法文版的译作《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⑨。该文反映了库柏从成都—崇州—打箭炉—巴塘一段旅程,载于《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六卷)。由于尚无完整的中译本问世,该书内容还不为国内学术界和一般历史爱好者广泛了解。本文拟对库柏的生平、中国至印度之行及其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作一初步探讨。
一、库柏生平及其主要旅行经历
托马斯·汤姆威尔·库柏(Thomas Thornville Cooper,1839—1878,有唐古巴、古柏、柯柏、库珀、库泊、库伯、库珀斯、顾巴、柯克等译名,其中“唐古巴”译自他《贸易先锋游记》书中所记的“Tang Koopah”),热衷冒险的近代英国旅行家,煤炭代理商和船东约翰·J·库柏的第八子,1839年9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东北部港市桑德兰境内的毕夏普维尔茅斯[2]1078。
库柏就读于毕夏普维尔茅斯的格兰奇学院;曾在苏塞克斯郡当过家庭教师,随后去游历了澳大利亚。1859年,他辗转来到印度,就职于马德拉斯的阿巴思诺特公司。1861年,他放弃工作,去印度信德邦探望定居于此的一位兄长。1862年,他又前往孟买,然后由此经贝布尔、马德拉斯前往英属缅甸。在仰光,他一心致力于学习缅甸语,很快在语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1863年,他来到上海,与其兄长再度相聚。[2]1078
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西方各国渴求打开中国内陆通商道路和市场。1867年,库柏应上海英商会之邀,着手进行穿越西藏前往印度的尝试,以促进“中英印”之间的三角贸易。1868年1月4日,他离开汉口,踏上计划已久的探路之旅,行至云南维西后被“阻回”,于同年11月11日返抵汉口。随后他回到英国,于1871年出版了他这次旅行的札记——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
鉴于从中国到印度之路没能走通,1869年库柏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即从阿萨姆去巴塘,以证明阿萨姆茶叶进入西藏市场的可行性。他从加尔各答出发,经萨地亚,沿布拉马普特拉河、鲁西特河(察隅河入印度境内后称鲁西特河),穿过米什米(Mishmi,即“僜人”)部落世居地区,到达距察隅日玛村大约20英里的僜人普兰部落的一个村子⑩,此地离巴塘还不到120英里。在这里,他又遇到察隅藏官的坚决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就地折回。在他1873年发表的《米什米山》(The Mishmee Hills)⑪里,讲述了此次探路经历。
1872年库柏回国后不久,英国印度事务部便指派他护送来伦敦访问的回民使团(以刘道衡为首)回云南边境。库柏陪同刘道衡一行于同年9月20日离开伦敦,取道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印度孟买、加尔各答,12月抵达缅甸仰光。当时杜文秀大理政权已在清军的进攻下失败,大理城陷落,库柏的护送使命就此完结。之后,他被任命为驻缅甸八莫的政治代表。
遗憾的是,健康不佳迫使他很快就回到英国,挂职于印度办事处政治部。1876年,他被派往印度,在德里向总督递交了派遣书;随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八莫的政治代表。1877年,库柏在八莫为成功穿越中国的威廉·吉尔上尉举办了欢迎会。吉尔在他1880年出版的著述《金沙江: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一书中提及此事,字里行间无不充满感激之情。
1878年4月24日,库柏不幸被其护卫队中的一个印度卫兵杀害[2]1079。
二、库柏中国至印度之行的背景、行程与主要收获
19世纪西方涌现出众多冒险旅行家,但大多都是身份不明、默默无闻之辈,而库柏却在其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他既是西方最早一批敢于直面风险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家之一,也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商路的第一人。
(一)背景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商人认为中国西部蕴藏着巨大商机,意欲设法探明路线并开辟该地区的市场。其中,在上海和印度的英商对能否通过云南和四川将其势力分别延伸至长江中、上游区域最为关切。早在1862年,库柏作为加尔各答英商会代表,曾企图以英属缅甸的首府仰光为起点,取道八莫等地,向东探察至云南大理的商路,但终因地理环境险恶而作罢。时至1867年,已在上海生活了数年的库柏,鉴于时机成熟和个人夙愿,接受了上海英商会的邀请,试图探寻从中国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商路捷径。其旅行目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英国人能进一步了解他们不熟悉的那一部分中国人,并开创一条有利于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贸易通道,实现两国的进步”[3]4。
严格来说,库柏旨在探寻中印商路捷径的探路之旅既具有民间商业背景,也带有一定官方背景。1871年,英国一杂志就称库柏当时是“在英国驻沪商人的鼓动与英国领事的支持下”[4]774着手考察的。库柏临行前,在上海得到了时任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⑫的建议,英国驻汉口领事梅德赫斯特(Medhurst)、驻上海的领事温彻斯特(Charles A.Winchester)则协助他获得了游历扬子江并穿越内地去印度的护照,而且后者在上海还积极会同霍格发起了一场募款活动,以减轻他的旅费负担;库柏在维西受阻,原路返回到打箭炉时,又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⑬批准的300两白银补助经费的及时救助。可见,以阿礼国、威妥玛等驻华外交使节为代表的英国官方是支持库柏的此次考察活动的。不过,他和驻打箭炉的法国天主教丁盛荣主教⑭交谈时,倒是特别解释说,此次旅行只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愿,与英国政府绝无关系”[3]181。
(二)行程路线
库柏决意尝试从中国至印度的探险之旅后,花了数月时间来精心准备和反复思虑他的旅行计划。他全面评估此行必然存在的重重困难,并想方设法加以一一解决,包括向朋友求助取得白银600两的银票作为旅费,听取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建议,求得四川法国传教使团沿途提供帮助的允诺,以及努力使自己蜕变成十足的“中国人”等等。
1867年11月库柏从上海来到汉口作最后的行前准备。他在汉口雇用了一名随行翻译(菲利普,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地基督徒)和一名去重庆的向导(老李,也是虔诚的基督徒)。1868年1月4日,剃头蓄辫、穿长袍马褂的库柏,怀揣英国领事发给的英式护照和武昌总督发给的中式护照,从汉口乘船出发,走湖泊及运河航线,行船至沙市,然后再入扬子江,溯急流过三峡,抵达重庆。库柏从汉口到重庆的行程,历时29天。
1868年2月19日,库柏由重庆走陆路,去往四川首府成都;在成都获得四川总督发给的取道拉萨去印度的护照后,于3月7日继续西行,途经崇州、雅州、泸定,抵达打箭炉。在打箭炉,库柏得到法国天主教丁盛荣主教的慷慨相助,用去400两银子置办好去西藏的各种装备和适于以物易物的必需品后,在4月30日,换成英式服装的他继续踏上穿越藏东的行程,翻越折多山,经河口(今四川雅江)、理塘,抵达巴塘。
在巴塘,库柏原计划穿越藏区中心拉萨去印度的路线被证实不可行后,千方百计地与当地官员周旋,希望能走他新发现的巴塘至紧邻阿萨姆邦边境的察隅日玛村(此地离印度阿萨姆大约20天的行程)这条线路,但因西藏喇嘛们坚决阻止外国人进入藏区腹心地带,清廷驻藏大臣亦明令禁止他继续西行,他希望破灭,只好南下,取道云南大理府去缅甸八莫,再由八莫到阿萨姆。
6月2日他离开巴塘,沿澜沧江河谷向南穿行,6月10日抵达阿墩子(今云南德钦),后继续南行至维西府(今云南维西),他在维西获得了去大理府的护照。然而,他从维西起程三天后,因时值滇西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与回民起义军对峙,局势不明,其去路遭到泽藩村寨头人劝阻,无奈之下库柏只好折回维西作罢。库柏返回维西后,当地汉官企图谋财,以“乱军奸细”之名将他秘密监禁起来,长达五周之久。
8月6日,库柏脱险重获自由,并获准离开维西。库柏明白他不太可能继续推进他的探险之旅后,按原路返回,于9月20日抵达打箭炉。库柏在打箭炉逗留了两周,再一次把自己打扮成蓄辫子、着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于10月6日踏上归途。库柏行至雅州时,他弃走成都,转而沿雅河行至洪雅,乘船至嘉定(今四川乐山),又经岷江行船至叙府(今四川宜宾),再入扬子江,顺流而下,于1868年11月11日晚抵达汉口,数日后乘船回到上海。库柏历时十多个月的行程路线大体如此。
(三)库柏游历考察活动的主要收获
库柏此行收获颇多。为了“使英国人能进一步了解他们不熟悉的那一部分中国人”,他竭尽所能,将观察、了解到的事实和亲历的感受,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包括沿途的山川地貌、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城镇概貌、贸易状况、风俗民情和宗教信仰,乃至地方疾病等诸多方面。下文择要略述其藏边贸易、城镇概貌、风俗习惯三方面的考察收获,以窥一斑。
1.藏边贸易
库柏热衷于鼓吹国际贸易,这也是他在书名中以“贸易先锋”自称的缘由。为了在中国和英属印度之间开创一条贸易增长之路,库柏此行考察的主要着眼点落在贸易方面,其中川藏边茶贸易最受其关注,而他从中发现的巨大商机就是印茶入藏。
所谓川藏边茶贸易,是指历史上四川雅州等地的汉民将茶叶加工制成砖茶后,经打箭炉输入拉萨等藏区各地的商贸活动。在打箭炉和巴塘,库柏着重考察了藏边贸易,尤其是边茶贸易。他观察到打箭炉的“汉人聚居区有陕西商人经营的商铺,他们买卖绿松石、茶叶和鼻烟,以这些商品与西藏人交换麝香、鹿角、药材、黄金和各种生皮”[3]204-205。而巴塘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集市,“中部藏人和蒙古人带来麝香、月石、皮货以及黄金,交换茶叶和鼻烟”[3]248-249。在他去大理受阻返回打箭炉的途中,时值八九月商贸旺季,在金沙江竹巴龙渡口过河时,他看到“大约有500头运茶叶的骡子正在渡河,它们要把茶叶运往西藏腹地。岸边的茶叶堆得像一座座小房子一样,等着定时往来的皮筏将它们运到对岸去……渡口一派繁忙景象,河面上的皮筏数不胜数,随处可见大堆大堆的茶叶,熙熙攘攘的商人,和成群结队的牦牛。如今是旺季,商人们都赶去巴塘买茶叶”[3]403。而他二过巴塘时,看见“镇郊到处是一堆堆的茶叶”,“街上牦牛和骡子川流不息,驮着满满的茶叶,去往西藏腹地和其他偏远的藏地”。[3]408库柏由此见识到藏区各地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巨大。
藏区消费的茶叶几乎都是来自雅州地区。早在经川西到藏东的来路上经过雅州之时,库柏就设法打探到了雅州砖茶的制作加工及运销情况。一篼篼砖茶(每篼重约20磅)由苦力从雅州运到200英里外的打箭炉,再运销藏区各地。砖茶按不同品质销往不同地区。上等茶输往拉萨,以及拉萨以西的地区,每篼售价大约是15两银子(或每磅售价为4先令8便士);二级茶主要销往理塘和巴塘,每篼卖价是5两银子(或每磅售价约1先令6便士);三级茶只适销于打箭炉及其紧邻一带,每磅卖9便士。当时他就粗略估计,每年从雅州输往西藏的砖茶已超过600万磅。[3]172-173
通过对边茶贸易的考察,库柏认识到茶是藏族人迫切需求,且不能自给自足的主要生活必需品,而印度能供给西藏人的商品唯有茶叶而已。他进一步设想印度阿萨姆的茶叶,如何能够取代中国的雅州砖茶而占领西藏的市场。他认为,“如果阿萨姆和喜马拉雅茶叶种植园的茶叶可以进入西藏市场,那么印度政府就可以大赚一笔,从而弥补鸦片贸易导致的利润下降。”[3]409“要是能够开放一条贸易路线,那么我们在阿萨姆生产的茶叶就能迅速以很大优势取代中国茶商在西藏市场的垄断地位。”“如果阿萨姆的茶叶能够在质量上超过中国茶叶,那么,它完全可以通过竞价销售的方式占领巴塘市场。”“如果政府能够做出更有效的决策,保护英国人的利益,那么也不会错失西藏这个茶叶市场,完全可以像现在的中国人和尼泊尔人那样自由地进行茶叶贸易。”[3]410事实证明,库柏对川藏边茶贸易情形的考察及其印茶入藏倾销的相关建议,大大激发了英商们的逐利之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政府将印藏通商与印茶入藏问题提上与清政府的谈判日程。
库柏南下至滇西北的阿墩子时,也考察了滇藏贸易。库柏在书中记述道:“在云南爆发回民起义之前,阿墩子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集市,藏族人带来数不胜数的麝香,来这里交换上等的红茶、糖、鼻烟和烟草,因为云南不但盛产这些东西,而且品质还相当出色。近年来,由于回民和当局战事连连,商业贸易大大缩水,市场甚至没落了。”[3]301库柏在泽藩提到了当时就已经很著名的云南烟草:“这片土地上生长着一种著名的云南烟草,烟叶自细茎长出,薄而纤巧,呈黄色,长宽均约8英寸,晒干后则呈淡黄色,据说,这种烟吸起来,味道像极了上等的马尼拉烟草,但是我品尝了后,倒觉得它的风味更胜一筹。”[3]345-346他由此认为,“如果清政府能修复与回民内战带来的破坏,且允许市场对在缅甸的欧洲商人开放,那么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仅仅云南这一带的烟草贸易就利润巨大。”[3]346
本来库柏希望能进一步贯穿滇中,到缅甸八莫,又从八莫到印度的阿萨姆,进一步考察云南和缅甸间的贸易,但由于当时云南回民起义,时局动荡,不得不中止计划而返回。对于缅甸八莫和云南的贸易,库柏虽然没有能够亲自考察,但也做了一些调查。他说,在缅甸和中国间存在着数额巨大的贸易,并且这条商路已存在了数百年。库柏一直希望建立云南和仰光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仰光取代加尔各答,成为英属印度和云南之间的贸易仓库。他认为,可以将仰光作为港口发展贸易,经伊洛瓦底江到达八莫,又由此到云南,这样一条水陆贸易通道对英属缅甸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大有裨益。并认为,只要云南的战事一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自然也会重新得到发展。[3]411-412
2.沿途城镇市井面貌
库柏对沿途所经之地的地貌、道路、城镇、海关、驻军等详情都有记述,对宜昌、忠县、重庆、成都、崇州、雅州、泸定、打箭炉、理塘、巴塘、阿墩子、维西等重要城镇的街容市貌描述得细致入微。
他乘船抵达重庆时正值春节后不久,两江码头熙熙攘攘的忙碌景象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库柏眼里,重庆城堪称“中国西部的利物浦”[3]103。在他乘轿去拜访驻重庆的法国天主教范若瑟主教⑮的时候,他乘机沿途观察了重庆城的市井面貌:“街头巷尾,店铺林立,它们似乎只经营某种特定的行当,要不是店外悬挂着各种汉字店招,店内坐着中国人,恐怕很难将它们和寻常的伦敦商店区分开来。有几条街上摆满了许多外国物品,其他街上则全是些钟表铺,橱窗里陈列着一些便宜的外国怀表和美国钟表。我们似乎是经由金—史密斯广场(史密斯牌手表广场),沿着玩具店小巷前进,穿过德雷伯大街(布商大街)进入布切斯巷(屠夫肉铺巷),然后顺着百鸟街走,鸟街上有许许多多活蹦乱跳的野鸡、野鸭和野鹅,还有一些会唱歌的鸟儿被关在竹笼子里,接着我们进入布特马克广场(鞋匠广场),上贝克斜坡(面包师斜坡),下格林戈鲁斯斜坡(蔬菜水果零售商贩斜坡),最后沿着官家花园来到主教宅邸。”[3]106
在成都,库柏利用等待四川总督下发去往西藏的护照的闲暇时间,在城内闲逛了一圈。其成都印象是,成都府堪称“中国巴黎”:“这里的商店里,艺术品琳琅满目,在当地官员阶层中十分畅销,这就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一种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不曾感受到的贵族气派。这儿还有数家绸缎铺、缝衣铺和书店。很多穿着考究、戴着眼镜的人不断出入书店,可见该地崇文之风极为浓厚。成都,地处富饶的平原中心,城郊广阔,四周环有20英尺厚的城墙。一条大街从东城门直通西城门,长约1.5英里。比起我之前参观过的其他大城市,成都的街道和建筑都呈现出都市风貌。”[3]160
在打箭炉,他记述了打箭炉藏、汉居民分而聚居的生活情况:“打箭炉城坐落在一处深谷里,该深谷横亘在积雪盖顶的山脉之间,这些山脉从峡谷的西口处开始向后倾斜。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藏人聚居区和汉人聚居区分别划分在河流的左右两岸。”“汉人聚居区里有许多陕西商人经营的店铺,做着绿松石、茶叶和鼻烟的生意。他们拿这些商品与西藏人交换麝香、鹿角、药材和黄金,此外他们还交换各种生皮,譬如猞猁皮、水獭皮、豹子皮、狼皮和熊皮等。汉人区里还能看到许多丝绸铺,出售各式各样的中国丝绸。茶庄遍街,肉铺无数,各家肉铺都备有充足的猪肉、羊肉和牦牛肉。后两者很受西藏人青睐,需求量很大,而且极为便宜——大约花2便士就能买到1磅。食品种类丰富,价格便宜……住在这儿的许多汉人都是回民,然而仅通过他们的衣着打扮,很难将他们从其回民同胞中区分开来。他们似乎并不太了解《古兰经》,但他们恪守猪肉和酒的禁忌。他们的清真寺紧挨着我住的客栈,是汉人区最漂亮的建筑,其圆顶和尖塔与印度清真寺如出一辙。看起来,这座清真寺里香火鼎盛,信徒云集,每天早晨和傍晚,寺里都会响起嘹亮而刺耳的号角声,将信徒们召集到寺里做祷告”。[3]203-205而藏人聚居区的大致面貌是,“一条条狭窄污秽的巷道连结着一栋栋房屋,房屋样式普通,形似监牢,巷道里挤满了蓬头垢面的孩子。”[3]206
3.风俗习惯
库柏从汉口一路西行,了解或体验到了诸多汉人的风俗习惯,譬如民间丧葬婚嫁习俗,祭神消灾的迷信仪式,妇女缠小脚的习俗,客栈伙计索要小费的习惯,等等;而在汉人、藏人分而聚居的打箭炉,他侧重考察了混血藏人的风俗习惯。
首先,在衣着打扮方面,打箭炉的藏族人大多是混血儿,他们长相俊美,女子尤甚。男子通常都很高大,体魄健壮,身着汉人服装,蓄着辫子。女子则穿着漂亮得体的裙装,蓝裙曳地,腰间束着一条黄色腰带,头上戴着长长的黄色方巾。她们非常喜爱珠宝,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银戒指,耳朵上坠着又大又重的金耳环。不过,她们最引以为豪的还要数金盘发髻,金盘上饰有漂亮的浮雕图案,她们将金盘佩戴在后脑勺,头发挽成发髻。贫穷的女子戴不起这种金盘,就用银盘代替。其次,在婚姻方面,混血藏人虽然坚持婚姻制度,却并不尊重婚姻。女性的第一任丈夫极少是她们的同族人,因为她们通常更愿意成为住在打箭炉的汉族商人和士兵们的临时妻子,这被视为是相当尊荣的地位,而且在这种婚姻里,她们恪守忠贞。她们是无忧无虑的乐天派,把各自汉族主人的家里整理得十分舒适。她们自己之间的联系则建立在宗族和友情之上,这两大纽带将她们紧紧绑在一起,可谓是一个大家族。如果一个女人遭到丈夫或主人遗弃,即使她无亲无故,也很容易找到安身之处。第三,在藏族混血女子的社交礼仪和习惯方面,她们的社交礼仪和习惯全然不同于汉族女子。汉族女子长期深居简出,胆怯娇羞。而她们却能四处闲逛,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能自由地与男性朋友搭话交谈,而且不会招来闲言碎语,她们像孩童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此外,库柏在打箭炉看见了几支主要来自藏区腹心地带的大商队,让他见识了“典型的纯血统西藏人”的模样和装束。他们身材高大,身高超过6英尺,肤色深棕,一头浓密的黑长发披在肩上。从容貌上来看,他们鼻梁高挺,眼窝深邃,眉毛粗浓,完全不像蒙古人。他们着装普通,外穿羊皮长外套,内搭羊毛衣物,镶有豹皮或猞猁皮滚边,脚蹬半统靴,靴子是羊皮底,由羊毛纺织品缝制而成。他们在腰间系条腰带,佩挂着一把锐利的刀,刀长4英尺,刀把至刀尖一样宽,装在木制刀鞘里,刀鞘通常饰以黄铜和绿松石。腰带上还挂着几只皮袋,里面装有小刀、针、打火石和火镰。[3]216-218
在巴塘大所山河谷,库柏目睹了藏族人的天葬习俗。“几具尸体暴露在溪流两岸,乌鸦和秃鹰正在啄食。不多时便只剩一副副尸骨。夏日里,溪流涨水,会将这些尸骨冲走。藏族人相信,秃鹰吃完污秽的腐肉,飞向天空,也会将逝者的一部分灵魂带往天堂。有钱人过世时,他们的家人会请来喇嘛将尸体分成小块,然后送到山顶,鹰鹫很快便来将之吃得干干净净。也有进行土葬的,但只限于较穷的藏民,他们请不起喇嘛来主持曝尸仪式。”[3]270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与一名芳龄16岁的藏族姑娘成亲的奇遇,称自己成了他一无所知的藏族婚俗的受害者。碍于藏族风俗和当时情势,他不得不带着“新娘”上路,打算一到加尔各答,就将她交给天主教的修女们,并让她视其为“父亲”,以父女相称。[3]271-275大约三四天后,他们行至一个村子,这位姑娘住在附近村子的叔父派来信使将她接走,这才使他如释重负。[3]285
除有关藏人的衣着打扮、风俗习俗等情况外,库柏也考察了滇西北澜沧江流域的哈尼族、傈僳族、怒族、摩梭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性和宗教信仰等情况。以摩梭人为例,库柏记录如下:
摩梭族本来强极一时,可是很快就没落了,接着就融入了雅族部落,由雅族头人统一管理。他们看起来很像汉人。男人们上着寻常的棉上衣,下穿短而宽大的裤子,剃了额发,留着发辫。女人们衣着光鲜,打扮优雅。她们头戴一顶红黑相间的小布帽,流苏从帽檐垂下,帽子微微倾斜,看上去十分时尚。内着束身胸衣,外面套上宽松的短上衣,衣袖长而宽大,再配上一条竖褶裙,裙子由自家纺织的棉布缝制而成,系在腰间,长度刚到膝盖,透出些许苏格兰风情。她们双腿修长,但不穿长统袜,由踝及膝的小腿部分都包裹在蓝白相间的棉布里,脚踩皮靴,鞋尖微露。这些摩梭族的夫人小姐们,或许不如汉族女子那般美貌,但身材匀称,面容姣好,少了汉族女子那股羞涩拘谨,举止大方得多。至于饰物,她们戴着大大的银耳环(形状类似寻常的钥匙柄)、银戒指、银手镯以及一条串珠项链。摩梭人信奉佛教,也如汉人一样敬奉祖先。
摩梭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汉语比摩梭语更为常用,而且学校只教授汉语读写。因此,假以时日,生活在云南这一地区的摩梭人为了与其他部族共通语言就都会使用汉语,摩梭语很有可能堙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摩梭人的房子主要由木头建成,外观上与汉居极为相似。摩梭人在山坡上的梯田里种植稻米。[3]312-313
三、库柏的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
(一)版本及主要内容
库柏的代表作《贸易先锋游记》,自1871年由伦敦约翰·默里(London:John Murray)出版社首次出版问世以来,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此版本在国外已成为稀有古籍。
因《贸易先锋游记》一书在文化意义上具有相当重要性,备受国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推崇,至今已被国外数家出版社重版了不下十次⑯,199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还将1871年的原版古籍加以影印数字化,在谷歌网站上可查阅全文⑰;在国内,该书亦被全文收录于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记录》第六辑,此汇刊的整理者将书名译为《一个留辫子穿马褂的商业先锋的旅行记》⑱。这些再版或影印的版本,虽然封面、扉页不完全一致,且有平装、精装之分,但内容都尽可能地忠实于1871年版的原著(除2013年The Classics.us出版的版本外)。
1871年版《贸易先锋游记》,由前言,目录,插图目录(含封面在内共有素描插图13张),正文十五章(1-452页),正文后附录六篇(453-471页),一张中国至印度的路线示意图,地名索引(473-475页)构成。各章标题分别为:第一章 导言,第二章 湖北平原,第三章宜昌到重庆,第四章 重庆,第五章 重庆到成都,第六章 成都到西阳碛,第七章 西阳碛到打箭炉,第八章 西藏东部,第九章 巴塘,第十章 巴塘到阿墩子,第十一章 澜沧江的部族,第十二章 身在泽藩,第十三章 维西的监禁日子,第十四章 返回打箭炉,第十五章 归途。
《贸易先锋游记》一书,除第一章导言外,各章篇幅比较均衡,不过,从其探寻中印贸易捷径的旅行目标来看,相对而言其内容最详于西藏东部地区。
库柏的叙述既详细又颇具感染力,字里行间亦时不时地透露出他本人作为一个旅行家必备的冷静胆识,及其低调而果敢的行事风范和对事件真相敏锐的洞察力。
库柏透过他同喇嘛和汉、藏官员的交往,以及对川藏边茶贸易的考察,对藏区的政治、宗教与经济关系做了一些相关评述,尤其是对汉藏官僧对西方人、新宗教和印茶入藏极力抵制和防范的根源的观察与分析颇为深入,得出了自己的认识。在打箭炉,他与前来试探他是否前往西藏的喇嘛交谈了数小时,向喇嘛表明他只是个到佛国游览风景名胜的旅人,而非新宗教的传道者后,受到的警告是:如果试图进入巴塘那边的西藏腹地,就会被逮捕,遣返;并告诫他路上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谈论宗教信仰,或让人误认为是外国传教士。此前,这位喇嘛听说他是来开路的,借由此路,英国的士兵可能会接踵而至来占领他们的土地,并把他们的民众变为新信仰的信徒![3]206-208由此可见西藏僧界对西方人的戒备和对外来宗教的抵制。在理塘镇,库柏本想买些去巴塘十天行程所需的食物,结果只买到几磅供牲口吃的干豌豆,其他东西完全买不到,后来他才知道其中缘由就是喇嘛们的敌意,他们背地里禁止商人给他提供食物。[3]233在理塘逗留期间,每一个碰见他的喇嘛都带着一脸憎恶的怒容,并诅咒他。他记述道:“喇嘛们看我来到理塘,情绪十分激动,他们受当地官员的教唆,认为我是白人的先驱,前来探路,为的就是吞并他们的家园,所以他们一见到我,就不停地诅咒我。”[3]235在巴塘,库柏同样洞察到西藏喇嘛对阿萨姆茶叶贸易深怀敌意,极力阻止洋人侵入,严密防范从印度阿萨姆进入西藏察隅的边界,禁止进口一切货物。
库柏据其亲身经历和多方打探,认为西方人、天主教和阿萨姆茶叶均遭抵制的根源是三者入藏势必将威胁到藏区的社会稳定和既有的统治秩序。他洞见“茶是西藏人的生活必需品,也正是因为他们对茶叶的需求,才使清政府最终成功控制了西藏东部地区”[3]409。“没有什么比引入阿萨姆的茶叶更与清政府和喇嘛们的政策相违背的了。就清政府而言,他们担心丧失其宝贵的砖茶批发垄断权,而把持这种垄断,便可赋予喇嘛们茶叶零售供应专卖权;喇嘛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完全统治将茶叶作为主要生活必需品的藏民。就喇嘛而言,他们则担心随着英国茶叶贸易的引入,新宗教的教师们便会纷至沓来,而自由贸易与自由思想一相结合,势必会使他们对藏区的精神统治土崩瓦解。”[3]263
库柏旨在探寻中印商路捷径的冒险之旅终归失败,但其记录的沿途考察所获不无价值和意义,不仅使其同时代的读者们有机会了解当时还鲜为西方人所知的关于中国西部尤其是藏东地区的情况,他在贸易方面特别是开辟藏东商路推进印茶入藏问题上提出的建议,以及在扬子江上游引入汽船以开拓四川贸易市场的论断,更是对19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面向藏东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贸易先锋游记》一书被后人评为“英帝国向外发展史上之一重要文件”[5]。该著述史料类别丰富,至今仍然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研究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和社会历史,尤其是研究近代外国人在扬子江及康藏地区的游历考察活动、中国西南边疆史、康藏文化等论题,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缺陷和错讹略举
尽管库柏主观上是想认真记录下他能够考察、了解到的事实,和亲身经历的感受,使英国人能较大程度地了解中国西部及藏边的情况,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时代和个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库柏在叙述中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与准确,我们不难发现书中的缺陷和错讹,甚至与我们的立场、观点全然相悖的论述。
由于西方人当时对藏区情况的了解极其有限,库柏对藏东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的认知明显带有主观判断,错误地认为中国版图疆界应以打箭炉为界。库柏在其书中记述道,“西藏东部地区,包括打箭炉以西至澜沧江这一带,大约于1792年开始附属于四川省,四川总督的辖地扩展到巴塘以西。据古伯察描述,那里竖立了一块石头作为界标,这似乎表明中国人从未将藏东视为中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西部边界沿着折多山脉延伸而去,正好与四川省的省界相一致。”[3]228。紧接着,他又据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等人以及自己对打箭炉以西的藏人与四川人在种族、体型、外貌、语言、衣着、举止等方面的显著差异的考察,主观地认为:“即使是出于政治目的,也只有无知之人才会错将中国的边境移至金沙江岸,并把巴塘和理塘纳入四川省。其实,这些地方的民事权全由一名藏官行使——甚至为数不多的汉民也受其管辖。一名清廷武官统领卫戍部队,这表明清廷是靠军事征服才取得该地的统治权。不过,与其说是清廷官兵使西藏成了四川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满族统治者使四川成了满洲的一部分。”[3]228-229库柏的这番论述,表明他并不清楚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南边地的政治治理政策以及边地与内地的统属关系,不了解自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其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或许就是英国歪曲中国与西藏(或康区)之间行政隶属关系的发端。
库柏在描述藏族人的天葬习俗时,称“藏族人相信,秃鹰吃完污秽的腐肉,飞向天空,也会将逝者的一部分灵魂带往天堂”[3]270,他这种“灵魂升天”的主观认识并不正确。按照佛教教义,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尸体就成了无用的皮囊,死后将尸体喂鹰,也算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善行,一种功德。笃信佛教的西藏人推崇天葬,认为拿“皮囊”来喂食鹰鹫,是最尊贵的布施,体现了大乘佛教波罗蜜舍身布施的最高境界,并非库柏所认为的吞噬了尸体的秃鹰能将逝者的部分灵魂带往天堂。藏传佛教里并无“人死了可以上天堂”的说法。
另外,库柏对中国的某些史实细节了解得不够深入和准确,再加上很多信息都是来自当地人士的讲述,因此“道听途说”难免不会导致错误。例如,他述及法国天主教四川使团的传教活动时,所记载的年份与史实往往相差一两年,或为中西历书换算时产生的差错,又或为库柏本人当时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如其记述道:“四川传教团以徐新德阁下为豪,其作为宗座代牧区主教的教务工作止于1814年,那时他在成都被斩首”[3]122,这里的“1814年”有误。按历史记载,应为1815年,当年嘉庆皇帝强化禁教,徐主教在成都被斩首,头颅在城门上挂了三日。库柏行文中提到“在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期间,……主教怕出现暴动,不得不离开成都暂避风头”[3]122-123,其中“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亦有误,库柏很可能不知道在省会城市科举考试并非一年举行一次,而是三年一次的乡试或三年两次的成都府院试。再如库柏行至泸定,误将泸定县记述为泸定州,他认为泸定“不同于蛮子王权得到承认的边地”,由此就得出“严格来说,这(泸定)是四川辖境的最后一座城市”[3]196,这种判断明显带有主观性。接着在述及横跨大渡河的泸定铁索桥的历史时,他援引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神父所言,说“此桥建成于1701年”[3]197,实际上,泸定桥始建于1705年,建成于1706年。有一定历史知识的细心读者不难发现书中存在凡此类似的种种细节错误。
由于库柏不懂汉语,似乎并没有什么中国历史知识背景,缺乏对清政府管辖西藏地区的知识和现实的了解,他在游历考察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赖其随行翻译和法国传教士等人的帮助。如此这般,行文中出错的几率便会大大增加。
需指明的是,作者在著述《贸易先锋游记》一书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读者可能会对其某些叙述或细节提出异议,书中采用的地名因转译自它处,或因参考了地区方言的发音,也可能会使读者混淆。因此,在原著序言中,库柏谦逊地表明自己完全是本着“贸易先锋”的心态写下这篇游记的,希望读者不要将他视作一位自命不凡或细致严谨的旅行家,而只是一个单纯而真诚的贸易先锋。
注释:
①T.T.Cooper.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London:John Murray,1871.国外学术界一般简称为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国内学界对此书名的中文译名并不如一,有《一个商业先驱在辫子和小袄之国的旅行记》《身着汉装的商业先驱之旅》《头戴发辫身着马褂的商业先驱游记》《一个留辫子穿马褂的商业先锋的旅行记》《穿越中国到印度的旅行》《中国至印度之行》等。除此代表作外,库柏还有4篇相关考察论文连续刊发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论文集》上,分别是《库柏先生从扬子江到西藏和印度的探险之旅》(详参T.T.Cooper.Expedition of Mr.T.T.Cooper from the Yang-tze-Kiang to Thibet and Indi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12,No.5(1867—1868),pp.336-339.);《华西及藏东旅行记》(详参 T.T.Cooper.Travels in Western China and Eastern Thibet,(1870:June 13),pp.335-346.);《来自库柏先生的信:关于赞波、伊洛瓦底江及西藏一线》(详参T.T.Cooper.Letter from Mr.T.T.Cooper,on the Course of the Tsan-Po and Irrawaddy and on Thibet,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14(1869—1870),pp.392-395.)和《关于中国云南省及其边界》(详参 T.T.Cooper.O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Yunnan and Its Border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15,No.3(1870—1871),pp.163-174.)
②详参 Cooper’s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1871:June 17,(31:816),pp.774;A Pioneer of Commerce.Chambers’s Journal of Popular 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1872:Feb 17,(No.425).pp.106-110.
③William John Gill.The River of Golden Sand: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ough China and Eastern Tibet to Burma.London:John Murray,1880.该书1883年再版。威廉·吉尔(William John Gill,1843—1882年),清代官方文档译为“吉为哩”,民国徐尔灏又译“祈尔”,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西方著名的探险旅行家。1877年夏,威廉·吉尔溯长江而上,经成都、松潘、雅州、打箭炉、巴塘、阿墩子、东竹林寺、沙鲁、巨甸、石鼓、剑川、大理到英属缅甸,是近代西方成功穿越中国内地和西藏东部的第一人。为了表彰吉尔穿越藏东的开创之功及其考察成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分别于1879年、1880年授予其金质奖章。吉尔于1880年出版了《金沙江: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一书,国内学术界一般简称为《金沙江》。
④详参赵艾东《唐古巴的考察与英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觊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第92—101页。
⑤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128—133页;于乃仍、于希谦《马嘉理事件始末》,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黄嘉《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1868—18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6年版,第 41—54页;董志勇《关于印茶入藏问题》,《中国藏学》1993年第 3期;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黄显康《清季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茶叶贸易》,《大陆杂志史学丛刊》第四辑,第五册,第262页;冯明珠《清藏边域史地考察——近代中英康藏议界之再释(下)》,《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向玉成《论威廉·吉尔的康区行及其代表作〈金沙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84页;向玉成、肖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部分会员在近代康区的游历考察活动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61、62—63页;向玉成、肖萍《近代入康活动之部分外国人及其重要史实考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第62页;向玉成、肖萍《19世纪40—60年代中期法国传教士“独占”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76页;赵艾东《从西方文献看19世纪下半叶中国内地会在康区的活动及与康藏社会的互动》,《西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97页;赵艾东《1846—1919年西方人在康区的活动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赵艾东《1846—1919年西方人在康藏活动之基本认识》,《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第98页;[美]M.G.Mason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 34页;Alastair Lamb.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1767 to 1905.London:Routledge and K.Paul,1960.pp.122;[英] 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美]何溯源(William M.Coleman IV)著,汤芸译,彭文斌校对《巴塘事变:康区及其在近代汉藏史上的重要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 3期,第1—9页;P.P.Karan.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the impact of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 on the landscape.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6;Thomas G.Rawski.Chinese dominance of treaty port commerce and its implications,1860-1875;Douglas Wissing.Pioneer in Tibet:The Life and Perils of Dr.Albert Shelton.PALGAVE MACMILLAN TM,2004;Patricia Buckley Ebrey.Women and the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atricia Buckley Ebrey.Gender and Sinology:Shifting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Footbinding,1300-1890.Late Imperial China,1999,(Vol.20,No.2) .pp.1-34;G.C.Allen,Audrey G.Donnithorne.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Routledge,2013;James George Frazer.The Golden Bough.Palgrave Macmillan UK,1990;Joseph Earle Spencer.Trade and Transshipment in the Yangtze Valley.Geographical Review Vol.28,No.1(Jan.,1938),pp.112-123;D.P.Choudhury.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Calcutta:The Asiatic Society,1978;Gaines K.C.Liu.The Silkworm and Chinese Culture.Osiris,1952,(Vol.10).pp.129-194;Paul Pelliot.Le voyage de MM.Gabetet Hucà Lhasa.T'oung Pao,Second Series,1925—1926,(Vol.24,No.2/3).pp.133-178;Tkroy Choudhury.Histori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of North-Eastern Studies.Ethnicity,Mov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Rawat Pubns,2007;Y.Lu,P.Watson.Grand Canal,Great River:The Travel Diary of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Poet.Frances lincoln ltd,2007;Samuel Thévoz.Du lieu vu au milieu vécu:Litang sur la route des explorateurs (1846—1912);R.Gardella.Qing administration of the tea trade:Four facets over three centuries.To Achieve Security and Wealth:The Qing Imperial,1992;J.Bacot,E.Chavannes.Les Mo-so:Ethnographie des Mo-so,leurs religions,leur langue et leur écriture.1913。
⑥详参龙云、卢汉《新纂云南通志》卷168《外交考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纪载卷》,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⑦N.Boothroyd,Muriel Detrie.Le voyage en China[M].Bouquis,France,2001.
⑧详参《亿万华民》译友会译,亦文编撰《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八)》,《教会》2015年第5期。http://book.aiisen.com/news-6721.html.
⑨曲小玲摘译《成都—藏区之旅:1867年一个欧洲人探寻商路札记》,载段渝主编《巴蜀文化研究集刊》(第六卷),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242-247页。
⑩大约在今西藏察隅县印占藏南地区瓦弄附近。
⑪ T.T.Cooper.The Mishmee Hills:An Account of a Journey Made in an Attempt to Penetrate Thibet from Assam to Open New Routes for Commerce.London:Henry S.King&Co.,1873.
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年),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任上海海关税务司,1866年时已出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1883年退职返回英国,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库柏在书中将威妥玛当时的头衔记作英国驻华使馆秘书。
⑬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年),1844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福州领事,赴任途中曾留在厦门担任领事数月。1846年任驻上海领事。1859—1865年任驻日公使,1865—1871年任驻华公使,1871年退休返英。
⑭丁盛荣(Joseph Pierre Chauveau,1816—1877年),中文名又作丁德安、丁硕卧,1844年来华,在云南传教,1850年7月6日升任云南教区副主教,负责滇中、滇西教务,1860年到阿墩子(今云南德钦),1864年任罗马教皇驻西藏代表(西藏教区主教),同年2月离滇抵打箭炉赴任,任打箭炉天主教司铎,1877年客死打箭炉。
⑮范若瑟(Eugene Jean Claude Desfleches,1814—1887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甫,1838年来华入川,后为罗马教宗第一任驻川东代表。
⑯1967 年版:精装本,Arno Press,[1871]出版;2001 年版:平装本,495 页,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出版;2002 年版:平装本,496页,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出版;2005年版:平装本,495页,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出版;2009年版:平装本,492页,2009年Kessinger Publishing,LLC出版;2010年版:平装本,J.Murray出版,是1871年原版的再版;2011年版,平装本,497页,Adegi Graphics LLC;Elibron Classics series edition出版;2011年版:平装本,510页,British Library,Historical Print Editions出版;2013年版:平装本,140页,The Classics.us出版;2013年版:平装本,502页,Nabu Press出版;2015年版:精装本,502页,Palala Press出版。
⑰详参 http://books.google.com。
⑱[美]李国庆整理:《“中国研究”外文旧籍汇刊·中国记录》(第六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2]ROBERT K D,COOPER T T.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1885-1900)Vol.12.pp.1078-1079.https://en.wikisource.org/wiki/Cooper,_Thomas_Thornville_(DNB00).
[3]COOPER T T.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M].Boston: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5.
[4]Cooper’s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J].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1871:June 17,(31:816),pp.774.
[5]龙云,卢汉.新纂云南通志·外交考[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An Inquiry into the Overland Journey of T.T.Cooper from China to India and his Masterpiece 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ZHANG Li
(Chongqing China Three Gorges Museum,Yuzhong Chongqing 400015,China)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 was the first English traveler who attempted to explore a more direct trade route to India from Eastern Tibet of China since 1840.In his masterpiece 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he conscientiously recorded his expedition from the Yangtze River to Tibet and his travel homewards from Weisee in 1868,in which presented lots of facts which he was able to observe and learn,and the experience undergone by him for readers,such as the geographic landscapes,local customs,trade conditions and others,so the valuable work was th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that foreigners could know about Chinese,Western China and especially Eastern Tibet.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Eastern Tibet;A More Direct Route fo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Exporting Indian Tea to Tibet;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K25
A
1009-8666(2017)09-0088-12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9.015
2017-04-27
重庆市2013年度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重大委托项目“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搜集及青年人才培养计划”(2013—ZDZX04)之子项目——海外档案资料著作“蓄辫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游记——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翻译项目(2013—ZDZX0408)
张莉(1980—),女,重庆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方向:西南史地、博物馆学。
[责任编辑、校对:王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