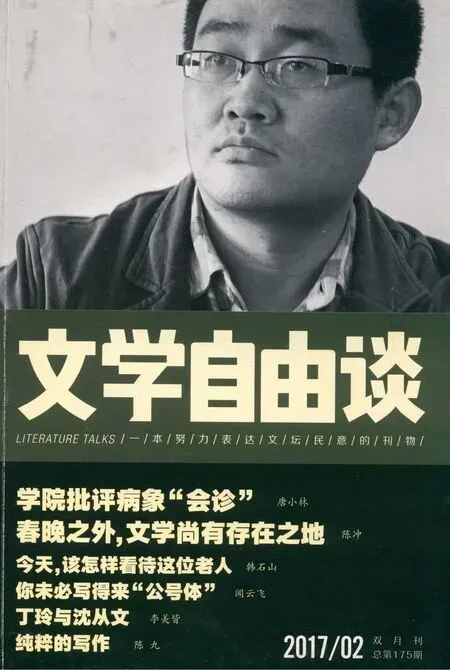今天,该怎样看待这位老人
韩石山
今天,该怎样看待这位老人
韩石山
2017年1月18日,张颔先生平静地离去了。活了九十七岁,可谓高寿。
这是一个从山西这块土地上走出来,又让山西这块土地增添了光彩的山西人。
从这一天起,这个发光体走了,留下的是永远不会消逝的光彩。
对他的离去,多少人都有悲痛之感,在我看来,准确地认识这位老人,认识他的身世和经历,认识他的功业和品质,不失为一种切实的悼念。
看他的经历,要逆着看,更要顺着看
张先生在世时,说到他的功绩,人们最常说的是,某年中央电视台的《大家》栏目分上下两集介绍了他,说他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侯马盟书》的破释者。从此以后,张先生在学术界的地位显著提高,过去只知道他是个专家,自此更知道他是一位大家。
若以外界的评价定地位的高下,我倒是觉得,《儒藏》书目收录了张先生的著作,更能彰显其学术成就。《儒藏》是2003年国务院立项,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篡中心组织国内外著名大学、研究所编篡的一套儒家思想文库,是一套书,也可以说是一个书目,收录了自《论语》以来堪称儒学经典著作的传世文献,共计200种,且都编了号。张先生一人就占了两种,分别是第90号的《侯马盟书》,和第137号的《古币文编》。
这样的成就,由不得让人想起了他的学历。
高小毕业!
用现在话说,就是小学六年级。
学历上失望了,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他的经历。
这时候,就看你怎么看了。
一种看法是逆着看,一种看法是顺着看。
什么是逆着看呢?就是站在他现有的学术成就上,回过头来,看他走过的学术道路。
这样看,让你震惊,也让你感叹。
震惊什么?感叹什么?
震惊和感叹的是,这个人,从小到大,一宗宗,一件件,像是专为他后来成为学术大家而设计的。甚至可以说,高人有意设计,都设计不了这么周到。
你看么——高小毕业这年,他的堂兄,一个在天津当铺做小伙计的年轻人,就出版了一本《天津典当业》,等于是他从小就知道出书这回事。毕业后,一时找不下工作,介休城里有家茶叶店的老板,风雅自命,组织了一个业余书画社。他参加了,跟上学习书法绘画篆刻,而他篆刻用的底本,恰是有名的《汗简》。够奇的吧。
解放后,他到了省委统战部。谁能想到,当时的省委里面,会有个文物陈列室,陈列着从解放区带过来的文物。他看了收藏的青铜器,竟动了写论文的念头。于是便写了两篇论文,遇上1958年大跃进,省上要成立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别的所一下子成立不了,考古所先成立了。要派个所长,一来二去,就选了他。别人都觉得可惜,而对他来说,不是将鱼儿扔进了海里?
总之是,逆着看,条条小路,都通向了一个辉煌的顶点。
但是,若顺着看,就不同了。
老百姓有句话,前头的路是黑的。也就是说,从小到大往前走,谁也不晓得前面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这样,你就知道,这个人这样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了。
他还没出生,父亲就死了,九岁上,母亲又死了。在祖父的呵护下,勉强念完高小,找不下事做,只能远赴湖北樊城,在一家介休人开的商店做学徒。解放后,如果在政界混下去,至少能做到省委统战部的部长,可是他身上文气太重,官气太少,便去了更适合他的考古所。一个不懂业务的人,当了业务干部,混日子就是了,而他偏不认这个命,刻苦自励,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
看他的学问,要看闪亮的地方,更要看扎实的地方
前面说了,若以收入《儒藏》目录的著作而论,张先生的成果有两项,一是《侯马盟书》,一是《古币文编》。
这两个成果,粗略看起来,是并列的,实则不然。应当说,《古币文编》是因,《侯马盟书》是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或许是早年学篆刻,张先生一到考古所,就喜欢上了古文字。他这个人,当过小伙计,凡做事,都爱做个簿子,见到古印玺、古钱币上的文字多了,便收集整理,做成一个本子,描摹下文字,一一注明出处。时间长了,起个名字叫《中国古代货币文编稿》,即《古币文编》的雏形。到1966年参与整理《侯马盟书》时,他已具备了扎实的古文字功底。
为什么在《儒藏》上《侯马盟书》排有前面,而《古币文编》排在后面呢?这是因为,《侯马盟书》1976年就出版了,而《古币文编》一直在搜集、充实中,直到1986年才出版。
说到张先生的学术成就,人们都说他运气好,当考古所长时候,正赶上山西发掘了“盟书”;要是没有这事,也成就不了他的事业。
我不这样看。
该是他的,想不是他的都不行。
“盟书”发掘出来了,就有人故意为难,要从中科院考古所请专家来,而省里有这样一位高水平的专家,中科院的人要来,也要想一想。说是这样说,那个年代,在学术上,没人敢开这样的玩笑。
还有人说,“盟书”上的字,没几个人认识,差不多全是蒙出来的。
这就是外行话了。
研究工作,十有八九都是靠“蒙”。胡适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个“大胆的假设”,说白了就是“蒙”。关键在于,有的人一“蒙”就对了,有的人一“蒙”就错了。“蒙”对了的,就是研究成果,“蒙”错了的,说什么都是白搭。
张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有机遇的一面,更有必然的一面。就是没有《侯马盟书》,光凭《古币文编》,他也是一流的学问家。
再就是,张先生在篆字摹写与研究上的功夫,也是不可小觑的。
记得前些年,我跟他闲谈的时候,他曾自负地说:“我这个人,就是在战国时代,也不会失业的,到了哪个国家,也会找个誊录的差事。”又说:“吕不韦写下《吕氏春秋》悬之城门,说能删一字者,可赏十金,即便黄铜,也是贵重的。我若在场,挣千金不成问题。”
这两句话,他都是当笑话说的,但我听了,却能听出说话人的自信。
他的自信,一是在古文字的书写上,一是在对文章的鉴赏上。只有写得了战国各国古文字的人,才做得了誊录的差事;只有写得一手好文章,又有鉴赏的能力,才能看了《吕氏春秋》,敢说可删去一百个字。
说张先生是个奇才,我承认,因为多少人有绝佳的训练,也做不出他这样的成绩。
但是,我更愿意承认,他是一个自学成才而又训练有素的学者。
看他的品质,要看常人具有的,更要看常人难以具有的
不管是青少年时期的历经艰辛,还是解放后的机遇及时,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外在的因素。
作为一个山西人,张先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业绩,还有他品质上的特异之处。
说两件事吧。
张先生的一生,还叫平顺,但是有两个节点,若把握不住,就不会有后来的张先生。一个是放弃了在樊城学生意,回到晋西,参加了山西的抗战;一个是解放后,从省委统战部,转到文管会,当了考古所的所长。后一个有服从组织分配的意思,不必说了。前一个,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若说联系人,就是写过《天津典当志》的那位堂兄,此时在晋西二战区驻地做事,知道了堂弟的志向,及时予以恰当的安排。能做出这个决定,有两个条件,一是毕竟高小毕业,有相当的社会见识,知道国难当头,有为青年应当奔赴抗战前线;还有一个条件,是他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又是个孤儿,不甘平庸,要为死去的父母争一口气。有见识,又有志气,再艰难也要回山西,这条路就走出去了。
再一件事,就是差一点把《古币文编》拱手让给了一位有名的古文字专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先生去北京开会,带着早已整理好的《中国古代货币文编稿》,让广州来的商承祚先生看了。商这个人可不简单:出身世家,父亲商衍鎏是前清的探花;少年成名,上大学时就出版过《殷墟文字类编》,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商先生看了张先生的书稿,说他也有许多古钱币文字资料,两人的资料可以合在一起,出一本《先秦货币文编》。过了不久,商先生从广州来信说,他已申请下一笔资金,请张先生将资料寄来。
在那个年代,这是个不小的诱惑。傍上商先生这样的名家,等于一步就跨上学术的高台阶。而张先生思前想后,觉得不妥,没有答应。后来商先生又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出了本书,水平之低,全在预料之中。
这件事情说明,张先生什么时候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受一时的诱惑。如果说他是图名,图的也是长久的盛名,不是一时的虚名。
这就说到张先生的品质。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在小事情上可以忍让,真要到了关系名声的时候,是绝不含糊的。就是平时,也不是个稀里糊涂的人。
常见写到名人的时候,爱说怎样的和蔼可亲,怎样的严以律己虚以待人,我觉得全是陈辞滥调,不合人情。张先生晚年,我去他那儿是比较多的。为写《张颔传》,有那么三四年,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趟。有时候我去了,张先生显出一副不胜其烦的样子。问他怎么啦,他说来了个什么人,喋喋不休,末了多半是要字或是题辞。
每当此时,我就想,我这么个三流作家,写一笔狗趴趴字,来人多了还烦,张先生这么大年纪的人,能不烦吗?
后来我见张先生用了个妙法,来人说得多了,他不愿意听,就糊涂起来,愣愣地呆在那儿,不知是痴了还是困了。来人见这个状况,也就不好多说什么,道个谢离去。
以我的观察,张先生一生的成功,若有什么品质上的保证的话,那就是执着,甚至有种“圪料”劲儿。圪料者,烧不透之炭渣也,质坚而带刺,晋地每以之喻人之顽劣。这,恐怕才是他品质中,最值得赞扬,也是最值得效法的地方。
张颔先生去世之次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