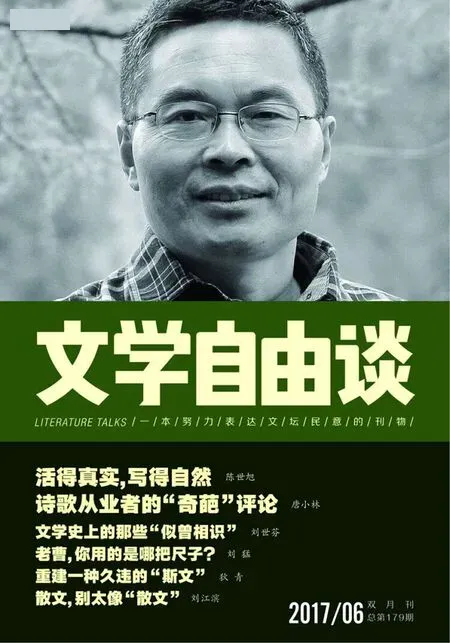凝望西南联大的背影
桑逢康
凝望西南联大的背影
桑逢康
《西南联大的背影》,是余斌由三联书店2017年7月新出的一本文史随笔集,恰逢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适时满足了社会上的需求。两年前,云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他的另一本同类的书:《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两者应为姊妹篇,我都拜读过,收益良多,印象颇深。
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艳丽的奇迹,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搭建茅屋上课,加上敌机不断轰炸袭扰,西南联大却在短短八九年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据前些年一项统计资料,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第一届评议产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西南联大师生总共有172人(学生90人,教师82人);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其中6位是联大学生。以上统计还仅仅是就理工科而言,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以及创作家,出自西南联大或与其有关者更是为数甚多,其中若干位称得上是大师级人物。正如余斌所言:“一个学校在培养人才上有如此卓越的贡献,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奇迹。”所以余斌把西南联大赞誉为“昆明天上永远的云”──灿烂的、辉煌的、令人敬仰与怀念的五彩祥云。
余斌原籍昆明,在故乡读小学和中学,1959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甘肃兰州工作。他是改革开放后新时期颇有影响的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创办人和主事者之一,其所著论文曾获中国社科院《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之后回到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从文艺评论家“转行”当了教授,二十多年来专门从事西南联大的相关研究,撰写了数量众多的文史类随笔,结集为上述两部专著。两本书都是以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期间的人和事为主,兼及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的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云南大学……两书的主题相同,内容互有侧重也有所重叠、交叉,可以起到相互印证和补充的作用。
西南联大地处昆明,想必作为昆明人的余斌写西南联大自然义不容辞,而且“天时地利人和”,写起来必定得心应手。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以往又不大注意遗迹保存,随着城市改造扩建,原西南联大校址、尤其师生们散居各处的房舍大多不复存在,寻找起来困难重重。余斌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写的文史类随笔重证据,重实地调查,绝不虚构瞎编。由于史料毕竟是死的而不是鲜活的,而且有欠缺和不够确切之处,所以必须加以丰富、提高、完善,通过实地调查加以印证或匡正。这样,余斌就选择了一条让自己费尽千辛万苦的路:眼到(尽量搜集和阅读大量有关史料,包括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腿到(四处奔波探寻各处旧址)、手到(访问知情人和联大名师后代并作详细记录)、心到(自始至终怀着对西南联大及前辈学人的敬仰之心)。真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靠笨工夫。”——这四句本是傅斯年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演讲中的名言。胡适很欣赏傅斯年的这种治学精神,我把它借用来加在余斌身上觉得也正合适。
当年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时,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常委会,实际主持具体工作的是梅贻琦;他们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教育家。云集于此的人文学科领域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就更多了,如西南联大的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王力、罗常培、唐兰、杨振声、川岛、陈梦家、游国恩、陈寅恪、钱穆、傅斯年、雷海宗、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贺麟、钱钟书、冯至、叶公超、吴宓、陈铨、卞之琳、潘光旦、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等。云南大学的也不少,如吴晗、李长之、林同济、胡小石、吴文藻、费孝通、吕叔湘、施蛰存、姜亮夫、纳忠、方国瑜、楚图南、徐嘉瑞等。当时在昆明的还有梁思成、李济、李方桂、顾颉刚、李何林、谢冰心、林徽因、光未然、李公朴、常书鸿、常任侠、查阜西、赵沨……可谓人文荟萃,卧虎藏龙。这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是一群以保存、延续中国学术与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为已任的知识分子。一句话: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与中坚。
这些文化名人的住地相当分散,而且居无定所,经常搬迁。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都留下过其中一些人的足迹,但要寻找旧址却相当困难,余斌戏称之为“门外考古”。仅举二例:
节孝巷13号是闻一多在昆明的旧居之一。余斌最早是在冯至写的《昆明往事》一文中得到线索的,其中有一句,冯至说他刚到昆明时,“住在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节孝巷是有的,但余斌多次走访,又遍查相关地方志资料,都未见有怡园巷一说。后来摸进紧挨着红十会医院的一所破旧小院,才从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嘴里得知这里就是怡园巷,早年只住了4户人家,她家老门牌是怡园巷3号。怡园巷现已名实双亡。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余斌又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得知:1940年8月,闻一多从外县回到昆明后,因一时找不到住处,便住在胞弟闻家驷的家里,“小东城脚下华山东路节孝巷13号,是周钟岳公馆的偏院”。住节孝巷得到了印证,但周公馆的偏院又在哪里呢?余斌做学问是一根筋,不得出个究竟绝不罢休。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回忆》中,查到了当时任内政部长的周钟岳在昆明的公馆位于“西仓坡若园巷”,又根据《吴宓日记》得知“若园巷就在玉龙堆”。余斌于是就去西仓坡、玉龙堆寻找若园巷,“问谁谁摇头,地名改来改去,记忆也随之丧失,蒸发”。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他经非常熟悉昆明老街老巷的同窗学友魏君介绍,走访了周钟岳的二公子周锡楠老师,这才确认了,在昆明“只有一处周钟岳公馆,在翠湖北路。节孝巷13号与周家无关,那房子既非周公馆正院,偏院更无从谈起”。节孝巷13号的房主是邹若衡,云南昭通人,担任过“云南王”龙云的侍卫长。魏君过去家住节孝巷11号,其父魏述征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挂牌行医,当年与闻一多是邻居。几经周折,闻一多的旧址才终于落到了实处。闻一多次子闻立雕2008年来昆明,曾由余斌陪同重访节孝巷的旧居遗址。
沈从文1946年夏写的《怀昆明》一文中,说他和家人在抗战初期在北门街蔡锷的公馆住过一段时间,那是“老式的一楼一底,楼梯已霉烂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声……大大的砖拱曲尺形长廊,早已倾斜,房东刘先生便因陋就简,在拱廊下加上几个砖柱。院子是个小小土坪,点缀有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两株”。余斌从沈文中得此信息,但三番五次考察,均无收获,在北门街根本见不到蔡公馆大门的任何遗迹。后经滇军耆宿黄毓成哲嗣黄清先生帮忙指点,初步确定蔡公馆位于北门街与丁字坡的夹角内,现在已是一个大杂院。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有一篇回忆,提到她和姐夫一家住此时,“在我窗下有一条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余斌循此提示,这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再次实地考察落实时,他没有和前几次那样从北门街那边的入口处进去,而是换了个方位,从丁字坡这边的入口处进去,一看,“果然是个大院落,虽说颓败杂乱些,但基本格局呈现出来了。确有两棵尤加利树(即桉树)……尤让人兴奋的是小楼还在,更关键的是那标志性的长廊居然也还在!”余斌终于落实了沈从文的这一处旧居,自然喜不自胜,因为这等于在昆明抗战期间的文化地图上又找到了一处文化名人的重要坐标。他在总结自己写作文史随笔的经验时说道:
在我看来,史料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依靠史料,人不能悬浮于空中而是生活在地上的。住要有居所,行就会在地上留下实实在在的足迹。二十年来,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寻访抗战时期许多文化名人(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作家)在昆明留下的旧居和遗址,找到那些旧居和遗址,相关的“记忆”才有依附体,写出来的文章才有可触摸的历史“现场感”。
这是余斌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 《西南联大的背影》和《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最大的特色、最耀眼的亮点。有评论说,余斌绘制了“战时昆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全息图”,丝毫也不过分。
还值得注意的是,余斌并非在为西南联大写校史,而是在写文史类随笔,通过人物群像的精雕细刻或粗线条勾勒描画,让西南联大及其精神风貌复活,让读者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看到西南联大的背影。这样的书写既是两本书的又一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所谓“文史类随笔”也者,内容是“史”,形式为“文”;具体一点说,历史是它的骨架,文学是附在骨架上的外衣。前者要求坚实厚重挺拔,后者要求华美生动感人,两者均不可偏废,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附质也”和“质待文也”。“文”强则“质”胜,“文”弱则“质”衰,“质”不行,“文”再好也无济于事,甚且有害。而“随笔”实际上是散文的变种,应当与散文同类。这种写法虽说比较自由,但“文”既与“史”挂钩,就必须要于史有据。
文史类随笔由于既可增长历史知识又能得到文学享受,所以近些年来大行其道,颇受读者欢迎。余斌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两本书,由约120篇随笔结集而成,“质胜”是不待说的,“文盛”也是不待说的——余斌科班出身,擅长文学评论,又是著述丰富的大学教授,学识深厚,文笔老到。他写文化名人及昆明风物,娓娓道来,文情并茂,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无论寻到遗址时的兴奋与喜悦,还是旧址已荡然无存的无奈与惋惜,一波三折,夹叙夹议,有的篇章或段落简直像小说一般引人入胜,让读者随作者之喜而喜,随作者之忧而忧。无论大事件还是小细节,说史有依据,笔下有文采,两者相得益彰,这样的文史随笔焉有不受读者欢迎之理?
余斌在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都怀着对西南联大的敬仰与怀念之心,怀着对故乡昆明深厚的眷恋之情。从中年到老年马不停蹄穿行在昆明的旧街老巷,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西南联大的背影,他心潮澎湃,文思勃发,不仅写当年的那些学者教授作家,同时也把自己摆进去,抒发自己的情怀。请读下面一段文字: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兴隆街毕竟变了……不光比从前显得更窄,也更少了街的意味。顺街观光,家家户户都在门口垒造了袖珍厨房,厨房两两相对,剩下的街面仅三米左右,从中穿行,不像逛街,倒像进入一条紧缩拉直的、长长的带形大杂院,街坊们投向我的目光分明在问:“你找哪个?”
我哪个也不找。
我找的是那条文化曾经兴隆过的兴隆街。关于这条酷似带形大杂院的兴隆街,查了查书,据说命名于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感觉告诉我,这条老老的兴隆街仍将静静地躺在那里象征逝去的岁月。
逝去的岁月,文化曾经兴隆过。凝望着西南联大的背影,想象着昆明天上的那片彩云,我们今天又该作何想,该做些什么呢?我想,余斌的这两本书一定会促使读者认真地思考。
《幸存者》
陆天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作者“中国三部曲·骄阳”之第一部。作品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代承上启下的热血青年,曾经的风雨激荡,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中所留下的足迹。
《三峡书简》
王 彬著 作家出版社
这本散文集充溢着对苍茫生命的解读,文字中透射出的感怀,具有时间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广阔性,物与理、情与辞相得益彰,俊朗、阔大而精微感人。诚如作者所言,散文无非是对生命的一种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