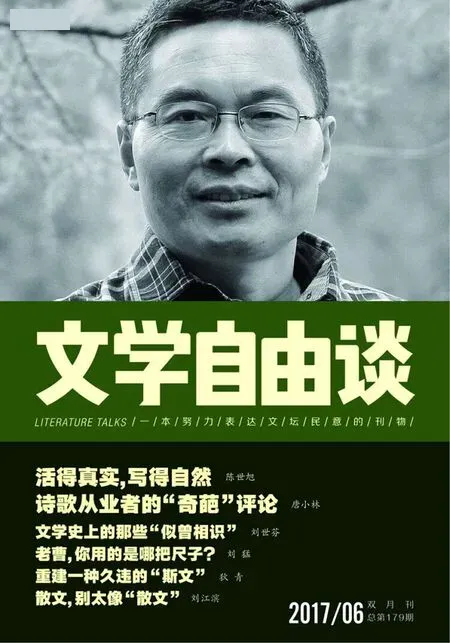诗歌从业者的“奇葩”评论
唐小林
诗歌从业者的“奇葩”评论
唐小林
晚唐诗人、诗歌理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开篇就深深感叹:“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在我看来,司空图所说的“辩于味”,实质上就是说,只有懂得诗歌艺术和具有欣赏能力的人,才能够谈论诗歌。但吊诡的是,在当今诗坛,一大批有极高学历,但并没有多少诗歌鉴赏能力的人,却在成天谈论诗歌,并且以此为业。这些来自学院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诗歌从业者,成了当今文坛诗歌研究的主体。他们那些美其名曰“诗歌评论家”的“研究”,大都谈不上有什么对诗歌的真正感悟,而往往都是抱着一大堆彼此相同的资料,为“研究”而“研究”,看似知识渊博,实际只是迷惑外行的学术“砖著”和高头讲章。
对于当今诗歌的弊病,流沙河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一切美好的诗歌都有秩序”,而“现在好多新诗不耐读,因为没有秩序”。他认为,诗歌的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一是意象:“语言要条理通顺,简单、准确、明了。不能自由散漫。意象的秩序更加艰难。优秀的诗人可以把常见的意象组合在一起,给人新鲜感和震撼。”但当今的诗人,可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浮躁的一代。他们对于前辈的诗人,不是采取艺术地继承和扬弃,而是动辄以推翻传统、另起炉灶的极端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自从“第三代诗人”“打倒”北岛、“打倒”朦胧诗之后,诗歌就再也不讲“秩序”,再也不讲音乐性和节奏感了。诗歌的音乐性,被当成敝屣,以致使诗歌堕落成了徒有其表的分行文字。在广场舞一样集体起舞的看似热闹的诗歌写作中,大量口水诗以“口语诗歌”的名义,披上“先锋”的外衣,将先前优良的诗歌传统连根拔掉。不断出现在各种文学期刊上的“烂诗”,更是受到某些诗评家们不遗余力的吹捧。这种自欺欺人的写作,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写诗再也没有门槛,凡是能够写几段分行文字,或者会敲回车键的人,都摇身一变成了“诗人”;诗集出版,从此成了出版毒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最终成了当今诗坛的经典笑话。
对于这样一种文坛怪现状,与诗人同在诗歌这口大锅里混饭吃的某些诗评家们,不是去直面当今诗坛艳若桃花的红肿,为当今诗人陷入泥淖的写作对症下药,而是失去理智地对某些诗人的平庸之作进行长年累月的热情讴歌,对读者进行瞎忽悠。有的诗评家甚至十三不靠地盛赞说:“有评论家和研究者说,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格局中,诗歌的成就要高于小说和其他文体,这似乎得到了国际的认同。在我看来,这并非就是诗歌的胜利,或者说是小说和其他文体的溃败,而是因为诗歌坚守了它的原点。”至于所谓的国际认同,或许只是个别汉学家——如顾彬所代表的外国人对当今某些诗人的友情赞扬。在他们的心目中,顾彬就代表着“国际”,这就像在某些小说家的心目中,马悦然就代表“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至于所谓“诗歌坚守了它的原点”,更像是一句呓语;我敢说,即便是那些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们,也根本就弄不清这样的“原点”,究竟指的是什么玩意儿。
更为蹊跷的是,诗评家们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诗歌评论和八卦似的“研究”文字,居然堂而皇之地被当作学术成果,大量炮制出来,这其中的原因,或许就像是一个文坛的“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以下几位诗评家,堪称当今诗评家中沉疴在身的典型代表,透过他们的奇葩评论和诗歌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为当今诗坛的乱象摇旗呐喊、烈火浇油,制造新的混乱。
耿占春:越玄幻越快乐
在当代诗评家中,耿占春的文章,素以艰深晦涩、掉洋书袋著称,就连其许多书名都起得跟玄幻小说似的,高深莫测,神神道道,让人莫名其妙,诸如《沙上的卜辞》《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失去象征的世界》等等。耿占春的这些书,就像九娘娘的天书,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在痛苦的阅读中不禁一声长叹:难道耿占春真的是在把学术文章当成玄幻小说来写,或者立志要写出一部理论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读书人难以下咽、彻底蒙圈?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家,从来就没有引述过任何一位“老外”的理论著作,照样能够将自己的理论、对诗歌的见解表述得一清二楚。但对耿占春来说,一旦没有外国人的理论和观点来为其撑腰打气,就彻底没有了底气。
在《失去象征的世界》一书中,耿占春恨不得将其理论仓库里所有的武器都一股脑用上,外国理论家在书中扎堆,挤得汗流浃背。哈贝马斯、考德威尔、托多罗夫、布尔迪厄、安德烈·巴利诺、让·波德里亚、查尔斯·泰勒等等,被耿占春拉扯出来为其专著“捧场”和“站台”。而耿占春一贯采用的,就是这种高射炮打蚊子的方法,武器看似非常先进,却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效果,反而更加让人云里雾里,找不着北。在这部研究汉语诗歌的书中,耿占春以所谓“象征”为切入口,居然大谈什么中国古代的分类体系所依据的最基本的原则是“空间上四个区域的划分”:“四个区域有四种动物命名并主管。青龙为东,朱雀为南,白虎为西,玄武为北……”然后再进一步将每一个方位之间的区域一分为二,就有了对应八个罗盘方位的八个分区和方向,依次与八种力量相联系……诸如此类喋喋不休、东拼西凑,与诗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裹脚文字,大量充斥在耿占春的这部诗学专著中。这样下笔千言、博士买驴的文字,海阔天空,上下古今,始终就像梦游一样,在耿占春的书中肆意泛滥,一路横行:“今天看来,除了研究汉朝的典章制度之外,《礼记》文本缜密的象征主义,它叙述上的形象与概念的融合,读来犹如一首宏大的象征主义诗篇。《礼记》不仅是一种对典章制度的解释,还是一个包容一切的象征主义的知识体系,其中的观察具有天文学和动植物学的精确性,然而又充满象征主义想象力。”
把文章写得如此貌似很有学问,其实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而又能够在学术界大受青睐,让人“不明觉厉”,确是一种“特异功能”。我始终觉得,耿占春就像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司机,总是喜欢猛踩油门,炫耀自己的“车技”,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飙,以致跑掉了车轮。在分析诗人沈苇的诗歌时,耿占春以所谓的诗歌“自我地理学”,不厌其烦地一直谈到沈苇的散文集《新疆地理》,然后再谈到其中的文章《吐鲁番》,继而大量引用原文,并由此得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沈苇在《新疆词典》中创造了一种诗歌式的论证话语。”至于什么叫做“诗歌式的论证话语”,恐怕连耿占春自己都不知道,但从此诗歌界又冒出了一个“新词”。
不仅如此,耿占春还满嘴跑火车地飙捧沈苇说:“诗人创造了关于吐鲁番的诸事物的一个谱系:水=葡萄=翡翠之灯=少女=葡萄树,也许还要加上那孜库姆舞+木卡姆+宴饮+狂欢,她们等于活着的吐鲁番;可是还有另一个等式:故城=古墓=千佛洞=残片=摩尼教残卷=‘民俗活化石’村庄=红色灰烬的火焰山=博物馆=木乃伊和化石……而且这两个等式之间既存在着区分也存在着等同。在这个等式的深处,隐匿和显现着一个修辞幻象的基础:死亡=生命。”如此应用加号与等号来罗列文字,故作高深地阐释诗歌,可说是耿占春的一大发明,它可以使那些对诗歌不甚了解的读者,对其巫师一样装神弄鬼的文字,崇拜得五体投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耿占春诗歌评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喜欢在文章中显才露己,卖弄学问。而这些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一大堆摆放在书中的僵死文字。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家们在阐述自己的诗歌理论或者评述诗歌时,往往只用极为精炼的文字,或者用几个形象的比喻。但耿占春在分析诗歌时,似乎根本就看不上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一律依赖于外国人的文艺理论。在分析王小妮的诗歌时,耿占春写道:“诗歌的象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象征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创造物,它依赖于我们语言的象征功能,事物普遍存在的象征作用,依赖于象征化的世界观。”或许,耿占春已经意识到这种梦幻似的文字很难有人能够真正弄得懂,于是便自己给自己铺设一个台阶说:“为了理解上的方便,姑且给语言的变化一个描写性的图式:从词语的立场上看,语言最初是‘象征的’,无论这种象征的基础是原始的自然宗教还是一神教的;其后语言演变为‘再现的’,福柯在《词与物》中把这个过程描述成17世纪以后才发生的,但在中国诗歌和文学中,语言的再现功能显然远为早于这个时间;在西方,自从马拉美开始,在语言的再现危机中转向语言的自我指涉功能。”
可以说,耿占春这种“套路”,完全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只能使读者越读越糊涂。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论述“含蓄”,仅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漉满酒,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48个字,就将其论述得清清楚楚了。而耿占春用了36万字来论述“象征”,但笔者在阅读之后,脑袋里始终像有一桶糨糊,总是稀里糊涂。
霍俊明:萝卜快了不洗泥
翻开文学杂志或学术期刊,“霍俊明”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我的眼前。1975年出生的霍俊明,在《文学评论》等中文核心期刊居然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在其他期刊发表论文和随笔数百篇。看到这个数字,我不禁大吃一惊:如此的高产,在世界学术史上,或许都是一个奇迹。可以说,霍俊明的写作,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
此刻,我的耳畔仿佛听到了霍俊明急速敲击键盘的声音。为了追求写作的速度和高产,他似乎快得连打标点符号的时间都没有,更不要说文章写好之后,再认真仔细地检查一遍。正因如此,霍俊明的文字,在众多诗评家中的“辨识度”非常之高,这就是:句子打搅,文字粗糙,字里行间冒出的“泥沙”,就像恒河沙数。如这样的长句子:“但是,反过来当智性追求下的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和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无形中诗歌写作的多元化这一说法 (,)是需要重新过滤和打量的。”(括号中的标点为笔者所加)又如这样一望便知的错别字:“在滇南高原我不其 (期)然间与成片的红艳曼陀罗花相遇。”“2012年深秋(,)我和沈浩波的(在)云南高原再次相遇。”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霍俊明这样的博士后,写出的文章总是疙疙瘩瘩,甚至连“的、地、得”的基本用法都分不清楚。如:
有小说家的诗歌朱零说到(道)“当叙事成了当下诗歌的主流,小说家们写起诗来,心中也就多了些底气。”
这样的句子,怎么看怎么别扭。这像一个博士后写出的文字吗?此句可改为:对于小说家的诗歌,朱零说道:“当叙事成了当下诗歌的主流,小说家们写起诗来,心中也就多了些底气。”
他(沈浩波)立足于充满活力语言基础上的对历史和社会空间下个体和灵魂的不留余地的自我剖析与撕裂当下诗坛无出其右者。
这是一个典型的句式杂糅的病句。犯这类语法错误的人,通常是小学和初中生,一个语文成绩中等的高中生,都不会犯如此低级的语法错误。此句可改为:他立足于在充满语言活力的基础之上,对历史和社会空间下的个体和灵魂,进行不留余地的剖析。这在当下撕裂的诗坛,无出其右者。
更多诗人的偏颇在于他们在很小的面积上找到身体的同时,急切而功利的(地)对欲望的奔走(,)却恰恰使灵魂再度受到忽略和沉沦。
“受到忽略”,在汉语里说得通,但“受到沉沦”却根本就说不通。这句话的毛病,一是表现为句式杂糅,二是语词搭配不当。
炫耀学识,卖弄理论名词,这在当今的批评家中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霍俊明虽然比耿占春年轻,但在名词大轰炸方面,却直追耿占春。如:
而随着“空间转向”,空间诗学以及“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也随之呈现了诸多哲学思想以及社会思潮的交叉影响 (比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空间的具有差异性的理解)。其中代表性的空间理论“空间社会学”、“异质空间”、“空间对话”、“诗性地理”、“诗意空间”、“想象性地理空间”、“建筑的空间伦理”、“光滑空间”、“条纹空间”、“多孔空间”、“第三空间”等。在福柯看来20世纪必然是一个空间的时代,而空间在公共生活中显得极其重要。空间、地方、地域、场域、地景(landscape)等词一旦与文学和文化相关(,)这些空间就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精神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在读到这样的“诗学理论”文章时,会不会直接“跳”过去,但就我而言,与其说这是理论文章,倒不如说更像是霍俊明在跟相声演员练习“贯口”,一口气可以说出如此众多的“空间”“地域”“场域”。
霍俊明极具“创新”意识,立志要做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论家。其文章比喻之怪异,恐怕连杜甫先生看了都会大吃一惊,天底下竟然有如此大胆比喻的:
江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着高烧的时代“乡愁”诗人,而他又以骨刺一般坚硬、疼痛的方式刺向一个时代病困重重的子宫和躯干。
她的诗歌在寻找到精神渊薮的繁密卦象和真实不虚的纹路的同时(,)却并没有关闭个体和世俗的通道和可能。
雷平阳在诗歌中不断抬高精神的高度,最终个体想象视域中的神学景观就诞生了。
我认为,霍俊明在写作时,更像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以为自己可以上通神灵、下愚读者。我从来就不相信,一个诗人会有什么“骨刺”,可以刺向时代的子宫和躯干。请教霍俊明先生,时代如果真有子宫的话,这个子宫究竟在哪里?如果这个“子宫”是霍俊明无中生有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我敢说,霍俊明的文章就像是堂·吉诃德的长矛,颟顸地刺向风车。如果真有诗人在其诗歌里寻找“精神渊薮的繁密的卦象和真实不虚的纹路”,我敢说,这样的“诗人”就是十足的神经病。我不知道,霍俊明在写作时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不可理喻的奇怪想法。说雷平阳凭几首诗歌就能不断抬高精神的高度,产生神学景观,这不就如同说雷平阳能够抓住自己的头发直接升空,纯属天方夜谭吗?
谭五昌:在诗坛“飙高音”
2013年,由学者谭五昌主编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隆重亮相,而主编者谭五昌的大作《诗意的放逐与重建》一书,也堂而皇之地选入其中。从此,我们便知道,中国文坛有一位叫做谭五昌的“新锐”批评家。至于谭五昌究竟“新锐”在何处,我在拜读了该书以后,根本就没有发现。客观地说,谭五昌的诗歌研究,在写作思路,以及具体的文本上,与当代一些学者不期而遇地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倾向。这里我们就其有关“女性写作”的文章,与其他学者的文章进行比较:
翟永明在为自己的《女人》组诗所写的序言《黑夜的意识》中最早直接地挪用了“女权主义”的术语,并从阐释 “黑夜意识”的角度给女性的诗歌下了这样的定义:“一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的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谭五昌
黑夜意识在女诗人创作中的突显,是随着个人和身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她们对黑夜经验的观照,开始是通过身体去感受,到后来逐渐转为以灵魂去接近和审视。“一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的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这就是诗。”
——刘波
女性诗人们普遍采取的一个女性话语建构策略便是大量寻找并使用女性身体语言或身体意象。这首先源于她们高度的女性觉悟,同时也受到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等人的强有力影响。
“女性写作”的另一个艺术向度是普遍的“自白”性话语方式。女性诗人早期都深受美国“自白派”诗人(尤其是普拉斯)的创作影响,这一点已是中国当代诗歌界公认不争事实。
——谭五昌
女性诗歌写作,首先要突出的就是“性别经验”,这种“性别经验”对于女诗人来说,就是将一些原来只能在闺密中私语的东西,用“独白”的方式,大胆地在诗歌中表现出来,这种方式,在女性诗歌出现的早期被认为是借鉴了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经验,此一说法,后来也得到了女性诗人们的回应与认可。
——刘波
陆忆敏的诗作《美国妇女杂志》则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宣告女性意识的“猛然”觉醒,不啻是一篇女权意识的诗歌宣言……
陆忆敏从一本《美国妇女生活》(笔者按:同一本杂志,在谭五昌的文章中居然出现了两个名字。陆忆敏原诗的名字为《美国妇女杂志》,由此可见,谭五昌对其所研究的诗歌作品根本就不熟悉)好像“突然”获得的女性觉醒确实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意义。
——谭五昌
像上海女诗人陆忆敏,她就因为一首《美国妇女杂志》,被认为是与翟永明齐名的源头性女诗人之一。
——刘波
在此,笔者无意去追寻究竟是谭五昌“借鉴”了刘波,还是刘波“借鉴”了谭五昌,或者他们共同“借鉴”了其他学者,但其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们的文章简直就像孪生兄弟一样,惊人地相似。
谭五昌在《在北师大课堂讲诗》中,对这样的“诗”推崇备至:
20米×48米/占地 960平方米/这是您的公寓/23米×5.1米/占地117.3平方米/这是您的套间/6.5米×4.2米/占地27.3平方米/这是您的客厅/5.6米×3.4米/占地19平方米/这是您的卧室……0.2×0.3米/占地0.06平方米/先生,这是……测量员停顿了一下/您的盒子
这首名为《便条集之二五八》的诗,出自《0档案》的作者于坚之手。有学者指出:“在过于‘聪明’的于坚身上,看不出什么大气、锐气和正气,他给人越来越多的是妖气、土气和匪气……”“当现代化变成世界唯一的未来之途之时,他的诗意诗思诗情渐渐消失,焦虑性、疯狂性和技术性已成为他诗学探索的审美表征。”在我看来,于坚的《0档案》和《便条集之二五八》这样的诗歌,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衣,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留给读者的,也许就是一个荒唐的笑话。以口语诗歌的名义,将诗歌蜕变成为口水,于坚已获得 “成功”。想不到谭五昌却告诉他的学生们说:“《便条集之二五八》一诗用非常日常化的口语方式创作,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诗里有一种虚构的成分,实际上这种表面非常写实的叙述充满了寓言性的,再次表明了于坚作为一个重量级当代诗人的过人智慧。”如果说于坚真的有什么过人智慧的话,这样的“智慧”就是能够让某些人在被当猴耍之后,还要服服帖帖地赞美他的口水一样的“诗”。
把诗歌评论写成“表扬稿”,用“飙高音”的方式,大肆讴歌诗坛风景独好,无疑是谭五昌的文章最清晰的“辨识度”。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谭五昌已经把自己历练成了一名出色的捧人高手。他吹捧黑大春:“人们根据黑大春在多年创作历程中始终保持着的坚定抒情姿态而将他称之为中国诗坛‘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吹捧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似乎是不可谈论的,他的生命存在与诗歌存在几乎类似于一个难以理喻的‘巨型神话’……海子的追求与矛盾表现都超出了人的想象与理解限度……正是海子身上土地般本能的旺盛的原创性抒情才能,才最终成就了海子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罕见的传奇。”对此,我想请教谭五昌先生:中国诗坛的浪漫主义者从什么时候遭到了彻底的阉割,在黑大春之后就已经彻底灭种?在诗坛制造神话,毫无节制地吹捧,使谭五昌的诗歌评论常常沦为“谀评”。
与霍俊明非常相似的是,谭五昌虽然出身名校,并且身为博士,但其中文基础,却常常令人哭笑不得。除了文章写不通顺之外,谭五昌连“他们”的用法都搞不清楚。如:
后来我又发现,有些研究生和本科生还将“第三代诗歌”作为他们(她们)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对象。
《现代汉语词典》明确指出:“在书面上,若干人全是女性时,用‘她们’;有男有女时用‘他们’,不用‘他(她)们’或‘他们和她们’。”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懂,难怪谭五昌的文章常常会闹出许多笑话。如:
海子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形式感。说其独特,是因为海子从不刻意追求形式(因为海子坚信“伟大的诗歌是一次性行为的诗歌”),但他作品中的形式却获得了某种自足与完美的性质。
看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我不知道,海子什么时候说过伟大的诗歌与“性行为”有关系。我猜想,谭五昌或许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次性”行为,但由于不尊重标点符号的使用,在文章中乱用“性”,也就出现了这种手不应心的“奇葩”写作。又如:
1989年,伊沙的诗作在美国华文诗刊《一行》上发表作品,受到《一行》主编、诗人严力的赏识。
这段文字中,“发表作品”的应该是伊沙,而不是他的 “诗作”,这里可去掉“的诗作”三个字,或者直接将后面的“作品”二字去掉。
刘波:在诗坛“笑熬糨糊”
在当今的诗评家中,刘波同样称得上是一位高产能手,仅我买到的就有《当代诗坛“刀锋”透视》《“第三代”诗歌研究》《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四部“诗学专著”。但这些专著,并没有让我看到多少值得欣赏的学术价值。刘波书中的内容,只不过是“交叉出版”,四部书中的文章和内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今天,年轻的刘波在诗坛上“笑熬糨糊”,居然能一口气出版如此之多的诗学著作,这确实是一个令众多学人羡慕不已的奇迹。
但“多种地,多打粮”这样的思维,并不适合学术研究。笔者发现,当今诗评家们的学术研究,大都乏善可陈。其写作套路颇类似于“诗歌史”的写法,不外乎时代背景、著名诗人的观点、作品特色及点评,然后就是曲终奏雅,进行一番海阔天空的狂热飙捧。在同一条思维路径上行走的这些诗评家们,只顾一个劲地忙着写,却很少去考虑是否能够慢下来,静心写出一部令人称道的诗学著作。研究诗歌,没有必要像当今那些扰攘不休的“诗人”一样内心狂躁。一个从事诗歌研究的学者,首先应该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就此而言,刘波的诗歌观点和对某些诗人的评论可说是极为怪异的。我甚至怀疑刘波是否真正懂诗。
在《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中,刘波写道:“朦胧诗人和海子所创造的箴言型诗歌,一方面赋予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以某种美学高度,另一方面,也让诗歌成了被简化的文学形态。有人就此认为,最好的文学就是能写出几个有哲理性的漂亮句子,最终让人记住。这种带有‘投机’性或简化的写作,其实为诗歌带来了一场美学灾难,最典型的莫过于汪国真……汪国真的诗歌影响甚至一直还在,导致很多读者在诗歌阅读和理解上单一化,认为除了汪国真那样的诗歌之外,其他写作就不是诗了。”
刘波这样的偏激和煽情,可说是思维混乱的结果。当今的诗歌遭受读者前所未有的冷遇,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样的板子岂能打在汪国真的身上?刘波在文章中气势汹汹地口诛笔伐汪国真,继而夸大其词地厚诬汪国真先生的写作是“投机”性的写作,为诗歌带来了一场灾难。如此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可谓有失学人品格。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读汪国真,有人喜欢读于坚和伊沙,难道我们可以就此断定,喜欢读汪国真的人就是低级庸俗,喜欢读于坚和伊沙的人就是情趣高尚吗?在刘波看来,汪国真简直就是当代诗歌的敌人,必须坚决、干净、彻底地清除其余毒,才能使中国的诗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但从刘波对雷平阳的诗歌《杀狗的过程》的追捧,笔者倒觉得,刘波的审美趣味和诗歌鉴赏能力,未必就比那些汪国真的“粉丝”们高明。
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学会包容。许多读者不读当今诗人的诗歌,而读汪国真,这或许正说明当今许多诗人的诗,确实不如汪国真的作品。读者并非都像刘波认为的那样,个个都是傻子,有好的诗歌却不去欣赏。诗人流沙河先生就一针见血地说:“现在很多诗都是口语、大白话,甚至口水话。”既然是口水话,读了又有什么用?
在刘波的眼里,只要与传统和朦胧诗对着干的诗歌,就是有难度的写作,就是有创新的好诗。有一位叫做余怒的诗人,本身并不为人们所知,其吸引读者眼球的方式,就是在写作中把胡思乱想排列成行,冒充诗歌。如其在《动物性》中写道:“艺术产生于困惑:一个女人/握着一个球。艺术使我敏感/从属于她/沉默中一顶说话的帽子/她拆字,拆一头动物。”对于这类或许连余怒自己都不知道要表达什么的“诗”,刘波强作解人地分析说:“在他笔下,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恒常的,他需要打破的就是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思维方式转为词语,就是以想象推动每一个意象前行,而我们在读到下一句之前,根本想不到诗人会出什么招数,这是疑惑,也是诗意本身。”基于这种不着四六的想法,刘波盛赞余怒的这首诗“有让人回味的力量”。
把狗肉当成海鲜,这是刘波飙捧那些平庸诗人的惯用写作方式。余怒《从画面中突出出来》的诗中有这样几句:
在视频里我看到桌子、椅子、灯泡、双人床、叠好的
被子、空气,尤其是她。像一个裹挟在嘴里的陈述句。
香水味凝成的空间感,形成一个倒三角。
猫趴在她的胸脯上,她用胸脯同它交谈。
整首诗犹如一个疯子的呓语,而刘波却称最后一句“她用胸脯同它交谈”是点睛之笔,既是画面形象的展现,又是一种精神交流的转换。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种精神交流的转换,倒不如说是一种撩拨荷尔蒙的肆意挑逗。但在刘波这样的诗歌研究专家看来,余怒所主张的歧义,其意图就是让语言中的现实变得复杂,让人有思考和审美的空间;余怒用这种色迷迷的“咸猪手”似的挑逗之词来刺激读者的做法,反而开阔了读者的思维,拓展了诗歌的美学空间。总而言之,余怒那些胡乱拼凑的诗歌,在刘波的眼里可说是通体完美。刘波激情无比地赞颂说:“余怒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同时也定位了自己的诗歌美学,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随着这两方面的融合,一种审美风格在余怒这里形成了自觉,自觉地拒绝简单,自觉地寻求难度。”“在当下,需要余怒这样的诗人,他会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创造和与众不同的审美。”“正是有余怒这样的诗人,或许我们才看得到现代汉语诗歌的希望和前景。”
刘波良莠不分,竟然匪夷所思地把余怒这样忽悠读者的分行文字吹捧得天花乱坠,如此畸变奇葩的审美情趣,反倒有可能误导那些对诗歌鉴赏一知半解的读者。一个把伪诗当做中国诗歌的希望和前景的学者,一个自以为是,在中国的诗坛上指点江山的“学术莽夫”,只能把本已是一潭浑水的诗坛,越搅越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