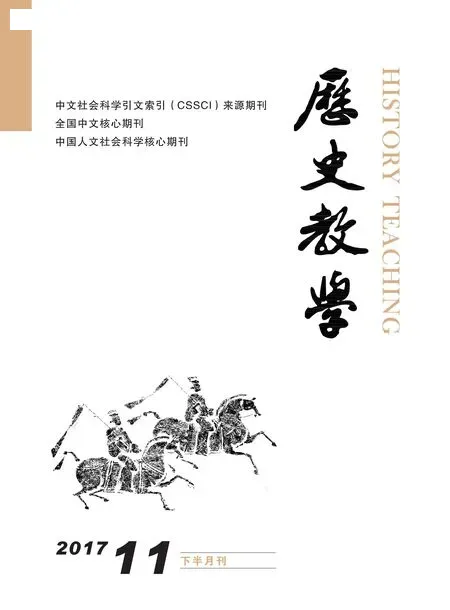两汉“上公”名号新探*
徐 鹏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学术界对于两汉时期“上公”名号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如对于“上公”名号的内涵,安作璋、熊铁基认为:“所谓上公,即是指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官。”①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1页。卜宪群认为:“所谓上公应指位在三公之上的公。”②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5页。谭景玉也认为,上公即三公之上。③谭景玉:《汉代上公制度考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阎步克认为:“上公、公、上卿、卿的概念,确实也为高级官僚的管理提供了便利。因为‘若干石’的禄秩至中二千石而止,中二千石之上的重臣,主要就是靠上公、公、上卿、卿的概念区分资位的。”④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46页。郭俊然认为“上公”存在三种含义:“分别为高于三公的官、类于三公位的官和爵位。”⑤郭俊然:《汉代“上公”职官述论》,《唐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上述说法有力推动了秦汉“上公”问题的研究,但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并不能止步于此,对于该名号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仍具有讨论的空间。“上公”何时出现于汉代现实政治当中?在两汉政治史上,“上公”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鉴于此,笔者将通过梳理“上公”名号在两汉时期的演变过程,探究“上公”在不同阶段的内涵。
一、元始四年以前无“上公”之位
汉代的“上公”何时出现于政治制度当中?由于认为“上公”乃高于三公的官员,学者遂将太师、太保、太傅视为西汉时期位居“上公”的官员。其依据出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⑥《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6页。“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绶。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⑦《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6页。由于太师、太保设置于平帝时期,而太傅曾在此前的西汉历史中多次设置,因此太傅设置的时间便被很多学者视为西汉时期“上公”出现的时间。如安作璋、熊铁基认为“上公”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傅第三次设置时,即哀帝时期。⑧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1页。卜宪群认为:“三公制度的确立是在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所以上公的设立应在三公制之后或同时,故《汉书·百官公卿表》讲哀帝时复置的太傅位在三公上,可视为上公形成的标志。”⑨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5页。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如谭景玉和郭俊然认为根据该则史料的记载,“上公”应出现于高后时期。
谭景玉和郭俊然均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位在三公上”一语应包括吕后时期的太傅。谭景玉认为三公应当包括整个西汉时期的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此外,他还根据《齐职仪》的记载:“汉惠帝崩,吕后以右丞相王陵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①据《艺文类聚》引《齐职仪》记载:“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为太傅,迁太师。秦无其职。汉惠帝崩,吕后以右丞相王陵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参见(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46《职官部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24页。引文标点为作者自加。从而推论“上公”出现于高后时期。他对于三公内涵的理解颇有可取之处。但其援引《齐职仪》论证“上公”出现时间则未免欠妥。该则史料仅见于《艺文类聚》。如果认为成书于南朝的《齐职仪》时代上较为接近汉朝,那么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应劭之《汉官仪》对于太傅的记述似乎更加可信。据《汉官仪》记载:“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时,康叔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绶。八年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②(汉)应劭撰,(清)孙星衍校集:《汉官仪》卷上,(清)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120页。该条史料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皆有收录。《汉官仪》的记载多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合,可能拥有同一史源。“位在三公上”一语均出现在元寿二年的记事之后,恐非偶然。此外,与《齐职仪》同为后出文献的《唐六典》云:“汉哀、平间,始尊师傅之位在三公上,谓之‘上公’,明虽天子必有所师。”③(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1,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页。较之汉人的说法,唐人更加明确地指出太傅“位在三公上”应在其第三次设置时。故而,与汉唐文献相比,《齐职仪》的说法反而成了孤证。在没有新的史料出现前,吕后时期太傅“位在三公上”的说法恐难以成立。
那么《唐六典》中所说的“谓之‘上公’”,是否可以证明太傅在第三次设置的时候,确实拥有了这样的地位呢?换言之,安作璋、卜宪群等学者关于“上公”出现于哀帝时期或太傅第三次设置时的说法,是否能够因此成立呢?
这一说法同样值得商榷。太傅的第三次设置并非在哀帝时期,而是平帝即位之后,只是此时尚未改元而已。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西汉末年太傅一职的再次设置时间为哀帝元寿二年。是年“五月甲子,丞相光为大司徒,九月辛酉为太傅”。④《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第852页。另据《汉书·平帝纪》的记载:“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谒高庙,大赦天下。”⑤《汉书》卷12《平帝纪》,第347页。但《汉纪》则记载为:“皇帝壬寅即位,九岁。大司徒孔光为太傅。”⑥(汉)荀悦:《汉纪》卷30《孝平皇帝纪》,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2页。《通鉴考异》认为:“按《长历》九月辛酉朔无壬寅,壬寅乃十月十二日。”⑦(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2《汉纪中》,《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缩印本,第9页。《汉书·孔光传》对孔光由大司徒转任太傅一事记载尤详:“莽权日盛,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师傅。’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⑧《汉书》卷81《孔光传》,第3362~3363页。可见,孔光出任太傅的时间当在平帝即位之后,故而平帝即位应在元寿二年九月辛酉,而非十月。同日,朝廷任命孔光为太傅,是为西汉太傅一职重设之标志。因此,太傅一职实际上是设置于元寿二年平帝即位之后,应为平帝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太傅从“位在三公上”到“位上公”在时间上存在一个过程。从《汉书·孔光传》的内容亦可知,平帝即位后设置的太傅并不是“位上公”,而是“位四辅”。元始元年(1年),太傅与太师、太保、少傅组成“四辅”。由于王莽此时身兼太傅与大司马双重官职,故而其既是“四辅”之一,同时也是三公之一。在当时的诏令奏议中,“四辅”名列三公之前,这可能是由于“四辅”是“位在三公上”的一个新的层级。直到元始四年,王莽以宰衡、太傅、大司马的身份“位上公”之时,太傅才真正拥有了“上公”之位。因此,西汉时期太傅第三次设置的时间与“上公”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
在元始四年之前,史书中唯一与“上公”身份相关的人,只有一位居于三公之位的大臣。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马生驹,三足,随群饮食,太守以闻。马,国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后侍中董贤年二十二为大司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⑨《汉书》卷27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第1470页。阎步克据此认为哀帝时期“大司马一度被视为‘上公’,但不过是大司马居大司徒、大司空之上的意思”。⑩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第247页。这样看来,将董贤视为“上公”者应当是这段史料的书写者。《汉书·五行志》中相当数量的解说存在明确的出处,但也有相当多的解说没有标明解说者。①有学者认为“《汉书·五行志》中有关西汉晚期的论述主要是出自班固之手”。详见向燕南:《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从内容来看,评论者使用“哀帝”一词,说明这一解读至少应是汉平帝即位后才出现的说法。这位解说者将董贤视为“上公”,显然是受到了元始四年以后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时王莽官拜宰衡,“位上公”,同时身兼太傅、大司马之职。因此,太傅“位上公”的记载,可能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太傅地位的认识。
二、宰衡与“位上公”的出现
平帝即位后,王莽复出并再次担任大司马。他成功争取到了儒生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并将自己塑造成儒者心目中周公的化身。②有关王莽与当时儒士阶层的关系,以及其复出后笼络儒士阶层的一系列举措,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349页。元始四年,大司徒司直陈崇上书建议朝廷对王莽“宜恢公国,令如周公”。③《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不久,又有八千余人上书朝廷支持陈崇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过上公之赏。宜如陈崇言”。④《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但直到此时,“上公”一词仍是一个存在于典籍中的称谓。
既然以王莽比附周公,那么文献中所提及的周公的相关身份与地位便需要逐一在王莽身上出现。元始四年,根据有司的建议,“采伊尹、周公之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⑤《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第4066~4067页。需要指出的是,《汉书》中还有关于王莽拜为宰衡的同时便已经“位在诸侯王上”的记载。如《孔光传》称:“莽又风群臣奏莽功德,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百官统焉。”(《汉书》卷81《孔光传》,第2263页)《外戚传》也记载:“皇后立三月,以礼见高庙。尊父安汉公号曰宰衡,位在诸侯王上。”(《汉书》卷97下《外戚传下》,第4010页)《孔光传》的叙述侧重于孔光在王莽地位变化过程中的心态,故仅在于强调王莽地位的变化,且缺少明确的时间。而王皇后尊其父为宰衡的史料存在疑点。据《汉书·元后传》记载:“莽风群臣奏立莽女为皇后。又奏尊莽为宰衡,莽母及两子皆封为列侯。”(《汉书》卷98《元后传》,第4030页)此外,《汉书·平帝纪》的记载:“夏,皇后见于高庙。加安汉公号曰‘宰衡’。”(《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7页)从《元后传》的记载来看,王莽曾两度发动群臣,且拜官封号为国家大事。此时王政君称制,新任皇后何以能够擅自赐其父亲尊号。故而《外戚传》记载可能有误。相对而言,《王莽传》在记述王莽地位变化时多引当时的诏令奏议。因此在王莽拜为宰衡的史事记述上,《王莽传》较之《外戚传》与《孔光传》应更为可靠。这里的“位上公”,显然是与王莽“宰衡”之号相匹配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的“上公”之位,是西汉朝廷首次将儒家典籍中的“上公”践行于现实政治之中。因此,西汉政治制度中真正出现“上公”当在平帝元始四年。
“上公”由历史进入现实,只是群臣为了迎合王莽而新创的名位。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古代名号,其象征意义显然大于现实意义。这一点从王莽的一份上书中同样能得到印证:
臣以元寿二年六月戊午仓猝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宫;庚申拜为大司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备四辅官;今年四月甲子复拜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诚非鄙臣所能堪。⑥《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
上述内容是王莽对自己元寿二年之后仕宦经历的回顾。而在王莽众多的身份之中,爵、号、官三者是其最为看重的。“上公”只是作为一个体现宰衡身份的符号而已。
“上公”再次出现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是在朝廷赐予王莽“九命之锡”的事件中。在张纯等九百余人的上书中提到“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⑦《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朝廷在赐王莽“九命之锡”的诏书中也提及“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为上公”。⑧《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
对于“上公”之位,当时人对其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群臣对“上公”地位的确定从拥戴王莽为宰衡之时便已经开始。元始四年,有司奏请拜王莽为宰衡的同时建议:“三公言事,称‘敢言之’。”⑨《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可见当时宰衡王莽确实是拥有超越三公的地位。更为特殊的是,王莽此时身兼宰衡、太傅、大司马三职于一身,同时拥有“位上公”“位四辅”“位三公”的地位,客观上对当时的职官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而到了讨论授予王莽“九命之锡”的时候,大臣们又提议“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⑩《汉书》卷 99上《王莽传上》,第 4063、4066、4068、4072、4074、4067、4089页。可见,当时人们只是一味致力于抬高王莽的政治地位,但对于某些因比附周公而添加的名号,则未必会作太多的斟酌。
王莽称帝之后,“上公”之位有了新的发展。原本低于宰衡的“四辅”成为新的“位上公”的官职:
以太傅、左辅、骠骑将军安阳侯王舜为太师,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广汉梓潼哀章为国将,美新公:是为四辅,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阳侯甄邯为大司马,承新公;丕进侯王寻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将军成都侯王邑为大司空,隆新公:是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广阳侯甄丰为更始将军,广新公;京兆王兴为卫将军,奉新公;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成新公;京兆王盛为前将军,崇新公:是为四将。凡十一公。①《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00~4101、4013~4014页。 《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53、4153、4181、4180页。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四辅中的“太傅”一职,很可能在这时才实现了居“上公”之位。太傅“位上公”的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此后东汉时期太傅一职的设置。
不久,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便开始了。《汉书·王莽传》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文多不具。②《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00~4101、4013~4014页。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此次职官制度改革,新朝的官员位阶也逐渐清晰。除了之前的“位为上公”外,还可见到“位皆孤卿”和“位皆上卿”等说法。
但若按照《周礼》的记载,“上公”与孤卿原本不属于同一范畴。“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③(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5《秋官·朝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77页下。在《周礼》的理论体系中,孤卿与大夫并称,属于公、卿、大夫、士的序列,而非公、侯、伯、子、男之列。新朝在官位问题上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很可能是源于西汉末年朝廷对“上公”定位的模糊。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典籍缺乏对“上公”内涵的详细阐释,从而为后人理解与阐发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④例如,在对于《周礼》“上公九命为伯”的解释中。郑玄认为:“上公,谓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为二伯。二王之后亦为上公。”(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春官·典命》,《十三经注疏》,第780页中)方懿认为:“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今人黄怀信认为“公位重于伯,不应曰‘上公九命为伯’且下有‘诸伯七命’,疑‘伯’当作‘王’。”(上述两种观点参见黄怀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参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卷12《朝事》,第1267页。)同时也可能是当时依附于王莽的一派经学家为使其能够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而有意回避了对“上公”名号的准确定位。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上公”在当时的官僚系统中都很难找到明确的位置。如上文所言,王莽在表述自己的官职时,对“上公”也是只字不提。这一援引儒家典籍的名号,本身的作用十分明确,即作为王莽行周制、致太平的一种点缀。
与此同时,“上公”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记载中出现了与官位相矛盾的记载。功崇公王宗因罪自杀后,王莽说:“宗属为皇孙,爵为上公。”⑤《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53、4153、4181、4180页。这似乎表明新莽时期“上公”也是爵位的一种。王莽对王宗的惩罚是“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贬厥爵,改厥号,赐谥为功崇缪伯”。⑥《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53、4153、4181、4180页。既然“贬爵”为由公降为伯,则更加明确新莽时期“上公”为爵位之一。
从前面所引的《周礼》内容可知,“上公”原为周代五等爵之首。早在居摄二年(7年),王莽成功镇压了翟义等反对者,又平定了西羌,于是上奏朝廷对有功者予以封赏。在奏疏中,王莽首次提出恢复周代的五等爵位制度:“臣请诸将帅当受赏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⑦《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第4089页。由于此时王莽身居安汉公之位,故而对有功者的册封中“高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⑧《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第4089页。进入新朝以后,五等爵制度全面建立,从上文所引《王莽传》内容可知,王莽称帝时便册封了“十一公”。此后,在对刘縯的购赏令中,王莽曾宣称:“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为上公,食邑万户,赐宝货五千万。”⑨《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53、4153、4181、4180页。《后汉书》称王莽“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⑩《后汉书》卷14《刘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50页。购赏令中的“上公”直接与食邑并举,应为爵位无疑。
因此,新莽时期的“上公”名号同时应用于官位与爵位两个系统之中,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经学家对于先秦典籍中“上公”概念缺乏明确解释有关。
三、新朝之后“上公”名号的新变化
地皇四年(23年),“平林、新市、下江兵主将王常、朱鲔等共立圣公为帝,改年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①《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00~4101、4013~4014页。 《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53、4153、4181、4180页。关于更始政权“拜置百官”的情况,《后汉书·刘玄传》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鲔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①《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69页。 《通典》卷20《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6页。
由此可知,在更始帝任命的第一批官员中,包括了两位“上公”,即成国上公与定国上公。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文中认为:“匡、凤皆位上公而加定国、成国美号也。”②《资治通鉴》卷39“淮阳王更始元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40页。若“上公”只是官位,则没有必要在表示等级的名号前再加美号。因此,更始政权中的两位“上公”很可能将新莽政权职官系统中的“上公”名号演变成了具体的官职。在更始帝进入长安后,曾大封功臣,王匡被封为比阳王,王凤被封为宜城王。但范晔在之后的叙述中对王匡仍使用定国上公的称谓。③据《后汉书》记载:“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参见《后汉书》卷16《邓禹传》,第600~601页。此外,从有关“白虎公”陈侨的记载来看,更始政权可能也存在公爵。④《东观汉记》作“陈矫”,详见(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9《冯异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18页。
那么,“上公”的头衔在当时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地位呢?我们可以对王匡与王凤分别进行分析。王凤在成为“定国上公”后,仅参与了一件大事,即昆阳之战。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刘玄称帝后,其军队分别集中于两个战场,一是以宛城为核心的南阳战场,二是以颍川郡为中心的豫州战场。⑤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仍处于新莽时期,如果依据新莽时期的州郡名称,则此处应写作:“一是以南阳为中心的前队战场,二是以左队为中心的豫州战场。”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元年,王莽“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36页)。南阳郡既称前队,而宛城“莽曰南阳”(《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第1563页)。更始政权分兵作战的目的是在夺取豫州与南阳郡后,获得进一步进攻洛阳的稳固基地。根据现有史料,曾在豫州战场作战的更始政权将领大致包括:刘秀、王常、邓晨、冯异、岑彭、赵熹、任光、刘隆、窦融、宗佻、李轶、王凤、王霸、傅俊。由于现有文本均以光武帝及其功臣为核心人物,故而有关王凤在豫州战场的诸多细节已无从查考。但这一时期豫州战场的统帅应是王凤而非刘秀,“当时刘秀是个偏将军,地位在王凤、王常之下”。⑥杜荣峙:《昆阳之战中的刘秀——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而另一个细节也暗示了王凤的地位。在昆阳之战中,刘秀率领一批将领出城求援,留王凤等人守城,实际上恰可证明此时王凤的身份应为坐镇于中军的统帅,而非可以冒险出城的普通将领。
王凤在获封宜城王后便再未出现于史书中,可能在封王之后不久便去世了。王匡曾参加更始政权进攻长安的战役,此后得以拥兵三辅,史称“王匡、张卬之属横暴长安,三辅苦之”。⑦(晋)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2“更始二年”,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页。《后汉书》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参见《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71页。王匡后来被派往河东抵抗赤眉军,最终因政权内部分裂而离开更始帝。⑧更始三年,由于张卬、廖湛等人发动政变,更始被迫逃往新丰。随后,“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卬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卬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卬于城内。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参见《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74页。杜荣峙:《昆阳之战中的刘秀——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因此,从上述分析来看,身为“上公”的王匡与王凤在更始政权中拥有兵权,且可能担任过局部战场的统帅。但由于某些原因,两位“上公”均未能成为权臣。限于史料,我们对于更始政权中的“上公”问题仅能作出上述分析。在政权初建时,更始政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新莽的职官制度,同时又有所改造,从而使“上公”成为官职名称。定都长安后,更始又采用了西汉的分封制度。这样看来,更始政权不仅继承了新莽的“上公”名号,还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损益。
东汉王朝建立后,“上公”成为太傅的政治身份。根据《续汉书》的记载:“太傅,上公一人。”⑨《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第3556页。另据《晋书》记载:“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⑩《晋书》卷24《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0页。唐人杜佑认为“后汉唯有太傅一人,谓之上公”。①《后汉书》卷11《刘玄传》,第469页。 《通典》卷20《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06页。太傅在东汉时期称“上公”的情况亦有史事可证。东汉末年,太傅马日磾出使山东为袁术所阻,含恨而死,朝廷有意为其“加礼”,孔融对此提出异议。孔融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①《后汉书》卷70《孔融传》,第2265页。 刘子立认为,《东观汉记》的内容在桓帝之后便没有编撰,灵帝时期的内容只是零散的史料而已。“这也意味着像范晔《后汉书》这样的后出史著,在撰写桓帝、灵帝、献帝时期的历史时,不得不乞灵于其他的史料。”详见刘子立:《〈东观汉记〉“自永初以下阙续”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可见太傅称上公的情形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存在。蔡邕在所撰《胡公碑》中称胡广“进作卿士,粤登上公”。②(汉)蔡邕著,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卷1《胡公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16页。可见《续汉书》称太傅为“上公”应该是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实际情况。
为何该时期的太傅会被称为“上公”?从西汉时期太傅一职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周代原有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太傅是西汉统治者最早采用的官职名称。王莽当政及新朝建立后,太傅依然处于至高的地位。东汉王朝保留太傅这一职位,是对以往政治传统的继承。而经历了新莽时期对“上公”之位的重建,太傅“位上公”的身份开始出现。“王莽的复古改革,似乎都随着新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实际上却在以反对王莽为名的光武帝与东汉王朝里获得重生的机会。除了谶纬符命及部分的社会改革之外,连‘太傅’一职也被光武帝保留下来。”③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页。 《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605页。此时的太傅“在政治上也有所影响,那是因为他们多半‘录尚书事’,所以‘百官总己以听’”。④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13页。 徐建委:《蔡谟〈汉书音义〉考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
“上公”的内涵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泛化现象。在《后汉书》关于东汉末年的历史叙述中,“上公”再次出现并被史官视为与大司马或太尉一职。⑤东汉初年仍存在大司马一职。建武二十七年,大司马改为太尉。详见《后汉书志》第二十四《百官一》,第3557页。例如,刘矩曾两度担任太尉,其在灵帝初年第二次担任太尉时,史称“矩再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⑥《后汉书》卷76《刘矩传》,第2477页。幽州牧刘虞在灵帝时曾被拜为太尉,董卓专权后“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⑦《后汉书》卷73《刘虞传》,第2354页。史称“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⑧《后汉书》卷73《刘虞传》,第2354页。由于刘虞最终没能接到太傅的任命,因此史书中称其“为上公”的说法应指其此前担任的大司马一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后汉书》之史源为《东观汉记》,但《东观汉记》散佚已久,今人已无法确知上述内容是否为《东观汉记》原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蔡邕曾撰写过《灵帝纪》、十意以及列传42篇。但“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⑨《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第2007页。《隋书·经籍志》称《东观汉记》“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隋朝人所见《东观汉记》的内容含有灵帝时期的史事。⑩《隋书》卷33《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4页。但《东观汉记》这一部分内容的成书时间当不早于蔡邕生活的时代。①《后汉书》卷70《孔融传》,第2265页。 刘子立认为,《东观汉记》的内容在桓帝之后便没有编撰,灵帝时期的内容只是零散的史料而已。“这也意味着像范晔《后汉书》这样的后出史著,在撰写桓帝、灵帝、献帝时期的历史时,不得不乞灵于其他的史料。”详见刘子立:《〈东观汉记〉“自永初以下阙续”考》,《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至于刘虞任上述官职的史料产生时间则更晚。因此,即使《后汉书》中的上述内容另有史源,其出现时间亦当在东汉末年甚至更晚的时代。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史记》与《汉书》的注文中。如裴骃的《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称:“大司马,上公也,故先进议。”②(汉)蔡邕著,邓安生编:《蔡邕集编年校注》卷1《胡公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16页。《汉书》注引文颍之言亦同:“大司马,上公,故先进议也。”③王惟贞:《东汉“明章之治”论析—明、章二帝巩固政权的措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页。 《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605页。徐建委认为:“裴骃引用的《汉书》古注本是一部名为《汉书音义》的集注。”④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13页。 徐建委:《蔡谟〈汉书音义〉考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如果该书确为集注性质,则文颍之言可能是该书所集各家言论之一。当然,学界一般认为现存于《汉书》中的23家后世学者之注文皆称《汉书音义》,而裴骃所引之书可能是文颍的《汉书音义》。文颍是汉末魏初之人,故而在汉末魏初时,仍然有人以“上公”诠释大司马的政治地位。这种以“上公”称大司马或太尉的现象又当如何理解呢?
《后汉书·袁安传》曾记载了一个关于袁氏家族的传说,这个传说的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却为我们透露了一个关于东汉末年“上公”内涵可能出现泛化的重要线索:“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提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①《后汉书》卷45《袁安传》,第1522页。从故事中所记载的预言来看,该故事的编纂者至少已经看到了汝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繁盛。因此,故事的产生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当无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太尉可以被称为“上公”,但袁氏家族并非“四世太尉”。事实上,袁氏家族中只有袁汤一人担任过太尉。可见,传说中的“世为上公”实际是指这一家族累世官居三公之位。因此,东汉末年的“上公”可能已经成为了三公的一种尊称。
至汉献帝时期,“上公”再次成为权臣的标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时曾有言:“往者初开魏国,锡君土宇,惧君之违命,虑君之固辞,故且怀志屈意,封君为上公,欲以钦顺高义,须俟勋绩。”②《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43页。此处之所以使用了“封君为上公”的说法,是因为早在建安十九年三月,汉献帝便已经“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了。③《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43页。可见,此时封曹操为上公,更多的只是为了迎合“加九锡”之礼。至于魏王之位究竟在三公之上还是诸侯王之上,早已不重要了。
结 论
综上可知,两汉时期的“上公”名号存在一个从理论进入现实的演变过程,而导致这一过程出现的重要阶段是汉平帝至新朝时期。元始四年之前,“上公”只是一个存在于儒家文献中的历史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的政治制度中。元始四年,王莽被授予宰衡之职后,儒家典籍中有关周代的职官爵位开始得以进入现实政治中,“位上公”也成了这一时期王莽比附周公的标识之一。但随着“上公”进入官爵系统之中,其在西汉的官爵体系中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定位。加之群臣一味地抬高王莽的政治地位,缺乏对“上公”名号的明确解读,最终使“上公”的含义变得模棱两可。这一情况也直接导致新莽王朝的“上公”同时出现在官位与爵位两个系统之中。
随着汉室复兴运动的兴起,在更始政权草创的职官系统中,出现了两个带有“上公”名号的官职——成国上公与定国上公。但身为“上公”的王匡与王凤除依然统兵作战外,并没有成为权臣。东汉王朝建立后,太傅成为拥有“上公”名号的官职。而随着东汉王朝的衰亡,“上公”的内涵也开始泛化,并逐渐成为三公的一种尊称。可以说,更始政权与东汉王朝在部分继承新莽政治遗产的同时,也悄然建构着新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