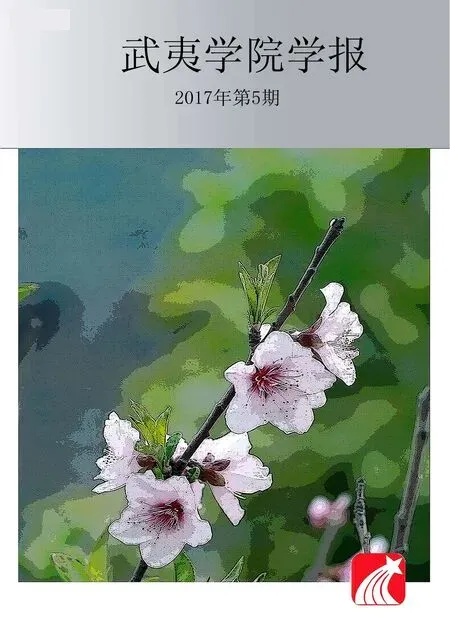卢梭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异议
——以严复为例
吴 曦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卢梭学说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异议
——以严复为例
吴 曦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卢梭学说传播到中国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其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实际上,严复对卢梭学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宣传介绍到质疑批判的过程。卢梭学说之所以遭受到严复的强烈抨击,究其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二者在思想上存在的冲突,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卢梭学说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缺陷。
卢梭;严复;异议
严复和卢梭,分别为东西方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东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进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卢梭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为十八世纪末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而严复在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辱,力求变法图强的历史时期,开眼看世界,将西方近代的政治、哲学、经济和法律名著系统地翻译介绍到中国,为知识阶层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卢梭学说传播到中国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其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实际上,严复对卢梭学说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宣传介绍到质疑批判的过程。卢梭学说之所以遭受到严复的强烈抨击,究其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点:二者在思想上存在的冲突;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卢梭学说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缺陷。
一、严复对卢梭学说的异议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独具慧眼的思想家,他就时代的自由人权问题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权法律观。这为传统观念的批判、改造和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严复在全面介绍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思想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卢梭。随着了解的深入,他对卢梭学说的看法不断发生着改变。
(一)宣传介绍阶段
作为精通西学的学者,严复熟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着中国维新思潮的兴起,严复在这一时代的浪潮中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奋笔直书,于1895年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而他在这一时期据以抨击封建专制的思想利器,正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肯定了卢梭是民约论的集大成者:“卢梭之为《民约论》也,其全书宗旨,实本于英之洛克,而取材于郝伯思”[1],“二人者,欧之哲学政治大家,不独于英为杰出。民约之义,创于郝而和于洛,卢梭特发挥昌大之而已”[1],并认为卢梭“为革命先声”[1]。他在吸纳了卢梭民约论中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的同时,肯定了社会的形成是基于民众的利益联合,但他并没有接受卢梭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观点。严复主张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前提下,创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民主之过渡。以便最终实现“悉听其自由”的民主共和国家。因此,“此期严复在思想上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拥护者,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是一个维新改良论者。”[2]
(二)质疑批评阶段
戊戌变法后,严复开始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进行质疑和批评。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作为响应、赞同君主立宪政体的严复,也在上海青年会和安徽高等学堂发表了他的宪政演讲。演讲的核心内容现存于《政治讲义》一文,其中对卢梭政治思想的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点:
1.从社会起源的问题出发,否定了社会契约论的基础
卢梭认为社会的形成是基于以下情形:“当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经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像以往一样的自由”[3]。也就是说,社会的形成源自个体无力承受的压力,人类为克服压力以保障原先自然状态下的自由,才达成相互联合的契约。并通过契约之上的共同体保障个人权利。“但是,严复认为,社会契约论不过是卢梭依自然法主观推演的结果,并无历史根据。”[2]他认为社会缘起于人们早期按照宗法关系或信仰崇拜形成的社群,因共同的利益逐渐设立规范和法度,遂成社会和国家的雏形,“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放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体制以成。”[1]也就是说,人群进化是社会与国家成形的基础,人类的自利天性在其中发挥着动力作用,从而否定了卢梭所谓约定成契,以公共意志来奠定国家的观点。
2.对卢梭“自由”理论的批判
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3]社会形成之后,“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的一切的权利,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3]因此,卢梭强调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天生权利,卢梭构想中的结合体亦在保障这些权利的尊严。严复显然没有意识到卢梭笔下“自由”的“被保护者”形象。这一“被保护者”代指的是人类天性中不可撼动的本质。相反,他将卢梭笔下的“自由”视作了中文意义上的 “放任”。在这样一种定义下,“自由”充满了不安因素,因此,需要规范和礼教的约束。在著作中严复对“自由”一词做了双重定义:一是与民智、民德的教化程度相符合的自由;二是不与政府管理,社会规范相忤逆的自由;他认为个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本身也不具备褒贬的意义,自由所带来的后果全 “视用之者何如耳”。由此,他总结出三点结论:第一,社会形成以前,人类野蛮原始,并不像卢梭所言,是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第二,政治体制的选择,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都无关民主自由的实现(都在于约束自由可能出现的放任);第三,由于在当时中国民众的头脑中,对所谓自由民主的观念尚缺深刻理解,此时若一味鼓吹自由民主,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破坏原有运行稳定的礼教纲常,从而埋下乱世的祸根。他说:“则向之所谓平等自由,适成其蔑礼无忌惮是之风,而汰淘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1]
3.对卢梭全盘否定君主制的批判
卢梭对君主专制感到厌恶,认为高度集中的专制君主盗取了人民给予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并在盗取公权力的基础上侵犯私人权利。严复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君主制政体都必定将君主的个人意志凌驾于民众之上,祸害人民。他结合东西方历史事实,认为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制度下,权利都可以属于人民。专制君主同样可以受民众拥戴而立。虽然专制政体下,君主有以权力压迫人民的时候。但这必见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时;其他情况下,专制君主还是能够以德服人,不率意妄行,以维持国家的稳定。严复举出了法王路易十四的例子,认为法国人尊崇国王的传统,正是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了顶峰。由此,严复断言:“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卢氏之说不可复用明矣。”[1]
(三)异议集中出现阶段
1914年2月,严复发表了《〈民约〉评议》一文,对卢梭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主要探讨的有以下问题:
1.对“人生而自由平等”观点的异议
严复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是,“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1]。可以看到,严复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民本理念。这显然不同于自由一词在西方所具有“权利”含义。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中自由是具有排他本质的,意味着某种“特权”,并不是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分配(上下之势不相悬)。但是,强调民本理念的严复却将其诠释为要实现统治者和民众之间权利的平等。同时,严复把这种权利间的平等视作是无法之胜,忽略了人人平等是法律实施的原则这一先后关系。因此,严复眼中的“自由平等”根植于传统儒家体系中的民本思想,它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概念相去甚远。
严复认为人类的竞争是伴随着其进化始终的,人人平等实为妄谈。他特别举例说,刚诞生的婴孩连自己都难以存活,因此不具备实现自由的能力,卢梭“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理论显然站不住脚。实际上,卢梭有言:“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首要的法则是要维系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3]他意在说明,自由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具有不可转让的特性。是人能够实现其自身在哲学意义上“自然”的前提,脱离了生而自由的原则,人就无法实现由此而来的意志表达和作为人的本质。严复却把这种原则意义上的自由,视作了人有无行使自由的能力。在注重人的社会状态时,忽略了其自然状态下的本质。而我们看到,卢梭之所以设定自然状态,就在于为反思现代文明寻找参照的原点,指出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合法权利代替了暴力掠夺,自然规则服从于法律原则,而建立在自然状态假设之上的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卢梭赖以纠正人类社会异化结果的政治构想。严复并没有理解卢梭关于:“自然自由”、“社会自由”和“道德自由”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把卢梭意在还原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性铺填上了现世人性中的种种繁杂。他认为:“卢梭所谓自然之境,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平等者,亦自言其为历史中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1]
2.关于卢梭其他观点的异议
严复认为卢梭著作中公养之物,莫之能私,如土地及其所产,非经人类全体公许,不得据为已有,产业者皆纂而得之者的观点是在否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尤其是对最后一句颇为反感。实际上,反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财产观念,我们就会发现,他并没反对财产私有,并且认为正是公民的结合体保障了财产私有的合法性。“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只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权利。但是使他成为某项财富的所有者这一积极行为,便排除了他对其余全部财富的所有权。这就是何以原来在自然状态中是如此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却不得不备受一切社会人尊敬的缘故了。”[3]卢梭所要说明的是,当人们将自身财产集中于共同体中时,实际上是通过契约确立了对原先财富的合法所有。财产汇聚的作用是在人们达成某种财产分配的契约之前,保证这些财产能够为共同体力量的所保护。在契约达成并扣除了那些所有权归公以兹管理的部分后,人们的合法财产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由于时代和翻译的局限,严复将卢梭的某些语句理解为了是其赞成公有制的标志。由是,他才会对卢梭的财产权观念大加批驳,认为他的理论会引发社会的动乱,造成对私有财产的侵夺。此外,卢梭提出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明确了用战争等武力夺取的权利,是没有公约基础的,被剥夺权利的人民有权反抗,夺回权利,恢复自己的自由。这正是卢梭思想的深刻之处。而严复却认为:“必如其说,凡人得一权利,必待一切人类之公许而后成,于事实为不可能。且战胜国逼战败国订立屈辱条约,安在力之不足畀人以权利耶!”[1]他以战争中的缔约为例,相信通过强力可以从他国夺取权利。
此外,严复十分反对卢梭认为必须通过革命来推翻专制政府的做法,这一态度在1914年一战后表现得更为强烈。严复认为中国民众的民主认识尚为肤浅,仓促推行民主政治,只能造成“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1]的局面,他深信历史渐进论,对激进的社会革命深恶痛绝。
二、卢梭学说遭受严复异议的原因
(一)卢梭与严复所处历史背景的差异
卢梭学说提出的时代,正是近代启蒙思想方兴未艾之际。人们在复兴古典文化和怀古情结的推动下,积极地在探求有关人的自然权利、理性、自然状态、主权国家的构建、政治道德和法律合法性之类的基本问题。在这样一个思想大背景下,涌现出了如伏尔泰、狄德罗等等的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以那个时代专制统治、封建制度弊端为批判的核心,为人类摆脱封建时代的压迫,创建资本主义理想社会构建了宏伟的蓝图。卢梭不仅看到了这些旧有的封建体制的弊端,还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人们寻找一种永远摆脱奴役状态的社会政治准则。卢梭走到了所有启蒙思想家的前列,甚至也因此站在了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对立面。他的理论给人一种强烈的对原始自然状态的向往,这也是为什么卢梭会给严复留下类似于中国老子的印象。可以说,卢梭所要解决的不仅是18世纪那些困扰人们的现实政治问题,他还为人们开拓了反思现代性的先河。
相较卢梭所处时代而言,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则十分不同。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西方列强欺凌,获得民族独立。对于中国人来说,此时所要解决的已不仅仅是摆脱封建统治,实现民主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习西方,让中国迅速强大,以追赶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严复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去寻找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最佳路径。而近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论。相较探讨人的本质问题,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显然更为重要,而他会将卢梭学说视为空想,不仅仅是因为其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无益,还因为卢梭的理念会引导中国人的自由泛滥,从而引发激进的社会革命,破坏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秩序。这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样一来,不仅民主自由难以实现,还会加重中国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更是遥遥无期。因此,严复赞同渐进的社会改革,希望通过加强对国民的教化去实现社会的进步。这也就是他激烈反对卢梭思想的原因所在。
(二)严复与卢梭在思想上的差异
从严复的思想观点上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个人本位和自由主义者。他推崇生物和社会进化论,认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认为理在法先,在人为法之上还有一个超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左右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人类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订立契约,达成“公意”;他认为人类都是自私的,不会甘心转让自己的利益和财产,通过公共的管理加以支配。他认为社会是个人出于趋利避害而结成的群体关系,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加入的。而卢梭则认为“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3]在他笔下,人类社会的形成基于“公意”的涌现,是人面对自身局限时的积极举动,是以道德代替自利与孤立,以法律代替无序与掠夺。社会契约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必经道路,是维系人类自由的保障。正如卢梭所说:“一旦承认了这种区别以后,那么在社会契约之中个人方面会作出任何真正牺牲的说法便是不真实的了。由于契约的结果,他们的处境确实比他们以前的情况更加可取得多;他们所做的并不是一项割让而是一件有益的交易,也就是以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自己侵害别人的权利,以一种由社会结合的保障其不可战胜的权利代替了自己有可能被别人所致胜的强力。”[3]可以看出,严复和卢梭虽然在所追求的理想上存在交集,但在核心理念,特别是在自由平等实现的方法上,是存在着很大不同的。
(三)卢梭的学说自身存在的缺陷
1.公意存在与否与如何得来
“公意”是卢梭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愿。然而,连他自己也承认:“事实上一个个别的事实或是权利只要有任何一点未为事先公约所规定的话,事情就会发生争议。在这样一场争诉里,有关的个人是一造,而公众是另一造。然而在这里我既看不到有必须遵循的法律,也看不到能够作出裁判的审判官。这时,要想把它诉之于公意的表决,就会是荒唐可笑的了;公意在这里只能是一造的结论,因而对于另一造就只不过是一个外部的,个别的意志……于是正如个别意志不能代表公意一样,公意当其具有个别目标时,也就轮到它自己变了质。”[3]实际上,要获得这么一个不容他见的最高意志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布十分复杂,人们的想法见解亦是层出不穷。共同体要从这些繁杂的意见中凝萃出统一的共识并非易事。此外,卢梭认为通过人们的约定俗成可以发现“公意”。然而,约定俗成即易于变化也难有成文的规范为后人效仿。因此,卢梭的公意理论缺乏一个权威的“立法者”,以替代普通人理性的局限。按他自己所说“人民需要启蒙,公意需要得到启蒙”[4],可是要找出这样一个,能够突破一切人类的局限,公正无私的“哲学王”却仿佛天方夜谭。这一公共人格超越了一切人类的自私自利后所创立的法规,果真能够在面对人类涌现不绝的复杂矛盾中持续发挥作用吗?卢梭没有给出答案,他在构想出这个“伟大”的“利维坦”后,将人类的负担承载其肩。却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它的空间。
2.有关人类不平等的学说
卢梭虽将不平等看作是社会和财产私有制的产物,却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并不具备社会性。“这就使他无法回避人类是如何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这一颇为艰难的问题,而只好求助于一些偶然的迫不得已的因素。”[5]他在追溯人类的自然状态时,笔端不由得流露出对原始人类生活的憧憬,相较与文明所带来的欲望、习惯和道德,他似乎更追求以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还原人的本质。这也正是其相似于东方老子学说的特征所在。
总的来说,卢梭学说虽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它不是从人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上考察社会、国家,而是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把‘自我保存’、‘个人自由’作为理论前提,由此去演绎契约社会,不能不走向唯心主义。”[2]这验证了罗素的说法:“德谟克利特以后的哲学——哪怕是最好的哲学——的错误之点就在于和宇宙对比之下不恰当地强调了人。”[6]因此,卢梭从对人不平等状态的关怀出发,意在追溯人生而平等的地位,却难以解释人何以具备社会性的难题。他将归零的人类呈现于笔下,带给世人无尽的反思。
3.卢梭的学说在历史中一直没有成功案例
卢梭提出了关于自由、平等、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公意等一系列理论,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现方案。而且,为了能够全方位的表达公意,必须取消任何形式的代议制度。“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类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在这时我们可以认为,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当,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当了。在数量上分歧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的一个是如此之大,而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也就不再是有许多小的分歧的总和,而仅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就是一个个别的意见。因此,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3]而现实是,“较大的国家在没有代议的情况下实行民主,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人口的角度都不现实。”[7]并且,因为现实的需要,主权者不可能亲自行使主权,他必须委托政府来执行,而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必然干扰个人意志的选择。与此同时,卢梭所假定的公意,为了保障执行,是必须强迫他人服从的。这使得一些独裁者、专制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可以假借卢梭的理论之名行专制暴政,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正是如此。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均告失败,党派争端,军阀混战,民主、自由、立宪等西方的先进理念见不到成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严复不仅没有在现实中看到卢梭学说的积极作用,反而认为辛亥革命后“举国礼乐崩”的局面,是卢梭所鼓吹自由的泛滥造成的。因此,严复会对其学说进行严厉批判也在情理之中。
三、结语
卢梭的学说在历史上曾引发无数哲人讨论争议,政客们也纷纷在卢梭的学说中寻找他们政治理论的合理支撑。今天,我们来看卢梭的学说以及严复等人对他的异议,不能够仅限于思想上的交锋和理论的对错,更要发现他们对人权的向往、呐喊与崇尚,向他们力图探索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锲而不舍地寻找人类发展方向的精神致敬。今天的人们所要做的,是把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发扬光大,并结合当下的社会历史现实,探索建立更切实可行、更科学合理的人类政治与社会体系。
[1]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9,334,1295,1268,594,1302,11,338,340,578.
[2]郑师渠.严复与卢梭的《民约论》[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2):45-50.
[3]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24,16,49,8,19,26-27,50,47,26.
[4]杜文丽.论卢梭社会契约中的公意[J].学术交流,2007(6):19-22.
[5]汤杰鹏.所有制与人类不平等的发展:解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J].黑龙江史志,2008(6):39-40.
[6]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7.
[7]任志军,欧佳佳.浅析《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由与公意[J].法制与社会,2009(4):355-356.
(责任编辑:陈 虹)
The Objection in the Spreading of Rousseau's Theory in China:w ith Yanfu as an Exam p le
WU X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00)
After Rousseau's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it had soon been questioned by Yan Fu and other Chinese scholars.In fact,there was a progress of transformation about the Yan Fu’s attitude toward Rousseau doctrine,which was at beginningmarked by positive introduction,but in the end by entirely criticism.When we try to find out the reason why this change had happened,we can mainly conclude three important aspects:first,the conflict exists in ideas;second,they are living in different epoches;the third,the limitation of Rousseau doctrine itself exist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Rousseau;Yan Fu;objection
D091
:A
:1674-2109(2017)05-0046-06
2017-03-09
吴曦(1991-),男,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