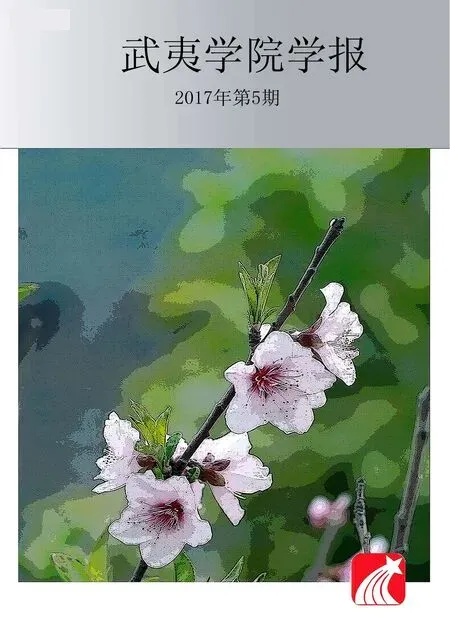“双剑化龙”传说的三类文学意象
张 隽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1)
“双剑化龙”传说的三类文学意象
张 隽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1)
《晋书·张华传》中所载的“双剑化龙”传说流传广泛。通过对涉及这一传说的历代作品的细致梳理,大致可以发现由传说衍生出了三种不同类别的文学意象,一是对传说本身的延续,二是对传说地点的指认,三是对传说意蕴的阐发,即通过结合具体文本来探讨这三类文学意象。
“双剑化龙”;传说;三类;文学意象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的核心要素,意象所涵括的思维导向是构成和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基础。一种意象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而经典的意象在历代作家的不断书写中又会形成类型化的存在,古代文论家谓之“典”,类似于现代文论中的“母题”。在对类型化的文学意象的追根溯源中,我们总能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即在“母题”的统摄之下,会衍生出几个甚或数个意象群体。这些意象群紧紧根植于 “母题”之上,是“母题”在某一方向上的延伸与外扩。正是由于有着意象群的存在,文学作品才能在迅速唤起读者共鸣的同时又不落窠臼。“巫山神女”传说及其生发出的“云雨”“朝云暮雨”“巫山”“高唐”“巫阳”是最显眼的例证。
单道此点,《晋书·张华传》中所载的“双剑化龙”传说和它在文学里的意象群体与“巫山神女”颇有相类之处。兹将原文节录如下:
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华)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1]
笔者将涉及这一传说的历代作品爬梳一过后,发现这些意象群体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别,一是对传说本身的赓续,二是对传说地点的指认,三是对传说意蕴的阐发,下面试分节讨论之。
一、传说的接续:光怪千年尤感人
从文学本位来说,“双剑化龙”情节曲折离奇,铺垫与结局环环相扣,人物与线索纠缠紧密,寥寥数百字便交代了横跨两代人的故事,可谓文小旨大。其暗含的人世变幻常常使人叹喟不止,以致千年之后的明人徐渭在舟过延平津时依然念念不忘,写出了如下题咏:“碧火吹云煅山紫,尤溪矿绝干将死。空令精气闭丰城,石函忆煞延平水。司空臂上青丝断,秋雨生愁别雷焕。从此深潭不敢窥,九峰青处摩寒电。春雨桃花急鸣峡,孤螭夜梦雷家匣。谁教经过值有情,那得长随君佩身。为龙为剑非二物,或合或离何所因。客子吊古不可测,浮天铁母惊湍织。光怪千年犹感人,风云欲作当时色。”[2]我们不妨仔细推敲一下徐渭在创作此诗时的心境。这是徐渭第一次入闽,闽地独特的山川形势无不给徐渭带去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当徐渭站在延平津头,空间的重叠使得徐渭与千年之前发生在此地的传说产生了强烈的联结,人与物诡秘陆离的命运变换在深深打动徐渭的同时又让他忍不住发出“吊古不可测”的感慨。这大约也是徐渭在原典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加工的原因,虽说情节主干犹在,但所有细节俱出于艺术再创造,笔下都是诸如“碧火”“寒电”“孤螭”一类的荒诞意象,较之原文明显多出几分异域色彩,实是故事给予徐渭的情感触动极大,非如此不足以表达。
《晋书》的叙述在“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处就戛然而止,因该书的编撰者们左右不过想要证成的是“华之博物多此类,不可详载焉”之说。但实际上传说这种不完全闭合的叙事策略,在不经意间为后续的敷衍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其中最为直观的一个问题便是“嘻嘻宝剑今何在”?有此一疑惑的人不在少数,形之于篇什的更是聚讼纷坛。一派以中唐窦巩为代表,其《题剑津》言:“风前推折千年剑,岩下澄空万古潭。双剑变成龙化去,两溪相并水归南。”[3]诗人来到事发地,联想到前朝的传说,只是望着深潭空无一物,所见唯有溪水长流,自然有“宝剑沈沙世已倾”之慨。与窦巩约略同时的闽人欧阳詹,所见与窦巩不谋而合,他在路过延平时留下了“想像精灵欲见难,通津一去水漫漫。空余昔日凌霜色,长与澄潭生昼寒”[3]之语,对龙剑的求之不得之情溢于言表。明人王镜在登临化剑阁时亦以揶揄的口吻道:“千秋神物几时去,空笑词人尚刻舟。”[4]他者如陈国玙谓:“我今呼龙龙不应,寒潭淼淼空烟波”,[4]官志涵言:“昔人久云徂,双剑亦已去”,[4]尤侗云:“神剑不可求,津水淙淙下”,[5]皆属此类。
还有一派所展示出的意象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由剑化龙的宝物并未遁去,而是留在延平当地。此说最早当推中唐诗人胡曾,在其七绝《龙津》中描述自己在剑津的见闻的就无比斩截地道:“延平津路水溶溶,峭壁危岑一万重。昨夜七星潭底见,分明神剑化为龙。”[4]胡曾之后,承其渊薮的代不乏人,宋时有司马光的“乃知神物不自藏,紫气依稀见牛斗”[6]之句。元人刘仁本在回忆客宿延平驿时谓:“半夜风雷吼神物,三川星斗印天文。”[7]对龙剑造成的异象描述最周详的是明人林鸿,其诗曰:“昔人双宝剑,经此化神物。晋室已寥寥,剑光犹未没。红缠斗牛气,黑漾蛟龙窟。千里一寒流,池波向溟渤。幻化窅莫测,沴气闭复开。有时潭水上,白日飞云雷。”[8]与林鸿同时的王恭,亦称“神物湮沈不复知,往往潭心飞霹雳。银河掩映流寒声,玻瓈井底双龙行”[9],一面说着“神物湮沈不复知”,似为中允,一面又向我们绘声绘色地罗列延平周边地区的天文异象,则神物的去留不言自明。
二、地点的标记:遂使关津皆号剑
在整个“双剑化龙”传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事件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区位发生的,即宝剑埋没之地丰城和宝剑化龙之地延平。如若单论二地在文中所占的比重,丰城显然比延平“戏份”更足。但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时却发现一个颇为费解的情况:传说对于两地的影响完全不对等,甚至可谓有云泥之别。先说丰城,在故事流传开后,较早援为典故的是王勃那句耳熟脍炙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以致紫气干牛斗几为丰城的专属天象。再次便只有“丰城宝剑”的意象,如杨炯句“宝剑丰城气,明珠魏国珍”[3],显是认为剑以丰城之气为上。又如达奚珣的《丰城宝剑赋》开章便直言:“剑之利者,有丰城之宝锷”,[10]亦是认为丰城宝剑为剑之佳品。当然,“丰城宝剑”还有埋没之意象,下节将有细述。除上之外,再难寻到传说与丰城之间的联结。
反观延平,情形就大为不同,历代来此题咏的文人多反复指认“神物当年化此中”,“神剑当年此化龙”。[4]对此北宋的诗僧惠洪无限感慨地道:“至今牛斗气,散作延平人。”[11]惠洪的见地可谓是极为精到。事实上,延平不仅因传说有了“剑津”“剑潭”“龙津”“剑溪”“化剑津”等等别号外,连正式的县名、府名也一度改为“剑浦”“镡州”“剑州”。作为双剑化龙之地,延平地区最显著的意象特征便是“剑气”。清人张远在攀临城郊百脚楼之际所见即“山青雨歇溪风至,秋老潭空剑气来”[4]。同是百脚楼,释智永在楼头感受到的是“徙倚不知归去晚,津头剑气逼人寒”[4]。离事发地更近的化剑阁,官志涵目睹的也是“夹城溪水并东流,潭上烟光剑气浮”[4]。明人刘璋在背井途中回忆起自己的故乡延平,惦念不忘的还是“澄潭剑气冲星斗”[4]。不仅这几处地方,在相隔不远的四贤祠和明翠阁亦有人声言“夜深坐看寒潭月,剑气依然贯斗牛”,“寒逼鱼龙星影动,气冲霄汉剑光浮”。[4]似乎到了晚上,由于没有日色与之争辉,剑光的气势更加恢弘炫灿。有剑气自然也有龙气,明万历间的郡守倪朝宾在凌虚阁奉和当时的守道吕中伟时宣称:“斗间隐跃双龙气”,[4]甚至连旌旗都带有龙剑之气。稍晚的明季清初,福清人薛敬孟在送别友人陈世承前往剑州亦凿言:“君到剑津占夜色,斗间龙气未曾收。”[12]可见“双剑化龙”传说已深深烙刻到延平的地域气质之中,成为延平独特的文化标记。
此外,不得不说,作为别号的“剑津”无论在本土人还是外乡人中都有着极高的辨识度与认可度。宋时邑人黄裳晚年在寓居他乡时有慨于 “泡影浮生梦幻身,十年南北寄红尘”而无比殷切地希冀“穷通有命归欤好,风月相期满剑津”。[13]黄裳为宋神宗元丰五年状元,历任福州知府、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尚书等。然而仕途上的顺畅并没有打消他“不如归去”的念头,家乡剑津在黄裳心中的份量可窥一斑。明初金幼孜在为友人题跋其书房绘图时欷吁到:“江海只今思旧业,梦魂长绕剑津波。”[14]金幼孜是今江西省峡江县人,考其一生行迹并未到过闽中,只因见了友人在延平的书房之胜就对剑津魂牵梦绕。提起闽北的山水,人们一般首先想到的是武夷,但早在南唐徐炫在送别友人致仕还建安时有句言“化剑津头寻故老,同亭会上问仙卿”[3]。诗后有小注曰“幔亭亦号同亭”,则同亭当为武夷幔亭峰,可见剑津和武夷在作者心中是等量齐观的。实际上,将剑津与武夷对举的例子为数不少,如骆问礼《大树篇》中的“云飞轻散武夷春,露洒遥添剑津泽”[15],祁彪佳《书诗草后》中的“武夷之明秀蜿迤也,剑津之怒腾奔壮也”[16]等等,无不说明时人对剑津的上佳观感。
三、咏怀的对象:试忆化龙今古事
众所共知,怀才不遇一直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常谈老调。传说中宝剑被埋没在丰城的牢狱之下,境遇不可不谓凄惨,然而它们却能自放精光,上彻于天,最终被起获而大焕异彩。这样一种前后命运的改逆无疑会搔到失意文人们的痒处,于是宝剑的经历成了这些文人自我激勉或劝慰他人的常用措语。北宋朝杨杰在《豫章行送周裕》中吟道:“又不见丰城剑埋尘土,几年秋水澄波澜。夜深直气射牛斗,变化风雷头角寒。丈夫穷通有时有,满腹诗书满樽酒。行行三月到扬州,故人莫笑麻衣旧。”[17]从诗作的内容来看,杨杰的这位友人的光景并不如意,杨杰只好以宝剑化龙的例子来告诉他丈夫穷达有时的道理。稍后,南宋初李光在追忆苏轼“晚年流落海南村,黎唱蛮讴随蜑叟”的贬谪境况后,旋即评以“先生已去五十年,遗墨残篇尚多有。丰城宝剑埋狱中,光熖犹能射牛斗”[18]之语。考虑到李光当时所处的情形与苏轼如出一辙,可以说他对苏轼的咏怀多少也是在指射自身。传说还适用于慰勉落第的考生,明人张宁就以“干将未出狱中泥,犹有神光射牛斗”来安慰赴试不中的同乡后进,并进一步阐发道:“进退荣枯事偶然,欣戚何须动颜色。冠盖相逢自有时,君归应惜少年时”,[19]言辞中示意他应尽于人事而安于天命。
与不遇相对的是知遇。有时候光有满腹经纶是远远不够的,要施展自己的生平抱负,尚需借助于能够真正赏识自己才华的高位者的引荐提拔。因此,文人们在失意时除了将一腔愤懑付诸篇什,最期望的还是遇见一位再世伯乐,由此而登上终南捷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张、雷二人辨气寻剑的情节被文人频频加以称颂。较有代表性的是胡奎的《赠揭学士孙和仲》:“剑江之水绿于酒,夜夜清光射牛斗。龙泉太阿飞上天,宝气千年应不朽。揭阳孙子玉无瑕,云是前朝学士家。藏器待时须努力,岂无雷焕与张华。”[20]表面上看此诗与前述张宁诗并无多少差异,内在的行文思路都是以剑光为喻来说明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有通达之时。然而,当我们细心比对两首诗作后会发现结尾处有微妙的区别。张诗只言“君归应惜少年时”,至于其后如何并不交代。胡诗同样嘱咐 “藏器待时须努力”,但之后又激励孙和仲“岂无雷焕与张华”,言下之意自身素养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有知遇之人。同理,像程敏政的《古风》谓:“倘无张华识,埋没吁可伤”,[21]林垐于《夜泊剑津不寐》中叹:“语到忧时天动色,泪横知己剑酬音”[22]及胡奎在另一首歌行中述说的“不逢张雷识奇宝,至今甘与凡铁同”[20],都表达了一致的情思。
还有的文人从出世与入世的角度来解读传说,借龙的显晦之态来倾吐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具体而言,他们常常因有感于“传闻龙剑能飞跃,不与英雄助斩魑”[4]而扼腕痛惜,深以为憾。朱熹门人陈淳在拜谒张华祠后写下“古来传说双剑灵,精气直上千云星。有如掘出为世用,一挥便可四海清。方今扰扰边尘起,中原分裂乱无纪。正好提携为扫平,何事双龙卧此水。试问张公知不知,英灵千载如生时。何时神物得神用,为报风云会合期”[23]。意欲假神剑之威而一扫彼时南宋偏居一隅的颓势。其它如宋儒刘子翚,在舟泊剑津时因忧虑“寓县兵犹斗,乾坤网正宽”而“殷勤属龙剑,莫久卧波澜”[4],显是在召唤时代英雄的出现。又如元人贡师泰借此典在其《感兴五首》中大声疾呼“一朝腾波去,化作苍龙吼。何时复归来,为国殄群丑”[24]。再如施开治记叙自己“每到登楼情未已,常怜神物世无多”,面对“茫茫独揽西收日,滚滚惟闻东逝波”这样一种山河日下的局面,所追问的亦是“安得潜鳞一再起,携云挈雨此中过”[4]。更有甚者,明人绉维琏就曾异想天开地问到:“我欲移文沧海去,檄龙还剑意如何?”[4]对龙剑的汲汲之情一致如斯。
“双剑化龙”的传说篇幅仅六百余字,所叙不过一事,却能为各朝文士所撷用,且能自出机枢,翻陈出新,生发出数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当我们对相关文本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品读时,屡屡会被这些意象与本事之间妙到毫厘的联结所折服。正如刘勰所言:“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25]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在长时段里历久弥新,维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历代文人不断以巧夺天工的才情神思去挖掘前朝文学遗产不无关系。
[1]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75-1076.
[2]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5-116.
[3]曹寅,彭定求,沈三曾,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3053,3913,617,8588.
[4]吴栻,蔡建贤.南平县志 [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1673,1599,1583,1659,1675-1676,1623-1624,1626,1650,1633,1626,1645,1620,1642,1561,1649,1616.
[5]尤侗.西堂诗集[M].清康熙刻本(卷三).
[6]司马光.司马光集[M].李文泽,霞绍晖,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23.
[7]刘仁本.羽庭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
[8]林鸿.鸣盛集[M].清初钞本(卷一).
[9]王恭.白云樵唱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
[10]董诰,阮元,徐松,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503.
[11]王象之.舆地纪胜[M].李勇先,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4213.
[12]薛敬孟.击铁集[M].清康熙刻本(卷五).
[13]黄裳.演山先生文集[M].清钞本(卷十二).
[14]金幼孜.金文靖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
[15]骆问礼.万一楼集[M].清嘉庆活字本(卷十四).
[16]祁彪佳.远山堂文稿[M].清初祁氏起元社钞本.
[17]杨杰.无为集[M].南宋刻本(卷三).
[18]李光.庄简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
[19]张宁.方州集[M].明万历重刻本(卷五).
[20]胡奎.斗南老人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
[21]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M].明正德十三年张芹刻本(卷二十一).
[22]林垐.居易堂诗集[M].明崇祯十七年刻本.
[23]陈淳.北溪大全集[M].明钞本(卷二).
[24]贡师泰.玩斋集[M].明嘉靖刻本(卷一).
[25]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436.
(责任编辑:冯起国)
Three Kinds of Literary Images about the Legend of“Double Swords Change To Dragon”
ZHANG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1)
The legend of"Double Swords Change To Dragon"recorded in Jin Shu is widely spread.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works which involve this legend,we can find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terary images about it.One is the continuation of legend itself,another i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location,the last one is the exposition of legend’smeaning.This paper is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text to explore the three kinds of literary images.
“Double Swords Change To Dragon”;legend;three kinds;literary images
I206.2
:A
:1674-2109(2017)05-0005-04
2016-12-14
张隽(1992-),男,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