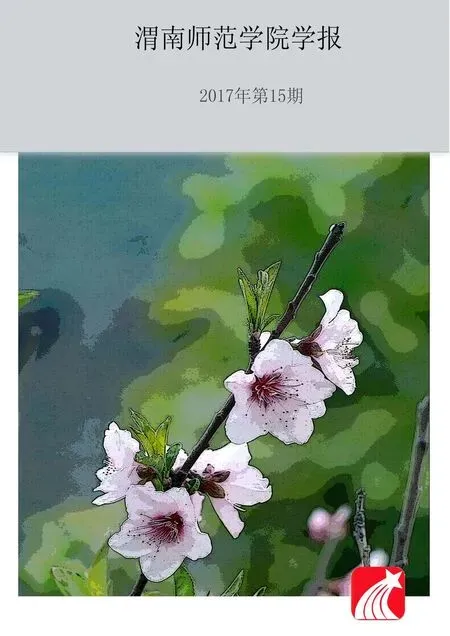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的经验建构
李 惠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语言文化与文为学研究】
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的经验建构
李 惠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直接生发于抗日民族革命的现实土壤,密切关注当时的文艺运动与现象,寻求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平实而鲜活的理论话语在总结文艺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指导着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促成了理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有效互动,显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探究延安时期文艺理论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建构文艺理论的中国气派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作为一种生发于民族革命历史现实土壤中的理论,有着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对敌战斗的气息,因此,常常被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其价值与意义被遮蔽。但当我们真正走进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文本,从民族革命的历史语境与理论实践的维度审视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文本,就会发现,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民族革命现实语境而创造出的时代特色鲜明、颇具中国气派的大众美学与文艺理论形态。文艺理论广泛吸纳劳苦大众意见,在总结文艺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指导着文艺大众化创作实践,显现出强烈的大众审美实践性。这些文艺理论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摆脱西方话语的束缚,建构颇具中国气派的文艺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意识激发的文艺理论民族性追求
延安时期民族革命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文艺理论打上了深深的民族性印记,突出强调文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国家意识。文艺理论家们能继承中国古代文论诗性感悟的理论表述方式,将对文艺真挚的生命感悟融入理性思考,化抽象为形象,颇具文学意味,凸显出鲜明的民族性。
首先,民族、民间文艺形式的倡导。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家浓郁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他们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艺术家偏向于学习外国文艺,民族民间文艺宝藏被搁置的经验教训,文艺理论积极倡导民族、民间文艺形式,彰显文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文艺理论家指出:“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1]152因此,文学艺术家要“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的营养”[2]621,为的是让民族的新文艺能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力量。“把‘五四’以来所获得的成绩,和中国优秀的文艺传统综合起来,使它向着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民族文艺的方向发展。”[3]598用中国的民族文艺形式表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以期建构一种“以我们民族的特色而能在世界上占一地位的新文艺”[4]604。理论家们深知,“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5]673,“那些失掉了文艺的民族性,忽略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作品”[6]633,在自己的民族中都无法立足,更谈不上立足世界。显然,民族、民间文艺形式不仅是唤醒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有效载体,而且是建构民族新文艺的有效途径,是文艺立足世界的有效保障。这种关于文艺民族性问题的思考超出了简单的文艺为抗战宣传的要求,而是站在世界文艺的广阔视域,将民族文艺形式的利用提升到了建构中国民族新文艺、彰显文艺民族性的高度。文艺的民族化与民间文艺形式的利用也不再是简单的接近民众的问题,而是文艺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凸显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问题,是中国文艺如何立足世界的问题,显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其次,平实而鲜活的文艺理论话语。延安时期许多文艺理论家本身就是文学艺术家,茅盾、何其芳、柯仲平、萧军、艾青、刘白羽等等,作家、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使得文艺理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偏重逻辑推演截然不同的感性直观形态,成为感性体验的描述,形成了平实而鲜活的文艺理论话语风格,颇具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诗性特征,可读性极强。譬如林默涵对当时文艺创作中两种错误论调的批驳:“一种是叫人站着不动,故步自封,不屑深入群众,放弃了可争取的读者不顾,却关起门来‘创造’读者;一种是叫人不学走路先学跑,要人一步就跨到彼岸。他们不知道,从起点到终点,是需要一个改造实践的过程,这貌似前进的论调,实际的结果是取消。说是树苗还非他理想的大树,就抡起斧子来砍掉,世界真有这样的蠢人呢。”[7]237没有抽象的理论演绎,没有枯燥的概念阐释,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既具感染力,又有说服力。塞克把作家文艺创作脱离现实的倾向比作是“脚不挨地”,针对脱离实际的幻想指出:“(幻想)这东西是专会骗青年,它既会飞又善变,它可以随便带着你飞到什么地方去,只是你千万不要睁开眼睛,你就能够永远得意,如果你睁开眼一看哪,我保证你要从天空跌下来,跌得昏头昏脑。”[8]生动的描述对于喜欢幻想的作家无疑是一剂清醒剂。文艺创作实践表明,即使是幻想也需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验基础之上。萧军对于相关文艺问题的阐释亦是感性十足。“天才是一块质地有差别的田地,学习就是肥料和耕耘。”作家“应该是座人类的百货商店”,读者是“你的主顾”,因此,“货物要好而廉、而精”,“否则,你一定要被遗弃”。作家体验生活是下海取珍珠,“珍珠要取到手,还要不为海水淹死才好”[9]。平实而鲜活的理论话语表达出对于文艺问题的独到体悟。艾思奇把文艺比作镜子,“作者的思想、世界观就是镜子反映的位置与方向,镜子因着位置不同,它可以直面现实,也可以侧面现实,甚至于会抹杀现实”。现实的形象“是文艺用以维持生命的养料的根源。离开现实的土壤,文艺就不能生活成长;离开了现实的形象,文艺就失去了反映现实的器官,失去了它的根”[10]269-271。因此,作家“要抱有恋爱一样的诚实坦白的决心与勇气”[11]309与现实合拍。生动形象的理论话语颇具文学意味,体现出文艺理论鲜明的中国气派。
可以说,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家兼文学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反对用成语来敷衍一切新的思想、情感和感觉”,文艺理论呈现出形象化、生动化的特点。他们并没有因深厚的西学积淀与宏阔的理论视野而居高临下,卖弄辞藻,而是立足民族文艺问题,深入浅出,撷取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颇具趣味的俗语加以譬喻,建构了鲜活而颇具民族色彩的文艺理论话语形态。文艺创作好比厨子做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演大戏的文艺现象被称为“只看见死人和洋人”;文艺的雅俗问题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抽象的文艺理论问题被现实化、形象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浓郁的生活气息。诚如艾克恩所说,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既无陈腐的学究气,也没有浅薄的八股腔。在清新、平实而又盈溢着激情的新型理论文体里,涌动着一股鲜活的精神。”[12]132不以逻辑演绎取胜,而以情感认同服人,突显出鲜明的民族性。
二、民族革命孕育的文艺理论时代性特征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从对文艺问题的感性捕捉到理性思索的每一个环节,理论始终向时代的文艺实践敞开。民族革命的时代任务容不得理论家们演绎形而上的抽象文艺定义,而是立足于时代要求,密切关注文艺运动与现象,探究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因此,文艺理论反对“那些抱着书本说梦话的空头理论家”,反对脱离现实的空喊,立足时代的使命,密切关注民族国家命运。针对抗战文艺问题,实时发出声音加以引导,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与鲜明的时代性。
首先,浓郁的战斗气息。延安时期文艺理论不是理论家们呆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抽象玄思,而是立足于时代任务的理性思辨。延安时期最重要的时代任务就是抗战,文艺理论亦从抗战这一时代重任出发,充满浓郁的战斗气息,主张文艺唤醒大众的民族国家意识,“用文字的方式号召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起来斗争”,用文艺作品讴歌“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怎样英勇地斗争,怎样为民族的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写我们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敌运动”[13]266,这是时代赋予文艺的历史重任,抗战的历史现实就是文艺理论预设的文艺的时代主题。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艺术都应该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记录民族英雄用血写下的悲壮史诗。现实主义文艺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这不仅是文艺理论对文学艺术的要求,更是历史时代的要求,因为这现实主义的现实“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现实,是我们时代的这个战斗着的历史现实”[14]251。因此,是否担负时代的重任成为文艺理论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之一,那些脱离抗战现实语境、脱离大众的艺术至上的创作倾向是不合时宜的,“舞台上看不见今天、本地的斗争生活,只看见死人和洋人”[15]的艺术是要被扬弃的。时代赋予文艺的根本任务是要“鼓舞青年知识分子为光明、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的实现而奋斗”[16]153,是要用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来教化大众,以求得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
其次,理论强烈的现实指向性。诚如赵超构所说,延安时期“延安人的作风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专顾目前的事业,没有工夫去玩弄缥缈虚无的‘游戏的理论’”[17]150。文艺理论密切关注文艺现实,总结实践经验,指导文艺实践,以期能更好地实现时代赋予文艺的历史重任。李伯钊《敌后文艺运动概况》全面总结了敌后戏剧运动、敌后文学、敌后音乐、敌后美术等文艺领域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对敌后文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胡蛮《抗战八年来解放区的美术运动》回顾了抗战爆发后各解放区美术领域的发展概况,肯定了美术反映边区建设与人民生活方面的巨大贡献,总结了美术工作的经验,对抗战期间边区美术的发展颇具启示。冼星海《边区的音乐运动》从音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任务谈起,回顾了抗战两年半以来全国音乐界的概况,进而客观评价了边区音乐运动的成绩、优点与缺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音乐工作者努力的方向。要加强音乐理论、创作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不脱离大众,深入实际生活等,促进了抗战期间音乐的发展。映华《谈谈边区的群众戏剧运动》立足边区戏剧运动现实,指出表演中存在背书似的对白,缺乏专门的人才和导演、演员长期的培养等问题,提出演员要深刻体验剧中人的身份,将自己化身于角色。要培养专门的导演与剧本写作人才,吸纳本地演员等理论建议,对当时戏剧表演艺术不无启发。
此外,周扬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雷铁鸣的《戏剧运动在陕北》、艾青的《展开街头诗运动》、林山的《关于街头诗运动》、茅盾的《抗战期间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等文章都能立足于抗战历史时代现实,指出抗战的政治形势给予艺术家的时代任务,并针对大众的审美趣味,提出一系列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主张,建构起了文艺理论的时代任务,在激发民族意识与大众审美趣味的探讨中进行着自己的理论思考,极具时代色彩。
第三,灵活多样的文艺理论形态。延安时期民族革命的历史现实使得人们无暇顾及刻板的理论模式,文艺理论颠覆了“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代之以灵活多样的理论形态。有实践经验的描述,如柯仲平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指出文艺创作要被老百姓认可,必须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你没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老百姓决不会相信你的领导。你一站到民众中去,你一讲话、行动,老百姓立刻分辨出你有没有中国味,正如听惯了平(京)戏的人,他一听得有人唱平戏,就会立刻感觉那有没有平戏的味儿。”[18]609有为纪念文艺刊物而写的心灵呼吁,“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19]。有对文艺作品的读后感,如陆定一《文化下乡——读古元的一幅木刻年画有感》指出:“了解了农民的生活与语言,才会真正实现‘文化下乡’。”[20]此外,还有各种讲话、演说,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塞克《在青年剧院学习总结会上的讲演》、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的问题》等。也有亲切交谈的书信体,如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十七封书信,周恩来《给郭沫若等同志的五封信》、老舍与周扬《关于文协工作的建议》的通信等,甚至是一些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决定、指示、社论亦包含着丰富的文艺思想。可见,务实的时代精神使得文艺理论突破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催生了灵活多样的文艺理论形态,突显出鲜明的时代感。
可以说,延安时期民族革命的现实,使得文艺理论家不局限于摘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只言片语,而是从其基本立场、方法出发,立足中国抗战的历史语境,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把文艺理论从教科书式的抽象玄谈转化成为具有浓郁生命气息的民族大众生活美学,为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理论指导,成为时代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
三、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的实践性互动
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吸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忽视大众接受水平与审美趣味的教训,突出强调大众的审美趣味、接受能力,将其作为衡量文艺的标准之一。大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意见被理论家吸纳,成为文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影响着文艺创作。因此,文艺理论反对那种拒读者于千里之外的印象派、未来派的作品,强调作家创作要符合大众审美趣味与接受能力。文艺理论明确表示,“一个作品如果读者根本不能读懂”,那么至少它是不合时宜的。文艺实践表明,“你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你比老百姓进步,他们一定会接受你的领导。你给老百姓弄一套八股,弄得他们莫名其妙,他们虽然也有讲你‘本事大’、‘了不起’的,但你的戏一唱久了,就一定‘粘不住’他们”[18]609。显然,那些不符合老百姓艺术审美趣味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因此,怎样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更通俗,在表现形式上更带有民族气派,而能为更多的人接受”成为延安时期文学艺术家与理论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立足抗战现实语境,“就广大人民的现有文化水平,给以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7]235,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走向农村,深入大众生活,创造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成为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向文学艺术家们发出的召唤。1942年文艺座谈会后,文学艺术家们纷纷走入工农大众,扬弃了以往文艺创作中脱离现实的倾向,积极投入工农大众生活,探索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创作,实现了文艺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的有效互动。
首先,文艺理论家基于文艺实践的理论研讨与批评。延安文艺的实践迫使理论家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而这种理论思考与批评又指导着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1938年1月,成立一年的战歌社举行诗歌、民歌演唱会,“发出300张入场券,到场者两百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但因朗诵效果不佳,室内太冷,晚会节目演出不到一半,听众已所剩不多。组织者打算中途收场,毛泽东却稳坐不动,支持按原计划进行到底”。事后文艺理论家展开研讨,总结经验教训,指出朗诵“不是口号或演说,也不是狂叫,要注意朗诵诗与念的诗、吟的诗的区别,要当场能吸引住听众”;“要有丰满的感情和动人的技巧,要合乎诗的音韵旋律,朗诵者的感情、表现应和诗歌的内容相吻合;避免不必要的动作与姿势”,“是朗诵不是演戏”[12]149等等。这种文艺实践问题的理论研讨有效指导了诗歌朗诵艺术的发展,使后来的朗诵像战鼓和号角一样,振奋人心。再比如,话剧《血祭上海》演出后,文艺理论家召开了作品座谈会,从艺术表现层面展开探讨,大家普遍认为主题是正确的,但存在“人物太公式化”,“戏不统一,恋爱气味太重;阿毛太漂亮,不像工人”,“剧本与事实不大符合”[12]137等问题,对后来的戏剧创作与表演颇具启发。针对《天皇的恩惠》剧本,理论家指出,剧本“巧妙地用平常的故事反映出日本国内劳苦大众生活的悲惨和他们对于这次战争的厌恶”,但“社会背景穿插太少”,未能“将日本国内劳苦大众反对日寇侵略战争的情绪表现出来”[12]138。这些关于作品艺术表现层面的实事求是的理论批评,有效指导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实践,使得延安文艺在追求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同时,更多地把关注的视角放置在文艺的现实语境与文艺的本质真实。
其次,大众对文艺作品基于生活经验的品评,促进了延安文艺真实性的追求,对于推动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意义重大。延安时期工农大众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对于文艺作品的接受、品评基本上是基于其生活经验。他们特别看重文艺的真实性,要求作品内容多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写虚无的故事”。这种对艺术真实再现现实的要求,使大众在知识分子作家深入农村生活的浪潮中,获得了参与文艺创作与评论的话语权。工农群众俨然成为最公正严格的批评者,秧歌剧的创作便是大众文艺评论话语权的集中体现。“写作过程中请农民参加,写好又读给他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文艺“成为和他们结合以后的产物,不仅剧作者如此,演员也是如此,演员为了表现一个动作,往往在农民中生活很久,观察他们、体会他们”。延安时期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许多动作就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有的则是经过他们修正的”[21]561。这种立足于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才被大众视为是真实的艺术。胡一川的木刻版画《军民合作》创作好后,被许多美术家视为精品,但当地老农则指出,“驴儿的胸靽画得太紧了”“驴儿的屁股没有那样高(太突出的意思),尾巴没有那样长”。[22]547胡一川接收了老农意见而修改了原来的画面,使作品细节更为真实,也为大众所认可。这种群众的批评意见,虽然称不上艺术理论,但因为有深厚生活经验的积淀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夯实了文艺的生活基础。对当时的文艺创作与表演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使得文艺创作“以富有生命力的活的语言,代替那没有生命的道白,表演手法上也加以现实的基础”,表演中“每一个角色,甚至跑龙套的,也表现出各个不同性格的内心情感”[21]564-565。这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有效互动避免了艺术家创作中忽略受众群体的自我陶醉,奠定了文艺创作坚实的现实基础。
第三,文艺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有效互动。延安时期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运动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文艺的热潮,工农大众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成了与艺术家对话交流的过程,他们对于文艺作品的意见,被文艺创作者吸纳,实现了文艺创作者与欣赏者的有效互动。譬如歌剧《白毛女》即是“一边排一边征求各方面群众意见进行修改”而成,并在“全剧彩排时又根据群众意见要增加最后一场,表现斗争黄世仁的群众场面”[23]11。不仅如此,有的甚至在反复演出后加以修正。比如秧歌《拥军花鼓》演出时,每次唱到“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时,观众都大笑不止,开始演出者“以为演员表演精彩,引起笑声,后来发现,不对!笑得有些蹊跷!几场演出都是在‘哎哩美翠花,黑不溜溜儿花’处大笑”后经咨询秧歌把式,得知“那是一句儿话(不好听的话)。是说男女下身部分……”于是,后来歌词改成了“哎哩美翠花,海哩海棠花”[24]171。之后,这个作品演出时,“当领唱者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时,作为听众的农民老乡马上就接唱道:‘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25]这种文艺创作者与接受者的有效互动使得延安文艺成了一种近乎狂欢化的全民活动,所有人都是文艺的创作者与参与者。对于文艺活动“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说,它是全民的”[26]6。这种文艺创作与接受的有效互动颠覆了传统文艺的等级秩序,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建构的文化秩序,实现了文艺的日常生活化,使得大众有了表达艺术见解的诉求。在文艺的全民狂欢中,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作家之间的距离感消失了,知识分子作家融入工农大众形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同志关系,极大地强化了大众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总之,延安时期民族革命的历史现实与文艺理论家兼文学艺术家的身份,使得文艺理论消解了纯粹观念化的抽象玄思,突破了理论研究纠缠于虚无概念的局限,获得一种生命体悟式的感性化存在。理论彻底向民族文艺实践开放,实现了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对话与交流,大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批评,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点评文艺作品。虽然这样的批评会消解理论的深度,但却使理论走入了文艺实践话语,变得鲜活,突显出强烈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为我们建构文艺理论的中国气派提供了切实的历史经验。
[1] 巴人.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M]∥苏光文.文学理论史料选.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
[2]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 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4] 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5] 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6] 光未然.民族的文艺形式问题[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7] 林默涵.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8] 塞克.在青年剧院学习总结会上的讲演[N].解放日报,1942-06-30.
[9] 萧军.对于当前文艺问题的我见[N].解放日报,1942-05-14.
[10] 艾思奇.文艺创作的三要素[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1] 刘白羽.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2] 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上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3] 成仿吾.写什么[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4] 冯雪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5] 萧三.可喜的转变[N].解放日报,1943-04-04.
[16]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7] 赵超构.延安一月[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
[18] 柯仲平.谈中国气派[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9]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N].解放日报,1942-03-11.
[20] 陆定一.文化下乡——读古元的一幅木刻年画有感[N].解放日报,1943-2-20.
[21] 周而复.边区的群众文艺运动[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22] 李伯钊.敌后文艺运动概况[M]∥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23] 贺敬之.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M]∥张军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
[24] 刘炽.“鲁艺家”的秧歌[M]∥任文.永远的鲁艺(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25] 黄钢.皆大欢喜——记鲁艺宣传队[N].解放日报,1943-02-02.
[26] [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导言[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贺 晴】
Popular Aesthetic Practice in the View of National Revolution
— Experienc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in Yan’an PeriodLI 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there is a tendency to deviate too much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n’an and to emphasize the ideological meaning. When we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Yan’an, stripping its ideology,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Yan’an’s literary theory, we found that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Yan’an period originated directly in the real soil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It was directed at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theory with plain and fresh theoretical discourse. Criticism and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of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It is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of the model, so exploring the Yan’an period literary theory to get rid of the great impact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uite Chinese style of literary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Yan’an period; literary theory; nationality; times; practice
I206
A
1009-5128(2017)15-0061-06
2017-04-24
陕西省教育厅2017年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研究;延安大学红色文艺研究中心资金项目:延安时期作家身份认同研究(ydhsy16003)
李惠(1976— ),男,陕西榆林人,延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