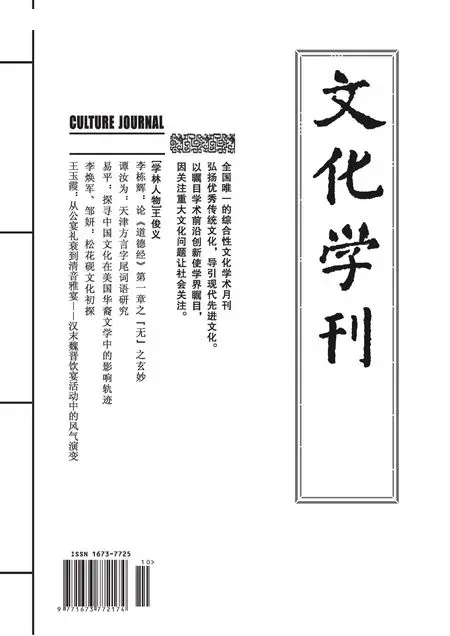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看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特征
郑潇雨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周丹】
【文史论苑】
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看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特征
郑潇雨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当今的政治学领域依旧占有一席之地。柏克的思想在众多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中极具代表性,柏克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保守主义的鼻祖,其在著作《法国革命论》中批判了大革命抽象性的荒谬和激进性的破坏,强调了抛弃传统经验的灾难性后果和对既定社会秩序思想体系的肯定及维护。
柏克;保守主义;法国大革命;反思
一、研究背景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法国,处于社会和政治的大动荡时代。大革命的发生,摧毁了在法国存在上百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在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指引下,无数民众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攻占了巴士底狱,将贵族统治推翻,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随着这场革命的愈演愈烈,激发了海峡对岸的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
在这场革命中,启蒙的理性主义激化演变为社会冲突,在这种反对力量和理性主义横行并且不断摧毁现有秩序和稳定财产的基础下,保守主义才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柏克提出。柏克的保守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冲突下的产物,其目的在于护卫旧有稳定的秩序及社会稳固的根基。因此,柏克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保守主义的鼻祖,其后所发展的保守主义学派虽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其核心思想都与柏克相通。
作为英国最早且最突出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者,柏克在其著作《法国革命论》中,批判了以让·雅克·卢梭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对理性的无限崇拜,在柏克看来是极其荒谬的。理性的理论模式无法应对现实,个体的情感和易错性在发挥实际作用上远超于理性,这种对个体的理性怀疑和对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一直贯穿柏克思想的始终。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柏克认为只能求助人类历史长期积累的共同智慧。
在柏克看来,大革命后期已经演变为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这场失败的实验,摧毁了法国多年积累的文明和智慧。混乱动荡的社会秩序下,必然产生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而其后果只能是一场大灾难。
二、理论与现实之间:对卢梭的批判
柏克称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哲学的革命”,因为其思想基础在于启蒙运动,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丰富的哲学理论色彩。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启蒙哲学家描述了他们所赞同的理想政权模型、国家的政权合法性所在及正义的立法模式。从“天赋人权”到“主权在民”,他们对于个体权利的呼吁,以及对建立新的自由秩序的主张等,都深深影响着法国大革命的方向。这其中,让·雅克·卢梭就是典型的代表,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全面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卢梭看来,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不利于生存的因素,因而通过契约的方式,联合组成了国家状态。在此基础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被建立于社会契约之上,由此个体将自身的权利交付于国家,因此国家的权利来源于人民,即“人民主权”。
但卢梭丰富的理论思想在柏克看来无比荒唐可笑。首先,从国家产生的起源来讲,柏克持有和卢梭截然不同的观点。柏克并不追究最初始的国家建立究竟是否来源于契约论,其认为目前最值得去关注的应该是现实的、现在的国家。也就是说,柏克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接近于18世纪自然法的思想,即国家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产物,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那么,国家既然联系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即便可以被叫做契约的模式,也不会是一种随时可以取消解除的模式。对于那些单纯以偶然的利益为目标的各种附属性契约,是可以随意解除的,但是国家却不可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不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协定,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1]因为如果按照卢梭的模式推进下去,那么一个政权一旦存在某些问题、破坏了契约,就应该被推翻,其会造成一种政权随着流变不定的公民要求而随时宣告解散的局面。“人民的权威,只要他愿意,无须任何理由便有权解除这一约定。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依附,仅仅是在国家赞同他们某些流变不定的规划时方才存在;那是随着政治体制之符合他们暂时的见解而开始和终结的。”[2]而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存续的可能性,显然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极其荒谬。
将国家纳入历史的时间线上来讨论,柏克赋予了国家极高的神圣性和崇高性,“所以国家就变成了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在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3]因而,柏克对于君主制的维护是相当虔诚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柏克就不否认任何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存在问题。
既然可能存在问题,那么该如何对待国家的错误呢?柏克认为应该持有一种像“接触父亲的创伤一样”的态度,而不是凭着一套不合于实际的理论就推翻了“父亲”,并直接判处父亲“死刑”。这种思想也是他对于革命的看法,即疯狂地去推翻一切在他看来是绝对的灾难。
因此,柏克认为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家之荒谬就在于其对于现实的忽略,对于国家存续的忽略。卢梭一味地强调抽象的政治理论和超验的政治理想,而对于现实的国家来说,这种理论在解决问题上毫无意义。“公意”如何得以可能?怎样去避免大多数人的暴政?“人民主权者”具体到实践如何落实权利?面对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柏克认为卢梭都没有进行正面的回答。
由此可以看出,柏克的原则展现了保守主义在基本意识形态上是倾向于现实而非理论的。为现存的秩序进行辩护、关注如何维持现实稳定的基础、进行更平稳的纠正错误才是保守主义所看重的,因而保守主义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没有理想的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会设计一种他们意识形态下的理想的政治模式,并给出一套理论构建,但保守主义没有理想,保守主义的理论也只是用来反驳一切对现存秩序进行挑战的理论而存在的,因而保守主义是对现存既定制度和价值的肯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改变,保守主义不拒绝次要的改变,也就是说这种改变必须不是推翻国家、重构社会性质的改变。
三、传统与决裂之间:习惯的可靠性
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成见还来源于他对于革命所宣扬理性思想的质疑。在他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过度强调了理性的作用,即用理性来评判衡量一切。但柏克从未赋予理性以很高的地位,不仅仅因为在这样的信条下,个体从理性出发推演出一套充分自洽的理论体系不能套用到现实的社会中;更因为柏克对人的理性持有像休谟一样的观念,即人性是容易犯错误的、感性的。因而在理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绝不能依靠理性的信条去处理现实的政治问题。那么应该依靠什么呢?偏向于支持经验论的柏克给出的回答是传统、惯例,或者说是习惯。
柏克认为习惯和传统相较于一个时代的个人理性来说,是丰富可靠的。“我们怕的是每个人单只是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储存而生活与交流,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每个个人的储存是少的,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总的库存和资产的话,他们就会做的更好。”[4]也就是说,在柏克的假设中,人是情感和理性的造物,但是经验和习惯确实比理性、逻辑、抽象和形而上学更好地指引人们。“一个国家按照这些准则行事,无论会得到什么好处,都会像是在一种家庭协议中那样地牢靠,像是在一种永久产业中那样地又有把握”。[5]因此,柏克赋予了经验以极大的可靠性,可以说柏克是持有经验论的观点,更倾向于真理存在于具体的经验之中而不是普遍的推理命题之上。
相反,抛弃传统的创新精神,在柏克看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创新的精神一般都是一种自私的气质和局限的眼光的结果。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子孙后代。”[6]抛弃历史传统经验的人,无法对后人负责。“经常大量地和多方地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和赶浪潮而在毫无原则地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索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7]那么照此逻辑来说,柏克的眼中,好的政治家的政治伦理底线在于维持整个国家的存续,关注世代的衔接而不是创造新的政治理论。
所以,秉持着创新、理性、破除旧制度的法国大革命在柏克的眼里就是一个相比于过去更加糟糕的灾难。这场革命破坏了原有的秩序,将法国毁为一片废墟。“它扬言是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我认为它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8]柏克精准地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历史的进程完全按照柏克的假设来继续,即“任何企图根除现有社会邪恶的努力往往会导致更大的邪恶”。
那么既然如此,就不需要革命了吗?并不是。在柏克看来,对待国家错误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保持这个国家现有财产稳定和存续的基础之上,进行温和地尝试。“保存现存事物的一项,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这就是我对一个政治家提出的标准。”[9]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英格兰的那场光荣革命被柏克奉为完美的改革范本,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没有发动任何的流血冲突便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实现了破坏性最小的革命。柏克的思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保守主义思想学派的一个重大前提,即他们依赖于时间累积下的经验和传统中的智慧,支持现有的既定的政府体制,而反对未经过实验的改革方案,因为这种方案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其建设性。
四、自由与秩序之间:反对激进主义
既然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反对创新性理论的提出,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自由?是不是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就意味着站在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纵观柏克的整个思想体系,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柏克决不反对自由,因为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他为之所辩护的英格兰的社会体制就是一个自由的体制。在18世纪后的英国,工业革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得以摆脱国家的控制而自由,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这种现象,这种自由的气息,是柏克所乐以见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归柏克所说的,他热爱“有秩序的自由”。那么何为“有秩序的自由”?“有秩序的自由”和“保守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首先,对比柏克对两场革命的态度来看,柏克肯定了美国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体,批判了法国大革命。这二者看似都破坏了所谓传统,但其实二者并不相同。美国的革命,使美国脱离其作为英属殖民地的状态,成为共和国且保存着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旧风俗,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可以实现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政体。而法国则不同,法国人将君主和皇后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确打破了之前的传统,但是他们并未有所建设,他们以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来伪装自己,声称达到了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然而这种理论下所包装的,依旧是一个旧的政体的内核。国会被解散,督政府上台,随后拿破仑称帝,这场革命的确摧毁了封建制度,可是在政治上并没有给每个公民带来新的自由,反而摧毁了法国社会原本就薄弱的自治传统,使整个社会滑向了寡头政治的深渊。
那么这样看来,柏克眼中的敌人是自由主义吗?显然不是。保守主义所追求的是自由的秩序,而不是扼杀自由的秩序。柏克真正反对的是没有秩序的自由,也就是说,柏克所反对的,是激进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因而柏克的思想在某些环境下,实际上维护了自由主义的制度,且柏克所强调的审慎的态度实际上只是反对了极端的激进主义者。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之一就是他们的对立面往往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那些激进主义者。激进主义者,从先验的理论上描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并以此套用评价现实社会的政治存在。当现存政治制度和他们的理想存在较大差距时,就会向现存秩序发起攻击。保守主义则相反,他们在观念上不具有先验的理论性,而是具有内在的制度性。这种制度性表现在,当激进主义者和现存的制度存在冲突时,保守主义则维护既定的秩序和制度。
五、结语
在法国大革命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柏克的保守思想对封建君主制的维护显然是过时的。并且他对英法革命的分析也忽视了法国政治传统、社会现状与英格兰之间的区别,对法国革命的复杂性作了较为粗暴的归纳和理解。但总体上来说,柏克思想上的前瞻性是远超于那个时代的,他首当其冲地对大革命提出了反对的观点,他看到了启蒙理性的不足,以及其片面性和抽象性所导致的对现实的忽视。他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审慎态度,以及对时间积累下的经验的提倡也对后世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1][2][3][4][5][6][7][8][9]柏克.法国革命论[M].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29.118.129.116.44.44.127.164.44.
D091.4
A
1673-7725(2017)10-0230-04
2017-08-01
郑潇雨(1996-),女,河北石家庄人,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