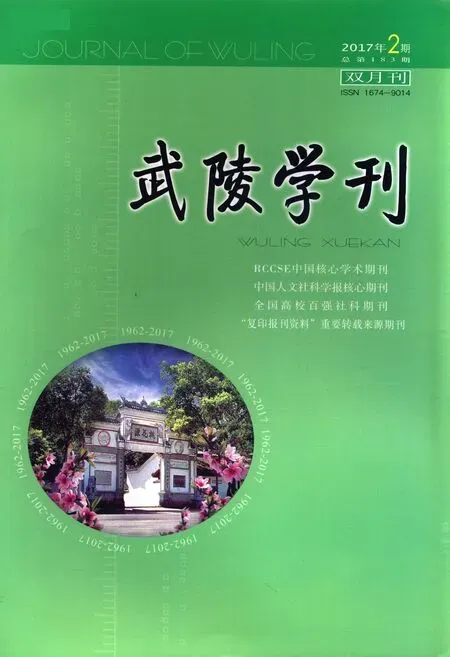郭象“相因”论思想析微
黄圣平
(上海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44)
郭象“相因”论思想析微
黄圣平
(上海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444)
“相因”论是郭象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建立在个体主义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的“独化而相因”的思想,是郭象对“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之自然机制内涵的独特把握。在郭象的“相因”论思想中存在着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名教和政治领域的扩展。探究郭象的“相因”论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其玄学思想和道家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理论传统的理解与把握。
郭象;《庄子注》;“相因”;独化
郭象(约公元252—312),字子玄,洛阳人,西晋时期著名玄学家。在魏晋玄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郭象哲学以其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理论立场凸现其鲜明的思想特质,并据此占有较为独特的思想史位置[1]191。笔者以郭象《庄子注》为文本依据,分析其哲学思想中的“相因”意涵及其自然观中的证明理路,探讨他在继承和发展道家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理论传统方面的独特智慧和运思轨迹,以深化对其玄学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一、“相因”的含义
“相因”是郭象玄学思想的中心范畴之一。在自然观的维度上,通过“独化而相因”的命题,郭象对传统道家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机制作出了具有独特性的诠释,在思想史尤其是在《庄》学诠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相因”中的“因”字,《广韵·真韵》说,“因:托也,仍也,缘也,就也”;《说文解字·口部》说“因:就也。从囗、大”,又,关于“就”字,《说文解字·京部》曰:“就:高也。从京从尤。尤,异于凡也。”桂馥注:“此言人就高以居也。”孔广居注:“京,高丘也。古时洪水横流,故高丘之异于凡者人就之。”可见“就”主要可以理解为“趋就”的意思。这样,“因”的含义,“托也,仍也,缘也,就也”,就是依托也,仍袭也,因缘也,趋就也。由此可见,“因”既有因果关系上之因缘、原因、依据的含义,也有行为方式上之因顺、因仍、因袭的含义。这两方面的含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以此为据,“相因”的含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客观事实;一是指双方之间对对方的因顺、顺应,指它们彼此间关系的特殊实现方式。换言之,“相因”一方面意味着相关双方间因果关系的存在,意味着相关双方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指这种因果关系的实现要采取彼此因顺、相互顺应的特殊方式。这样的理解,在《庄子注》中,是有直接依据的:
夫物之偏也,皆不见彼之所见,而独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则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则以彼为非矣。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2]66
这是郭象在注解《庄子》“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一句时说的,其中“相因而生”是对“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所谓“方生之说”)一句的直接解释。何谓“方生”呢?《说文解字·方部》说“方:并船也”,则“方生”者,并生也。“彼”“是”之间,正如“是”“非”之间一样,它们相对而生、相依并存,故此处之“因”乃依据、原因、缘由之意,而在郭注中所谓“彼是相因而生”,其含义也是指彼、是之间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彼此作用而生,故“相因”就有了相互依托、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含义。在本句中,郭象对“相因”范畴的使用是随文作注,其注文是对《庄子》原文内容的简单解释。但是,这恰恰说明在郭象处,其所谓“相因”,是包括了相互作用、互为依据、彼此影响等含义的。
但是,作为《庄子注》中的重要范畴,郭象对“相因”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与“独化”“玄合”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郭象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夫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反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两之因景也,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也。[2]111
在原文中,郭象说“众形之自物”,“造物无主,而物各自造”,然后在此万物各“自生”“独化”的基础上提出“彼我相因,形景俱生”“罔两之因景也,犹云俱生而非待也”的命题,似乎是否认在罔两、景、形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相生与因果关系。但是,同样是在《庄子注》中,郭象关于物、物关系的分析又是肯定这种因果关系存在的。他说:
夫竭唇非以寒齿而齿寒,鲁酒薄非以围邯郸而邯郸围;圣人生非以起大盗而大盗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势也。夫圣人不立尚于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无贵贱,事无真伪,苟尚圣法,则天下吞声而暗服之,斯乃盗跖之所至赖而以成其大盗者也。[2]349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在唇、齿之间,“鲁酒薄”与“邯郸围”之间,“圣人生”与“大盗起”之间,它们在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具有因果和生成关系。只不过郭象强调了这种客观关系在实现上的无目的性,不是相应的主观动机所致。为此,郭象进一步分析说: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2]579
这是对唇、齿间客观上存在的相生与因果关系之实现机制的揭示。此机制,可以概括为“自为”而“相济”。若套用《齐物论注》中描述罔两与影、形之关系的话语,则可以概括为“独化”而“相因”。可见,在罔两、影、形等彼此之间,不是一种线性的、单向的外在归因,而是一种彼我并立、共时俱生的双存格局。关于这种双存格局,一方面,其中的物、物关系,如形生影,影生罔两等,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关系性事实。作为一种关系性事实,其对关系的双方都具有客观的实际影响,从而与“相因”范畴的第一层含义(即相互依托、影响和作用的含义)相符合。表面上看,似乎罔两、影、形之间不存在相互间的依赖关系,彼此互不相待,而各自在独立地发展自己,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彼此配合的关系,且只有在彼此配合的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性事实方能得以实现和完成,因此,如果有一方未曾处于“独化”状态,那么双方之间的配合就实现不了,相应会影响到对方“独化”状态的完成,二者间“相因”的事实性关系就无法完成。因此,在似不相涉的“相因”“玄合”状态下,每一物之“独化”均存在着对相关他物“独化”状态之依赖,彼此互为条件、互相影响与作用,而这种作用和影响,从正面看是一种互济与配合,而当其得不到实现时即一转而成为彼此间的限制条件。所以,“相因”的含义,在物、物关系上,首先意指双方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具有彼此依托、影响和作用之义。而另一方面,郭象在《庄子注》中应用“相因”范畴,主要重在强调建立在各自“独化”基础上的物、物间彼此因果、作用关系之特殊的实现方式。这种特殊的实现方式,就是物、物间的各“自为”而“相济”,“独化”而“相因”以及“相因”而“玄合”之彼此因顺和相互顺应的实现方式。对此,郭象进一步说:
卓者,独化之谓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唯命之从也。[2]241
“故人之所因者,天也”,且“人皆以天为父”,则此“因”乃因顺、顺应之义,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同理,“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则物、物间的“相因之功”乃是它们彼此之各自“独化”的结果。既然是各自“独化”,当然首先是自身之“独化”,然后则是对对方之“独化”状态的因顺和顺应,以及因此而来的彼此间的默契、玄合。这种默契与“玄合”,作为物、物彼此因顺、顺应的结果,就是所谓“相因之功”。因此,在此处,郭象所谓“相因”之“因”,其含义主要是因顺、顺应之义,“相因”即指物、物彼此之间的相互因顺和顺应,而所谓“玄合”者,亦即是指由此相互的因顺、顺应所带来之物、物间彼此的默契、协调与配合。要而言之,在物、物关系上,“相因”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彼此因顺的双重含义,且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是以彼此因顺的方式实现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客观关系。这是我们在分析郭象的“相因”范畴时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
二、“独化而相因”在自然观上的证明
在郭象哲学中,“独化而相因”可以说是其自然观上的核心命题。关于这一命题,在郭象那里,不只是对物与物关系中所存在之自然机制的一种简单揭示,更重要的是他从本体论维度对该命题所进行的必然性之证明。郭象对这一命题的证明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本体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在现象界,物与物之间的“独化而相因”,要从物之“独性”的“无待”与“自生”特征及其“自物—他物”和“自物—世界”的内在结构上加以证明。
(一)物之“独性”
在郭象哲学中,物“性”的含义需要从物之存在的形式因的角度加以理解,主要是指个体物的本质和本性,因此也可以用亚里士多德“属+种差”的公式去把握。例如,郭象说“目能睹,翼能逝,此鸟之真性也”[2]696,就可以表述为“鸟是有目能睹,有翼能逝的动物”,其中的“动物”是“属”,而“目能睹,翼能逝”则是“种差”。又如,郭象说“夫民之德,小异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废者,耕织也;此天下之所同而为本者也。守斯道者,无为之至也”[2]334,就可以表述为“民是以耕织为事,以求满足衣食之需的社会角色”,郭象的这一分析显然也可以纳入“属+种差”的公式之中。又如,郭象说“马之真性,非辞鞍而恶乘,但无羡于荣华”[2]331,这是将马的社会性纳入到了其自然本性之中,可以表述为“马是能够为人设鞍而乘的家畜”等,从社会性的角度看,这一分析也有其合理性。当然,以上诸例都是对个体物所属之类性的把握,可见郭象所言之物“性”的内涵之中包含了物的类性,此正所谓“小异而大同”也。
进一步来看,在《庄子注》中,个体物之物“性”的内涵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这是因为任何个体物的类性本身是多层次的。这些层次,依照《庄子注》中的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物质性层面,指阴阳、殊气等相应的构成质料和存在特征,如“殊气自有,故能常有”[2]910等;其二,生命性层面,指知、情、欲等本然性生命需求的内容和相应特征,如“言物嗜好不同,愿各有极”[2]606,“物皆以任力称情为爱”[2]1075等;其三,社会性层面,指人和万物之社会性、角色性和名教性的内容与特征,如“言人之性舍长而亲幼”[2]533,“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2]318等。显然,这些方面和层次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之“理”可以通过“属+种差”的方式加以把握和分析。这样,个体物的“性”本体,在类性层面,其内涵就是一个涵括了物质性、生命性和社会性等多层面的立体结构,并因此能为该个体物的所有类性特征提供本体论的依据。
尽管如此,郭象对物“性”的分析,还是应该更多地从物之个性的角度去把握,这也是他将个体物之物“性”称为该物之“独”性的缘由所在。比如:
言卫君亢阳之性充张于内而甚扬于外,强御之至也。[2]142
不问远之与近,虽去己一分,颜孔之际,终莫之得也。[2]221
……以其性各有极也。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以相跂……[2]13
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际,即不可以相跂……[2]313
依照郭象所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2]11,且此“性”与“极”乃“毫分不可以相跂”者,则这种“不可以相跂”之“毫分”就是该物与其同类他物间的“个体差”。换句话说,一物之物“性”的内涵,除了该物所属的类性之“属+种差”的方面外,还具有“种+个体差”的方面[3]。例如,卫君之个体差(亦即他与其他君王间的差别)即是他之“强御之至”的“亢阳之性”,而颜回之个体差就在于他与孔父之间的贤、圣之别。这样,由于所谓物“性”不仅具有“种差”,更具有“个体差”,且此种“个体差”是本质意义上的,具有独异性和独一性,故郭象认为物“性”为物之“独”性。总之,依照郭象所言,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任何两个个体物,每一个体物都是独异和独一的,而这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一片树叶也都是独异和独一的一样。我们看到,郭象对物“性”之“独”的强调,其目的在于彰显个体物本“性”之特殊性和独一性。
(二)物“性”之“无待”与“自生”
进一步追问:在郭象哲学中,物之“独”性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对此,郭象给出了特殊的解答。他说:
初,谓性命之本。[2]554
初未有而欻有,故游于物初,然后明有物之不为而自有也。[2]712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2]425
在此处,“有”即个体物的存在,“有之初”即个体物的成形之“初”,也就是其“未生而得生”“未有而欻有”的那一瞬间,因此它是一个时间性范畴。依照郭象所言,此“初”不仅为物“形”之始,且亦为该物的“性命之本”,因此,在此“初”时的瞬间所定型的,不仅是物之“形”,且亦有物之“性”,或说是该物之“形”与“性”在此“初”时同时定型、发生。这样,关于个体物之“性”的存在方式,郭象首先就否弃了它们在物“形”之外的独立的实体性存在,也就是说物“性”不可能以类似“理念”的方式存在于现象世界之外,它们不可能是先天性和超验性的存在,不可能在具体的、经验的个体物尚未成形之前和之先就已经以“理念”和“实体”的方式存在于超验的逻辑性的“理”的世界之中了,因此,一物之“独性”,作为该物存在的本体依据,它只能是以“形式因”的方式存在于物“形”的现象之域中。同时,作为一个秉持本质主义思想理路的思想家,郭象也不可能认同物之存在先于本质,不可能认为物“性”是在物“形”的生成过程中后得的,所以他只好将此物“性”的发生和定型放在了此个体物之将“形”而又未“形”的“有之初”,认为它是在此“初”之瞬间而“突然而自得此生矣”①。然则,何谓“突然而自得此生矣”?郭象说: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寻其原以至乎其极,则无故而自尔耳。[2]496
天机自尔,坐起无待。无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而责其所以哉?[2]111
这是对物“性”之因的终极性追问,而追问的结果则是“无待”而“自生”。具体追问的过程,若联系郭象在《齐物论注》中对“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之常识性追因理路的否弃,即可见其运思理路之内蕴。
1.物“性”之“无待”。在郭象看来,由于物“性”在“初”时定型、发生而存在,同时它又不存在于物“形”之外,故不能将其脱离现象领域而在超验之域中作逻辑推演,而只能在现象界的物、物关系领域追问其因缘与来由。在现象世界的追因过程中,由于物之“独”性的独异与独一,更由于物之“独性”所具有的在物“初”即定型、发生而存在的独特存在形式,使得在否弃了“造物者”的前提下,郭象认为此物之“独性”,在形式因的维度上它无所归因,即是说它不能归因于任何他物(包括其母体物)之“独性”,其存在及其内涵也不能由任何他物(包括其母体物)之“独”性予以推出,此即是该物之“独性”的“无待”②。换句话说,尽管在现象领域物与他物间存在着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的因果关系,但是就它们各自的“独性”而言,它们之间却并不存在任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逻辑关系,它们之间不能彼此推导,而是各自封闭与独立。这一点,反映在罔两、影、形关系中,即指它们之“独性”各自“无待”而独立,也就是说“罔两”之“独性”不依赖于“景”之“独性”,“景”之“独性”也不依赖于“形”之“独性”。
2.由“无待”而“自生”。在《庄子注》中,“自生”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指物之“独”性的“非他生”“非有因”和“非有故”[4]232,也就是说乃“无待”而“自生”。这一点,反映在罔两、影、形之“独性”的关系上,即指它们各自乃“自生”,乃“无因而自尔”,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关系,因此各物的“独性”自身乃是封闭的,相互之间也是隔绝的,是没有窗户可供彼此出入的。另一方面,则是指个体物之现象存在即以其“独”性为依据,而不以任何其他外在的东西为依据。这一点,表现在罔两的生发问题上,即指其之生发出来,其依据只在于罔两自身之“独”性,而与影之“性”、形之“性”、造物者等皆无关系③。
3.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区分。进一步考察,在郭象哲学思想中,尽管他认为物之“独性”不是独立性的实体存在,而只是以形式因的方式存在于物“形”的现象之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认识论角度将其剥离和抽象出来,进而认为在其思想中存在着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区分,并因此形成一个性本论的思想体系[5]。在现象界与本体界两分的理路下,所谓“无待”“自生”就只是郭象关于物“性”本体的概念,而在现象界是不存在无待的、自生的事物的④。若问:何以非要主张物之“独”性为“无待”而“自生”?答曰:唯有如此,方能赋予事物自身之“独”性以本体论上的首要位置,并因此将个体性原则上升为理论建构的首要原则。这一点,可以说是郭象哲学在中国哲学之思想传统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地方,也是他作为独特性思想家之地位得以奠基于其上的关键所在[1]31。要而言之,在性本论的理论基础上,郭象建构了一个个体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他对个体主义之本体论首要地位的建构,主要落实在他关于物之“独”性的“无待”与“自生”的论断之上⑤。
(三)独化而相因
在个体主义本体论哲学的理论立场上,郭象提出了“独化”而“相因”的理论,其目的在于在本体界物之“独性”各自“无待”而“自生”的基础上,对现象界中物、物间之相待、相生的事实性关系予以诠释和说明。那么,何谓“独化”而“相因”呢?
由“自生”而“独化”。“物性有极”,而“终始者,物之极”[2]635,所以“独化”指物“性”之由“始”而“终”地实现出来,这一过程是自然的,是物“性”之本体存在落实和完成在现象领域中的过程,所以“独化”是一个贯穿于本体界和现象界的综合性概念。综合起来看,“独化”之含义,就“化”之内容看,是指物之“独”性由“始”而“终”地实现出来,而就“化”之机制看,是指这一实现过程中的自生、自化,是一个自发、自动即自然实现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郭象说:“夫生之难也,犹独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于生之不得而为之哉!”[2]251即强调物“性”之实现如同其“自生”一样,应该是在其自然状态中达到“自得”,即自动完成。换句话说,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物之“独性”的实现是自然自发的,因此其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实现的自动机制。由于物之“独性”是一种逻辑性的“理”的存在,它本身无法自动自发,因此这种所谓物“性”实现的自动机制,其内在动因其实在于构成物“形”之“气”的自然聚散。气之积聚与消散是自动的,而其“聚”为物“形”之生成,其“散”则是物“形”之消蜕。在物“形”之由生成而消蜕的过程,就是物之由生而死、由始而终的过程。如前所述,“终始者,物之极”,而“物性有极”,所以物“形”之由生而死的过程,同时也是物“性”之由始而终的过程。至于在一个体物之“气”化流衍的过程中,何以是此物之“独性”,而非他物之“独性”得以在由始而终的过程中实现出来,这只能说是一个命定的过程。郭象说:“若身是汝有者,则美恶死生,当制之由汝。今气聚而生,汝不能禁;气散而死,汝不能止。明其委结而自成耳,非汝有也。”[2]739可见气化的流程及其“美恶死生”,均是命定的,这一自然进程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
进一步来说,依托于个体物之“独化”,在物与他物的关系上,郭象强调了它们之间“独化而相因”的特殊机制。这种特殊机制,在《庄子注》中,被描述为物与物之间的“自为而相济”。郭象说:
夫体天地,冥变化者,虽手足异任,五藏殊官,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运其股肱以营五藏,则相营愈笃而外内愈困矣。故以天下为一体者,无爱为于其间也。[2]265
显然,这是对一物与相关他物之关系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自然机制的揭示。这种自然机制,宽泛而言,可以说是对传统道家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道的深化和具体化。盖依照郭象所言,“未尝相与”“未尝相为”者,无为也;“百节同和”“表里俱济”者,无不为也;故,“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者,即道家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在这一过程中,何以需要“体天地,冥变化”,“无爱为于其间”呢?笔者以为,其实这是强调物、物关系中“无为而无不为”之自然机制实现的无心与无为,即不受人为的干扰而能自然自得地实现出来。显然,在《庄子注》中,“独化”而“相因”的自然机制其存在和作用是具有普遍性的。
再进一步来看,若将这种“自为而相济”的自然机制应用于罔两、影、形之间的关系上,则可对它们之间所存在的“独化而相因”“相因而玄合”的机理有更深入的理解。在《齐物论注》中,郭象注曰:
……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今罔两之因景也,犹云俱生而非待也,则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也。故罔两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无之所化也,则化与不化,然与不然,从人之与由己,莫不自尔,吾安识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则本末内外,畅然俱得,泯然无迹……[2]112
依照郭象所言,天下万物,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的关系正如手与足、唇与齿的关系一样,存在着各自为而彼此相济的独特机制。因此,罔两与影,以及影与形之间,“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也是“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宏矣”的“自为而相济”之自然机制。如是而论,则“自为”者,罔两、影、形等各自之“独见”“独化”也;“相济”者,罔两与影、影与形等彼此关系之“相因”与“玄合”也。“独化而相因”,在这里其实并不玄虚,其之所言者不过是事物间存在的“自为而相济”的自然机制,只不过是特别强调了“相济”之效果的实现途径在于物、物的各自“独化”(“自为”),在于由彼我双方各自之“独化”所带来的“相因”和“玄合”罢了。若问何以由“相因”而有“玄合”的结果?则以罔两与影之母子关系可见一斑:“罔两”之“独化”的结果是“景生罔两”,而“景”之“独化”的结果就是“罔两生于景”。“景生罔两”与“罔两生于景”的实现是它们各自“独化”的结果,但是在客观效果上确实具有彼此间配合和协调的关系,并因此在二者的相互因顺、彼此互济中实现了罔两与影之母子关系。
这种由“独化”而“相因”,再由“相因”而“玄合”的关系是可以沿着一物与他物关系的无限链条而不断外推,并因此构成该物与世界关系的整体性境界的。在《庄子注》中,郭象说“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说“独化于玄冥之境”,其中的“玄冥之境”,作为物之“独化”而“至于”的结果,笔者以为,可理解为在这种外推中所达到和实现出来的一种该物与世界之整体性关系的“玄合”之境。究竟一物与他物之“玄合”关系如何实现出来?其关键则在于二者彼此间的各自“独化”与“相因”。同理,一物与世界之整体性关系的“玄冥之境”如何实现出来?其关键也在于该物与世界所有其他个体物之各自“独化”与“相因”。整体性的“玄冥之境”落实在物、物间的“玄合”与“相因”上,而这种“相因”与“玄合”的实现则进一步落实在所有个体物依据各自“独性”的“自生”与“独化”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郭象在个体主义本体论基础上理解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世界关系问题的独特理路,蕴含了他独特的智慧。
(四)物“性”中的“自物—他物”和“自物—世界”结构
若欲进一步追问一物与相关他物之间在现象界所存在的“独化而相因”的独特机制的本体论依据,则需要探究物“性”本体中所具有的“自物—他物”和“自物—世界”的结构。关于前者,郭象说:
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哉?自以大物必自生此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于其间哉![2]4
依此,则巨鲲作为“大物”,其“独性”中有其“自生于此冥海(大处)之理”,而冥海,作为“大处”,其“独性”中亦有其“自生此巨鲲(大物)之理”。因此,尽管在现象领域存在巨鲲生于冥海的因果关系,但是这是两者各自“独化”而“相因”,然后再彼此“玄合”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面,巨鲲生于冥海,这是巨鲲自身“独性”中的“自生于此冥海(大处)之理”自然实现的结果;另一方面,冥海生巨鲲,也是冥海自身“独性”中的“自生此巨鲲(大物)之理”自然实现的结果。这两方面各自“独化”,但是在其客观效果中却存在着一种玄妙的配合,并使得巨鲲与冥海间的因果关系作为一种事实得以完成和实现,此之谓“相因”而“玄合”。显然,这种因“独化”而“相因”、因“相因”而“玄合”的道理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在巨鲲的“独性”中自有其与冥海的关系之“理”,而在冥海的“独性”中也自有其与巨鲲的关系之“理”。在郭象思想中,这种关系及其结构可以推而言之,使之普遍化和必然化。换句话说,在现象界存在着一物与他物的客观关系,它们的本体论依据即在于该个体物的“独性”中所具有之相应的“自物—他物”之“理”,或说这种“自物—他物”之“理”是该个体物的“独性”的内涵中所具有的一种必然结构。但是,若再进一步问何以个体物的“独性”中会具有这种“自物—他物”结构?则答曰:这是“无因”而“自尔”的,是“无待”而“自生”的,是在物生之“初”时忽然如此的。这一点,在巨鲲化为大鹏之后,在巨鲲与大鹏之间,在大鹏与九万里的高空之间,在一切相与为彼我的物、物关系,如唇、齿之间,以及在罔两、影、形之间等等,它们都是存在的。
在现象领域,个体物的“独化”过程,物与他物的彼我关系是多维度的。这种多维度的物与他物的关系,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联系环节,形成了一张全方位和整体性的关系网络,而每一个体物即是此整体网络中的一个网结,而且在其自身中不仅存在着一种“自物—他物”的关系性结构,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自物—世界”的关系性结构。这种“自物—世界”的关系性结构,不仅存在于现象领域,同时也存在于本体界中的个体物之“独性”中。郭象说:
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趣。[2]219
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2]225
在郭象哲学中,“天者,万物之总名也”[2]50,因此,“天年”是指天地万物性命之情的总体实现。“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说明人之“独性”内涵中自有“五常”之“理”,也自有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之“理”。“人”之“独性”是如此,其他天地万物之“独性”亦是如此。天地万物,各自依照其“独性”而自生、自化,所谓“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2]579。但是,由于它们各自“独性”中所存在的这种“自物—他物”和“自物—世界”的关系性结构,使得在其“独化”中却有着彼此之间以及与世界整体之间的“相因”之功,此“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2]579。显然,这种物之“独性”所具有的“自物—世界”性结构,正如其“自物—他物”性结构一样,都是“无待而自生”和“无因而自尔”的,是于物生之“初”时偶然如此,也命定如此的。当然,由于各物之“独性”具有独特性,故其中的“自物—他物”和“自物—世界”之“理”也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独特性。
三、“独化而相因”之向其他领域的扩展
在郭象哲学中,“独化而相因”的命题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它不仅用于揭示自然哲学领域中物与物关系的自然机制,而且用来揭示社会名教和政治思想领域中人与他人关系,尤其是君王与臣民关系的社会机制。因此,在《庄子注》中,郭象的“相因”义明显向其他领域扩展了。
(一)社会领域中人与他人关系上的“独化而相因”
将“独化而相因”的机制推扩到社会领域,郭象主张在人与他人关系上“自为而相济”。在《大宗师》篇“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的寓言中,子桑因为贫饿而病倒,其友子舆裹饭而往食之。在常识看来,子舆是出于两人的友情和关心,才会裹饭而往食之,因此他的行为是有心、有为的,而不是无心、无为的。但是,郭象却注曰:
此二人相为于无相为也。今裹饭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尔,非相为而后往也。[2]286
所谓“相为于无相为”,“相为”是效果,而“无相为”是动机。可见,这是传统道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理”在社会关系上的体现,只不过在这里呈现为“自为”而“相济”,“独化”而“相因”的独特性结构罢了。显然,就现象领域而言,倘若子舆不裹饭而往食之,则子桑很可能会因冻饿而病逝,故在他们的关系中是存在因果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但是,郭象注解的重点则在于强调二人间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与影响之实现的无为和无心。因为出于无心而自为,“乃任之天理而自尔”,“非相为而后往也”,所以在实现方式上是彼此各自之“独化”,但在客观效果上则是在各自之“独化”中自然地实现了对对方之“独化”的因循、顺应与配合,此为“相因”,亦为“玄合”。因“独化”而有“相因之功”,则所谓“相因之功”,亦即二者关系的客观实现。可见,在社会关系领域,人与他人关系之“相因之功”的客观实现,在于相关双方各自之“独化之至”所带来的彼此间的相互因顺和顺应,以及由此而来的在二者关系上的协调与配合。
(二)名教领域中“五亲六族”的“独化而相因”在《庄子注》中,郭象将这种“独化而相因”的理论原则向名教领域进行了扩展。他说:
夫人之一体,非有亲也,而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腑脏居内,皮毛处外,外内上下,尊卑贵贱,于其体中各任其极,而未有亲爱于其间也。然至仁足矣,故五亲六族,贤愚远近,不失分于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于有亲哉![2]498
“夫至仁者,无爱而直前也”[2]479,说明“至仁”之作为理想目标的实现,不在于“有亲”之“相为”,而在于“无爱而直前也”。之所以如此,在郭象看来,原因在于“自为”自能“相济”,而“相为”反而“生患”。关于这一点,在首与足之间是如此,在腑脏和皮毛之间是如此,在“五亲六族,贤愚远近”之间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所谓“至仁”的状态,在“人之一体”中指的是人之自然性生命存在及其各种关系的普遍性实现,而在“五亲六族”中,则指的是名教领域中各种血缘关系和家族角色的普遍实现。因为“至仁极乎无亲”,所以“至仁”是在“无亲”的无心、无为状态下,通过相关社会角色在“各任其极”中各自“独化”而得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五亲六族”的名教制度下,所谓“各任其极”,就是指为父母者要尽其作为父母的角色职责,为子女者要尽其作为子女的角色职责。父母和子女各自“自为”和“独化”,在客观效果上自然就能形成一种彼此契合、协调与共振的关系,从而保证整个名教规范与要求的完全实现。在郭象看来,各种名教角色之间也存在着“独化而相因”的客观机制。这种客观机制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机制在名教领域的呈现。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和作用,名教制度就能发挥对各种相关社会角色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功能,从而有效保证“无为而无不为”之客观效果的自然实现。当然,在这一意义上的名教制度本身是自然的,因此它作为社会制度的存在也是理想性和价值性的。
(三)政治领域中君王与臣民之间的“独化而相因”
再进一步来看,郭象将“独化而相因”应用到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处理君王与臣民关系时,他提出了与天下“相因而成”的圣王人格。他说:
吾一人之所闻,不如众技多,故因众则宁也。若不因众,则众之千万,皆我敌也。夫欲为人之国者,不因众之自为而以己意为之者,此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见己为之患也。然则三王之所以利,岂为之哉?因天下之自为而任耳。己与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专制天下,则天下塞矣。己岂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天下有余伤矣。[2]393
在此注中,郭象重点强调了君王无为而治的治世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天下、众人的因循。但是,作为“独化而相因”理论的应用结果,他却以“三王”为例提出了圣王与天下臣民“相因而成”的独创性观点。如前所述,所谓“相因”,一方面是指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指一种相互因顺、彼此顺应的独特实现方式。依此,所谓“相因而成”,一方面是指圣王与天下之间的彼此依待和相互影响,盖若圣不世出,道世交丧,则社会时势会向恶性循环方向发展,而欲道世交兴,则需要圣人应世而出,因时为治,推动社会时势由动荡乱世向理想状态回归;另一方面,是指三王之治“因天下之自为”的实现途径。在郭象看来,通过“因天下之自为”,君王与天下臣民各安其职,各自“独化”,从而在君王与天下臣民间形成一种“相因”、配合与协调的关系,进而造成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和至治之政治理想的实现。显然,这种“相因而成”的为治原则,不仅存在于君王与天下臣民之间,也存在于天下臣民的各种社会、政治角色之间。郭象说:
若皆私之,则志过其分,上下相冒,而莫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夫臣妾但各当其分耳,未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体,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措于当而必自当也……[2]58
在此注中,所谓“相治”,其含义是“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就是社会角色各自尽其“所司”之责,而“更相御用”,是说他们彼此间存在一种互相配合、彼此协调、各自为而相济的关系。郭象说:“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位,君臣上下,莫非尔极,而天下无患矣。”[2]376可见此种“相因而成”的社会政治机制,既是名教化和秩序化的,又是圣王与天下臣民之间,以及天下臣民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并立,然后方能在对自己和对方之“独化”状态的因顺和顺应中俱生与相因、玄合与共成的。因为这种“相因而成”机制的存在和作用,作为有理想的君王和圣人应该充分因循和顺应这种机制进行治理。在郭象看来,圣人的无为之治既是其“独化而相因”之自然原理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呈现和落实,也是其自然原理在现实中的理论指向和价值旨归。
总之,在《庄子注》中,“独化”而“相因”是一条根本性的思想原则,不仅贯穿在郭象的自然哲学中,也贯穿在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分析郭象的“相因”义,为我们深化理解郭象《庄子注》的思想内容以及道家之“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传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入口。
注释:
①对此可以这样来理解。相对于在现象界中的苏格拉底之具体的、经验的存在,不能认为在此现象界之先和之前就有一个苏格拉底的理念式存在以超验的、实体的方式独立存在,也不能认为此苏格拉底之概念式的本体、本性是在现象界的经验发展过程中后天形成的,则只好认为它在苏格拉底成“形”之“初”时“突然而自得”的。苏格拉底的本性、“独性”在此“初”时为什么会被赋予苏格拉底之“形”中呢?郭象的回答是:此乃无因而自尔,乃是偶然而自得之,故称之为无待而自生,即无法解释,不能给出一个根因,尤其是在郭象已经否定造物者和真主宰的情况下。
②郭象对“无”“天”“道”等一切“真宰物”均予以消解,原因就在于将个体之“性”上升到本体位置。因为,若存在“真宰物”和“造物者”,则无论如何特殊,物之“独”性均是有待的,是依待于“真宰物”和“造物者”,是能在后者处得到依据和说明的。
③所谓“自生”,即指物之现象存在只是以己之“性”为依据,而与他物之“性”无关,但是并不是与他物之“形”的现象存在亦无关。在现象界,物与他物间是相生、相待的。为什么与他物之“性”无关呢?因为尽管存在现象上的彼此关系,但是物“性”之间却是无待和“自生”的,也就是彼此封闭、隔绝的。
④在“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一句中的“一”与“至一”的含义,应分别从现象界和本体界加以分析。“一”是指物之“初”时在“形”“性”上的统一性存在,而“至一”的含义,则既指现象界的物与相关他物之间的各“独化”而自“一”,也指本体界的物与相关他物间在“独性”上的各“无待”而“自生”。由于本体界不具有独立的实体性存在,因此对“至一”的理解还是应该更多地从物“性”与物“形”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
⑤也正是如此,一旦不持有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理论立场,即可立即将郭象所谓物之“独性”的“无待”“自生”的理论观点加以化解。在现实世界中,每一个体物均是具有独特性,因此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每一物之“本性”与他物(含其母体)无关,而各自“无待”“自生”的结论。例如,在认识论上,物之“独性”可以被抽象出来而对其内涵之“理”加以分析,而且在一物之“独性”中存在着多层次的“类性”之“理”。这些多层次的“类性”之“理”,沿着普遍性的方向逐次提升,可以抵至王弼之所谓“大音”和“大象”,进而再抵至“纯有”和“纯无”,也就是“无”本体的层面,然后再通过此“无”本体作为绝对整体性存在而对个体物之“独”性中的“个体差”予以奠基和解释。这是郭象之后(例如,在张湛《列子注》和韩康伯《系辞注》中)“独化”说能够与“无”本体论相结合的原因所在。
[1]王江松.郭象个体主义哲学的现代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徐长福.走向实践智慧社会[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46.
[4]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王晓毅.郭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6.
(责任编辑:张群喜)
本刊特色栏目约稿
为了彰显刊物特色,打造学术期刊品牌,更好地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本刊从2010年起重点推出“中华德文化研究”和“环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两个特色栏目。“中华德文化研究”是一个既具有地方特色又有包容性、学理性和现实性的栏目。“德文化”一方面是指融合了常德地方性文化、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区域性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厚重的底蕴和广阔的视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方略的关键时期,“德文化”资源的开掘、利用和转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价值。“环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栏目的设置,将为研究环洞庭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把洞庭湖区域建设成为发达的生态经济区、绿色经济区和低碳经济区提供理论阵地,推进该地区的综合治理和开发。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尚没有这方面的专栏,本刊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开设这两个特色栏目,以吸引和聚集国内有关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为办好特色栏目,为创“名栏”“名刊”打下基础,现特向社会各界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约稿,热忱欢迎惠赐佳作。
“中华德文化研究”投稿邮箱:wlxyxb01@163.com
“环洞庭湖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投稿邮箱:wlxyxb02@163.com
Guo Xiang's Theory of"Xiang Yin"
HUANG Shengp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The Theory of"Xiang Yin"(causality),an important part of Guo Xiang's philosophy thoughts based on individual ontology,is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mechanism of"action and inaction of Daoism".The Theory of"Xiang Yin"tends to expan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 from the natural field.Studying the Theory of "Xiang Yin"is beneficial to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Guo's metaphysics and the theoretical tradition of"action and inaction of Daoism".
Guo Xiang;Notes on Zhuangzi;"Xiang Yin";uniqueness
B235.6
A
1674-9014(2017)02-0017-09
2016-12-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研究”(A E A120001)。
黄圣平,男,湖北石首人,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传统道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