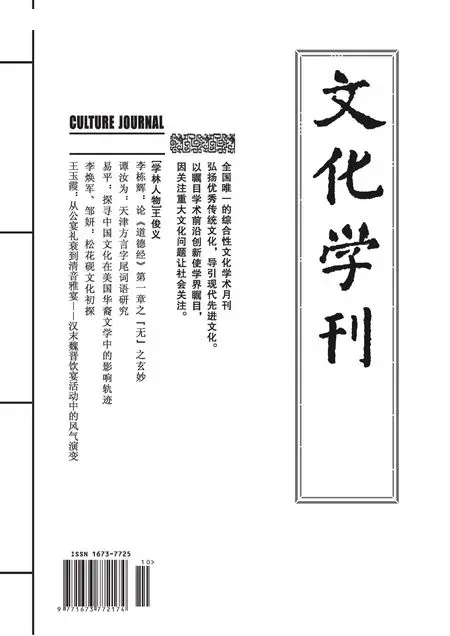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百年孤独》
——“美洲式痛苦”的文化镜像
赵 星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责任编辑:王崇】
【文学评论】
《百年孤独》
——“美洲式痛苦”的文化镜像
赵 星
(宝鸡文理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自《百年孤独》问世以来,其不仅获奖无数且持续再版,更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和最杰出文学创作之一。本书中的“孤独”,不仅是小说中虚幻出的各色人物终身不得摆脱的精神痼疾,更是遭受侵略后多元文化碰撞与冲击的整个拉美大陆从经济到文化、从历史到现代的“美洲式痛苦”。这部小说不仅勾画出一个想象世界的诞生和消亡,更是对拉美民族文化、历史、社会发展等客观现实的影射,形成了以文化形式出现的镜像,并展现了作者在其中深刻的反思。
《百年孤独》;“美洲式痛苦”;文化;镜像
《百年孤独》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其采取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映了拉美国家百余年的生存、发展、战争、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进程。[1]作者在现实中融入神话、魔幻、传说、荒诞、喜剧等各类文学艺术体裁,通过一个假想中的家族由盛转衰的故事折射出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民族变迁史。这部小说不仅向全球读者展示了如梦幻般的拉美世界,也是作者对本民族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及对未来提出的希望。
一、《百年孤独》展示的“美洲式痛苦”
《百年孤独》中有一根贯穿小说始终的主线,即“孤独”,这在小说中成为近似于宿命般的魔咒。比如,“布恩蒂亚家族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一望可知的特有的孤独神情”,即便历经了七代人,且这些代代相传的族人也在不断尝试摆脱这样的孤独,然而“他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突破孤独的怪圈,但激烈的行动总是归于挫败地沮丧”。[2]甚至可以说,这个延续了百余年的大家族已经被禁锢在孤独的循环或轮回之中,“他们又以不同方式,一个个陷入更深沉的孤独之中,对他们来说,孤独仿佛一种神秘的命运难以抗拒”。
在小说虚幻的村庄,“马贡多”最初出现的时候,这里的人并非生而孤独,相反,“一切都是刚开始,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指指着说”,向读者展现的是一派创世纪初时的模样。“人们用泥和芦苇盖房子,往在河边,河水清澈、明亮,取水方便”,描绘的是相对原始的人类早期的生活状态,这个村庄不仅人烟稀少且生活环境简单、单纯,人们的精神世界还停留在如同婴儿般的人类早期。尤其是“必须用手指指着说”,其是作者引用的《圣经》中的内容,可见此刻的孤独并没有出现。
然而,一切平静美好的生活在一个“好像一个厨房拖着一个村庄”的东西到来后被打破,这个怪物就是火车。小说中写道,“黄色火车将给马贡多带来多少捉摸不定的困惑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多少恭维、奉承、倒霉、不幸、变化、灾难、怀念啊”,火车的出现显然是现代文明的入侵,也就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占据美洲大陆及其后不断出现的新殖民者持续的经济与文化入侵,其开启了百年孤独的序幕。因此,“百年孤独”的本质其实是这个区域的民族生存与发展丧失了主权地位,如同漂泊的浮萍般任由外来入侵者摆布而产生的结果。[3]
二、《百年孤独》中“美洲式痛苦”的文化镜像
(一)历史层面的文化镜像
纵观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不难发现,在十六世纪前,美洲印地安人作为原住民创造了非常繁荣的印地安传统文化,这在众多考古发现和遗迹中可见一斑。然而,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使欧洲启动了对美洲的殖民进程,西班牙殖民拉美大陆直至美国资本主义对拉美的资金与文化入侵让曾经悠久的印地安文化不断被吞食与鲸吞。
小说中,原本闭塞的村庄因为吉卜赛人的到来而第一次见识到了磁铁、望远镜等代表现代文明的事物,这不仅在曾经原始简单的马贡多引起了一阵轰动,而且也使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被发现,继而出现了第一批移民的进入。《百年孤独》中的这一段情节正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哥伦比亚这段历史的文化镜像。西班牙人用武力打开了哥伦比亚的大门,原本是唯一文化来源的印地安文化从此开始和西班牙、阿拉伯、吉卜赛、黑人等多种文化进行交集,使宗教信仰、文化成分乃至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九世纪三十至九十年代期间,哥伦比亚虽然得到了独立,但是本土白人掌控了国家政权。为了各自阵营的利益,白人商人、地主等纷纷以自由党或保守党的名义展开权利争夺,由此开始了哥伦比亚漫长的内战历史。小说中以奥雷连诺·布恩迪亚上校三十二次的武装起义作为哥伦比亚二十七次内战的缩影,反映了这一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
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进入后,拉美大陆更是形成了既传统又现代、既闭塞又开放、既愚昧又文明的混合文化形式。小说以电影这种新鲜事物进入马贡多并引发村民不满作为这一历史文化的投射,“马贡多人对电影上活动的人物非常生气,因为他们为上一个电影死了被埋了的人流下痛苦的眼泪,而他却在下一个电影中变成阿拉伯人出现,马孔多人受不了这样对他们感情的嘲弄……马贡多人终于明白上了吉卜赛人新玩意儿的当,决定再也不看电影”,而美国资本家却在给哥伦比亚带来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后造成了其文化层面更深的边缘化与孤独感。在对资源进行无情掠夺与剥削的同时,美国还不遗余力地对外输出美式文化,同时对反抗力量进行无情地镇压。“何塞·阿卡迪奥第二苏醒时才发现自己躺在塞满尸体的火车车厢上”,小说中描写了一次香蕉园工人罢工遭到血腥屠杀的故事,“透过些微弱的亮光,便看出了死了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像报废的香蕉给扔到大海里……这是他见过的最长的列车,几乎有二百节运货车厢。”
(二)宗教层面的文化镜像
在外来文化侵入本土后,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大陆中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出现了剧烈的改变,曾经是多神崇拜的原住民、印地安文化遭到信奉单一神的基督教的入侵甚至取代,这使当地人在精神层面受到了再次的压迫和剥夺,也成为百年孤独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之一。
小说中,第一代的布恩蒂亚“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蒂亚”与其妻“乌苏拉”具有亲缘关系,是堂兄妹的近亲联姻,而布恩蒂亚家族的祖先曾经有过近亲联姻后生下长了猪尾巴的孩子的噩兆先例,但何塞与乌苏拉却不顾这样的历史教训强行结婚,这便成了整个七代家族绵延不去的孤独魔咒的开始。这样的故事描写其实是《圣经》的《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和夏娃故事的引用,是将布恩蒂亚家族的百年孤独赋予了宗教色彩的文化投影,也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原罪”意识。
马贡多最初出现时的单纯美好其实等同于《圣经》中伊甸园的神圣与洁净,然而布恩蒂亚家族在第一代的近亲联姻就与魔鬼幻化的毒蛇引诱夏娃偷尝了禁果近似。《圣经》中本是兄妹关系的亚当和夏娃成了夫妻关系,这使人类的起源背负起了“原罪”的重负,何塞与乌苏拉明知祖先有过噩兆却依然故我。其后,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罚下人世受苦,这与布恩蒂亚家族开始了百年孤独形成了对应。
三、《百年孤独》中“美洲式痛苦”的文化启示
从“马贡多”遭受到一轮又一轮外来移民文化入侵而形成“百年孤独”的描写,以及其所投射的拉美大陆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冲击形成“美洲式痛苦”的事实可以看出,丧失主权、任人摆布的被殖民地文化永远是孤独与痛苦的载体,而要战胜孤独、驱逐痛苦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这只能借助于民族内部自我的力量而无法依靠任何外来的辅助。
小说《百年孤独》结尾处“飓风刮走了马贡多”“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是作者对拉美民族文化的反思,也是希望陈旧闭塞的传统文化消逝后能迎来崭新的发展,但现实中文化的更新换代远比飓风刮走困难得多,其必须经由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甚至流血牺牲方能有所成就。小说在这一点上略显消极,其没有为彻底解决孤独提出一个更加富于斗争精神的积极策略。
四、结语
《百年孤独》虽是一部魔幻现实题材的巨制,但其并不是以魔幻、想象等感官刺激博取读者的好奇心,反而是在荒诞不经的表象下蕴含了作者对本民族乃至整个美洲大陆传统文化遭受外来冲击、本土文化被现代西方文化侵蚀甚至湮灭的沉重思考。《百年孤独》中的孤独感既是指相对落后的拉美文化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的愤懑,是整个拉美大陆本土传统文化被外来文化侵略、侵蚀而产生的刻骨的痛苦,也是这些饱受苦难的民族奋力挣扎求存、以古老的传统文化勉力支撑、对抗外来入侵并不断找寻新的发展道路的精神写照。
[1]杨晓莲.拉丁美洲的孤独——《百年孤独》的文化批判意识[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4,(10):83-87.
[2]田炳祥.南北美洲交相辉映的奇葩——论《百年孤独》与《所罗门之歌》的成功与魅力[J].国外文学季刊,2013,(4):85-91.
[3]张燕.从好莱坞电影看美国文化传播及对中国的启示[J].今传媒,2014,(3):24-26.
I77
A
1673-7725(2017)10-0073-03
2017-08-01
赵星(1981-),女,陕西西安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