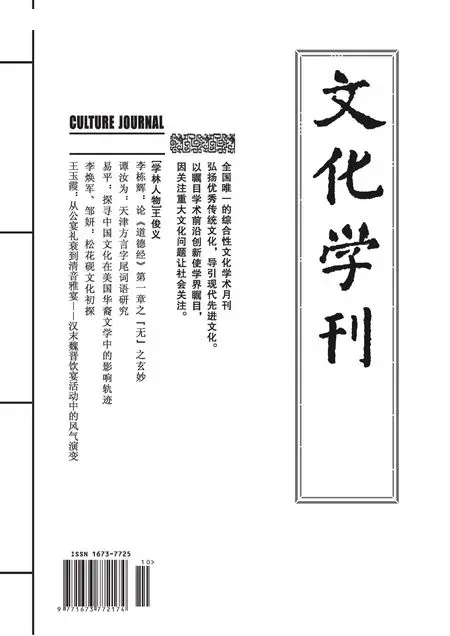库切《耻》中的空间流动与身份建构
郭丽峰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责任编辑:周丹】
【文学评论】
库切《耻》中的空间流动与身份建构
郭丽峰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库切的小说《耻》以时间为线性结构,围绕主人公卢里教授及其女儿露茜的耻辱而展开,小说的空间流动与人物的身份建构紧密相连,展现了后殖民时代、后隔离时代白人种族的身份问题和生存状态。本文试从空间角度探讨《耻》中的空间流动与置换,以及人物身份的建构,以揭示主人公卢里教授和女儿露茜的身份认同和身份重构的过程。
库切;《耻》;空间;身份
库切(J.M. Coetzee)是当代南非著名小说家,于200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耻》荣获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小说《耻》从男主人公卢里教授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父女两人身上的耻辱,以及各自对待耻辱的不同态度,其生动展现了后殖民时代、后隔离时代南非白人种族的人性挣扎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痛楚、窘境、无奈和选择,内容发人深省。国外对《耻》的研究多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国内对《耻》最早的研究文献是译者张冲的中译本序言“越界的代价”一文,该文从年龄、身份、种族等的繤越(非法越界)对小说进行了解读。[1]迄今为止,中国知网上对库切《耻》的研究论文共有37篇,其分别从女性生态视角、性别研究、互文对话关系、伦理学、后殖民主义、生态伦理等多个角度对小说做出了解读。本文试从空间角度探讨《耻》中的空间流动与置换,以及人物身份的建构,以动态揭示主人公卢里教授和女儿露茜的身份认同和身份重构的过程。
一、卢里:空间流动与身份重构
小说《耻》前6章主要讲述卢里的城市生活,即在开普敦技术大学的风流韵事乃至性丑闻;小说第7—18章讲述了为逃避性丑闻给他造成的压力和困扰,卢里来到边缘乡下萨来姆镇,在女儿农场的放逐之旅;小说第19—21章讲述了卢里返城并短暂逗留的故事;小说最后3章讲述了卢里重返乡下,等待着露茜分娩及在动物保护站暂时开启新生活的故事。小说空间的流动和置换围绕着城乡展开,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卢里的自我精神世界寻求与文化认同重构的过程也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开普敦时,卢里是大学教授,讲授华兹华斯等英国文学课程,其优越感和殖民者的态度体现在他对待女性,如索拉娅和梅兰妮的态度中。卢里是西方白人文化的代表,其认同的文化也是西方的白人文化和殖民文化。
因性丑闻流亡乡下后,卢里的身份认同逐渐发生了变化。乡下的生活完全颠覆了卢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首先表现在身份地位的颠覆,卢里由高高在上的教授变成了帮工和动物保护站的护狗员;其次表现在语言观的颠覆,在乡下因无法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卢里只能用些支离破碎的土语;最后,卢里对动物及女人等弱势群里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直以来,卢里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势来审视女人,且对动物漠不关心,认为动物的灵魂不完善,因此也不配享有更多的权利。当女儿遭强暴后,女儿逼问他是不是因为仇恨会产生更强烈的兴奋时,他的信念动摇了,开始站在弱者的角度来思考,意识到了“性的强权与不公”,这“真正摧毁了他原先情欲无罪论的伦理判断”。[2]这一切都说明卢里对自己的身份做出了新的选择,并踏上了道德救赎的道路。
再次重返城市时,卢里带着忏悔的心境努力去直面过去和现状。中途绕道梅兰妮家,就曾对梅兰妮造成的伤害向梅兰妮父亲真诚谢罪忏悔;到了开普敦,面对惨遭洗劫,珍贵物品和生活用品抢劫一空的家,按白人思维本该选择报警的他选择了不作为;去偷看梅兰妮演出,被梅兰妮的男朋友嘲笑讥讽般教训“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之后,卢里更清楚意识到自己曾经认同的白人文化在这片土壤上已失去了根基。
重返乡下后,面对话语权的彻底丧失,以及白人优越感的消失殆尽,卢里彻底放弃了自己曾经认同的白人主体思想及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情爱观点,也迟迟不能写出《拜伦在意大利》这部歌剧,其开始换上了新的面孔,承认岁月、种族、时代、背景的现实,并接受现时的生存境遇,放下私怨,准备照顾因遭强暴受孕的女儿以及即将出生的混血儿外孙。从空间的置换可以动态地看出卢里的精神世界及文化身份认同重建的过程,也可以看到一个殖民帝国逐渐衰退,一个新的混血文化即将产生的过程。
二、露茜:空间置换与身份建构
作为故事展开的第二个维度的关键人物露茜,在小说中其空间流动性可以表现为“开普敦市—乡村—蜗居的‘家园’”,其身份建构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露茜出生在城市高级知识分子之家,父亲卢里是传播学教授,母亲是荷兰裔白人。露茜从小接受的是白人的传统教育,认同的也是白人的主流文化,但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白人姑娘在父母离异后,彻底放弃了城市优越的白人生活条件,返回黑人聚居的乡镇,和自己的同性恋伴侣海伦“护养狗,看菜园,看星相书……”,坚实地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农家女人,乡下女”。正如卢里的描述,“真奇怪,他和她母亲都是城里人,生下的却是一个返祖的孩子,一个年轻健壮的移民。”[3]“返祖”及同性恋生活,都表明露茜试图摆脱南非父权制下的阴影,并建立自己独立的身份和人格,也说明露茜已经逐渐失去了对城市文化的认同,逐渐失去白人优越感和白人品格的特征。
为了在乡下生存,露茜雇佣佩特鲁斯当帮佣工,甚至学习土语,与周围人和睦相处,试图融入黑人社区,但因为肤色,露茜依然成为黑人种族仇恨的对象,这注定露西在南非也是一个他者。从空间上来看,露西的房子实际上处于黑人父权、黑人社会的包围下,也隐射了她的处境。本来平静的日子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三个黑人以寻求帮助为由,伺机袭击了农场,烧伤了卢里,轮奸了露茜。受辱后的露茜坚持认为是隐私,拒绝报警,这点说明她对南非的局势有更清醒的认识。露茜拒绝父亲关于回到前宗主国荷兰的建议,而是为了在乡下生存,以身体和尊严为代价,坚持留在偏远的黑人村镇生活。为了生存,土地权转移给曾经的佣工佩特鲁斯,沦为他的名义上的第三任妻子,在有限的空间内维持生存,可以说,露茜的生活空间成了一个蜗居的“家园”。
露茜选择尴尬地生存,无奈蜗居在自我的家园中,从真正的一无所有开始,“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4],在“城市—乡村—蜗居的‘家园’”这样的空间置换中,露茜也逐渐彻底放弃了对白人殖民文化的认同,逐渐选择去接受、宽恕黑人,选择为曾经的白人殖民者祖辈去赎罪。殖民过程之耻在后殖民时代被扣在了白人男性和女性身上,而殖民时期对南非黑人的他者化如今也颠倒成了对白人的他者化,但是作为“新一代的拓荒者”,露茜坚持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权力,并坚持要生下强奸受孕的孩子(作为这片土地的孩子),做一个好母亲,这无疑是新的基点,新的起点。库切在小说中也隐约地表现出对露茜选择的一种乐观,露茜作为和土地十分接近的人,必能获得生存的尊严和权利,其生命和文化也必能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延续。
三、库切的“第三空间”
库切作为荷兰移民后裔,成长于南非,作为两种文化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人,其处于文化上的“第三空间”。[5]库切从文化“第三空间”出发,关注南非种族隔离下人民的生活,并在小说《耻》中深入探讨了南非白人种族在这样的社会中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活,并严肃思考了黑人翻身做主人后,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将自己当初所受的野蛮和暴力施于白人身上是否能解决问题。
读者可以感受到库切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社会动乱和暴力是困扰南非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取以暴制暴的种族对抗方式,而需要消除“黑”“白”二元对立,建构一个跨越种族、肤色、性别的多文化的“第三空间”。因此,库切在《耻》中既谴责了白人殖民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黑人造成的伤害与文化创伤,同时也谴责了南非黑人对白人的暴行;既批判了卢里所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意识,认为其必将衰亡,也批判了佩特鲁斯所代表的本土民族主义和黑人被奴役的文化,批判了其残暴。库切含糊地指出了第三条道路,即两种文化、两个种族交流和融合的必要性。
[1]张冲.越界的代价(译者序)[A].库切.耻[M].张冲,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1.
[2]潘延.解读《耻》的主题内涵与情节寓意[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4-68.
[3]库切.耻[M].张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61.
[4]杨淑丽.库切小说《耻》中人物身份之探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2):41-43.
[5]曹琳,程张根.库切的自由观解读[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35-38.
I478.074
A
1673-7725(2017)10-0060-03
2017-08-01
郭丽峰(1988-),女,山西长治人,助教,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