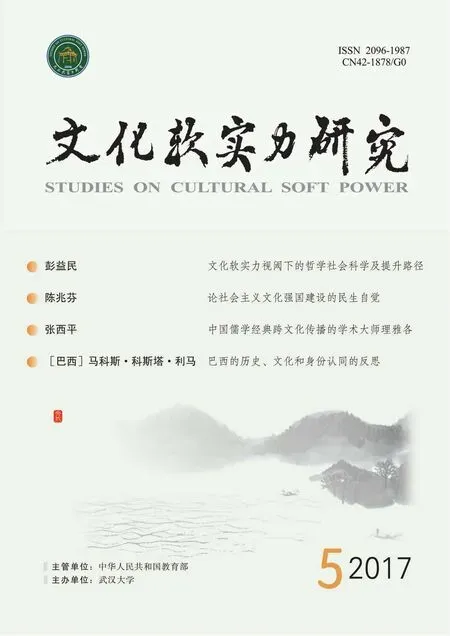中国儒学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大师理雅各
张西平
中国儒学经典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大师理雅各
张西平
理雅各,19世纪中国儒学经典翻译大师,先后翻译了五卷本《中国经典》等,其翻译的中国经典在数量上前无古人,在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上至今仍有重要地位,开创了英国汉学新时期。《中国经典》是一部西方汉学的简史。理雅各广泛阅读中国历史经典注释著作,特别是清代学者训诂著作,在每一本经典的翻译前各加入一长篇绪论,并在各卷后列出相关中文参考书、西方汉学参考书,翻译风格别具特色,较为详细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重要典籍。理雅各在汉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一则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二则在于与中国文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他者”的理雅各,在对中国经典精神的理解上,在对中国经典的具体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上都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讨论,这里既有思想理解上的问题,也有在翻译中的知识性问题。但“他者”作为“异文化”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永远是其所阅读和观察文化反思自身和确立自身的对话者,跨文化之间的“误读”是文化间交流与思想移动的正常现象。从中国经典外译的维度,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从推动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角度看,理雅各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其工作是伟大的,可圈可点,值得尊敬。
理雅各 儒学经典 翻译 跨文化
1873年,欧洲首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在巴黎召开,这是对法国从雷慕萨到儒连汉学成就的肯定,作为大学体制内的汉学发展,法国的首创之功受到欧洲东方学界的尊重是很自然的。1874年,第二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在英国召开,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回到了英国,这次会议在欧洲东方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伦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东方学、比较科学以及汉学研究的火炬,已经从欧洲大陆传递到英国。汉学研究的一段进程,也可以说从儒连时代,进入理雅各时代。理雅各最终返回英国是1873年,也是伟大的儒连在巴黎辞世的那一年。”*[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优静:《英国19世纪汉学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一、理雅各的翻译历程
理雅各1840年来到马六甲,1873年回到英国,1897年去世,无论在中国作为一名传教士和汉学家兼于一身的时候,还是返回英国开创了牛津汉学时代的时候,他都是一名极其勤奋的人,每日4点起床,开始写作,直到晚年这个习惯都未改变。理雅各一生著作等身,从1861年在香港出版《中国经典》的第一二卷后,先后在香港出版的五卷本《中国经典》分别包含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1873年他返回牛津后与麦克斯·缪勒(Fr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年)合作,在其主编的《东方圣书》中翻译出版了《儒家文本》和《道家文本》,先后翻译和修订了《书经》《诗经》《易经》《礼记》《孝经》《道德经》《庄子》《太上感应篇》等中国典籍的重要著作。在牛津期间他不仅先后翻译和写出了《法显行传》《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帝国儒学讲稿四篇》《扶桑为何及在何处?是在美国吗?》《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孟子生平及其学说》《诗经》《离骚》等著作,而且对其早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经典》进行修订,完善了自己对儒家文化的看法。理雅各一生耕耘不止,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毫无疑问,费乐仁教授是近十余年来在理雅各研究中著述最为丰富的研究者,关于理雅各翻译多样性的总结,请参阅费乐仁《力争“人所当尽得本分”:理雅各和苏格兰基督教在中国的相遇》(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ont Encounte with China ) 第二卷,第261~262页。关于《中国经典》出版的版本情况参考张西平、费乐仁《理雅各〈中国经典〉绪论》,《中国经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二、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在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
理雅各作为19世纪西方汉学的大师,作为中国经典英语翻译的实践者,在整个西方汉学史上,在中国经典外译史上都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参阅Legge,Helen Edith: 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
首先,他翻译中国经典的数量是前无古人的。在西方汉学史上,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从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基督新教传教士开始的。就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来说,对中国典籍翻译的集大成者是卫方济(Francois Noel,1651—1721年)。卫方济的翻译代表作是《中国六部古典文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显然,这些在翻译数量上是无法和理雅各相比的。而理雅各之前的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的中文经典翻译则是零星展开的。
尽管雷慕萨和儒连在对中国经典翻译的种类上大大开拓了以往传教士所不注意的翻译领域,但他们在翻译的数量上也是无法和理雅各相比的。理雅各在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上是前无古人的,作为个人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其实,即便将其放到整个17—20世纪的西方汉学史中,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有人将他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与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年)并称为西方汉学的中国古代经典的三大翻译家,在这三大翻译家中,“理雅各是把所有儒家经典翻译成非亚裔语言的第一个非亚裔人”*《中国经典》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这个评价是如实的,在这三个翻译家中,就其翻译的数量来说,理雅各仍居于首位,这点在下面的研究中我们还会涉及。*参阅黄文江:《理雅各:中西十字路口的先驱》(James Lesse—A Pioneer at the Crossrads of East and West)。
其次,从翻译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上至今仍有重要的地位。*参阅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是近三十年来国内第一本专题研究理雅各的专著。
1875年,理雅各获得了第一个儒连奖(Prix Stanislas Julien),说明他的汉学研究得到了欧洲大陆汉学界的认可。*参阅巴瑞特:《奇异的冷淡:英国汉学简史》(T. 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p.76.)。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出版后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引起了好评,这些评论是对其长年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一种认可,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汉学家欧德理(Ernst Johann Eitel,1838—1908年)对理雅各汉学翻译成就的评价,他在《中国评论》(ChinaReview)上所写的对理雅各译著的评论实际上是学术界第一次对理雅各翻译著作的学术评论,他说:“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抑或国外,没有一个外国人对这个文明古国的经典之花的熟悉,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在可靠性上,能够与理雅各博士相匹敌。”*转引自[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5页。
显然,在欧德理看来,理雅各汉学翻译和研究上的水平已经超越了法国汉学界,如儒连等人。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编排方式是十分特别的,这种编排方式不仅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力,也是《中国经典》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费乐仁认为理雅各《中国经典》在编排上有十大特点,《中国经典》绪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最后,他开创了英国汉学的新时期。*参阅潘琳《理雅各的牛津时代》博士论文抽样本。
19世纪的英国汉学处于起步阶段*早在1825年马礼逊就希望在英国设立汉学教席,但未成功。1838年伦敦大学学院(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基德(Samuel Kidd)成为第一位主任。但他退休后,这个位置一直空置到了1873年。1846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设立了汉学教席,直到1888年剑桥大学才设立了汉学教席。参阅:H. 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tish Scholars,London:Wellsweep Press,1989,p.60;魏思齐:《不列颠(英国)汉学研究的概况》,台北《汉学研究通讯》,总106期,民国97年5月,第45~52页。,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任教,用他在就职演讲中的话来说是“牛津大学每次首立一个教授位置,就标志着一门新学科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James Legge:Inaugural Lecture:On the Constituting of a Chinese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这使汉学成为“英国学术界第一次在东方学的学科中出现的一种新学科”,而理雅各从传教士到职业汉学家这个身份的转变也“从远在巴黎的儒连和其他一流的专门从事汉学研究的东方学家那里得到了肯定”。*[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同时,理雅各和欧洲汉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英国汉学获得了好的声誉。早期他与儒连的会面虽然只有两次,但使英国汉学接续了与欧陆汉学的学术联系,他对德国汉学家甲柏连孜教授(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年)代表作《汉文经纬》(ChinesischeGrammatik)的热情赞扬,对青年汉学家们的帮助都显示出一位长者的大度与宽容,这些都提高了英国汉学的地位。1893年,荷兰皇家科学院授予了理雅各荣誉研究员头衔,表明了他在欧洲汉学中的地位。*参阅潘琳博士论文《理雅各牛津时代思想研究》。生前与理雅各有过文字争论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年)在理雅各去世后写文说:“理雅各的著作对中国研究是最伟大的贡献,在今后汉学研究中,人们将永记他的贡献。”*Lindsa Ride:Biographical Note,The Chinese Classics,p.21.
三、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评略
《中国经典》本身就是一部西方汉学的简史,在每一本经典的翻译前理雅各都有一个长篇的绪论,对所翻译的中国经典作详细的学术介绍。《中国经典》第一卷的绪论长达136页,在这篇绪论中,理雅各首先介绍《中国经典》的一般情况,从作者到书名,将《四书》《五经》的含义、来源作了介绍;然后,对《论语》《大学》《中庸》、孔子和他的门徒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样的介绍从西方汉学史上来看是前所未有的,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也有一个长篇的序言,如果我们对照这两篇序言,可以清楚地发现,柏应理的序言护教成分太大,在对儒家知识的实际介绍上远远不如理雅各。*Thierry Meynard S.J. (ed.):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The First Translatio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Rom,2011.*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1,Prolegomena.在《中国经典》第二卷,理雅各写了123页的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介绍了《孟子》这本书的成书历史,孟子和他的弟子,因为《孟子》著作中辩论性很强,理雅各也介绍了在《孟子》中所批评的两个主要学派:杨朱和墨子。*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2,Prolegomena.
《中国经典》第三卷是理雅各对《书经》的翻译,他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书经》的历史,接着讨论了《书经》中记载的历史的可靠性问题。在绪论的第三部分认为《书经》尚无完全表现出中国历史部分的原因,他认为《书经》并非是一个中国古代的纪年史,它只是记载了中国早期几个君主的王朝,《书经》并未包含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君王和朝代的纪年。因此在第三部分后附了湛约翰(John Chalmers Rev,1825—1899年)所写的《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AstronomyofTheAncientChinese)。在绪论的第四部分,他翻译了《竹书纪年》,此书在西晋出土,但《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散失。从唐到清一直有人训诂考究,理雅各在书目中提到了清儒徐文靖的《竹书纪年统笺》和陈逢衡的《竹书纪年集证》两本书。在绪论的第五部分理雅各讨论了古代的中国,从中文文献进入中国古代历史,说明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少于2000年。*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3,Prolegomena.
《中国经典》第四卷是理雅各对《诗经》的翻译,这个译本,理雅各共出版过三次,即1871年版、1876年版和1895年版。*理雅各三个《诗经》译本,表现出了他对《诗经》认识的不断深化,三个译本在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上也有较明显的变化。参阅山东大学姜燕博士论文《理雅各〈诗经〉英译》(抽样本)。在绪论的第一章中,理雅各介绍了《诗经》的历史和版本,讨论了孔子和《诗经》的关系,他认为《诗经》的流行版本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为展示中国诗歌的特点,他在附录中列出了历史上40个不同的历史文献中的古代诗歌43首,并做了翻译。在第二章他主要回答如果《诗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在这一章的附录1中他直接插入了《诗经》中的“大序”和“小序”的翻译,以此说明《诗经》的形成史。为说明《诗经》所形成的历史时代,他在附录2中列出一个从商开始的历史年表简要说明。为了更好说明《诗经》诗歌的内容,他在附录3翻译了汉代韩婴的《诗经》解释内容。理雅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这位著名的儒教诗歌学者是如何整理他的主题的”。*《中国经典》第三卷,费乐仁引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在第三章,理雅各讨论了《诗经》中所反映的音律问题,介绍了中国诗歌的音韵特点和基本的内容,通过引用和翻译中国古代诗歌的例证来说明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特点,平仄的使用。在第四章,理雅各希望通过对《诗经》的研究揭示这些诗歌所发生的地区,它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条件。理雅各在做完了自己的初步分析后,在附录中专门翻译了法国汉学家毕欧(E.Biot,1803—1850年)在1843年所发表的论文《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礼仪的研究》(ResearchesintoMannersofAncientChinese,AccordingtotheSHE-King)*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4,Prolegomena,pp.142-17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经典》第五卷是理雅各对《春秋》和《左传》的翻译,在绪论中他首先说明《春秋》这本书的性质和价值,理雅各在这里开篇就开始讨论《春秋》是否孔子所做,他对孟子早期对《春秋》为孔子所做的说法表示质疑。刘家和先生将理雅各的这种怀疑理由概括为两条:其一,从孟子所肯定的理由中找不出孟子所说的“义”;其二,理雅各用清代文人袁枚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看法。*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5,Prolegomena,pp.1-16. 参阅刘家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引言》,《中国经典》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理雅各对《春秋》的价值有所怀疑,这样,在这一部分的附录中他翻译了《公羊传》和《榖梁传》的例子来做说明。在第二章,他考察了《春秋》的纪年问题,通过和《左传》的年代时间相对比,说明《春秋》在历史记载上的问题,从而否认《春秋》的历史价值。*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5,Prolegomena,pp.85-112. 参阅刘家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引言》,《中国经典》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在第三章,理雅各进一步讨论《春秋》所记载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他通过将《春秋》和《左传》比较的具体例证来说明这个观点,对《春秋》在历史记载中的隐讳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理雅各对《春秋》的批评和对《左传》的肯定构成了他在全文翻译中的基调。*请见The Chinese Classics,Vol.5,Prolegomena,理雅各《中国经典》在翻译上也有变化,从香港时期的译本到《东方圣书》的译本,在对待中国文化的一些看法以及翻译内容甚至风格上都有了变化。这里我们不做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只是勾勒出19世纪中国典籍外译的概况、主要人物、机构和刊物,对理雅各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做一个概略性的分析,这样的介绍也是侧重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来展开的。
理雅各在晚年还翻译了《法显行传》(ARecordofBuddhisticKingdoms,BeinganAccountbytheChineseMonk,Fa-HienofHisTravelinIndiaandCeylon(A.D.399-414)inSearchoftheBuddhistBooksofDiscipline),1888年译出了《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TheNestorianMonumentofHis-anFuinShen-His,China,RelatingtotheDiffusionofChristianityinChinaintheSeventhandEighthCenturies),1891年译出《东方圣书》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经》与《庄子》的全译本,并将道教的一些著作译为节译本《太上感应篇》(TheThaiShangTractateofActionsandTheirRetributions)。
从西方汉学史的角度看,理雅各在《中国经典》每一卷中所提供的中外书目也很有特点。在《中国经典》第一卷,他列出了中文参考书43本;在第二卷,他列出中文参考书2本;在第三卷,他列出中文参考书58本;在第四卷,他列出中文参考书55种;在第五卷,他列出中文参考书57种。整个《中国经典》介绍了215种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参考书。从孔颖达的《十三经注疏》、马端瑞的《文献通考》到阮元的《皇轻经解》《钦定春秋传说汇簒》等等,几乎当时能找到的主要的经学注释著作他都找到了,书目之详细令人吃惊,显示了理雅各渊博的学识。重要的是他并非简单地列出书名,而是对每一本中文参考书用英文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个中文文献的介绍在西方汉学史是前无古人的,这是到理雅各时代为止,西方汉学史上对中国古代文献介绍得最为详尽的一次,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文化重要典籍较为详细的一次。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各卷的中文参考书后还列出了相关的西方汉学的参考书目,从这几个书目中实际上我们可以大略地梳理出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研究的历史,这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的。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中列出了20本西方汉学的研究著作。从这20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理雅各以前西方对《四书》《大学》和《中庸》的翻译史与研究史,从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到雷慕莎的译本,马士曼到高大卫(David Collie),当时主要的译本理雅各全部提到了,这个书目中3个为拉丁文,6个为法文,11个为英文,也包含了多卷本的《中国丛报》中有关中国经典的翻译内容和天主教传教士所写的信,从汉学史的角度来看,“根据这个总体书目,我们能够发现理雅各在试图理解相关中文材料的同时,还想建立一项被公认达到和超过现行19世纪欧洲及北美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汉学学术成果”。*费乐仁《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引言》第8页,参阅The Chinese Classics,Vol.1,Prolegomena,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理雅各实际上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19世纪的西方汉学史的基本书目。
理雅各在第二卷中谈到《孟子》的翻译时,他认为当时欧洲只有法国汉学家儒连翻译了此书。*“Meng Tseu,vel Mencium,inter Sinense Philosophos,Ingenio,Doctrina,Nominisque Claritate,ConFUCIO PROXIMUM ,edidit,Latina interpretation ad interpretationem Tartaricam utramque recensita,instruxit,et perpetuo commen tario,e Sinicis deprompto,illustravit Stanislaus Julie.Paris,1824-1829.对《孟子》的第一个拉丁文全文翻译是来华的耶稣会士卫方济。在第三卷《尚书》的翻译中,他提到自己在翻译中参考了10本西方汉学的书籍,其中法文本5本,英文著作5本。
西方汉学关于《诗经》翻译的书,最早的一本是1830年在德国图宾根出版,由Julius Mohl编辑。此外有拉丁文2本,英文7本,法文1本。《中国经典》第五卷是理雅各对《春秋》的翻译,他对自己所参考的西方汉学书籍做了说明,他说:“Bretshneider在1870年12月,在《中国丛报》第173页将《春秋》翻译成欧洲语言,我在1871年在丛报的第51、52页很快回答了他。他说在40年前,在北京的东正教神父Daniel 将《春秋》翻译成了俄语,但据我所知,这个译本从未出版。不过手稿是在的。另外,《春秋》的部分译文被译成了俄语,被其他的俄罗斯汉学家发表,但我从未见到这个译本。Bretshneider说《春秋》的第一个译本是由俄罗斯汉学家巴耶*巴耶(Gottlie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年),德国历史学家,1792年到俄罗斯彼得堡科学院任古希腊罗马史院士,后兴趣转向中国研究,成为俄罗斯乃至欧洲最早的职业汉学家。参阅T.S.Bayer (1738-1894) Pioneer Sinologist,Curzon Press,1896.用拉丁文所翻译的,在CommentariaAcademicePetropolitane第7卷发表,但我从未见到过这本书。”*参阅《中国经典》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参阅柳若梅等著:《沟通中俄文化的桥梁:俄罗斯汉学史上的院士汉学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提到理雅各所说的巴耶翻译《春秋》:De Confucii Libro Ch’un cien //Com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 imp.Peropolitanae.Ad Annum 1736 SPB.1740.T.7.P. 362-426.感谢柳若梅教授给我提供了这条信息。
这样,我们看到在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时,他参阅或提到的西方早期汉学著作有44本之多。
理雅各《中国经典》对欧洲汉学历史的介绍不仅体现在详尽地引证了欧洲汉学史的诸多学术著作,而且还在自己的各卷绪论中插入了一些西方汉学家重要的学术论文,作为自己对《中国经典》的说明,例如在《中国经典》第五卷对《诗经》解释的绪论中直接刊出了传教士青年汉学家湛约翰所写的《古代中国人的天文学》,从法文翻译了法国汉学家毕欧所写的《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礼仪的研究》。
在西方汉学史上,在中国经典的外译史上,理雅各的成绩和贡献是可圈可点的,将其称为19世纪中国经典的英译第一人实不为过。但作为一名英国的汉学家,他在对中国经典精神的理解上,在对中国经典的具体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上都仍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讨论,这里既有思想理解上的问题,也有翻译中的知识性问题。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以理雅各的《尚书》翻译为例,从这两个方面做了具体的研究和说明。*刘家和先生认为理雅各在对《尚书》的翻译中受英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1795—1881年)的影响,否认儒家的古圣先贤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历史的。同样,理雅各根据当时西方的历史进步观,认为“进步成为西方思想的一个中心观念,即人类社会是由落后野蛮向先进文明进步而来的。依照这种观点,理氏认为在尧、舜的远古时代不可能出现那样庞大的国家,而只能存在一些小邦或部落,他们的领袖不可能是什么大帝国的皇帝,而只能是一些小邦或部落的君主或酋长。正因为如此,理氏自然不会赞同儒家的‘古胜于今’的历史观,毋宁相信‘古文’的《五子之歌》里的话”。另外,他认为,三代政权的得失,关键在于实力,而不相信关键在君主是否有德。刘先生认为,“他的这一见解与儒家传统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迭,从表面上看是实力的问题,政权是否得人心这样的问题似乎不起决定作用。“然而,一个政权的最终成功或失败,却归根到底是由人心向背决定的。”因此,理雅各否定儒家的这个观点是不合理的。在知识侧面上,理雅各肯定《古文尚书》是个明显的不足,另外在具体词语的翻译上也看出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翻译上有知识性错误。参阅刘家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三卷引言》,《中国经典》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理雅各在翻译《书经》到一半时,认识到《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他采取了增加中文评论摘要的办法说明这个问题。请见理雅各1895年版《中国经典》第三卷,第297~299页和第318~319页,有关中国文本揭示前面章节被当作伪造内容的原因,请见第三卷第361、380、433、561、612页。参阅《中国经典》第四卷,费乐仁引言第3页,注释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作为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理雅各通过对中国经典的翻译,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看法,这些观点与他广泛阅读中国历代的经典注释著作,特别是与他广泛阅读清代学者训诂著作分不开的。在这样的研究中,理雅各也显示了他的学术见解,一旦将他的这些见解放在中国19—20世纪的学术史中就会发现他的不少研究与观点是相当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例如,他对《春秋》真实性的评论和中国近代史学界的疑古思潮有异工同曲之感,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的,在理雅各的《春秋》翻译出版以后,“在中国学术界首先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经今文公羊学派,他们对于《春秋》《左传》的态度与理氏正好相反。可是,康氏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失败了。到了20世纪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已对知识界失去了号召力,‘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直入云霄,在史学界随即也兴起了疑古思潮。《春秋》被看成‘最不成东西’的东西,《左传》也被视为刘歆之伪作,一切儒家经典都被视为过时的历史垃圾,激烈抨击的程度不知要比理氏高出多少倍。尽管疑古学者与理氏在正面的方向指引上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同视中国文化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了,在这一点上双方则完全一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把理氏对于《春秋》的观点看作一种有意义的远见,他竟然先于当时中国学者而有见于此。当然,那也并非理氏个人的见识高于当时中国学者的问题,差别在于他和中国学者身历的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环境”。*刘家和:《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五卷引言》,The Chinese Classics,Vol.5,Prolegomena,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2页。
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大大开拓了中国学术研究的疆域,这些与中国学术界同行的汉学家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后,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要提一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年)对中国近代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的敦煌研究和历史研究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学界的冲击就可以了。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如何将他们的研究纳入对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思考之中?如何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熟悉他们的研究路数和话语?如何在与其对话中合理吸收其研究成果,推进本土中国研究的进展?如何在与对话中,坚守中国本土立场,纠正其知识与观点上的不足?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自言自语已经不再可能,随汉学家起舞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立场。从陈寅恪提出的“预流”到清华国学院的“汉学之国学”,前辈学者都有所尝试。今日的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仍显准备不足,十分可喜的是继刘家和先生之后,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葛兆光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表现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国外汉学家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并给予自己独立而有见地的回答。这本书使我们以往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耳目一新。
四、理雅各翻译的思想文化背景
理雅各在汉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与其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同法国儒连所代表的欧洲汉学界相比,中国的实际经验,尤其他在返回英国时的华北之行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中国文人的密切合作。关于理雅各与中国文人的合作,费乐仁教授(Lauren Pfister)有一系列的论文,说明了他和这些文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重认路径:对何进善著作的若干看法》(Reconfirming the Way:Perspectives from the Writings of Rev. Ho Tsun-sheen,Ching Feng 36:4 December 1993,pp.218-259);《一神论的探讨:理雅各和罗仲藩的解经学思考》(Discovering Monotheistic Metaphysics:The Exegetical Reflections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and Lo Chung-fan (d. circa 1850), in Ng On-cho,et.al.,eds.,Imagining Boundaries: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Texts and Hermeneutics,Albany:SUNY Press,1999,pp.213-254);《王韬与理雅各对新儒家忧患意识的回应》(The Response of Wang Tao and James Legge to the Modern Ruist Melancholy,History and Culture (Hong Kong) 2 (2001),pp.1-20,38)。
王韬1862年到香港之后,对理雅各翻译后三卷《中国经典》都有所帮助,尤其是在理雅各翻译《诗经》上。王韬自己曾撰有《春秋左氏传集释》、《春秋朔闰日至考》《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至表》等著作。理雅各在谈到王韬时说:“有时候我根本用不着他,因为一整个星期我都不需要咨询他。不过,可能有时候又会出现这样的需要,而此时他对我又有巨大帮助,而且,当我撰写学术绪论的时候,他的作用就更大了。”*转引自[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0页。王韬对理雅各也十分欣赏,他说:“先生不独惮其难,注全力于十三经,贯串考核,讨流诉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说,物极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宋汉之学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感叹其详命该洽,奉为南针。”*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8,第218页,1959年。参阅林启彦 黄文江 主编《王韬与近代世界》费乐仁《王韬与理雅各对新儒家忧患意识的回应》;姜燕《理雅各〈诗经〉英译》(博士论文),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晴改革》,江苏人民2006;岳峰:《架设东西文化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理雅各在香港布道,王韬则因太平天国逃到香港,两人在香港的合作促成了《中国经典》翻译事业的继续。这种合作如余英时所说:“理雅各如果不到香港,他便不可能直接接触到当时中国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的译注的学术价值将不免大为减色。另一方面,王韬到香港以后,接受了西方算学和天文学的新知识,这对于他研究春秋时代的立法和日蚀有了莫大的帮助。”*余英时:《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见《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7页。
理雅各在19世纪西方汉学史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个介乎传教士汉学家和专业汉学家之间的人物,或者说是传教士汉学家转换成为专业汉学家。这样一种身份使他对中国经典带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这种理解直接反映在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之中。因此,认真梳理出理雅各思想的特点是我们全面把握他的汉学成就的一个基本点。*费乐仁教授指出:“作为一位传教士和汉学家,理雅各在做任何古代经文解释时,都会自己先研究并决定采用哪些资料的立场。理雅各对学术的态度来自苏格兰实在主义或常识哲学的研究和他在公理会教派受到的比较自由的福音派基督新教培养的经历。前者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哲学观重新解释的基础上的。理雅各坚信每一个文化都有共同的真理,这类真理能够被理性的人通过仔细观察并且思考人类的问题而发现。理雅各又从基督新教的立场,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责任来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做最后决定之前,人们应该认真思考任何有关上帝于其他人的问题。作为一位传教士学者和汉学翻译家,这些原则给理雅各建设性引导。”参阅费乐仁为《中国经典》第二卷所写的“引言”第1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理雅各在香港传教期间所从事的《中国经典》翻译的基本思想立足点是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有着一神论的信仰*参阅费乐仁著:From Derision to Respect:the Hermeneutic Passage within James Legge’s(1815-1897)Ameliorated Evaluation of Master Kong (Confucius),载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6(2002),第53~88页。,在中国的《五经》中有着和四福音书相类似的信仰。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个看法可以将他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崇敬与其每日所做的布道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如他所说:“传教士们应当祝贺他们自己,因为在儒家思想中有那么多关于上帝的内容。”*转引自[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93页。这样的一个立足点自然使他对孔子、孟子的评价不高。在他对《春秋》一书的翻译中,对孔子的看法表明他的文化立场。最初理雅各相信此书为孔子所做,后来认为此书不是孔子所做。在《中国经典》的第五卷绪论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春秋》非孔子所为。他说:“如果他们不再赞同《春秋》中所记载的这些和长期以来他们已经接受与保持的信仰,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将是比任何帝国的衰落都要巨大的灾难性结果。当孔子的著作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能再作为行为的指南时,中国人便将陷入危急的境地。如果我的《春秋》研究对他们确信这一点有帮助,并能促使他们离开孔子而另寻一位导师,那么我就实现了我终生的一个重大目标。”*The Chinese Classics,Vol.5,Prolegomena,p.53.理雅各这样的学术立场很自然会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批评,辜鸿铭在他的《中国学》《春秋大义》就直接点名批评了理雅各,尤其不赞同他的《论语》翻译。参阅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第183~185页;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1页。
熟悉西方汉学史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理雅各这样的中国古代文化观并非他的创造,明末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所采取的“适应政策”的基点就是承认中国古代有着和西方一样的上帝信仰,只是到以后中国的后儒们遗忘了这种信仰,传教士的任务就是唤醒中国人的这种信仰。所以,崇先儒而批后儒成为利玛窦的基本文化策略。在他的《天主实义》上卷第二篇中有段很有名的话:“夫至尊无二,唯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商颂》曰:‘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一乎’。《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唯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唯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这些话全部都引自《中庸》《诗》《书》《易》《礼》这些中国古代经典。*关于利玛窦的研究参阅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作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西平:《跟着利玛窦来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理雅各在华期间在译名问题上坚持用“上帝”译名就和他的这一理解有关。理雅各晚年所写的《陕西西安府的景教碑,公元7—8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TheNestoranMonumentofHis-anFuinshen-his,CjinaRelatingtotheDiffusionofChristiantyinChinaintheSeventhandEighthCenturries) 在这本书中,“理雅各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伟大的利玛窦‘自由’方法一边,这种方法试图调和对中国的一些‘总结术语’和‘祭祀习惯’的使用”。*[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理雅各在离华前的华北之行对其以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回到牛津后与比较宗教学家缪勒的共事,他在《东方圣书》中开始重新修订出版中国的古代文化经典,缪勒的比较思想为他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思想的角度和方法。缪勒在第二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的发言很经典,他说:“首先,东方研究曾经被当作同北方民族在罗马和雅典所学的课程一样来学习,那就是,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还有别的宗教、别的神话、别的法则,而且从泰利斯到黑格尔的哲学史,并非人类思想的所有历史,在所有的主题上,东方都为我们提供了平行的相似性,即在所有包含在平行的相似性之中的比较的、检测的和理解的可能性。”*[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显然,这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是连在一起的,尽管这种对异文化的宽容仍是以西方固有的文化价值为尺度来比较的,但已经承认了文化的多元性,承认了“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还有别的宗教、别的神话、别的法则,而且从泰利斯到黑格尔的哲学史,并非人类思想的所有历史”。这已经在走出基督教思想的唯一性的狭隘理解。
我们可以将理雅各前后对孔子的评价做个对比。
在1861年版中,他写道:
“但是现在我必须离开这位圣人。我希望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不正确的评论;但是经过对其人人品和观点的研究,我不会将他称为一位伟大的人。虽然他比同时代的官员和学者更优秀,但他目光不具备高瞻远瞩性。他对普遍关注的问题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他没有推动宗教进步。他也不赞同社会进步。他的影响力曾鼎盛一时,但终究会衰落。我认为,中华民族对他的推崇将会快速而全面地消退。”
1893年版中,他写道: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放弃研究这位圣人。我希望我没有对他做任何不正确的评论。关于这位圣人的个性和观点,我研究他越多,就越尊重他。他是一位很伟大的人,并且他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来说是巨大的。他的教学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位圣人属于基督学派。”*引自费乐仁《中国经典》第一卷引言,第12页,参阅The Chinese Classics,Vol.1,Prolegomena,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在1893年版中,理雅各将孔子称为“中国伟大圣贤”“中国伟大哲学家”和“圣人”*参阅1893年版理雅各《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第11、87页,参阅费乐仁:《中国经典》第一卷引言,The Chinese Classics,Vol.1,Prolegomena,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雅各晚年在思想上的变化。但同时仍应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汉学家,他的文化立场是不可能完全改变的。
如何看待理雅各这样的文化立场呢?吉瑞德将“理雅各主义”说成一种“汉学东方主义”,其实“东方主义”是不足以解释西方汉学历史的*段怀清《理雅各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汉学:评吉瑞德教授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英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理雅各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是很难用一个后现代思潮和方法来解释的。*参阅王辉:《理雅各布的中庸译本与传教士的的东方主义》,《孔子研究》2008年第5期;王辉:《理雅各布的儒教一神论》,《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张西平:《对赛义德〈东方学〉的思考》,《跨文化对话》第22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从中国学术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来看,理雅各直到晚年仍未完全透彻地理解中国思想中的远古思想和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关联以及这种转变的原因,仍坚持认为远古的思想更为纯洁。他也一直未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复杂和多元的关系,从而无法解释儒家所代表的知识阶层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参阅1893年《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部分第97~101页对孔子宗教观的解释。对孔子地位的起伏与变迁,他很难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给予合理的说明。*参阅1893年《中国经典》第一卷绪论部分第92页对孔子历史地位变化的评价。同时,他的翻译也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费乐仁认为,理雅各在翻译《孟子》时没有参考清代研究《孟子》最重要的学者焦循的《孟子正义》。
尽管“理雅各将自己整个生命用来发现、理解和评价这个古老的中国世界”*The Chinese Classics,Vol.2,Prolegomena,p.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关于苏格兰哲学学派的影响及其历史,请参阅费乐仁:《力争“人所当尽得本分”:理雅各和苏格兰基督新教与中国的相遇》第一卷,第74~82页和第227~230页。,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他者”,他在苏格兰时期所奠基的世界观,“苏格兰常识哲学学派,特别是此流派与福音教会形式的新教世界观之间的关联,业已成为理雅各的强大理智的全副武器。理雅各将其运用于评估日常生活中所发掘的多种多样的中国观点和立场,其中亦包括儒教典籍经文”。*费乐仁:《中国经典》第2卷引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理雅各永远不可能像一个中国学者那样来理解中国文化,像他同时代的中国文人那样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在理雅各对于孔子的解释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本色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我们对理雅各在中国文化的翻译和解释上所做的工作表示尊敬和敬仰,一个人用其一生来传播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令每一个中国人对其怀有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对理雅各在对儒家和孔子的解释中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表示理解。作为中国文化“他者”的理雅各,我们不能期待将其看成王夫子,看成黄宗羲。“他者”作为“异文化”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永远是其所阅读和观察文化反思自身和确立自身的对话者。跨文化之间的“误读”是文化间交流与思想移动的正常现象,对于这种“误读”既不能将其看成毫无意义的解释,像一些本土学者以一种傲慢的态度看待域外汉学那样,或者像跟随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那些学者,将这种“误读”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扭曲的铁证;同样,也不能因为这些在不同文化间的思想“转移者”,这些架起文化之间桥梁的人的辛劳,对中国文化的尊敬而忽视他们的“误读”。简单地用西方学术界创造出来的“乌托邦”和“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来对待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来解释这些文化间的“转移者”的复杂性格与特点是远远不够的。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必须有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无批判地移植西方时髦的理论,来解释西方汉学历史的复杂人物和复杂过程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中国学界一些人看不到西方汉学作为不同的知识和思想体系的学术产物,它的“异质性”,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时,简单将西方汉学的一些经典译本拿来就用,而没有考虑其“异质性”。在这些学者眼中“汉学”或者说“中国学”就是关于中国的知识,它和“国学”以及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一般而言在知识系统上,汉学家们的研究是可取的,在这点上是无中外之分的,但在知识的评价系统上,就十分复杂,要做跨文化的分析,例如理雅各。因此,在中国经典的翻译上不加批判和分析地采用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是要格外谨慎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采用的是理雅各的《四书》译本,中国学者刘重德、罗志野校注。这本书将理雅各译注中有价值的全部删去了,而对理雅各的译文并未做实质性的修改。
理雅各在西方汉学史上的评价是复杂的,他的立场始终受到来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方面的批评。*[美]吉瑞德著,段怀清等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1页。无论理雅各坚信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还是当代汉学家已经完全抛弃了关于理雅各所认同的中国古代思想宗教性的论述,中国文化独特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都困扰着西方的汉学家。用“东方主义”是说不清这种文化间移动的复杂状态的*段怀清认为,对于王韬穷其一生的努力“简单地归因于一个传教士的宗教现身精神或者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一种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的文化狂热,显然过于牵强,甚至还是一种大不敬”。(参阅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晴口岸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笔者认同这一观点。,我们必须看到理雅各作为文化之间的传播者,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最有影响的翻译者,他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变化,最终呈现出来的原有文化底色的坚持与对东方文化的重新理解都是文化间移动的必然产物,这些都必须在跨文化的角度给予理解和解释。*但这对我们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论研究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文化理论问题,这里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观点认为,对中国的文化典籍,外国人很难理解,很难翻译得准确,故主张中国典籍的外译应以中国学者为主;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典籍的外译最终是给外国人看的,外语再好好不过母语,而且从翻译的数量上也基本应由汉学家来翻译。如果以汉学家为主来进行翻译,理雅各的问题就会自然出现,如果中国典籍的外译都由中国人来翻译,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要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纳入西方近代的思想史中考察,这样的翻译研究绝不仅是一个翻译的技能问题,而是当西方面对东方思想时的理解问题。但这只是我们考察中国经典外译的一个维度,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从将中国介绍给世界,推动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角度看,理雅各的工作是伟大的,是前无古人的。他是19世纪后半叶西方汉学的真正领袖。这里用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中国评论》的主编艾德(Ernst Johann Eitel / Ernest John Eitel,1838—1908年),对他的评价来结束我对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初步的研究。
“他的目标在于打开并阐明中国人的思想领域,揭示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这种工作百年当中只可能被人们极为罕见地做一次。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是在为传教士们以及其他一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生们真正地服务。他还认为,这也是为那些西方读者和思想者们服务。从国土面积之辽阔,人口比例之众多,民族特性等来考虑,中国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获悉了儒家‘圣经’所包含的内容,也就使我们处于一种有力的地位来判断其人民。从这里,欧洲的政治家可以看到其仁民道德标准之本质。他们所阅读的历史,他们风格之楷模,他们的保守主义之基础,都可由此而得到评估。
如今,即便理雅各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殚精竭虑经年累月的付出,那些卷帙浩繁的译著,依然包含着丰富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欧洲和美国的观察者可以如此正确地判断中国人,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箴言,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流行,这里所包含、所阐明的思想观点,规范着他们的学者和人民的思想。这里所包含的原则、打破了区域性界限,将整个民族连接在一起。想想《圣经》对于基督教徒意味着什么;想想莎士比亚对于学习英国的学生意味着什么;想想《可兰经》对于穆罕默德的信徒意味着什么,这些儒家经典通往普通的中国思想。将这些书置放在那些满怀着渴望地观看《孟子》或者《书经》的人手上,就是一种最坚实的服务,一种最有用的进展。在他献身于这种工作期间,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个目标,他不会背离这一目标,并且将直接的传教工作看成是需要或者接受他的首要关注。”*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晴口岸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1页。
艾德在谈到理雅各的汉学翻译成就时说:“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是理雅各博士的翻译工作使我们有机会阅读中国原始文献。我们坚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理雅各博士一样对中国的经典文献有如此深入、广泛而可靠的了解。”“理雅各博士在年轻的时候就把研究、翻译和阐释中国经典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荣耀。在中国的30年中,理雅各投入了他所有的闲暇时间和巨大精力,目的就是完成这一伟大的目标。如果有人花费时间对比他所翻译的《中国经典》中的第一部和最近的一部,就可以发现虽然理雅各在研究和分析枯燥无味的中国哲学过程中熬白了头发,但他的翻译仍然很好地保持了年轻人所特有的新鲜和朝气,并且他对中国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和广泛,对中国思想的评论也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愈加中肯和成熟,所以说他的翻译是非常可靠的。”*转引自王国强:《〈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38~139页。
Legge:aChineseConfucianClassicsTranslationMaster
ZhangXipi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China)
Legge,a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ion master in the 19th century,successively translated five volumes ofChineseClassicsand so on. His translation is unprecedented in quantity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academe so far,creating a new era of British Sinology.ChineseClassicsis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Legge widely read historical classic book annotation works,especially exegetical works of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 His translation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adding a long introduc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every classic and listing the relevant Chinese and Western Sinology reference books at the end of every volume,and introduced remarkable culture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ese to the West. Legge obtained achievements in Sinology research from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keeping clos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literati. As a foreigner of Chinese culture,his translation,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 spirit and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s,ha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ssues needed to be discussed about both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knowledge. But as the reader and the critic of a “different culture” is always an interlocutor of his reading and observing the culture to reflect and establish itself. Intercultural “misreading” is the normal phenomenon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thought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China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and of promoting the Western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Legge’s work introduced China to the world and is remarkable and worthy of respect.
Legge;the Confucian Classics;Translation;Intercultural
刘水静,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团队“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带头人、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思想研究”(17CKS023)。
10.19468/j.cnki.2096-1987.2017.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