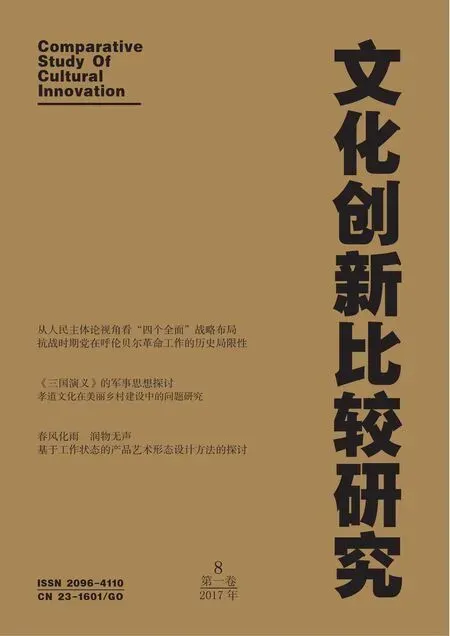《谢氏南征记》的叙事艺术
李宏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谢氏南征记》的叙事艺术
李宏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北京 100089)
《谢氏南征记》是韩国古代作家金万重创作的长篇小说,意在讽谏,因影射肃宗废后和张禧嫔的荒淫乱政,出于明哲保身和主动避祸的现实考量,小说背景设置在中国明朝,作者有意将常用的叙事场景如花园、小妾居所百子堂、书房等做了反讽性处理,并将叙事空间扩展到家园之外,对冥界、神界等非现实空间的运用和开拓不仅有效地展示了主要人物漂泊和离散的受难过程,而且反映出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困窘。小说叙事策略的成功运用体现了韩国古代叙事艺术取得的成就。
《谢氏南征记》背景设置;叙事场景;叙事空间
《谢氏南征记》朝鲜古代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小说,由李氏朝鲜中期著名文人金万重 (1637-1692)创作。金万重,字重叔,号西浦,出生于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曾祖金长生是一代名儒,父亲金益兼在1637年为抗击女真族的入侵,弃笔从戎,战死于江华岛,兄长金万基是肃宗国王(1674-1719年在位)的岳父,金万重自己有极高的才华和文学造诣,尽管如此,但因为当时朝廷内部严酷的党争,他被罢官、流放,最终客死谪所。他为后世所铭记,主要是因他的诗集《西浦集》、文学评论集《西浦漫笔》以及小说《九云梦》和《谢氏南征记》,特别是他在贬谪流放生活中创作的这两部小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视为韩国古代长篇小说诞生的标志。两部小说相比,中韩学界对《九云梦》的研究远超出《谢氏南征记》,如果说《九云梦》中杨少游的经历是作者的理想,最终杨少游由儒入佛、回归为蒲团上打坐诵经的性真的价值取向是作者在饱尝宦海沉浮、仕途险恶对现实彻底失望后自我在精神上的选择,是作者的写心之作,那么《谢氏南征记》则不同,讲的并非作者自身的故事,而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劝谏之作。这样一部小说是作者金万重有意为之,他的真实处境是充满后宫纠纷和朝廷党争的朝鲜肃宗时期,李氏朝鲜的肃宗(1661-1720)是李氏朝鲜的第19代王,1674-1720年在位。这位国王在他即位之前的1671年,与金万重的兄长金万基之女结为连理,在他即位后,金万基之女成为肃宗王的正妃仁敬王后(后于肃宗六年即1680年死于天花),仁敬王妃死后册立大臣闵维重之女为王妃,即仁显王后,但没有子嗣,后来宠爱张禧嫔,张禧嫔生育后不断进谗言诬陷仁贤王后闵氏,导致国王在肃宗十五年(1689年)废掉闵氏立张禧嫔为王妃。党争是李氏朝鲜时期的政治重弊,肃宗时期南人党与西人党的争斗十分激烈,朝臣与后宫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张禧嫔行为不端,与肃宗的叔辈东平君私通,声名狼藉,但南人党支持张禧嫔,而且因为张禧嫔的得宠而十分得势,西人派对于张禧嫔的丑行力谏肃宗,反屡遭诛戮与流放。正如韦旭昇先生所言,“金万重属于西人,愤于肃宗的昏暗,于是作《谢氏南征记》加以影射,用以讽谏。”废掉仁显王妃五年后即1694年,肃宗幡然悔悟,“又将闵氏复位,并把张氏降为禧嫔。”“据传肃宗而后废张氏,复立闵氏,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直到肃宗二十七年(1701年)仁显王后闵氏离世,肃宗发现心有不甘的张禧嫔意图重返王妃之位曾诅咒闵氏短命,于是下旨赐死张氏,此时南人党溃败,西人党重起。金万重没能等到这一天,他在1689年南人党全盛时第二次被流放后,于1692年死于流放地南海,他既没有等到仁显王后被重立为王妃,更没有看到张禧嫔被赐死的结局,但他的作品精准地预示了这一切。在此,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肃宗的悔悟是否与读到这本小说有关系,但金万重的确是与王妃废立相关联的党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他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的创作动机基本是真实可信的——《谢氏南征记》是金万重有意撰写的劝谏之作,既然如此,《谢氏南征记》叙事策略就值得深究,其高超的叙事艺术造就了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卓越的表现力,在当时和后世受到读者的喜爱,本论拟就《谢氏南征记》的叙事艺术做深入的分析。
1 背景设置的隐喻意义
这样一部现实感较强、主观上创作动机十分明显的小说,其背景的设置就显得非常重要。从现实角度看,稍有不慎,作品非但不会起到预期的劝谏效果,反而会给作者招来杀身之祸;从艺术的角度看,背景和人物同等重要,在作品的感染力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谢氏南征记》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中国明朝世宗时期,是作者匠心所运,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1 有效地避祸
作者分明是指涉本国现实,却往往将背景设置为别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少见,而且这并不影响作品的现实意义。如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背景是丹麦,这个忧郁王子在剧中身份是丹麦王子,但丝毫不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读者会知晓莎士比亚在剧中要反映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与困境,与丹麦没什么关系。背景设置在另外一个国度只是作者的一种表现手法而已。
《谢氏南征记》中,背景的设置首先出于避祸。如上文所述,金万重作为西人党,在肃宗王宠爱南人党支持的张禧嫔、废掉仁显王妃后,西人党失势的现实境遇下写作的这部小说。一方面为仁显王妃鸣不平,因一方面希望唤醒肃宗王,意识到朝廷党争与后宫宠辱关系密切。此时,金万重正在因为党派之争而罹难,被流放中,从作者的现实处境来讲,需要避祸,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别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作者用发生在明世宗时期一个贵族家庭中的故事和官员在朝廷中经历的党派争斗影射朝鲜肃宗时期的现实,对于作者心目中的指定读者——肃宗本人,影射总是比直言容易接受,对于作者,用一个中国的故事隐喻比直接议论当朝事件要安全得多。
1.2 加强艺术真实
金万重如果仅仅是出于避祸的考虑,他可以将背景设置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金万重是个官员,更是个小说家。他要让自己的故事真实可信,小说的具体背景就不能随便安排,明世宗时期是作者缜密思考后设置的背景。
《谢氏南征记》是以小妾迫害正妻为主线,同时牵扯朝廷中党派斗争,针对的就是朝鲜肃宗王废立王妃,从而造成党派争斗加剧的现实状况。小说中最重要的形象毋庸置疑是谢贞玉,可谓天下第一贤妇,突出谢贞玉这一特点需要与之相对的反面形象,就是刘延寿的小妾乔彩鸾,但作者对这个反面形象没有做扁平化、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将其塑造成了骨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形象。她容貌秀丽、善于弹唱,很有心计,性格残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采取了一些怪异的法术,如当她得知身怀女胎时,她请了有奇妙法术的李十娘用符箓和怪方将女胎变为男胎,怀胎十月后产下一个“眉清目秀、气肤如玉”的男儿,才使得一家人如获至宝,命名为“掌珠”,取掌上明珠之意,从而坚固地树立了自己在刘家的地位,也为随后因谢夫人劝慰她勿唱流俗艳曲怀恨在心,在丈夫面前花言巧语陷害夫人打下了基础。谢夫人不久也有了身孕,生一男子,名麟儿,乔彩鸾感到不安,再次求助李十娘,学到了用木人蛊惑丈夫的法术,使得丈夫精神恍惚,沉溺于乔氏一人。
一般情况下,借助法术,变女为男,迷乱丈夫心智,这是令人吃惊和难以置信的。金万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背景的选择——明世宗时期。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年号嘉靖,在位长达45年(1521-1566在位),早期励精图治,后期崇信道教,痴迷于炼丹,荒诞不经,导致宫女反抗引发 “壬寅宫变”。上行下效,小说选择在这样一位崇奉道教的皇帝任内,为乔彩鸾种种荒诞行径和李十娘的怪诞法术提供了一个大背景。
嘉靖帝因为痴迷于道教,所以重用善写青词的严嵩,这位“青词宰相”结私营党、铲除异己,擅权多年,在小说中对此也有描写,刘延寿的父亲就是与严崇 (严嵩)不和而辞官的,刘延寿家里的无行门客董清为陷害主人投靠了严崇,在严崇失宠后被处以斩行。中国名垂青史的一代清官海瑞,为了劝谏追求长生、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做了必死的准备,直言死谏,对此在小说中也有所表现,小说描写严崇倒台后,嘉靖帝重用海瑞“为都御史,翰林学士刘延寿为吏部侍郎”。小说就是这样虚实结合,将虚构的人物、事件放置在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家庭中的善恶、朝堂上的忠奸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生动曲折的情节展现出来,恰当真实的历史背景使得虚构的艺术变得真实可感。
1.3 重视接受效果——忠言也需顺耳
小说中的丈夫刘延寿影射的就是肃宗本人,“为尊者讳”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在小说中谢贞玉所遭受的所有磨难都是奸妾所害,而刘延寿是因为被乔彩鸾的木人法术迷惑了心智,是被蒙蔽者,是受害者,似乎对妻子谢贞玉对儿子麟儿的不幸经历没有任何责任,事实上作为一家之主,没有责任是不可能的,对刘延寿的赦免和他所负责任的规避,本质上是对在废立王妃事件中肃宗国王的免责,对高高在上的国王只能警醒,不宜谴责,采取这样的立场,《谢氏南征记》的“目标读者”——肃宗国王,被劝谏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在这一点上,金万重作为创作主体,其意识相当明确,《谢氏南征记》是供人欣赏、轻松品读的小说,不是上奏朝廷的书、表,希望国王回心转意,需要用可感的艺术形象,而不是堂堂的大道理、逆耳的忠言。
2 叙事场景的反讽效果
在叙事作品中,场景往往具有特定的含义。比如戏剧、小说中的花园场景,特别是在姹紫嫣红的春天,花园往往与青春萌动、温馨相爱、繁华热烈等美好的情愫相联系,一般而言在此空间中发生的故事与场景营造的整体氛围是和谐美好的。但是,在《谢氏南征记》中,作者在常见的叙事场景中展示了不同寻常的内容,寓言性地表明家族的被破坏、家庭成员的离散、家门的不幸,充斥着反常、不安、阴谋、动荡,家庭已不再是给家庭成员以安全与庇护的温暖家园,由此造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2.1 花园场景
花园场景是古代家族小说中的重要场景,贵族家庭中的花园,春日融融,品茗赏花,妻妾共享,何等风雅!这一场景本应是以春和景明的自然风光预示妻妾和睦、家庭昌盛的天伦盛景。但在《谢氏南征记》中,花园场景却上演了妻妾冲突,为家族的灾变埋下伏笔。在小说第二回,当时正值暮春,刘家花园百花争艳,花香袭人,红花绿柳,一派繁华景象,刘家正室谢夫人看到春光喜人,于是来到自家花园赏花,在如火如荼、热烈春光的映衬下,谢夫人更显得幽静贤淑,人与自然动静相宜,表现的是夫人“宜室宜家”的品行,小妾乔彩鸾生下儿子掌珠不久,也来游园,兴致高时,吟唱起来,虽声情并茂,婉转动人,但从儒家的“乐教”观念来看,却是淫邪之曲,谢夫人好言相劝,乔氏听后阳奉阴违,表面应承,内心怀恨,当晚便在丈夫面前编造谎言、颠倒黑白地诬陷了夫人,由此播下不和的种子,引发了家族灾难。
自然中原本祥和的春天花园场景,却暗藏杀机,和美的春光下邪恶的暗流正在汹涌,酝酿着一场灾变。以至于全知视角的叙事者预言:“殆极将成大祸之根底。”花园场景的反常运用给小说打下阴郁的基调,对小说的叙事起到了预叙的效果。
2.2 百子堂
儒家强调百行孝为先,无后是大不孝。 对于封建社会中贵族家庭中的夫人而言,婚后无子,是否为丈夫纳妾本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是谢贞玉作为贤妇,她要为夫家的昌盛着想,要为刘家延续子嗣后代,所以主动为丈夫选择了姿色秀丽、女工出众的女子乔彩鸾为妾。乔氏进入刘家后,一家之主刘延寿将乔氏所居之地命名为“百子堂”,直白地表明了刘家纳妾的目的。百子堂在叙事中前后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回,一笔带过,第二次出现在第三回中,侧面介绍了百子堂位于距离刘家内府较远的地方,是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第三次出现是在第八回,百子堂的荒诞感在第三次出现时凸显出来。
从情节发展来看,乔氏在百子堂的生活贯穿了家族中的妻妾争斗。在百子堂,她生了儿子掌珠,顾名思义,可以看出这孩子在刘家人心目中的位置。乔氏借助这个孩子地位得以提升,她又故意设计构陷夫人,当她的贴身侍女腊梅将掌珠杀死并嫁祸夫人后,乔氏终于如愿以偿,谢夫人蒙冤被逐出家门,经历着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之时,乔氏作为刘延寿的正妻,登堂入室,入住了刘家内府,掌执着刘家内务。但是乔氏却完全没有担负起对家族的责任,甚至没有对丈夫的忠诚。在丈夫在朝廷值夜时公然与为她出谋划策的董清在百子堂私会,“家人无不切齿,而畏死含默矣。”终于被丈夫发现。百子堂最初承载着刘家绵延子嗣、光大门庭的愿望而设,掌珠生于此死于此,掌珠死后,乔氏又在此生下了与情夫私通的孩子,原本出于儒家正统观念为传宗接代而设的百子堂,此时却成为道德沦丧、伤风败俗、使家族蒙羞之地,目的与效果南辕北辙,百子堂成为一个反讽性的场景,体现了强烈的悖谬感和荒诞感。
2.3 书房
在古代贵族家庭中,书房是男主人的专属领地,是公务在家庭中的延伸,与朝廷上的谨言慎行相比,在这里人的精神相对松弛,可以更多地流露对朝廷事务的真实想法和主张,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和安全感,是相对私密的场所,设在家庭中的书房理应给主人以安全和庇护。但是,在小说中,刘延寿发现乔彩鸾在百子堂过夜后,乔彩鸾心有不安,借丈夫上朝之际,将董清招到书房,商议对策。对书房而言,这两个人不是主人,是闯入者,他们的擅入,改变了书房场景的本源意义,充满不祥之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刘延寿议论朝廷、讥讽严崇、针砭嘉靖帝求仙之事的诗作,董清拿着这“反诗”投靠奸相,去卖主求荣了。这场在书房酝酿的阴谋,造成书房的主人一家之主刘延寿的贬谪、流放,刘家再次蒙难。书房在这里,与本来具有的功能彻底背离,成为又一个充满反讽的场景。
3 叙事空间的拓展与意义
既然家园不再温馨祥和,离家出走倒是可能带来转机,在《谢氏南征记》中展示了家庭之外的叙事空间,在叙事空间的转换与拓展中表现了小说曲折丰富的情节,主要人物在现实空间中的遭厄和非现实空间的获救,险象环生却又化险为夷,他们绝处逢生的遭遇和跌宕起伏的命运更容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唤起读者的深切同情,较之于一般的家族小说因其叙事空间的拓展,大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3.1 荒山坟茔
谢贞玉被休后,被逐出刘家,令人称奇的是她没有回娘家,而是住进了刘家祖坟旁的几间草屋中,她的弟弟得知后专程来接她,但是被她谢绝了。因“敏于女工,造衣织布,以资生业。且有妆奁中些少首饰,卖珠继粮,赖而不饥。”她如此坚持,一是相信自己的清白,仍以刘家子妇自居,丈夫不容她,她相信祖先会保佑她的;二来坚信丈夫只是一时被蒙蔽,终会悔悟。所以在荒山中艰难度日,但是她的心思,乔氏和董清也明了,所以他们要断了谢贞玉的念想,勾结董清的心腹冷振,一面由董清模仿刘延寿姑母杜夫人(因儿子在长沙任职,她随居长沙)的笔迹,请谢贞玉前往长沙,一面让冷振在路上强娶谢贞玉,坏了谢贞玉的清白,也就断了她与刘家的联系。危难之际,谢贞玉似乎只有死路一条,但作者将笔荡开,进入另一维度的叙事空间。
3.2 异度空间
文本中三次对异度空间的叙事,都是以梦的形式展示的,这表明作者具有自觉的创作意识——非现实因素要通过梦境来展示。
《谢氏南征记》中通过三次不同的完整叙事展示了亡灵所在的冥界和神灵所处的神界。第一次是在幽暗的冥界。谢贞玉在刘家坟茔旁苦熬,却意外接到姑母杜夫人的书信,信以为真,处境极为险恶,早已过世的公婆告诉谢贞玉,因为“幽明路殊,不得相救”,但提示她书信有诈,坟茔草房不可久居,指示她南行五千里方能避难,并预言“兹后六年六月望日,泊舟于白萍洲而济人,铭心不忘焉!”并且指明这里是九泉之下的非现实空间:“此地泉下,贤妇不可久留,须速归去”。这段描写文字不长,意义非凡,死者为生者指明一条生路,从结构上勾连了前后共四回书(第六回到第十回),实现了对谢贞玉和刘延寿的两次救助。在第十回,谢贞玉计算日期,到白萍洲,恰逢刘延寿被董清追杀,于是用一叶轻舟带刘延寿脱离了险境。第二次是来自娥皇女瑛等仙界神灵的解救。谢贞玉在乳母和丫鬟的陪伴下,历尽艰辛来到长沙,得知自己前来投奔的姑母杜夫人因儿子升迁成都知府,已经随迁了,可是钱财已尽,面对滔滔江水,谢贞玉再次陷入绝境,她决定投水自尽,剩下的有限的盘缠分给乳母和丫鬟,让她们去逃生。伤心气绝之计,小说展示了一个神灵的世界,“高殿崔巍,广庭肃肃,缀琉璃而盖屋,缀白玉而为砌。灿烂炫耀,夺人耳目,可知其非烟火世界也。”正殿之上是娥皇、女英,两侧座上均是历代贤妇烈女,娥皇礼遇谢贞玉并且预言南海观音将会给她帮助。醒后依梦中所见寻到黄陵庙,果然不久后有两位女尼前来将谢贞玉接到“幽邃清净,一尘不到”的佛门净地水月庵。第三次是刘延寿到达被贬地,因瘴气中毒,一病不起,生命垂危之际,有一位白衣夫人,携壶而来,表明壶中神水有疗救瘴疠的奇效,神奇之处在于第二天竟然于平地之上出了一口清泉,刘延寿饮毕果然神清气爽,瘴毒全消,刘延寿于是筑了一口井,造福于当地百姓。
梦作为潜意识活动,可能是对现实的曲折反映,但不可能对现实发挥实际的作用,可是小说中这三个梦却都介入了现实世界,异度空间中的鬼魂、神仙、菩萨等非现实力量对现实中的受难者施行了拯救。这样的想象与虚构呈现出作者主观意识和作品叙事者之间的矛盾,暴露了作者思想深处的困惑。孔子曰“勿语怪力乱神”,又曰“未知生,焉知死?”金万重作为儒门弟子是坚持这一看法,但小说中儒家君子、贤妇遭厄之际,对他们施以拯救的却是与他们所信奉的儒家思想相抵牾的力量,反映了坚持儒家道统的金万重在复杂矛盾的现实生活和险象丛生的政治斗争中,意识到他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在他受难时却不能给他现实的救助,通过笔下异度空间的叙事,形象而深刻地表达了尊儒的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痛苦和矛盾,体现了儒家思想在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力和软弱,使人们理解到在儒家正统之外,还应该有更强大的力量承担对儒家道统的补救。
《谢氏南征记》在朝鲜古典小说中享有盛誉,具有开创之功,其叙事背景的异国设置、叙事场景的反讽性处理,叙事空间的虚实转化等等叙事策略被后世小说广为借鉴,金万重在小说叙事艺术方面的匠心独运在现实中成功“干预”了一代王室王后的废立,在艺术领域,对朝鲜后世的小说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1]孙萌.朝鲜家庭类汉文小说中的儒家伦理及其礼学背景——以《谢氏南征记》、《彰善感义录》、《玉麟梦》为中心[J].明清小说研究,2016(3):205-217.
[2]周雪萍.韩国汉文小说《谢氏南征记》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6.
[3]景春婷.浅谈《谢氏南征记》中的儒家思想[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2(6):157-158.
[4]李宝龙.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37-41.
[5]韦旭升.谈朝鲜古典小说 《谢氏南征记》[J].国外文学,1984(1):4-12.
I312
A
2096-4110(2017)03(b)-0031-05
李宏伟(1971-),女,山西侯马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韩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