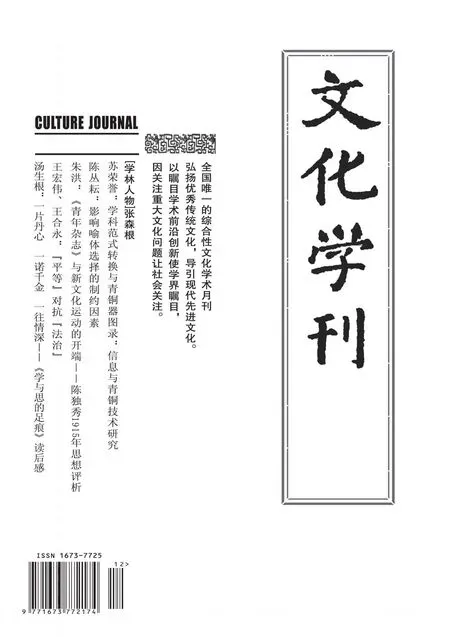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逃离》的汉译研究
——以李文俊《逃离》的中译本为例
梁淑英 徐翠霞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0)
【语言与文化】
女性主义视角下《逃离》的汉译研究
——以李文俊《逃离》的中译本为例
梁淑英 徐翠霞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0)
女性主义促进了女性对身体话语权的追求,继而推动了两性平等建构的社会阶层的实质性改良。曾获布克文学奖的《逃离》,是爱丽丝·门罗的著名短篇集,其揭示和展现了女性在追求主体自由时的困境。女性主义视角对《逃离》中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的中译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女性主义;爱丽丝·门罗;《逃离》;中译本研究
随着追求男女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的女权运动愈演愈烈,女性主义作为解读和传播女性作家作品的先导,其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压制着女性追求平等的身体、空间等话语权诉求。爱丽丝·门罗系加拿大女性作家,其作品以关注女性命运著称,以“静水流深”式的叙述手法,展现了处于边缘的失声的女性困境。《逃离》这部短篇集以暗线组织描述了八个故事,其中《逃离》是遥相呼应的第一篇,对女性命运的启示和发展有着隐忍式的先知预告。曾钰娟指出“其小说聚焦于现代女性日常生活中承受的种种精神压力,她们精神上的醒悟和为了追求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而进行着的种种努力。”[1]本文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本篇小说的中译本,探讨其译本体现的开放背后隐含着的命定论似的悲剧情怀,追问女性出走后的命运。
一、卡拉“逃离”的前奏
饶宁宁曾说:“门罗特别精于描写女性的迷惘和困惑,作品常以敏感、精神生活中充满烦恼的女性为主角,用简洁亲切的笔调描写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尤为关注她们的爱情、家庭以及内心世界。”[2]故事以卡拉和克拉拉得知贾米森先生的讣告开始。传言生前是诗人的贾米森曾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诗歌奖金,某夜,妻子卡拉与其丈夫克拉拉夜半无人私语时,谈到了一桩疑似贾米森生前非礼卡拉的事件,克拉拉怂恿卡拉借此丑闻要挟贾米森夫人,以索取精神损失费。门罗以全能全知的视角,描写了卡拉和克拉拉兴奋地讨论讹诈计划,回顾丑闻细节的过程。
原文:This was asked and told in whispers, even if there was nobody to hear, even when they were in the neverland in their bed. A bedtime story...and this with convincing reluctance, shyness, giggles, dirty, dirty...She was too... Grateful every time it still worked.[3]
译文:这样的一问一答都是用耳语悄声说的,即使没有人在偷听,即使是他们在床上如痴似醉的那一刻。这是卧室里的闺中腻语……同时配合以很起作用的延宕、羞怯和咯咯痴笑,下流,真下流……她自己也会感到兴奋……还真是天从人愿,每回都会起作用。[4]
首句为被动语态,话题主语“this”指代的是上文的对话,转化成译文的定语,即译文的主语重新确定为“一问一答”而不是“问答的这些”。“neverland”意指梦幻岛,译文通过转换法把英语中的名词转换成动词“如痴似醉”,带引读者进入克拉拉和卡拉虚构的病态兴奋中。“A bedtime story”常指父母在夜晚给孩子讲故事助其入睡,此处意指卡拉夫妇的睡前私语,实为门罗刻画夫妻之间沟通精神危机的伏笔。译文调整为“闺中腻语”,与前文的“如痴似醉”前后呼应,结合其夫妻谈话内容,可见门罗在竭力描写他们几近病态的情感牵掣。“had to be added to”转译为“添油加醋”,足见克拉拉对卡拉的丑闻重建占上位主导作用,他以强硬的姿态胁迫卡拉自我改写子虚乌有的被侮辱的叙事,以此获得自己尊严受损中呈现的扭曲心理。
“convincing reluctance”是卡拉的不情不愿,被译为“延宕”,仿佛被蒙上了反讽的高贵迟疑的色彩。后文又将“She was too”补充译为她自己也会感到兴奋,笔锋延绵直指卡拉女性主体身份的坍塌,只剩下克拉拉男权操纵意识傀儡的空壳。“Grateful”被增译为天从人愿,深刻地描写出了卡拉对克拉拉的惟命是从,下位对上位服从的膨胀与遽缩形成强烈对比。在克拉拉看来,妻子卡拉被贾米森非礼是对其夫男子尊严的挑战和伤害,但门罗故意描述卡拉拉是在贾米森死后才严肃讨论该事并准备实施勒索,使克拉拉口是心非的软弱心理一览无遗,可预见克拉拉对卡拉的情感操纵和威胁,无形中逼迫卡拉放弃其独立的女性身份,最后的“逃离”只能是以“归来”的失败告终。和谐的两性关系本是崇高、健康、愉悦的,但门罗笔下的卡拉和克拉拉以病态的话题和自我情感伤害为筹码,获得夫妻间的情感升温和固定扭结,凸显出卡拉的女性主体意识渐渐被消解。
二、卡拉“逃离”的变奏
卡拉在西尔维娅的帮助下,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逃离现实生活的大巴。一路上,卡拉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反而是阴霾笼罩,甚至委屈啼哭。满是陌生人的大巴如同一座孤岛,密闭空间的窒息感逼迫卡拉重新思考此次逃离的意义。此时的卡拉如在舞台剧中独白,叩问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和期望。原本意图改变无聊、无望的婚姻现实的逃离,却很快被自身的疑虑、抵抗所消解,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揭示了卡拉所谓的逃离,只是陷入了更深的无可自拔的、没有自我的境地里。
原文:The strange and terrible thing coming clear to her about the world of the future, as she now pictured it...She would only walk around, and open her mouth and speak, and do this and do that...she was riding on this bus in the hope of recovering herself…when she just went on, what would she put in his place...[5]
译文:她现在逐渐看出,那个逐渐逼近的未来世界的奇特之处与可怕之处,就在于,她并不能融入其间。她只能在它周边走走,张嘴,说话,干这,干那,却不能真正进入到里面去。可是奇怪的是,她却在干这所有这样的事,乘着大巴希望能寻回自己……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6]
首句无灵主语“thing”似带攻击性地袭向卡拉,是与“as she now…”并列的两个主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正是卡拉此刻思考的逃离意义,塑造了其怀疑自身和眼前现实存在的形象。译文将她转换成为主语,把所思所想囊括在人之内,增强了霸道的意味。第二句仍是其所想内容,却似以灵魂出窍的特立独行的方式,成为卡拉旁观的研究对象。在看与被看间,两次出现的“strange”都提示了逃离在此尴尬不适的定义。译者将一连串的动作处理成双声词的排比:走走、张嘴、说话、干这、干那,刻画了卡拉在逃离路上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至此,卡拉发现了作为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发声是暗哑无力、形同虚设的,因为其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
此悖论似的身不由己的逃离,旨在“recovering herself”,“recover”有恢复之意。纵观全文,卡拉最先选择与克拉拉一起,是为了逃离父母;今日选择逃离克拉拉,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能休养生息,而是希望能回答最初选择与克拉拉共度一生的意义所在,所以译者将其译为寻回自己。译者将“when she just went on”增译为自顾自,更好地体现了卡拉某个瞬间对其女性身份独立的无限向往。无所畏惧地追求自由与情感羁绊的沉重形成虚实对比,引出卡拉存在的意义命题,即“what would she put in his place?”原文体现了卡拉的无奈和软弱,与克拉拉的大男子主义形成对比反差,译文深谙意义相符的要义,增译了取代,表现了卡拉看似有自主选择权,实际却只能沦为依赖克拉拉的精神奴隶,其女性主体身份轰然瓦解。
三、卡拉“逃离”的结束
西尔维娅系贾米森太太,即克拉拉怂恿卡拉去敲诈勒索的对象。西尔维娅在丈夫死后,希望之前来家里帮过忙的卡拉继续帮忙收拾屋子。回想起自己教植物学时与女学生的交往,眼前卡拉给她的额心一吻,非常打动她。她的年龄与卡拉相仿,且在与卡拉的交谈中得知卡拉过得并不快乐。实际上,卡拉畏于丈夫克拉拉欲讹诈西尔维娅的压力,面对西尔维娅时情绪失控,把与克拉拉之间的不愉快全部讲了出来,如克拉拉对她苛刻、言语粗暴等。西尔维娅问及克拉拉是否对其进行了家暴时,卡拉没有明确地替克拉拉辩驳,游移不定、编造事实的手法与对克拉拉谎称自己被贾米森非礼的行为趋于一致,揭示出卡拉不管是在男女权力关系中还是女女关系中都处于下位,自动让位于他者的精神控制。西尔维娅怂恿其出走离开克拉拉,卡拉如同木偶般—连家都没回,带着西尔维娅提供的衣服和现金,坐上大巴,前往西尔维娅朋友家呆着。
原文:“Like an apparition,” he said, recovering. And pleased he had thought of this description…“The goat from outer space. That’s what you are. You are a goddamn goat from outer space,” He said, patting Flora. But when Sylvia put out her free hand to do the same - her other hand still held the bag of clothes that Carla had worn - Flora immediately lowered her head as if prepare some serious butting.[7]
译文:“简直就像个幽灵呀。”他说,一点点缓过劲儿来了,很为能想出这个生僻的词儿而感到得意。……“从外层空间来的山羊。这就是你了。你这狗日的来自外层空间的山羊。”他边说边拍着弗洛拉。可是在西尔维娅伸出她空着的那只手——她另外那只手里还提着装卡拉穿过的衣服的口袋——想跟着也那样做的时候,弗洛拉立刻低下头来作出要顶她的样子。[8]
弗洛拉是卡拉走丢了的山羊,出现在前文“闺房腻语”后,系卡拉的烦恼之一。弗洛拉的出走系卡拉的物化隐喻。“apparition”有幻象之意,译为幽灵,衬托出深夜克拉拉前往西尔维娅住处质问其怂恿卡拉出走的恐怖气氛。译者将句中做现在分词表伴随状态的“recovering”增译为一点点缓过劲儿来了,凸显了克拉拉的情绪从质问西尔维娅的“炽热”,到因弗洛拉忽然冒出来而惊吓“速冻”的急剧变化。“description”指“apparition”,随着场景的变化,克拉拉的用词也发生了变化,心境也随之改变。“pleased…”部分描绘了克拉拉的大男人主义从权力的上位(质问西尔维娅)到权力的下位(受夜幕山羊怪相惊吓),到选词风格的骤变(对山羊怪相的重新命名体现了对他者异化的强势压制)又再次回到权力上位的嬗变过程。
“…her other hand still held the bag of…”中的“bag”是袋子,不应译为口袋,此带有破折号的长句在译文中也应继续沿用破折号,是“free hand”(空着的手)发泄多余精力的符号象征,象征着对未来命运不知何从的卡拉与弗洛拉的接近触碰,把“另外还提着之前给卡拉装出走衣服的”手放置在破折号之中,显得此前劝说卡拉逃离克拉拉精神钳制的做法全属徒劳。弗洛拉不喜西尔维娅的碰触,而接受克拉拉的“命名”和抚摸,象征着卡拉最终选择继续臣服于克拉拉而“叛离”精神导师西尔维娅的抉择。弗洛拉先于卡拉出走,后于卡拉回来,双重的复调揭露了情感不自主的卡拉的出走逃离只会走回原点,只能滋生出更多的羞辱和可笑。
四、结语
杜诗说:“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详细描述了女孩儿卡拉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小说中,卡拉多次逃离:逃离家庭,逃离婚姻,逃离同伴,最终回归旧日生活。”[9]原著“逃离”中的卡拉,从最开始为了离开父母选择与克拉拉一起生活,到为了取悦克拉拉而不得不自我催眠地编造被贾米森先生非礼的丑闻,再到听从西尔维娅的意见坐上逃离现实生活的大巴,到最后狼狈回到克拉拉身边,其是软弱的、从属的女性形象。李文俊的译文多次采用增译法,试图再现卡拉在追求其女性独立自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叙事技巧和艺术特色都与原文一致,反思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应以丧失自我独立为牺牲。译文多次将卡拉作为主语来谋篇布局,有别于原文的无灵主语,成功地塑造了卡拉独特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体验。
[1]曾钰娟.从象征主义角度解读爱丽丝·门罗的《逃离》的主题[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5.
[2]饶宁宁.逃离:身份的探寻[D].成都:四川外国语大学,2015.
[3][5][7]Alice Munro.Runaway[M].New York:Vintage Books,2005.5.11-12.14-15.
[4][6][8]李文俊.逃离[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4.34.41.
[9]杜诗.从女性成长的角度分析爱丽丝·门罗《逃离》[J].人才资源开发,2014,(20):195.
H315.9;I046
A
1673-7725(2017)12-0178-04
2017-09-25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翻译—以爱丽丝门罗Runaway译本为例”(项目编号:201710576009)的研究成果。
梁淑英(1986-),女,广东韶关人,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
王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