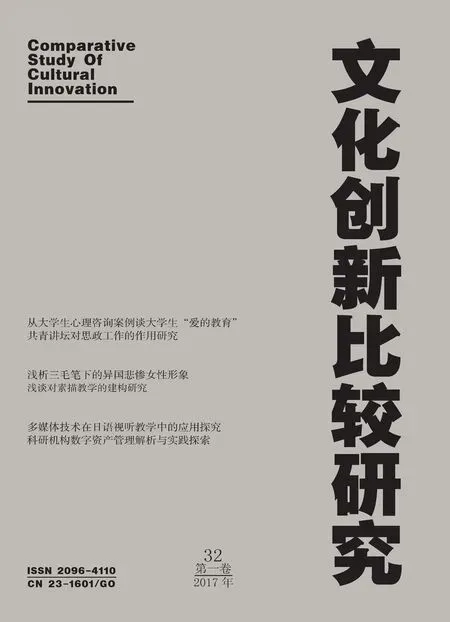浅析三毛笔下的异国悲惨女性形象
陈晓优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绍兴 312000)
三毛,原名陈懋平,后改为陈平。她的人生如“平”,平淡而不平凡,她的文字如 “平”,通俗而不庸俗。三毛的文字成就了一个不一样的三毛,不按常理出牌,以自由不羁的灵魂浪迹天涯。在偌大的撒哈拉沙漠,在平淡的家庭生活里,在独特的爱情关系里,三毛遇到了难忘的景,不同的人。
1 沙漠娃娃新娘——姑卡
无意间翻到了介绍撒哈拉的杂志,前世情缘召唤着三毛,流浪的灵魂摆脱了束缚。“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一片陌生的大地。”不顾沙漠环境的艰苦,三毛毅然而然地决定搬到那里,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片精神文化落后的土地,三毛却一次次地被打动…
娃娃新娘姑卡,才十岁,是警察罕地的大女儿,声音清脆而活泼,是一个快乐的小女孩,却被父亲安排结婚。三毛对撒哈拉威的女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年龄的现状表示吃惊和荒谬。暗示着男权主义在当时的西属撒哈拉横行霸道,形成了一种对女性的长期束缚,使女性无法自我解放。表达了三毛对麻木不仁的女性的痛恨和无奈,却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姑卡虽然对结婚之事略有担忧,但是心里却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姑卡代表着不懂得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弱势一方,也是撒哈拉威没有自由的女权的代表,思想受到了男权的压制和束缚,潜意识里也接受这种控制,无法反抗。
结婚当天,姑卡哭闹、被众人拖着走,三毛觉得要求十岁小女孩结婚简直是一个闹剧,不合常理,甚至愤怒众人强迫姑卡的行为。但是三毛无力做出任何的改变,只能心疼又紧张地安慰姑卡。这是西属撒哈拉结婚的习俗,也暗示了该地区精神文化的落后。女性没有主权,被迫用结婚哭闹的形式来取悦别人。三毛痛恨没有人改变奇怪的、不可理喻的风俗,表达了自己无能为力的无奈之情,也是对女性的麻木不仁、不懂反抗的、心甘情愿被男权主义统治的愤怒之情。
“想想看,她到底只是个十岁的小孩,残忍!”三毛甚是愤怒,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一荒谬的习俗,起到警示现代文明的作用,同时批判撒哈拉威人的无知和撒哈拉威文明的落后。当姑卡的丈夫阿布弟拿着一块染有血迹的白布,他的朋友都呼叫起来,“在他们的观念里,结婚初夜只是公然用暴力去夺取一个小女孩的贞操而已。”三毛对撒哈拉威的文化感到失望和可笑,没有一个人反对荒谬的风俗,也暗示着女性地位被无情践踏。婚礼之后,十岁的姑卡唯一的担心是——“三毛,你想我这样很快会有小孩吗?...给我药好吗?那种吃了没有小孩的药?”十岁,还是孩子的年纪,却已经结婚了,很可能也要生小孩。孩子生孩子,悲剧就在这里一代代的延续。在姑卡的观念里,女性的作用就是产生下一代。这种思想摧残着她的身心,落后的观念从孩子时代起,便伴随着女性一生,造就了女性悲剧的一生。
2 政治和宗教斗争的葬送者——沙伊达
沙伊达是一名受过高度文明教养的助产师,却惨遭保守的撒哈拉威人唾弃和侮辱。在外人眼中沙伊达不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不检点的异教徒。但三毛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有一个领导游击队的男人,有一个孩子,却不能公开。所以苦果都由这个单薄的女人承受,她是伟大的。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一个坏女人受到惩罚,是死有余辜。真相只有三毛知道,却只能淹没在骆驼的嘶叫之中。
西属撒哈拉一直是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的,摩洛哥和南边的毛里塔尼亚都对这片土地蠢蠢欲动,因此撒哈拉威人游击队兴起,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渴望独立。在动荡不安,政治主权混乱的西属撒哈拉,人们比起本国的主权,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生死。沙伊达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却死在这种混乱的斗争当中,表现了人性的残忍,也暗示了许许多多像沙伊达一样追求独立的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葬送品。
“沙伊达可是的啊!那个婊子,认识游击队…她跟每一个男人说话…她还跟不同的男人睡觉…”这是撒哈拉女孩们对她的评价,充满了鄙夷的口气。暗示撒哈拉威人对沙伊达有着很深的误解,把沙伊达与政治挂钩。三毛无法理解一个洁白高雅、丽如春花似的受过高度文明教养的可爱沙漠女子在自己的风俗下被人如此地鄙视,也暗示了三毛对落后保守的撒哈拉威文化的不认可和失望。
三毛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用“象牙白”“漆黑”“淡水色”等颜色来形容她的五官,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沙伊达长相的精致。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沙伊达的脸孔比作无懈可击的塑像,把她沉静的微笑比作初生的明月,描写了沙伊达身上的光芒,也映照了沙伊达极大的魅力,照应了全文撒哈拉威女孩对她的妒和恨。沙伊达让三毛感受到了一种沉寂的、永恒的美,三毛看到的是与世俗、黑暗政治脱离的一种圣洁,所以三毛萌生了一种“这片沙漠没有真正配得上她的人”的感觉。
与一般粗俗的撒哈拉威人不同的是,沙伊达对国家主权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独立,我留下来。瓜分,我不干。”沙伊达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相信殖民主义迟早要过去,民族自治的时代终有一天会到来。
游击队暗中宣扬独立,把导致政治混乱的矛头都指向西班牙,这让三毛既愤怒又害怕。国民们无法准确分析形势,思想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三毛不赞成独立的想法,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无知的暴民,建国一定是艰辛的。她认为游击队把独立理想化了,这是一种盲目乐观。过分的理想浪漫主义,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浪漫的情怀。他们以为独立之后,就可以自由解放,成立自己的国家,不再受到别的国家的殖民统治。表现了撒哈拉威人的天真和目光短浅,表达了三毛对西属撒哈拉命运的担忧和无奈。同时她因无法改变撒哈拉威人自作聪明的想法而感到痛苦和愤恨。而沙伊达看得清楚,表现了沙伊达有远见,料到了西属撒哈拉想独立没那么简单。
最终摩洛哥人进军了,战争爆发。撒哈拉威人又将政治混乱怪罪在游击队的身上,阿吉比——沙伊达的追求者,不顾国家政权,竟为个人恩怨,诬陷和审判沙伊达。而所谓的审判,却从冠冕堂皇的会审过渡到对一个女子的凌辱。这一切都是一场闹剧。三毛觉得不可思议,在乱世,才会出现这样没有天理的事情。沙伊达和鲁阿最终死了,成为政治斗争的埋葬品。
3 结语
在无知的撒哈拉地区,女性地位的低下导致了悲剧的出现。姑卡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被落后的男权主义文化戕害,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束缚,造成了她一生以及下一代的悲剧。沙伊达是受过高度文明教养的女子,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宗教意识,却在落后的政治中殒灭,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姑卡和沙伊达的形象也是当时广大女性的真实写照。三毛痛恨男权主义统治世界,对女性在男权主义世界惨遭践踏表示同情,也暗示着三毛的期望——只有改变女性的地位才能改变女性的悲剧。
[1]三毛.撒哈拉的故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2]罗静晶.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修辞分析[D].天津大学,2011.
[3]何海明,孙连珍.浅谈三毛散文的艺术魅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1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