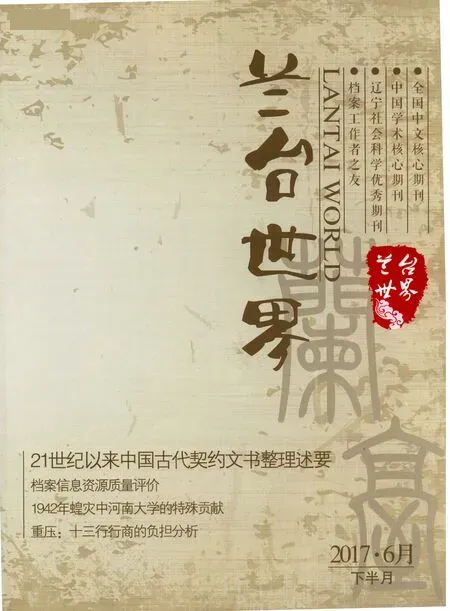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不同译文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李博
(陕西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 咸阳 712046)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不同译文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李博
(陕西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 咸阳 712046)
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目前主要有拉丁文本、英译文本和汉译文本三种文本。通过对不同译文本的比较发现,这些译文本各有其长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佉卢文文书 译文本 新疆
一、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
佉卢文全称佉卢虱吒文(kharosthī),是一种“由音节字母组成的”[1]60古代文字。佉卢文书指的是用佉卢文字书写而成的一些文献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记载。其主要的书写材料包括木质简牍、皮革、纸和帛等,其中又以简牍居多[2]7-8。另外,在一些金属钱币和石头上也发现有用佉卢文字书写的铭文。这里所说的佉卢文文书主要指的是,20世纪初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南部地区考察发掘所获且经过拉普生等人释读转写后形成的佉卢文文献资料。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这批佉卢文文书年代应在公元三世纪至公元五世纪,“佉卢文文书所记录的多是公元3世纪至5世纪的事实”[3]136。这些文书记录的内容多是关于古代于阗和鄯善王国的历史,“这些佉卢文字资料分属于古代于阗和鄯善两个王国”[1]68,其中以鄯善王国史为主,“经整理刊布的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书中,除了斯661号文书属于于阗王国外,其余的763件均属鄯善王国”[1]160,并且佉卢文书出土地点最主要地集中在古代鄯善王国的境内[2]2。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些佉卢文资料基本反映的是鄯善古王国的历史。这批佉卢文书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印欧语系的形成和发展,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四、五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4]13。
二、佉卢文文书的不同译文本
目前所知,经整理后的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主要分为拉丁文本、英译文本和汉译文本三类不同的译文本。下面对这些不同的译文本作以简要地介绍。
1.拉丁文本。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拉丁文本指的是《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文书》[5]这一著作。这一著作是经拉普生、波耶尔、塞纳等人对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的佉卢文书进行释读、转写后的成果。此书共分为三册,于1920至1929年期间由牛津大学出版。第一分册《1901年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文书释文》包含有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1900—1901)所获佉卢文书。此册收录的文书编号为第1—427号,其中第1—425号全部出自尼雅遗址,第426、427号这两件获自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遗址。第二分册《1906—1907年在尼雅、安德悦和楼兰诸遗址发现的文书释文》包含有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1906—1909)所获的佉卢文书。此册收录的文书编号为第428-708号,其中第428—659号为尼雅出土文书,第660-664号为安德悦遗址出土文书,第665号为安德悦堡出土文书,第666-707号为楼兰遗址出土文书,第708号为敦煌T·XII号遗址出土文书。由拉普生和诺布尔两人转写编订的第三分册《1913—1914年在尼雅和楼兰诸遗址发现的文书释文》中含有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1913—1916)所获佉卢文书。此册收录的文书编号为第709—764号,其中第709—751号为尼雅遗址出土文书,第752—757号为楼兰遗址出土文书,第758-763号为美国地理学探险家艾尔斯沃斯·亨廷顿在尼雅遗址所获文书,第764号则为第一分册中遗漏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所获尼雅出土文书[6]21-24。
2.英译文本。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英译文本有两个:一个是《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7]。此书由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T·巴罗(Thomas Burrow)所作。这一著作是对斯坦因前三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拉丁文本的英文翻译。T·巴罗的这一英译文本“以拉普孙等人的《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文书》第一分册、第二分册、第三分册所收录的第1-764号文书的转写与考释为依据,一共英译了其中486个号的文书(另外278个号的文书因为只写有人名或太残缺无法翻译而被省略)。”[6]25
另一个是T·巴罗的《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8]111—123一文。这其中主要包含有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古所获的第765—782号佉卢文文书中的10件文书在进行释读、拉丁转写后的英文翻译。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书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33年,斯坦因将他第四次中亚考察获取的48件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木牍文书的照片交给拉普生进行考释。拉普生在整理之后,写了一份题为《收自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佉卢文文书照片》的札记,并对整理后的18件文书也进行了编号(第765号——第782号)。但拉普生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得的佉卢文文书并未进行转写,这一转写工作最终是由其学生T·巴罗来完成。T·巴罗对这18件(第765—782号)佉卢文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整理,并对其中的10件文书进行释读转写并译成英文,最终成果就是《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的问世[9]20。
3.汉译文本。
(1)我国学者王广智翻译的《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10]。此书是对前面所介绍过的T·巴罗教授的《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一书的汉译。因此,该汉译文本中的文书数量、编号与T·巴罗英译本中的数量、编号一致。该汉译文本先是在1965年由新疆民族研究所出了铅印本,后又被收录在《尼雅考古资料》[11]当中。
(2)林梅村所著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12]。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我国学者直接释读转写佉卢文书形成的新成果。该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在佉卢文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林梅村先生的这一汉译文本“力图对所有已正式发表的我国佉卢文资料作全文转写和翻译”[4]30。正是因为如此,林梅村先生的汉译本中保留了佉卢文书原有的简牍书写形式,从中可以详细地了解到佉卢文书的形制、书写格式及其相对较为完整的内容。这是其他汉译文本所不具备的优点所在。另外,这一著作对原件转写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之处予以指出,并做了进一步地校勘[4]31。
(3)刘文锁翻译的《尼雅出土佉卢文书别集》[2]365-388。这是对T·巴罗教授对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书研究成果(英译文本)进行的汉文翻译。这一汉译文本正好弥补了T·巴罗教授在他的《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这一译文集著作中,没有收录的关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书当中的十件英译文,“不知什么原因,布娄在该译文集中并没有收录他新译的斯坦因地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十件译文”[6]25。以上这些论著当中所用的佉卢文书的编号是统一的,都是沿用拉普生、波耶尔、塞纳和诺布尔等人所著《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文书》一书中的编号,即相同的文书编号指的是同一件文书。
三、不同译文本存在的问题
1.拉丁文本的问题。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拉丁文本《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突厥斯坦发现的佉卢文文书》的问世,是打开佉卢文研究大门的第一把钥匙,为后来学者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石。这也标志着国外在佉卢文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著作的问世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林梅村先生的《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的出版,才使得这一拉丁文本不再是孤本。虽然目前笔者还不能直接阅读这些佉卢文书的拉丁转写原文,但至少可以将两者进行比较,从中看出些异同。以同一编号的文书为例,若其拉丁转写相同的话,那当然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而若拉丁转写不同的话,则说明存在着差异。差异性则牵涉到了对佉卢文书释读是否正确的问题了。而对佉卢文书释读则又直接关系到文书内容能否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问题。
2.英译本的问题。如前所言,T·巴罗的英译文本《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是建立在拉普生等人的《Kharosthi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这一著作基础上的英文翻译。而《Further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Niya》则是在其直接释读佉卢文书原件的基础上进行拉丁转写之后的英文翻译。但由于其个人主观认识方面的问题,在他的英译文中并没有保留佉卢文书原有的书写格式,因此他的译文本存在着格式方面的问题,如刘文锁先生所言,“贝罗(即指T·巴罗——笔者注)的释译存在的问题是:关于国王谕令的开头,即按照这一类文书的格式写明由‘伟大国王(大王)陛下敕谕某某官员’的部分,他认为不够重要都未予以释译。”[2]9若只阅读这些英译文的话,文书中所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就被遗漏掉了,从而影响到对文书内容的理解。
3.汉译本的比较及其存在的问题。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汉译本分别是前述的王广智译文本、林梅村译文本、刘文锁译文本。王广智先生的汉译文本译自T·巴罗的英译文本,整体而言,汉译文内容基本符合英译文原文,但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汉译文中在翻译个别字词方面存在着不恰当的问题。这里以佉卢文11号文书为例予以说明。在这件译文中,王广智先生的汉译本中将T·巴罗英译文中的“witness”译作了证据。笔者认为将“witness”翻译为“证据”不太准确。英文的“witness”有两种解释,除了有“证据”的意思之外,还有“证人、目击者”的意思[13]2672。若单从词语翻译的角度来看的话,将“witness”翻译为“证据”是可以的。但是,汉语“证据”这个词却包含双重含义:“(1)可作为证明用的事实依据(2)法律名词。指在诉讼上用以证明事实之一般资料。”[14]1692结合11号文书的内容来看,文书内容中提到的“誓约”亦应属于证据之范畴,即证据当中包含着誓约,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而在该汉译本中却将“证据”和“誓约”作为并列关系放在一起显然不合适。因此,笔者以为将“witness”译为“证人”比较好些,其与“誓约”二者是并列的关系,都属于判案之证据。
刘文锁的汉译文也基本符合英译文原文意思。他的译文本在翻译人名的时候在旁边保留了英文原文,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与其他译本进行比较时提供了便利。而对涉及的某些残缺、不清楚的地方则保持原貌,如编号769号文书中的Su[…]sriae、Sarva?riae。
由于王广智和刘文锁两位的汉译本直接翻译自T·巴罗的英译文本,所以他们的汉译文本也就沿袭了T·巴罗英译本中存在的格式不完整的问题。这一格式上的不完整导致整个文书内容上存在着的某些信息不全面的缺陷。因此,他们的汉译本与林梅村先生的汉译本相比较,显然少了很多相关方面的内容,从中所获得的信息就较为有限。林梅村先生的汉译文本包含了拉丁转写和译文两部分内容,并且保留了佉卢文书的书写格式,因此它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一个汉译文本,这也是目前国内研究者们主要利用的资料。但该版本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拉丁转写部分可以和拉普生等人的转写相互对比,但这也只是部分转写罢了,因为在这一译本中一部分转写的内容依照的是原有的拉丁转写[4]30。王氏、刘氏汉译文本与林氏汉译文本在内容上则可以相互印证,以见其异同之所在。通过比较发现,汉文本在人名、地名等的翻译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没有形成一个人名、地名对应表。林氏译文本与王氏译文本在某些内容的翻译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可以说是林氏与T·巴罗两人对佉卢文书内容理解上的不同表现。如在编号39号文书中,王氏的译文是“应由莱比耶向迦钵吉之奴隶取一匹tirsa牝马或一匹tirsa马”[10]13,而林氏的译文却是“应向迦波格耶诸奴仆索取三岁之牝骡一匹或三岁之牝马一匹”[4]51-52。这里暂将问题指出来,以引起注意。
译文的不同,它直接牵涉到佉卢文书原文释读正确与否的问题,也导致文书内容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截然不同。对于佉卢文书再次进行新的释读研究,这在当今学术界依旧是一大难题。如何攻破这一世界性的学术难题,对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后继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先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去突破语言关,能够直接释读佉卢文字,然后再对新疆出土的佉卢文书原件释读并进行新的拉丁转写、英文翻译、汉文翻译,唯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地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当今此种环境氛围之中,这条道路必将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有志于此的吾后辈学人更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魄力勇往直前。
[1]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刘文锁.沙海古卷释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4]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文书(初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5]A·M·Boyle,E·J·Rapson,E·Senart,P·S·Noble:Kharosthi Inscriptions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M]. part I,II,III,Oxford:attheC larendon Press,1920,1927,1929.
[6]王冀青.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J],敦煌学辑刊,2000(1).
[7]ThomasBurrow:A Translation of the Kharosthī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M].The RoyalAsiatic Society,London,1940.
[8]ThomasBurrow:‘Further KharosthiDocumentsfrom Niya’,Bulletin of the SchoolofO rientialStudies[J].London University,Vol.9,No.1,1937.
[9]张秀萍.布娄及其对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
[10]T·巴罗.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M].王广智译,乌鲁木齐: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所印,1965.
[11]韩翔,王炳华,张临华.尼雅考古资料[M].乌鲁木齐: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88.
[12]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文书(初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3]吴光华.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
[14]王同亿.高级汉语词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Different Translation Texts of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Unearthed in Xinjinag and Their Problems
Li Bo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ianyan 712046,China)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unearthed in Xinjiang have three translated texts at present,which are Latin,English and Chinese.Through the comparison,we found that each of these translations has its advantages aswell as some problems.
Kharosthi documents;translation text;Xinjiang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70043)。
李博,陕西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研究方向为民族史。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12.35
K877
A
2017-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