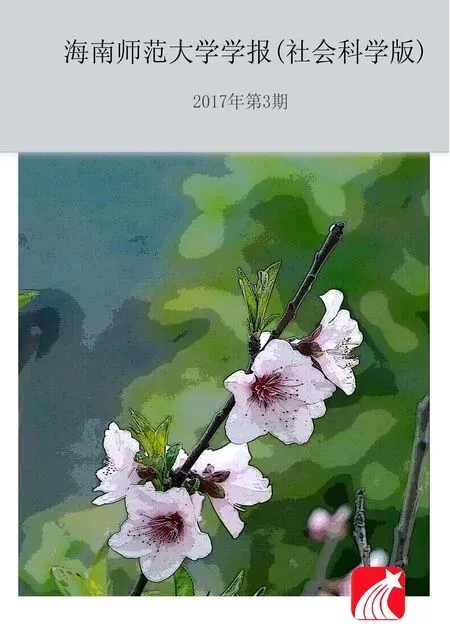《软埋》:历史语境下的存在之困
夏 靖,王达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软埋》:历史语境下的存在之困
夏 靖,王达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方方是一位对历史题材颇感兴趣的作家,无论是新写实时期描绘普通人之生活情状,还是近年来以人道主义观照人之生存困境,历史都常常作为其作品重要的意义载体。同时,存在主义的哲思也充溢在方方的多部小说中,人的生存困境一直是她乐于表现的主题。在近作《软埋》中,历史的视角与存在主义的思辨相遇、碰撞了,历史被作为存在而书写,其神圣意义被消解;另一方面,历史本身被赋予的价值判断也制约着作为存在的个体的自由。方方以个体的存在之困指涉历史的“无处不在”,二者的相互博弈增强了小说的思想张力,延伸了小说的言说空间。
方方;《软埋》;历史语境;存在;记忆;选择
2016年2月,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在《人民文学》第2期上发表。新世纪以来,方方一直执着于“在叙写人的生存之困的基础上表现‘人的生存命运’、‘人性之困’和‘人道主义’等思想内容”*王达敏:《方方新世纪小说的叙事变化》,《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这一次方方的探索更远、更深,她将个体的存在困境置于历史语境之下,让历史为个体的存在套上沉重的枷锁,又让个体的存在与选择消解着历史的神圣意义,这种博弈式的结构从两个方向共同深化了小说的内涵,很好地处理了书写历史的远与近、虚与实、主观与客观、正面与侧面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软埋》是方方继《风景》《琴断口》《水在时间之下》之后,又一部深透历史和人性的标志性作品。
《软埋》围绕两个主要人物展开叙述:丁子桃和她的儿子吴青林。丁子桃在经历了“土改”后失去了之前的记忆,老了之后记忆力进一步衰退。为了孝敬母亲,事业上有所成就的吴青林决定将母亲接入新家。无意中,他几次听到母亲让人不解的只言片语,却也没有细究。直到某一天,丁子桃彻底陷入了“痴呆”似的状态,从此不发一语。吴青林在焦急中找到了父亲吴家名留给他的日记,进而走入了双亲黑暗、疼痛的过往。之后,在陪同老同学龙忠勇去川东考察的途中,他又无意中发现了一处破败的庄园,而它竟然就是母亲口中曾经念叨过的“三知堂”。以此为线索,在与当地村干部的交流中,他怀疑母亲就是“土改”中举家自杀的陆家媳妇,同时也是这一事件中惟一的幸存者。慢慢浮出水面的真相给吴青林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不愿继续追究下去,选择了放下这段历史,重新投入当下的生活。小说的另一线索,是以“痴呆”后的丁子桃脑海中的回忆为主线。她的意识带领她穿过“十八层地狱”,以倒叙的方式逐一复原了失忆前的生活片段,回忆起陆家自杀的全过程。最后,在挣扎着说出“我不要软埋”后,她离开了人世,也带走了有关自己家族史的记忆。
“软埋”在小说中有两层含义。人死后不入棺,直接就地以土掩埋,就叫做软埋。在民间的习俗中,选择这种彻底归于尘土的丧葬方式,意味着无法获得转世的可能,是一种决绝的告别。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生者也时时刻刻都在“软埋”,埋的是对历史与过往的记忆,埋葬它们的是时间。丁子桃生前的失忆,吴青林面对家族史的退避,都可视为“软埋”的一种方式:让时间自然地带走不堪回首的记忆。“软埋”是个体对待历史与记忆的态度,因而从主题上来看,这可以说是一部有关于“选择”的小说。同时,方方将个体的选择置于历史语境之下,二者的对立、纠缠又催生了道德的命题(笔者将其视为《软埋》的隐性主题),表现了个体在历史语境下的存在之困。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看《软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一、作为存在的历史
中国当代作家处理起历史题材的作品总是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历史成为很多作家写作的素材来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显得更为贴切。在绝大部分作家的笔下,历史或是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或是以改写、戏说的方式被解构,进入当下语境成为当代叙事的话语资源,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又或是作为作家构建某种观念、图景的工具,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将历史高度抽象化、寓言化,成为某种对当代现实的能指符号,又如张炜的《你在高原》系列小说,则是将历史作为承担作家本人精神、观念的价值载体。与此不同的是,方方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与历史的距离,这或许可以视为“新写实小说”时期“零度情感”的延续。即便是在以《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为代表作的早期,除了以世俗眼光和底层平民立场描绘原生态的生存现状之外,她也总是能开掘出“现实”之外的某种更为“真实”的意蕴。方方从不将“现实”与“真实”混为一谈,也因此,她的小说从不止步于“现实”的描写,“现实”的背后蕴含着某种形而上的思考,《软埋》延续了这种倾向。即使面对“土改”这样的重大题材,方方仍然克制住了重现历史的冲动,她将历史作为存在来书写,历史的面目也因此变得模糊。
诚然,历史的难以捉摸不等于历史的虚无,就如同《软埋》中所涉及的“土改”历史,作为被记录在案的信史,没有人会否认它曾真实地发生过。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尤其是小说中吴青林这类人,他们没有亲历过这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是后天的、被动的。更不用说,个体的认知也从不能等同于真实,“被感知物的存在不能还原为感知者的存在”*〔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页。。历史对于吴青林来说,就像是“薛定谔的猫”:一只猫与一种有50%几率会发生衰变的化学物质共处于一个盒子内,盒盖没有被揭开前(即人类的观测行为),在量子理论的视角中,“活猫”与“死猫”是同时存在的。以此类比,历史的形态也可视作一种可能性的集合。历史书上的历史是一种可能性,民间的历史故事是一种可能性,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历史也是一种可能性。具体到《软埋》中,丁子桃的回忆是一种可能性,吴医生的日记是一种可能性,村长陆欢喜的讲述也是一种可能性。个体取信于哪一种可能性,取决于个体的身份、认知水平、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这就形成了一个“罗生门”式的迷局。《软埋》中对于吴青林家史的言说,也暗含着这种“罗生门”式的格局。
吴青林对家族历史的认知完全来自于他者的言说,而历史的言说者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叙述者。他是通过父亲的日记了解到这段历史的。而在文学叙事的领域内,日记是比较不可靠的一种叙述形式,例如鲁迅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另一方面,丁子桃的“回忆”也并非完全可靠,毕竟那只是她无意识状态下的思维流动。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不可靠”并不等同于世俗意义上的“不正确”、“不可信”,它仅仅说明了个体的认知与记忆并不具有惟一性,也无法穷尽存在的可能性。话虽如此,在阅读《软埋》的过程中,读者在心理预期上,恐怕还是会倾向于将吴医生和丁子桃的“叙述”视为绝对的真实,因为他们的叙述基本符合大众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
方方在关于《软埋》的采访中,也谈到过她对于“历史”的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重要的历史阶段,都被交由时间软埋了。尤其在年轻人的记忆里,无数历史的重大事件,都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金莹、方方:《方方:时间的软埋,就是生生世世》,《文学报》2016年3月3日第2版。“以不存在的方式存在”几乎可以用来解读《软埋》所呈现出的历史观,前一个“存在”是指现实意义上的“在场”,后一个“存在”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在场”是短暂的,然而它可以通过记忆的传承与分享继续“存在”。吴青林和丁子桃正是希望通过“遗忘”来消除这种现实意义上的“存在”。而哲学上意义的“存在”,个体是无法触碰的。方方将历史作为存在书写,一方面可能与她对历史的思考有关;另一方面,这种设置客观上使小说的叙述有了更多可发挥的空间:既然历史是作为存在被书写,那么作家就不必耗费过多精力去重现历史,其价值立场也不会被历史的“意义”所绑架。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与后文将要言及的内容密切相关。
二、“意义”的消解
人是感性与理性并存的动物,总是不满足于认识事物的表象,孜孜以求地探寻事物的本质与意义。然而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在福柯对理性发出质疑与挑战之后,“意义”已经很难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它只是被言说、被创造的话语。面对历史,理性同样驱使着人们发掘它的意义,所谓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皆是如此。然而,当历史以存在之维呈现时,它的“意义”成为了话语的虚构。这绝不等同于“历史虚无主义”,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人是不可能脱离“意义”而生活的,甚至活着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只是个体认知、感悟、反思后生成的一种可能性,依然无法冲破“可能的维度”。对于个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个统一标准下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神圣不可侵的“意义”在此隐没。
《软埋》中有一处很有意味的细节:陆家的仆人金点得知,自己父亲的死亡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陆家不肯相借马车而未能及时得到救助,对陆家的仇恨使他决然地背叛了陆家,并甘愿在日后的土改运动中充当急先锋的角色,而他的报复也侧面推动了陆家悲剧结局的到来。然而在此之前,陆家所有人都对金点父亲的死亡真相讳莫如深,金点又如何知晓这一切呢?在丁子桃的“十八层地狱漫游”中,答案逐渐被揭晓。事实上,正是由于丁子桃(黛云)与小茶、金点闲聊时无意中的多嘴,将金点的身世秘密和盘托出,才招致了金点的背叛乃至陆家的杀身之祸。在当代史的语境下,陆家的悲剧本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贴上“时代悲剧”、“历史悲剧”的标签。可正是丁子桃的这一句闲话,让这桩悲剧的“时代性”、“历史性”被淡化,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悲剧被解构为世俗伦常的人情悲剧。以理性的历史思维来考量,即便没有金点的背叛与报复,陆家人也理应会在“土改”中受到冲击。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陆家是地主家庭,是“土改”的直接对象。这固然没错,然而金点的个人选择给这种判断增添了些许干扰,历史对于陆家悲剧的“作用”变得可疑了,历史对于陆家悲剧的“意义”被削弱了。
回到“现在”,吴青林同样无法把握历史的“意义”,在决定放下这段历史后,他向龙忠勇提出一种假设:“我想我们可否就当它不存在过?”龙忠勇对此有些失望,不无遗憾地慨叹到:“三知堂呀三知堂,竟然是天知地知鬼知,却是你不知我也不知。”此时,吴青林的那让人略有不快的“辩解”又出现了:“你算了吧。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一切的意义都是最没有意义的。”*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第87页。由此可见,吴青林与龙忠勇最大的区别在于,吴青林无意于追寻“意义”,他只想“顺其自然地记住,顺其自然地忘却”,顺其自然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意义”能比当下平静的生活更重要;而龙忠勇渴望获得“意义”,“历史需要真相”是他的信念,是他心中预先设定的观念,也是他所作所为(调查、著书)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意义”在个体的选择中被拆分、解构了。
历史的“意义”既然被消解,个体也就不必在这种“意义”之下去限定自己的选择,又或者说,这种选择本身就可以带来“意义”,无需再去额外地追求其他的什么“意义”了。《武昌城》中罗以南这个人物,就是这种“选择”的最佳注脚。他参加革命前一度因为好友的惨死而渴望出家当和尚,结果却被同伴梁克思硬拖着加入了北伐军。他胆小而脆弱,被其他的战友们瞧不起,他对革命既没有太大的热情,也谈不上什么反感,他的怯懦仅仅是因为害怕。逐渐适应了环境后,他勇敢了起来,甚至主动承担起营救梁克思等负伤战士的任务。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或是多了一份热情。对于他来说,参加北伐是出家当和尚的替代行为,而营救梁克思是单纯地出于对同伴的担忧和挂念,不愿让同伴的期望与等待落了空。随军护士张文秀无法理解,一个没有丝毫革命热情的人为何要参加北伐,为何还能主动地承担危险任务。罗以南同样不能理解,为何没有革命理想就不能参加革命行动,为何一定要为着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来规划自己的行动,难道营救战友这件事本身不比什么革命理想、献身精神更有意义?罗以南对于“意义”的态度介乎吴青林与龙忠勇之间,他既不回避“意义”,也不预设任何“意义”,他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最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让这种选择自然地生成意义。这有点类似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当然,罗以南还缺少里厄那种直面绝望的无畏精神),只关注自己必须做什么,不对目的和后果作太多的遐想。若将罗以南作为标尺,龙忠勇和吴青林恰好站在了他的身前身后。龙忠勇对历史有着自觉的责任感,这或许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相比罗以南,他的思想、价值体系更加稳固,他很清楚自己的追求。吴青林要复杂得多,总体来看他更认同世俗的价值观,即所谓“活在当下”的态度。但他的情绪中也时刻有种焦虑在暗涌,这表现为他对历史时常有种欲拒还迎的态度。最初他阅读了父亲的日记后,也曾讶异、好奇、兴奋、慨叹过,像一个侦探似的,恨不能立即解开家族的秘史。然而,他那探索、求真的热情很快就被沉重的历史压垮,越是触及到家族史黑暗、隐秘的地带,那种退缩、回避的欲望也就越强烈。但尽管如此,每当家族的历史进一步暴露于眼前时,他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激动、兴奋,紧接着又会用种种世俗的价值判断冲淡这种热情。虽然他最终仍然选择了回避历史,但这与《出门寻死》中何汉晴“寻死”不得后的“认命”不同,他的态度中明显带有对意义缺失的恐惧,这种恐惧始终处在一种临界状态,随时可以引发他对自身选择的否定。可见,历史的“意义”消解后,仍然制约着个体的存在与选择。
三、历史语境下的个体选择
我们知道,存在主义的核心要义是“自由选择”,然而这种“自由”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中所感知的“自由”。吴青林“自由选择”了,可这种选择并没有给他的内心带来完全的平静,历史并没有真正退场。一方面,个体的选择消解了历史的神圣意义;另一方面,历史本身被赋予的价值判断也制约着作为存在的个体的自由,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结构。对于自身或是身边人的惨痛历史,人们往往会有意回避,不愿提起,这本是人之常情,一般不会受到苛责。然而这种面对历史与过往的世俗态度,一旦面对全国性、全民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这种重大事件往往还包含着某种非正义、非道德因素)时,则很容易受到道德上的非议。历史在被集体言说的过程中,会同步地被赋予价值上的判断:光明的、黑暗的,光荣的、耻辱的,正义的、非正义的,道德的、非道德的。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提到,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重要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2-13页。在这个层面上,记忆与忘却不再仅仅是世俗的选择,转而成为道德、良知的要求。对于《软埋》中涉及的“土改”历史,暂且不论其在政策上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但其推行过程中无疑包含了非道德、非理性因素。对于丁子桃来说,它承载了太多负面意义。吴青林作为丁子桃的儿子,似乎理应去了解、关注母亲的所思所想,也有“义务”与母亲一起承担痛苦。可是吴青林在经过多次的思想斗争后,仍然选择了退避。在这种情境下,吴青林就很容被贴上“软弱”、“没有担当”的标签。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方方的名作《祖父在父亲心中》。在这部小说中,父亲是一个谨小慎微却又常常耽于想象的角色。他在生活中明哲保身,希望尽力保全平静的生活,面对造反派的暴力行为,他总是选择退缩与顺从。这与祖父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时的大义凛然、不卑不亢形成了对比。祖父那喷洒着血气的刚强生命,时时刻刻都在逼迫着父亲面对自己的平凡与卑琐。在祖父的光辉形象下,父亲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最终,在观看某部电影中日军杀人的场面时,父亲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出了影院便黯然倒下死去。然而有趣的是,小说叙述者“我”对祖父的认识全部来源于他人之口或是他人的记载,至于祖父的真实形象究竟如何,“我”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这样,祖父就成了某种观念性的存在,成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与其说父亲死于历史本身的重负,不如说是死于某种历史存在之可能性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回到《软埋》中,无论是面对“痴呆”的母亲,还是热情、较真的龙忠勇,吴青林也常常会有道德负罪感。为了缓解这种负罪感,他将自己定位为“平庸者”,而“平庸者不对抗”。更何况,父亲在日记的最后曾劝说他放下这一切,好好生活,对于母亲的过往也不必再追究。这似乎为吴青林的退避提供了最好的理由:遵父母之命。然而在母亲去世后,早已放下了一切的吴青林接到龙忠勇的电话,得知他进一步查清了自己的家史,并准备将其写进书中后,仍然“心咚了一下”,“忽然觉得心口一阵刺疼”,“心下怅然”地感叹道:“我选择了忘记,你选择了记录。但你选择了记录在案,我又怎能忘得掉?”*方方:《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第106页。同样的,丁子桃一生都在遗忘、逃避自己的过往,到了晚年,历史的幽灵却仍然找上了她,强迫她注视着曾被软埋的一切。历史还是没有放过他们,这对母子如同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中的“带菌者”,一旦触及历史的黑暗,便成为这种黑暗的一部分,无处逃逃。
由此看来,历史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既包含了理性的认知,也充斥着感性的情感判断,然而它最终会以集体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中的非理性因素被自然地抹去,成为一种绝对的合理,对个体的存在与选择作出严格的限定。不妨做个假设,若是以我国“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启蒙立场来看待吴青林的选择,不但“平庸者不对抗”这一论断值得批驳,就连安于“平庸者”的这一姿态也可能受到质疑。任何一种话语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形成,在被不同的个体反复言说后,形成一种“共语”,进而成为某种共识、标准。这种标准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但个体的存在样式却在不断变化。因此,仅仅将吴青林的退避视为世俗的“逃避”是不全面的。就如同《局外人》中的莫尔索最终放下内心的挣扎,接受审判,迎接世人的非议与指责,并非是对他者的妥协,而是认清真理与意义的不可触摸与虚无后所达到的内心平静。又如西西弗斯的“快乐”是含泪的,是绝望后的生命重建。诚然,吴青林的行为无法被上升至如此的哲学、美学高度,但他的选择依然充分展示出了历史语境下个体的存在之困。相比之下,丁子桃的选择更值得玩味。她临死时留下了五字遗言:“我不要软埋。”她不愿意放弃转世的机会,不愿意让一切过往随风而逝,不愿意决然与这个充满着自己黑暗历史的世界说再见。对于曾经逃避的一切,她愿意重新接受,这是她对存在之困的突围。这种“突围”的方式既不是对抗,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释然”,而是接受历史之存在的必然后,选择的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安然姿态。也因此,丁子桃的选择比吴青林的选择多了些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小说的情感浓度也在这里达到最高点。只有一个行将就木、对余生不再有期许的人,才能最终逃脱存在的困境。个体存在的悲剧性被无限放大,它以一种悲悯的姿态,为个体选择中的世俗取向找到了最佳的“理由”。
结 语
“历史”与“存在”在方方的小说中被多次言说,但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的作品不多。况且,这种“结合”并不是简单地杂糅,而是将历史的书写与存在主义的思辨作为两股原力,使二者在博弈中形成小说的内在推动力。这使《软埋》产生了如下的阅读感受:小说几乎通篇都在写“历史”,但历史似乎并不是作品所指涉的核心;另一方面,存在主义的思想浮现在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以及相关情节设置中,却又在历史叙事的掌控下显得忽明忽暗。同时,从“新写实”时期就一直被保留下来世俗价值立场与平民视角,也冲击着前两者所构建起的意义结构,这些都增强了小说文本的内部张力。但在笔者看来,对存在的思考仍然是这部小说的内在逻辑支撑。可以说,《软埋》大体上延续了方方近些年来的写作方向:从《琴断口》到《刀锋上的蚂蚁》,再到《武昌城》,都关注着个体存在的困境,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如何完美地处理当代史的书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首先,对于当代史中一些具有争议的节点,文学表现的尺度就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问题。其次,当代史是“进行时”的,未盖棺定论之处尚有很多,即便是已盖棺定论的“官方信史”,也不是没有被修正、改写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当代史和作家们的创作靠得太近,尤其对于年龄稍大的作家来说,几乎与他们的成长共时。鉴于这两点,当代史对于作家们缺少审美的距离感,又蕴涵了太多写作主体的情感投射,因此历史很容易被抽象化、观念化、简约化为某种价值载体(且常常是负面的)。《软埋》没有沾染上这种倾向,这得益于方方观照历史的角度。她基本放弃了重构历史的努力,让历史重新回到被认知之前,以个体的存在困境指涉历史的“无处不在”,这其实扩大了历史的认知空间,同时也使得个体的存在之困拥有了悲剧的审美意蕴,这些大体就是《软埋》的成功之所在。
(责任编辑:王学振)
RuanMai(SoftBurial): The Plight of Existenc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XIA Jing, WANG Da-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29, China)
Fang Fang is a writer extremely interested in historical topics, so be it a depiction of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era of neo-realism 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istence plight of 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m in recent years, history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er works. Meanwhile,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can also be discerned in many novels by Fang Fang, for the existence plight of humans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popular with her. In her newly published novelRuanMai(SoftBuri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existentialist speculation met and collided with each other, with history being written as a kind of exist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dissolved on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lue judgment endowed by history restricts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s. In short, Fang Fang has been able to refer to “the omnipresence” of history by virtue of the existence plight of individuals while their mutual contention has enhanced the ideological tension of the novel and extended its discourse space.
Fang Fang;RuanMai(SoftBurial); the historical context; existence; memory; choices
2016-10-06
夏靖(1991-),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达敏(1953-),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7)03-00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