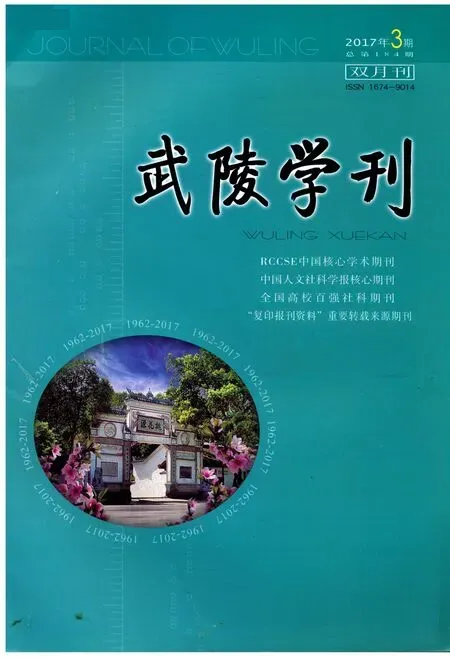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观及其启示
——以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例
王泽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观及其启示
——以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为例
王泽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运用经济学的话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及运行规则,在这种话语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深厚的经济伦理意蕴,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就是众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这些隐藏着的经济伦理观可以被简约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辩护,追求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经济正义,建构符合道德理想的商业社会秩序。重新解读和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观,对于推动当前经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开展符合道德运行逻辑的市场经济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典经济学;经济伦理;经济正义;秩序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在此之前它还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随着边际效用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经济学研究的“纯粹化”“去伦理化”倾向日益凸显,经济学道德中立、经济学道德无涉成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增长、财富增加成为考评经济行为正确与否的唯一指标,随之而来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不择手段、以物质富足为表象的精神贫乏充斥着社会生活。面对现实的困境,人们不禁追问:生活的目的与意义何在?注重纯数量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现代经济学无力解释这些问题,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1]13,而导致贫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传统理论的误读乃至背离,“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供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1]32。因此,真实再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观对当前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观
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及苏格兰启蒙运动引发英国思想的普遍解放与人性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摆脱封建专制及宗教神权的奴役与束缚,探寻自由自主的行为方式及活动空间。伴随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与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经济活动日益从政治活动与宗教活动中分离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为顺应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及市场经济形成与完善的时代呼声而产生的,其宗旨就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道德性。纵观这一时期经济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他们在运用经济学的话语揭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及运行规则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深厚的经济伦理意蕴,其中以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伦理观最为典型。综合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辩护、追求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经济正义、建构合理的商业社会秩序。
(一)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辩护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将自由竞争视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也将其视为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准则与价值规范。从内容上讲,为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辩护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揭示互利的行为逻辑。经济人追求自利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研究的逻辑起点,他们认为每个人相对其他任何人而言总是更为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自利作为人之自然本性是不言自明的,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以及自我处境的改善的行为动机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欲望与激情,正如斯密所说:“各个人都不绝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觅最有利的用途。放在他心里的,诚然不是社会的利益,只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检考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22但是,人所具有的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自然倾向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加深了人际交往的关联度和依赖性,个体只有通过获取他人的协助或加强与他人的合作才能满足自身的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因此,互利为自利行为设定了限制条件,互利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准则。其二,承认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自由自主的行为选择权利。季德认为:“假定承认每一个个人最能判断自己的利益,那就十分清楚,最聪明的办法是让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3]从这个意义上讲,约翰·穆勒做了最为充分的论证,他从权利与权力、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指出,所谓自由就是社会所能合法地施予个人的权力的限度,因此,自由的最低限度即为不伤害他人,遵循不伤害的消极自由和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积极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在他看来,每个人只有自己对自身利益了解最深,也最为关切,只要不关涉他人利益,个体合法地享有对自身的完全自主权。“无论我们把什么事情叫做一个人的权利,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合法要求社会用法律,或是教育与舆论的力量使他保有这个权利。”[4]其三,确立自由放任的依据与限度。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对重商学派限制对外贸易的批判与重农学派注重自然秩序的扬弃,指出自由竞争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推动力,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经济规律,但自由竞争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一定弊端,因此,如何确立自由竞争的范围与限度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斯密认为:“一切特惠的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的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将自然而然地自己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愿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自己的利益,而以勤勉及资本,加入对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2]240
(二)追求注重财富增长与财富分配的经济正义
经济正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衡量财富增长合理性及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理论依据。在斯密时代,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遵循经济运行规律促进经济增长及财富增加,因此富国裕民是其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基本目标。他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交换正义,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保障生命和身体安全,即不受他人伤害;二是保护财产和所有物不受他人侵犯;三是保护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此,斯密认为所谓正义就是个人拥有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存权及扩展的财产权,这是构成社会秩序之基础的底线道德,正义的法律制度即为自然权利的外在表现行为,它为个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及市场竞争提供自由而安全的环境。斯密强调经济增长与普遍富裕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应有之意。“社会最大部分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社会全体的不利。居民有大部分陷于贫乏悲惨的状态,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2]69到穆勒时期,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及海外殖民贸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财富合理分配成为经济增长与财富增加的必然要求,与此相适应,与个人主义相关的协调利益冲突及体现财富分配正义的规则随之兴起。穆勒对生产法则与分配法则进行区分,认为人们不能改变生产的经济法则,而社会分配法则是由人所创造的,能够根据人们的意愿做出调整与改变。作为功利主义者,约翰·穆勒认为分配规则和财产所有权的正当性不能诉诸于自然权利或内在价值,所有权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产权作为制度化的形式仅在能够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的范围内有价值。在穆勒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三个正义原则是经济正义理念的核心。这三个正义原则是:其一,努力原则,即生产者拥有使用劳动力的权利,并依照自己的劳动能力获取收益,如果某一产品是由多个劳动者完成的,每个人都应按照生产性劳动的数量获得一定的份额;其二,节制原则,即人们节制欲望,将自身拥有的资源用于投资而非即时消费的应获得补偿;其三,转让原则,即人们有权转让财产或进行交易。其中努力原则与节制原则比转让原则更为重要。
(三)建构理想的商业社会秩序
建立理想的商业社会秩序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社会发展目标。斯密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商业社会中人的欲望膨胀与资源有限性矛盾的深刻分析,探寻建立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斯密关于理想的商业社会秩序的探索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理想社会秩序的具体形态;二是理想商业社会秩序实现的路径。在斯密眼中,“理想社会的真正形态——一个将‘富足社会’与‘良序社会’有机统一的、人人皆可‘富而有德’的社会;而且他富有逻辑地证明,如果能够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恶’、弘扬人性中的‘善’以保证社会成员间的合作,这样的理想并非不能实现”[5]。关于理想社会如何实现,他早年基于人的自利需求与物物交换的自然倾向,认为以分工为基础的物质富足和以正义法律为保障的良序社会构成的理想社会可以自发实现。晚年,斯密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表现出了对商业社会中财富与美德背离的忧虑。他对《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机制”及“公正旁观者”做了重新审视,认为人的致命弱点“对财富的钦佩,对贫穷的藐视”破坏了人的同情共感能力,人对财富、荣誉、地位等追逐的虚荣心既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动力,也是社会秩序混乱、道德败坏的根源,通往财富之路与通往美德之路往往并不统一。当财富与金钱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人们不惜践踏社会道德底线时,影响制约人们行为的“同情共感”机制以及公正的旁观者所认同的行为仅仅是实际生活中获得他人关注及尊重的行为,而非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由此斯密深入分析了客观存在的公正的旁观者以及内心的真正公正旁观者,强调自制美德是更为可贵的道德品质,拥有自制美德的人的同情共感能力可使自己免于被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侵蚀,能审慎地进行行为选择,适宜地调整自身行为,市民美德的培养与提升是建立理想的商业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而约翰·穆勒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探寻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停滞状态的思索中,可以说,约翰·穆勒之前的经济学家,对社会静止状态的到来都深感忧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卫·李嘉图,他严正声明担心静止状态的到来。在李嘉图看来,当利润率跌至较低点时,资本主义企业将会缺乏长远性的激励,会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还假定这种状态与马尔萨斯的饱和状态一样,农业部门回报的消减导致增加的劳动力食不果腹。而穆勒则不同,他以乐观的态度明确地提出静止状态优于停滞状态。通过充分的规划与展望,他认为人们能够进入财富与收入更为平等的世界。尽管他没有对停滞状态进行明确的阐述,但是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停滞状态就是人们不再以财富追求作为唯一的生活目标,即子孙后代结束以获取更多的财富作为驱动竞争的手段,实现创造财富与财富分配公平的均衡发展。
二、学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伦理观的讨论
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发展中商业丑闻、企业腐败、权力寻租等负面效应的社会影响,学术界愈来愈重视从市场经济发展的源头——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有价值的资源。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国内外学者多角度、多层面深入考察了古典经济学家“经济人”思想的本质内涵以及古典经济学家政治经济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立和谐稳定的商业社会秩序具有借鉴意义。在此有必要交待的是,政治经济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的关联也属经济伦理观研究的范畴,因为我们在研究经济伦理时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把经济伦理当做一个整体性的对象,探讨其内部那些独立的经济伦理价值范畴,如经济正义、经济自由、经济平等等;一是把经济和伦理道德当作分属两个独立领域的东西,探讨经济价值范畴与伦理价值范畴的关系。本文即是在这样两种思路的意义上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观的。
(一)对“经济人”方法论或思想体系的批判以及“经济人”本质内涵的再阐释
“经济人”假设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在西方学术界已达成广泛共识。当代西方学者对“经济人”的相关研究热度不减,具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或思想体系进行批判、审视,主要代表人物有科恩(William S.Kern,2001),帕加内利(Maria Pia Paganelli,2008),丽莎·希尔(Lisa Hill,2012),杨春学(1998),叶航、陈叶烽等(2013)。科恩指出,随着《国富论》的出版,经济学家愈来愈认为自利追求是人类主要的心理驱动,自利追求主导着经济学家的思维。然而,经济学对人性自利的分析是不全面的,他们忽视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中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以及对个人自利、社会经济进步以及政策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阐明的是,诸多古典经济学家假定追求地位是自利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自关于人具有追逐地位的欲望的观点奠定了对经济进步、穷人的发展受限的分析的基础。”[6]科恩指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不同的经济学家对社会地位与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劳苦大众问题的分析持各不相同的观点,斯密认为提升地位的欲望是人性中固有的一部分,对所有的社会阶层而言都是真实存在的。约翰·穆勒则认为关注社会地位是重要的驱动力,但仅局限于中上等阶层,劳动阶层可能对“他们的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遗失感到忧虑,然而由于贫穷与教育的缺乏,他们改善自身境遇的欲望却相当少见。因此斯密主张自由竞争是经济进步、解决“穷人问题”的强有力引擎,约翰·穆勒则认为唯有强有力的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担负起“贫困陷阱”产生的可能性后果。帕加内利认为人们对斯密的自利思想存在误读,自利及自爱是斯密思想的基本出发点,自利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社会的经济繁荣,运行良好的自利行为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用,但是斯密从个人与社会、物质与道德关系的层面指出,过度自利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将自利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7]。希尔质疑传统意义上人们对斯密经济体系中自利的解读,他指出人们通常认为与金钱至上、欲望、功利最大化以及人性的贪婪相联系的理性利己主义是斯密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力。然而,在他看来,斯密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感驱动。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情感趋动成为秩序、生存与人类繁荣的推动力。斯密将灵魂中的喜爱平静、感官满意视为情感的附属,为了实现社会认同、获得赞许,行为主体总是会推延当前的满足[8]。叶航等则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或理性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批判,他们通过神经科学的前沿知识及模拟实验,指出人不仅有自利的偏好,还有亲社会的偏好,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定,即人有充足的能力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是站不住脚的,他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否定了人具有无限自私的行为偏好及能力假定,而真正促进人类合作是基于人的同理心所形成的互惠法则[9]。以上学者都赞同经济人具有自利本性的观点:自利在经济进步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的是对自利的理解以及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权重的认识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希尔认识到情感因素对经济人的行为规范具有约制功能,叶航等通过科学实验进一步验证了现实中人的利他性偏好的客观存在。
第二,部分学者深入考察了“经济人”的缘起、本质及内涵,典型代表人物有柯兹纳(1960)、麦伦·梅尔斯(Milon Myers,1983)、约瑟夫·帕斯基(Joseph Persky,1995)、杨春学(1998)。柯兹纳梳理了古典经济学派关注财富生产分配理论转向罗宾斯的选择理论的历史,他认为在当代的多数用法里,“经济人”的本质并不依赖于他的“所指”,而是做出选择的理性化方法。在具有深刻洞见的《经济人的灵魂》一书中,麦伦·梅尔斯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总结了经济人自利行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尽管近代初期西欧学者对经济人自利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对于公共福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0]。帕斯基在《经济人行为学的回顾》中指出约翰·穆勒通常被认定为“经济人”的创始人,虽然他从未在其作品中使用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出现在历史学派对穆勒思想带有贬损意味的批判之中;历史学派代表人物莱利斯(Leslie,1879)、戈申(Goschen,1893)认为穆勒思想中“经济人”作为一种明目张胆的自私自利的假说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而对自利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考虑相对于“经济人”假说的提出以及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立而言具有优先性。在帕斯基看来,穆勒的“经济人”有四个明显的偏好:积累、闲暇、享受和生产[11]。尽管“理性人”的抽象概念对于经济学而言是极为有用的,但不能将穆勒的“经济人”视为完全理性的,因为穆勒坚持将“经济人”的选择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那些永久性地与财富欲望相一致的动机才被视为是合理的,由此可见,穆勒主张有限理性“经济人”。杨春学认为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基础,除理论目的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建构社会秩序原则的基础,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个人既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自由行动,同时个人利益又无意中推动社会利益的实现。然而,经济人思想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对其含义的理解都过于偏狭,仅将其视为简单的概念或假设都不足以揭示其全部的内在含义。杨春学在斯密的基础上,把经济人视为一种内容丰富的假说,他认为经济人假说包含自利动机、理性行为及正义法律框架下的利益最大化三个基本命题,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重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重视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对经济人的制约[12]。由此可见,“经济人”假设中不言而喻地包含着人的自利本性、理性行为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解读自利的本质、理性的范围及限度,而如何实现适度自利、伦理道德以及情感如何在经济系统中发挥作用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对古典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复兴的理解
努德·哈孔森(Knud Haakonssen,1981,2006)、查尔斯·格里斯沃尔德(CharlesGriswold,1999)、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2004)、汉利(R.Hanley,2006)、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2008)等,他们反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斯密看成是一位反道德意识的经济学家的做法,认为斯密主要是道德哲学家、美德伦理学家。哈孔森指出斯密的两本著作都表明自利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斯密问题已成为“旧的宿愿”[13]。在他看来,斯密是以广泛的社会概念来理解人的行为方式的,人的亲社会情感可以运用于商业经营之中。格里斯沃尔德则认为审慎美德与适当的理解力、惩罚、安全等个人自利要求相关,斯密可能是最后一位将审慎视为适宜美德的哲学家。人们追求财富的动机根植于人们更易于与愉悦的感受产生同情共鸣,因此追求财富与感受愉悦相联系,人们乐意拥有财富并炫耀它以获取他人的赞扬与认同。格里斯沃尔德与斯密一样对人们因钦佩富贵带来道德堕落持批判态度,他不仅阐明追求财富是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还进一步指出通过追求财富获得他人的认同相当于错误地将财富视为幸福。在格里斯沃尔德看来,斯密把追求财富视为欺骗性的目标,甚至会使人们偏离实际上应当追求的安宁与幸福的目标[14]。与格里斯沃尔德不同,弗莱施哈克尔则认为斯密最为关注的是贫穷问题,对财富持批判态度,他区分了为满足人的虚荣心而追求财富与为改善自身境遇而追求财富之间的区别。他还指出依斯密之见,关注人们的需要不仅是道德上允许的,而且是道德上要求的。有道德的人基于合理的理由追求财富,因此,“完全由体面、谦逊的人组成的世界仍然能实现经济的繁荣”[15]。汉利认为斯密阐释广泛的社会框架如何指导道德行为,并清晰地阐明合宜的情感应指导社会成员的各项活动;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自利是主要的驱动力,但自利与人的美德不可分离,美德理想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限制着人的自利,有德之人“不仅有获得认同的欲望,而且有值得被认同的欲望”[16]。麦克洛斯基则明确指出斯密主要是美德伦理学家,斯密认为道德之人需要具备爱、勇气、自制、正义、审慎五种美德,爱作为家庭之德,勇气是企业家之精神,而任何社会都依赖于自制、审慎及正义等人为之美德,而斯密的审慎美德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审慎作为商业社会的主要美德,正如正义对于亚里士多德、仁慈对于基督教道德。在他们看来,斯密的伦理道德思想长期以来被忽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受法国大革命中反动派及冷战时期美国反激进主义经济的影响,斯密的道德思想被剔除或者被进行反伦理学的解读;其二,长期以来将斯密的美德伦理学视为过时的道德哲学,主要关注康德(1785)、边沁(1789)、辛格(1993)、法兰克福(2004)等思想家的伦理思想;其三,以斯特劳斯(Strauss,1953)、芬尼斯(Finnis,1980)、洪特(cf.Hont)、伊格纳季耶夫(Ignatieff,1983)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及天主教知识分子认为斯密受洛克、普芬道夫的自然权利思想传统的影响,将斯密视为自然法学家;其四,以布坎南(Buchanan)、图洛克(Tullock,1962)、罗尔斯(Rawls,1971)、努斯鲍姆(Nussbaum,2006)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斯密思想中范围狭小的道德思想与广泛的政治理论是共同存在的;其五,从18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期,美德伦理思想遭到冷遇,直至安斯科姆(Anscombe,1958、1997);福特(Foot 1978)、麦金泰尔(MacIntyre,1981)、斯特豪斯(Hursthouse,1999)重新复兴美德伦理思想[17]。
部分学者基于现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理论误读产生的严重后果,主张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引入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典型代表人物有:阿玛蒂亚·森(1986、2009)、沃尔什(Walsh,2000)、库珀(Richard Cooper,2000)、普特南(Putnam,2002)、马丁斯(Nuno OrnelasMartins,2012)。阿玛蒂亚·森认为政治理论不应当仅仅存在于完美正义的理想状态,他批评主流经济学的理想化和虚构的经济人的观点,指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是因为对斯密经济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化的狭隘理解、对斯密经济情操与伦理道德的忽视所致。在经济学中,斯密不仅关心交换时是否充分满足自我利益,而且关注有助于经济活动的道德动机和制度保障;在伦理学中,斯密提出的公正旁观者有助于充分理解正义要求。哈佛大学教授库珀也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认真地考虑了道德问题,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恢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的广泛兴趣。马丁斯详细地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复兴经历的阶段、斯拉法与森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认识上的差别;马丁斯还检验了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复苏思想,赞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认为这种复兴有助于解决当前经济学研究单纯注重数理模型及量化分析带来的对人的多样化行为的解释无力及理论苍白。与森相比,斯拉法的复兴思想要更早一些,斯拉法更有可能为经济学带来一种更为多元的、理想化的视角[18]。依据沃尔什和普特南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的复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由斯拉法批判边际主义的分析框架,到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价格与数量相关的最小的分析框架所引起的;第二个阶段是阿玛蒂亚·森引发的,他提出复兴以人类行为与幸福生活的紧密结合为典型特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可以看出,学界对斯密道德哲学思想的重新审视及古典经济学的复兴思潮很大程度上都是对现实中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带来的困境的积极回应,反映出学界对追求财富的行为方式与人类幸福生活目标之间关系的反思与关注。
(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政治经济思想与伦理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及本质内涵的研探
其代表人物有杰瑞·埃文斯凯(Jerry Evensky,2005)、卢迪·费尔堡(RudiVerburg,2006)、斯蒂芬·纳坦森(Stephen Nathanson,2012)、袁立国(2015)、吴瑾菁(2015)等。埃文斯凯强调了斯密思想中的自由市场制度、正义法律及市民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个体自爱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仅具工具性价值。而在当代经济学中,自爱的工具价值却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基本假定。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揭示了自由社会包含着人民自由与市场自由两个层面的内容,而要建立自由社会必须保障所有参与者的安全,这种安全来源于正义的社会制度。斯密在《国富论》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斯密对自由市场制度、正义法律以及市民道德的分析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在《国富论》中,他分析了由正义法律以及市民道德所确定和强化的正义制度,指出成熟的正义制度的出现依赖于人类的物质进步,而物质进步有助于劳动力的精细化分工。在《法学讲稿》中,他提出正义的法律制度有助于自由市场社会的出现,制度成熟促进社会发展,法律对于个体行为具有外在强制性。当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如若警察的强制性力量成为社会安全的最终保障,那么这种追求发展的自由反而受到确保自由的反动政府的打压,最终,自由秩序的粘结性和建构性并不是依赖于制度性政府而是自治性政府以及市民道德的日益完备[19]。埃文斯凯还阐述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对于道德的分析,即人之本性与培育市民普遍道德的交互作用、个体以及社会的动态交互作用,这种交互性作用有助于公民道德的日渐完善并为自由主义制度创造条件。他还从人性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紧密相连的基础是人的同情共感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埃文斯凯对斯密的不同著作进行了关联性的解读。在他看来,斯密的思想显现出政治、经济、道德不同层面的有机统一,人的道德情感能力的培养与完善既是社会交往的基石,也是社会发展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无疑开辟了一条全面理解斯密思想的新路径。
部分学者也对穆勒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与审视。费尔堡指出穆勒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他认为如果社会与道德进步问题是穆勒思想体系的关键,那么他的经济学应当在一个宏大的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框架中来理解;穆勒经济学对于实现社会道德进步的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因此,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在道德进步中处于从属性地位[20]。纳坦森与费尔堡的立场相同,他认为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经济正义思想很少引起哲学家的关注,但他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了深入分析与阐述,认为这部著作事实上包含了经济制度、贫困、正义及政府角色等相关问题在社会哲学上的相关运用[21]。其一,穆勒将功利主义视为评价行为或政策正确与否的主要道德标准,而大多数人认为功利主义忽略了正义问题。事实上,在经济正义问题上的哲学研究的复兴是由对功利主义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思想家提出的。他们持有与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的观点,如罗尔斯、诺奇克,他们建立了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论思想体系,并将功利主义视为理解正义理论的主要障碍。其二,学界普遍认为穆勒在《论自由》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他充分论证了社会所能合法施予个人的权力的限度与范围,并在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定界限,这就意味着只要经济活动没有通过强力或欺诈直接伤害到他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就应奉行不干涉政策。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则指出:“国家不可用它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些公民帮助另一些公民;也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或自我保护的活动。”[22]这更像是对穆勒观点的回应。穆勒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在乔纳森·赖利(Jonathan Riley)、弗瑞德·贝格尔(Fred Berger)以及其他学者的作品中都有提及,这些作品肯定了穆勒关于经济正义以及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近期,中国学者袁立国与吴瑾菁从整体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及理论演变进行了梳理,袁立国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意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苏格兰启蒙学派以政治经济学与道德哲学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了市民社会的政治秩序,因此,苏格兰所构建的市民社会具有政治与伦理的特征,但它却止步于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性论证,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解放开辟道路的。吴瑾菁则对古典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专题分析,对学界存在争议的古典经济学派与经济伦理的界定进行了研究,指出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不应将新古典经济学排除在外,并将其研究范围拓展至马歇尔的经济伦理思想。她阐述了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并从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财富道德观、经济公正论以及社会发展价值观等方面梳理了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总结了古典经济学派经济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其现代价值。
(四)多视角、多路径、多方法重新审视古典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思想
其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娜(ChristinaMcRorie,2015)、吴红列(2014)。克里斯蒂娜认为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道德心理学为前提,从宗教伦理的角度考察斯密思想既增强了斯密思想的价值,又加深了宗教伦理学领域与经济主题之间的对话[23]。他认为,在《国富论》中不仅存在道德心理学的内容,而且摆脱了将自利作为美德的解读。市场交换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方式不是源自人类自利的自然本性,而是人的同情能力使市场交换成为可能,交易得以实现是基于同情、理解他人的利益,追求财富也建立在与同情能力相伴随的赞许欲望的基础之上。市场秩序的形成是神的力量或者建立在某种哈耶克主义的自发秩序的基础之上,市场通常使自利转向公共善。因此,在克里斯蒂娜看来,斯密不仅在宗教伦理学领域是一个天然的对话者,更可以将其视为在道德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进行对话的范例。吴红列则从自然法理学的角度研究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背后蕴含着道德哲学和法理学的研究路径,苏格兰自然法传统就是在自然法与道德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斯密将他对自然法的反思和对文明社会的思考引入其政治经济学中。
综上所述,学界普遍重视挖掘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道德资源并力求使这种经济伦理观转化为解决商业社会中经济发展与道德腐蚀之间矛盾的重要理论参考。尽管目前的研究还带有零散性,人们对经济伦理的研究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人们对人类行为动机的复杂性的解读以及道德对商业社会秩序的形成与运行的重要性的理解已达成基本共识。综合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及稳定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经济伦理观的当代启示
通过回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学界对这种经济伦理观的讨论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制度正义是建立稳定、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调节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体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当前的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形态变迁的转型期,也是利益矛盾急剧分化、利益格局调整重构的关键时期,制度调节作为规范性的公共调节机制在社会调解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是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的集中反应。一般而言,保障人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功能,而对人之基本权利的保护是正义的应有之义,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4]。可以看出,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中应当占据绝对优先地位,这就要求政府机构在理性把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以及社会整体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将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正义制度的公共调节主要指对经济主体权责的确认、保障以及对利益关系的合理公正的安排。首先,建立正义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创造实现起点公平的基本条件、保证参与主体机会的公开平等,同时确保行为主体尽职尽责履行基本义务、执行契约。具体来讲,包括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及福利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产权制度是由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法定表现形式,我国现阶段要实现的产权正义就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认获取财产的正当性以及确保正当获得的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帮扶,调整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障理念,将“输血型”的、直接的、短期的帮扶转变为“造血型”的自助型帮扶,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生存及自我发展能力;建立范围广泛的、执行力强的信用体系以提高社会整体信用度、降低社会交往成本。其次,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是制度正义的应有之义。制度安排的实质就是对不同行为主体权力、地位、义务进行分配。社会制度作为政治上层建筑,是由所处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建立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就在于追求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均衡,最终实现共同的物质富裕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合理的再分配符合社会主义的福利水平整体提升的正义原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二,公民道德的不断提升与完善是实现市场经济健康活力、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5]。由此可见,人们的道德观念根植于特定的物质文化环境之中,这也意味着经济基础、社会交往实践对人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具有塑造功能。一方面,个人道德水平的提升有赖于社会物质水平的改善与提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物质水平的提升,人的需求呈现出从低级的生理、安全层面的满足向高级层面的尊重、自我实现满足的演变;另一方面,道德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人们对财富的过度追逐带来的不是道德的自然进步,而是道德情感的退化与堕落。因此,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要受法律制度的外在强制以及个人理性的双重约束。法律制度明确了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对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做了明确规定;个人理性则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对市场及个人处境做出客观分析与判断。在传统意义上,理性作为一种美德,是人们对利己本性的克制与约束,但是如果法律制度不健全、理性泛化与滥用以及理性能力不足,会使自利行为犹如脱缰野马,失去应有的控制与约束。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形成的谨慎品质就是行为主体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深谋远虑,对市场的实际状况以及个人的现实处境、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客观合理的审视与思考;自制品质作为一种克制激情与欲望的美德表现出相对稳定性、一致性以及均等性,这种自制的道德品质也是确保人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有一种根植于内心的、自我认同的行为合宜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并将自我的欲望控制在他人及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适时调整自我的行为。因此,公民在经济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谨慎、自制的道德品质,经济交往活动的复杂多样、重复交易与利益博弈有助于克服制度的缺陷,实现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公民道德的不断提升与完善还有赖于社会的交往实践活动以及公共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从实践层面来讲,多次交易、重复博弈的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合作秩序;从理论层面来说,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审慎、自制道德品质有助于克服他律机制的固有缺陷,形成稳定的行为合宜的自我调节机制。
[1]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亚当·斯密.国富论[M].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下[M].徐卓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13.
[4]约翰·穆勒.功用主义[M].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57.
[5]吴大新.市场边界、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秩序——对亚当·斯密经济自由思想的再解读[J].经济学动态,2013(12):132-140.
[6]KernWilliam S..Classicaleconomicman:was he interested in keeping upwith the Joneses?[J].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1,23(3):353-368.
[7]Paganelli,Maria Pia.The Adam Smith Problem in Reverse:Self-Interest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40(2):365-382.
[8]Hill Lisa.Adam Smithon thumosand irrationaleconomic'man'[J].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012,19(1):1-22.
[9]叶航,陈叶烽.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33-129.
[10]Myers Milton.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M].Chicago: ChicagoUniversity Press,1983:27.
[11]PerskyJoseph.TheEthologyofHomoEconomic[J].Journal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5,9(2):221-231.
[12]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8:7-13.
[13]HaakonssenKnud.TheScienceofaLegislator:TheNatural Jurisprudence of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97.
[14]Griswold Charles.Adam Smith and the Virtues of Enlightenment[M].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9:204-295.
[15]FleischackerSamuel.On Adam Smith'sWealth ofNations[M].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104-119.
[16]Hanley R.Adam Smith and the character of virtu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94.
[17]McCloskeyDeirdre.Adam Smith,the LastoftheFormerVirtue Ethicists [J].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40(1):43-71.
[18]Nuno OrnelasMartins.Sen.Sraffaand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political economy[J].JournalofEconomicMethodology,2012,19(2):143-157.
[19]Evensky Jerry.Adam Smith's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On Morals and Why They Matter to a Liberal Society of Free People and Free Markets[J].Journalof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3):109–130.
[20]RudiVerburg.John StuartMill'sPoliticalEconomy:EducationalMeans toMoralProgress[J].Review ofSocialEconomy,2006,64(2):225-246.
[21]NathansonStephen.JohnStuarton Economic Justiceand theAlleviation ofPoverty[J].Journalof Social Philosophy,2012,43(2):161-176.
[22]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前言.
[23]McRorie Christina.Adam Smith,EthicistACase for Reading Political Economy as Moral Anthropology [J].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2015,43(4):674-696.
[2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4.
(责任编辑:张群喜)
The Econom ic M oral Values and Enlightenment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 ists
WANG Zezhi
(Collegeof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Economics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were hidden in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sts'words which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operational laws,Adam Smith and J.S.Mill being the most typical.The thesis simplifies into three aspects:market operationalmechanism in free competition;economic justice of emphasizing wealth's growth and distribution;ideal social order.To seek themoral basis from the reasonable commercial social order is the important topic of business ethics.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al basi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moral philosophy h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market economic activity conformingwithmoraloperational logic.
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economic ethics;economic justice;socialorder
B82-053
A
1674-9014(2017)03-0006-09
《武陵学刊》2016年被转载文章数量位居省内综合性大学学报第一
2017-03-12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形成机制与演变规律研究”(13q120);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重点学科开放式基金委托项目“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演化”(201601)。
王泽芝,女,湖北襄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文理学院经济与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学。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统计,2016年《武陵学刊》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光明日报》(理论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文科学报概览)等权威二次文献及重要报刊转载文章29篇,转载量与转载率均创历史新高,在2 191种被检索的期刊中排第286位,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排第24位,在湖南省综合性大学学报排序中继续位居第一。近年来,《武陵学刊》连续获得“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湖南省高校文科学报优秀学报一等奖”等荣誉。《武陵学刊》组织策划特色栏目和专题文章,用特色栏目彰显刊物特色,用专题文章聚集优质稿源。着力打造的特色栏目“中华德文化研究”形成了“依托地方文化、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服务时代和现实”的栏目定位,所刊发文章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社会影响,2016年该栏目被转载文章7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和《光明日报》(理论版)转载各1篇。